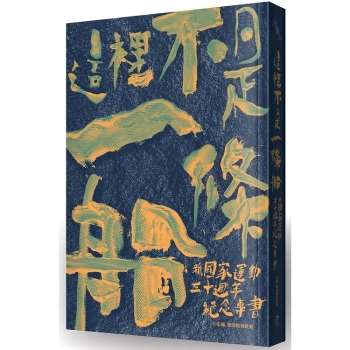狂飆年代的絕對主義者,用生命證明價值
◎口述:林濁水
◎採訪整理:亦竹
在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濁水眼中,一九八九年前後的台灣社會正處在一個壓抑後的狂飆年代。
解除戒嚴後,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戒嚴時期被壓抑住的所有議題,在那個時候一起奔放出來,包括政治訴求、社會訴求……各式主張都在那時候被提出來,因為壓抑太久,以致於一發動就慷慨激昂。在整個大狂飆風潮中,鄭南榕從推動新國家運動一路到捍衛言論自由的自焚,那種堅持理想的純粹與悲劇性,最是撼動了林濁水,使他震驚於人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以生命換取外界對基本人權:言論自由的正視?
▲狂飆的八〇年代
鄭南榕新國家運動發生的時刻,正好卡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和一九九一年廢除刑法第一百條中間。這個時間點代表著:雖然解除戒嚴社會運動開始奔放,然而依據刑法第一百條以及國安法,「台灣獨立」是屬於分裂國土的叛亂主張,是一個叛亂行為。
如果再晚幾年,結果可能會不一樣:刑法第一百條廢除後,台獨不再是叛亂罪,解除戒嚴後,台獨運動當然也可以跟著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檯面化,不需要鄭南榕以生命去換取推動的自由。在此之前,那些因未除的「罪」而累積的壓力,實引爆了鄭南榕的自焚。
那時,因為台獨還是叛亂主張,被列黑名單流亡海外是不能回來的,於是陸陸續續有很多人,像是許信良、陳婉真,闖關回來就被抓去關。當中最傳奇的莫過於一九八九年郭倍宏偷渡回台灣,神祕出現在政見發表會開中外記者會,之後在台下民眾戴「黑名單」面罩下,成功地再神祕脫逃,那是十分戲劇性的一幕。
所以那樣的激昂、亢奮,累積到引爆出自焚事件,我認為是一個關鍵。如果早一點,群眾不會那麼激昂,沒有相激相盪的氣氛,而晚一點,張力就消失了,所以在那個解除戒嚴但台獨仍是叛亂主張、叛亂行為的時候發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兩個追求價值
現在回頭看鄭南榕,他以犧牲生命同時完成了兩個核心價值:
第一:自由主義,人的自由主體不可侵犯。
第二:共同體追求獨立建國的理念,這是台獨價值,是台灣人作為一個共同體所追求的價值。
由於人的主體性不可被侵犯,卻因為他主張台獨就要去抓他,那麼他堅持的兩個核心價值就同時被侵犯了。
我主張台獨,你認為我是叛亂,我要對抗,對抗的台灣人並不少,但是鄭南榕採取的途徑最慘烈。他為什麼會走到這麼慘烈的地步?在我看來,是因為鄭南榕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悲劇性,他強調「我容不得人生的一絲不清白」,聽到這句話當時我很震撼,心想「我容不得人生的一絲不清白」,這怎麼可能?不錯,這句話有不少人講,他就是這樣自許,但是我這句能當真嗎?誰一旦當真,誰就注定走向悲劇。
既然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我的言論自由,包含主張台獨、包括解除戒嚴,還有包括各種各樣的主張,怎麼能夠被禁錮呢?那就是他容不得的不清不白之一。
再加上:人是自由的主體,怎麼可以被逮捕、受到拘束?台獨既然是一個他認為台灣共同應當追求的目標,他認為有其神聖性,那為什麼被禁止?這幾樣的不清不白,總和在一起,就令他不能忍受。
因此他面臨死亡的時候,真的就像蘇格拉底面對雅典人對他判決時一樣,認為:你們的判決是不對的,這個法律秩序我雖然必須要遵守,但我寧願犧牲生命也不屈服。能夠做到這樣的人,擁有非常強烈的悲劇性格,一般人不會尋求這一條道路。就這個角度來講,我說鄭南榕才是一個真正的絕對主義。
因為絕對主義有一個天生的困難,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更是有限的,人可以運用的資源還是有限的,人所處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那麼作為一個有限存在的人,又去把信持的價值絕對化,說一定要實踐到,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在台灣當時那樣的特殊處境更是如此,在那樣的環境中,他種種主張都不可能徹底實踐到讓他的人生沒有任何一絲的不清白。
一旦他要把「不容人生的一絲不清白」的信念貫徹到底,只有犧牲生命。
於是他就遇到非常困難的哲學和道德的難題,他怎麼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難題,基督教的回答直截了當:生命是上帝賦予的,人沒有權利自我取消,但是他並不相信上帝,於是他面臨的處境比教徒更自由也更艱難。因為,教徒一旦為宗教犧牲生命,不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他們最後有他們的神作為歸屬。
但鄭南榕面臨的是,結束生命就沒有了。即使是這樣,他還做了這個選擇,真是慘烈到極點。做到這樣的程度,他已經走入不是我能夠了解的世界了。
雖然表面上看來,他沒有神作為歸屬,但是他產生一個非常強大的牽引力量,把這個已經沒有神在巡行的世界拉住,使除魅的俗世在價值獲得確認後不致進一步沉淪。換句話說,在俗世裡,人要堅持價值、要在這個價值的引導下能夠堅持,很不容易。而他證明了這一點,且還不是用宗教的形式,這更是難上加難。
我沒有問過鄭南榕,人跟台獨之間是什麼關係。如果以宗教來說,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並沒有創造國家,國家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不是主體,是客體。那麼一個人作為主體,竟然可以為了追求客體的實踐,去犧牲生命,這對我來講實在太震撼了。
▲新國家運動的漣漪
鄭南榕的死雖然壯烈,但對廣大的社會而言,造成的衝擊恐怕沒有那麼快發生。台獨的支持度,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台獨黨綱通過的那一年一九九一年,大概只有五個百分點左右,至於他犧牲時的一九八九年,照道理說會更少。支持的人都這麼少,所以他的犧牲要擴大成多麼廣泛的社會漣漪有其限制。但是由於鄭南榕的犧牲,對人畢竟是太強烈的衝擊了,於是會開始思考:既然鄭南榕願意為了台獨犧牲自己的生命,那我是不是應該做一點什麼?
所以他的激勵是發揮在累積台獨運動者的這個層面,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是很少數。只是,社會的進步變遷,永遠是從核心的極少數人開始。
鄭南榕在一九八九年自焚之後,台獨支持度並沒有急速攀升,可見影響的速度不是那麼快,但確實對核心的幹部帶來影響。之後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台灣進一步自由化的時候,擴散的速度就非常迅速。所以台獨運動在鄭南榕自焚的前後階段,台獨運動階段性的核心目標應當是台獨原始觀念的提出。這個階段要做到提出的價值要能被人信賴,有人跟隨—-雖然只是少數,可以被信賴嗎?鄭南榕用他的生命做出交代: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用我的生命,來證明它是可以相信的。
接下來我要談談民進黨建黨後在台獨運動上的努力。一九八七年民進黨通過<台灣主權獨立的決議文>,決議文使台獨運動走上了一個新階段。走到一個新的軌道上,那是以前老台獨採取台灣地位未定論立場。在這立場上,老台獨派認為,透過制憲正名公投,表達台灣人民的意志,就可以成為獨立國家而加入聯合國。但是他們的這個想法,姚嘉文和我都很保留。我們認為兩岸分立各有中央政府已經是一個長久的、持續的事實,所以台灣的獨立主權已經不必要由公投去創造;何況在一、二十年之內,都不可能因為公投而能進入聯合國。除非開會的時候把中共的代表綁起來,不讓他們行使否決權,不然如何可能進入?那麼台灣豈不是就一直不是獨立國家?
這是台獨運動上一個革命性的改變。只是這革命帶來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現在台灣主權既然已經獨立,那獨立運動要做什麼?
我的看法是,美國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有韓戰的背景,在那様的背景下,美國主導了台灣法律地位未定,來定位台灣,無可厚非。但是,二次大戰結束後到一九九〇年前夕,兩岸分立已差不多四十多年了,各自擁有中央政府,互不隸屬,所以獨立已經是一個事實。且在經過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後,台灣人民實踐了自我統治,所以在決議文通過時,就認定台獨運動、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這三個主張要一起推動,一旦民主化,台灣人自己統治自己,台灣就是獨立了。
至於外部國際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的問題,在我看來不是法理的問題,而是政治現實的問題。需要努力的是「政治工作」,而不是完備什麼法律要件。
▲價值的實踐者,造就如今的獨立波濤
在這樣的認識下,當時台獨工作大概有幾個必須要非常努力的面向:第一,主權已經獨立,整個法律政治秩序不符合獨立現實。第二,主權獨立,有一些政策和法律秩序不符合獨立現實。第三,國家認同要改變,國民文化教材、歷史文化教材不改變、不本土化,不符合獨立現實。
在鄭南榕過世後兩年,一九九一年民進黨台獨黨綱通過,就是站在一個革命性的主權獨立的立場上,為台獨運動者規劃接下來該做的事。把上面提到三個要努力的面向歸納整理下來,就變成台獨黨綱的主要內容。
從這樣一個台獨黨綱出發,回顧鄭南榕,就可以見到在台獨運動裡面,他扮演了好幾個重要角色:第一,他推動制憲,這對後來制定台獨黨綱時是有影響的。第二,他推動運動要改變台灣國民認同。在台獨黨綱通過的前夕,對於台灣獨立最重要的認同與轉換,鄭南榕承擔了最核心的工作,而他為了證明這個價值,以自己的生命作代價。
至於台獨真正具體的實踐,是在憲政方面。一九九一、九二年,國會改選、廢省,接下來有直選總統,以及本土文化進入國民教育,都是在他過世以後逐一發生,最可嘆的是,他竟然都來不及看到。在梳理過往脈絡時持續生長變化──「台灣文化」的重新熔鑄
◎臥斧
一九六九年,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
這本書收錄台灣作家黃春明發表在報章雜誌的六篇故事,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七年都經不同出版社做過改版;二〇〇〇年皇冠出版社改版發行《黃春明典藏作品集》,第二集也叫《兒子的大玩偶》,不過只保留了當作書名的〈兒子的大玩偶〉,其餘五篇改放到其他合集,另加入了包括〈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等八篇短篇。將〈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收進同一本選集的考量之一,在於一九八三年這三個故事被拍成三段短片,組成一部電影,片名就叫《兒子的大玩偶》。
合集電影中的〈蘋果的滋味〉,當年曾引發有名的「削蘋果事件」。
▲不能說的「蘋果的滋味」
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描述江阿發上班途中,被美國駐台軍官座車撞斷雙腿住院,不料因此獲得鉅額賠償、啞女有了到美國留學的機會,全家人還初次嚐到蘋果如天堂般甜美的滋味。如實描繪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底層生活景況的劇情,卻被「中國影評人協會」以黑函密告,指出片中出現的貧苦生活、違章建築等有礙台灣國際形象,導致隸屬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打算在未經萬仁同意下修剪內容。此事經《聯合報》記者楊士琪在報上揭發,輿論嘩然。
從一九六九年的小說集到一九八三年的電影遭遇,可以看出台灣文化界的幾個現象。
一九四九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原來只是接收代管台灣、卻以主權擁有者自居的中國國民黨頒布了《台灣省戒嚴令》,相關法令包括對各式出版品的禁制,以日語或台語發表的各種作品,無論書籍、報刊、影視或音樂,都受到高壓控管。此舉使得原來的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無法發聲,「本土文化」與真正在台灣生活的民眾漸行漸遠。黃春明的創作展現庶民關懷,並未碰觸尖銳敏感的政治議題,雖在六〇年代末期得以發表,卻在十多年後因為改編成表現方式更直接明白、接觸群眾可能更多的電影時,仍然遇上政黨惡意的介入。
迫於輿論壓力,中央電影公司放棄刪剪〈蘋果的滋味〉,但文化與大眾長期悖離造成的歪斜,已然形成。
▲語言與文學是最完美的洗腦工具
日語及台語使用者被奪去發語權之後,中國國民黨宣揚大中華主義、自身權力正統的相關產品成為文化界的主流,其中不但假造神話推崇國民黨人物,甚至刻意低貶醜化台籍、日籍人士,以及原住民。這類文化產品充斥出版及影音市場,並且強力滲入教育體系,描寫台灣鄉村及底層生活的作品被壓到末流,也缺乏反應社會整體現況的力道。一九七七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看起來是「現代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對抗,事實上是「官方」與「反官方」文化的對抗,但就算是反對當時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反官方」論者當中,仍存在「中國國族主義」色彩,顯示本土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在威權體制及強力洗腦下,對於「台灣主體」產生不同見解,或者不願太過強調。
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如此,一般的閱聽大眾受到的影響就更明顯。▲言論自由與叛亂罪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生活普遍富裕之後,消費性的文化產品需求更高,但文化市場流通的主流產品包裹的意識型態,多為黨國教育當中的一言堂產物,黨外言論,例如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週刊,無論內容為何,都極易被冠上「擾亂社會秩序」甚或「親共」罪名。就連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鄭南榕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自由時代》週刊第二五四期刊載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國民黨政府都還以該篇文章主張國土分裂為由,在當月月底查禁雜誌,並在隔年以「涉嫌叛亂」的罪名起訴鄭南榕。
這是對言論自由的迫害,也是對文化的迫害。
▲文化的有機生長
文化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一個社會當中所有活動的綜合展現,無論由單一民族組成或不同民族聚合,無論是官方的歷史紀錄還是民間的鄉野傳奇,無論是本地凝聚的習俗還是外來移入的信仰,無論是供諸殿堂的藝術還是庶民日常的娛樂;文化承載了這個社會過去發展歷程裡存留的知識及見解,同時在社會組成分子不斷成長、轉變當中,融合社會當中自發展生或從其他社會汲取的思想與資訊,繼續形塑這個社會未來的樣貌。
也就是說,文化理應有機而且多元,雖然不停變化,但保有清楚的脈絡。
是故,官方,尤其是威權體制下的權力當局,或許可以在某些層面上支持文化形式,但極不應當管控文化內容。台灣固有文化先是被這樣的權力直接截斷,再是被偏狹的思考體系掌控,社會大眾對文化的理解於是產生巨大的偏差──固有文化難以延續,本土歷史被大中國歷史取代,但這樣的認知與世界發展局勢格格不入,而國民黨政府甚少自省,大多將這種狀況簡單地歸咎於中國共產黨政權。
▲解嚴後的持續傾斜
解嚴之後,偏差的角度還愈來愈大。
九〇年代開始,國民黨的專權雖然開始面對較以往更強力的挑戰,但在經年累月黨國教育及言論管控下造成的文化裂口,無法馬上重新銜接。以出版市場為例,根植本土的出版品數量不多,新生代創作者可能依隨原先由威權教育養成的思考模式創作,也可能因為已被設定的自我審查習慣,所以不在創作品中談論社會議題,轉而專述內裡情緒;加上各個文學獎項主辦單位及評審仍多由早先的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主管,獲獎後進入出版市場的作品更容易出現口味偏頗的情況,明明是本土創作,卻愈來愈難與普羅大眾親近。
八〇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本土文化萎縮的程度十分駭人。
解嚴後的出版市場一度活絡,由於進入門檻不高,除了原已存在的出版社之外,也出現了不少新廠牌。但學校的教材教程還沒出現太大改變,本土創作者與商業市場的需求難以扣接,是故無論新舊出版社,都開始較以往更積極地引入國外作品,尤其受到國外讀者喜愛的大眾讀物。這種方法雖然讓出版市場蓬勃發展,同時讓國內讀者能夠更快更廣地接觸世界各地創作,但其實也是一種炒短線的投機手段。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當時國內書市營業額占比最大的文學小說類型,有超過六成的書籍是翻譯作品,暢銷書中難得看見本土創作;如果除去出版量較大的言情小說,純文學創作的銷售不佳,而理應更貼近普羅讀者的大眾文學光出版量就少得可憐。▲台灣,你的聲音在哪裡?
引進國外作品絕非壞事,但數量上的失衡卻會引發惡性循環。
編輯經年累月引入國外已出版的暢銷作品,缺乏與作者溝通討論創作的機會,遑論好好培埴新作者,就算在網路上找到具有人氣、作品已有一定水準的作者,也很難協助作者長期穩定創作,僅能靠作者個人力量堅持;純文學創作者感嘆讀者購買意願低落,大眾文學創作者的學習標的又只有良莠不齊的外來作品,加上編輯支援不夠,努力寫出來的東西也不容易被讀者接受。在這種情況下,讀者幾乎已經產生「本土文學作品看不懂、本土大眾小說不好看」的觀念,在選購出版品時,大約都會以翻譯作品為主。
出版市場的這個現象,在其他文化產品市場中也可見到,包括影視及音樂。
九〇年代中後段,中國開始有限度地改革開放,國內文化產品市場的經營者開始把焦點轉向中國市場──國內市場不佳?那麼不用提升水準或設法進入國際市場,只要能讓產品輸入中國就好,中國人口多,市場一定大──無論是將台灣產品輸入到中國,或者將中國產品引進到台灣,只要不涉及政治議題,這麼做都可以省掉大部分的翻譯成本,十分方便。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製作成本需求較大的影市產業乘勢而起,台灣業者將其引入的動作就更積極,只要製作內容與政治現況無涉或與中華文化有關,台灣的閱聽群眾就不難接受──因為那與洗腦教育所傳授的內容大致相同。但令人憂慮的是,因為文化是社會集體意識的濃縮,所以這類來自中國的大眾文化產品仍然可能慢慢改變台灣民眾,例如對民主制度的曲解,或對台灣主體性的疑惑。
先因政治,後因經濟,台灣的文化市場長年來都有點畸形。
身為海島國家,往來商賈、四方移民,加上曾有不同外來政權進駐,台灣文化理應豐富多樣,呈現一種融合樣態──這種樣態在日常飲食當中可以發現,在民間信仰裡頭也能體會,在這些層面不但可以看見歷史當中各階段的不同影響,還能看見從八〇年代末期開始移入台灣的新住民元素。但從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的社會狀況,源於政治與經濟因素產生的歷史斷裂、思考受制,以及創作者與閱聽者缺乏對話,使得現在要談台灣文化,似乎難以確定某種說得清發展理路的中心骨幹。
所幸,這個狀況並非無法改變。
▲新生代長出新骨幹
仍以出版為例。二〇一〇年之後,有愈來愈多年輕編輯進入職場,無論自己成立小型出版社或者進入較具規模的中、大型出版社工作,無論專精的是文學、歷史、科學還是商業,許多年輕編輯十分關心社會議題,尤其是與台灣相關的題目;他們或許仍會出版翻譯作品,但也投注大量時間心力與本土作者合作,試圖重建本土創作者與閱聽者的連結。也有致力從各種角度討論台灣議題的創作者,透過網路論壇或社群平台,直接與閱聽群眾進行對話;而閱聽群眾逐漸聚焦在這些作品的同時,這些作品也更有機會躍入現今資訊流動更快速的國際市場。
官方單位也應提供協助,但協助方式或許不完全是資金。
要能健全獨立,文化產業應當建立從產製端到消費端的自給自足商業模式;既是「產業」,營業方自然必須設法存活,但也因產品與「文化」相關,是故以炒短線方式獲利並不足取,設法探究台灣歷史、解析社會現象,以及培育輔助創作者,才是與閱聽群長扣接的長久之計。官方能夠提供的協助,是教育內容──例如歷史資料的完整坦誠以及閱讀能力的培養訓練,還有相關的文化建設──例如方便查找開誠布公的歷史資料庫、鼓勵民眾參與的地方文化活動、幫忙在地文史工作者蒐集與統整紀錄,以及盡力保存台灣各地的文化遺跡,就算是代表威權遺毒的建物,也能用來揭示正確史實。
文化絕非特定權力階級能夠單憑己意決定的物事。
▲沒有主流的繁花盛世
中國文化對台灣影響深遠,的確是目前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但先前遭政治因素壓抑的南島文化、閩南與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甚至早在大航海時代就出現的歐洲文化,也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台灣不能也不該視因政治力量強加而來的中國文化為唯一主流,而是應當一方面認清歷史沿革,一方面吸收新進元素,在梳理過往脈絡時持續生長變化,才能重新熔鑄出堅實的「台灣文化」骨幹。
這是所有台灣人民必須面對的功課。不用唱什麼高調,因為文化就扎根在每個人的日常當中。
◎口述:林濁水
◎採訪整理:亦竹
在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濁水眼中,一九八九年前後的台灣社會正處在一個壓抑後的狂飆年代。
解除戒嚴後,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戒嚴時期被壓抑住的所有議題,在那個時候一起奔放出來,包括政治訴求、社會訴求……各式主張都在那時候被提出來,因為壓抑太久,以致於一發動就慷慨激昂。在整個大狂飆風潮中,鄭南榕從推動新國家運動一路到捍衛言論自由的自焚,那種堅持理想的純粹與悲劇性,最是撼動了林濁水,使他震驚於人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以生命換取外界對基本人權:言論自由的正視?
▲狂飆的八〇年代
鄭南榕新國家運動發生的時刻,正好卡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和一九九一年廢除刑法第一百條中間。這個時間點代表著:雖然解除戒嚴社會運動開始奔放,然而依據刑法第一百條以及國安法,「台灣獨立」是屬於分裂國土的叛亂主張,是一個叛亂行為。
如果再晚幾年,結果可能會不一樣:刑法第一百條廢除後,台獨不再是叛亂罪,解除戒嚴後,台獨運動當然也可以跟著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檯面化,不需要鄭南榕以生命去換取推動的自由。在此之前,那些因未除的「罪」而累積的壓力,實引爆了鄭南榕的自焚。
那時,因為台獨還是叛亂主張,被列黑名單流亡海外是不能回來的,於是陸陸續續有很多人,像是許信良、陳婉真,闖關回來就被抓去關。當中最傳奇的莫過於一九八九年郭倍宏偷渡回台灣,神祕出現在政見發表會開中外記者會,之後在台下民眾戴「黑名單」面罩下,成功地再神祕脫逃,那是十分戲劇性的一幕。
所以那樣的激昂、亢奮,累積到引爆出自焚事件,我認為是一個關鍵。如果早一點,群眾不會那麼激昂,沒有相激相盪的氣氛,而晚一點,張力就消失了,所以在那個解除戒嚴但台獨仍是叛亂主張、叛亂行為的時候發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兩個追求價值
現在回頭看鄭南榕,他以犧牲生命同時完成了兩個核心價值:
第一:自由主義,人的自由主體不可侵犯。
第二:共同體追求獨立建國的理念,這是台獨價值,是台灣人作為一個共同體所追求的價值。
由於人的主體性不可被侵犯,卻因為他主張台獨就要去抓他,那麼他堅持的兩個核心價值就同時被侵犯了。
我主張台獨,你認為我是叛亂,我要對抗,對抗的台灣人並不少,但是鄭南榕採取的途徑最慘烈。他為什麼會走到這麼慘烈的地步?在我看來,是因為鄭南榕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悲劇性,他強調「我容不得人生的一絲不清白」,聽到這句話當時我很震撼,心想「我容不得人生的一絲不清白」,這怎麼可能?不錯,這句話有不少人講,他就是這樣自許,但是我這句能當真嗎?誰一旦當真,誰就注定走向悲劇。
既然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我的言論自由,包含主張台獨、包括解除戒嚴,還有包括各種各樣的主張,怎麼能夠被禁錮呢?那就是他容不得的不清不白之一。
再加上:人是自由的主體,怎麼可以被逮捕、受到拘束?台獨既然是一個他認為台灣共同應當追求的目標,他認為有其神聖性,那為什麼被禁止?這幾樣的不清不白,總和在一起,就令他不能忍受。
因此他面臨死亡的時候,真的就像蘇格拉底面對雅典人對他判決時一樣,認為:你們的判決是不對的,這個法律秩序我雖然必須要遵守,但我寧願犧牲生命也不屈服。能夠做到這樣的人,擁有非常強烈的悲劇性格,一般人不會尋求這一條道路。就這個角度來講,我說鄭南榕才是一個真正的絕對主義。
因為絕對主義有一個天生的困難,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更是有限的,人可以運用的資源還是有限的,人所處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那麼作為一個有限存在的人,又去把信持的價值絕對化,說一定要實踐到,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在台灣當時那樣的特殊處境更是如此,在那樣的環境中,他種種主張都不可能徹底實踐到讓他的人生沒有任何一絲的不清白。
一旦他要把「不容人生的一絲不清白」的信念貫徹到底,只有犧牲生命。
於是他就遇到非常困難的哲學和道德的難題,他怎麼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難題,基督教的回答直截了當:生命是上帝賦予的,人沒有權利自我取消,但是他並不相信上帝,於是他面臨的處境比教徒更自由也更艱難。因為,教徒一旦為宗教犧牲生命,不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他們最後有他們的神作為歸屬。
但鄭南榕面臨的是,結束生命就沒有了。即使是這樣,他還做了這個選擇,真是慘烈到極點。做到這樣的程度,他已經走入不是我能夠了解的世界了。
雖然表面上看來,他沒有神作為歸屬,但是他產生一個非常強大的牽引力量,把這個已經沒有神在巡行的世界拉住,使除魅的俗世在價值獲得確認後不致進一步沉淪。換句話說,在俗世裡,人要堅持價值、要在這個價值的引導下能夠堅持,很不容易。而他證明了這一點,且還不是用宗教的形式,這更是難上加難。
我沒有問過鄭南榕,人跟台獨之間是什麼關係。如果以宗教來說,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並沒有創造國家,國家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不是主體,是客體。那麼一個人作為主體,竟然可以為了追求客體的實踐,去犧牲生命,這對我來講實在太震撼了。
▲新國家運動的漣漪
鄭南榕的死雖然壯烈,但對廣大的社會而言,造成的衝擊恐怕沒有那麼快發生。台獨的支持度,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台獨黨綱通過的那一年一九九一年,大概只有五個百分點左右,至於他犧牲時的一九八九年,照道理說會更少。支持的人都這麼少,所以他的犧牲要擴大成多麼廣泛的社會漣漪有其限制。但是由於鄭南榕的犧牲,對人畢竟是太強烈的衝擊了,於是會開始思考:既然鄭南榕願意為了台獨犧牲自己的生命,那我是不是應該做一點什麼?
所以他的激勵是發揮在累積台獨運動者的這個層面,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是很少數。只是,社會的進步變遷,永遠是從核心的極少數人開始。
鄭南榕在一九八九年自焚之後,台獨支持度並沒有急速攀升,可見影響的速度不是那麼快,但確實對核心的幹部帶來影響。之後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台灣進一步自由化的時候,擴散的速度就非常迅速。所以台獨運動在鄭南榕自焚的前後階段,台獨運動階段性的核心目標應當是台獨原始觀念的提出。這個階段要做到提出的價值要能被人信賴,有人跟隨—-雖然只是少數,可以被信賴嗎?鄭南榕用他的生命做出交代: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用我的生命,來證明它是可以相信的。
接下來我要談談民進黨建黨後在台獨運動上的努力。一九八七年民進黨通過<台灣主權獨立的決議文>,決議文使台獨運動走上了一個新階段。走到一個新的軌道上,那是以前老台獨採取台灣地位未定論立場。在這立場上,老台獨派認為,透過制憲正名公投,表達台灣人民的意志,就可以成為獨立國家而加入聯合國。但是他們的這個想法,姚嘉文和我都很保留。我們認為兩岸分立各有中央政府已經是一個長久的、持續的事實,所以台灣的獨立主權已經不必要由公投去創造;何況在一、二十年之內,都不可能因為公投而能進入聯合國。除非開會的時候把中共的代表綁起來,不讓他們行使否決權,不然如何可能進入?那麼台灣豈不是就一直不是獨立國家?
這是台獨運動上一個革命性的改變。只是這革命帶來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現在台灣主權既然已經獨立,那獨立運動要做什麼?
我的看法是,美國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有韓戰的背景,在那様的背景下,美國主導了台灣法律地位未定,來定位台灣,無可厚非。但是,二次大戰結束後到一九九〇年前夕,兩岸分立已差不多四十多年了,各自擁有中央政府,互不隸屬,所以獨立已經是一個事實。且在經過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後,台灣人民實踐了自我統治,所以在決議文通過時,就認定台獨運動、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這三個主張要一起推動,一旦民主化,台灣人自己統治自己,台灣就是獨立了。
至於外部國際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的問題,在我看來不是法理的問題,而是政治現實的問題。需要努力的是「政治工作」,而不是完備什麼法律要件。
▲價值的實踐者,造就如今的獨立波濤
在這樣的認識下,當時台獨工作大概有幾個必須要非常努力的面向:第一,主權已經獨立,整個法律政治秩序不符合獨立現實。第二,主權獨立,有一些政策和法律秩序不符合獨立現實。第三,國家認同要改變,國民文化教材、歷史文化教材不改變、不本土化,不符合獨立現實。
在鄭南榕過世後兩年,一九九一年民進黨台獨黨綱通過,就是站在一個革命性的主權獨立的立場上,為台獨運動者規劃接下來該做的事。把上面提到三個要努力的面向歸納整理下來,就變成台獨黨綱的主要內容。
從這樣一個台獨黨綱出發,回顧鄭南榕,就可以見到在台獨運動裡面,他扮演了好幾個重要角色:第一,他推動制憲,這對後來制定台獨黨綱時是有影響的。第二,他推動運動要改變台灣國民認同。在台獨黨綱通過的前夕,對於台灣獨立最重要的認同與轉換,鄭南榕承擔了最核心的工作,而他為了證明這個價值,以自己的生命作代價。
至於台獨真正具體的實踐,是在憲政方面。一九九一、九二年,國會改選、廢省,接下來有直選總統,以及本土文化進入國民教育,都是在他過世以後逐一發生,最可嘆的是,他竟然都來不及看到。在梳理過往脈絡時持續生長變化──「台灣文化」的重新熔鑄
◎臥斧
一九六九年,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
這本書收錄台灣作家黃春明發表在報章雜誌的六篇故事,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七年都經不同出版社做過改版;二〇〇〇年皇冠出版社改版發行《黃春明典藏作品集》,第二集也叫《兒子的大玩偶》,不過只保留了當作書名的〈兒子的大玩偶〉,其餘五篇改放到其他合集,另加入了包括〈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等八篇短篇。將〈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收進同一本選集的考量之一,在於一九八三年這三個故事被拍成三段短片,組成一部電影,片名就叫《兒子的大玩偶》。
合集電影中的〈蘋果的滋味〉,當年曾引發有名的「削蘋果事件」。
▲不能說的「蘋果的滋味」
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描述江阿發上班途中,被美國駐台軍官座車撞斷雙腿住院,不料因此獲得鉅額賠償、啞女有了到美國留學的機會,全家人還初次嚐到蘋果如天堂般甜美的滋味。如實描繪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底層生活景況的劇情,卻被「中國影評人協會」以黑函密告,指出片中出現的貧苦生活、違章建築等有礙台灣國際形象,導致隸屬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打算在未經萬仁同意下修剪內容。此事經《聯合報》記者楊士琪在報上揭發,輿論嘩然。
從一九六九年的小說集到一九八三年的電影遭遇,可以看出台灣文化界的幾個現象。
一九四九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原來只是接收代管台灣、卻以主權擁有者自居的中國國民黨頒布了《台灣省戒嚴令》,相關法令包括對各式出版品的禁制,以日語或台語發表的各種作品,無論書籍、報刊、影視或音樂,都受到高壓控管。此舉使得原來的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無法發聲,「本土文化」與真正在台灣生活的民眾漸行漸遠。黃春明的創作展現庶民關懷,並未碰觸尖銳敏感的政治議題,雖在六〇年代末期得以發表,卻在十多年後因為改編成表現方式更直接明白、接觸群眾可能更多的電影時,仍然遇上政黨惡意的介入。
迫於輿論壓力,中央電影公司放棄刪剪〈蘋果的滋味〉,但文化與大眾長期悖離造成的歪斜,已然形成。
▲語言與文學是最完美的洗腦工具
日語及台語使用者被奪去發語權之後,中國國民黨宣揚大中華主義、自身權力正統的相關產品成為文化界的主流,其中不但假造神話推崇國民黨人物,甚至刻意低貶醜化台籍、日籍人士,以及原住民。這類文化產品充斥出版及影音市場,並且強力滲入教育體系,描寫台灣鄉村及底層生活的作品被壓到末流,也缺乏反應社會整體現況的力道。一九七七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看起來是「現代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對抗,事實上是「官方」與「反官方」文化的對抗,但就算是反對當時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反官方」論者當中,仍存在「中國國族主義」色彩,顯示本土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在威權體制及強力洗腦下,對於「台灣主體」產生不同見解,或者不願太過強調。
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如此,一般的閱聽大眾受到的影響就更明顯。▲言論自由與叛亂罪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生活普遍富裕之後,消費性的文化產品需求更高,但文化市場流通的主流產品包裹的意識型態,多為黨國教育當中的一言堂產物,黨外言論,例如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週刊,無論內容為何,都極易被冠上「擾亂社會秩序」甚或「親共」罪名。就連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鄭南榕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自由時代》週刊第二五四期刊載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國民黨政府都還以該篇文章主張國土分裂為由,在當月月底查禁雜誌,並在隔年以「涉嫌叛亂」的罪名起訴鄭南榕。
這是對言論自由的迫害,也是對文化的迫害。
▲文化的有機生長
文化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一個社會當中所有活動的綜合展現,無論由單一民族組成或不同民族聚合,無論是官方的歷史紀錄還是民間的鄉野傳奇,無論是本地凝聚的習俗還是外來移入的信仰,無論是供諸殿堂的藝術還是庶民日常的娛樂;文化承載了這個社會過去發展歷程裡存留的知識及見解,同時在社會組成分子不斷成長、轉變當中,融合社會當中自發展生或從其他社會汲取的思想與資訊,繼續形塑這個社會未來的樣貌。
也就是說,文化理應有機而且多元,雖然不停變化,但保有清楚的脈絡。
是故,官方,尤其是威權體制下的權力當局,或許可以在某些層面上支持文化形式,但極不應當管控文化內容。台灣固有文化先是被這樣的權力直接截斷,再是被偏狹的思考體系掌控,社會大眾對文化的理解於是產生巨大的偏差──固有文化難以延續,本土歷史被大中國歷史取代,但這樣的認知與世界發展局勢格格不入,而國民黨政府甚少自省,大多將這種狀況簡單地歸咎於中國共產黨政權。
▲解嚴後的持續傾斜
解嚴之後,偏差的角度還愈來愈大。
九〇年代開始,國民黨的專權雖然開始面對較以往更強力的挑戰,但在經年累月黨國教育及言論管控下造成的文化裂口,無法馬上重新銜接。以出版市場為例,根植本土的出版品數量不多,新生代創作者可能依隨原先由威權教育養成的思考模式創作,也可能因為已被設定的自我審查習慣,所以不在創作品中談論社會議題,轉而專述內裡情緒;加上各個文學獎項主辦單位及評審仍多由早先的知識分子及文化創作者主管,獲獎後進入出版市場的作品更容易出現口味偏頗的情況,明明是本土創作,卻愈來愈難與普羅大眾親近。
八〇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本土文化萎縮的程度十分駭人。
解嚴後的出版市場一度活絡,由於進入門檻不高,除了原已存在的出版社之外,也出現了不少新廠牌。但學校的教材教程還沒出現太大改變,本土創作者與商業市場的需求難以扣接,是故無論新舊出版社,都開始較以往更積極地引入國外作品,尤其受到國外讀者喜愛的大眾讀物。這種方法雖然讓出版市場蓬勃發展,同時讓國內讀者能夠更快更廣地接觸世界各地創作,但其實也是一種炒短線的投機手段。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當時國內書市營業額占比最大的文學小說類型,有超過六成的書籍是翻譯作品,暢銷書中難得看見本土創作;如果除去出版量較大的言情小說,純文學創作的銷售不佳,而理應更貼近普羅讀者的大眾文學光出版量就少得可憐。▲台灣,你的聲音在哪裡?
引進國外作品絕非壞事,但數量上的失衡卻會引發惡性循環。
編輯經年累月引入國外已出版的暢銷作品,缺乏與作者溝通討論創作的機會,遑論好好培埴新作者,就算在網路上找到具有人氣、作品已有一定水準的作者,也很難協助作者長期穩定創作,僅能靠作者個人力量堅持;純文學創作者感嘆讀者購買意願低落,大眾文學創作者的學習標的又只有良莠不齊的外來作品,加上編輯支援不夠,努力寫出來的東西也不容易被讀者接受。在這種情況下,讀者幾乎已經產生「本土文學作品看不懂、本土大眾小說不好看」的觀念,在選購出版品時,大約都會以翻譯作品為主。
出版市場的這個現象,在其他文化產品市場中也可見到,包括影視及音樂。
九〇年代中後段,中國開始有限度地改革開放,國內文化產品市場的經營者開始把焦點轉向中國市場──國內市場不佳?那麼不用提升水準或設法進入國際市場,只要能讓產品輸入中國就好,中國人口多,市場一定大──無論是將台灣產品輸入到中國,或者將中國產品引進到台灣,只要不涉及政治議題,這麼做都可以省掉大部分的翻譯成本,十分方便。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製作成本需求較大的影市產業乘勢而起,台灣業者將其引入的動作就更積極,只要製作內容與政治現況無涉或與中華文化有關,台灣的閱聽群眾就不難接受──因為那與洗腦教育所傳授的內容大致相同。但令人憂慮的是,因為文化是社會集體意識的濃縮,所以這類來自中國的大眾文化產品仍然可能慢慢改變台灣民眾,例如對民主制度的曲解,或對台灣主體性的疑惑。
先因政治,後因經濟,台灣的文化市場長年來都有點畸形。
身為海島國家,往來商賈、四方移民,加上曾有不同外來政權進駐,台灣文化理應豐富多樣,呈現一種融合樣態──這種樣態在日常飲食當中可以發現,在民間信仰裡頭也能體會,在這些層面不但可以看見歷史當中各階段的不同影響,還能看見從八〇年代末期開始移入台灣的新住民元素。但從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的社會狀況,源於政治與經濟因素產生的歷史斷裂、思考受制,以及創作者與閱聽者缺乏對話,使得現在要談台灣文化,似乎難以確定某種說得清發展理路的中心骨幹。
所幸,這個狀況並非無法改變。
▲新生代長出新骨幹
仍以出版為例。二〇一〇年之後,有愈來愈多年輕編輯進入職場,無論自己成立小型出版社或者進入較具規模的中、大型出版社工作,無論專精的是文學、歷史、科學還是商業,許多年輕編輯十分關心社會議題,尤其是與台灣相關的題目;他們或許仍會出版翻譯作品,但也投注大量時間心力與本土作者合作,試圖重建本土創作者與閱聽者的連結。也有致力從各種角度討論台灣議題的創作者,透過網路論壇或社群平台,直接與閱聽群眾進行對話;而閱聽群眾逐漸聚焦在這些作品的同時,這些作品也更有機會躍入現今資訊流動更快速的國際市場。
官方單位也應提供協助,但協助方式或許不完全是資金。
要能健全獨立,文化產業應當建立從產製端到消費端的自給自足商業模式;既是「產業」,營業方自然必須設法存活,但也因產品與「文化」相關,是故以炒短線方式獲利並不足取,設法探究台灣歷史、解析社會現象,以及培育輔助創作者,才是與閱聽群長扣接的長久之計。官方能夠提供的協助,是教育內容──例如歷史資料的完整坦誠以及閱讀能力的培養訓練,還有相關的文化建設──例如方便查找開誠布公的歷史資料庫、鼓勵民眾參與的地方文化活動、幫忙在地文史工作者蒐集與統整紀錄,以及盡力保存台灣各地的文化遺跡,就算是代表威權遺毒的建物,也能用來揭示正確史實。
文化絕非特定權力階級能夠單憑己意決定的物事。
▲沒有主流的繁花盛世
中國文化對台灣影響深遠,的確是目前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但先前遭政治因素壓抑的南島文化、閩南與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甚至早在大航海時代就出現的歐洲文化,也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台灣不能也不該視因政治力量強加而來的中國文化為唯一主流,而是應當一方面認清歷史沿革,一方面吸收新進元素,在梳理過往脈絡時持續生長變化,才能重新熔鑄出堅實的「台灣文化」骨幹。
這是所有台灣人民必須面對的功課。不用唱什麼高調,因為文化就扎根在每個人的日常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