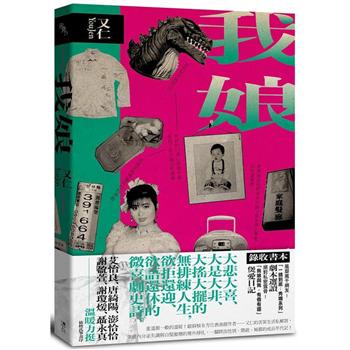SCENE 01 學著當媽媽
長大後發現,媽媽對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有著各種矛盾,現在想起,對於她的這些矛盾,充滿心疼。
像是她對我們在課業上的要求,許多成分或許來自於鄰居與親戚之間的比較,叛逆的中學時期我會特別點出「比較心態」回嘴,當然、一位天秤座媽媽在氣頭上聽到「頂嘴」只會更加爆炸,下一步就是上演將我的參考書或練習測驗卷丟入垃圾桶的戲碼,等氣消了會撿回來告訴我說媽媽都是為我好。我想許多爸媽也是如此,將期望放在小孩的課業上,另一方面就是壓力。但她打從心底,真的這麼在乎課業上的「分數」嗎?或者也是周遭各方耳語帶來的壓力?後來我和老妹都走上戲劇路,媽媽和老爸北上來看我每一場演出,似乎代表她終於放下了那些標準與限制。可能是大學後我們都離家,她管不著了,或許覺得小孩沒學壞就好,也可能回想過去對我們的要求,像是她在守住某種自己設下的底線;又或者是如今,我們都更認識彼此了。
另一種矛盾,是在我幼稚園大班時發現的。
幼稚園時她總是每天早上騎著機車載我到學校後,再開張家中客廳的家庭髮廊。但那一天我清晰記得,雨下得很大,機車被老爸騎去警局上班,她盡快將我套上一件輕便雨衣,牽著我和老妹到隔壁,將老妹暫時託給張太太後借了機車。張太太是媽媽的常客,來做頭髮時會跟著爸媽一樣叫我的小名「涂寶」,記得我小時很愛模仿她高亢親切的語調說話,我媽就會笑到東倒西歪。
跳上機車後座,媽要我緊抱她,迅速將身穿的大件桃紅色雨衣一大塊包覆住我的頭,不讓迎風射過來的支支雨點往我臉上來。那段路我被整片桃紅包圍,伴著媽媽熟悉的香水味。桃紅之外的世界蒙著一層悶悶的不斷掃過的唰唰雨聲,聲響越來越密集、節拍越來越快,交雜各種人車聲嗡嗡地出現又瞬間閃逝,當時媽媽肯定被時間逼得焦躁。
在心理時間預測快到學校時,突然一個強力停頓,擺動,將我用力往後甩動又大力彈回,碰一聲撞上老媽的背部。聽見一聲尖銳的女人喊叫後,整片桃紅世界往左下方傾斜,我頭上安全帽先碰到一面牆,力道不算太大,到左腳小腿肚內側有擠壓的力道襲來,帶點灼熱讓我下意識立刻抽出。我才發現那是柏油路,不是牆,我是躺著的,剛剛是她的喊叫聲,機車是不是倒了?我才迅速鑽出那片桃紅,媽媽側躺在我眼前,安全帽依然在頭上,旁邊的雨聲和人車聲變得尖銳清晰。我緩緩抬起頭才看見,四周許多人圍上,前方停著一輛藍色小貨車,視線掃回倒下的機車,後照鏡都碎裂了,啊,車禍,是我們自己出車禍了,媽媽!愣了一小段時間,才開始搖晃我媽,只覺得剛剛的一切都是慢動作。剛好左方對面有間醫院,對,我已經快到幼稚園了,那是學校附近的醫院欸,我當時這樣想。很快地,有幾位穿著白衣的人衝向我們,還有人推著一張有滾輪的床,又有人將我扶起,一切才從慢速轉回正常。
後來我就坐在病房中了。記得護士一邊幫我擦藥一邊說好在只有小腿擦傷,沒多久,媽醒來了。周圍除了醫護人員,爸也趕來了,似乎還有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小貨車司機,我的大班導師和園長也來了。我怎麼在醫院?媽醒來後開始問問題,爸爸簡單回覆也要她不要擔心。涂寶呢?我立刻湊上前讓媽媽看見我。妹妹呢?爸爸回說妹妹在張太太家,要她放心。但那時我已經知道怪了,果然沒五分鐘,媽媽開始重複這些問題,又問到我時,我立刻抓著她的手告訴她:我在這裡。心裡開始慌,園長先將我帶往學校。
想必已過中午,周圍沒有時鐘,園長先帶我到學校的廚房,她陪我坐在廚房某個角落吃飯,廚房阿姨們已經開始收拾各班的大型餐具。那天吃的是我最愛的炒飯,一如往常吃了兩盤以上,園長笑我很會吃,這樣很好。而我一邊扒著飯一邊沒忘媽媽的狀況而開始問園長,她只要我別擔心,說媽媽沒事。左小腿上的擦傷提醒著,刺刺的。
過兩天後媽媽回來了,那幾天爸爸都沒去上班,在家陪她,跟著媽在家裡外走來走去,媽媽一樣重複各種問題,大多是生活上的瑣事或是我和妹妹在哪裡之類的。我下課回到家只敢偷偷在一旁看著,寫功課也看,洗完澡也會在房間偷聽,一心很怕媽媽會不會哪天忘記我們。
某天晚上,媽媽一個人走到陽臺紗門前,小心翼翼地左顧右盼像在找什麼,像是對眼前的一切充滿陌生,爸爸沒一會出現問她要不要出去陽臺吹吹風,媽突然探了一下陽臺方向說,很暗。媽媽怕暗嗎?我當時跳出這想法,偷偷在房間望著爸媽的一舉一動,爸爸立刻安慰說,放心、陽臺有小燈。
原來媽媽也怕黑。
比較大了之後,才知道當時媽媽因為在小貨車後方的那一下撞擊,導致腦部有些微的出血並結塊,因而產生選擇性忘記事情、問了又忘的症狀,大概經過兩週的治療後就復原了。
原來媽媽怕黑,這是那時很大的衝擊。因為媽常在晚上要我們到陽臺幫忙洗衣或晾衣,我總會喊著好暗好暗,她總是回說怕什麼,又沒有東西會把你吃掉,然後我就回答誰叫妳都騙人說有虎姑婆。更大了之後,媽也跟我承認她怕黑、怕蛇、怕走在小巷子裡。
直到有天我明白了,所有的口是心非與矛盾,是為了孩子端出的逞強,或說是她慢慢長出的勇敢,更是她在我們成長的路上從未停止學著,如何當媽媽。
SCENE 09 送餅乾的男孩
二零一六年因為創作短片爆紅後,與經紀公司開始合作,特別辦了出道記者會,與大眾正式打招呼。會後的平面訪談,我直接向媒體朋友表明同志身分,一方面不想存有曖昧地帶就直接了當吧,也不願日後被特別檢視或是做文章。另一方面,這真的是再正常、再一般不過的事啊,我跟別人沒有不一樣。
曾經有人因此對於我在表演或角色詮釋上的能力產生質疑,初期的灰心是一定有的,甚至冒出「又被貼了標籤嗎」、「是不是不適合走這條路」等疑問,久了,根本無需跟這些人計較,我不需要向他們證明什麼,只要持續在專業上發揮,努力把對的事做好,帶給人力量,總有一天他們會明白的。
後來,我常會碰到同一個提問:小時候是否曾遭到霸凌對待呢?
首先,慶幸從小就對所謂的「霸凌」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從國小開始就有各種考試,「比較」無所不在,無論同儕之間、大人之間、親戚之間等等太多太多,只要嗅到這樣的情況,要嘛閃人,如果閃不開,乾脆回覆「我也拿過畫畫比賽第一名啊」,抱持一種你說A我回B的轉移方式,結束一切。
這兩種方式也應用在被言語霸凌的時候。國小五年級開始,我的身材越吃越胖,足以讓一些同學指著喊「死胖子」,再者是性別氣質上的辱罵,「娘炮」、「娘娘腔」真的習以為常了。碰到辱罵,除了上述兩種方式,冷處理也滿有效的,要嘛冷冷看著他們許久,覺得不好玩了就會離開,要嘛就是連我自己都愣住的方式——
有次合唱比賽,被音樂老師指派為班上的指揮,記得是唱臺語歌〈農村曲〉,曲調輕快,需要一位節奏感和肢體豐富的學生,我沒有讓音樂老師失望,除了班上拿到好成績,還拿下最佳指揮獎。但因為那次比賽,有個男同學知道我在哪一班,從那天起對我展開更密集的攻擊。
可能因為常跟女生混在一起,也可能從國小到高中,最常擔任的是學藝股長,興趣和專長也都是被刻板歸類在「女生喜歡」的各種事物上,因此時常被那些臭男生罵「娘」。那位男同學曾在掃地時間,三番兩次「特地」跑來罵我娘炮,有時下課一打鐘就出現在教室門口嚇我,死胖子、娘炮等字眼連珠炮,我都閃避或冷眼。後來甚至開始動手,扯我褲子、推我肩膀,那時我意識到他不會罷休。
有次他推我的力道太大,我踉蹌了一下,用力轉身看著他,他似乎因為我的大動作頓了一下,當下想大聲回罵,或是將他的行為吼出來,讓所有同學聽到,但我忍住了。下一秒慢慢走向他,走到彼此只有二十公分的距離,「謝謝。」我淡淡地脫口而出這兩個字,他愣住了,突然石化。我到底為什麼會說謝謝啊?
好的,竟然還有更荒謬的進展。隔天第一堂下課鐘響沒五分鐘,他出現在教室門口,收起平時的浮躁,首次叫了我名字,揮手示意要我過去。我有點忐忑,不忘提醒隔壁同學,若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立刻叫老師。
「這給你。」他從合作社買了包餅乾,遞給我。
「謝謝。」這次的謝謝,總算是合情合理了。
他點了頭,迅速跑走,消失在我面前。餅乾包裝上,貼著一張小紙條,寫著「對不起」。
奇怪又奇妙的感覺突然在胸口搔著,他道歉了,因為我昨天那聲莫名其妙的謝謝嗎?當天下午,我買了餅乾回送給他。回想起來,不知道自己那聲「謝謝」,讓他在那一天之內經歷了什麼,他從此不再欺負我,甚至不再那樣對待任何同學。
而有個夢,在那時期時常出現。
我在國小教室外的走廊奔跑,像在躲著誰,不斷往前慌張奔跑,但走廊不尋常地越來越長,左彎右拐沒有盡頭。冷不防一道刺眼的白光射了過來,充滿整個畫面。大概到第三次做這個夢時,我已經知道會抵達一間超大的寺廟。果然,白光之後我已經在那間寺廟外的廣場,也知道繼續往右手邊跑,會經過一條巨型的龍雕像,再往前跑,看到老虎雕像時,會出現寺廟角落的提款機。不知道為什麼,爸每次都會在那裡提款。如同前一次夢境一樣穿著警察制服出現,我還在逃命,得向他求救,但已經第三次了,之前不敢叫爸爸,這次想賭賭看,結果會不會跟上次不一樣。我吼著爸爸、爸爸,一邊拍著他,孰料他轉過頭來是一張比旁邊老虎雕像還可怕的老虎臉,扭曲、帶著血紅,而且充滿皺褶,不是爸爸的臉,他快速地俯衝過來,啊!
我醒了,又是那個噩夢。
後來稍微理出這個夢,和被霸凌的經歷似乎有所連結,尤其是時間點的巧合。我是個報喜不報憂的小孩,如果跟爸媽說出經歷,相信他們應該會挺難過的。到了中學時,類似的言語或肢體霸凌沒有消失,尷尬的是,除了花很長的時間,內心糾結地問自己,這樣的性別氣質是否是不對的,也總認為自己可以處理這些情緒和處境,而選擇隱瞞。
當時的我在心理上確實產生過各種影響,不管是送餅乾的男孩,或是其他遭受過的類似行為,這夢就是其一。夢裡映照出潛意識的恐懼,恰好都在遭遇這些攻擊行為之後。真心希望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都不要成為這樣的被害者或加害者,不僅是孩子,許多大人更需要理解相關教育的重要。
送餅乾的男孩,還有過去的又仁啊,讓我抱抱你們,好嗎?
SCENE 13 媽媽的背影
「我很想繼續升學啊,只是那時候阿嬤叫我快點出來工作幫忙家裡,我又是老大,所以國中畢業後就離開家到臺北學美髮……」媽哽咽著。
戲劇系大二時的暑假,我和妹妹一起籌備一個劇場演出,回老家找靈感,也想翻找老家存放的回憶小物。當晚和媽在她的房間聊著。我們坐在床邊的木質地板上,雙手舒適地靠在床面,可以聞到床上有媽媽的淡淡香水味。媽穿著最愛的酒紅色細肩連身過膝裙睡衣,粉色鯊魚夾隨意將她的波浪長髮固定在頭頂,她盤坐在床上擦著指甲油,一邊和我們聊著。媽是感性的人,從小到大看她哭過許多次,她不避諱在我們面前表達各種情感。不知道是否受職業影響,也或許她本來就這麼健談,不管是她的客人,或是身為兒女的我們,和她說話很容易放鬆,很容易被她吸引。
她說在臺北學美髮時,跟到不錯的老闆娘,但是對於環境不熟悉,時常覺得沒人可以訴說心事。冬天時最痛苦,一天洗完好幾顆頭、持續練習染髮,洗劑、藥水等長時間的使用和浸泡,冰冷的雙手早就破皮紅腫。幫客人洗頭時,雙手痛到顫抖只能忍著不敢吭聲,還是得把整天的工作好好完成,把該學的學好。晚上回到和其他學徒合租的小租屋,雙手擦了擦藥,回到房間只能躲在棉被裡偷哭,不敢每天打電話回家哭訴,她說阿嬤真不是普通的嚴厲啊,要她好好堅強,之後就可以回雲林的髮廊工作。
「那時候真的很氣你們外婆耶,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這樣覺得,小時候真的很辛苦。我好喜歡讀書,但阿公阿嬤覺得女生不用讀那麼高啦,趕快出來幫忙家裡比較實際。家裡有好多事要幫忙,他們每天都一早出去工作,我凌晨就要起床,天還沒亮,抱著整袋衣服和工具,騎腳踏車穿越一整片樹林,啊路燈也不多喔,很黑,自己一個人到河邊洗衣服。每次都好怕沿路有人跟蹤我,還是河邊有什麼東西跑出來,欸,我一個女生在那邊洗衣服,很恐怖。」
媽媽邊留著眼淚,邊笑著回顧這些往事,我們抽了面紙給她,她擦了臉上的淚水,忍不住笑了一下,我和妹妹也含淚看著她笑了。
「洗完衣服回到家,我就要趕快煮飯煮菜喔,因為要叫你們阿姨和舅舅起床上學,讓他們可以吃早餐。有幾次太晚回來煮飯,被妳外婆抓到,我就被打被罵,帶著瘀青的小腿去學校。以前真的重男輕女,你舅舅不愛念書,很會打扮也很會玩,阿公阿嬤還是對他最好,啊也不會逼你舅舅去工作,只因算命師說舅舅和阿姨都很聰明不用擔心。換作我,只要事情做錯就挨罵、被打。國三的時候我終於轉到最好的升學班,還一直被阻止念高中,好奇怪耶。」
那時候才知道,為什麼媽在我們都上幼稚園後,堅持去考高職夜校。念完高中,一直是她小小的夢想。「你們爸爸也是很好啦,很支持我去上學,而且媽媽很爭氣,全校第二名畢業喔。」
回想起來是有一段時間,傍晚幼稚園下了課就被帶去爸爸的莿桐老家給阿公阿嬤帶。吃完阿嬤煮的晚餐,陪阿公看新聞和他最愛的《大陸尋奇》,或是跟住在附近的堂哥堂姊玩,等十點多媽媽下課來接我們回家。回家洗完澡,最常看到的就是媽專心趴在床上念書複習筆記的背影。那個背影,給我的力量超乎想像。
高三學測後,考上靜宜大學觀光學系,那時開心地離家,卻也突然意識到好多事情得開始自己面對。那時戲劇系面試後落榜,下定決心好好念觀光,給自己許多壓力,無論是生活、人際、課業或各類活動,參加啦啦隊、參與活動主持、實習當領隊賺錢,也經歷了不敢說的初戀。後來給了自己更多期許,卻無法放下戲劇的夢想,跑到新竹參加面試而錄取了劇團的儲備演員,開始東奔西跑,邊念書邊揹著大小道具演出的日子,那時只能尋求家裡經濟上更多的協助,爸的不諒解也加深了心理上的沉重感,尤其大二上學期偷偷休學,決定轉考戲劇系的那段時間。
對家人,我總是報喜不報憂。直到有天走在往學校餐廳的路上,伴著即將爆發的情緒,望著手機許久撥給了媽。種種壓力和隱瞞,在聽到媽的聲音那一刻,眼淚直接衝了下來。「媽媽,我……我覺得好累。」試圖讓哽咽斷續的聲音,顯得堅強些。媽沉默了幾秒,溫柔地要我加油,告訴我,想休息的時候就要休息。好多事情不敢說,無論是感情狀態、偷偷休學的事、在劇團排練演出的壓力等等。調適好情緒,沉默了一陣子,最後只鼓起勇氣告訴她,我休學了。她沒多說什麼,繼續為我打氣,要我找一天回家。
通話結束後,我快步走到無人角落,蹲坐下來好好哭一場。那時我想到媽的背影,在髮廊忙完一整天,夜校下課回家後還要照顧兩個小孩,繼續讀書到半夜的,那個美麗又堅強的背影。
整個夜晚,我、妹妹和媽,哭笑著聊到凌晨,才肯互道晚安,一旁爸的打呼聲也陪伴著我們。我到現在都還沒跟媽說過,那些夜晚的她的背影,在我感到無助、無力或挫折時,始終給我好大的力量。她帶給我們的,不僅是一種堅毅,還有一分我和妹妹都遺傳到她的給人鼓舞又溫暖的超能力。
長大後發現,媽媽對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有著各種矛盾,現在想起,對於她的這些矛盾,充滿心疼。
像是她對我們在課業上的要求,許多成分或許來自於鄰居與親戚之間的比較,叛逆的中學時期我會特別點出「比較心態」回嘴,當然、一位天秤座媽媽在氣頭上聽到「頂嘴」只會更加爆炸,下一步就是上演將我的參考書或練習測驗卷丟入垃圾桶的戲碼,等氣消了會撿回來告訴我說媽媽都是為我好。我想許多爸媽也是如此,將期望放在小孩的課業上,另一方面就是壓力。但她打從心底,真的這麼在乎課業上的「分數」嗎?或者也是周遭各方耳語帶來的壓力?後來我和老妹都走上戲劇路,媽媽和老爸北上來看我每一場演出,似乎代表她終於放下了那些標準與限制。可能是大學後我們都離家,她管不著了,或許覺得小孩沒學壞就好,也可能回想過去對我們的要求,像是她在守住某種自己設下的底線;又或者是如今,我們都更認識彼此了。
另一種矛盾,是在我幼稚園大班時發現的。
幼稚園時她總是每天早上騎著機車載我到學校後,再開張家中客廳的家庭髮廊。但那一天我清晰記得,雨下得很大,機車被老爸騎去警局上班,她盡快將我套上一件輕便雨衣,牽著我和老妹到隔壁,將老妹暫時託給張太太後借了機車。張太太是媽媽的常客,來做頭髮時會跟著爸媽一樣叫我的小名「涂寶」,記得我小時很愛模仿她高亢親切的語調說話,我媽就會笑到東倒西歪。
跳上機車後座,媽要我緊抱她,迅速將身穿的大件桃紅色雨衣一大塊包覆住我的頭,不讓迎風射過來的支支雨點往我臉上來。那段路我被整片桃紅包圍,伴著媽媽熟悉的香水味。桃紅之外的世界蒙著一層悶悶的不斷掃過的唰唰雨聲,聲響越來越密集、節拍越來越快,交雜各種人車聲嗡嗡地出現又瞬間閃逝,當時媽媽肯定被時間逼得焦躁。
在心理時間預測快到學校時,突然一個強力停頓,擺動,將我用力往後甩動又大力彈回,碰一聲撞上老媽的背部。聽見一聲尖銳的女人喊叫後,整片桃紅世界往左下方傾斜,我頭上安全帽先碰到一面牆,力道不算太大,到左腳小腿肚內側有擠壓的力道襲來,帶點灼熱讓我下意識立刻抽出。我才發現那是柏油路,不是牆,我是躺著的,剛剛是她的喊叫聲,機車是不是倒了?我才迅速鑽出那片桃紅,媽媽側躺在我眼前,安全帽依然在頭上,旁邊的雨聲和人車聲變得尖銳清晰。我緩緩抬起頭才看見,四周許多人圍上,前方停著一輛藍色小貨車,視線掃回倒下的機車,後照鏡都碎裂了,啊,車禍,是我們自己出車禍了,媽媽!愣了一小段時間,才開始搖晃我媽,只覺得剛剛的一切都是慢動作。剛好左方對面有間醫院,對,我已經快到幼稚園了,那是學校附近的醫院欸,我當時這樣想。很快地,有幾位穿著白衣的人衝向我們,還有人推著一張有滾輪的床,又有人將我扶起,一切才從慢速轉回正常。
後來我就坐在病房中了。記得護士一邊幫我擦藥一邊說好在只有小腿擦傷,沒多久,媽醒來了。周圍除了醫護人員,爸也趕來了,似乎還有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小貨車司機,我的大班導師和園長也來了。我怎麼在醫院?媽醒來後開始問問題,爸爸簡單回覆也要她不要擔心。涂寶呢?我立刻湊上前讓媽媽看見我。妹妹呢?爸爸回說妹妹在張太太家,要她放心。但那時我已經知道怪了,果然沒五分鐘,媽媽開始重複這些問題,又問到我時,我立刻抓著她的手告訴她:我在這裡。心裡開始慌,園長先將我帶往學校。
想必已過中午,周圍沒有時鐘,園長先帶我到學校的廚房,她陪我坐在廚房某個角落吃飯,廚房阿姨們已經開始收拾各班的大型餐具。那天吃的是我最愛的炒飯,一如往常吃了兩盤以上,園長笑我很會吃,這樣很好。而我一邊扒著飯一邊沒忘媽媽的狀況而開始問園長,她只要我別擔心,說媽媽沒事。左小腿上的擦傷提醒著,刺刺的。
過兩天後媽媽回來了,那幾天爸爸都沒去上班,在家陪她,跟著媽在家裡外走來走去,媽媽一樣重複各種問題,大多是生活上的瑣事或是我和妹妹在哪裡之類的。我下課回到家只敢偷偷在一旁看著,寫功課也看,洗完澡也會在房間偷聽,一心很怕媽媽會不會哪天忘記我們。
某天晚上,媽媽一個人走到陽臺紗門前,小心翼翼地左顧右盼像在找什麼,像是對眼前的一切充滿陌生,爸爸沒一會出現問她要不要出去陽臺吹吹風,媽突然探了一下陽臺方向說,很暗。媽媽怕暗嗎?我當時跳出這想法,偷偷在房間望著爸媽的一舉一動,爸爸立刻安慰說,放心、陽臺有小燈。
原來媽媽也怕黑。
比較大了之後,才知道當時媽媽因為在小貨車後方的那一下撞擊,導致腦部有些微的出血並結塊,因而產生選擇性忘記事情、問了又忘的症狀,大概經過兩週的治療後就復原了。
原來媽媽怕黑,這是那時很大的衝擊。因為媽常在晚上要我們到陽臺幫忙洗衣或晾衣,我總會喊著好暗好暗,她總是回說怕什麼,又沒有東西會把你吃掉,然後我就回答誰叫妳都騙人說有虎姑婆。更大了之後,媽也跟我承認她怕黑、怕蛇、怕走在小巷子裡。
直到有天我明白了,所有的口是心非與矛盾,是為了孩子端出的逞強,或說是她慢慢長出的勇敢,更是她在我們成長的路上從未停止學著,如何當媽媽。
SCENE 09 送餅乾的男孩
二零一六年因為創作短片爆紅後,與經紀公司開始合作,特別辦了出道記者會,與大眾正式打招呼。會後的平面訪談,我直接向媒體朋友表明同志身分,一方面不想存有曖昧地帶就直接了當吧,也不願日後被特別檢視或是做文章。另一方面,這真的是再正常、再一般不過的事啊,我跟別人沒有不一樣。
曾經有人因此對於我在表演或角色詮釋上的能力產生質疑,初期的灰心是一定有的,甚至冒出「又被貼了標籤嗎」、「是不是不適合走這條路」等疑問,久了,根本無需跟這些人計較,我不需要向他們證明什麼,只要持續在專業上發揮,努力把對的事做好,帶給人力量,總有一天他們會明白的。
後來,我常會碰到同一個提問:小時候是否曾遭到霸凌對待呢?
首先,慶幸從小就對所謂的「霸凌」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從國小開始就有各種考試,「比較」無所不在,無論同儕之間、大人之間、親戚之間等等太多太多,只要嗅到這樣的情況,要嘛閃人,如果閃不開,乾脆回覆「我也拿過畫畫比賽第一名啊」,抱持一種你說A我回B的轉移方式,結束一切。
這兩種方式也應用在被言語霸凌的時候。國小五年級開始,我的身材越吃越胖,足以讓一些同學指著喊「死胖子」,再者是性別氣質上的辱罵,「娘炮」、「娘娘腔」真的習以為常了。碰到辱罵,除了上述兩種方式,冷處理也滿有效的,要嘛冷冷看著他們許久,覺得不好玩了就會離開,要嘛就是連我自己都愣住的方式——
有次合唱比賽,被音樂老師指派為班上的指揮,記得是唱臺語歌〈農村曲〉,曲調輕快,需要一位節奏感和肢體豐富的學生,我沒有讓音樂老師失望,除了班上拿到好成績,還拿下最佳指揮獎。但因為那次比賽,有個男同學知道我在哪一班,從那天起對我展開更密集的攻擊。
可能因為常跟女生混在一起,也可能從國小到高中,最常擔任的是學藝股長,興趣和專長也都是被刻板歸類在「女生喜歡」的各種事物上,因此時常被那些臭男生罵「娘」。那位男同學曾在掃地時間,三番兩次「特地」跑來罵我娘炮,有時下課一打鐘就出現在教室門口嚇我,死胖子、娘炮等字眼連珠炮,我都閃避或冷眼。後來甚至開始動手,扯我褲子、推我肩膀,那時我意識到他不會罷休。
有次他推我的力道太大,我踉蹌了一下,用力轉身看著他,他似乎因為我的大動作頓了一下,當下想大聲回罵,或是將他的行為吼出來,讓所有同學聽到,但我忍住了。下一秒慢慢走向他,走到彼此只有二十公分的距離,「謝謝。」我淡淡地脫口而出這兩個字,他愣住了,突然石化。我到底為什麼會說謝謝啊?
好的,竟然還有更荒謬的進展。隔天第一堂下課鐘響沒五分鐘,他出現在教室門口,收起平時的浮躁,首次叫了我名字,揮手示意要我過去。我有點忐忑,不忘提醒隔壁同學,若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立刻叫老師。
「這給你。」他從合作社買了包餅乾,遞給我。
「謝謝。」這次的謝謝,總算是合情合理了。
他點了頭,迅速跑走,消失在我面前。餅乾包裝上,貼著一張小紙條,寫著「對不起」。
奇怪又奇妙的感覺突然在胸口搔著,他道歉了,因為我昨天那聲莫名其妙的謝謝嗎?當天下午,我買了餅乾回送給他。回想起來,不知道自己那聲「謝謝」,讓他在那一天之內經歷了什麼,他從此不再欺負我,甚至不再那樣對待任何同學。
而有個夢,在那時期時常出現。
我在國小教室外的走廊奔跑,像在躲著誰,不斷往前慌張奔跑,但走廊不尋常地越來越長,左彎右拐沒有盡頭。冷不防一道刺眼的白光射了過來,充滿整個畫面。大概到第三次做這個夢時,我已經知道會抵達一間超大的寺廟。果然,白光之後我已經在那間寺廟外的廣場,也知道繼續往右手邊跑,會經過一條巨型的龍雕像,再往前跑,看到老虎雕像時,會出現寺廟角落的提款機。不知道為什麼,爸每次都會在那裡提款。如同前一次夢境一樣穿著警察制服出現,我還在逃命,得向他求救,但已經第三次了,之前不敢叫爸爸,這次想賭賭看,結果會不會跟上次不一樣。我吼著爸爸、爸爸,一邊拍著他,孰料他轉過頭來是一張比旁邊老虎雕像還可怕的老虎臉,扭曲、帶著血紅,而且充滿皺褶,不是爸爸的臉,他快速地俯衝過來,啊!
我醒了,又是那個噩夢。
後來稍微理出這個夢,和被霸凌的經歷似乎有所連結,尤其是時間點的巧合。我是個報喜不報憂的小孩,如果跟爸媽說出經歷,相信他們應該會挺難過的。到了中學時,類似的言語或肢體霸凌沒有消失,尷尬的是,除了花很長的時間,內心糾結地問自己,這樣的性別氣質是否是不對的,也總認為自己可以處理這些情緒和處境,而選擇隱瞞。
當時的我在心理上確實產生過各種影響,不管是送餅乾的男孩,或是其他遭受過的類似行為,這夢就是其一。夢裡映照出潛意識的恐懼,恰好都在遭遇這些攻擊行為之後。真心希望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都不要成為這樣的被害者或加害者,不僅是孩子,許多大人更需要理解相關教育的重要。
送餅乾的男孩,還有過去的又仁啊,讓我抱抱你們,好嗎?
SCENE 13 媽媽的背影
「我很想繼續升學啊,只是那時候阿嬤叫我快點出來工作幫忙家裡,我又是老大,所以國中畢業後就離開家到臺北學美髮……」媽哽咽著。
戲劇系大二時的暑假,我和妹妹一起籌備一個劇場演出,回老家找靈感,也想翻找老家存放的回憶小物。當晚和媽在她的房間聊著。我們坐在床邊的木質地板上,雙手舒適地靠在床面,可以聞到床上有媽媽的淡淡香水味。媽穿著最愛的酒紅色細肩連身過膝裙睡衣,粉色鯊魚夾隨意將她的波浪長髮固定在頭頂,她盤坐在床上擦著指甲油,一邊和我們聊著。媽是感性的人,從小到大看她哭過許多次,她不避諱在我們面前表達各種情感。不知道是否受職業影響,也或許她本來就這麼健談,不管是她的客人,或是身為兒女的我們,和她說話很容易放鬆,很容易被她吸引。
她說在臺北學美髮時,跟到不錯的老闆娘,但是對於環境不熟悉,時常覺得沒人可以訴說心事。冬天時最痛苦,一天洗完好幾顆頭、持續練習染髮,洗劑、藥水等長時間的使用和浸泡,冰冷的雙手早就破皮紅腫。幫客人洗頭時,雙手痛到顫抖只能忍著不敢吭聲,還是得把整天的工作好好完成,把該學的學好。晚上回到和其他學徒合租的小租屋,雙手擦了擦藥,回到房間只能躲在棉被裡偷哭,不敢每天打電話回家哭訴,她說阿嬤真不是普通的嚴厲啊,要她好好堅強,之後就可以回雲林的髮廊工作。
「那時候真的很氣你們外婆耶,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這樣覺得,小時候真的很辛苦。我好喜歡讀書,但阿公阿嬤覺得女生不用讀那麼高啦,趕快出來幫忙家裡比較實際。家裡有好多事要幫忙,他們每天都一早出去工作,我凌晨就要起床,天還沒亮,抱著整袋衣服和工具,騎腳踏車穿越一整片樹林,啊路燈也不多喔,很黑,自己一個人到河邊洗衣服。每次都好怕沿路有人跟蹤我,還是河邊有什麼東西跑出來,欸,我一個女生在那邊洗衣服,很恐怖。」
媽媽邊留著眼淚,邊笑著回顧這些往事,我們抽了面紙給她,她擦了臉上的淚水,忍不住笑了一下,我和妹妹也含淚看著她笑了。
「洗完衣服回到家,我就要趕快煮飯煮菜喔,因為要叫你們阿姨和舅舅起床上學,讓他們可以吃早餐。有幾次太晚回來煮飯,被妳外婆抓到,我就被打被罵,帶著瘀青的小腿去學校。以前真的重男輕女,你舅舅不愛念書,很會打扮也很會玩,阿公阿嬤還是對他最好,啊也不會逼你舅舅去工作,只因算命師說舅舅和阿姨都很聰明不用擔心。換作我,只要事情做錯就挨罵、被打。國三的時候我終於轉到最好的升學班,還一直被阻止念高中,好奇怪耶。」
那時候才知道,為什麼媽在我們都上幼稚園後,堅持去考高職夜校。念完高中,一直是她小小的夢想。「你們爸爸也是很好啦,很支持我去上學,而且媽媽很爭氣,全校第二名畢業喔。」
回想起來是有一段時間,傍晚幼稚園下了課就被帶去爸爸的莿桐老家給阿公阿嬤帶。吃完阿嬤煮的晚餐,陪阿公看新聞和他最愛的《大陸尋奇》,或是跟住在附近的堂哥堂姊玩,等十點多媽媽下課來接我們回家。回家洗完澡,最常看到的就是媽專心趴在床上念書複習筆記的背影。那個背影,給我的力量超乎想像。
高三學測後,考上靜宜大學觀光學系,那時開心地離家,卻也突然意識到好多事情得開始自己面對。那時戲劇系面試後落榜,下定決心好好念觀光,給自己許多壓力,無論是生活、人際、課業或各類活動,參加啦啦隊、參與活動主持、實習當領隊賺錢,也經歷了不敢說的初戀。後來給了自己更多期許,卻無法放下戲劇的夢想,跑到新竹參加面試而錄取了劇團的儲備演員,開始東奔西跑,邊念書邊揹著大小道具演出的日子,那時只能尋求家裡經濟上更多的協助,爸的不諒解也加深了心理上的沉重感,尤其大二上學期偷偷休學,決定轉考戲劇系的那段時間。
對家人,我總是報喜不報憂。直到有天走在往學校餐廳的路上,伴著即將爆發的情緒,望著手機許久撥給了媽。種種壓力和隱瞞,在聽到媽的聲音那一刻,眼淚直接衝了下來。「媽媽,我……我覺得好累。」試圖讓哽咽斷續的聲音,顯得堅強些。媽沉默了幾秒,溫柔地要我加油,告訴我,想休息的時候就要休息。好多事情不敢說,無論是感情狀態、偷偷休學的事、在劇團排練演出的壓力等等。調適好情緒,沉默了一陣子,最後只鼓起勇氣告訴她,我休學了。她沒多說什麼,繼續為我打氣,要我找一天回家。
通話結束後,我快步走到無人角落,蹲坐下來好好哭一場。那時我想到媽的背影,在髮廊忙完一整天,夜校下課回家後還要照顧兩個小孩,繼續讀書到半夜的,那個美麗又堅強的背影。
整個夜晚,我、妹妹和媽,哭笑著聊到凌晨,才肯互道晚安,一旁爸的打呼聲也陪伴著我們。我到現在都還沒跟媽說過,那些夜晚的她的背影,在我感到無助、無力或挫折時,始終給我好大的力量。她帶給我們的,不僅是一種堅毅,還有一分我和妹妹都遺傳到她的給人鼓舞又溫暖的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