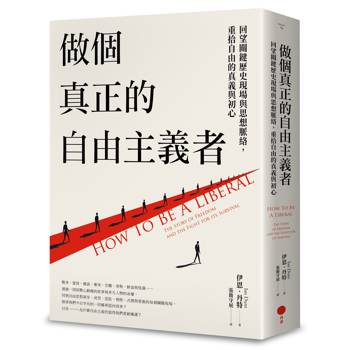一、誕生(部分摘錄)
為了寫他的第一本書《世界論》(The World),笛卡兒在一六三〇年到一六三三年間獨自隱居於阿姆斯特丹。他在開頭的句子中寫道:「我打算在本書中探討光,我想清楚指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對光的知覺可能與物體中使我們產生該知覺的本質不同。」
很難想像必須有人特地指出,光和我們對光的感知其實不同。我們知道周圍有光,不過我們必須仰賴人體的視覺和心理器官(即眼睛和大腦)轉化光的現象,我們才能產生感知。但在笛卡兒的年代,對世界的正統觀點完全以人為中心。當時的人認為,物體本身就具有人眼所看見的特質,例如血液本身就具備「紅色」的特性,火具有「熱」的特色。
笛卡兒的論點完全相反,他認為物體獨立存在於我們對物體的感受之外。我們的感知器官並未向我們呈現世界的真正樣貌,只是傳達物體帶給我們的感受。
他在努力挖掘對世界的深層體會。從他提出這個想法之後,科學便隨之興起。如果你不信任感官帶來的感覺,你必須建構假設,對事情的可能樣貌提出一套說法,接著你必須測試假設,過程中你會需要運用工具,補足感官不足之處。當你這麼做的時候,等於在從事科學了。
如同哥白尼將人類從太空的中心移走,笛卡兒則是除去人類在現實世界的中心地位。以前神父和古希臘人透過撫慰人心的話語建構起一個確切篤定的世界,這個世界突然間變得陌生,腳下的土地變得神祕難解。
笛卡兒一向堅稱這個想法與教會的主張不謀而合,但事實上,他提出的思想極具革命意義,其中的意涵可能會徹底推翻傳統權威結構。
一旦讀者認同感官不是他們認識世界的可靠管道,笛卡兒便開始追問萬物究竟是如何運作。他以火為主要例子。中世紀的人普遍認為火具有「火」的外形、「熱」的特性,以及「燃燒」的動作。笛卡兒不採信這個觀點,反而認定「與木頭交纏的火焰本體是由許多微小的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個別閃爍,互不牽連,且閃動的動作極為快速、猛烈。」
這些他稱為「小體」(corpuscle)的部份「小到人眼無法辨識」。這就是原子理論最早的雛型。
這是笛卡兒第二個偉大的見解:對物質的解釋仰賴於根本上可以透過數學來表示的微結構特質。他不僅描繪了科學革命的初始輪廓,更朝科學革命的初步成果邁出一大步。他用書中一開頭的十三個段落就達成這個創舉。
就在他即將完稿前夕,笛卡兒耳聞伽利略的遭遇。那簡直是場災難。笛卡兒的物理原則明顯與伽利略的主張相互呼應,與地動說一樣已正式成為異端邪說。就在他準備寄出完成的手稿公開發表之前,他決定先暫緩出版。
「我已決定絕口不提,」他告訴梅森,「四年來的心血幾乎全部都付諸流水」。
♦
笛卡兒著實飽受驚嚇。他在千鈞一髮之際決定不出版作品,才躲過淪為階下囚的命運,免於遭受宗教權威質問。荷蘭的風氣已經比義大利或西班牙更包容,但他所做的事還是猶如在玩火,這點他心知肚明。
他一時之間變得極度謹慎,時常煩惱教會用什麼態度看待他的著作。有時他忍氣吞聲,有時則試著先發制人,大肆抨擊默默無聞的評論家,藉此迴避批評。他的寫作時間逐漸被一連串神學爭辯所占據,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捲入與耶穌會學院的長期論戰。荷蘭喀爾文教派神學家吉斯伯圖斯.沃修斯(Gisbertus Voetius)託人寫了長篇大論大力抨擊笛卡兒,直指他「處心積慮地偷偷將無神論的毒液注射到人們體內,人們因為心靈軟弱而從未發現躲在草叢中的毒蛇」。真正危險的時候,世人甚至把他與盧西利歐.瓦尼尼(Lucilio Vanini)相提並論,這位義大利無神論者在土魯斯慘遭割舌、絞殺和火燒等酷刑。
長久以來,笛卡兒始終以他的觀點試著說服世人,但猶如在打一場毫無勝算的仗。真正的情況是,他的整個世界觀、對錯誤感官認知的說法,以及優先從機械論的角度解釋物理現象的做法,在在挑戰教會的權威。
因此他起心動念,決定將所有神學的爭論拋諸腦後,專心探索真正重要的事。他要表達上帝確定是百分之百存在,這麼一來,他就能防止自己被貼上異教徒或無神論者的標籤,從爭議中獲得釋放,進而可以更廣泛地繼續他從質疑的角度探究世間萬物的研究,不必時時戒慎恐懼。
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很嚴重的誤判。笛卡兒太擅長解析,暴露事物的內在瑕疵。重點轉移到上帝後,他最終破解了人類知識的整體組成,最糟的是,他是在不經意間做到了這點。
一六三七年,笛卡兒終於出版第一本書。這本書共有三篇分別探討光學、幾何學和氣象學的論文,並附上一篇隨筆《談談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作為導讀。現在幾乎沒人記得這三篇論文,但《談談方法》成了西方哲學的準則。這是他首次展現自己有系統地質疑萬事萬物的嚴謹態度,一種面對任何問題都能堅定不移的批判精神。
這套方法分成四個步驟。第一步,將肯定的事實從可能有所質疑的部分中分離出來。第二步,將留下來的問題分解成更小的單位。第三步,從簡單的問題開始逐一解決。最後,檢查整個過程,評估是否有任何遺漏之處。
以現代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問題解決流程。但在當時,這是極具顛覆性的探究方式,不管笛卡兒如何費盡心思地修飾,還是難掩其本質。這個方法暗示現實可供人類智力任意探索。任何人想要認真思考,都能自行評估其所掌握的證據。除非權威能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給予任何助益(大部分情況下都沒有),否則沒有權威介入的空間。
笛卡兒在書中小心地保護自己。他匿名出版《談談方法》,並在書中安插名為「實踐此方法應依循的道德準則」的篇章,明確將信仰和國家法律從適用範疇中排除。他清楚指出,大部分人應該都無法正當地運用該方法。
還有一個重要的保護措施。他在書中刻意試圖說明,他看待其他萬事萬物的質疑態度,不可能應用於上帝。他確切指出三件事情不在懷疑論的討論範圍:他本人存在與否、理性和上帝。
可惜沒用。這段文字的篇幅簡短,語氣勉強,引發了更多疑問。幾乎可以確定,這段文字並未在他對上帝的信仰和以懷疑為基礎的探究精神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
這讓笛卡兒落入危險處境。儘管書是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作者。任何想追捕他的神學家(當時的確有好幾位)都能聲稱,他認同上帝的論述孱弱無力,其實是在試圖散播無神論。
因此他下了一個攸關命運的決定。他決心正面處理問題。他要寫另一本書,確實證明他的質疑精神並非對上帝的威脅。
他會在書中拆解並駁斥惡魔理論之類的懷疑論述,該理論暗示人類一無所知。他會以絕對肯定的態度確立上帝存在的事實。之後,他就能探討那些他真正感興趣的問題。
其實笛卡兒不樂見自己走到這一步。為了駁倒懷疑論,他必須說明其中的論述,而這麼做相當危險。
「我不敢這麼做,因為我將必須詳盡解釋懷疑論者最強而有力的論述。」他在一六三七年五月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擔心這樣的澄清看起來會像是要介紹懷疑論者的觀點,進而擾亂軟弱的心靈。」
因此,笛卡兒捨棄他的母語法文,改以拉丁文寫作。這麼做可以增加他在世界各國學識飽滿的讀者,同時讓缺乏教育的一般人無法閱讀,這樣他就可以說自己已努力保護一般人免受過於狂熱的思想所影響。
但還不夠。笛卡兒的如意算盤並未實現,這本書帶來的影響比他做過最可怕的惡夢還驚人。不僅心靈不夠強大的人認識了懷疑論的概念,書中對懷疑論的描述生動逼真,扣人心弦,後世反而認定他就是這些論點的代言人,殊不知他當時其實是要企圖駁斥這些論點。
♦
這本書叫《沉思錄》(The Meditations)。笛卡兒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了這本書。敘事者有點像是他本人的綜合體,坐在房間內的火爐旁,質疑著世上的一切。
他要篩選所有他認定為真的事物,判斷自己能否真正加以證明。如果沒辦法做到,就要捨棄原本的認知。
他不必檢查每一件相信的事情,這會花太多時間。他只需要檢視基礎信念即可。如果基礎信念有誤,建構於其上的概念就會倒塌崩解。
所以他從自己的感官開始檢驗。「我怎麼可能否定我擁有這雙手和軀體?」他問自己。但他可以,因為睡著時,他同樣確定夢是真的,然而事實上是假的。
「沒有什麼毫無疑問的標記可以區分清醒和睡著的狀態。」他說,「我大感驚訝,而在震驚的情緒中,我幾乎就要相信自己正在做夢。」
做夢讓實體世界中所有確定的事物變得不再可信。在夢中,醫學、物理學、天文學全都不可靠。不過,我們透過思考賦予意義、不依存於物理現實的那些概念,像是數學或幾何學,則為例外,畢竟二加二等於四不會因為你清醒或做夢而改變。
但就連這點,笛卡兒也無法確定了。他再度擔心會有萬能的惡魔欺騙他。惡魔也許已在我們心中植入對數學和幾何學的錯誤想法,二加二或許其實等於五。
這麼一想,萬物萬事便無一禁得起質疑,甚至連我們自己的想法也是。「天空、空氣、大地、顏色、外形、聲音和外在的一切,都與夢的假象無異,惡魔已然設下圈套,就等著我輕易受騙。」笛卡兒寫道。
他感到迷惘。「我突然落入深水之中,如此焦慮不安,想要穩穩地站在水底,抑或游在靠近水面的地方,好讓自己活命,都無法辦到。」一切都不牢靠。「還有什麼可以視為真實?」他問起。「沒有什麼可以百分之百篤定,或許只能這麼相信了。」
這是思想史上舊世界滅亡的確切時刻。
在一片廢墟中,笛卡兒開始四處搜索,就算只找到一小塊無懈可擊的真實,可以讓他開始重新拼湊起世界都好。「只要夠幸運發現一樣完全真確、不容置疑的事物,我就有資格懷抱最高的期待。」他說。
然後,他找到了通往真實的途徑:自己。
只因一個念頭:如果我受到蒙蔽,一定有個受到蒙蔽的我。這證明了我存在。
除了你本身以外,一切都能從你身上奪走。你可以質疑一切,但無法懷疑「你在質疑」這件事,因此你必定存在。「每當我開口表達或心中想起,此陳述──我質疑,我存在──必定為真。」
以拉丁文表示則為: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
這大概是整個西方哲學中最知名的一句話。這也是人類史上最優美的見解,這並非誇飾。唯一你可以毫不質疑、萬分確定為真的見解,非此莫屬。沒有其他見解比得上。這句話還能自我證明,靠著其隱含的意義反覆循環自證。這是無庸置疑的封閉系統。
笛卡兒摧毀了整座偉大的知識宮殿,找到唯一可以確定為真的,正是個體。
但不只這樣。「我思」還包含其他意涵,彷彿有個隱而不見的夥伴。個體並非白板(blank slate),而是具備明確的特徵。個體會思考。唯有透過思考,個體才知道自己存在。
「我是真正的實體,真實存在,但是什麼呢?」笛卡兒自問。「會思考的實體。」具有心智,具有理解力,換言之,具有理性。
這是自由主義誕生的時刻。
這麼說似乎有點奇怪。大多數人不會把笛卡兒歸類為自由主義者,他的著作甚至無關政治。在世人眼中,德國倫理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之類的其他重要思想家才是自由主義的先驅。但在這裡,自由主義的基本元件──完全出乎意外──突然運轉了起來。個體的存在事實取代了教會和國家老舊過時的教條。
然而,誕生的不只有自由主義。沒有思考就無法證實「我在」,沒有「我在」也無法發生思考。
自由主義和理性就像雙胞胎般降生於世間。
為了寫他的第一本書《世界論》(The World),笛卡兒在一六三〇年到一六三三年間獨自隱居於阿姆斯特丹。他在開頭的句子中寫道:「我打算在本書中探討光,我想清楚指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對光的知覺可能與物體中使我們產生該知覺的本質不同。」
很難想像必須有人特地指出,光和我們對光的感知其實不同。我們知道周圍有光,不過我們必須仰賴人體的視覺和心理器官(即眼睛和大腦)轉化光的現象,我們才能產生感知。但在笛卡兒的年代,對世界的正統觀點完全以人為中心。當時的人認為,物體本身就具有人眼所看見的特質,例如血液本身就具備「紅色」的特性,火具有「熱」的特色。
笛卡兒的論點完全相反,他認為物體獨立存在於我們對物體的感受之外。我們的感知器官並未向我們呈現世界的真正樣貌,只是傳達物體帶給我們的感受。
他在努力挖掘對世界的深層體會。從他提出這個想法之後,科學便隨之興起。如果你不信任感官帶來的感覺,你必須建構假設,對事情的可能樣貌提出一套說法,接著你必須測試假設,過程中你會需要運用工具,補足感官不足之處。當你這麼做的時候,等於在從事科學了。
如同哥白尼將人類從太空的中心移走,笛卡兒則是除去人類在現實世界的中心地位。以前神父和古希臘人透過撫慰人心的話語建構起一個確切篤定的世界,這個世界突然間變得陌生,腳下的土地變得神祕難解。
笛卡兒一向堅稱這個想法與教會的主張不謀而合,但事實上,他提出的思想極具革命意義,其中的意涵可能會徹底推翻傳統權威結構。
一旦讀者認同感官不是他們認識世界的可靠管道,笛卡兒便開始追問萬物究竟是如何運作。他以火為主要例子。中世紀的人普遍認為火具有「火」的外形、「熱」的特性,以及「燃燒」的動作。笛卡兒不採信這個觀點,反而認定「與木頭交纏的火焰本體是由許多微小的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個別閃爍,互不牽連,且閃動的動作極為快速、猛烈。」
這些他稱為「小體」(corpuscle)的部份「小到人眼無法辨識」。這就是原子理論最早的雛型。
這是笛卡兒第二個偉大的見解:對物質的解釋仰賴於根本上可以透過數學來表示的微結構特質。他不僅描繪了科學革命的初始輪廓,更朝科學革命的初步成果邁出一大步。他用書中一開頭的十三個段落就達成這個創舉。
就在他即將完稿前夕,笛卡兒耳聞伽利略的遭遇。那簡直是場災難。笛卡兒的物理原則明顯與伽利略的主張相互呼應,與地動說一樣已正式成為異端邪說。就在他準備寄出完成的手稿公開發表之前,他決定先暫緩出版。
「我已決定絕口不提,」他告訴梅森,「四年來的心血幾乎全部都付諸流水」。
♦
笛卡兒著實飽受驚嚇。他在千鈞一髮之際決定不出版作品,才躲過淪為階下囚的命運,免於遭受宗教權威質問。荷蘭的風氣已經比義大利或西班牙更包容,但他所做的事還是猶如在玩火,這點他心知肚明。
他一時之間變得極度謹慎,時常煩惱教會用什麼態度看待他的著作。有時他忍氣吞聲,有時則試著先發制人,大肆抨擊默默無聞的評論家,藉此迴避批評。他的寫作時間逐漸被一連串神學爭辯所占據,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捲入與耶穌會學院的長期論戰。荷蘭喀爾文教派神學家吉斯伯圖斯.沃修斯(Gisbertus Voetius)託人寫了長篇大論大力抨擊笛卡兒,直指他「處心積慮地偷偷將無神論的毒液注射到人們體內,人們因為心靈軟弱而從未發現躲在草叢中的毒蛇」。真正危險的時候,世人甚至把他與盧西利歐.瓦尼尼(Lucilio Vanini)相提並論,這位義大利無神論者在土魯斯慘遭割舌、絞殺和火燒等酷刑。
長久以來,笛卡兒始終以他的觀點試著說服世人,但猶如在打一場毫無勝算的仗。真正的情況是,他的整個世界觀、對錯誤感官認知的說法,以及優先從機械論的角度解釋物理現象的做法,在在挑戰教會的權威。
因此他起心動念,決定將所有神學的爭論拋諸腦後,專心探索真正重要的事。他要表達上帝確定是百分之百存在,這麼一來,他就能防止自己被貼上異教徒或無神論者的標籤,從爭議中獲得釋放,進而可以更廣泛地繼續他從質疑的角度探究世間萬物的研究,不必時時戒慎恐懼。
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很嚴重的誤判。笛卡兒太擅長解析,暴露事物的內在瑕疵。重點轉移到上帝後,他最終破解了人類知識的整體組成,最糟的是,他是在不經意間做到了這點。
一六三七年,笛卡兒終於出版第一本書。這本書共有三篇分別探討光學、幾何學和氣象學的論文,並附上一篇隨筆《談談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作為導讀。現在幾乎沒人記得這三篇論文,但《談談方法》成了西方哲學的準則。這是他首次展現自己有系統地質疑萬事萬物的嚴謹態度,一種面對任何問題都能堅定不移的批判精神。
這套方法分成四個步驟。第一步,將肯定的事實從可能有所質疑的部分中分離出來。第二步,將留下來的問題分解成更小的單位。第三步,從簡單的問題開始逐一解決。最後,檢查整個過程,評估是否有任何遺漏之處。
以現代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問題解決流程。但在當時,這是極具顛覆性的探究方式,不管笛卡兒如何費盡心思地修飾,還是難掩其本質。這個方法暗示現實可供人類智力任意探索。任何人想要認真思考,都能自行評估其所掌握的證據。除非權威能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給予任何助益(大部分情況下都沒有),否則沒有權威介入的空間。
笛卡兒在書中小心地保護自己。他匿名出版《談談方法》,並在書中安插名為「實踐此方法應依循的道德準則」的篇章,明確將信仰和國家法律從適用範疇中排除。他清楚指出,大部分人應該都無法正當地運用該方法。
還有一個重要的保護措施。他在書中刻意試圖說明,他看待其他萬事萬物的質疑態度,不可能應用於上帝。他確切指出三件事情不在懷疑論的討論範圍:他本人存在與否、理性和上帝。
可惜沒用。這段文字的篇幅簡短,語氣勉強,引發了更多疑問。幾乎可以確定,這段文字並未在他對上帝的信仰和以懷疑為基礎的探究精神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
這讓笛卡兒落入危險處境。儘管書是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作者。任何想追捕他的神學家(當時的確有好幾位)都能聲稱,他認同上帝的論述孱弱無力,其實是在試圖散播無神論。
因此他下了一個攸關命運的決定。他決心正面處理問題。他要寫另一本書,確實證明他的質疑精神並非對上帝的威脅。
他會在書中拆解並駁斥惡魔理論之類的懷疑論述,該理論暗示人類一無所知。他會以絕對肯定的態度確立上帝存在的事實。之後,他就能探討那些他真正感興趣的問題。
其實笛卡兒不樂見自己走到這一步。為了駁倒懷疑論,他必須說明其中的論述,而這麼做相當危險。
「我不敢這麼做,因為我將必須詳盡解釋懷疑論者最強而有力的論述。」他在一六三七年五月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擔心這樣的澄清看起來會像是要介紹懷疑論者的觀點,進而擾亂軟弱的心靈。」
因此,笛卡兒捨棄他的母語法文,改以拉丁文寫作。這麼做可以增加他在世界各國學識飽滿的讀者,同時讓缺乏教育的一般人無法閱讀,這樣他就可以說自己已努力保護一般人免受過於狂熱的思想所影響。
但還不夠。笛卡兒的如意算盤並未實現,這本書帶來的影響比他做過最可怕的惡夢還驚人。不僅心靈不夠強大的人認識了懷疑論的概念,書中對懷疑論的描述生動逼真,扣人心弦,後世反而認定他就是這些論點的代言人,殊不知他當時其實是要企圖駁斥這些論點。
♦
這本書叫《沉思錄》(The Meditations)。笛卡兒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了這本書。敘事者有點像是他本人的綜合體,坐在房間內的火爐旁,質疑著世上的一切。
他要篩選所有他認定為真的事物,判斷自己能否真正加以證明。如果沒辦法做到,就要捨棄原本的認知。
他不必檢查每一件相信的事情,這會花太多時間。他只需要檢視基礎信念即可。如果基礎信念有誤,建構於其上的概念就會倒塌崩解。
所以他從自己的感官開始檢驗。「我怎麼可能否定我擁有這雙手和軀體?」他問自己。但他可以,因為睡著時,他同樣確定夢是真的,然而事實上是假的。
「沒有什麼毫無疑問的標記可以區分清醒和睡著的狀態。」他說,「我大感驚訝,而在震驚的情緒中,我幾乎就要相信自己正在做夢。」
做夢讓實體世界中所有確定的事物變得不再可信。在夢中,醫學、物理學、天文學全都不可靠。不過,我們透過思考賦予意義、不依存於物理現實的那些概念,像是數學或幾何學,則為例外,畢竟二加二等於四不會因為你清醒或做夢而改變。
但就連這點,笛卡兒也無法確定了。他再度擔心會有萬能的惡魔欺騙他。惡魔也許已在我們心中植入對數學和幾何學的錯誤想法,二加二或許其實等於五。
這麼一想,萬物萬事便無一禁得起質疑,甚至連我們自己的想法也是。「天空、空氣、大地、顏色、外形、聲音和外在的一切,都與夢的假象無異,惡魔已然設下圈套,就等著我輕易受騙。」笛卡兒寫道。
他感到迷惘。「我突然落入深水之中,如此焦慮不安,想要穩穩地站在水底,抑或游在靠近水面的地方,好讓自己活命,都無法辦到。」一切都不牢靠。「還有什麼可以視為真實?」他問起。「沒有什麼可以百分之百篤定,或許只能這麼相信了。」
這是思想史上舊世界滅亡的確切時刻。
在一片廢墟中,笛卡兒開始四處搜索,就算只找到一小塊無懈可擊的真實,可以讓他開始重新拼湊起世界都好。「只要夠幸運發現一樣完全真確、不容置疑的事物,我就有資格懷抱最高的期待。」他說。
然後,他找到了通往真實的途徑:自己。
只因一個念頭:如果我受到蒙蔽,一定有個受到蒙蔽的我。這證明了我存在。
除了你本身以外,一切都能從你身上奪走。你可以質疑一切,但無法懷疑「你在質疑」這件事,因此你必定存在。「每當我開口表達或心中想起,此陳述──我質疑,我存在──必定為真。」
以拉丁文表示則為: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
這大概是整個西方哲學中最知名的一句話。這也是人類史上最優美的見解,這並非誇飾。唯一你可以毫不質疑、萬分確定為真的見解,非此莫屬。沒有其他見解比得上。這句話還能自我證明,靠著其隱含的意義反覆循環自證。這是無庸置疑的封閉系統。
笛卡兒摧毀了整座偉大的知識宮殿,找到唯一可以確定為真的,正是個體。
但不只這樣。「我思」還包含其他意涵,彷彿有個隱而不見的夥伴。個體並非白板(blank slate),而是具備明確的特徵。個體會思考。唯有透過思考,個體才知道自己存在。
「我是真正的實體,真實存在,但是什麼呢?」笛卡兒自問。「會思考的實體。」具有心智,具有理解力,換言之,具有理性。
這是自由主義誕生的時刻。
這麼說似乎有點奇怪。大多數人不會把笛卡兒歸類為自由主義者,他的著作甚至無關政治。在世人眼中,德國倫理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之類的其他重要思想家才是自由主義的先驅。但在這裡,自由主義的基本元件──完全出乎意外──突然運轉了起來。個體的存在事實取代了教會和國家老舊過時的教條。
然而,誕生的不只有自由主義。沒有思考就無法證實「我在」,沒有「我在」也無法發生思考。
自由主義和理性就像雙胞胎般降生於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