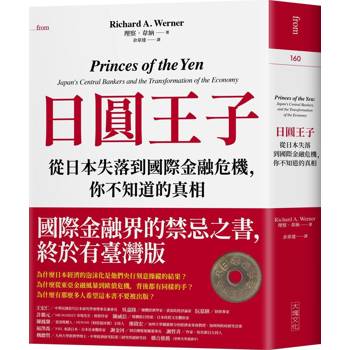二○○三年英文版序(節錄)
二○○一年一月,某個歐洲國家的駐日本大使向我分享他在東京官邸舉辦跨年派對時的趣事。賓客之中有位來自日本大藏省的高階官員。大多數賓客都興高采烈。他們期待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人人暢飲著香檳,派對氣氛十分熱烈。但並非所有人都開心。
「我注意到,」這位大使告訴我,「當午夜時分漸近,這位男士看起來越來越憂愁。他來自大藏省,神情相當沮喪。我很納悶發生了什麼事。我認為這情況很不尋常。最後,當午夜鐘聲響起,他走向我,以極為哀傷的語氣說:
『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您是什麼意思?』我問他。
『我們失去了名字,』他回答道。『結束了⋯⋯從二○○一年一月起,大藏省就不復存在了。』
我試著安慰他:『但是,那不過只是個名字而已。您不必太在意一個名字。這個部門依然存在。你們仍有權力與影響力。』
但他說:『他們要是至少留下我們的名字也好⋯⋯他們已經奪走了我們的權力。如今一切都沒了⋯⋯可他們竟然連我們的名字也要奪走⋯⋯』他無奈地搖著頭。」
對許多英語人士而言,舊有的大藏省就只是財務省的代稱,他們並未察覺到在二○○一年一月,一段悠久輝煌的歷史就此驟然落幕。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至少就法律上來說,大藏省一直是日本最具權力的機構。這個隆重而古老的名稱,更精確的翻譯應該是「大倉庫省」或「大寶庫省」,因為其歷史可追溯到仍是以實物賦稅的時代,當時該部門確實是負責儲存來自全國各地稻米的倉庫。
結構改革
民眾對大藏省的沒落並不感到惋惜。人們普遍認為,大藏省應為日本現代承平時期中最嚴重的經濟管理疏失負責:他們造就了一九八○年代的泡沫經濟,以及隨之而來在一九九○年代的長期衰退。
這場經濟衰退使得社會大眾認定,由當今官僚體制所領導的日本舊有經濟體制已不再有用,因此必須徹底改革。現在大多數的評論家都主張政府「迫切需要」推行結構改革。首相小泉純一郎最常重複的口號就是:「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景氣復甦。」日行的資深官員幾乎每天都在呼籲對結構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這些聲音認為,自由化、解除管制和民營化,也就是說引進美式資本主義,是日本經濟復甦的必要條件。
但真的有必要放棄日式資本主義嗎?若只考量一九九○年代日本經濟的慘澹表現,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奇怪的是,一九八○年代的日本經濟體制更為封閉、有更多的卡特爾(cartel)且有更多管制,但當時卻沒有人抱怨經濟成長太慢。一九五○年代或一九六○年代也是同樣如此,當時幾乎完全遭受聯合壟斷的經濟體制實現了兩位數的成長。此外,美國經濟本身仍會遭受景氣週期與衰退的影響。因此,相同的經濟結構似乎可能帶來高成長或低成長的結果,而成長的表現也得取決於其他因素。本書的看法是,日本的衰退確實是由驅動景氣週期的主要力量—貨幣所造成。而主張結構改革的人士恰好就是那些掌控日本貨幣的人,這絕非純屬巧合。
抗命的日本銀行
日本央行一直公然反抗政府、大藏大臣和首相的呼籲:他們要求創造更多貨幣來刺激經濟並結束長期的衰退。在幾個關鍵時刻,如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五年初,以及一九九九年的大多數時間裡,日本銀行甚至主動減少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數量。這個作法使得購買力萎縮、國內需求降低,讓政府干預貨幣的政策失效,並使日圓走強,進而使原先可能的復甦胎死腹中。由於沒有獲得足夠的貨幣政策支持,政府不得不仰賴財政政策。這些財政政策不僅沒效,反而形成工業國家中規模最龐大的國債。
一九九○年代的最大謎團就在於,儘管有創紀錄的失業率和通縮程度,日本銀行為何未能進一步擴大貨幣數量,從而創造經濟復甦、降低通縮並穩定就業。有時候,懼怕通膨被視為這個謎團的答案。但日本在一九九○年代前半期歷經了通膨率的急遽下降,後半期則出現明顯的通縮。當物價上漲且出現通膨時,我們會知道貨幣政策過於寬鬆且創造了太多貨幣。此時央行會需要收緊貨幣政策。當物價下跌且出現通縮時,央行有責任創造更大的購買力。一般而言,央行的職責是創造足夠的貨幣,使實際成長率接近潛在成長率,從而避免通膨和通縮。
既然通膨的問題顯而易見,日本銀行早已承認對通膨的恐懼,並非他們採取謹慎立場的原因。反而是日本銀行多年來持續表示自己正在努力刺激經濟,並指出自己已將利率降至零。但它宣稱,問題一直是市場缺乏對貨幣的需求。可是,顯然全世界貨幣需求最大的國家正是日本。首先,政府部門需要創紀錄的貨幣數量來資助其財政支出。其次,身為日本民眾主要僱主的眾多中小企業也希望借入貨幣。但背負呆帳的銀行只願意借款給規模較大、風險較低的借款人。這就是為何央行需要介入並替代這些銀行放款。
有時日本銀行聲稱它已向經濟體注入大量資金。但它主要是將資金注入只有銀行才能進入的極狹義貨幣市場。在其他時候,央行發言人以「通縮是因為合意的結構改革所致,因此是好事」,來回應社會對通縮的擔憂。但如果這些結構改革確實提高了日本經濟的生產力,這將提高日本的潛在成長率,並加大與實際成長率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央行將需要創造更多的貨幣以減少通縮缺口。
央行官員的最新論點(顯然這看法也得到首相和經濟與財政大臣的支持)是日本的「過剩產能」太多。事實的確如此,有另一種說法是總供給大於總需求。但他們卻未從中得出應該刺激需求的合理結論—這是央行可以輕易做到的—而是建議透過讓公司倒閉來限制供給。這讓人想起日本、德國和美國某些大蕭條時期政治家的失敗政策:這種「過剩產能」據說導致了「過度競爭」,必須透過使公司破產來處理這問題。諷刺的是,提出這般論點的評論家也正是那些主張日本需要更大力解除管制的人,因為他們認為日本「缺乏競爭」。
他們的手法很明確:雖然日本銀行的論點不斷變化(且在遭到反駁時很快就改變),但它們總是得出相同的結論,即央行的貨幣政策是恰當的,問題出在日本的經濟結構。
日本銀行本可伸出援手,卻未曾出手
一般而言,貨幣是由銀行所創造。正因為銀行不願放款,央行才需要直接向經濟體注入更多資金。央行因此將扮演國家銀行的角色—其他央行過去曾這麼做,事實上,日本銀行在一九四五年後也是如此,當時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狀況比一九九○年代更加嚴峻。這項政策在一九四五年後相當成功,信用很快就恢復成長,經濟也蓬勃發展。但在一九九○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日本銀行卻未採取這些經過驗證的政策,也未能創造足夠的貨幣來支持經濟持續復甦。此外,它也拒絕向最需要資金的政府和中小企業放款。日本銀行其實有能力在不造成自身、納稅人或整體社會任何成本的情況下,消除銀行體制裡山一般高的呆帳。然而它卻選擇袖手旁觀。為什麼?
人們很自然會先提出「無能假說」。「無能」確實能夠解釋這場戲的部分參與者的作為。舉例來說,大藏省和一九九○年代的政府高層其實只要改變籌措財政支出的方式就能創造復甦。他們本可以不用發行債券向民眾借款—這樣做會從經濟體抽走資金—而是利用向銀行的直接貸款契約來籌措公部門的借款需求。當銀行放款時,它們可以憑空創造出貨幣,不需要從經濟體的其他部分抽走資金。如此一來,財政政策就不會如實際發生的那樣,對民間部門的活動造成等量的排擠效應。如果他們能完全理解這概念,我相信他們會採用這個方法來創造經濟復甦。然而,日本、歐洲或美國的經濟學家卻少有人知道這套機制。
更明顯且廣為人知的機制是那種連初階經濟學課本都會提到的:即使在銀行破產的情況下,央行也可以透過增加購買資產(包括政府債券),直接向經濟體注入資金。然而日本央行多年來一直忽視這套機制的存在—難道真的只是因為無能?我越深入研究這些議題及其歷史,就越清楚地發現日本銀行的高層其實非常熟悉日本的困境以及對應的解方。在過去幾次因信用緊縮而導致的衰退中(例如一九六○年代的景氣低迷),央行就增加了對公司部門和政府的放款。即使在今天,央行仍有許多工具可用來達成這個目標。舉幾個例子來說,它可以購買公司發行的債券、借款給政府、購買更多債券、買入不動產並將其改建為公園,或者直接印鈔票分給每位國民。在所有情境裡,購買力都會增加,需求也會受到刺激。印鈔可能也會使日圓貶值,這對出口有利。
這麼做並不會導致通膨:因為衰退的問題和原因正是缺乏貨幣,進而導致通縮。
在一九九○年代的任何時候,政府只要擴張央行的信用,就能促成經濟復甦。如果日本銀行願意,日本在整個一九九○年代都可以維持高度成長。
這些都不是什麼太深奧的學問。而且,如今央行官員可以回顧日本銀行或其他處理過相同議題的央行(如德國央行或美國聯準會)的豐富歷史和經驗。因此謎團依然存在:那為什麼日本銀行不創造更多貨幣?
就有關人士的動機來看,一九九○年代的大藏省和來來去去的眾多政府機構,毫無疑問都有創造經濟復甦的動機。承受猛烈批評砲火的大藏省,痛切地意識到長期衰退不僅危及自己位居主導地位的正當性,而這也正是戰後日本經濟架構的根基。而經過仔細審視過後,央行的動機似乎就不那麼明確。
一九九二年,當我在日本銀行擔任訪問研究員時,我發現到信用擴張及信用配置的重要性。我意識到如果央行的施政方向錯誤,日本的衰退會惡化,失業率也會飆升。光靠降息和財政政策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央行創造更多貨幣。但當時央行卻在做相反的事,積極地從經濟體中收回資金。我無法理解這麼做的原因,因而持續詢問好幾名日本銀行的官員,希望得到解答。最後,其中一名央行官員向我解釋:「如果我們印更多鈔票,我們的經濟就能復甦。但那樣做的話什麼都不會改變。日本的結構問題不會獲得解決。」當時我無法相信他的話。日本央行會為了改變經濟結構而刻意延長經濟衰退嗎?推動經濟和社會改革(尤其是規模如此浩大、經濟和人力成本如此龐大,且作法也如此不透明)是否該是央行的工作?到了一九九八年,自殺人數達到戰後新高,許多都是因經濟衰退所致。
日本銀行對於其政策的官方聲明一直充滿矛盾。一方面,央行堅持認為衰退不是因為其政策,而是因為經濟結構所致。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結構改革而不是貨幣刺激,正如其官員一再表示的。然而央行職員(包括總裁)也表示他們不想刺激經濟(這也間接承認他們有能力這麼做),因為這會推遲「急需的」結構改革。央行職員甚至主張,大規模的貨幣寬鬆「可能會造成傷害」,因為「更加延遲結構調整的進展」。因此,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波森(Adam Posen)得出結論:「透過消去法和仔細閱讀日銀政策委員會成員的聲明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促進日本經濟結構改革的願望,是該行表面消極但實則刻意地容忍通縮的主要動機。」
如果讀者和我在一九九○年代初一樣對日本經濟充滿懷疑,那麼確實會很難接受這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