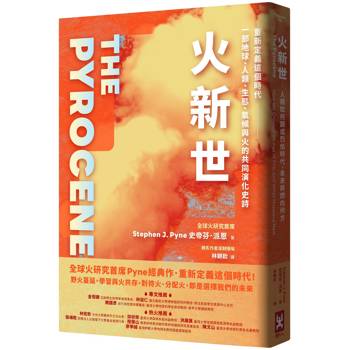序章 地球三重火
‧火,似乎無所不在
那些慣常遭野火肆虐之地——澳洲、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俄羅斯西伯利亞——正以史詩級的廣度與烈度燃燒。2009年澳洲的「黑色星期六」曾為單場野火立下歷史尺規;其後2019至2020年的「黑色夏季」大火,則刷新了澳洲火季燃燒紀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連續焚城中熬過了第4個年頭(2020年),每一季烈焰均超越前一年的極限,如同瘟疫蔓延,大火侵入俄勒岡州與華盛頓州,繼而翻越大陸分水嶺,將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夷為焦土。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野火向北吞噬故土,甚至竄入北極圈內。
那些本不該燃燒或只該零星起火之地,如今卻陷入燎原之勢,南美洲腹地的潘塔納爾溼地竟遭火噬,亞馬遜雨林迎來20年迄今最兇險的火季。即便未被火焰舔舐之處,亦難逃濃煙之劫,澳洲野火的煙塵環遊了全球,美國西海岸大火的陰霾籠罩了大半個國家,其象徵性震撼與視覺衝擊,堪比1930年代沙塵暴肆虐時的末日圖景。白晝,煙霧遮蔽了次大陸級的遼闊地域;夜晚,火光如星斑點綴沉睡大地,宛如一條火焰星辰匯成的銀河。野火火焰照不到的角落,城市燈火與燃氣火炬依然通明:那是煤炭與天然氣轉化為電能的燃燒之證。於眾多觀察者眼中,它們恰似步步緊逼的末世引信。連格陵蘭島,也燃起了冷焰。
然而,煙與火只是症候,而非癥結。地球的「野火版圖」理應由那些自然演化與人類文明磨合出的火所形塑,如今失衡了。土地以生態退化回應,同時囤積更多可燃物,助長更兇猛的野火。地球的火危機,不僅是那些焚毀荒野、撲向城鎮的野性火,更關乎因刻意撲滅或不再引燃的良性火。地球生物群落的崩解,既因狂火肆虐,也因已馴化火的缺席而分崩離析。2013年「平肖自然保育研究所」評估了美國森林的現狀與未來,集結專家完成〈人新世中的森林保育〉報告,此報告如同一份生態全身斷層掃描,檢視植物、水、空氣、土壤與野生動物的現狀。「火」是唯一貫穿所有領域的關鍵元素,是所有學科的交集點。在這急速變貌的圖景中,火觸及每一環節,它整合了其他一切。若無法正確理解火,便無法理解其餘事物。
地球之火三角的燃燒機制中,除了人類當前與過去的火現象外,還有超越此兩者的第三個面向,那是深層時間封存的化石燃料燃燒的火,這類源自地質紀元的碳基燃料,與現生生物質燃料存在本質差異。人類隨著狂熱情緒的升高,正過度使用化石燃料。其燃燒過程非常複雜,可能包括許多尚未完全理解的化學和物理反應,而人類對這些過程的了解相對有限,其結果不僅影響現在,也會對未來的地質環境產生影響;燃燒所產生的汙染物和溫室氣體,更將在未來的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內,持續影響地球。
工業化將化石燃料轉化為未來地質的碳債務,這種跨越時空的能量置換機制,實質重構了行星尺度的火循環體系。我們不僅將古生代沉積的碳庫搬移至地表釋放,更經由燃燒產物造成氣候回饋與生態連鎖效應,重塑了整個生物圈的燃燒閾值。簡言之,化石燃料的火扮演三種角色,一,促發者:提供能量和動力支持;二,增強者:加強人類對能源的利用效率和規模;三,全球化者:使得火的影響範圍遍及全球。儘管並非所有地方都會被完全控制,但火的存在和影響確實遍布地球。
燃燒活態(living landscapes)與石態地景(lithic landscapes)之間的辯證關係,解釋了地球野火場景中的大多數矛盾。……
‧何謂火新世?
……歷史記錄了三種火,第一種是自然火──自從植物開始在陸地上定居以來,火便隨之出現,化石炭的痕跡可追溯至4.2億年前。第二種火是由人類點燃並促進,由於烹飪的需要,火依賴性已經成為人類基因的一部分,在上次冰河時期結束後的有利條件下,第二種火隨著人類的擴散而逐漸蔓延,這些火與自然火競爭,並擴大了燃燒的範圍,幾乎任何地方──無論是被冰雪覆蓋的區域、無情的沙漠,還是潮溼的熱帶雨林都不缺火。人類點燃的火就像自然火一樣,發生在活態地景中,並受到共同的條件與限制影響。第三種火則在本質上有所不同。……
這三重火相互競爭、互補並謀和諧——形成了一個生態上的三體問題。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它們相互作用的條件發生了變化,曾經的調節器變成了開關,地球的火系統越過了一個頂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這種狀態不易逆轉,曾經良性的火變成了野性的火。地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經歷了眾多野性的火、太少良性的火,以及整體上超限燃燒。不僅僅是火與氣候的間接關係破裂,火也脫離了原有的軌道,人類對於火的總體執行成果壓倒了生態韌性,更甚者為野性火創造了條件,成為火時代,但人類是否能夠適應這個新境尚不明確。
未來看起來如此嚴峻,其可能的軌跡如此陌生,以至於一些觀察者認為過去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他們憂心人類正走向一個沒有敘事與類比的明天,將至的動盪如此巨大且難以想像,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知識弧線已經斷裂。人類即將經歷的時代未有先例,亦無法從累積的智慧中推測。……
第五章 火新世
‧火紀元
……火已臨之地將更繁劇,如美國溼潤的高草原、長葉松林,非洲稀樹草原,巴西熱帶草原,北方林和沼澤地,地中海灌叢和南非石楠灌叢。另外,頻繁地表火影響區域的松樹、橡樹、山核桃樹,以及金合歡樹和相思樹林地,將如冰蓋擴張般迎來更暴烈的火之宰制。火不再是壓力矩陣中的普通變數,而升格為定義生態的元代碼。至於泥炭地、灌叢、有機質土壤等間歇性火域,在火與氣候的共謀下,其火情模態將突破歷史閾值,使易燃生物群系蛻變為火控型燃燒地域。
畏火之地可能淬煉出耐火植群,刀耕火種的催化下,雨林正被改寫成牧場與油棕園。一旦土地烙上焦痕,便會對後續火敞開門戶,反覆灼燒將永久封印生態復原的可能——大地正在切換作業系統。……
‧與火共生之道
幾十年來,美國的郊野社區幾乎一致地反覆傳達:我們必須學會「與火共存」。這意味著試圖從每個地景中消除火是錯誤的,火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不應該盲目滅火,而是需要重新定義與火的關係。最初主要關注的是郊野地區,但隨著火新世到來,此觀點已適用於人類所有的火實踐。
這樣的觀點意味著什麼?其一,需要理解火不會消失,且在許多情況下,亦無法承受火的離去。其二,需要改變對火的認知,把它從邊緣的危險因素,轉變為更核心的存在,重新評價它的重要性。其三,工業火的生態和活態地景中的火生態一樣重要,兩者都需要被認真看待和理解。其四,工業化並沒有根除火,而是把它從自然界中移走,轉移到機器中,還有那些經過控制的火,取代不受控制的火。其五,人類可將火焰從人為環境中去除,但無法將其從鄉村和荒野去除。其六,應該調整第一火、第二火與第三火間的平衡,減少第三火,增加第二火。其七,要以一種有益的方式來管理火。其八,與火為友非為敵。
對於解決當前問題,不需要重新發明或發現新的科學理論,我們已經知道該做什麼(事實上,這些知識曾經是我們的常識,只是後來人類因為貪婪而遺忘了)。常識一,知道需要用其他能源來取代化石燃料。常識二,知道如何保護社區和關鍵資源(如水源區)免受有害的火影響。常識三,知道我們需要將有益的火引入活態地景中,非以精確控制的方式,而是讓火的變化和不確定性成為建立生態韌性的資產。常識四,知道我們需要來自多個來源的許多可控火,並且每一種火都有其特點,有各自的位置,往往會在相同的地點進行。所有這些說起來很簡單,但它涵蓋了每個選擇背後所需的數千個決策。不過,我們不需要解析每一個細節和因素,因為火本身會幫助我們處理這些事。火具有某種自然力量、直覺或經驗,如果我們讓它去運作,它能夠自動進行整合與處理,甚至比最強大的超級電腦還要有效。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從真實的火中學習,而不是僅僅依賴電腦模擬的數據來學習。……
終章
第六輪太陽
墨西哥谷的中央矗立著星辰山,在前哥倫布時代,這是一座島嶼,特斯科科湖的湖水在此與霍奇米爾科湖交融。正是在此處,阿茲特克人每52年舉行一次新火儀式。當260日曆法與365日曆法重合,昴宿星團高懸天際,宇宙即將墜入黑暗或重燃新生光芒之際,新火將救贖世界,誕生新一輪太陽。
這場儀式精妙絕倫,星辰山的選址更顯恢弘氣勢,環繞的鄉野,遼闊湖面有如明鏡,每處爐灶與村落、每座神廟、每支火把與每處營地之火盡數熄滅,直至人類文明的光輝徹底消逝於暮色,唯餘星辰微光閃爍,太陽主宰的已知世界在未知中顫慄,黑暗與惡魔悄然逼近,唯有以古老方式——人類最初掌握的方法——重新點燃的火焰,方能喚醒新一輪太陽歸來。
………
是的,我深知自己的本源!
如火焰般永不熄滅,
我燃燒自我,綻放光芒。
觸及之物皆化光明,遺留一切盡成焦碳:
我確然是火焰本身!
——弗里德里希·尼采《瞧!這個人》
藉它你賜予我們黑夜中的光明:
它明亮、歡欣、雄渾而強健。
——聖方濟各〈萬物頌〉
在火新世的宏大史詩中,直至近世,人類只需不斷追尋更多燃料、在更多地點燃燒。兩條互補的敘事曾並行於世:普羅米修斯式(或尼采式)敘事將火視為力量,把掙脫自然桎梏(或許通過暴力)轉為己用的人為之火奉為圭臬。原始式(或方濟各式)敘事則將火視為旅途夥伴,人類作為火之管家,為自身與萬物福祉而治理。兩種敘事皆彰顯人類獨有的火之能力——前者聚斂,後者分享。二者雖路徑各異,卻共行於活態地景的疆域。
化石燃料的燃燒令道路分岔,人類以愈發激烈的姿態背棄方濟各式理念,捨活態地景而就岩層世界。原始之火式微,普羅米修斯之火膨脹,終至掙脫鎖鏈君臨天下。人類火力呈指數爆發,我們棲居的生機世界卻滿目瘡痍,漸失宜居性。如今,我們正從盛大的冰河紀元,滑向失控的火紀元。……
‧火,似乎無所不在
那些慣常遭野火肆虐之地——澳洲、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俄羅斯西伯利亞——正以史詩級的廣度與烈度燃燒。2009年澳洲的「黑色星期六」曾為單場野火立下歷史尺規;其後2019至2020年的「黑色夏季」大火,則刷新了澳洲火季燃燒紀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連續焚城中熬過了第4個年頭(2020年),每一季烈焰均超越前一年的極限,如同瘟疫蔓延,大火侵入俄勒岡州與華盛頓州,繼而翻越大陸分水嶺,將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夷為焦土。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野火向北吞噬故土,甚至竄入北極圈內。
那些本不該燃燒或只該零星起火之地,如今卻陷入燎原之勢,南美洲腹地的潘塔納爾溼地竟遭火噬,亞馬遜雨林迎來20年迄今最兇險的火季。即便未被火焰舔舐之處,亦難逃濃煙之劫,澳洲野火的煙塵環遊了全球,美國西海岸大火的陰霾籠罩了大半個國家,其象徵性震撼與視覺衝擊,堪比1930年代沙塵暴肆虐時的末日圖景。白晝,煙霧遮蔽了次大陸級的遼闊地域;夜晚,火光如星斑點綴沉睡大地,宛如一條火焰星辰匯成的銀河。野火火焰照不到的角落,城市燈火與燃氣火炬依然通明:那是煤炭與天然氣轉化為電能的燃燒之證。於眾多觀察者眼中,它們恰似步步緊逼的末世引信。連格陵蘭島,也燃起了冷焰。
然而,煙與火只是症候,而非癥結。地球的「野火版圖」理應由那些自然演化與人類文明磨合出的火所形塑,如今失衡了。土地以生態退化回應,同時囤積更多可燃物,助長更兇猛的野火。地球的火危機,不僅是那些焚毀荒野、撲向城鎮的野性火,更關乎因刻意撲滅或不再引燃的良性火。地球生物群落的崩解,既因狂火肆虐,也因已馴化火的缺席而分崩離析。2013年「平肖自然保育研究所」評估了美國森林的現狀與未來,集結專家完成〈人新世中的森林保育〉報告,此報告如同一份生態全身斷層掃描,檢視植物、水、空氣、土壤與野生動物的現狀。「火」是唯一貫穿所有領域的關鍵元素,是所有學科的交集點。在這急速變貌的圖景中,火觸及每一環節,它整合了其他一切。若無法正確理解火,便無法理解其餘事物。
地球之火三角的燃燒機制中,除了人類當前與過去的火現象外,還有超越此兩者的第三個面向,那是深層時間封存的化石燃料燃燒的火,這類源自地質紀元的碳基燃料,與現生生物質燃料存在本質差異。人類隨著狂熱情緒的升高,正過度使用化石燃料。其燃燒過程非常複雜,可能包括許多尚未完全理解的化學和物理反應,而人類對這些過程的了解相對有限,其結果不僅影響現在,也會對未來的地質環境產生影響;燃燒所產生的汙染物和溫室氣體,更將在未來的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內,持續影響地球。
工業化將化石燃料轉化為未來地質的碳債務,這種跨越時空的能量置換機制,實質重構了行星尺度的火循環體系。我們不僅將古生代沉積的碳庫搬移至地表釋放,更經由燃燒產物造成氣候回饋與生態連鎖效應,重塑了整個生物圈的燃燒閾值。簡言之,化石燃料的火扮演三種角色,一,促發者:提供能量和動力支持;二,增強者:加強人類對能源的利用效率和規模;三,全球化者:使得火的影響範圍遍及全球。儘管並非所有地方都會被完全控制,但火的存在和影響確實遍布地球。
燃燒活態(living landscapes)與石態地景(lithic landscapes)之間的辯證關係,解釋了地球野火場景中的大多數矛盾。……
‧何謂火新世?
……歷史記錄了三種火,第一種是自然火──自從植物開始在陸地上定居以來,火便隨之出現,化石炭的痕跡可追溯至4.2億年前。第二種火是由人類點燃並促進,由於烹飪的需要,火依賴性已經成為人類基因的一部分,在上次冰河時期結束後的有利條件下,第二種火隨著人類的擴散而逐漸蔓延,這些火與自然火競爭,並擴大了燃燒的範圍,幾乎任何地方──無論是被冰雪覆蓋的區域、無情的沙漠,還是潮溼的熱帶雨林都不缺火。人類點燃的火就像自然火一樣,發生在活態地景中,並受到共同的條件與限制影響。第三種火則在本質上有所不同。……
這三重火相互競爭、互補並謀和諧——形成了一個生態上的三體問題。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它們相互作用的條件發生了變化,曾經的調節器變成了開關,地球的火系統越過了一個頂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這種狀態不易逆轉,曾經良性的火變成了野性的火。地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經歷了眾多野性的火、太少良性的火,以及整體上超限燃燒。不僅僅是火與氣候的間接關係破裂,火也脫離了原有的軌道,人類對於火的總體執行成果壓倒了生態韌性,更甚者為野性火創造了條件,成為火時代,但人類是否能夠適應這個新境尚不明確。
未來看起來如此嚴峻,其可能的軌跡如此陌生,以至於一些觀察者認為過去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他們憂心人類正走向一個沒有敘事與類比的明天,將至的動盪如此巨大且難以想像,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知識弧線已經斷裂。人類即將經歷的時代未有先例,亦無法從累積的智慧中推測。……
第五章 火新世
‧火紀元
……火已臨之地將更繁劇,如美國溼潤的高草原、長葉松林,非洲稀樹草原,巴西熱帶草原,北方林和沼澤地,地中海灌叢和南非石楠灌叢。另外,頻繁地表火影響區域的松樹、橡樹、山核桃樹,以及金合歡樹和相思樹林地,將如冰蓋擴張般迎來更暴烈的火之宰制。火不再是壓力矩陣中的普通變數,而升格為定義生態的元代碼。至於泥炭地、灌叢、有機質土壤等間歇性火域,在火與氣候的共謀下,其火情模態將突破歷史閾值,使易燃生物群系蛻變為火控型燃燒地域。
畏火之地可能淬煉出耐火植群,刀耕火種的催化下,雨林正被改寫成牧場與油棕園。一旦土地烙上焦痕,便會對後續火敞開門戶,反覆灼燒將永久封印生態復原的可能——大地正在切換作業系統。……
‧與火共生之道
幾十年來,美國的郊野社區幾乎一致地反覆傳達:我們必須學會「與火共存」。這意味著試圖從每個地景中消除火是錯誤的,火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不應該盲目滅火,而是需要重新定義與火的關係。最初主要關注的是郊野地區,但隨著火新世到來,此觀點已適用於人類所有的火實踐。
這樣的觀點意味著什麼?其一,需要理解火不會消失,且在許多情況下,亦無法承受火的離去。其二,需要改變對火的認知,把它從邊緣的危險因素,轉變為更核心的存在,重新評價它的重要性。其三,工業火的生態和活態地景中的火生態一樣重要,兩者都需要被認真看待和理解。其四,工業化並沒有根除火,而是把它從自然界中移走,轉移到機器中,還有那些經過控制的火,取代不受控制的火。其五,人類可將火焰從人為環境中去除,但無法將其從鄉村和荒野去除。其六,應該調整第一火、第二火與第三火間的平衡,減少第三火,增加第二火。其七,要以一種有益的方式來管理火。其八,與火為友非為敵。
對於解決當前問題,不需要重新發明或發現新的科學理論,我們已經知道該做什麼(事實上,這些知識曾經是我們的常識,只是後來人類因為貪婪而遺忘了)。常識一,知道需要用其他能源來取代化石燃料。常識二,知道如何保護社區和關鍵資源(如水源區)免受有害的火影響。常識三,知道我們需要將有益的火引入活態地景中,非以精確控制的方式,而是讓火的變化和不確定性成為建立生態韌性的資產。常識四,知道我們需要來自多個來源的許多可控火,並且每一種火都有其特點,有各自的位置,往往會在相同的地點進行。所有這些說起來很簡單,但它涵蓋了每個選擇背後所需的數千個決策。不過,我們不需要解析每一個細節和因素,因為火本身會幫助我們處理這些事。火具有某種自然力量、直覺或經驗,如果我們讓它去運作,它能夠自動進行整合與處理,甚至比最強大的超級電腦還要有效。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從真實的火中學習,而不是僅僅依賴電腦模擬的數據來學習。……
終章
第六輪太陽
墨西哥谷的中央矗立著星辰山,在前哥倫布時代,這是一座島嶼,特斯科科湖的湖水在此與霍奇米爾科湖交融。正是在此處,阿茲特克人每52年舉行一次新火儀式。當260日曆法與365日曆法重合,昴宿星團高懸天際,宇宙即將墜入黑暗或重燃新生光芒之際,新火將救贖世界,誕生新一輪太陽。
這場儀式精妙絕倫,星辰山的選址更顯恢弘氣勢,環繞的鄉野,遼闊湖面有如明鏡,每處爐灶與村落、每座神廟、每支火把與每處營地之火盡數熄滅,直至人類文明的光輝徹底消逝於暮色,唯餘星辰微光閃爍,太陽主宰的已知世界在未知中顫慄,黑暗與惡魔悄然逼近,唯有以古老方式——人類最初掌握的方法——重新點燃的火焰,方能喚醒新一輪太陽歸來。
………
是的,我深知自己的本源!
如火焰般永不熄滅,
我燃燒自我,綻放光芒。
觸及之物皆化光明,遺留一切盡成焦碳:
我確然是火焰本身!
——弗里德里希·尼采《瞧!這個人》
藉它你賜予我們黑夜中的光明:
它明亮、歡欣、雄渾而強健。
——聖方濟各〈萬物頌〉
在火新世的宏大史詩中,直至近世,人類只需不斷追尋更多燃料、在更多地點燃燒。兩條互補的敘事曾並行於世:普羅米修斯式(或尼采式)敘事將火視為力量,把掙脫自然桎梏(或許通過暴力)轉為己用的人為之火奉為圭臬。原始式(或方濟各式)敘事則將火視為旅途夥伴,人類作為火之管家,為自身與萬物福祉而治理。兩種敘事皆彰顯人類獨有的火之能力——前者聚斂,後者分享。二者雖路徑各異,卻共行於活態地景的疆域。
化石燃料的燃燒令道路分岔,人類以愈發激烈的姿態背棄方濟各式理念,捨活態地景而就岩層世界。原始之火式微,普羅米修斯之火膨脹,終至掙脫鎖鏈君臨天下。人類火力呈指數爆發,我們棲居的生機世界卻滿目瘡痍,漸失宜居性。如今,我們正從盛大的冰河紀元,滑向失控的火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