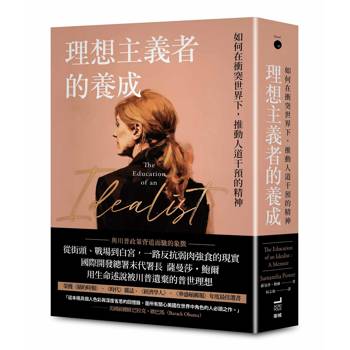我在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初次造訪橢圓形辦公室,當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前來拜會歐巴馬總統。
我以為我會一下就找到橢圓形辦公室的位置。畢竟,在我的新宇宙中,那裡就是所有行星圍繞旋轉的太陽。當時我已經多次從在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走到西翼的一樓,去參與戰情室的會議,和橢圓形辦公室距離並不遠。
不幸的是,我一進入白宮,就發現我不知該往哪裡走。我衝回我在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在網路搜尋「橢圓形辦公室西翼地圖」。結果我列印出《華盛頓郵報》網站上的某張小地圖,畫出西翼平面圖。可是那張圖沒有按照比例繪製,給了我錯誤的安全感。我一路遊蕩到二樓,但橢圓形辦公室是在一樓,而且其實很難錯過。
等我終於找到位置,加入和總統的「會前簡報」時,其他與會者早已就坐,國家安全顧問瓊斯正在講話。我尷尬地坐下,勉力把我七個月身孕的身體移動到兩名同事之間的座椅上,試圖在總統點我發言前調整好呼吸。
多次突發昏倒後,我都會隨身帶著一只破舊的波蘭春天牌礦泉水瓶,而我沒多想就把水瓶放在優雅的木質咖啡桌上、一大碗的新鮮蘋果旁。然而,我一擺上,一名管家就迅速把那不美觀的物品移開眾人視線。蘇珊坐在瓊斯旁邊,試圖對我露出鼓勵的微笑,但他的臉有一絲扭曲。
歐巴馬總統親切地問候我。「你好嗎,鮑爾?」他說:「我先給你一分鐘熟悉一下環境。」我試著把呼吸速度放慢。
他示意我提出意見後,我告訴他,他和秘書長的會面發生在一個關鍵時刻。前一週,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席爾因為在達爾富爾軍隊犯下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遭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為了報復,他剛將十三個國際救援團體驅逐出蘇丹,導致達爾富爾流離失所的人民賴以維生的重要糧食運送中斷。
我以前在歐巴馬面前從沒這麼緊張過,我告訴他,達爾富爾正處在「戰略性時刻」。我強調超過一百萬名達爾富爾人所面臨的危險,並力勸他利用和秘書長共同對媒體發表言論的機會,公開譴責巴席爾的行為。
「這會是世人第一次聽到你表示,不能接受驅逐人道工作者。」我說。
「可是如果我這麼說的話,我們有什麼籌碼可以堅持到底?」
坐在我面前總統座椅上的男士,外表和聲音都和我在參議院與競選團隊工作時一模一樣。然而,即使才開始新工作兩個月,他也變得不一樣了。
「沒有人會去逮捕巴席爾,他自己的人馬也不會把他拉下台。」歐巴馬繼續說。國安會的非洲資深主任試圖回應,但總統也打斷他。「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巴席爾就範?阿拉伯人支持我們嗎?」
我搖搖頭。
「非洲人呢?」
「有些支持。」我說。
「中國?」
我低下頭。
中國政府正崛起成為強大的國際事務勢力,他們主張主權國家政府有權在其境內為所欲為。這個立場是出於自身利益,因為中國不希望外界仔細審查其國內違反人權的情況。即使許多非洲領導人已經表達絕不允許「盧安達事件重演」,但他們並不打算正面對抗石油藏量豐富的蘇丹政府。
「那我們有什麼籌碼呢?」歐巴馬再次問道。
蘇珊插話,概述了我們可以對蘇丹政府官員實施的經濟制裁範圍,並提及歐巴馬在競選期間提出的禁航區方案。可是歐巴馬是因為承諾逐步減少戰爭才當選總統的。出軍實施禁航來阻止蘇丹空軍行動,可能會開啟一場新的戰爭。
總統說:「我不是要刁難你們,但我們就是沒有許多手段可用,而蘇丹人一定知道這一點。」
會前會議快要結束時,我最後再次試圖說服他,就算沒有萬靈丹,他仍應該發聲。
「蘇丹政府長期以來都經常四處威脅,接著又在輿論壓力下收回。」我說:「他們非常渴望要和政府建立有效的關係,你的發聲可以帶來改變。」
歐巴馬並不滿意,但他拍手合掌,示意是時候迎接秘書長了。
在《地獄的難題》中,我特別強調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的著作,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者,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了劃時代的《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一書。赫緒曼的理論是,不願遵循特定行動路線的人,往往會主張某個政策無效(無效論)、會讓情況惡化(悖謬論),或會危及其他目標(危害論)。
歐巴馬當參議員時,我們曾討論過赫緒曼的著作,我也十分欽佩歐巴馬能夠同時識別出美國面臨的限制,又能有創意地構思出越過那些障礙的方法。然而,現在他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卻似乎不再相信美國能夠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總統對「過度承諾和難以兌現」的風險非常敏銳警覺,這是赫緒曼擔憂的無效論的另一種說法,但他開始把這種風險掛在嘴邊。
潘基文被護送進橢圓形辦公室,並開始告訴歐巴馬,他非常期待和團隊的成員合作,他逐一向我們打招呼:「蘇珊・萊斯、瓊斯上將、希拉蕊・柯林頓、薩曼莎・瓊斯……。」雖然我在進政府工作前曾見過秘書長幾次,但我並不訝異他搞錯我的姓氏。真正令我震驚的是,他把我想成金・凱特羅(Kim Cattrall)在HBO影集《慾望城市》中扮演的虛構角色,那個性成癮的女商人。潘基文的其中三位顧問立刻屈身靠向他,小聲說「是鮑爾、鮑爾」。
那場會面平安進行。後來,令我驚喜的是,歐巴馬利用他和秘書長接受聯訪的時間,大力譴責了蘇丹政府的行為。蘇丹政府並沒有重新准許那十三個非政府組織入境,但會核准其他救援團體,來補足失去的人道救援量能。
聯合國代表團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後,歐巴馬來詢問我的預產期。「我想巴拉克會是個好名字。」他開玩笑說。
我非常渴望和他討論實質的外交政策議題,以致於我脫口而出幾個我還在研擬的主張。我一說出口,就看見他繃緊雙肩,並說他必須趕去下一場會議。
雖然我起初感到受傷,但事後想過後就明白他為何如此反應。「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對他有所求。」我告訴凱斯:「他可能只是想要簡單閒聊寶寶的名字。」
在參議院和競選期間,我和歐巴馬的對話經常在私人和政治對話間切換。可是現在他成為總統,他有權力命令政府官員為世界上幾乎任何議題採取行動。這代表著當我向他提起某個外交政策的話題,我不是在展開有趣的討論,而是在含蓄提出要求。
我以為我會一下就找到橢圓形辦公室的位置。畢竟,在我的新宇宙中,那裡就是所有行星圍繞旋轉的太陽。當時我已經多次從在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走到西翼的一樓,去參與戰情室的會議,和橢圓形辦公室距離並不遠。
不幸的是,我一進入白宮,就發現我不知該往哪裡走。我衝回我在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的辦公室,在網路搜尋「橢圓形辦公室西翼地圖」。結果我列印出《華盛頓郵報》網站上的某張小地圖,畫出西翼平面圖。可是那張圖沒有按照比例繪製,給了我錯誤的安全感。我一路遊蕩到二樓,但橢圓形辦公室是在一樓,而且其實很難錯過。
等我終於找到位置,加入和總統的「會前簡報」時,其他與會者早已就坐,國家安全顧問瓊斯正在講話。我尷尬地坐下,勉力把我七個月身孕的身體移動到兩名同事之間的座椅上,試圖在總統點我發言前調整好呼吸。
多次突發昏倒後,我都會隨身帶著一只破舊的波蘭春天牌礦泉水瓶,而我沒多想就把水瓶放在優雅的木質咖啡桌上、一大碗的新鮮蘋果旁。然而,我一擺上,一名管家就迅速把那不美觀的物品移開眾人視線。蘇珊坐在瓊斯旁邊,試圖對我露出鼓勵的微笑,但他的臉有一絲扭曲。
歐巴馬總統親切地問候我。「你好嗎,鮑爾?」他說:「我先給你一分鐘熟悉一下環境。」我試著把呼吸速度放慢。
他示意我提出意見後,我告訴他,他和秘書長的會面發生在一個關鍵時刻。前一週,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席爾因為在達爾富爾軍隊犯下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遭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為了報復,他剛將十三個國際救援團體驅逐出蘇丹,導致達爾富爾流離失所的人民賴以維生的重要糧食運送中斷。
我以前在歐巴馬面前從沒這麼緊張過,我告訴他,達爾富爾正處在「戰略性時刻」。我強調超過一百萬名達爾富爾人所面臨的危險,並力勸他利用和秘書長共同對媒體發表言論的機會,公開譴責巴席爾的行為。
「這會是世人第一次聽到你表示,不能接受驅逐人道工作者。」我說。
「可是如果我這麼說的話,我們有什麼籌碼可以堅持到底?」
坐在我面前總統座椅上的男士,外表和聲音都和我在參議院與競選團隊工作時一模一樣。然而,即使才開始新工作兩個月,他也變得不一樣了。
「沒有人會去逮捕巴席爾,他自己的人馬也不會把他拉下台。」歐巴馬繼續說。國安會的非洲資深主任試圖回應,但總統也打斷他。「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巴席爾就範?阿拉伯人支持我們嗎?」
我搖搖頭。
「非洲人呢?」
「有些支持。」我說。
「中國?」
我低下頭。
中國政府正崛起成為強大的國際事務勢力,他們主張主權國家政府有權在其境內為所欲為。這個立場是出於自身利益,因為中國不希望外界仔細審查其國內違反人權的情況。即使許多非洲領導人已經表達絕不允許「盧安達事件重演」,但他們並不打算正面對抗石油藏量豐富的蘇丹政府。
「那我們有什麼籌碼呢?」歐巴馬再次問道。
蘇珊插話,概述了我們可以對蘇丹政府官員實施的經濟制裁範圍,並提及歐巴馬在競選期間提出的禁航區方案。可是歐巴馬是因為承諾逐步減少戰爭才當選總統的。出軍實施禁航來阻止蘇丹空軍行動,可能會開啟一場新的戰爭。
總統說:「我不是要刁難你們,但我們就是沒有許多手段可用,而蘇丹人一定知道這一點。」
會前會議快要結束時,我最後再次試圖說服他,就算沒有萬靈丹,他仍應該發聲。
「蘇丹政府長期以來都經常四處威脅,接著又在輿論壓力下收回。」我說:「他們非常渴望要和政府建立有效的關係,你的發聲可以帶來改變。」
歐巴馬並不滿意,但他拍手合掌,示意是時候迎接秘書長了。
在《地獄的難題》中,我特別強調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的著作,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者,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了劃時代的《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一書。赫緒曼的理論是,不願遵循特定行動路線的人,往往會主張某個政策無效(無效論)、會讓情況惡化(悖謬論),或會危及其他目標(危害論)。
歐巴馬當參議員時,我們曾討論過赫緒曼的著作,我也十分欽佩歐巴馬能夠同時識別出美國面臨的限制,又能有創意地構思出越過那些障礙的方法。然而,現在他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卻似乎不再相信美國能夠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總統對「過度承諾和難以兌現」的風險非常敏銳警覺,這是赫緒曼擔憂的無效論的另一種說法,但他開始把這種風險掛在嘴邊。
潘基文被護送進橢圓形辦公室,並開始告訴歐巴馬,他非常期待和團隊的成員合作,他逐一向我們打招呼:「蘇珊・萊斯、瓊斯上將、希拉蕊・柯林頓、薩曼莎・瓊斯……。」雖然我在進政府工作前曾見過秘書長幾次,但我並不訝異他搞錯我的姓氏。真正令我震驚的是,他把我想成金・凱特羅(Kim Cattrall)在HBO影集《慾望城市》中扮演的虛構角色,那個性成癮的女商人。潘基文的其中三位顧問立刻屈身靠向他,小聲說「是鮑爾、鮑爾」。
那場會面平安進行。後來,令我驚喜的是,歐巴馬利用他和秘書長接受聯訪的時間,大力譴責了蘇丹政府的行為。蘇丹政府並沒有重新准許那十三個非政府組織入境,但會核准其他救援團體,來補足失去的人道救援量能。
聯合國代表團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後,歐巴馬來詢問我的預產期。「我想巴拉克會是個好名字。」他開玩笑說。
我非常渴望和他討論實質的外交政策議題,以致於我脫口而出幾個我還在研擬的主張。我一說出口,就看見他繃緊雙肩,並說他必須趕去下一場會議。
雖然我起初感到受傷,但事後想過後就明白他為何如此反應。「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對他有所求。」我告訴凱斯:「他可能只是想要簡單閒聊寶寶的名字。」
在參議院和競選期間,我和歐巴馬的對話經常在私人和政治對話間切換。可是現在他成為總統,他有權力命令政府官員為世界上幾乎任何議題採取行動。這代表著當我向他提起某個外交政策的話題,我不是在展開有趣的討論,而是在含蓄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