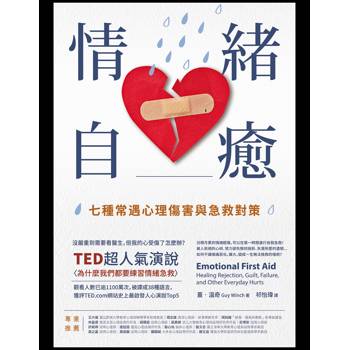第一章 遭拒:日常生活中的情緒皮肉傷(節錄)
在人一生所有的情緒傷害中,遭到拒絕或許是最常見的一種。升上國中之前,我們就已嚐過沒人揪你去玩、選隊友最後一個被選中、辦慶生會不邀你、老朋友撇下你加入新的小團體、被班上同學戲弄或霸凌等滋味。待我們終於挺過小時候的各種打擊,卻發現長大後還得迎向全新系列的遭拒大考驗。我們被心儀的對象拒絕、被徵才的雇主淘汰、被渴望結交的朋友無視。另一半拒絕跟我們親熱,鄰居對我們態度冷淡,家人跟我們各過各的。
遭拒是心理上的皮肉傷。它擦破我們的情緒之皮,刺穿我們的情緒之肉。有些傷勢嚴重到在內心深處造成大量失血的傷口,需要緊急救護才行;有些則像被紙割傷,輕輕痛了一下,但沒流什麼血。有鑒於我們遭到五花八門各種拒絕的頻繁度,你可能會以為,我們對於自己的情緒、想法和行為因此受到什麼影響,想必有很清楚的理解與體認。但實則不然,我們嚴重低估了遭拒的痛楚和它造成的心理創傷。
遭拒造成的心理創傷
遭拒可能造成四種不同的心理創傷,傷勢依當時的情況和我們本身的情緒健康而定。確切說來,遭拒引發的情緒痛苦,劇烈得足以影響我們的思維、點燃滿腔的怒火、侵蝕我們的自信與自尊,並動搖我們根本的歸屬感。
我們遭到的拒絕有許多都相對輕微,傷口隨著時間過去就癒合了。但若是置之不理,就連輕微的拒絕造成的創傷都可能「感染」,引發心理上的併發症,嚴重衝擊我們的心理健康。一旦遭到重量級的拒絕,用情緒急救術治療傷口的急迫性就大得多。急救不僅能將「感染」或併發症的風險降到最低,也能加速情緒癒合的過程。為了搶救壞情緒,成功治療遭拒造成的四種創傷,我們需要對這每一種創傷都有清楚的概念,並對我們遭拒後的情緒、思想和行為受到什麼危害有充分的認識。
1.情緒痛苦:為什麼連無足輕重的拒絕都很痛?
想像你和兩個陌生人坐在一間等候室,其中一人看到桌上有顆球,便拿起球來丟給另一人。那人笑了笑,眼睛看過來,接著把球丟給你。我們姑且假設你丟接球的技術不錯,玩得起這個小遊戲。你把球丟回給第一個人,那人又很快把球丟給第二個人。但第二個人沒再把球丟給你,反倒丟回給第一個人,把你排除在他們的遊戲之外。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有什麼感覺?你會覺得受傷嗎?你的心情會受到影響嗎?還有你的自尊呢?
多數人都會對這個想法不以為然──「等候室裡的兩個陌生人不把球丟給我,有什麼大不了的?誰在乎啊!」但經過實測之後,心理學家發現了驚人的事實。我們還真的很在乎,遠比我們自以為的在乎得多。丟接球的情境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心理學實驗,實驗中的兩名「陌生人」其實是研究人員,每位「受試者」(以為自己在等候接受一個截然不同的實驗)都在第一輪或第二輪丟接球後受到冷落。歷經數十次的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一律表示:被排除在丟接球遊戲外的「心情很受傷」。
這些研究結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相較於人生中遭到的多數拒絕,兩個陌生人不跟你玩丟接球是再輕微不過的一種拒絕了。如果這麼無足輕重的小事都能令人一陣心痛(乃至於情緒低落、自信動搖),那就可以想見意義重大的拒絕有多傷人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被交往對象甩掉、被老闆炒魷魚、或發現朋友相約唯獨漏了你,對我們的情緒健康會是那麼沉重的打擊了。
的確,遭拒之痛和人生中其他負面情緒的區別,就在於它痛到什麼地步。我們常形容遭到嚴重拒絕的感受就像肚子挨了一拳,或胸口挨了一刀。是啦,很少人真的胸口挨過刀,但當心理學家問及遭拒之痛可與什麼肢體上的疼痛相比擬時,得到的答案是那種痛可比自然產和癌症治療之痛!相形之下,仔細想想其他負面的經驗,例如失望、沮喪或恐懼,不愉快歸不愉快,但若論及那種直搗五臟六腑之痛,跟遭到拒絕的感受比起來,其他的不愉快可都要略遜一籌了。
但遭到拒絕為什麼比其他情緒創傷痛上許多呢?
答案藏在我們的演化歷程裡。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在蠻荒時代,被部落或團體拒絕就意味著得不到食物、保護和配偶,生存變得難如登天。遭到驅逐形同獲判死刑。由於被驅逐的下場是那麼慘烈,我們的大腦就發展出一套預警系統,一旦面臨個人的去留由眾人表決的風險時,即使只是接收到一點點被社會拒絕的暗示,大腦都會引發劇烈的痛感。
事實上,腦部掃描顯示,人在遭拒時活躍起來的大腦區塊,就跟肢體疼痛對應的區塊一樣。說來不可思議,這兩套系統關係之密切,連止痛藥都能驗證。科學家嘗試在展開殘忍的丟接球遭拒實驗之前,先讓受試者服下泰諾止痛藥(Tylenol),結果服藥組比未服藥組感受到的情緒打擊輕微得多。只可惜其他負面情緒就沒有一樣的效果了,例如止痛藥就舒緩不了難堪的感受。所以當我們搞錯公司辦萬聖節派對的日期,打扮成美枝.辛普森(Marge Simpson)的模樣去上班時,吃再多泰諾止痛藥也沒用。
遭拒之痛沒有道理可言
瑪莎和安傑羅來做伴侶諮商,因為安傑羅從六個月前遭到公司裁員後就找不到工作,他倆為此頻頻吵架。「我在那家航運公司做了二十年。」安傑羅一臉受傷的表情還是很明顯。「這些人是我的朋友欸!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瑪莎一開始很同情他,但安傑羅一直沒能從情緒打擊中振作起來、開始去找新的工作,瑪莎變得對他越來越灰心。我很快就發現,安傑羅對自己也一樣灰心。他設法激勵自己、勸自己要努力,但他純粹就是被情緒上的痛苦耗盡心力。他試圖跟自己講道理,要自己放下那份傷痛、「克服」受傷的感受,但都沒有用。
當我們遭到拒絕時,許多人都會發現很難勸自己不要痛。遭拒之所以常有強大的殺傷力,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理智、邏輯和常識都緩和不了心痛的感受。舉例而言,在名為「虛擬球」(Cyberball)的電腦版丟接球實驗中,科學家告訴受到冷落的參與者說局面是由電腦操控的,但就算發現自己遭到的拒絕甚至不是「真實的」,參與者也難以緩和心痛的感受。科學家是鍥而不捨的一種生物,於是他們又告訴另一組參與者說冷落他們的人是三K黨成員。如果拒絕我們的是我們壓根就瞧不起的人,那麼遭拒的感覺想必就沒那麼痛了吧。但實則不然,感覺還是一樣痛。科學家甚至試過把虛擬球換成動畫虛擬炸彈,按照程式的設計,炸彈隨機爆炸。不管是誰,只要爆炸當下拿到炸彈就會被炸死。但當別人不把虛擬炸彈傳給自己時,受試者感覺到的遭拒之痛,就跟拿不到虛擬球是一樣的。
在其他方面,遭拒也會影響我們運用健全邏輯和清晰思考的能力。舉例而言,光是被要求去回想慘痛的遭拒經驗,就足以讓當事人在後續的智商測驗、短期記憶力測驗、理性能力評量和決策能力評量上拿到超低分。
說到打亂思緒和破壞良好的判斷力,戀情上遭到的拒絕威力尤其強大──即使情愫才剛萌芽,連「戀愛關係」都還不成立之時(第三章會談到長期交往或認真交往後的分手)。我曾輔導過一位年輕男士,他在為期一週的夏日假期裡邂逅了一名女性,儘管她已明確表示無意與他交往,他在心痛之餘還是飛到歐洲,想給她一個「驚喜」,一心認為自己臨時起意的「浪漫之舉一定會融化她的心,改變她的主意」!當他一大清早不適時地出現在她家門口時,這位女士嚇得花容失色,結果她唯一改變的就是她家門鎖。在某些情況下,遭拒後心裡那股奮不顧身的感受,可能會讓許多人錯把變態行徑當成浪漫之舉。
2.憤怒與攻擊:為什麼門要被摔、牆要被捶?
遭拒常引發憤怒與攻擊的衝動,導致我們亟欲把情緒發洩出來,尤其是針對拒絕我們的人;但在別無選擇之際,無辜的路人也可以將就著用。其中一種深知箇中滋味的倒楣鬼,就是無數被剛剛遭拒的男人(也有時是女人)飽以老拳的門和牆壁,儘管磚牆和實木門通常才是笑到最後的一方。當我們身為拒絕者時也務必謹記這種危險,即使我們打算拒絕的人是好人好事代表,我們收藏的喜姆娃娃瓷偶還是有可能遭殃。
為免我們對捶牆者和砸偶者的評斷太嚴厲,我們應該考量到:就連天下第一大好人受到了最無足輕重的拒絕,都會被激起逞凶鬥狠的衝動。舉例而言,在一場虛擬球的遊戲過後,受試者可以選擇用刺耳的白噪音轟炸某個無辜的玩家(他們被明確告知這位玩家並非丟接球遊戲的一分子)。比起並未遭拒的受試者,遭到拒絕的受試者用更大聲的噪音轟炸無辜玩家,而且轟炸得更久。在另一系列的研究中,遭拒者比未遭拒者逼無辜玩家吃下多出四倍的辣椒醬、喝下難喝的飲料、聆聽難聽到極點的錄音帶。如果你想知道這些實驗背後的科學家有多常被真人實境秀的製作團隊找去,為參賽者設計噁心的挑戰內容,嗯哼,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不幸的是,遭拒後的憤怒反應還有更黑暗也更嚴重的表現方式。一再遭到嚴重拒絕所引發的攻擊行為,遠不止於白噪音或辣椒醬而已。若是將此一性質的心理創傷置之不理,傷口很快就會「感染」,並對一個人的心理健康造成重大危害。遭拒後傷人和自傷的新聞事件層出不窮。長期嚴重遭拒形成的心理創傷,若不加以治療會有什麼後果呢?失戀的人尋求報復、被郵局解雇的員工抓狂殺人、校園霸凌掀起可怕的自殺潮……只是少數幾個例子而已。
二○○一年,美國醫事總署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在社交方面遭拒是青少年表現出暴力行為的一大因素,影響更甚於加入幫派、貧窮或吸毒。遭拒的感受對情侶之間的暴力也有很大的作用。許多暴力事件都是爭風吃醋和懷疑對方劈腿所致,背後與遭拒的感受有密切的關聯。科學家調查了五百五十一起殺妻案,發現其中將近半數都是在分居或臨分居前發生的;確實也常有殺妻男在犯後坦承難以面對遭到拒絕的感受。
包括一九九九年的科倫拜(Columbine)高中慘案在內,有關校園槍擊案的研究發現,十五起事件中有十三起的凶手都曾在人際上遭受重大拒絕,並遭到同學排擠。在許多案件中,凶手特別針對曾經霸凌、捉弄或拒絕他們的同學,動手時往往先挑這些人下手。
我們或多或少都體會過被人拒絕的感受,幸而只有極少數人後來登上了頭條新聞。然而,遭拒和攻擊之間有著很強的關係,我們一定要知道:遭拒之痛很可能刺激一個人表現出平常絕不會有的行為。
3.自尊受損:就已經倒地不起了,我們還猛踹自己
遭到沉重或反覆的拒絕對自尊的傷害很大。事實上,光是回想上次遭拒的情景,就足以導致一時的自我價值感低落。不幸的是,自尊遭到的打擊通常不會到此為止。我們常在遭拒後嚴厲批評自己,徒然加重既有的痛苦,本質上無異於已經倒地不起還猛踹自己。這種反應很常見,但它很容易導致原來遭拒時的心理皮肉傷惡化感染,進而對我們的心理健康造成真正的危害。
安傑羅失去了他在航運公司的工作,因為他所屬的整個部門都在降低成本的措施下被裁掉了,然而,他卻把這種拒絕看成是針對他個人(「這些人是我的朋友欸!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將拒絕個人化使得安傑羅感覺像是朋友們不要他了,長久以來的老同事拋棄他了。他避免和前公司的任何人聯絡。他認定他們不把他看在眼裡,跟他們接觸只是自討沒趣,儘管他這種恐懼完全沒有根據。當朋友和同事主動和他聯絡時(他們當然會這麼做),他不願回覆他們的來信或留言,即使內容跟其他的工作機會有關。幾個月後,朋友們就完全不再與他聯絡了。在安傑羅的心目中,他們最後的沉默只證實了他心中的恐懼,亦即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沒關心他過。
安傑羅並不孤單。我們都會把拒絕想成是針對個人,並得出問題出在我們身上的結論,即使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種假設。回頭想想(即便要回溯到很久以前),當你被心儀的對象拒絕時,你是不是一件一件挑起自己的毛病來了?你是不是怪自己魅力不足、沒見過世面、不夠聰明、不夠多金、不夠年輕,或以上皆是?你是不是心想「這種事老是發生在我身上」、或「永遠也不會有人愛我」、或「我永遠也找不到對的人」?別人對我們的拒絕,多半不像我們認為的那麼具有針對性。就算具有針對性好了,多半也和我們滿身的缺點無關。
除了徒然將拒絕個人化之外,我們也常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以偏概全、一概而論(例如認為「這種事老是發生在我身上」或「我永遠也找不到對的人」),或是徒然苛責自己,假設做法不同就不會被拒絕。在求愛遭拒之後的自我批評尤其是個問題,因為許多人都會花很多時間分析自己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亟欲找出難以捉摸的「致命錯誤」(例如:「我為什麼等這麼久才打電話給她?」「我當初就不該喝那最後一杯酒!」「或許不該這麼快就給她看我的艾默小獵人(Elmer Fudd)卡通系列內褲。」)。
事實上,遭拒很少是因為某個致命錯誤(儘管不容否認,給心儀的女生看艾默小獵人內褲這種事,大概沒有什麼對的時機存在)。求愛(或求職)遭拒最常見的原因是彼此之間沒有火花。我們可能不符合那個人(或那間公司)在當時的需求,也可能對方心目中預設了特定的條件,而我們剛好不是對方的理想型。問題不是出在我們踏錯了關鍵的一步,或我們的人格有什麼致命的缺陷。
這些思維謬誤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只是徒增偏頗的自責,加深既有的痛苦,加倍打擊本來就已傷痕累累的自尊。被人拒絕已經夠傷的了,我們實在不需要對自己的傷口撒鹽,或已經倒地不起了還狠踹自己。
在人一生所有的情緒傷害中,遭到拒絕或許是最常見的一種。升上國中之前,我們就已嚐過沒人揪你去玩、選隊友最後一個被選中、辦慶生會不邀你、老朋友撇下你加入新的小團體、被班上同學戲弄或霸凌等滋味。待我們終於挺過小時候的各種打擊,卻發現長大後還得迎向全新系列的遭拒大考驗。我們被心儀的對象拒絕、被徵才的雇主淘汰、被渴望結交的朋友無視。另一半拒絕跟我們親熱,鄰居對我們態度冷淡,家人跟我們各過各的。
遭拒是心理上的皮肉傷。它擦破我們的情緒之皮,刺穿我們的情緒之肉。有些傷勢嚴重到在內心深處造成大量失血的傷口,需要緊急救護才行;有些則像被紙割傷,輕輕痛了一下,但沒流什麼血。有鑒於我們遭到五花八門各種拒絕的頻繁度,你可能會以為,我們對於自己的情緒、想法和行為因此受到什麼影響,想必有很清楚的理解與體認。但實則不然,我們嚴重低估了遭拒的痛楚和它造成的心理創傷。
遭拒造成的心理創傷
遭拒可能造成四種不同的心理創傷,傷勢依當時的情況和我們本身的情緒健康而定。確切說來,遭拒引發的情緒痛苦,劇烈得足以影響我們的思維、點燃滿腔的怒火、侵蝕我們的自信與自尊,並動搖我們根本的歸屬感。
我們遭到的拒絕有許多都相對輕微,傷口隨著時間過去就癒合了。但若是置之不理,就連輕微的拒絕造成的創傷都可能「感染」,引發心理上的併發症,嚴重衝擊我們的心理健康。一旦遭到重量級的拒絕,用情緒急救術治療傷口的急迫性就大得多。急救不僅能將「感染」或併發症的風險降到最低,也能加速情緒癒合的過程。為了搶救壞情緒,成功治療遭拒造成的四種創傷,我們需要對這每一種創傷都有清楚的概念,並對我們遭拒後的情緒、思想和行為受到什麼危害有充分的認識。
1.情緒痛苦:為什麼連無足輕重的拒絕都很痛?
想像你和兩個陌生人坐在一間等候室,其中一人看到桌上有顆球,便拿起球來丟給另一人。那人笑了笑,眼睛看過來,接著把球丟給你。我們姑且假設你丟接球的技術不錯,玩得起這個小遊戲。你把球丟回給第一個人,那人又很快把球丟給第二個人。但第二個人沒再把球丟給你,反倒丟回給第一個人,把你排除在他們的遊戲之外。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有什麼感覺?你會覺得受傷嗎?你的心情會受到影響嗎?還有你的自尊呢?
多數人都會對這個想法不以為然──「等候室裡的兩個陌生人不把球丟給我,有什麼大不了的?誰在乎啊!」但經過實測之後,心理學家發現了驚人的事實。我們還真的很在乎,遠比我們自以為的在乎得多。丟接球的情境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心理學實驗,實驗中的兩名「陌生人」其實是研究人員,每位「受試者」(以為自己在等候接受一個截然不同的實驗)都在第一輪或第二輪丟接球後受到冷落。歷經數十次的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一律表示:被排除在丟接球遊戲外的「心情很受傷」。
這些研究結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相較於人生中遭到的多數拒絕,兩個陌生人不跟你玩丟接球是再輕微不過的一種拒絕了。如果這麼無足輕重的小事都能令人一陣心痛(乃至於情緒低落、自信動搖),那就可以想見意義重大的拒絕有多傷人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被交往對象甩掉、被老闆炒魷魚、或發現朋友相約唯獨漏了你,對我們的情緒健康會是那麼沉重的打擊了。
的確,遭拒之痛和人生中其他負面情緒的區別,就在於它痛到什麼地步。我們常形容遭到嚴重拒絕的感受就像肚子挨了一拳,或胸口挨了一刀。是啦,很少人真的胸口挨過刀,但當心理學家問及遭拒之痛可與什麼肢體上的疼痛相比擬時,得到的答案是那種痛可比自然產和癌症治療之痛!相形之下,仔細想想其他負面的經驗,例如失望、沮喪或恐懼,不愉快歸不愉快,但若論及那種直搗五臟六腑之痛,跟遭到拒絕的感受比起來,其他的不愉快可都要略遜一籌了。
但遭到拒絕為什麼比其他情緒創傷痛上許多呢?
答案藏在我們的演化歷程裡。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在蠻荒時代,被部落或團體拒絕就意味著得不到食物、保護和配偶,生存變得難如登天。遭到驅逐形同獲判死刑。由於被驅逐的下場是那麼慘烈,我們的大腦就發展出一套預警系統,一旦面臨個人的去留由眾人表決的風險時,即使只是接收到一點點被社會拒絕的暗示,大腦都會引發劇烈的痛感。
事實上,腦部掃描顯示,人在遭拒時活躍起來的大腦區塊,就跟肢體疼痛對應的區塊一樣。說來不可思議,這兩套系統關係之密切,連止痛藥都能驗證。科學家嘗試在展開殘忍的丟接球遭拒實驗之前,先讓受試者服下泰諾止痛藥(Tylenol),結果服藥組比未服藥組感受到的情緒打擊輕微得多。只可惜其他負面情緒就沒有一樣的效果了,例如止痛藥就舒緩不了難堪的感受。所以當我們搞錯公司辦萬聖節派對的日期,打扮成美枝.辛普森(Marge Simpson)的模樣去上班時,吃再多泰諾止痛藥也沒用。
遭拒之痛沒有道理可言
瑪莎和安傑羅來做伴侶諮商,因為安傑羅從六個月前遭到公司裁員後就找不到工作,他倆為此頻頻吵架。「我在那家航運公司做了二十年。」安傑羅一臉受傷的表情還是很明顯。「這些人是我的朋友欸!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瑪莎一開始很同情他,但安傑羅一直沒能從情緒打擊中振作起來、開始去找新的工作,瑪莎變得對他越來越灰心。我很快就發現,安傑羅對自己也一樣灰心。他設法激勵自己、勸自己要努力,但他純粹就是被情緒上的痛苦耗盡心力。他試圖跟自己講道理,要自己放下那份傷痛、「克服」受傷的感受,但都沒有用。
當我們遭到拒絕時,許多人都會發現很難勸自己不要痛。遭拒之所以常有強大的殺傷力,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理智、邏輯和常識都緩和不了心痛的感受。舉例而言,在名為「虛擬球」(Cyberball)的電腦版丟接球實驗中,科學家告訴受到冷落的參與者說局面是由電腦操控的,但就算發現自己遭到的拒絕甚至不是「真實的」,參與者也難以緩和心痛的感受。科學家是鍥而不捨的一種生物,於是他們又告訴另一組參與者說冷落他們的人是三K黨成員。如果拒絕我們的是我們壓根就瞧不起的人,那麼遭拒的感覺想必就沒那麼痛了吧。但實則不然,感覺還是一樣痛。科學家甚至試過把虛擬球換成動畫虛擬炸彈,按照程式的設計,炸彈隨機爆炸。不管是誰,只要爆炸當下拿到炸彈就會被炸死。但當別人不把虛擬炸彈傳給自己時,受試者感覺到的遭拒之痛,就跟拿不到虛擬球是一樣的。
在其他方面,遭拒也會影響我們運用健全邏輯和清晰思考的能力。舉例而言,光是被要求去回想慘痛的遭拒經驗,就足以讓當事人在後續的智商測驗、短期記憶力測驗、理性能力評量和決策能力評量上拿到超低分。
說到打亂思緒和破壞良好的判斷力,戀情上遭到的拒絕威力尤其強大──即使情愫才剛萌芽,連「戀愛關係」都還不成立之時(第三章會談到長期交往或認真交往後的分手)。我曾輔導過一位年輕男士,他在為期一週的夏日假期裡邂逅了一名女性,儘管她已明確表示無意與他交往,他在心痛之餘還是飛到歐洲,想給她一個「驚喜」,一心認為自己臨時起意的「浪漫之舉一定會融化她的心,改變她的主意」!當他一大清早不適時地出現在她家門口時,這位女士嚇得花容失色,結果她唯一改變的就是她家門鎖。在某些情況下,遭拒後心裡那股奮不顧身的感受,可能會讓許多人錯把變態行徑當成浪漫之舉。
2.憤怒與攻擊:為什麼門要被摔、牆要被捶?
遭拒常引發憤怒與攻擊的衝動,導致我們亟欲把情緒發洩出來,尤其是針對拒絕我們的人;但在別無選擇之際,無辜的路人也可以將就著用。其中一種深知箇中滋味的倒楣鬼,就是無數被剛剛遭拒的男人(也有時是女人)飽以老拳的門和牆壁,儘管磚牆和實木門通常才是笑到最後的一方。當我們身為拒絕者時也務必謹記這種危險,即使我們打算拒絕的人是好人好事代表,我們收藏的喜姆娃娃瓷偶還是有可能遭殃。
為免我們對捶牆者和砸偶者的評斷太嚴厲,我們應該考量到:就連天下第一大好人受到了最無足輕重的拒絕,都會被激起逞凶鬥狠的衝動。舉例而言,在一場虛擬球的遊戲過後,受試者可以選擇用刺耳的白噪音轟炸某個無辜的玩家(他們被明確告知這位玩家並非丟接球遊戲的一分子)。比起並未遭拒的受試者,遭到拒絕的受試者用更大聲的噪音轟炸無辜玩家,而且轟炸得更久。在另一系列的研究中,遭拒者比未遭拒者逼無辜玩家吃下多出四倍的辣椒醬、喝下難喝的飲料、聆聽難聽到極點的錄音帶。如果你想知道這些實驗背後的科學家有多常被真人實境秀的製作團隊找去,為參賽者設計噁心的挑戰內容,嗯哼,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不幸的是,遭拒後的憤怒反應還有更黑暗也更嚴重的表現方式。一再遭到嚴重拒絕所引發的攻擊行為,遠不止於白噪音或辣椒醬而已。若是將此一性質的心理創傷置之不理,傷口很快就會「感染」,並對一個人的心理健康造成重大危害。遭拒後傷人和自傷的新聞事件層出不窮。長期嚴重遭拒形成的心理創傷,若不加以治療會有什麼後果呢?失戀的人尋求報復、被郵局解雇的員工抓狂殺人、校園霸凌掀起可怕的自殺潮……只是少數幾個例子而已。
二○○一年,美國醫事總署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在社交方面遭拒是青少年表現出暴力行為的一大因素,影響更甚於加入幫派、貧窮或吸毒。遭拒的感受對情侶之間的暴力也有很大的作用。許多暴力事件都是爭風吃醋和懷疑對方劈腿所致,背後與遭拒的感受有密切的關聯。科學家調查了五百五十一起殺妻案,發現其中將近半數都是在分居或臨分居前發生的;確實也常有殺妻男在犯後坦承難以面對遭到拒絕的感受。
包括一九九九年的科倫拜(Columbine)高中慘案在內,有關校園槍擊案的研究發現,十五起事件中有十三起的凶手都曾在人際上遭受重大拒絕,並遭到同學排擠。在許多案件中,凶手特別針對曾經霸凌、捉弄或拒絕他們的同學,動手時往往先挑這些人下手。
我們或多或少都體會過被人拒絕的感受,幸而只有極少數人後來登上了頭條新聞。然而,遭拒和攻擊之間有著很強的關係,我們一定要知道:遭拒之痛很可能刺激一個人表現出平常絕不會有的行為。
3.自尊受損:就已經倒地不起了,我們還猛踹自己
遭到沉重或反覆的拒絕對自尊的傷害很大。事實上,光是回想上次遭拒的情景,就足以導致一時的自我價值感低落。不幸的是,自尊遭到的打擊通常不會到此為止。我們常在遭拒後嚴厲批評自己,徒然加重既有的痛苦,本質上無異於已經倒地不起還猛踹自己。這種反應很常見,但它很容易導致原來遭拒時的心理皮肉傷惡化感染,進而對我們的心理健康造成真正的危害。
安傑羅失去了他在航運公司的工作,因為他所屬的整個部門都在降低成本的措施下被裁掉了,然而,他卻把這種拒絕看成是針對他個人(「這些人是我的朋友欸!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將拒絕個人化使得安傑羅感覺像是朋友們不要他了,長久以來的老同事拋棄他了。他避免和前公司的任何人聯絡。他認定他們不把他看在眼裡,跟他們接觸只是自討沒趣,儘管他這種恐懼完全沒有根據。當朋友和同事主動和他聯絡時(他們當然會這麼做),他不願回覆他們的來信或留言,即使內容跟其他的工作機會有關。幾個月後,朋友們就完全不再與他聯絡了。在安傑羅的心目中,他們最後的沉默只證實了他心中的恐懼,亦即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沒關心他過。
安傑羅並不孤單。我們都會把拒絕想成是針對個人,並得出問題出在我們身上的結論,即使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種假設。回頭想想(即便要回溯到很久以前),當你被心儀的對象拒絕時,你是不是一件一件挑起自己的毛病來了?你是不是怪自己魅力不足、沒見過世面、不夠聰明、不夠多金、不夠年輕,或以上皆是?你是不是心想「這種事老是發生在我身上」、或「永遠也不會有人愛我」、或「我永遠也找不到對的人」?別人對我們的拒絕,多半不像我們認為的那麼具有針對性。就算具有針對性好了,多半也和我們滿身的缺點無關。
除了徒然將拒絕個人化之外,我們也常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以偏概全、一概而論(例如認為「這種事老是發生在我身上」或「我永遠也找不到對的人」),或是徒然苛責自己,假設做法不同就不會被拒絕。在求愛遭拒之後的自我批評尤其是個問題,因為許多人都會花很多時間分析自己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亟欲找出難以捉摸的「致命錯誤」(例如:「我為什麼等這麼久才打電話給她?」「我當初就不該喝那最後一杯酒!」「或許不該這麼快就給她看我的艾默小獵人(Elmer Fudd)卡通系列內褲。」)。
事實上,遭拒很少是因為某個致命錯誤(儘管不容否認,給心儀的女生看艾默小獵人內褲這種事,大概沒有什麼對的時機存在)。求愛(或求職)遭拒最常見的原因是彼此之間沒有火花。我們可能不符合那個人(或那間公司)在當時的需求,也可能對方心目中預設了特定的條件,而我們剛好不是對方的理想型。問題不是出在我們踏錯了關鍵的一步,或我們的人格有什麼致命的缺陷。
這些思維謬誤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只是徒增偏頗的自責,加深既有的痛苦,加倍打擊本來就已傷痕累累的自尊。被人拒絕已經夠傷的了,我們實在不需要對自己的傷口撒鹽,或已經倒地不起了還狠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