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
對於宋代以迄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中,重要思想課題、歷史人物和原始文獻,本書的研究都是開創性的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十三篇專題論文的結集。如果「辨證」是對以往學術思想史中視為當然的一些問題予以澄清,還其本來面目;「鉤沉」是對以往佚失或忽略的歷史文獻予以發掘,揭示其學術思想史的價值和意義,則本書各篇文字大都「辨證」與「鉤沉」兼而有之、融為一體。
對於宋代以迄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中,學界以往未嘗措意的一些重要思想課題、歷史人物和原始文獻,本書的研究都是開創性的。比如,作為宋明儒學史的重要原始文獻,黃宗羲和姜希轍兩部同名的《理學錄》,就是學界以往不知而為作者首次發掘而出的。《龍溪會語》這部王龍溪生前已經刊刻的最早的文集包含哪些後來王龍溪全集中沒有的文獻?王龍溪文集諸版本之間有何同異?王龍溪的《中鑒錄》是怎樣一部書?對於我們更為周延地思考明代儒學「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與「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之間的關聯具有怎樣意義?也是作者首次進行了探討。《周海門先生年譜稿》,更是迄今為止周海門年譜的首作。
而楊時已經佚失的《三經義辨》來龍去脈如何?在道學逐漸取代新學成為思想界主流的過程中究竟發揮過怎樣的作用?周汝登是否應被劃入泰州學派?《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的劃分存在哪些問題?作為晚明浙東佛教尤其禪宗振興的推動者,周汝登與佛教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如何利用《明儒王東堧東隅東日天真四先生殘稿》這部以往研究者不曾注意的文獻,結合其他相關史料考察對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填補以往泰州學派研究中的空白?如何透過《儒門法語》這部以往不太為人所知的著作,瞭解清康熙朝理學人物彭定求其人其學?本書都進行了開疆拓土的研究。
對於宋代以迄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中,學界以往未嘗措意的一些重要思想課題、歷史人物和原始文獻,本書的研究都是開創性的。比如,作為宋明儒學史的重要原始文獻,黃宗羲和姜希轍兩部同名的《理學錄》,就是學界以往不知而為作者首次發掘而出的。《龍溪會語》這部王龍溪生前已經刊刻的最早的文集包含哪些後來王龍溪全集中沒有的文獻?王龍溪文集諸版本之間有何同異?王龍溪的《中鑒錄》是怎樣一部書?對於我們更為周延地思考明代儒學「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與「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之間的關聯具有怎樣意義?也是作者首次進行了探討。《周海門先生年譜稿》,更是迄今為止周海門年譜的首作。
而楊時已經佚失的《三經義辨》來龍去脈如何?在道學逐漸取代新學成為思想界主流的過程中究竟發揮過怎樣的作用?周汝登是否應被劃入泰州學派?《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的劃分存在哪些問題?作為晚明浙東佛教尤其禪宗振興的推動者,周汝登與佛教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如何利用《明儒王東堧東隅東日天真四先生殘稿》這部以往研究者不曾注意的文獻,結合其他相關史料考察對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填補以往泰州學派研究中的空白?如何透過《儒門法語》這部以往不太為人所知的著作,瞭解清康熙朝理學人物彭定求其人其學?本書都進行了開疆拓土的研究。
目錄
序╱余英時
前言
第一章 楊時《三經義辨》考論
第二章 《樗全集》及其作者
第三章 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
第四章 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
第五章 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第六章 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有關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
第七章 日本內閣文庫藏善本明刊《中鑒錄》及其價值和意義
第八章 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
第九章 周海門與佛教——歷史與思想
第十章 周海門先生年譜稿
第十一 章黃宗羲佚著《理學錄》考論
第十二 章姜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第十三 章清康熙朝理學的異軍——彭定求的《儒門法語》初探
前言
第一章 楊時《三經義辨》考論
第二章 《樗全集》及其作者
第三章 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
第四章 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
第五章 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第六章 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有關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
第七章 日本內閣文庫藏善本明刊《中鑒錄》及其價值和意義
第八章 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
第九章 周海門與佛教——歷史與思想
第十章 周海門先生年譜稿
第十一 章黃宗羲佚著《理學錄》考論
第十二 章姜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第十三 章清康熙朝理學的異軍——彭定求的《儒門法語》初探
序/導讀
序 ∕ 余英時
2000 年 7 月我在台北初次認識國翔,他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研究生,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即後來修訂出版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北京:三聯書店,2005)。當天聚會匆促,未及詳談,不過他好學的熱忱在我心中卻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四年後他到哈佛大學進行研究工作,曾抽空來訪普林斯頓,我們才有充分的論學機會。以後他多次訪美,每來必和我有數日的交流,由於治學範圍和價值取向都很相近,這種交流為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樂趣。
國翔的專業是中國哲學,而中國哲學自正式進入大學課程之日起,便和中國哲學史是分不開的,馮友蘭雖有「照著講」(哲學史)和「接著講」(哲學)之分,但這一分別祇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因為嚴格地說,「照著講」之中已滲進了數不清的「接著講」,而「接著講」也處處離不開「照著講」。所以中國人文學界早就出現了一個共識:研究中國哲學必須雙管齊下,同時進入哲學和史學兩大領域。自胡適以來,哲史雙修便已形成北京大學的哲學傳統,國翔師承有自,並且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在本書〈前言〉中對此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但國翔尊重傳統,卻不為傳統所限,從學思發展的歷程看,他一直在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並嘗試不同的方法和觀點。自《良知學的展開》以來,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種論集問世(包括本書),重點和取向各不相同,恰可為他在學問上與時俱進的情況作見證。
本書題作《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國翔認為在他的哲學專業之外,「而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前言〉)以他的幾部論集而言,《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偏重於宗教學的進路,《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所處理的是他最擅長的哲學與哲學史方面的問題,而本書則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本史學的作品;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學科雖跨三門,研究宗旨卻一貫而下,同在闡明儒學傳統及其現代意義,故相互之間配合得很緊湊。本書所收「辨正」與「鉤沉」十三篇,事實上,都和哲學及哲學史密切相關,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上引「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之說。因為以中國的情形而言,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之間的界線是無法清楚劃分的。據我所見,關於《龍溪會語》和兩部《理學錄》的考論都涉及了明、清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正如 先師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中有關陳確《大學辨》、潘平格《求仁錄》及章學誠遺書抄本的發現與考訂也為後來清代哲學的研究提供了關鍵性的基礎文獻,其貢獻決不限於「學術史的領域」。
國翔在〈前言〉中特別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訂,他借用傳統的概念,要求哲學和哲學史的工作者「將『宋學』的思想闡發建立在『漢學』的歷史研究之上」。自「五四」整理國故以來,這一要求曾不斷有人提出,似乎早已成人文學界的一個共識。但按之實際,此說竟流為口頭禪,言之者眾而行之者寡。因此我認為國翔的論點仍值得再強調一次。他在〈合法性、視域與主體性─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的反省與前瞻〉一文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說過下面一段生動而又沉痛的話:
如果不能首先虛心、平心吃透文獻,還沒讀幾頁書就浮想聯翩,結果只能是在缺乏深透與堅實的理解和領會的情況下放縱個人的想像力,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哲學傳統終究難有相契的了解。其研究結果也只能是「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與「過度詮釋」。(收在彭國翔《儒家傳統與中國哲學:新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80。)
此文撰於 2003 年,國翔的話當然是有感而發。可知對於文獻基礎的輕忽,一直到最近還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時有所見的現象。我完全同情國翔的立場,所以下面舉一個實例來加強他的論點。
很多年前我偶然讀到一篇討論《中庸》「修道之謂教」的文字,作者斷定此處「修」字作「學」字解,乃漢初流行語,並引《淮南子.脩務訓》為證。這句引文說: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著之所脩。
作者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一層又一層的推理,最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結論。其實《脩務訓》此處的「脩」(同「修」)字是「長短」之「長」的意思,高誘在句下注得明明白白:
短、缺;脩、長也。
而且同篇還有另一處「脩短」連用之語:
人性各有所脩短。
此處「脩」字作「長短」之「長」解,更是毫無致疑的餘地。作者即使不信高注,也不應對此內證視若無睹。問題尚不止此,高誘在〈敘目〉中指出:
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
這就將劉安及其門下賓客何以用「脩」代「長」的最深層原因掘發出來了。(這裡我必須補充一句:《淮南子》所諱的是「長短」之「長」,讀作 “chang”,而不是「長幼」或「生長」之「長」,讀作 “zhang”。)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為什麼竟會誤讀「脩」字呢?這決不是由於他對古典文本的修養不足。恰恰相反,就我所知,無論是「宋學」、「漢學」或哲學,該作者的造詣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依我的推測,他大概是急於證成他的哲學論點,看到〈脩務訓〉中這個「脩」字可資利用,便不再追問此字有無歧義及其在《淮南子》中的複雜背景了。其結果則正如國翔所說,完成了一種「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
我認為這個例子特別值得哲學史研究者的警愓,因為它提供的最大教訓是︰「在哲學起飛之前,研究者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他的歷史文本,其中任何一個字都不能輕易放過!」
這是國翔第一部關於思想史和歷史文獻考釋的專集,我希望他繼續在這個園地中開墾,所以很高興地應他之約,匆匆寫下這篇短序。
2000 年 7 月我在台北初次認識國翔,他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研究生,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即後來修訂出版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北京:三聯書店,2005)。當天聚會匆促,未及詳談,不過他好學的熱忱在我心中卻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四年後他到哈佛大學進行研究工作,曾抽空來訪普林斯頓,我們才有充分的論學機會。以後他多次訪美,每來必和我有數日的交流,由於治學範圍和價值取向都很相近,這種交流為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樂趣。
國翔的專業是中國哲學,而中國哲學自正式進入大學課程之日起,便和中國哲學史是分不開的,馮友蘭雖有「照著講」(哲學史)和「接著講」(哲學)之分,但這一分別祇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因為嚴格地說,「照著講」之中已滲進了數不清的「接著講」,而「接著講」也處處離不開「照著講」。所以中國人文學界早就出現了一個共識:研究中國哲學必須雙管齊下,同時進入哲學和史學兩大領域。自胡適以來,哲史雙修便已形成北京大學的哲學傳統,國翔師承有自,並且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在本書〈前言〉中對此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但國翔尊重傳統,卻不為傳統所限,從學思發展的歷程看,他一直在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並嘗試不同的方法和觀點。自《良知學的展開》以來,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種論集問世(包括本書),重點和取向各不相同,恰可為他在學問上與時俱進的情況作見證。
本書題作《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國翔認為在他的哲學專業之外,「而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前言〉)以他的幾部論集而言,《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偏重於宗教學的進路,《儒家傳統的詮釋與思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所處理的是他最擅長的哲學與哲學史方面的問題,而本書則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本史學的作品;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學科雖跨三門,研究宗旨卻一貫而下,同在闡明儒學傳統及其現代意義,故相互之間配合得很緊湊。本書所收「辨正」與「鉤沉」十三篇,事實上,都和哲學及哲學史密切相關,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上引「屬於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的領域」之說。因為以中國的情形而言,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之間的界線是無法清楚劃分的。據我所見,關於《龍溪會語》和兩部《理學錄》的考論都涉及了明、清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正如 先師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中有關陳確《大學辨》、潘平格《求仁錄》及章學誠遺書抄本的發現與考訂也為後來清代哲學的研究提供了關鍵性的基礎文獻,其貢獻決不限於「學術史的領域」。
國翔在〈前言〉中特別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訂,他借用傳統的概念,要求哲學和哲學史的工作者「將『宋學』的思想闡發建立在『漢學』的歷史研究之上」。自「五四」整理國故以來,這一要求曾不斷有人提出,似乎早已成人文學界的一個共識。但按之實際,此說竟流為口頭禪,言之者眾而行之者寡。因此我認為國翔的論點仍值得再強調一次。他在〈合法性、視域與主體性─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的反省與前瞻〉一文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說過下面一段生動而又沉痛的話:
如果不能首先虛心、平心吃透文獻,還沒讀幾頁書就浮想聯翩,結果只能是在缺乏深透與堅實的理解和領會的情況下放縱個人的想像力,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哲學傳統終究難有相契的了解。其研究結果也只能是「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與「過度詮釋」。(收在彭國翔《儒家傳統與中國哲學:新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80。)
此文撰於 2003 年,國翔的話當然是有感而發。可知對於文獻基礎的輕忽,一直到最近還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時有所見的現象。我完全同情國翔的立場,所以下面舉一個實例來加強他的論點。
很多年前我偶然讀到一篇討論《中庸》「修道之謂教」的文字,作者斷定此處「修」字作「學」字解,乃漢初流行語,並引《淮南子.脩務訓》為證。這句引文說: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著之所脩。
作者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一層又一層的推理,最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結論。其實《脩務訓》此處的「脩」(同「修」)字是「長短」之「長」的意思,高誘在句下注得明明白白:
短、缺;脩、長也。
而且同篇還有另一處「脩短」連用之語:
人性各有所脩短。
此處「脩」字作「長短」之「長」解,更是毫無致疑的餘地。作者即使不信高注,也不應對此內證視若無睹。問題尚不止此,高誘在〈敘目〉中指出:
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
這就將劉安及其門下賓客何以用「脩」代「長」的最深層原因掘發出來了。(這裡我必須補充一句:《淮南子》所諱的是「長短」之「長」,讀作 “chang”,而不是「長幼」或「生長」之「長」,讀作 “zhang”。)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為什麼竟會誤讀「脩」字呢?這決不是由於他對古典文本的修養不足。恰恰相反,就我所知,無論是「宋學」、「漢學」或哲學,該作者的造詣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依我的推測,他大概是急於證成他的哲學論點,看到〈脩務訓〉中這個「脩」字可資利用,便不再追問此字有無歧義及其在《淮南子》中的複雜背景了。其結果則正如國翔所說,完成了一種「六經注我」式的「借題發揮」。
我認為這個例子特別值得哲學史研究者的警愓,因為它提供的最大教訓是︰「在哲學起飛之前,研究者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他的歷史文本,其中任何一個字都不能輕易放過!」
這是國翔第一部關於思想史和歷史文獻考釋的專集,我希望他繼續在這個園地中開墾,所以很高興地應他之約,匆匆寫下這篇短序。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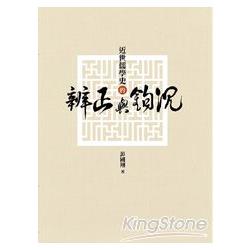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