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是叔本華於1813年撰寫完成,對經典邏輯中的充足理由律進行了詳盡的闡述,於1847年大幅擴充和改寫重新出版,成為今日的版本。叔本華強調閱讀本書的必要性,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序言裡說如果沒有熟悉《四重根》一書,「那就不可能恰當地理解現在這本著作,而且那《四重根》研究的主題內容在此總是被預設著彷彿就包含在現在這本書裡」(WI xiv)。
叔本華認為,平常的世界由四類對象(即:現實對象;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組合而成的判斷;時間和空間;人類的行為)構成,它們都是表象。充足理由律則是指,事物皆有其如其所是的理由或解釋。據此,平常世界的四類對象的存在都有其根據或理由,即存在着四種必然聯繫,每一種都構成充足理由律的一個根源,充足理由律因此便擁有了四重源根。人的行為動機是充足理由律第四種形式,人的行為必有動機、從動機得到解釋,這便通向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叔本華認為,平常的世界由四類對象(即:現實對象;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組合而成的判斷;時間和空間;人類的行為)構成,它們都是表象。充足理由律則是指,事物皆有其如其所是的理由或解釋。據此,平常世界的四類對象的存在都有其根據或理由,即存在着四種必然聯繫,每一種都構成充足理由律的一個根源,充足理由律因此便擁有了四重源根。人的行為動機是充足理由律第四種形式,人的行為必有動機、從動機得到解釋,這便通向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目錄
導讀/彭文本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迄今有關充足理由律的最重要觀點概述
第三章 以往論證的缺陷和新論證的概述
第四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一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五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二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六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三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七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四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八章 總的論點和結論
人名索引
亞瑟‧叔本華年表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迄今有關充足理由律的最重要觀點概述
第三章 以往論證的缺陷和新論證的概述
第四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一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五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二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六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三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七章 論主體物件的第四個層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
第八章 總的論點和結論
人名索引
亞瑟‧叔本華年表
序/導讀
第二版 序言
我這篇為獲取博士學位而最初在一八一三年問世的早期哲學論文,後來又成了我的整個體系的基礎。因此,不能讓它像近四年來我所不知道的那樣繼續售缺了。
另一方面,把這樣一部青年時期的著作連同它的全部錯誤和缺陷一併再次公之於世,對我來說似乎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我清楚,要不了多久,我就沒有能力再來修正它了;而到那時也將是我真正產生影響的時期,我相信,這將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因為我堅定地信守著塞涅卡的諾言:「即使嫉妒曾使你同時代的人都保持沉默,也總會有人出來公正地做出中肯判斷的。」因此,我對這部年輕時的著作做了力所能及的改進,並且,考慮到生命的短暫和難以把握,我甚至必須把這看作是一個特別的機遇,能在六十歲的時候去修正我在二十六歲時寫的東西。
然而,我在這樣做的時候,是打算寬容地對待年輕時的我自己,並且盡可能地讓他自由地討論乃至暢所欲言。只是在他提出了不正確的或多餘的東西時,或者忽略了最精彩的方面時,我才不得不打斷他的討論進程。而這種情況又是經常地出現的,這就使我的一些讀者也許會想像,他們是在聽一位老人大聲地朗讀一本年輕人寫的書,然而又不對地把它拋在一旁,以便沉浸在同一主題本身的細節之中。
不難看出,一部這樣地被修正了並經過如此長期間隔的著作,是不能達到那種只有一氣呵成的著作才具備的統一性和完美性的。甚至從風格和表達上也能發現如此巨大的差異,使得任何聰明的讀者,都會懷疑自己是在聽一位老年人還是在聽一位年輕人講話。因為一位年輕人在信心十足地提出自己的論證時的溫和而謙遜的語氣(因為這位還是相當單純的年輕人十分認真地相信,一切致力於哲學的人都只在於追求真理,而且只要是在追求真理的人都是有價值的),與一位老年人(這位老年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發現了唯利是圖的趨炎附勢之徒的上流社會的真實特徵和目的,並且自己也墜入其中)的堅定的但有時又是刺耳的音調形成了鮮明對照。而且,假如他偶爾也隨意地發洩自己的憤怒的話,公正的讀者是很難加以挑剔的;因為我們看到了當宣稱以真理為唯一目的的那些人總是在關注著他們頂頭上司的各種意圖,以及當「上帝是可以用任何一種材料來進行塑造的」(阿普列烏斯:《魔法》)延及最偉大的哲學家,而且像黑格爾這樣笨拙的騙子也厚顏無恥地躋身此列時所導致的後果。的確,德國哲學正備受著其他民族的輕蔑和嘲笑,被趕出了全部真正科學的領域,就像是為了骯髒的收入而今天賣身於這個人、明天賣身於那個人的妓女;當今一代學者的頭腦被黑格爾的胡說攪亂了:他們不會反思,既粗俗又糊塗,完全淪為一種從蛇妖的蛋裡爬出來的淺薄的唯物主義的犧牲品。多麼幸運! 下面言歸正傳。
這樣,我的讀者就將只得原諒這篇論著中語氣上的差別了;因為我在這裡不能像我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所做的那樣,以後再在一個專門的附錄中加以增補。而且,讓人們知道哪些是我在二十六歲時寫的,哪些是我在六十歲時寫的,也是無關緊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那些想通過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來獲得堅實的依據和明確的見識的人,將會從這本小薄書中獲得一點內容,以便能夠學到一些本質的、牢固的和真實的東西:我希望這將是問題的所在。對某些部分提出的進一步闡述,現在甚至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關於整個認識能力的簡要的理論,並且這種理論通過把自身嚴格限制在關於充足理由律的探討上,從一個新的特殊的側面揭示了問題;而它後來又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卷中和第二卷的有關章節中,以及在我的《康德哲學批判》中得到了完成。
叔本華
1847年9月於緬因河畔法蘭克福
我這篇為獲取博士學位而最初在一八一三年問世的早期哲學論文,後來又成了我的整個體系的基礎。因此,不能讓它像近四年來我所不知道的那樣繼續售缺了。
另一方面,把這樣一部青年時期的著作連同它的全部錯誤和缺陷一併再次公之於世,對我來說似乎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我清楚,要不了多久,我就沒有能力再來修正它了;而到那時也將是我真正產生影響的時期,我相信,這將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因為我堅定地信守著塞涅卡的諾言:「即使嫉妒曾使你同時代的人都保持沉默,也總會有人出來公正地做出中肯判斷的。」因此,我對這部年輕時的著作做了力所能及的改進,並且,考慮到生命的短暫和難以把握,我甚至必須把這看作是一個特別的機遇,能在六十歲的時候去修正我在二十六歲時寫的東西。
然而,我在這樣做的時候,是打算寬容地對待年輕時的我自己,並且盡可能地讓他自由地討論乃至暢所欲言。只是在他提出了不正確的或多餘的東西時,或者忽略了最精彩的方面時,我才不得不打斷他的討論進程。而這種情況又是經常地出現的,這就使我的一些讀者也許會想像,他們是在聽一位老人大聲地朗讀一本年輕人寫的書,然而又不對地把它拋在一旁,以便沉浸在同一主題本身的細節之中。
不難看出,一部這樣地被修正了並經過如此長期間隔的著作,是不能達到那種只有一氣呵成的著作才具備的統一性和完美性的。甚至從風格和表達上也能發現如此巨大的差異,使得任何聰明的讀者,都會懷疑自己是在聽一位老年人還是在聽一位年輕人講話。因為一位年輕人在信心十足地提出自己的論證時的溫和而謙遜的語氣(因為這位還是相當單純的年輕人十分認真地相信,一切致力於哲學的人都只在於追求真理,而且只要是在追求真理的人都是有價值的),與一位老年人(這位老年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發現了唯利是圖的趨炎附勢之徒的上流社會的真實特徵和目的,並且自己也墜入其中)的堅定的但有時又是刺耳的音調形成了鮮明對照。而且,假如他偶爾也隨意地發洩自己的憤怒的話,公正的讀者是很難加以挑剔的;因為我們看到了當宣稱以真理為唯一目的的那些人總是在關注著他們頂頭上司的各種意圖,以及當「上帝是可以用任何一種材料來進行塑造的」(阿普列烏斯:《魔法》)延及最偉大的哲學家,而且像黑格爾這樣笨拙的騙子也厚顏無恥地躋身此列時所導致的後果。的確,德國哲學正備受著其他民族的輕蔑和嘲笑,被趕出了全部真正科學的領域,就像是為了骯髒的收入而今天賣身於這個人、明天賣身於那個人的妓女;當今一代學者的頭腦被黑格爾的胡說攪亂了:他們不會反思,既粗俗又糊塗,完全淪為一種從蛇妖的蛋裡爬出來的淺薄的唯物主義的犧牲品。多麼幸運! 下面言歸正傳。
這樣,我的讀者就將只得原諒這篇論著中語氣上的差別了;因為我在這裡不能像我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所做的那樣,以後再在一個專門的附錄中加以增補。而且,讓人們知道哪些是我在二十六歲時寫的,哪些是我在六十歲時寫的,也是無關緊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那些想通過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來獲得堅實的依據和明確的見識的人,將會從這本小薄書中獲得一點內容,以便能夠學到一些本質的、牢固的和真實的東西:我希望這將是問題的所在。對某些部分提出的進一步闡述,現在甚至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關於整個認識能力的簡要的理論,並且這種理論通過把自身嚴格限制在關於充足理由律的探討上,從一個新的特殊的側面揭示了問題;而它後來又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卷中和第二卷的有關章節中,以及在我的《康德哲學批判》中得到了完成。
叔本華
1847年9月於緬因河畔法蘭克福
試閱
第一章 緒論
方法
神妙非凡的柏拉圖和令人驚異的康得一致用深沉有力的口氣,推薦了一條作為一切哲學研究以及一切科學方法的原則。他們說,我們應當同等地遵守兩個法則,即歸同法則(/01023435676)和分異法則((93:5;5<=6504),而不能有所偏廢。歸同法則指引我們按照事物之間的相似之處與共同點,把它們歸結為一些類,然後進一步把這些類歸結為種,再由種歸結為屬,等等,一直到最後得到一個包羅萬象的最高概念。由於這條法則是先驗的,即對於我們的理性來說是本質的,所以它預先就假定了自然同它自身的一致,這一假設在一條古老的規則中得到了表達:「如無必要,切勿增加實體的數目。」反之,關於分異法則,康得是這樣說的:「不要輕率地減少實體的多樣性。」這就要求我們,應當把包含在一個綜合概念中的不同的屬彼此加以區分;同樣,我們也不應當混淆包含在每一個屬中的較高級的種和較低級的種;我們還應當注意不要跳過任何下級的種,並且絕不要直接地在綜合概念下面把它們加以分類,更不必說個別的事物了:因為每一個概念都是允許向下進行分類的,並且沒有任何概念可以退回到單純的直觀。康得教導說,這兩個法則是我們理性的「超驗的」基本原則,它們先驗地假定了與事物的一致性;當柏拉圖告訴我們說,這兩個使所有科學得以產生的法則是得賜於眾神寶座上的普羅米修士之火,他看來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同一個思想。
這種方法在目前場合中的運用
儘管這種推薦很有分量,但我發現這兩個法則中的第二個,卻極少應用於我們一切知識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充足理由律這個原則。因為,雖然這個原則經常並早已被一般地陳述了,但對於它的那些極不相同的運用卻沒有做出足夠的區分,而它在每一個這種極不相同的運用中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而它在各種思維能力中的起源也就變得清楚了。如果我們將康得的哲學和所有前人的體系做一個比較,我們就會發覺,正是在我們對我們思維能力的觀察上,許多根深蒂固的錯誤乃是出自對於歸同法則的運用,而與之相對立的分異法則卻被忽略了;但是分異法則卻導致了巨大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因此我希望能允許引用康得的一段話,這段話特別強調了作為我們知識源泉的分異法則,這對於我現在的努力也是一種支持:「最重要的是把在種類和起源上與其他知識不同的各種知識分離出來,並且非常細心地避免使這些知識混同於那些在實踐的目的上一般是與它們聯在一起的其他知識。哲學家更有責任去做化學家在元素分析和數學家在純數學方面所做的事情,以便能夠清楚地闡明在知識的濫用中屬於知識的一個特殊種類的那一部分,及其特有的價值和影響。」
這一研究的有用性
如果我能成功地指明,這個構成我們研究主題的原則並不是直接地產生於我們理智的一個原始觀念,而是產生於一些不同的觀念,那麼就可以推知,它作為先天確定的原則而自身表現出來的必然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一個並且是同樣的;相反,它必定是與這一原則本身的來源一樣是多重的。因此,誰要是把自己的結論建立在這個原則之上,他就有責任清楚地闡明他的結論由以建立的那種特殊的必然基礎,並且把這個基礎用一個特殊的名字來表達(這正是我所要指出的)。我希望這樣做將使我們在進行哲學思考的時候,能夠更加清楚和準確;因為我認為,我們必須借助於對每一單個表述的精確定義來獲得最大限度的明確性,這是抵制謬誤和故意欺騙的手段,也是保證我們永久地、牢固地佔有我們在哲學領域中每一個新獲得的觀念而不必害怕因為任何誤解和可能在後來發現的歧義而使它得而復失。真正的哲學家總是追求真知灼見,並力圖使自己像一個瑞士的湖泊而不像那混濁而湍急的山洪,———瑞士的湖泊以她的平靜而將幽深與清澈結合起來,正是由於清澈而使幽深自身得到了展示。瓦文納格斯(>=?@34=A2?3B)說道:「C=:D=A6E33B6D=F0443;05G3B9H5D0B09H3B「(明晰性是哲學論證的信用證)。相反,那些偽哲學家,他們的那些措辭,實際上並不像塔里蘭特說的那樣是為了掩飾他們的思想,而是要掩蓋他們的空虛,並且往往要讀者為他們的不可理解的體系負責,這種體系其實是產生於他們的混亂思想本身。這就說明瞭為什麼在某些哲學家那裡———例如在謝林那裡———教訓的口氣是如此經常地變成了指責的口氣,並且讀者常常由於假定的缺乏理解能力而事先就受到挑剔。
充足理由律的重要意義
充足理由律的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真正地被稱為一切科學的基礎。所謂科學就是指一個觀念的體系,也就是一個與彼此無聯繫的觀念的單純堆積相對立的由互相聯繫著的觀念構成的總體。然而,把這個體系中的各個成員組織到一起的,如果不是充足理由律,又是什麼呢? 把每一種科學同單純的觀念堆積區分開來,恰恰就是說這樣的觀念都是從它們的理由那裡由此及彼地推導出來的。所以,柏拉圖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即使是些真實的觀念,如果不是有人通過因果的證明而把它們聯繫到一起,也不具有多大的價值。」。而且,正如在我們的研究進程中將會看到的,幾乎每一種科學中都包含著一些可以由之而推演出結果的原因的觀念,同樣,也包含著其他一些來自於理由的作為結論的必然性觀念。對此,亞裡斯多德曾這樣表述道:「一切理智的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理智的知識,都涉及了一些原因和原則。」這樣,正是由於一切事物都必定有其理由的先驗假設,它使我們有權利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探求為什麼,我們才能夠有把握地把這個為什麼稱為一切科學之母。
關於充足理由律本身
我打算進一步表明,充足理由律是與某些先驗的觀念相通用的一種表達。同時,它也必須按照這樣或那樣的公式來被陳述。我選擇了沃爾夫的一個最富有內容的公式:「任何事物都有其為什麼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的由。」。
方法
神妙非凡的柏拉圖和令人驚異的康得一致用深沉有力的口氣,推薦了一條作為一切哲學研究以及一切科學方法的原則。他們說,我們應當同等地遵守兩個法則,即歸同法則(/01023435676)和分異法則((93:5;5<=6504),而不能有所偏廢。歸同法則指引我們按照事物之間的相似之處與共同點,把它們歸結為一些類,然後進一步把這些類歸結為種,再由種歸結為屬,等等,一直到最後得到一個包羅萬象的最高概念。由於這條法則是先驗的,即對於我們的理性來說是本質的,所以它預先就假定了自然同它自身的一致,這一假設在一條古老的規則中得到了表達:「如無必要,切勿增加實體的數目。」反之,關於分異法則,康得是這樣說的:「不要輕率地減少實體的多樣性。」這就要求我們,應當把包含在一個綜合概念中的不同的屬彼此加以區分;同樣,我們也不應當混淆包含在每一個屬中的較高級的種和較低級的種;我們還應當注意不要跳過任何下級的種,並且絕不要直接地在綜合概念下面把它們加以分類,更不必說個別的事物了:因為每一個概念都是允許向下進行分類的,並且沒有任何概念可以退回到單純的直觀。康得教導說,這兩個法則是我們理性的「超驗的」基本原則,它們先驗地假定了與事物的一致性;當柏拉圖告訴我們說,這兩個使所有科學得以產生的法則是得賜於眾神寶座上的普羅米修士之火,他看來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同一個思想。
這種方法在目前場合中的運用
儘管這種推薦很有分量,但我發現這兩個法則中的第二個,卻極少應用於我們一切知識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充足理由律這個原則。因為,雖然這個原則經常並早已被一般地陳述了,但對於它的那些極不相同的運用卻沒有做出足夠的區分,而它在每一個這種極不相同的運用中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而它在各種思維能力中的起源也就變得清楚了。如果我們將康得的哲學和所有前人的體系做一個比較,我們就會發覺,正是在我們對我們思維能力的觀察上,許多根深蒂固的錯誤乃是出自對於歸同法則的運用,而與之相對立的分異法則卻被忽略了;但是分異法則卻導致了巨大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因此我希望能允許引用康得的一段話,這段話特別強調了作為我們知識源泉的分異法則,這對於我現在的努力也是一種支持:「最重要的是把在種類和起源上與其他知識不同的各種知識分離出來,並且非常細心地避免使這些知識混同於那些在實踐的目的上一般是與它們聯在一起的其他知識。哲學家更有責任去做化學家在元素分析和數學家在純數學方面所做的事情,以便能夠清楚地闡明在知識的濫用中屬於知識的一個特殊種類的那一部分,及其特有的價值和影響。」
這一研究的有用性
如果我能成功地指明,這個構成我們研究主題的原則並不是直接地產生於我們理智的一個原始觀念,而是產生於一些不同的觀念,那麼就可以推知,它作為先天確定的原則而自身表現出來的必然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一個並且是同樣的;相反,它必定是與這一原則本身的來源一樣是多重的。因此,誰要是把自己的結論建立在這個原則之上,他就有責任清楚地闡明他的結論由以建立的那種特殊的必然基礎,並且把這個基礎用一個特殊的名字來表達(這正是我所要指出的)。我希望這樣做將使我們在進行哲學思考的時候,能夠更加清楚和準確;因為我認為,我們必須借助於對每一單個表述的精確定義來獲得最大限度的明確性,這是抵制謬誤和故意欺騙的手段,也是保證我們永久地、牢固地佔有我們在哲學領域中每一個新獲得的觀念而不必害怕因為任何誤解和可能在後來發現的歧義而使它得而復失。真正的哲學家總是追求真知灼見,並力圖使自己像一個瑞士的湖泊而不像那混濁而湍急的山洪,———瑞士的湖泊以她的平靜而將幽深與清澈結合起來,正是由於清澈而使幽深自身得到了展示。瓦文納格斯(>=?@34=A2?3B)說道:「C=:D=A6E33B6D=F0443;05G3B9H5D0B09H3B「(明晰性是哲學論證的信用證)。相反,那些偽哲學家,他們的那些措辭,實際上並不像塔里蘭特說的那樣是為了掩飾他們的思想,而是要掩蓋他們的空虛,並且往往要讀者為他們的不可理解的體系負責,這種體系其實是產生於他們的混亂思想本身。這就說明瞭為什麼在某些哲學家那裡———例如在謝林那裡———教訓的口氣是如此經常地變成了指責的口氣,並且讀者常常由於假定的缺乏理解能力而事先就受到挑剔。
充足理由律的重要意義
充足理由律的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真正地被稱為一切科學的基礎。所謂科學就是指一個觀念的體系,也就是一個與彼此無聯繫的觀念的單純堆積相對立的由互相聯繫著的觀念構成的總體。然而,把這個體系中的各個成員組織到一起的,如果不是充足理由律,又是什麼呢? 把每一種科學同單純的觀念堆積區分開來,恰恰就是說這樣的觀念都是從它們的理由那裡由此及彼地推導出來的。所以,柏拉圖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即使是些真實的觀念,如果不是有人通過因果的證明而把它們聯繫到一起,也不具有多大的價值。」。而且,正如在我們的研究進程中將會看到的,幾乎每一種科學中都包含著一些可以由之而推演出結果的原因的觀念,同樣,也包含著其他一些來自於理由的作為結論的必然性觀念。對此,亞裡斯多德曾這樣表述道:「一切理智的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理智的知識,都涉及了一些原因和原則。」這樣,正是由於一切事物都必定有其理由的先驗假設,它使我們有權利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探求為什麼,我們才能夠有把握地把這個為什麼稱為一切科學之母。
關於充足理由律本身
我打算進一步表明,充足理由律是與某些先驗的觀念相通用的一種表達。同時,它也必須按照這樣或那樣的公式來被陳述。我選擇了沃爾夫的一個最富有內容的公式:「任何事物都有其為什麼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的由。」。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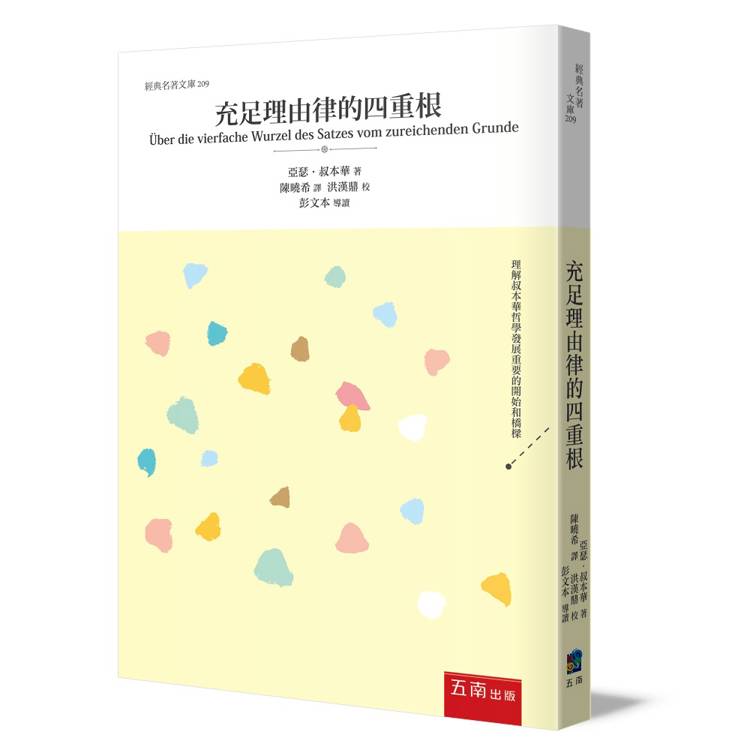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