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鷲山外山:心道法師傳(增訂版)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一位大修行者的求道歷程,繫乎人性又超越世間的生命風光
心道法師,一九四八年出生於緬甸,長於台灣,一生極富傳奇色彩。十五歲那年,他在兩臂及身上刺下「悟性報觀音」、「吾不成佛誓不休」、「真如度眾生」的堅定求道誓言。二十五歲出家為僧,修習無比艱苦的頭陀行,經歷世間最幽隱不堪的塚間苦修與斷食閉關。出關後,創立「靈鷲山.無生道場」和「世界宗教博物館」,開展普度天下眾生的志業。心道法師那股矢志不移的求道毅力、樂觀且寬容的個性、恢宏的國際視野,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畏精神,讓每個見證過、追隨過他步伐的人深受感染。
《靈鷲山外山》詮釋了心道法師的苦修與菩薩道精神。他的故事以戰雲密布的滇緬山區為起點,隨後穿過台灣大乘佛教的叢林,深入艱苦的塚間修和頭陀行,並於一九八三年創立靈鷲山,以「慈悲與禪」為宗風,以世界和平為終極目標,展開他的弘法志業。此書在十年前發行的初版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寫與增訂,對心道法師的三乘法脈之傳承、個人的禪修經歷和弘化大願,提出更完整、細微,且精闢的詮釋;同時也新增了近十年來的事跡,從宏觀角度闡述了心道法師如何從世界宗教博物館,走向倡導世界宗教和平的道路,以及他佇足於華嚴聖山計畫的藍圖上,向世人勾勒的那爛陀夢想。
心道法師,一九四八年出生於緬甸,長於台灣,一生極富傳奇色彩。十五歲那年,他在兩臂及身上刺下「悟性報觀音」、「吾不成佛誓不休」、「真如度眾生」的堅定求道誓言。二十五歲出家為僧,修習無比艱苦的頭陀行,經歷世間最幽隱不堪的塚間苦修與斷食閉關。出關後,創立「靈鷲山.無生道場」和「世界宗教博物館」,開展普度天下眾生的志業。心道法師那股矢志不移的求道毅力、樂觀且寬容的個性、恢宏的國際視野,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畏精神,讓每個見證過、追隨過他步伐的人深受感染。
《靈鷲山外山》詮釋了心道法師的苦修與菩薩道精神。他的故事以戰雲密布的滇緬山區為起點,隨後穿過台灣大乘佛教的叢林,深入艱苦的塚間修和頭陀行,並於一九八三年創立靈鷲山,以「慈悲與禪」為宗風,以世界和平為終極目標,展開他的弘法志業。此書在十年前發行的初版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寫與增訂,對心道法師的三乘法脈之傳承、個人的禪修經歷和弘化大願,提出更完整、細微,且精闢的詮釋;同時也新增了近十年來的事跡,從宏觀角度闡述了心道法師如何從世界宗教博物館,走向倡導世界宗教和平的道路,以及他佇足於華嚴聖山計畫的藍圖上,向世人勾勒的那爛陀夢想。
目錄
序 釋心道 2
第1章 在緬甸的童年1948~1960
緬甸,一九四八 10
紅色羅漢鞋,巨大的蟻穴 14
頹壞的幸福,行走的江湖 18
滇緬孤軍的生活版圖 21
飛行的羅漢,出家的種子 24
罌粟的天堂,滇緬邊區的煉獄 28
第2章 少年楊進生1961~1972
撤向一九六一年春天的台灣 36
觀音聖號,開啟佛法大門 40
十五歲的刺青,起誓求道之心 43
大俠夢,劍及履及的人格特質 45
乾媽謝鳳英,一貫道的點傳師 48
梅花盟,返鄉治世的狂想 50
求一個坐牢的罪名 54
逆境中的貴人 56
被時間揉成小小一團的情書 62
摯友李逢春的身故 64
第3章 出家後的苦修1973~1982
在佛光山剃度出家 68
只要打坐就勇猛精進的漢子 72
蘭花房,參透孤獨 76
頭陀行,以摩訶迦葉、密勒日巴為師 80
圓明寺的魑魅魍魎 83
靈山塔內,思索死生 88
塚間修,參透諸行無常 92
密勒日巴示現於禪定中 96
如幻山房,道心的試煉場 99
出家弟子的緣分與考驗 103
禪師的修行與生活 107
顯密圓融,本來一味 109
關於成佛的困惑 111
修行之餘,物我無間 113
武舉人古堡,斷食以了脫生死 115
第4章 初建靈鷲山1983~1988
鷹仔山,出火與請火的傳說 124
普陀巖,更艱難的閉關斷食 126
懸崖之下,別有洞天 132
山風海雨交接處的道場 135
無生道場的命名與宏願 141
隨機逗教的生活禪 144
臨濟宗風,大機大用 150
善待眾生,凡事用心 158
第5章 法脈傳承與弘化大願1989~2013
臨濟法脈,以禪為體 164
禪定戒律,以南傳為基石 169
噶陀傳承,以密為用 174
三乘合一,從頭陀行到菩薩道 179
宇宙是一個記憶體 182
毀謗是度化的緣起 184
菩薩道,讓眾生離苦得樂 187
冥陽兩利的圓滿施食 190
以大悲法會為起點 191
啟建水陸,度盡眾生 195
戒德老和尚主法十五年 202
造就一個解冤釋結的淨土 204
弘法度眾不言累 207
以道場為家的義工和護法 210
第6章 世界宗教與華嚴聖山1989~2013
遙契太虛大師的理念 214
窮和尚的春秋大夢 218
不知天高地厚的宗博計畫 221
沒有心理負擔的宗教接觸 223
徐徐展開垂天的大翼 225
結結實實踏出了一大步 228
心和平,世界就和平 230
我來看看我能做些什麼? 234
諸神殿堂的落成 238
史無前例的「回佛對談」 243
伊斯蘭教的友誼 250
寧靜運動,禪修的極大化 253
斷食閉關,回歸本山 258
「華嚴世界」是「緣起成佛」的工作 264
現代「那爛陀」的宏願 267
我這一生就沒有白來了 271
心道法師暨靈鷲山大事年表 275
附錄
萬教並生蓮花─心道法師前傳 柏楊 306
春深猶有子規啼—訪道與勘驗 林谷芳 309
第1章 在緬甸的童年1948~1960
緬甸,一九四八 10
紅色羅漢鞋,巨大的蟻穴 14
頹壞的幸福,行走的江湖 18
滇緬孤軍的生活版圖 21
飛行的羅漢,出家的種子 24
罌粟的天堂,滇緬邊區的煉獄 28
第2章 少年楊進生1961~1972
撤向一九六一年春天的台灣 36
觀音聖號,開啟佛法大門 40
十五歲的刺青,起誓求道之心 43
大俠夢,劍及履及的人格特質 45
乾媽謝鳳英,一貫道的點傳師 48
梅花盟,返鄉治世的狂想 50
求一個坐牢的罪名 54
逆境中的貴人 56
被時間揉成小小一團的情書 62
摯友李逢春的身故 64
第3章 出家後的苦修1973~1982
在佛光山剃度出家 68
只要打坐就勇猛精進的漢子 72
蘭花房,參透孤獨 76
頭陀行,以摩訶迦葉、密勒日巴為師 80
圓明寺的魑魅魍魎 83
靈山塔內,思索死生 88
塚間修,參透諸行無常 92
密勒日巴示現於禪定中 96
如幻山房,道心的試煉場 99
出家弟子的緣分與考驗 103
禪師的修行與生活 107
顯密圓融,本來一味 109
關於成佛的困惑 111
修行之餘,物我無間 113
武舉人古堡,斷食以了脫生死 115
第4章 初建靈鷲山1983~1988
鷹仔山,出火與請火的傳說 124
普陀巖,更艱難的閉關斷食 126
懸崖之下,別有洞天 132
山風海雨交接處的道場 135
無生道場的命名與宏願 141
隨機逗教的生活禪 144
臨濟宗風,大機大用 150
善待眾生,凡事用心 158
第5章 法脈傳承與弘化大願1989~2013
臨濟法脈,以禪為體 164
禪定戒律,以南傳為基石 169
噶陀傳承,以密為用 174
三乘合一,從頭陀行到菩薩道 179
宇宙是一個記憶體 182
毀謗是度化的緣起 184
菩薩道,讓眾生離苦得樂 187
冥陽兩利的圓滿施食 190
以大悲法會為起點 191
啟建水陸,度盡眾生 195
戒德老和尚主法十五年 202
造就一個解冤釋結的淨土 204
弘法度眾不言累 207
以道場為家的義工和護法 210
第6章 世界宗教與華嚴聖山1989~2013
遙契太虛大師的理念 214
窮和尚的春秋大夢 218
不知天高地厚的宗博計畫 221
沒有心理負擔的宗教接觸 223
徐徐展開垂天的大翼 225
結結實實踏出了一大步 228
心和平,世界就和平 230
我來看看我能做些什麼? 234
諸神殿堂的落成 238
史無前例的「回佛對談」 243
伊斯蘭教的友誼 250
寧靜運動,禪修的極大化 253
斷食閉關,回歸本山 258
「華嚴世界」是「緣起成佛」的工作 264
現代「那爛陀」的宏願 267
我這一生就沒有白來了 271
心道法師暨靈鷲山大事年表 275
附錄
萬教並生蓮花─心道法師前傳 柏楊 306
春深猶有子規啼—訪道與勘驗 林谷芳 309
序/導讀
序
釋心道
三十年前,我到荖蘭山閉關斷食,很辛苦,幾乎連命都沒有了。
剛開始借住在普陀巖山洞,那時看管仙公廟的詹廟祝和福隆當地的耆老,還有後來把聖山寺捐給我的吳春泉老先生,都說這山很奇,是聖山。
這裡一片荒山漫漫,沒有水,沒有電,什麼都沒有,只有前山腰的仙公廟、普陀巖。
有一天,我坐在斷巖上望著海,一望無際,海潮一波波推送過來,日日夜夜的潮音,我感到這裡未來會度很多的人,很多海外的緣。當時徒弟法性還笑我說:師父啊,你會不會餓到「起了肖」?明天怎麼過還是問題,這裡什麼也沒有啊!師父你是怎麼看到未來的呢?
出關後,每天有很多人來找我,我天天等著人上門來「踢館」;都是問些人生問題,什麼都問,還有很多宗教問題,也是緣起。
這樣一路過到今天。回頭看看這裡,就是一個菩薩居的地方,這裡處處是緣起,處處是菩提。它不屬於羅漢,也不只是道廟,這裡是觀音訂走的地方,觀音在這裡產生能量,祂要做的事就是對應這時代的疑難雜症,祂有一套呈現教化因緣的方法與工具,我覺得我只是祂的手腳,這裡是菩薩居地。
一切從零開始。靈鷲山團隊是從籌設世界宗教博物館開始的,沒有建宗博這個大願力,就沒有這個團體。一開始,我們在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找一些專家顧問互動,慢慢激盪出五大志業,其中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因緣先成熟。有了計畫,接下來就是怎麼啟動?當時宜蘭有一家證券公司,他們主管來結緣,整個公司的人都來皈依,讓我們去說明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理念。
從宜蘭開始,再往台北,到全台走透透,我們開始做人的連結,有了人就成立護法會;為了募款,後來水陸法會的因緣也開始了。又因為建宗教博物館要得到各宗教的見解與支持,我們四處參訪各宗教,主動去敲門,謙卑地向他們請教,就這樣,一路把願力擴散開來,把很多資源串聯起來,可以說大家有什麼就出什麼、會什麼就幫忙什麼,一遇到問題就是突破,突破到底。
我是一個窮和尚,什麼也沒有,什麼專業也不懂,就是一直拜會、一直做關懷、一直在緣上去貫串我的體會,只是把這些有緣的人都啟動起來,這樣日以繼夜地做。可以說,我這一生到現在最大的供佛,就是宗博。然後,接著就是要把這個和平的基因延伸出去,複製這個和平基因,延伸到一個人人可以成佛的學園。
不修行,我不可能有這個願力。這個願,就是〈大悲咒〉的力量,也是觀音菩薩的力量,一一化為我的實踐。
專文推薦
萬教並生蓮花──心道法師傳∕柏楊
當一個舊星球破碎時,另一個新星球會再昇起;當一個舊人生破碎時,另一個新人生會再創造。祇要你有足夠的虔敬,總有一天你會感謝你苦難的來源,同時也是你營養的來源。人,不可能瀟灑走一回,他的負擔跟他的使命,同時沈重。
心道大師奇離的喪父,又詭異的失母,我讀到那一段,滿紙眼淚,他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妹妹,夜深人靜,悄悄走到年紀還不到四歲的心道床前,掖了掖被子,向半睡半醒的孩子凝視著,沒有吻他,沒有抱他,沒有一句叮嚀他的話,只留下來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回頭走去,從此沒有任何消息,孩子的心滴血,我們讀者的心也隨著滴血。
這個無法彌補的遺憾,永遠掛在心道大師的心頭,對他的影響是入骨的,所以,他終身從不離棄一個人,尤其是那些心靈上倚靠他的人。
在另一片世界裡,我和心道大師有一個共同奇特的緣分,一九五○年代,我在報上寫「異域」,十年監牢之後,我又繼續寫「金三角.荒城」,曾引起廣泛的「送炭到泰北運動」,而心道大師就是第一次撤退的第一代孤軍(《異域》一書中對這第一次的撤退有過介紹)。心道大師那時候才十幾歲!寫到這裡,回想五十年前,當還是孩子的心道在清泉崗赤膊操練的時候,柏楊在汗流浹背的伏案報導孤軍故事,而今心道安坐在他的宗教博物館,柏楊繼續汗流浹背的伏案為心道的傳記寫序,這就是緣分吧!
每個人生來都有宗教情感,心道大師生在緬甸這個佛教國家裡,他來台灣後,又不斷的接觸到佛教大師,所以他的悟道很早,而且有更廣的開拓。真正為心道大師剃度,把他領進佛門的是星雲大師。邊區孤軍第一次撤退到台灣後,心道年紀實在太小,那年才十四歲,身子還沒有鎗的三分之二高,他既扛不動鎗,鎗也扛不動他,軍事訓練單位對這一批孩子們,實在無從著手,於是由教育部分別把他們轉入各小學──白天到學校讀書,晚上回營房睡覺。心道大師讀過員樹林國小,而就在這個時候,他迷上了武俠小說,他和一般小朋友一樣,決定當大俠,打盡世界不公平的事,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一本武俠秘笈,幾個小毛頭自己練起神功,尤其又練起輕功,方法很簡單,祇要在腳上綁個砂袋即可,在上學的路上走得怪模怪樣,堅信有一天,可以練成飛簷走壁,他們有一個信條,當大俠不是夢,而是正義與力量的延伸。
大俠當然沒有當成,心道大師最後被星雲大師接入佛門,剃度出家。我想起一個比喻,星雲大師好像唐僧,莊嚴肅穆,嚴守戒律,慷慨高貴,捨身佈施。而心道大師則像孫悟空,雲遊各界。二十年後,心道大師成立宗教博物館,組成新的淨土。使萬教並生蓮花,星雲為他祝福。星雲東天送經,使當年玄奘西天所取的經,更加豐滿後,再東傳萬邦。
出家千千萬萬,高僧是國家之寶,面對高僧,我們合十頂禮。
導讀
春深猶有子規啼─訪道與勘驗∕林谷芳
禪問答中有個大家熟悉得不得了的故事:
白居易向鳥窠禪師問佛法大意,鳥窠給予最「傳統」的答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以為這答案三歲小兒都曉得,鳥窠則回以「三歲小兒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的回答。
這回答在佛門是老生常談,鳥窠的對應從機鋒高峻的禪者來說,更係聞之須掩耳疾走之論,不過,如此卑之無甚高論的言語,後來卻仍不斷出現在披雲狂笑的禪門,究其故,則因它扣準了修行的原點。
修行是什麼?對禪或其他法門而言,核心都在「了生死」。而「了生死」並非語言文字的遊戲,它只能親身體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因此,看個修行人,重點不在他談的理論有多系統,多玄妙,而在他是否有能力「化抽象的哲理為具體的證悟」。
的確,修行是化抽象哲理為具體證悟之事,因此,求道雖強調解行並重,但所有的解如果未有化成行的能量,就只能是一種戲論。也所以,讀遍經論,常不如直接閱讀行者所體踐出來的生命大書有用,所謂「聽其言」,不如「觀其行」,正是許多人所以須親近大德的原因。而在特別標舉言語道斷的宗門,祖師行儀更是一個離乎言語相的公案,師徒能否承續,關鍵往往就在徒弟能否從師門行儀中得到自己聞思的印證。
不過,能親炙固然最好,但還得具備一定的時節因緣,因此,祖師傳記乃常成為有心者的重要資糧,歷史中從較簡的高僧傳、傳燈錄,到詳細的祖師年譜及傳記之所以能不絕於書,也正緣於此。它是我們在談修行、談傳承、談法門所不能忽略的一環,而其中的內容、體例,以及讀者切入角度的不同,則使它們在修行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從體例而言,年譜較如實,傳記則常有主觀的想像,而小說式的寫法,主人公更往往只是寫者觀點的代言。當然,公案、語錄的記載,精簡且直扣核心,最能予人啟發,但行儀既略,有心者乃很難由之窺知行者那點滴在心頭的轉折歷程,於是也只能停留在心嚮往之的階段。
至於內容,老實深刻的行者本以整個生命面對生死,不著一處,全體即是,下筆就難,以此行儀中應以何者為核心,乃成為寫者落筆取捨的關鍵。而在此,因不同人的不同詮釋,彼此自可差異極大,例如弘一法師,要以俗情的文化藝術,還是似根柢的宗教情懷寫他出家的因緣,結果就可判若兩人。
而即使體例及寫法問題不大,誰來讀這本書也可以導出不同的判準,有些人看祖師行儀像在求靈異紀錄,有些人則永遠以人的世界為最終關懷,有的人看度眾事業,有的人卻窺內心幽微,有人想理出修行步驟,有人則強調悟後風光。
就這樣,雖說高僧傳略、祖師行儀是重要資糧,但就如佛法講因緣般,不同對應乃可以使它是藥,也可以使它是毒,而就中,讀者既是攝受者,自己能否獨具隻眼就成為個中關鍵,過去講「師訪徒三年,徒訪師三年」即因於此。
師訪徒是尋人才,伯樂找千里馬,機率小,但不容易看走眼,因為是以先進印後學;可徒訪師就不然,以外行看「內行」,未證之地談已證之人,看走眼的機率基本就大,而這也正是怪力亂神始終可大張旗鼓的原因,多少人或為印象所惑,或因理事不夠圓融強作最勝義解,結果不要說魔軍可以惑眾,連江湖小卒也常沐猴而冠,可憐的是訪道之人,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莫此為甚。
***
不過,勘驗雖不易,卻也非完全無法可想。首先,修行的系統固提供了一個基底座標,不同行儀的比較也讓勘驗有了相對基準。這些基準,有些是所有行者必須共同體現的,例如,向道之心、如實行儀。有些則是不同法門所欲達致的,例如禪者根柢上有其自性天真或截斷眾流的要求,密宗行者則要求理事相即,在不同因緣內呈現不同對應,其間的不同,在禪是一絲不掛,直取本心,只破不立;在密則為即事而真,我手即為佛手,從妙有體証。
當然,宗派之外,還有個人生命情性與修持法門顯現的不同生命風光。
如此,若能從上述三個面相切入,對行者的勘驗固不能說能立即相契,但雖不中亦不遠矣!而這也正是修行的原點儘管在體證,深入經論卻永遠有其重要性的原因。因為,當應世的人格不在時,故應「以法為師」,而即使在世,習者若要免於識而不見,仍需系統修行理論的指引。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行者的行儀,下面的一些重點恐怕是大家必須注意到的。
首先:行者的向道因緣何在?是生具夙慧,天生具有宗教心?還是因某種因緣使然?這種因緣是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世間情?還是對死生天塹的諦觀?也或者只是對未知世界的嚮往?
其次:行者是以如何的心情,如何的實踐來對應這向道的因緣?是捨離萬緣,孤獨求道?還是寄身叢林,直領宗風?甚或是慈悲應緣,度人自度?在此,行者對世間變動事務依戀的俗情總要能不在,也所以老實、堅忍、綿密就是許多行者人格的基本特質,常常讓人為其一生的投入而動容。
此外,更關鍵的是他修習什麼法門,又如何相應?坦白說,這才真是考驗習者的地方,而就此,哪個法門是以信為本?哪個法門強調智為能入?哪種法門直取慈悲?哪種法門強調能量轉換?又有哪個法門當下即是?習者不僅基點的認知要準,對行者相應的勘驗尤其要在訪道中不斷反思觀照,終至具備識人的法眼才行。
最後,行者成就整體生命的風光何在?或他面臨生死所映現的成就為何?更是觀照的焦點。前者就整體觀之,可免去「但見秋毫,不見輿薪」之病,例如有些乩童雖有靈通,但除此之外,一無可取,不僅缺乏生命境界,法門其實也不足恃;而後者則是最核心,最無可重來的應現,也是最嚴厲的考驗,因此禪者示寂乃成為禪門最大量也最值得參究的公案,就如天童宏智臨終偈有「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淹沒,秋水連天」之句,以此,他一生標舉的默照風光才有堅實的支撐,而弘一雖不在宗門,但去掉了「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去掉了「悲欣交集」,則一生行儀所能照亮人者,恐怕也將減半。
坦白說,一個人掌握了這些基點要來勘驗行者,則除非對方真乃潛修密行之輩,應該都能窺見一些真實;甚且,經由理論與實證的磨練,對「內修菩薩密,外顯羅漢形」的微細行儀,也能體得事情並非只是外表所見到的那般;至於那些妖言惑眾,未證言證者更就難逃法眼了。
有了勘驗,求道者就會回到「更如實」的立場,來看修行者應現的一切,不會活在一種假相的追求中。這就如同釋尊有背痛,行者觀照的不應是他有沒有背痛,而是悟者究係如何面對苦痛。猶記得年輕時,有一好友一次提及他在寺院中聽經,看到座主面對炎炎夏日,汗如雨下,邊拭汗邊講經時的震撼般,一個求道者在了解了「和尚也是人,也要流汗」時,其在「如實」上就又過了一層。當然,話說回頭,行者真的在炎夏中都必會揮汗嗎?有沒有不畏寒暑的情形?有沒有以心轉物的生命?「安禪不須入山水,滅卻切心頭火自涼」真只是一句唯心的
釋心道
三十年前,我到荖蘭山閉關斷食,很辛苦,幾乎連命都沒有了。
剛開始借住在普陀巖山洞,那時看管仙公廟的詹廟祝和福隆當地的耆老,還有後來把聖山寺捐給我的吳春泉老先生,都說這山很奇,是聖山。
這裡一片荒山漫漫,沒有水,沒有電,什麼都沒有,只有前山腰的仙公廟、普陀巖。
有一天,我坐在斷巖上望著海,一望無際,海潮一波波推送過來,日日夜夜的潮音,我感到這裡未來會度很多的人,很多海外的緣。當時徒弟法性還笑我說:師父啊,你會不會餓到「起了肖」?明天怎麼過還是問題,這裡什麼也沒有啊!師父你是怎麼看到未來的呢?
出關後,每天有很多人來找我,我天天等著人上門來「踢館」;都是問些人生問題,什麼都問,還有很多宗教問題,也是緣起。
這樣一路過到今天。回頭看看這裡,就是一個菩薩居的地方,這裡處處是緣起,處處是菩提。它不屬於羅漢,也不只是道廟,這裡是觀音訂走的地方,觀音在這裡產生能量,祂要做的事就是對應這時代的疑難雜症,祂有一套呈現教化因緣的方法與工具,我覺得我只是祂的手腳,這裡是菩薩居地。
一切從零開始。靈鷲山團隊是從籌設世界宗教博物館開始的,沒有建宗博這個大願力,就沒有這個團體。一開始,我們在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找一些專家顧問互動,慢慢激盪出五大志業,其中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因緣先成熟。有了計畫,接下來就是怎麼啟動?當時宜蘭有一家證券公司,他們主管來結緣,整個公司的人都來皈依,讓我們去說明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理念。
從宜蘭開始,再往台北,到全台走透透,我們開始做人的連結,有了人就成立護法會;為了募款,後來水陸法會的因緣也開始了。又因為建宗教博物館要得到各宗教的見解與支持,我們四處參訪各宗教,主動去敲門,謙卑地向他們請教,就這樣,一路把願力擴散開來,把很多資源串聯起來,可以說大家有什麼就出什麼、會什麼就幫忙什麼,一遇到問題就是突破,突破到底。
我是一個窮和尚,什麼也沒有,什麼專業也不懂,就是一直拜會、一直做關懷、一直在緣上去貫串我的體會,只是把這些有緣的人都啟動起來,這樣日以繼夜地做。可以說,我這一生到現在最大的供佛,就是宗博。然後,接著就是要把這個和平的基因延伸出去,複製這個和平基因,延伸到一個人人可以成佛的學園。
不修行,我不可能有這個願力。這個願,就是〈大悲咒〉的力量,也是觀音菩薩的力量,一一化為我的實踐。
專文推薦
萬教並生蓮花──心道法師傳∕柏楊
當一個舊星球破碎時,另一個新星球會再昇起;當一個舊人生破碎時,另一個新人生會再創造。祇要你有足夠的虔敬,總有一天你會感謝你苦難的來源,同時也是你營養的來源。人,不可能瀟灑走一回,他的負擔跟他的使命,同時沈重。
心道大師奇離的喪父,又詭異的失母,我讀到那一段,滿紙眼淚,他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妹妹,夜深人靜,悄悄走到年紀還不到四歲的心道床前,掖了掖被子,向半睡半醒的孩子凝視著,沒有吻他,沒有抱他,沒有一句叮嚀他的話,只留下來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回頭走去,從此沒有任何消息,孩子的心滴血,我們讀者的心也隨著滴血。
這個無法彌補的遺憾,永遠掛在心道大師的心頭,對他的影響是入骨的,所以,他終身從不離棄一個人,尤其是那些心靈上倚靠他的人。
在另一片世界裡,我和心道大師有一個共同奇特的緣分,一九五○年代,我在報上寫「異域」,十年監牢之後,我又繼續寫「金三角.荒城」,曾引起廣泛的「送炭到泰北運動」,而心道大師就是第一次撤退的第一代孤軍(《異域》一書中對這第一次的撤退有過介紹)。心道大師那時候才十幾歲!寫到這裡,回想五十年前,當還是孩子的心道在清泉崗赤膊操練的時候,柏楊在汗流浹背的伏案報導孤軍故事,而今心道安坐在他的宗教博物館,柏楊繼續汗流浹背的伏案為心道的傳記寫序,這就是緣分吧!
每個人生來都有宗教情感,心道大師生在緬甸這個佛教國家裡,他來台灣後,又不斷的接觸到佛教大師,所以他的悟道很早,而且有更廣的開拓。真正為心道大師剃度,把他領進佛門的是星雲大師。邊區孤軍第一次撤退到台灣後,心道年紀實在太小,那年才十四歲,身子還沒有鎗的三分之二高,他既扛不動鎗,鎗也扛不動他,軍事訓練單位對這一批孩子們,實在無從著手,於是由教育部分別把他們轉入各小學──白天到學校讀書,晚上回營房睡覺。心道大師讀過員樹林國小,而就在這個時候,他迷上了武俠小說,他和一般小朋友一樣,決定當大俠,打盡世界不公平的事,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一本武俠秘笈,幾個小毛頭自己練起神功,尤其又練起輕功,方法很簡單,祇要在腳上綁個砂袋即可,在上學的路上走得怪模怪樣,堅信有一天,可以練成飛簷走壁,他們有一個信條,當大俠不是夢,而是正義與力量的延伸。
大俠當然沒有當成,心道大師最後被星雲大師接入佛門,剃度出家。我想起一個比喻,星雲大師好像唐僧,莊嚴肅穆,嚴守戒律,慷慨高貴,捨身佈施。而心道大師則像孫悟空,雲遊各界。二十年後,心道大師成立宗教博物館,組成新的淨土。使萬教並生蓮花,星雲為他祝福。星雲東天送經,使當年玄奘西天所取的經,更加豐滿後,再東傳萬邦。
出家千千萬萬,高僧是國家之寶,面對高僧,我們合十頂禮。
導讀
春深猶有子規啼─訪道與勘驗∕林谷芳
禪問答中有個大家熟悉得不得了的故事:
白居易向鳥窠禪師問佛法大意,鳥窠給予最「傳統」的答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以為這答案三歲小兒都曉得,鳥窠則回以「三歲小兒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的回答。
這回答在佛門是老生常談,鳥窠的對應從機鋒高峻的禪者來說,更係聞之須掩耳疾走之論,不過,如此卑之無甚高論的言語,後來卻仍不斷出現在披雲狂笑的禪門,究其故,則因它扣準了修行的原點。
修行是什麼?對禪或其他法門而言,核心都在「了生死」。而「了生死」並非語言文字的遊戲,它只能親身體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因此,看個修行人,重點不在他談的理論有多系統,多玄妙,而在他是否有能力「化抽象的哲理為具體的證悟」。
的確,修行是化抽象哲理為具體證悟之事,因此,求道雖強調解行並重,但所有的解如果未有化成行的能量,就只能是一種戲論。也所以,讀遍經論,常不如直接閱讀行者所體踐出來的生命大書有用,所謂「聽其言」,不如「觀其行」,正是許多人所以須親近大德的原因。而在特別標舉言語道斷的宗門,祖師行儀更是一個離乎言語相的公案,師徒能否承續,關鍵往往就在徒弟能否從師門行儀中得到自己聞思的印證。
不過,能親炙固然最好,但還得具備一定的時節因緣,因此,祖師傳記乃常成為有心者的重要資糧,歷史中從較簡的高僧傳、傳燈錄,到詳細的祖師年譜及傳記之所以能不絕於書,也正緣於此。它是我們在談修行、談傳承、談法門所不能忽略的一環,而其中的內容、體例,以及讀者切入角度的不同,則使它們在修行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從體例而言,年譜較如實,傳記則常有主觀的想像,而小說式的寫法,主人公更往往只是寫者觀點的代言。當然,公案、語錄的記載,精簡且直扣核心,最能予人啟發,但行儀既略,有心者乃很難由之窺知行者那點滴在心頭的轉折歷程,於是也只能停留在心嚮往之的階段。
至於內容,老實深刻的行者本以整個生命面對生死,不著一處,全體即是,下筆就難,以此行儀中應以何者為核心,乃成為寫者落筆取捨的關鍵。而在此,因不同人的不同詮釋,彼此自可差異極大,例如弘一法師,要以俗情的文化藝術,還是似根柢的宗教情懷寫他出家的因緣,結果就可判若兩人。
而即使體例及寫法問題不大,誰來讀這本書也可以導出不同的判準,有些人看祖師行儀像在求靈異紀錄,有些人則永遠以人的世界為最終關懷,有的人看度眾事業,有的人卻窺內心幽微,有人想理出修行步驟,有人則強調悟後風光。
就這樣,雖說高僧傳略、祖師行儀是重要資糧,但就如佛法講因緣般,不同對應乃可以使它是藥,也可以使它是毒,而就中,讀者既是攝受者,自己能否獨具隻眼就成為個中關鍵,過去講「師訪徒三年,徒訪師三年」即因於此。
師訪徒是尋人才,伯樂找千里馬,機率小,但不容易看走眼,因為是以先進印後學;可徒訪師就不然,以外行看「內行」,未證之地談已證之人,看走眼的機率基本就大,而這也正是怪力亂神始終可大張旗鼓的原因,多少人或為印象所惑,或因理事不夠圓融強作最勝義解,結果不要說魔軍可以惑眾,連江湖小卒也常沐猴而冠,可憐的是訪道之人,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莫此為甚。
***
不過,勘驗雖不易,卻也非完全無法可想。首先,修行的系統固提供了一個基底座標,不同行儀的比較也讓勘驗有了相對基準。這些基準,有些是所有行者必須共同體現的,例如,向道之心、如實行儀。有些則是不同法門所欲達致的,例如禪者根柢上有其自性天真或截斷眾流的要求,密宗行者則要求理事相即,在不同因緣內呈現不同對應,其間的不同,在禪是一絲不掛,直取本心,只破不立;在密則為即事而真,我手即為佛手,從妙有體証。
當然,宗派之外,還有個人生命情性與修持法門顯現的不同生命風光。
如此,若能從上述三個面相切入,對行者的勘驗固不能說能立即相契,但雖不中亦不遠矣!而這也正是修行的原點儘管在體證,深入經論卻永遠有其重要性的原因。因為,當應世的人格不在時,故應「以法為師」,而即使在世,習者若要免於識而不見,仍需系統修行理論的指引。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行者的行儀,下面的一些重點恐怕是大家必須注意到的。
首先:行者的向道因緣何在?是生具夙慧,天生具有宗教心?還是因某種因緣使然?這種因緣是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世間情?還是對死生天塹的諦觀?也或者只是對未知世界的嚮往?
其次:行者是以如何的心情,如何的實踐來對應這向道的因緣?是捨離萬緣,孤獨求道?還是寄身叢林,直領宗風?甚或是慈悲應緣,度人自度?在此,行者對世間變動事務依戀的俗情總要能不在,也所以老實、堅忍、綿密就是許多行者人格的基本特質,常常讓人為其一生的投入而動容。
此外,更關鍵的是他修習什麼法門,又如何相應?坦白說,這才真是考驗習者的地方,而就此,哪個法門是以信為本?哪個法門強調智為能入?哪種法門直取慈悲?哪種法門強調能量轉換?又有哪個法門當下即是?習者不僅基點的認知要準,對行者相應的勘驗尤其要在訪道中不斷反思觀照,終至具備識人的法眼才行。
最後,行者成就整體生命的風光何在?或他面臨生死所映現的成就為何?更是觀照的焦點。前者就整體觀之,可免去「但見秋毫,不見輿薪」之病,例如有些乩童雖有靈通,但除此之外,一無可取,不僅缺乏生命境界,法門其實也不足恃;而後者則是最核心,最無可重來的應現,也是最嚴厲的考驗,因此禪者示寂乃成為禪門最大量也最值得參究的公案,就如天童宏智臨終偈有「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淹沒,秋水連天」之句,以此,他一生標舉的默照風光才有堅實的支撐,而弘一雖不在宗門,但去掉了「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去掉了「悲欣交集」,則一生行儀所能照亮人者,恐怕也將減半。
坦白說,一個人掌握了這些基點要來勘驗行者,則除非對方真乃潛修密行之輩,應該都能窺見一些真實;甚且,經由理論與實證的磨練,對「內修菩薩密,外顯羅漢形」的微細行儀,也能體得事情並非只是外表所見到的那般;至於那些妖言惑眾,未證言證者更就難逃法眼了。
有了勘驗,求道者就會回到「更如實」的立場,來看修行者應現的一切,不會活在一種假相的追求中。這就如同釋尊有背痛,行者觀照的不應是他有沒有背痛,而是悟者究係如何面對苦痛。猶記得年輕時,有一好友一次提及他在寺院中聽經,看到座主面對炎炎夏日,汗如雨下,邊拭汗邊講經時的震撼般,一個求道者在了解了「和尚也是人,也要流汗」時,其在「如實」上就又過了一層。當然,話說回頭,行者真的在炎夏中都必會揮汗嗎?有沒有不畏寒暑的情形?有沒有以心轉物的生命?「安禪不須入山水,滅卻切心頭火自涼」真只是一句唯心的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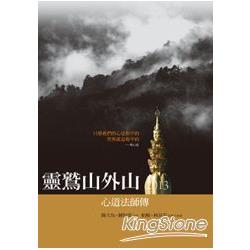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