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醫生,在監獄上班
本書告訴你,那些發生在大韓民國監獄的診間故事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監獄醫師才能告訴你的──監獄診間故事。
收容人詐病、藥物成癮、吞食異物…
在這個地方早已不足為奇,
然而,在大韓民國這塊土地上,
守護他們健康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監獄。
大多數醫學院生畢業後,壓根不會想到矯正機關(看守所和監獄)服務,作者崔世鎭卻選擇這裡作為他醫師生涯的第一站,成為1500名收容人的唯一醫生,將在監獄裡看到的一切記錄下來:
· 在這裡,詐病幾乎天天上演。為了多領藥、為了逃避勞役、為了搬到其他舍房、為了戒護外醫……我也因此練就了一身詐病判定功夫。
· 身上別著藍色號碼牌的,就是「煙毒犯」。他們要的不只是毒品,還有各式各樣的藥物。為了把藥拿到手,甚至威脅醫生也在所不惜。
· 為了達到目的,有些收容人會自殘、吞食異物。照了X光之後,我完全想不透他到底是怎麼把這麼大一顆警報器塞進喉嚨裡的。
然而監獄裡,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
· 許多人幼年時都沒接種過B型肝炎疫苗,他們成為犯罪者的機率之高,幾乎可以說是「天生的」。
· 因為自離開監獄起,醫藥費就不再由監獄負擔,許多收容人縱使已病入膏肓,但礙於經濟壓力,也只能等待死亡。
· 許多毒品成癮患者,多半都是生長在惡劣環境,從小開始跟著身邊的人吸食強力膠。監獄官們說:他們被關一次、兩次、三次,如果好一陣子沒再進來,不會認為他們戒毒成功,反而會覺得他們應該是自殺了。
透過書裡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思考:
究竟是社會的灰色地帶催生了犯罪者,還是因為人性本惡?
「報應主義」真的能讓社會更好嗎?
「公共醫療」該如何發揮最大實質效益?
監獄這個地方,自成一個世界,是社會的縮影,
裡面的人,真的生病了。
本書特色
● 帶領讀者站在第一線,以醫師角度看收容人與其背後故事。其中,醫師該如何不受情感影響、保持專業,發人省思。
● 不僅點出監獄醫療的問題,也具體舉出他國矯正機關的方式、作者在體制內所做的新嘗試,亦能提供台灣借鏡。
● 作者崔世鎭:「如果因為對方是犯罪者,就無視他們的醫療需求,不僅是侵害人權,也會醞釀出更多的被害者。」引領你我一同思考個人與社會的健康是如何相互影響,又該如何降低再犯率,甚至預防犯罪,打造更安全健康的社會。
影音介紹
名人推薦
好評推薦
朱剛勇|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貧窮人的台北策展人
林啓嵐|羅東聖母醫院主治醫師、法務部頒定法醫師
林麗珊|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劉淑瓊|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戴伸峰|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哇賽心理學與鏡好聽合作主持人
謝松善(阿善師)|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主任
(依首字筆畫排序)
目前國內尚無以醫學的角度介紹監所的專書。日月文化出版社計畫將《我是醫生,在監獄上班》譯成繁體中文版並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和社會。讓社會大眾對同在一個社會但被隔絕的監所收容人之醫療與生活能進一步瞭解;同時本書也是法律、獄政、警政、醫療相關人員體驗社會角落、豐富職業文化內涵的一本好書!──林啓嵐|羅東聖母醫院主治醫師、法務部頒定法醫師
杜斯妥也夫斯基說:「評價一個社會,不要看它如何對待良民,而是看它如何對待罪犯。」我們應該審慎評估罪與罰的對應與意義,悲憫社會邊緣人在監獄矯正與醫療的困境。──林麗珊|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健康監所」是國際趨勢。受刑人被剝奪人身自由是刑罰手段,但健康既是基本人權也牽動健保支出。本書從監所醫師視角,探討受刑人健康問題的社會成因與公衛風險,值得臺灣借鑑。──劉淑瓊|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目錄
序/導讀
前言
故事,從一個「特別」的地方開始
多數醫學院生會選擇到曾經臨床見習過的醫院,開始自己的實習生活,在那些有名的大學附設醫院裡,穿起繡有自己名字的白袍。每個人的實習生活都不容易,但對於在知名大醫院實習的同學來說,他們擁有更多資源,有問題時可以問前輩同事或住院醫師,再往上還有研究醫師,然後是最具權威與聲望的教授,而且,他們的患者,大多是主動求醫,主動去醫院掛號的人們。
這可以說是醫學院生十之八九會走的一條路,但我卻選擇「脫隊」,闖入一群我從未接觸過的人群之中。畢業後,我在矯正機關(看守所和監獄)當了三年的公共保健醫師 代替入伍服役。其實我大可以和其他公共保健醫師一樣,選擇到外島或山區保健所服務。但基於一股好奇心,我選擇了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矯正機關。
在那之前,我從未去過矯正機關,也沒見過監獄官,更別說是收容人了。就這樣,我成為了收容一千五百名收容人的順天監獄唯一一名駐院醫師,從零開始,為我那最陌生的實習生活拉開了帷幕。
我們有句老話說,患者,是醫生最重要的老師。對於剛從醫學系畢業的人而言,絕對不可能有「一次就上手」這種事。而讓我步上軌道的,是監獄這個地方。我的老師,則是監獄裡的收容人們。
雖然我是自願進到監獄服務,但剛開始也經歷了一段混亂時期。人家都說起跑點很重要,難道是我站錯起跑點了嗎?如果在首爾大學附設醫院開始實習生活的話,一切會不一樣嗎?還好最後,我撐過來了。很多我以為會不一樣的事情,最後並沒有改變,當然,也有不少超乎當初想像的部分。現在回想起來,這些「特別」的經驗好像並不糟,甚至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寶貴經歷。因為在監獄裡,有別的地方絕對遇不到的老師——我的收容人患者們。
在我的第一個「職場」,也就是順天監獄,每天平均看診人數是八十人。雖然工作時間是早上九點到傍晚六點,不過因為收容人有所謂「收封時間」(必須在下午四點回到房間),因此實際看診時間其實少於表定工作時間……但可別高興得太早,因為在表定診療時間以外,緊急要求看診的收容人不計其數。
我在這裡進行了各式各樣的醫療處置,一天一天慢慢累積經驗,剛開始難掩一身「菜味」,以前只用模型練習過傷口縫合,但在這裡,活生生的病患就這樣毫無預警出現在眼前。
用摔破的鏡子碎片割腕的收容人、跟同房的其他收容人打架打到眉毛撕裂的患者……要不是身在監獄,根本不可能有機會這麼頻繁見到的患者們,在這裡卻日復一日地出現。每次見到這些患者,我就會像「白色巨塔」裡的外科醫師,淡定地消毒、縫合傷口。或者應該說,「假裝」淡定。「沒事的,保持平常心。」我總是對自己這麼說,努力掩飾緊張的情緒。正因為有了這些過程,我才能學會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我的工作地點——監獄診間。
在監獄診間這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無論是患者還是醫生,都逃不出對方的手掌心。當收容人想偷溜到監獄外看診時,醫生會睜大眼睛找出其中真正的病人;當病患拖著一身病來到診間求救,有些醫生會在看診前就一口咬定這些人在裝病。有些收容人會嚷嚷要把不認真看診的醫生告上國家人權委員會,但也有些醫生會仗著敬業精神絕不低頭,堅持繼續把份內工作做好。
然而,在監獄診間裡,最能近距離觀察收容人身體狀態的就是醫生,在最不舒服的時刻,當痛苦爬滿整張臉,終究會被醫生給發現。有些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經生病了,甚至根本不清楚自己可以接受什麼樣的治療,看在醫生眼裡十分不捨。有人認為這些收容人根本不配當人,但也有醫生會將他們一視同仁,當作該被憐憫的患者,唯有這樣才能找到自己工作的意義。即便如此,監獄診間裡的每個瞬間,都像是一場又一場的角逐戰。我經常在監獄裡祈禱,希望自己不要被每天大大小小的狀況給擊倒。
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到矯正機關工作?又是為了什麼自告奮勇將這些故事寫成一本書?不是因為我是多了不起的醫生,不是為了實現什麼遠大的理想,也不是因為我有多豐富的經歷,更不是因為擁有過人的文筆。
矯正機關這個地方,可以讓一個醫生,讓一個「人」,思考很多事情。在這裡,有太多相互矛盾的人事物共存。而我想透過這本書,和讀者分享三年來不斷在我腦海裡徘徊的一些疑問。究竟該不該把稅金用在治療犯罪者?究竟是社會的灰色地帶催生了犯罪者,還是一切都是因為人性本惡?究竟照護與監視有沒有辦法杜絕犯罪?究竟犯罪者有沒有辦法真的被矯正?犯罪者到底有沒有幸福的權利?過失與故意該如何區分?一個人的意志會在什麼情況下到達極限……於是,我開始訴說我那不完美卻最熱血的監獄醫師生活。
這本書,記錄著我在順天監獄和首爾看守所當公共保健醫師的三年。以及被外派到大邱監獄、金泉少年監獄、光州監獄、首爾東部看守所工作,在危急時刻和新冠肺炎搏鬥的點滴。對於剛披上白袍還沒幾年的我而言,與其說這本書裡充滿沉重的文字,我更希望用有趣的筆觸去詮釋這些故事當中存在的意義。真心希望這本書,能帶給各位讀者一場與眾不同的閱讀體驗。
試閱
迎向美好的明天,充滿希望的矯正
從宿舍出發,步行約十五分鐘,就會看見看守所大門招牌。再往前走,通過五道門,就會抵達我每天打卡上班的診間。走過一道又一道的門,不禁讓人產生一種置身京都「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由超過一千座的赤紅色鳥居排列成的長長隧道)的錯覺。鳥居是人間與神界的交界點,看守所這一道道的門,卻不是通往神界,而是進入一個「矯正世界」。這個世界,大概類似《神隱少女》裡隧道另一頭的那個神祕村落。
電影中,神祕村落裡的人們都沒有名字,而收容在這裡的人,名字則被編號取代。在這個世界裡,多的是不被允許的事,比如男性收容人的空間裡不允許出現女性,反之亦然。
翻遍網路地圖,也絕對找不到矯正機關的正確位置。因此必須先搜尋「首爾看守所十字路口」,掌握好大概地理位置,抵達定點後,再依指標前往目的地。點開衛星地圖,看到的也只是一大片被樹林覆蓋的地區。這是因為矯正機關屬於「國防機要設施」,如此歸類的原因,存在好幾種說法。其中一說,是擔心發生戰事時,若矯正設施遭破壞,收容人逃出,會引發社會動盪不安,但這也只是傳言而已。話說回來,以前是真的有一種隸屬軍方的「警備矯導隊」編制,有些役男會被分發到矯正機關去服兵役。
穿越第一道門,一步步往診間的方向走。這道寫著「迎向美好的明天,充滿希望的矯正」、充滿教化意味的門,叫作「外正門」。必須佩戴法務部公務員證,才能通過這道門。每當脖子上掛著職員證,我的心情便會不自覺跟著好起來。「法務部」這三個字還真是討人喜歡。像我這種行醫的人,一輩子能掛上法務部職員證的機會,應該也不多。
全國五十一所矯正機關皆為矯正本部管轄,矯正本部則隸屬法務部。這也許可以算是常識,但坦白說,在進入看守所工作之前,我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一問三不知,就知道我有多漠不關心。
位於外正門與監獄圍牆之間的,是一個類似矯正園區的地方。不被歸類於機密設施的典獄長室、各種行政辦公室,以及接見室都在這一區。其他還有像是停車場、網球場、武藝館也都在這裡。首爾看守所因為規模龐大,園區內還有職員專用幼兒園和矯正委員專用設施。
第二道門是內正門。從這道門穿越圍牆,就能進入監獄內部。職員以外的一般訪客,必須在這裡接受安檢才能進出。除了得將手機等3C產品寄放在這裡,還必須透過X光機檢查個人物品。會經由這道門進入監獄內部的,通常有律師、志工,或是偵查人員。除非是出獄,否則收容人絕不可走出內正門。
穿越內正門後,是一個看起來像操場的寬闊空間。在這裡經常可以看到穿戴防護裝備的收容人上下護送車。這些人通常是要出庭,或是被移送到其他設施。看著眼前這些上下車的收容人,才突然有一種「原來我真的在監獄裡」的感覺。另外,移送急救患者的救護車,也會在這裡待命。
再往前走,就會抵達收容樓,這裡才是收容人生活的地方。進到收容樓,會看到整個矯正機關裡規模最大的戒護科辦公室和職員休息室。跟其他職員休息室不同的是,這裡有手機寄放箱。除了特定人員之外,其他職員在工作時必須把手機寄放在此。因為從下一道門開始,是禁止攜帶手機進入的。
為何此處手機管得這麼嚴呢?絕大多數的規定,都是因為曾經出過狀況而被制定出來,這條手機禁令也是。其實早先這裡是可以使用手機的,但據說後來爆出有收容人和監獄官透過手機進行金錢交易的弊案。對於與外界隔絕的收容人來說,手機確實是無比珍貴的存在。美劇《勁爆女子監獄》(Orange Is the New Black)中,就有偷帶手機入獄的收容人死命將手機往廁所牆壁裡藏的情節,我想這應該不是只有在美國才會上演。
剛開始在順天監獄工作時,對於不能使用手機這件事感到十分無奈。畢竟平常手機不離身,在沒有手機的情況下,度過漫長的七、八小時,直接逼出了我的「戒斷症狀」。
在解釋「戒斷症狀」的時候,通常會用「不安與焦慮」來形容,而這正是無法使用手機的我所處的狀態。不過幸好幾天後便順利克服,現在反而很享受手機不在身邊的感覺。
穿越首爾看守所的收容樓之後,會有一個辦理入獄、出獄、出庭的地方。這裡的人們,介於服刑與出獄之間。最後,再走過鐵門,就終於抵達收容人生活的空間——由許多舍房所組成的「舍棟」。
宛如監獄電影一般,四、五十歲左右、理著大平頭的收容人,一個接著一個彎腰打招呼,偶爾也會遇到雙眼直盯著我的收容人。經過他們身邊時,我總是故作鎮定、視若無睹,跨出堅決的步伐,氣勢不能輸。這條像是百米田徑賽道的收容樓走道,曾有政壇、商界的大人物走過,「N號房」和「Burning Sun夜店事件」的嫌疑人走過,也有上過各大媒體頭條的連環殺人犯走過。這條鋪著水泥的老舊走道,就是我每天要走的「上班路」。
寫著「醫療科」三個字的門牌終於映入眼簾。這裡正是我的工作地點——診間。首爾看守所的醫療科,位於死刑台旁。據說是因為槍決後必須由醫生確認屍體,並宣告死亡……雖然距離上次執行死刑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但緊緊鎖上的死刑台大門,總會飄出一陣陣莫名的涼意。
讀到這裡,你是否也感到幾分緊張呢?就像第一次來到矯正機關的人們,在安檢台前總是會不自覺握緊雙手,我也曾經有過這種感覺。不過畢竟這裡是我工作的地方,沒多久就習慣了。想想人的適應能力還真是了不起。不對,應該說「上班族」的適應能力,真的很了不起。
監獄裡放羊的孩子
「人能吞下的東西很多,遠超過你的想像。」這是矯正機關教我的,而不是從醫學院學到的。三十歲的收容人B吞了原子筆後,被送來診間。X光片上面還看得見他吞下的那支筆。不過幸好只是筆身的一部分,長度不到八公分,有可能自然排出體外,所以最後決定採取追蹤觀察。我們每天幫他拍一張X光,確認原子筆的「進度」到哪裡了。
不過,追蹤觀察第二天,又出事了。B將滅火器砸向X光室的鏡子,並用碎玻璃劃破自己手腕。在監獄官上前制止前,B不斷尖叫,割了手腕不下二十次。他絕望地大喊,要大家停下來聽他說話。機動巡邏小組壓制了B並將他帶到診間來。B被裝上腳踝保護裝置,我開始縫合他手腕上的傷口。
現場除了我,還有十多名機動巡邏小組的監獄官,我們一群人包圍著B。沒有人開口說話,但每個人的表情都若有所思。
「究竟B是為了什麼而選擇自殘?」在矯正機關工作的人,都會不自覺往這個方向想。大概是想戒護外醫、想搬到單人房,或是想拿到特定藥物,才會把事情鬧得這麼大。從過去經驗來看,這種情況不在少數,這樣的懷疑也是非常合理。
一邊縫合傷口的同時,我問B為什麼吞筆,又為什麼割腕。B說,家屬會面時,太太告訴他女兒生了重病。他擔心女兒,卻幫不上忙,會面結束後用力踹了桌子,附近職員見他大吵大鬧,並不是上前安慰,反而認為他在鬧事。一氣之下,就這樣吞下了原子筆。吞筆隔天,一位監獄官對B說:「又不是親女兒,你激動什麼?」那句話,讓他憤而選擇割腕。
我一邊縫合傷口,一邊告訴B,我懂他現在心裡十分難受,也知道他非常擔心女兒健康,但自殘不能解決問題,一定有更好的方式,能幫助他克服這個困境、找到解決辦法。然而,除了安慰,我能為B做的真的不多。
B沒有回到舍房,而是被送到調查室,當天下午,B再次被帶來醫療科,他用牙齒把傷口縫線全部咬斷。監獄官們圍成一圈,問他到底怎麼了。由於情況實在太荒謬,令我控制不住自己語氣,辛辛苦苦才把傷口縫好,怎麼又搞成這樣呢?這次,B說因為自己想看書,但被拒絕。此時,我突然開始懷疑,B自殘的原因可能沒有想像中單純,也許他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也說不定。
我問B是否曾接受精神科治療。B說,入獄前曾因間歇性暴怒症而服藥。可是都入獄好幾個月了,難道這段時間暴怒症都不曾發作嗎?他又說是因為監獄官經常幫他心理諮商。的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有時候效果是會大過於藥物的。
看來「間歇性暴怒症」這個病名並不是主要因素。我再次替B仔細縫合傷口,並告訴他,如果平常感到生氣或鬱悶,就申請到醫療科接受診療。
「如果他們不讓我出來呢?」
「就告訴他們你要接受精神科諮商呀,這種小謊應該說得出口吧?」
聽我這麼說,B害羞地笑了。
後來,B每天固定會來診間兩次。逐漸開朗的神情,多多少少讓我感到有些陌生。他那如雨過天晴般的神色,讓人不想失去,也不想忘記。
獄裡獄外都一樣,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只是需要有人聽自己說說話。這些不尋常的行為舉止,很多時候都只是希望身邊的人能給自己多一點關心。
在監獄和看守所待久了,會發現這裡有不少「放羊的孩子」。然而這些隱藏在謊言之間的「請幫幫我」,卻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不要對他人的求助視而不見,如果我們肯花點時間問放羊的孩子「你為何一直說狼來了?」也許放羊的孩子就不會被狼吃掉了。就算已經因為自殘或是藥物成癮,被村民們當成放羊的孩子,他們也依然是孩子,不是嗎?
M的故事
M入獄之後,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連一口飯也沒吃,他是五十多歲的男性收容人,一開始以為只是單純的「拒食」患者,但看著他一句話也不說,我開始發現有些地方不太對勁。M不是單純不說話,而是完全「不開口」。
若是心懷不軌的拒食,通常會開口表明自己的目的,或說「我絕對不會告訴你們我為何不吃東西」。然而若是像M這樣完全不吃東西的話,有可能屬於精神疾病。拒絕進食也是精神分裂的陰性症狀之一。
隨著M拒絕進食時間越來越長,我決定把他轉到精神疾病專責監獄——晉州監獄。不知為何,轉送申請沒被批准,只好讓M接受精神科遠距診療,並以戒護外醫方式領藥。可是,M不開口就是不開口,連藥都不吞。體力不支的M,最後幾乎只能躺著不動。我曾試著用較溫和的方式想打開他嘴巴,但他總是咬緊牙關,堅決不張開。M有著一對像外國人的藍眼睛,總是天真無邪地看著我們。我依稀記得他那雙藍色眼睛,眨呀眨的。
有時,醫生會幫患者做抗精神性藥物(anti-psychotics)的肌肉注射,但監獄裡並未備有這類藥劑,而M已因同樣問題戒護外醫過,想再送外醫,醫療科科長和戒護科人員都持反對意見。只怪上次外醫時,院方沒有好好處理。我猜大概是因為當時沒能掛到精神科醫師門診,只在急診室做簡單處置就回來了。還好M並不抗拒打點滴,還算能勉強度日。
記得那天,我們下了最終結論——再次讓M戒護外醫。不知為何,內心總有股不祥預感,總覺得那個晚上會是關鍵。我通常六點下班,但那天我選擇留在醫療科,讓M躺在診間打點滴,坐他對面持續確認狀態,到了晚上十點左右,M突然失去意識,也沒了呼吸和脈搏。我二話不說,立刻幫他做心肺復甦術,那是我成為醫生之後的第一次心肺復甦術。做的當下,整個世界彷彿停止轉動,不知道會不會每次都有這種錯覺。幸好做到第二輪時,救護人員抵達現場,M也恢復了自主循環。
戒護外醫的M,住進全南大學醫院加護病房。由於健康狀態相當不樂觀,可能活不到出獄,因此獲得暫停受刑許可。
後來,M被他哥哥接走了。聽說M的哥哥經濟狀況不甚理想,全南大學醫院認為M病情十分嚴重,不讓M辦出院,可是M的哥哥負擔不起大學附設醫院加護病房的住院費用,因此決定轉到類似療養醫院之類的機構。
最後,M在轉院的救護車上,嚥下最後一口氣。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民間有一種私營救護車,是專門讓「即將在車上臨終」的患者搭乘的。M大概是在那樣的環境中結束了生命吧?雖然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但要在這附近找到療養醫院並不容易,而且經濟因素也讓繼續接受治療變得難上加難,我想最後剩下的選項應該也不多了。
M走了之後,他哥哥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控告監獄醫療待遇不佳。接著,國家人權委員會開始針對我進行實質審查。調查人員調了監視器畫面出來看,監視器拍到的,是我下班之後留在M身邊觀察他狀態的影像。調查人員接著問了我幾個問題,大概是「你是否盡到最大責任提供應有醫療服務?」之類的。我告訴調查人員,第二次要送M戒護外醫前,他心跳一度停止,但這是無法預測的狀況,我在診間採取所有可行措施,只為了讓他恢復心跳。當下我很慶幸,自己能坦蕩蕩說出所有事實,沒有一句謊言。
我也會想,若自己有更多針對M這類精神疾病患者的臨床經驗就好了。撇開這個不談,M的事件帶給我的最大啟發是──「我們的社會是否有夠完整的系統能保護這樣的患者?」M從一開始被關進來時就不吃東西了。當初為什麼要堅持逮捕一名精神病患呢?由於經濟因素必須放棄治療的情況,是否還在繼續上演呢?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針對收容人該有的人權做出足夠考量呢?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該為這些需要接受治療的收容人發聲?
調到首爾看守所之後,我又遇到了幾名跟M相似的收容人。其中一名中國籍收容人也幾乎不說話、不吃飯,不過看起來狀態比M好一些。我不想再因為同樣問題放棄患者,於是要求他來醫療科找我,花了好一番力氣才讓他喝下加了藥丸磨粉的咖啡和可樂。不久後,他病情逐漸好轉。難怪我們總說——「患者,是醫生最重要的老師。」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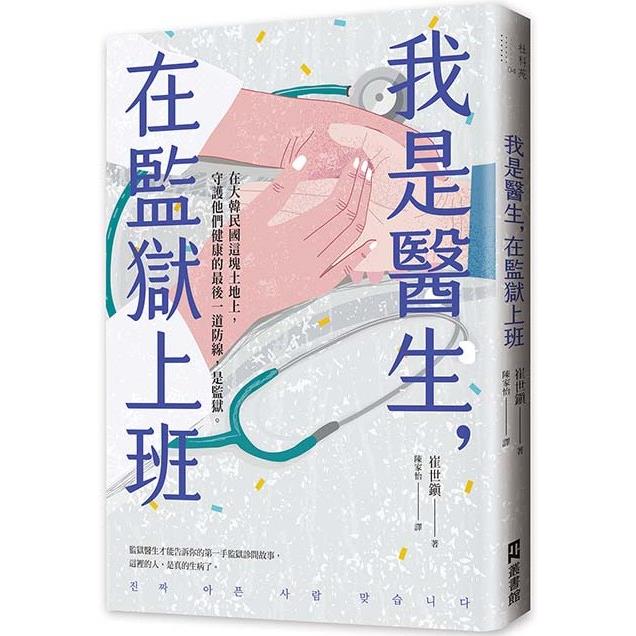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