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一本關於台灣認同的書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Kolas Yotaka,以流動與包容為核心概念,探討台灣多元認同、歷史創傷與文化延續,並思考在地緣政治緊張中如何維持和平與主體性。它既是個人的生命敘事,也是世界理解台灣的窗口。書名「禮物」象徵認同與和平的選擇——台灣多元的認同,是獻給世界最真實的禮物。
這本書談的核心問題很直接:台灣人是誰?台灣是什麼?
作者 Kolas Yotaka 以自己的生命經歷回答。她出身花蓮阿美族家庭,血脈裡有日本祖先的記憶,家族曾在白色恐怖時代受到迫害。這些背景,使她的人生充滿矛盾與標籤:原住民、日裔、女性、政治人物。她沒有迴避,選擇把這些經歷寫下來,作為一種誠實的對話。
書中從自述開始,但不止於私人故事。它帶領讀者看見更大的脈絡:原住民族在國家體制下的邊緣處境,二二八與威權時代留下的深層創傷,戰爭陰影如何滲入日常,以及台灣如何在國際政治裡被擺放、被解釋、甚至被誤解。這些內容不僅屬於個人,更屬於整個社會。
同時,本書展現台灣與世界的連結。作者走上國際講堂,與各國官員學者討論安全、能源與地緣政治。透過這些經驗,她把台灣的問題放進全球框架來思考:在民族主義復甦、地緣政治緊張的今天,台灣如何找到生存之道?答案不在於被迫的單一認同,而在於能否承認差異、保持流動、實踐包容。
書名《禮物》就是這層思考的結論。禮物不是物質,而是一種選擇。台灣若能在清楚的國界下維持多元認同,拒絕被單一身份綁死,那麼台海的和平就不只是戰略算計,而能成為世界共享的禮物。
這本書直白而清楚:它是一趟自我認識的旅程,是世界理解台灣的窗口,也是台灣社會照見自己的鏡子。它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提出了最迫切的命題——台灣要如何在歷史傷痕與國際壓力之間,堅持自己的存在?
《禮物》告訴我們,答案就在於多元與包容。這是台灣能給自己的真實禮物,也是台灣能獻給世界的禮物。
這本書談的核心問題很直接:台灣人是誰?台灣是什麼?
作者 Kolas Yotaka 以自己的生命經歷回答。她出身花蓮阿美族家庭,血脈裡有日本祖先的記憶,家族曾在白色恐怖時代受到迫害。這些背景,使她的人生充滿矛盾與標籤:原住民、日裔、女性、政治人物。她沒有迴避,選擇把這些經歷寫下來,作為一種誠實的對話。
書中從自述開始,但不止於私人故事。它帶領讀者看見更大的脈絡:原住民族在國家體制下的邊緣處境,二二八與威權時代留下的深層創傷,戰爭陰影如何滲入日常,以及台灣如何在國際政治裡被擺放、被解釋、甚至被誤解。這些內容不僅屬於個人,更屬於整個社會。
同時,本書展現台灣與世界的連結。作者走上國際講堂,與各國官員學者討論安全、能源與地緣政治。透過這些經驗,她把台灣的問題放進全球框架來思考:在民族主義復甦、地緣政治緊張的今天,台灣如何找到生存之道?答案不在於被迫的單一認同,而在於能否承認差異、保持流動、實踐包容。
書名《禮物》就是這層思考的結論。禮物不是物質,而是一種選擇。台灣若能在清楚的國界下維持多元認同,拒絕被單一身份綁死,那麼台海的和平就不只是戰略算計,而能成為世界共享的禮物。
這本書直白而清楚:它是一趟自我認識的旅程,是世界理解台灣的窗口,也是台灣社會照見自己的鏡子。它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提出了最迫切的命題——台灣要如何在歷史傷痕與國際壓力之間,堅持自己的存在?
《禮物》告訴我們,答案就在於多元與包容。這是台灣能給自己的真實禮物,也是台灣能獻給世界的禮物。
目錄
前言 認同
第一章 我是Kolas
第二章 我的另一半
第三章 超現實的理想主義實驗
第四章 收復「美好國家」
第五章 瀨戶內海與查爾斯河
第六章 禮物⸺劃清界線 共享和平
第一章 我是Kolas
第二章 我的另一半
第三章 超現實的理想主義實驗
第四章 收復「美好國家」
第五章 瀨戶內海與查爾斯河
第六章 禮物⸺劃清界線 共享和平
試閱
前言 認同
這是一本關於「認同」的書,不只是我個人的認同,還有我所觀察普遍台灣人的認同。
當二〇二五年一月,台灣重要的盟友―美國―政黨輪替,美國新政府對中國發動關稅、軍事、外交新政,使中國共產黨感到被羞辱。八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刻意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十週年」活動現場散播中共史觀,稱日本在二戰犯下戰爭罪,又稱當年的「波茨坦公告」已經要求日本「把從中國竊取的領土包括台灣歸還中國」。二〇二五年九月,美國在台協會(AIT)在回應媒體詢問時公開表示中共扭曲「波茨坦公告」,美方稱不論「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舊金山和約」等二戰文件「並未決定台灣最終政治地位」。當中國與美國一來一往辯論著「台灣」或「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此刻,台灣人內心認同哪一方的說法?令人尷尬的,台灣內部竟對這個議題尚未形成共識。
法律上的詭辯,可以無窮無盡,但個人內心的認同,只有一個答案。我認為台灣人當然不是中國人。本書不是要爭辯法理問題,是要探索台灣豐富的認同問題。
在過去數千年間,台灣島上有原住民族人,大航海時代有荷蘭、西班牙、清國進入台灣的西南部短暫屯墾,台灣從來都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直到一八九五年,台灣才真正有了「國家」的概念,這個「國」,不是「清國」,是「日本國」: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台灣成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至一九五二年間出現主權歸屬的空窗期,直到一九五二年中華民國與日本國簽訂「中日和平條約」後,台灣才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算起來,台灣人民真正有「國家」的年資,從「日本國」到「中華民國」也不過一百多年。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國家,「台灣」相對年輕,人民的身份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依然是新鮮的產物。很不幸的,由於「台灣認同」仍在形成中,尚未定型,也因此,在這來來回回的百年間,台灣人被強迫加上不同的「認同」,產生怪奇且不自然的後果。在我看來,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加上澎湖、金門、馬祖)傾向把「身份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民族認同」混雜在一起。相當混亂。
我有很多不同國籍的朋友,大部分人只有一個國籍,卻有很多認同,多元認同並不會令他們焦慮,其實很自然。大部分人無需在「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選擇,但在台灣,「選擇」成了一個問題。且「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這兩種選擇,經常被混淆,如果選了一方,就會在道德上遭另一方批判,使人陷入零和的困境。例如,很多人以為選擇某種「身份」就必須認同某個「國家」。例如,如果你若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你就一定被當作「中國人」;反之,你若是「台灣囝仔」,就不可能想當「中國人」。如此小心翼翼卻混亂的認同,不但影響你的個人生活,也影響你的公眾生活,不但影響政治結果,甚至會引起戰爭。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台灣與中國的角力,皆凸顯大國的「種族國族主義」正對每個人的「認同」提出最嚴厲的要求。例如,習近平會說只要你講「中國話」、讀「中國書」、吃「中國菜」、就是「中國人(中國公民)」。這強烈的認同主張具有高度支配性,既貪婪,又嗜血。
米蘭昆德拉在《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一書指出:「俄羅斯人喜歡把所有東西都稱為斯拉夫,這樣他們以後就可以把所有斯拉夫的東西都稱為俄羅斯。」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始終無法忘情曾經統治過的帝國,不斷灌輸全世界即便蘇聯早已解體,脫離舊蘇聯獨立建國的波蘭、捷克、烏克蘭等國家仍是「斯拉夫」的一員,終須回歸帝國的懷抱。那是一種具有侵略性的斯拉夫種族民族主義,像一股看不見的毒氣,入侵你的每個細胞。
當人民被迫在錯亂的身心狀態下做出單一認同的選擇,就代表我們正面臨某種形式的暴力。我們在不自然的狀態下被標籤,為了生存而刻意為自己貼上某種標籤,或刻意說某種語言。例如:「斯拉夫人」、「雅利安人」、「黑人」、「白人」、「拉丁裔」、「猶太人」、「穆斯林」、「中國人」、「台灣人」、「外省人」、「原住民」、「台語」、「閩南語」、「客語」、「北京話」……。一旦被貼上某種標籤,就代表掌控某種權力;反之,一但被貼上這些標籤,就註定要面對某種對立形式的壓迫。
這些標籤,是政治強迫的結果。其實,在自然的狀態下,一個擁有單一國籍的人,未必只有一個認同,可能會有多元的「身份認同」:她可以同時是一個母親、也是一個女兒;她可以是美國公民、同時是文化上的墨西哥人;她可以會講美式英語、也會講波多黎各的西班牙語;他可以是猶太人、但是在穆斯林的半島電視台工作;她可以有台灣原住民的母親、也有一個來自中國浙江的父親;她可以是一個台灣媳婦、但娘家在越南的河內……。認同是複雜的結合,在必要的時候,會在不同的認同與身份間切換,轉換認同時不應遭遇道德的批判。若把單一的身份認同強加在一人(或一國)身上,或威脅要把特定的國家認同強加在一人(或一國)身上,抹煞單一個體(或國家)的多元性,就是一種壓迫。
國家就像一個人,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她有她的長相、性格、特質、好惡。她可能換過好幾個名字,但她仍舊是她,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會因為換名字而死去。
台灣原本就相當多元,因為曾經被多國殖民,自然會發展出不同的記憶。例如,台灣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原住民族人口,也有四百多年前開始從中國東南沿海移入的移民,也有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遺跡,還有跨族通婚的真實歷史,有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政權來的中國移民及其後代,也有二十一世紀大量來自東南亞新住民第一代,以及他們與台灣人通婚後生下的第二代。如此多元的血統、文化、歷史、語言的組成,自然不會只有一種認同,也不會是一個狹義的「民族國家」。
但很不幸地,台灣(ROC)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卻被迫就嚴肅的憲法、主權、領土、國號議題與中國(PRC)競爭。由於在競爭的過程不時遭遇中國的戰爭與軍事威脅,導致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為取得國際社會的情感、外交、軍事支持,在過去七十幾年間,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學會不斷在「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間慌亂地選擇,只為滿足別人的期待。我個人認為,這種舉棋不定的現象,會在這個時代為台灣帶來危機。
「中華民族」是否等同「中華民國(ROC)」?
「中華兒女」是否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講『台灣台語』是否等同『台獨』」?
「去中國探親是否等同『舔共』」?
「說『台灣人』曾是『日本人』是否就是『民族敗類』」?
「台灣是不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後台灣歷經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政黨統治,不斷替換「認同」,以向外界證明作為一個「國家」的立場。這也使得台灣人民被迫在單一認同與單一國籍中選擇。以下就以國際上、媒體間普遍的簡稱,來稱呼這兩個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
中華民國:簡稱「台灣」
愚蠢的競爭:競逐誰才是真正的「中國」
中國與台灣政府,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就不斷競逐誰才是真正的「中國」:不斷較勁誰才擁有最美的繁體中文字;競爭誰才擁有故宮博物院最豐富的瑰寶;遠在台灣的政府在過去數十年來仍不斷遙祭遠在天邊的「黃帝陵」、「成吉思汗」與「鄭成功」,不斷在校園中興建蔣介石的銅像供學生膜拜並稱要「反攻大陸」;學生的作業本上面總是印上「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台灣歷經數千年歷史,若發展出「一個國家,多個認同」並不奇怪,但歷史並非如此發展。
「單一認同」的毒藥已深入人民的骨髓。
為了抵抗中共蠻橫的「一個中國」解釋(在此「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歷屆台灣的舊統治者選擇向世界秀肌肉,要證明台灣可以比中國更中國。因為太想成為真正的「中國」,自一九四五年後刻意模仿遙不可及的中國,為原本擁有多元歷史的台灣帶來認同壓迫。所造成的惡果,就是個人∕國家意識的模糊、人格∕國格解體。一旦本身對「認同」沒有堅定的論述,自然對外來的詮釋毫無抵抗力,使中國可針對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身份認知發動攻擊。因此「認同」成為過去數十年台灣政治上喧囂吵鬧的話題,「國家認同」成為比「國家利益」更具吸引力的鬥爭工具,各式各樣的政治辯論最終淪為「傾中」「愛台」的二元論,相當無趣。台灣人民也因此對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口水戰產生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與疏離感。甚至把「認同」當成負債,以為釐清認同會為自己帶來傷害。
當台灣成為「客體」,說不出自己多元的認同,就只能從第三者視角聽見別人詮釋台灣人應該要有的認同。例如中國及其在台灣的代理人,便強加「中華民族」的單一認同在台灣人民身上,且不斷對外宣傳虛構的「中華民族」觀點,不斷向外宣傳「台灣是中國神聖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人民皆為炎黃子孫」。讓世界以為這是台灣人的想法。
當台灣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的那一刻,台灣歷屆政權就注定無法擺脫「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魔咒。不斷在國際間與中國競爭,導致歷屆台灣國家領導人不得不把「認同」政治化,刻意混淆人民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以確保不斷與中國競爭的過程中,仍可對外獲得支持,對內維繫政權。如:蔣經國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李登輝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陳水扁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馬英九與習近平見面稱「兩岸中國人」、「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 蔡英文說「中華民國台灣」;賴清德說「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
到底是「中國」還是「台灣」?到底什麼樣的人叫「中國人」或「台灣人」?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如果連國家領導人,都無法大方、自然地告訴自己的人民「我是誰」,甚至還有卸任的國家領導人到中國告白稱自己也是「中國人」,難怪國際社會無法辨識這兩國的差異,無怪乎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至今仍一廂情願地、錯亂地令人摸不著邊際。
錯亂
「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你的「認同」是什麼?是基於種族、血統、宗教、語言、文字、文化?或國籍、學歷、職業、教育、飲食、道德或政治立場?這些問題,是在過去這幾年,所有關心世界局勢發展的朋友們,常問我的問題。在台灣,有很多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會刻意地把「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這兩個問題拿來一起問,希望看似科學的數字可以彼此呼應佐證,用他∕她想要的方式解讀給你聽、或證明給你看。數字與敘事被巧妙地搭配運用,透過編輯與遮蓋的技術,展示他們想讓別人看見的。因為每個人只願意相信他/她想相信的,但這幾年陸續出現數字間無法相互呼應的尷尬。
例如,有親近台灣本土認同的組織「台灣民意基金會」在二〇二四年一月台灣總統大選落幕之後,公布一份民調:
自認「台灣人」:76%
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11.6%
自認「中國人」:7.2%
該報告對外主張,台灣已經出現壓倒性的「單一民族認同」,主張「台灣人」認同抬頭。但同一份報告又顯示一個趨勢:
支持「台灣獨立」:44.2% (2023年為48.9%)
支持「維持現狀」:33.3% (2023年為 26.6%))
支持「兩岸統一」:10.9%
若拿上述二〇二四年的數字與台灣民意基金會自己在二〇二三年所做的相同調查比較,二〇二四年支持「台灣獨立」的數字較二〇二三年下降4.7%,「維持現狀」的比例較二〇二三年上升6.7%。這個相反的趨勢被台灣民意基金會刻意解讀為「整體而言,這次台灣人統獨傾向的起伏,或許某個程度反映了二〇二四主要總統候選人高唱『維持現狀』的效應,但期盼未來台灣獨立的人仍遠多於期盼維持現狀的人。」這樣的解讀,一方面反映調查機構主觀期待的落空,同時也反應人民「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錯亂。但令人尷尬的只有這樣嗎?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已長達三十年連續每年∕每半年針對台灣人的認同趨勢調查,在二〇二四年初公布截至二〇二三年底的發現:
自認「台灣人」:61.7% (2020年為64.3%)
自認「台灣人」也是「中國人」:32.0%
自認「中國人」:2.4%
姑且不論61.7%「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已經比上述另一機構「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比例(76%)更低,也比「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己在二〇二〇年統計的結果「64.3%」還低。同一份研究,針對「統獨立場」的調查,也發現意外的結果:
「永遠維持現狀」:33.2%
「維持現狀再決定」:27.9%
「維持現況再獨立」:21.5%
「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6.2%
「盡快獨立」:3.8%
「盡快統一」:1.2%
各式不同程度「維持現狀」的選項加總起來共有88.8%,將近九成,比例相當高。這要如何解讀?例如,挺台灣的媒體或觀察家不顧一切地忽略近九成的結果,但放大他們想看的數字稱「僅2.4%台灣人把『中國人』當作唯一身份認同,創調查紀錄新低」云云。但若誠實面對數字,經過八年訴求「台灣獨立」的民進黨的全面執政,「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自二〇二〇年起年年攀升,「偏向獨立」的人口也自二〇二〇年下滑。為什麼歷經台灣本土政黨的全面執政,會有與該政黨的政治目標有不同的發展?
你以為這是最意外?還有更意外二〇二三年末,訴求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台灣安保協會」共同公佈一項有關「統獨」傾向的民調,調查結果連公布的團體本身都感到憂心,包括:
自認「台灣人」:30.7%
自認「中華民國台灣人」:36.7%
自認「中華民國人」:24.6%
自認「中國人」:6%
該團體在記者會中公布時表示,「認同自己是『只有台灣人』三年來從40.5%下降到30.7%,總共下滑9.8%。」對長年推動台灣獨立的團體來說,這個趨勢令人尷尬,在記者會上只能尋求合理化的解讀稱這樣的結果是「顯示中國打壓,正溫水煮青蛙,在影響台灣人。」
當人遇到攻擊或認同的衝突,自然會產生心理防衛機制,以減輕壓力,減少產生低自尊,以降低焦慮和負面感。所以,看到這些數字後,當事人會責怪中國,認為是中國的文攻武嚇造成台灣人不敢稱自己是台灣人,尤其指控中國的戰爭威脅更是壓迫台灣認同的主因。但若誠實反省,中國的武力威脅是造成台灣人民認同混淆的唯一原因嗎?難道都是別人害的嗎?
「我是誰」是人一出生就要面對的認同問題。就像一個剛學會講話的三歲孩子,當外人看見孩子可愛的模樣,忍不住逗弄問他「你是誰」,孩子牙牙學語,仍可輕易區別自己與他人不同,最後會對著大人說出自己的名字「我是xxx」。台灣自一九四五年戰後算起已七十五年,若以人類的年歲來算,七十五歲的人已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已是一個看盡人生、笑看江湖的老人。
「我是誰?」
我們期待,一名七十五歲的人,已經有足夠的人生經驗與勇氣,回答這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
多元主義與民族主義
身份認同,是一個標籤,一種分類,我作為一個「台灣原住民」,對中國毫無感情羈絆、毫無懸念、不帶感情,理論上見到那些民調數字應該非常難受。但我同時也是「台灣人」,也是一個「媒體人」,也是關心公眾議題的「政治人」,也是受過社會學與社會調查訓練的「社會人」。見到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
這些有關國家與認同的民調結果,絕非代表中國長年的統戰「贏了」。數字不是結論,而是過程,顯示一個被政治、社會、經濟操控的不自然的計算結果。的確,若人民的認同錯亂,很容易遭惡意的勢力趁虛而入,自我的認同會被他人定義。對自我認識的模糊,會帶來危機,包括:自我矮化、有意識地模仿壓迫者,逃避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出生於法屬殖民地馬丁尼克的知名作家法農(Frantz Fanon)也是有名的心理分析師,也是二十世紀研究後殖民主義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一九五四年的阿爾及利亞抵抗法國殖民的解放戰爭期間,被法國政府派到阿爾及利亞戰區的一處戰爭精神療養院,負責治療戰後餘生的法國軍官。但很多人不知道,基於反殖民的動機,法農白天為法軍提供服務,夜間為「敵人」提供醫療服務,經常私下在夜間訪問阿爾及利亞的軍營,並為對方的官兵進行治療。法農發現不管施以何種治療,雙方受傷官兵的精神疾患皆難以獲得改善,直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獲得勝利,阿方戰士的精神疾病才完全獲得痊癒。在這些血淋淋的個案中,法農認定一旦殖民結構被瓦解,人格才可獲得重建。於是法農在一九五六年向法國政府辭職,在辭職信中,他指出:
作為一名精神病醫師,他深深地認識到,在一個非人道的殖民系統中,治療精神疾病是不現實的。因為那些順從這種殖民系統的正常人,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台灣根本的問題:過度順應他國的期待,企圖滿足他國的利益,忽略改善自我的潛力。我自私地以個人有限的生命經驗提出觀察,並自我反省。本書不能代表所有台灣人的觀點,但鐵定是看台灣的觀點之一。同時,也是我個人對強大認同壓迫的抵抗。我捍衛的不是特定、單一的身份認同,而是企圖以個人的親身經歷,捍衛一種「多元性」的價值,一種台灣人無從被模仿的獨特美感。
這是一本關於「認同」的書,不只是我個人的認同,還有我所觀察普遍台灣人的認同。
當二〇二五年一月,台灣重要的盟友―美國―政黨輪替,美國新政府對中國發動關稅、軍事、外交新政,使中國共產黨感到被羞辱。八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刻意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十週年」活動現場散播中共史觀,稱日本在二戰犯下戰爭罪,又稱當年的「波茨坦公告」已經要求日本「把從中國竊取的領土包括台灣歸還中國」。二〇二五年九月,美國在台協會(AIT)在回應媒體詢問時公開表示中共扭曲「波茨坦公告」,美方稱不論「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舊金山和約」等二戰文件「並未決定台灣最終政治地位」。當中國與美國一來一往辯論著「台灣」或「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此刻,台灣人內心認同哪一方的說法?令人尷尬的,台灣內部竟對這個議題尚未形成共識。
法律上的詭辯,可以無窮無盡,但個人內心的認同,只有一個答案。我認為台灣人當然不是中國人。本書不是要爭辯法理問題,是要探索台灣豐富的認同問題。
在過去數千年間,台灣島上有原住民族人,大航海時代有荷蘭、西班牙、清國進入台灣的西南部短暫屯墾,台灣從來都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直到一八九五年,台灣才真正有了「國家」的概念,這個「國」,不是「清國」,是「日本國」: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台灣成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至一九五二年間出現主權歸屬的空窗期,直到一九五二年中華民國與日本國簽訂「中日和平條約」後,台灣才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算起來,台灣人民真正有「國家」的年資,從「日本國」到「中華民國」也不過一百多年。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國家,「台灣」相對年輕,人民的身份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依然是新鮮的產物。很不幸的,由於「台灣認同」仍在形成中,尚未定型,也因此,在這來來回回的百年間,台灣人被強迫加上不同的「認同」,產生怪奇且不自然的後果。在我看來,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加上澎湖、金門、馬祖)傾向把「身份認同」、「國家認同」以及「民族認同」混雜在一起。相當混亂。
我有很多不同國籍的朋友,大部分人只有一個國籍,卻有很多認同,多元認同並不會令他們焦慮,其實很自然。大部分人無需在「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選擇,但在台灣,「選擇」成了一個問題。且「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這兩種選擇,經常被混淆,如果選了一方,就會在道德上遭另一方批判,使人陷入零和的困境。例如,很多人以為選擇某種「身份」就必須認同某個「國家」。例如,如果你若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你就一定被當作「中國人」;反之,你若是「台灣囝仔」,就不可能想當「中國人」。如此小心翼翼卻混亂的認同,不但影響你的個人生活,也影響你的公眾生活,不但影響政治結果,甚至會引起戰爭。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台灣與中國的角力,皆凸顯大國的「種族國族主義」正對每個人的「認同」提出最嚴厲的要求。例如,習近平會說只要你講「中國話」、讀「中國書」、吃「中國菜」、就是「中國人(中國公民)」。這強烈的認同主張具有高度支配性,既貪婪,又嗜血。
米蘭昆德拉在《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一書指出:「俄羅斯人喜歡把所有東西都稱為斯拉夫,這樣他們以後就可以把所有斯拉夫的東西都稱為俄羅斯。」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始終無法忘情曾經統治過的帝國,不斷灌輸全世界即便蘇聯早已解體,脫離舊蘇聯獨立建國的波蘭、捷克、烏克蘭等國家仍是「斯拉夫」的一員,終須回歸帝國的懷抱。那是一種具有侵略性的斯拉夫種族民族主義,像一股看不見的毒氣,入侵你的每個細胞。
當人民被迫在錯亂的身心狀態下做出單一認同的選擇,就代表我們正面臨某種形式的暴力。我們在不自然的狀態下被標籤,為了生存而刻意為自己貼上某種標籤,或刻意說某種語言。例如:「斯拉夫人」、「雅利安人」、「黑人」、「白人」、「拉丁裔」、「猶太人」、「穆斯林」、「中國人」、「台灣人」、「外省人」、「原住民」、「台語」、「閩南語」、「客語」、「北京話」……。一旦被貼上某種標籤,就代表掌控某種權力;反之,一但被貼上這些標籤,就註定要面對某種對立形式的壓迫。
這些標籤,是政治強迫的結果。其實,在自然的狀態下,一個擁有單一國籍的人,未必只有一個認同,可能會有多元的「身份認同」:她可以同時是一個母親、也是一個女兒;她可以是美國公民、同時是文化上的墨西哥人;她可以會講美式英語、也會講波多黎各的西班牙語;他可以是猶太人、但是在穆斯林的半島電視台工作;她可以有台灣原住民的母親、也有一個來自中國浙江的父親;她可以是一個台灣媳婦、但娘家在越南的河內……。認同是複雜的結合,在必要的時候,會在不同的認同與身份間切換,轉換認同時不應遭遇道德的批判。若把單一的身份認同強加在一人(或一國)身上,或威脅要把特定的國家認同強加在一人(或一國)身上,抹煞單一個體(或國家)的多元性,就是一種壓迫。
國家就像一個人,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她有她的長相、性格、特質、好惡。她可能換過好幾個名字,但她仍舊是她,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會因為換名字而死去。
台灣原本就相當多元,因為曾經被多國殖民,自然會發展出不同的記憶。例如,台灣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原住民族人口,也有四百多年前開始從中國東南沿海移入的移民,也有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遺跡,還有跨族通婚的真實歷史,有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政權來的中國移民及其後代,也有二十一世紀大量來自東南亞新住民第一代,以及他們與台灣人通婚後生下的第二代。如此多元的血統、文化、歷史、語言的組成,自然不會只有一種認同,也不會是一個狹義的「民族國家」。
但很不幸地,台灣(ROC)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卻被迫就嚴肅的憲法、主權、領土、國號議題與中國(PRC)競爭。由於在競爭的過程不時遭遇中國的戰爭與軍事威脅,導致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為取得國際社會的情感、外交、軍事支持,在過去七十幾年間,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學會不斷在「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間慌亂地選擇,只為滿足別人的期待。我個人認為,這種舉棋不定的現象,會在這個時代為台灣帶來危機。
「中華民族」是否等同「中華民國(ROC)」?
「中華兒女」是否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講『台灣台語』是否等同『台獨』」?
「去中國探親是否等同『舔共』」?
「說『台灣人』曾是『日本人』是否就是『民族敗類』」?
「台灣是不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後台灣歷經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政黨統治,不斷替換「認同」,以向外界證明作為一個「國家」的立場。這也使得台灣人民被迫在單一認同與單一國籍中選擇。以下就以國際上、媒體間普遍的簡稱,來稱呼這兩個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
中華民國:簡稱「台灣」
愚蠢的競爭:競逐誰才是真正的「中國」
中國與台灣政府,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就不斷競逐誰才是真正的「中國」:不斷較勁誰才擁有最美的繁體中文字;競爭誰才擁有故宮博物院最豐富的瑰寶;遠在台灣的政府在過去數十年來仍不斷遙祭遠在天邊的「黃帝陵」、「成吉思汗」與「鄭成功」,不斷在校園中興建蔣介石的銅像供學生膜拜並稱要「反攻大陸」;學生的作業本上面總是印上「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台灣歷經數千年歷史,若發展出「一個國家,多個認同」並不奇怪,但歷史並非如此發展。
「單一認同」的毒藥已深入人民的骨髓。
為了抵抗中共蠻橫的「一個中國」解釋(在此「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歷屆台灣的舊統治者選擇向世界秀肌肉,要證明台灣可以比中國更中國。因為太想成為真正的「中國」,自一九四五年後刻意模仿遙不可及的中國,為原本擁有多元歷史的台灣帶來認同壓迫。所造成的惡果,就是個人∕國家意識的模糊、人格∕國格解體。一旦本身對「認同」沒有堅定的論述,自然對外來的詮釋毫無抵抗力,使中國可針對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身份認知發動攻擊。因此「認同」成為過去數十年台灣政治上喧囂吵鬧的話題,「國家認同」成為比「國家利益」更具吸引力的鬥爭工具,各式各樣的政治辯論最終淪為「傾中」「愛台」的二元論,相當無趣。台灣人民也因此對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口水戰產生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與疏離感。甚至把「認同」當成負債,以為釐清認同會為自己帶來傷害。
當台灣成為「客體」,說不出自己多元的認同,就只能從第三者視角聽見別人詮釋台灣人應該要有的認同。例如中國及其在台灣的代理人,便強加「中華民族」的單一認同在台灣人民身上,且不斷對外宣傳虛構的「中華民族」觀點,不斷向外宣傳「台灣是中國神聖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人民皆為炎黃子孫」。讓世界以為這是台灣人的想法。
當台灣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的那一刻,台灣歷屆政權就注定無法擺脫「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魔咒。不斷在國際間與中國競爭,導致歷屆台灣國家領導人不得不把「認同」政治化,刻意混淆人民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以確保不斷與中國競爭的過程中,仍可對外獲得支持,對內維繫政權。如:蔣經國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李登輝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陳水扁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馬英九與習近平見面稱「兩岸中國人」、「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 蔡英文說「中華民國台灣」;賴清德說「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
到底是「中國」還是「台灣」?到底什麼樣的人叫「中國人」或「台灣人」?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如果連國家領導人,都無法大方、自然地告訴自己的人民「我是誰」,甚至還有卸任的國家領導人到中國告白稱自己也是「中國人」,難怪國際社會無法辨識這兩國的差異,無怪乎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至今仍一廂情願地、錯亂地令人摸不著邊際。
錯亂
「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你的「認同」是什麼?是基於種族、血統、宗教、語言、文字、文化?或國籍、學歷、職業、教育、飲食、道德或政治立場?這些問題,是在過去這幾年,所有關心世界局勢發展的朋友們,常問我的問題。在台灣,有很多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會刻意地把「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這兩個問題拿來一起問,希望看似科學的數字可以彼此呼應佐證,用他∕她想要的方式解讀給你聽、或證明給你看。數字與敘事被巧妙地搭配運用,透過編輯與遮蓋的技術,展示他們想讓別人看見的。因為每個人只願意相信他/她想相信的,但這幾年陸續出現數字間無法相互呼應的尷尬。
例如,有親近台灣本土認同的組織「台灣民意基金會」在二〇二四年一月台灣總統大選落幕之後,公布一份民調:
自認「台灣人」:76%
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11.6%
自認「中國人」:7.2%
該報告對外主張,台灣已經出現壓倒性的「單一民族認同」,主張「台灣人」認同抬頭。但同一份報告又顯示一個趨勢:
支持「台灣獨立」:44.2% (2023年為48.9%)
支持「維持現狀」:33.3% (2023年為 26.6%))
支持「兩岸統一」:10.9%
若拿上述二〇二四年的數字與台灣民意基金會自己在二〇二三年所做的相同調查比較,二〇二四年支持「台灣獨立」的數字較二〇二三年下降4.7%,「維持現狀」的比例較二〇二三年上升6.7%。這個相反的趨勢被台灣民意基金會刻意解讀為「整體而言,這次台灣人統獨傾向的起伏,或許某個程度反映了二〇二四主要總統候選人高唱『維持現狀』的效應,但期盼未來台灣獨立的人仍遠多於期盼維持現狀的人。」這樣的解讀,一方面反映調查機構主觀期待的落空,同時也反應人民「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錯亂。但令人尷尬的只有這樣嗎?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已長達三十年連續每年∕每半年針對台灣人的認同趨勢調查,在二〇二四年初公布截至二〇二三年底的發現:
自認「台灣人」:61.7% (2020年為64.3%)
自認「台灣人」也是「中國人」:32.0%
自認「中國人」:2.4%
姑且不論61.7%「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已經比上述另一機構「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比例(76%)更低,也比「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己在二〇二〇年統計的結果「64.3%」還低。同一份研究,針對「統獨立場」的調查,也發現意外的結果:
「永遠維持現狀」:33.2%
「維持現狀再決定」:27.9%
「維持現況再獨立」:21.5%
「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6.2%
「盡快獨立」:3.8%
「盡快統一」:1.2%
各式不同程度「維持現狀」的選項加總起來共有88.8%,將近九成,比例相當高。這要如何解讀?例如,挺台灣的媒體或觀察家不顧一切地忽略近九成的結果,但放大他們想看的數字稱「僅2.4%台灣人把『中國人』當作唯一身份認同,創調查紀錄新低」云云。但若誠實面對數字,經過八年訴求「台灣獨立」的民進黨的全面執政,「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自二〇二〇年起年年攀升,「偏向獨立」的人口也自二〇二〇年下滑。為什麼歷經台灣本土政黨的全面執政,會有與該政黨的政治目標有不同的發展?
你以為這是最意外?還有更意外二〇二三年末,訴求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台灣安保協會」共同公佈一項有關「統獨」傾向的民調,調查結果連公布的團體本身都感到憂心,包括:
自認「台灣人」:30.7%
自認「中華民國台灣人」:36.7%
自認「中華民國人」:24.6%
自認「中國人」:6%
該團體在記者會中公布時表示,「認同自己是『只有台灣人』三年來從40.5%下降到30.7%,總共下滑9.8%。」對長年推動台灣獨立的團體來說,這個趨勢令人尷尬,在記者會上只能尋求合理化的解讀稱這樣的結果是「顯示中國打壓,正溫水煮青蛙,在影響台灣人。」
當人遇到攻擊或認同的衝突,自然會產生心理防衛機制,以減輕壓力,減少產生低自尊,以降低焦慮和負面感。所以,看到這些數字後,當事人會責怪中國,認為是中國的文攻武嚇造成台灣人不敢稱自己是台灣人,尤其指控中國的戰爭威脅更是壓迫台灣認同的主因。但若誠實反省,中國的武力威脅是造成台灣人民認同混淆的唯一原因嗎?難道都是別人害的嗎?
「我是誰」是人一出生就要面對的認同問題。就像一個剛學會講話的三歲孩子,當外人看見孩子可愛的模樣,忍不住逗弄問他「你是誰」,孩子牙牙學語,仍可輕易區別自己與他人不同,最後會對著大人說出自己的名字「我是xxx」。台灣自一九四五年戰後算起已七十五年,若以人類的年歲來算,七十五歲的人已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已是一個看盡人生、笑看江湖的老人。
「我是誰?」
我們期待,一名七十五歲的人,已經有足夠的人生經驗與勇氣,回答這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
多元主義與民族主義
身份認同,是一個標籤,一種分類,我作為一個「台灣原住民」,對中國毫無感情羈絆、毫無懸念、不帶感情,理論上見到那些民調數字應該非常難受。但我同時也是「台灣人」,也是一個「媒體人」,也是關心公眾議題的「政治人」,也是受過社會學與社會調查訓練的「社會人」。見到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
這些有關國家與認同的民調結果,絕非代表中國長年的統戰「贏了」。數字不是結論,而是過程,顯示一個被政治、社會、經濟操控的不自然的計算結果。的確,若人民的認同錯亂,很容易遭惡意的勢力趁虛而入,自我的認同會被他人定義。對自我認識的模糊,會帶來危機,包括:自我矮化、有意識地模仿壓迫者,逃避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出生於法屬殖民地馬丁尼克的知名作家法農(Frantz Fanon)也是有名的心理分析師,也是二十世紀研究後殖民主義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一九五四年的阿爾及利亞抵抗法國殖民的解放戰爭期間,被法國政府派到阿爾及利亞戰區的一處戰爭精神療養院,負責治療戰後餘生的法國軍官。但很多人不知道,基於反殖民的動機,法農白天為法軍提供服務,夜間為「敵人」提供醫療服務,經常私下在夜間訪問阿爾及利亞的軍營,並為對方的官兵進行治療。法農發現不管施以何種治療,雙方受傷官兵的精神疾患皆難以獲得改善,直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獲得勝利,阿方戰士的精神疾病才完全獲得痊癒。在這些血淋淋的個案中,法農認定一旦殖民結構被瓦解,人格才可獲得重建。於是法農在一九五六年向法國政府辭職,在辭職信中,他指出:
作為一名精神病醫師,他深深地認識到,在一個非人道的殖民系統中,治療精神疾病是不現實的。因為那些順從這種殖民系統的正常人,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台灣根本的問題:過度順應他國的期待,企圖滿足他國的利益,忽略改善自我的潛力。我自私地以個人有限的生命經驗提出觀察,並自我反省。本書不能代表所有台灣人的觀點,但鐵定是看台灣的觀點之一。同時,也是我個人對強大認同壓迫的抵抗。我捍衛的不是特定、單一的身份認同,而是企圖以個人的親身經歷,捍衛一種「多元性」的價值,一種台灣人無從被模仿的獨特美感。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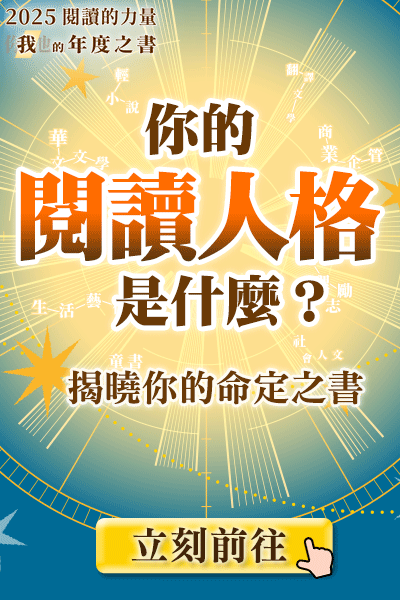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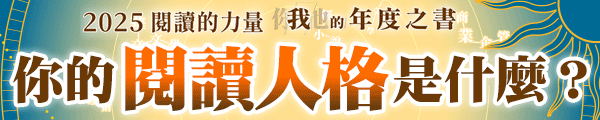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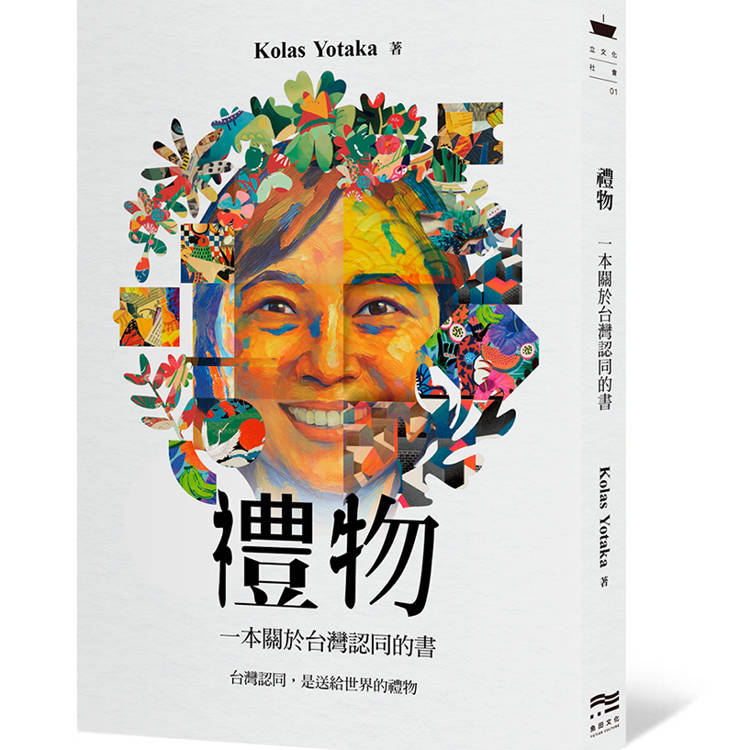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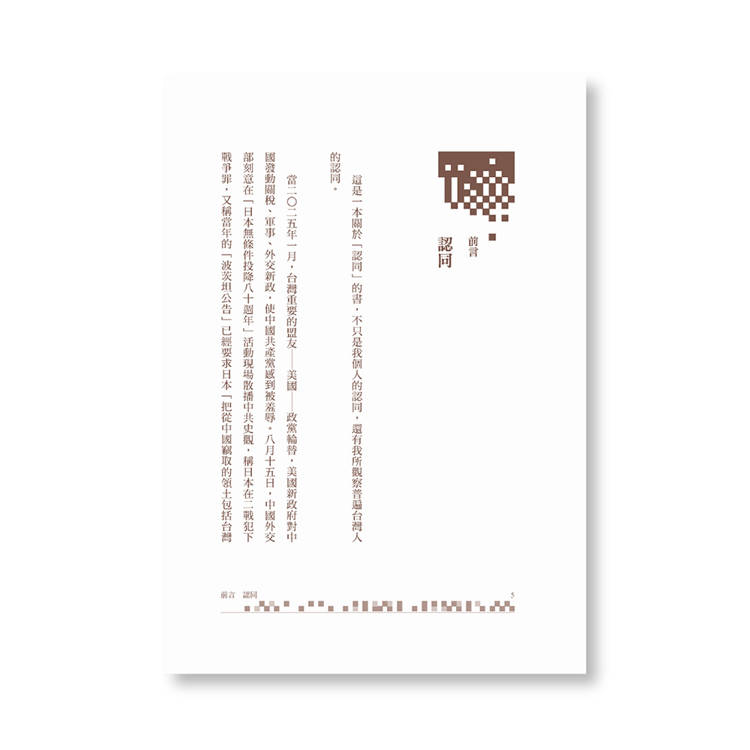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