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從歷史的黑洞中打撈即將消逝的回憶,
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後,震撼人心的抗戰紀錄!
那一場長達八年的抗戰,是誰的抗戰?
八年,牽引了整個中國的命運,大小戰役不斷──松瀘會戰、台兒莊戰役、平行關戰役、東北抗戰,打完對日抗戰,又是國共內戰,決策者僅僅是下一個指令,千百萬士兵、人民即陷入水深火熱。
戰爭過去了,歷史只記住決策者,卻逐漸遺忘出生入死的配角們,所以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本書由細節與側面還原戰爭的全貌,藉由一個個參戰者的經歷,完整呈現一個戰亂時代,那一些你曾經覺得不起眼的老叟,他可能躲過大大小小的槍林彈雨,避開敵軍的追殺,逃過斷糧的飢餓,他承載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戰爭歷史!
「不了解歷史,就不知道將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去多了解那段心酸的歷史,也感受那些曾經有過的人性亮點,同時也要反思自己。」──北京的網友
名人推薦
推薦: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監製/王小棣導演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維開
目錄
上編:他們拒絕沉淪
1.盧溝歲月
2.八百孤軍
3.伏擊
4.第五戰區
5.松山之戰
6.白山黑水
7.反掃蕩
8.潛伏
9.在延安長大
10.鋼筋鐵骨
11.生命線
12.擊斃
下編:他們,她們:大離亂時代的沉浮
13.天使
14.戰火紅顏
15.永遠的微笑
16.戰俘
17.將軍之死
18.長城謠
19.飛虎飛虎
20.偽君
21.壯志凌志
22.紅燭
23.活下去
24.勝利了
序/導讀
【序言】
故事背後那些未完的故事
《我的抗戰》播出後得到大家的認可,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和鼓勵。作為一個與抗戰老兵直接接觸採訪的前方記者,想想兩年多來在全國尋訪抗戰老兵的經歷,就兩個字,「值了」。
這些老人其實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如此普通,普通得走在大街上,和我們面對面地走過,我們都注意不到他們。這些人又是如此的不平凡,在他們日漸衰老的容顏下麵,在他們輕鬆的語態和平靜的神情中,娓娓道出的,是半個多世紀前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這段歷史,正逐漸被人們遺忘。
似乎不能說是遺忘,因為這段歷史,已經烙印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裡。雖然有些說不明,但卻隱隱約約地感受得到,不時地會蹦出來,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和情緒。這是一段怎樣的歷史呢?
我們把這些在城市和鄉村裡沉默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請到了我們的攝影機前面。對,他就坐在我的對面,講述著埋藏在心底的讓人熱血沸騰的故事。
一、耐心的傾聽者
《我的抗戰》裡面有許多具體的故事。正如崔老師所說,要的是故事,要的是細節。如何從老人的記憶中挖掘出對於他們生命最重要的片段?這需要耐心,需要傾聽。
「你想聽嗎?想聽,我給你講講。」許多老人是伴隨著這樣的開場白,打開了他們的記憶。你想怎麼聽,決定了他們要怎麼說。你是否願意傾聽,決定了他們的興致有多高。
但面對這些老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耐心,興趣缺缺。甚至許多老人的親人對老人的故事都知之甚少。不能責備人們缺少耐心,因為現實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面對。可惜的,是那些埋藏在老人內心的波瀾。
我們其實沒有做什麼,我們只是在做一個耐心的傾聽者。故事,就在老人的「囉唆」中流出,如此自然。一個故事,他能講一天,絕對精彩。
二、那些漸漸遠去的老人
朱鴻是我採訪的第一個老兵,一名新四軍老戰士。每次採訪前夜,他都會把第二天要講的內容整理出來,密密麻麻地寫滿好幾張紙條。朱鴻對我說:「我年紀大了,能貢獻的事情少了,對你們的採訪提供幫助,可能是我最後能做出的貢獻了。」
聽著非常心酸,卻在以後不得不見證著一個又一個老人的離去。宋錫善去世了、王文川去世了、武幹卿去世了、單先麟去世了……我知道,這個名單還要繼續增加。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也如煙。多少生動的故事,都隨著老人的離去而永遠地消散了。
二十九軍老兵曹廷明是張自忠的衛兵。十幾歲他,把自己賣兵得來的八十三塊錢全交給了父母,從此再沒回去。「一輩子只給了父母八十三塊」成為他最大的遺憾。九十多歲的曹廷明,想到父母,哭起來像個孩子。
哭過後,曹廷明擦幹眼淚,「我們繼續工作吧」他說。
這些老人,青年時期參加抗戰,是他們為國盡忠,為民族求生存的主動選擇。如今接受我們的採訪,在他們看來是一份責任,是必須完成的任務。老人們認真的態度讓我們感動,他們講述出來的精彩故事讓我們振奮。他們在講述自己,也在紀念倒下的戰友;他們留住自己的經歷,也在留住那個時代。
與這些老人接觸的每一個場景,都已經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腦海。那是一幅幅畫卷,畫卷裡,有重慶冬天薄薄的霧色中,山坡上破舊小屋內的微笑;有江南大片青綠色的稻田掩映的老屋內,竹椅上悠然的小憩;有大連的海灘邊,身經百戰老將軍遠眺的眼神。
三、個人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都是王侯將相,才子佳人,你方唱罷,我方登場。大歷史談的多了,小人物比較缺少。但大歷史容易被篡改,小人物,往往更加真實。
你說的可能誇張,他講的可能片面,我的記憶也不一定準確。但每個人還原出來的,都是一個獨特的抗戰:抗戰初期參戰的老兵,會對你講述中日雙方的差距有多麼的懸殊,我們的部隊損失是多麼的慘重。抗戰後期參軍的老兵,會意氣風發地對你講述,他們的作戰是多麼的酣暢,日本人是多麼的不堪一擊。他們有的講述正面戰場的慘烈,有的講述敵後戰場的艱辛。
其實,我們永遠無法還原一個完整的、純客觀的歷史。口述歷史,就是帶著強烈的個人視角。但至少,每個人的講述彙集起來,就會更加接近真實。
正如一束光照進三棱鏡,折射出來的是炫麗的彩虹。《我的抗戰》只是一個三棱鏡,把抗戰的這束光,分散成各種好看的顏色。
希望這樣的《抗戰》,不是不負責任的調侃,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也不是揮舞拳頭的狂熱。只希望通過這些老人的講述,讓大家更親切、更生動地觸感到以前被忽略的細節、那無法回溯的過往。
老人在講述屬於他的歷史,相信看過的人,最終都會找到自己還原的「歷史」。
紀錄片《我的抗戰》首席記者 郭曉明
二○一○年十月
試閱
松山之戰
親身經歷者
張羽富——時為第八軍工兵營戰士
閻啟志——時為炮兵十團一營戰士
曹含經——時為第八軍八十二師二十六團戰士
崔化山——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
李文德——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
付心德——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
早見政則——時為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
編導手記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松山之戰。一個發生在明朝末年的東北,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興趣,是因為洪承疇。後者我同樣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團長我的團》。這一節的故事屬於後一個松山之戰,沒錯,就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的那場血腥戰鬥,就是《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南天門戰役的原型。
這一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給出一個主人公來,那我只能說松山戰役就是這個故事的「男一號」,和他相比,所有的戰役親身經歷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許正因為是配角,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在戰爭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將遺體交給山野的戰友們而言,這些無字碑下的英雄們還是幸運的,至少,他們還可以得到後人的瞻仰——雖然來過的後人們並不算太多,墓地裡最常見的,還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們。
這是我所做過的選題中最血腥最殘酷的一個,不是因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為歷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殘忍得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們貌似平靜的敍述,將原本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到的血腥和絕望轉嫁給了我們,讓我們一旦知道,就再也無法忘懷。我甚至開始懷疑,就在此時此刻,在我們太平無事、機械地、自足地生活著的同時,在世界上某一個仍然籠罩在硝煙中的角落,還在發生著什麼?
兩個素不相識、從未謀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這就是戰爭。
看採訪素材的時候,有段畫面讓我始終難忘:夕陽下,簡陋的南方農舍前,一位老農打扮的老兵對著攝影機激動地說:「你們這些搞電視的,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知道什麼是打仗嗎?知道什麼是槍林彈雨嗎?那槍,真的就像林子一樣;那子彈,真的就像下雨一樣,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樣啊!」出於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禮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電視嘛,哪有那麼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誰知道你們的事啊?」
最終,由於播出時長的限制,我還是沒能將上述這段畫面編進片子。二十八分三十秒的時長,要講的東西、想講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許就如同這場六十多年前的戰爭一樣,有些東西,註定無法留下痕跡。二次入緬決戰松山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日軍攻占緬甸首都仰光,切斷了滇緬公路南端運輸。當時,滇緬公路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日軍據此還可以威脅中國西南大後方。為了確保這條交通線的暢通,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入緬,聯合英美軍隊共同抗日。但是,由於盟軍之間的配合失誤,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遠征軍在緬北戰場便敗局已定。
五月五日,由於日軍已兵臨怒江西岸,國民政府被迫炸毀連接怒江兩岸的唯一橋樑惠通橋,滯留緬北的中國遠征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一九四二年夏季,除少數戰士隨英軍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戰士被迫走進野人山,準備從這裡繞道回國。
野人山,位於緬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稱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綿數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沒而得名。在這裡,滿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荊棘,山大林密,瘴癘橫行。遠征軍退入野人山後,僅僅過了十天就斷糧了,再加上環境惡劣,許多戰士都犧牲在這片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區中。
據戰後統計,在長達兩個月的撤退中,有將近五萬名遠征軍官兵,因饑渴疾病而永遠留在了野人山,最後集結於印度和滇西的遠征軍部隊,僅剩四萬餘人。在這四萬名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中,有一名筆名叫做穆旦的年輕詩人。幾年後,親身經歷野人山撤退的他,寫下了一首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軍占領緬甸全境,殘存的中國遠征軍全部撤出緬甸,第一次入緬作戰宣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歲的工兵戰士張羽富跟隨戰友們開抵怒江。此時,距離他參加部隊的那一天,還不到半年。張羽富所在的第八軍,隸屬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所屬人員除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倖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張羽富這樣在雲貴當地農村補充的新兵。對於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來說,有關參軍的記憶,其實並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憶說:「來了兩三個人把我捆起來,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說,說要拿你去當兵,怕你跑,我就說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這樣做,也不行。」
就是這樣一支全新的遠征軍,由於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為當時國內裝備最好的軍隊。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為打通滇緬公路交通線,配合盟軍在緬甸北部的反攻作戰,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在司令衛立煌的指揮下強渡怒江,第二次入緬作戰開始。
按照作戰計畫,渡過怒江之後,潮水般的中國遠征軍便湧向了松山。
松山,位於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由二十餘個峰巒構成,主峰海拔二千二百公尺,因全山遍佈松樹而得名。松山緊臨怒江西岸,是滇緬公路的必經之地,因此,在當時被西方記者稱作「東方直布羅陀」。
松山的西北是騰衝,西南是龍陵,松山位於中間。這個地方控制著一百五十公里直徑的區域,不把它攻占下來,兩面就不會暢通。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奉命進攻松山的部隊開始攻打松山週邊陣地竹子坡,松山戰役正式打響。當天,遠征軍戰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炮兵閻啟志從來沒打過這麼痛快的仗,他回憶說:「光打敵人,敵人沒有反擊,可能都被消滅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的上午,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對松山主峰的屏障陰登山進行了一番轟炸。轟炸結束後,遠征軍重炮團再次轟擊山頂,陰登山頓時被籠罩在一片硝煙之下。回憶起當時的慘烈情景,閻啟志說:「松山那麼粗的大樹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還有飛機轟炸。」
中午時分,火力掩護結束,遠征軍戰士們以為陰登山上的敵人工事已經被摧毀得差不多了,便開始向一片死寂的山頭推進。當兩個連的中國軍隊前進至敵人陣地一百公尺時,日軍突然開火。轉眼之間,衝擊陰登山的大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僅一個排的人生還。原來,經過飛機、大炮的轟炸,日軍的大多數地堡雖然彈痕累累,但依然沒有喪失作用。
早見政則是原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當時在松山與中國遠征軍對陣的,正是這支部隊。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在熊本組建成軍。最初編入侵華日軍第一○六師團來華參戰。一九四○年三月,因在南昌會戰中損失嚴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後,該聯隊又在日本福岡重建。一九四二年,這支部隊隨五十六師團入侵緬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軍部隊。從這一年起,該聯隊就一直駐守松山陣地。兩年的時間裡,日本軍人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類暗堡四十多座,地下坑道不計其數。
早間政則回憶當時日軍在松山構築的工事時說:「到處都是地堡,還安放了機關槍,眼前十五公尺左右還挖了溝,拉上了鐵絲網,掛上二十公分寬度的鐵板,每隔五公分掛一塊。敵人要是碰上的話,會發出『咯楞咯楞』的響聲。」
這些工事在建造之時,日軍已經用飛機炸彈做過試驗,結果是毫髮無損。所以,對於松山的工事,日軍緬甸方面軍司令河邊正三相信,它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強度的猛烈攻擊,並可堅守八個月以上。
自渡過怒江後一直進展順利的遠征軍戰士,開始意識到這座山上的敵人不太簡單。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六月中旬,滇西進入雨季。由於掐住滇緬公路要衝的松山仍未攻克,渡過怒江的中國遠征軍分散到騰衝、松山、龍陵三大戰場作戰,彈藥補給日益困難。能否拿下松山,逐漸成為整個緬北戰局的關鍵。
炮兵閻啟志此時早已感覺不到絲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認識的很多步兵戰友再也沒有回來。面對我們的鏡頭,他回憶說:「屍體黑壓壓的,死了多少人啊!僅僅攻了一個月,慘得很!」此時的戰地上,遍佈著各式各樣的傷患,頭部受傷的、眼部受傷的、鼻子受傷的、嘴受傷的,還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個松山戰役期間,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共出動轟炸機數百架次,試圖炸毀阻擋中國軍隊前進的日軍工事。松山上的松樹被炸得一乾二淨,但由於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鋼板架起來的,所以大炮和炸彈轟炸對日軍工事根本發生不了絲毫的作用。
轟炸產生不了作用,面對似乎堅不可摧的日軍地堡,中國軍隊只能以士兵的生命為代價,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進。面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日軍拼死抵抗,遠征軍正面和側面遍佈日軍火力,再加上日軍大炮和轟炸機的配合,至六月二十日,遠征軍已傷亡近三千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軍手中。
在閻啟志的記憶裡,日軍非常兇悍,每射出一發子彈,必須要打死或打傷敵人,不然他們就絕不開槍。他說:「日本人那個頑抗勁就沒法說了,一個傷兵,守著個暗堡一天一夜。」
這個跟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內抗戰劇裡日軍窩囊、愚蠢的形象刻畫有些不同——反動至極的日軍為什麼會為軍國主義者拼死效忠?一個簡單而可以接受的解釋就是文化與倫理的解釋:日本是一個推崇集體主義獻身的國家。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專著《德川宗教》裡曾經講過,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種所謂「目標達成」的文化,為了達到自己國家的特定目標,個人可以毫不計較地犧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無論是非對錯。
六月三十日,新編第八軍接替七十一軍擔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協助部隊過江的工兵張羽富,他所裝備的美式火焰噴射器派上了大用場。他和戰友們先用火焰噴射器往日軍地道裡噴射,然後再扔入幾箱炸藥將它爆塌,最後用土將坑道掩埋,這樣即使燒不死日軍,也會悶死他們。
早間政則至今回憶起火焰噴射器來還害怕不已:「火焰噴射器很厲害,地道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呻吟聲,就如同地獄一般。」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松山戰鬥陷入僵局,攻防雙方都已筋疲力盡。
七月底,由於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國遠征軍決定利用坑道作業,在日軍主堡壘下方開挖地道放置炸藥,從而一次性炸毀日軍堡壘。八月三日,張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連,開始一天三班制地輪流挖掘坑道。一連挖左邊,二連挖右邊,兩邊一起挖。挖出來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敵人發現。戰士曹含經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敵人的碉堡下麵,然後再搬運兩三噸炸藥。」
與此同時,日軍也覺察到遠征軍進行坑道爆破的意圖,開始悄悄向鄰近陣地疏散兵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四十分,遠征軍司令衛立煌早早渡過怒江,來到隱蔽觀察所。九點十五分,第八軍軍長何紹周用電話下達起爆命令。刹那間,兩個坑道共計三噸重的烈性炸藥被同時引爆。張羽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轟隆一聲,泥巴石頭飛上去兩三百公尺,炸死大概四十多個人,這兩個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個人。」
成功爆破後,遠征軍戰士終於衝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犧牲卻並沒有結束。就在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鄰近陣地的日軍,突然向子高地發起兇猛反撲。雙方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瘋狂的肉搏。
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的崔化山回憶:
半夜裡,敵人不聲不響地衝上來,我們全都發了瘋,不顧死活;我一槍托打倒一個鬼子,他還在地上滾,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沒想到他一口咬來,我的三個手指就被咬斷了;我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右手摸出一顆手榴彈,連續砸了他七八下,硬將他的腦袋敲爛了。
九月一日,蔣介石下達命令,限第八軍在「九一八」國恥日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從事。為了在規定時間內消滅殘餘日軍,第八軍副軍長李彌親自帶領特務營衝上松山,一連激戰數日。九月六日,他被人從松山扶下。據目擊者描述,此時的他鬍子拉碴,眼眶充血,赤著雙腳,軍服爛成碎條狀,身上兩處負傷,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戰役終於宣告結束。
生存下來的遠征軍戰士將戰友們的屍體從松山子高地拖下來。雖然事隔多年,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的李文德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著說:「我的老天啊,因為打日本人,死了那麼多的人。」雙方的屍骨已經分辨不清了
松山戰役結束後,日本軍部發布「拉孟守備隊全員玉碎」的消息。事實上,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還是有一部分日軍士兵化整為零逃出了包圍圈,早見政則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早見政則被遣返回國,回到家後,他看到了日本軍部當年發給他家人的戰亡通知書。
松山之戰,在早見政則身上留下了永遠的記號。面對我們的鏡頭,他脫下衣服,露出渾身彈痕,一邊撫摸著其中的一個彈孔,一邊說:「這裡是被捷克式機槍打的,子彈直接將這裡打穿了,現在按上去還會覺得疼。」
早間政則出身於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從戰場上回來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看他,連他們家的牛也高興地一直跟著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幹活了。早間政則說:「終於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松山之戰是一場玉碎之戰,現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採訪中,早間政則還告訴我們,他記得松山戰役自己至少打死了六十五個中國人。有一次他正在戰壕裡獨自思鄉,外邊的一個炸彈突然打到了戰壕裡,將他炸傷,當時情況緊急,並沒有藥,醫療兵只好先給他打了一針獸醫的消炎藥,然後將他抬下了陣地。恰恰因為這樣,他逃過了高地爆破,撿回了一條命。松山戰役結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戰役結束後,工兵張羽富並沒有馬上跟隨大部隊離開松山。他們還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當時,犧牲的戰士們全部都沒有被妥善埋葬。張羽富回憶說:「到了十月份,已經留了幾百來斤的骨頭,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戰役共歷時九十五天,中國遠征軍先後投入十個團二萬餘人,總計傷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陣亡四千餘人,日軍陣亡人數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人。
隨著松山戰役的結束,滇西緬北會戰的僵局終於被打破。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國軍隊光復騰衝。十一月三日,龍陵戰役結束。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國駐印軍隊在緬甸芒友與遠征軍會師,滇西緬北會戰至此勝利結束。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後,曾救治過一個在松山守備的日本兵。上個世紀八○年代,在滇西緬北戰役中日老兵見面會上,他再一次見到這個日本兵,付心德回憶說:「我到那裡去以後,碰到那個當年的日本兵,他上來抱著我就哭。他說他來了這裡六次,每次來都是想找我。」
在我們找到付心德的時候,老人已經一百零五歲了。「文革」的時候,他被槍斃了八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開始的時候還很害怕,到第四次以後就無所謂了,反而覺得還不如早點槍斃了來得乾脆。這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一百零五歲老人,到現在還自己開門診維持生計。在我們去採訪的前幾天,他的門診剛剛被查封,原因是他沒有行醫執照。老人說,他當然沒有現在的行醫執照,當年給他頒發行醫執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們難以想像,對於一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人,和平年代的這些小苦惱,在老人心裡會有怎樣的波瀾。
騰衝的中國遠征軍國殤墓園裡,一排排的墓碑下長眠著為國捐軀的戰士。其實,犧牲的那些遠征軍將士們,一部分埋在了緬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後來被拆除了。很多已經找不到屍首,有些就是找到了屍首卻已經認不出是誰了。回憶起當年的那些事,張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說:「這些農民的兒子確實可憐。像我這樣還活著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進中國,我就不會出來當兵了。」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六十多年過去了,讀著穆旦這首詩的結尾部分,我們彷彿看到了當年那些浴血奮戰的年輕身影,他們的名字也許不為人知,但歷史將會永遠載下這壯烈的一筆。
親身經歷者
張羽富——時為第八軍工兵營戰士
閻啟志——時為炮兵十團一營戰士
曹含經——時為第八軍八十二師二十六團戰士
崔化山——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
李文德——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
付心德——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
早見政則——時為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
編導手記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松山之戰。一個發生在明朝末年的東北,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興趣,是因為洪承疇。後者我同樣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團長我的團》。這一節的故事屬於後一個松山之戰,沒錯,就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的那場血腥戰鬥,就是《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南天門戰役的原型。
這一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給出一個主人公來,那我只能說松山戰役就是這個故事的「男一號」,和他相比,所有的戰役親身經歷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許正因為是配角,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在戰爭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將遺體交給山野的戰友們而言,這些無字碑下的英雄們還是幸運的,至少,他們還可以得到後人的瞻仰——雖然來過的後人們並不算太多,墓地裡最常見的,還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們。
這是我所做過的選題中最血腥最殘酷的一個,不是因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為歷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殘忍得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們貌似平靜的敍述,將原本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到的血腥和絕望轉嫁給了我們,讓我們一旦知道,就再也無法忘懷。我甚至開始懷疑,就在此時此刻,在我們太平無事、機械地、自足地生活著的同時,在世界上某一個仍然籠罩在硝煙中的角落,還在發生著什麼?
兩個素不相識、從未謀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這就是戰爭。
看採訪素材的時候,有段畫面讓我始終難忘:夕陽下,簡陋的南方農舍前,一位老農打扮的老兵對著攝影機激動地說:「你們這些搞電視的,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知道什麼是打仗嗎?知道什麼是槍林彈雨嗎?那槍,真的就像林子一樣;那子彈,真的就像下雨一樣,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樣啊!」出於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禮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電視嘛,哪有那麼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誰知道你們的事啊?」
最終,由於播出時長的限制,我還是沒能將上述這段畫面編進片子。二十八分三十秒的時長,要講的東西、想講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許就如同這場六十多年前的戰爭一樣,有些東西,註定無法留下痕跡。二次入緬決戰松山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日軍攻占緬甸首都仰光,切斷了滇緬公路南端運輸。當時,滇緬公路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日軍據此還可以威脅中國西南大後方。為了確保這條交通線的暢通,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入緬,聯合英美軍隊共同抗日。但是,由於盟軍之間的配合失誤,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遠征軍在緬北戰場便敗局已定。
五月五日,由於日軍已兵臨怒江西岸,國民政府被迫炸毀連接怒江兩岸的唯一橋樑惠通橋,滯留緬北的中國遠征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一九四二年夏季,除少數戰士隨英軍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戰士被迫走進野人山,準備從這裡繞道回國。
野人山,位於緬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稱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綿數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沒而得名。在這裡,滿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荊棘,山大林密,瘴癘橫行。遠征軍退入野人山後,僅僅過了十天就斷糧了,再加上環境惡劣,許多戰士都犧牲在這片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區中。
據戰後統計,在長達兩個月的撤退中,有將近五萬名遠征軍官兵,因饑渴疾病而永遠留在了野人山,最後集結於印度和滇西的遠征軍部隊,僅剩四萬餘人。在這四萬名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中,有一名筆名叫做穆旦的年輕詩人。幾年後,親身經歷野人山撤退的他,寫下了一首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軍占領緬甸全境,殘存的中國遠征軍全部撤出緬甸,第一次入緬作戰宣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歲的工兵戰士張羽富跟隨戰友們開抵怒江。此時,距離他參加部隊的那一天,還不到半年。張羽富所在的第八軍,隸屬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所屬人員除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倖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張羽富這樣在雲貴當地農村補充的新兵。對於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來說,有關參軍的記憶,其實並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憶說:「來了兩三個人把我捆起來,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說,說要拿你去當兵,怕你跑,我就說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這樣做,也不行。」
就是這樣一支全新的遠征軍,由於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為當時國內裝備最好的軍隊。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為打通滇緬公路交通線,配合盟軍在緬甸北部的反攻作戰,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在司令衛立煌的指揮下強渡怒江,第二次入緬作戰開始。
按照作戰計畫,渡過怒江之後,潮水般的中國遠征軍便湧向了松山。
松山,位於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由二十餘個峰巒構成,主峰海拔二千二百公尺,因全山遍佈松樹而得名。松山緊臨怒江西岸,是滇緬公路的必經之地,因此,在當時被西方記者稱作「東方直布羅陀」。
松山的西北是騰衝,西南是龍陵,松山位於中間。這個地方控制著一百五十公里直徑的區域,不把它攻占下來,兩面就不會暢通。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奉命進攻松山的部隊開始攻打松山週邊陣地竹子坡,松山戰役正式打響。當天,遠征軍戰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炮兵閻啟志從來沒打過這麼痛快的仗,他回憶說:「光打敵人,敵人沒有反擊,可能都被消滅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的上午,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對松山主峰的屏障陰登山進行了一番轟炸。轟炸結束後,遠征軍重炮團再次轟擊山頂,陰登山頓時被籠罩在一片硝煙之下。回憶起當時的慘烈情景,閻啟志說:「松山那麼粗的大樹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還有飛機轟炸。」
中午時分,火力掩護結束,遠征軍戰士們以為陰登山上的敵人工事已經被摧毀得差不多了,便開始向一片死寂的山頭推進。當兩個連的中國軍隊前進至敵人陣地一百公尺時,日軍突然開火。轉眼之間,衝擊陰登山的大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僅一個排的人生還。原來,經過飛機、大炮的轟炸,日軍的大多數地堡雖然彈痕累累,但依然沒有喪失作用。
早見政則是原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當時在松山與中國遠征軍對陣的,正是這支部隊。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在熊本組建成軍。最初編入侵華日軍第一○六師團來華參戰。一九四○年三月,因在南昌會戰中損失嚴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後,該聯隊又在日本福岡重建。一九四二年,這支部隊隨五十六師團入侵緬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軍部隊。從這一年起,該聯隊就一直駐守松山陣地。兩年的時間裡,日本軍人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類暗堡四十多座,地下坑道不計其數。
早間政則回憶當時日軍在松山構築的工事時說:「到處都是地堡,還安放了機關槍,眼前十五公尺左右還挖了溝,拉上了鐵絲網,掛上二十公分寬度的鐵板,每隔五公分掛一塊。敵人要是碰上的話,會發出『咯楞咯楞』的響聲。」
這些工事在建造之時,日軍已經用飛機炸彈做過試驗,結果是毫髮無損。所以,對於松山的工事,日軍緬甸方面軍司令河邊正三相信,它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強度的猛烈攻擊,並可堅守八個月以上。
自渡過怒江後一直進展順利的遠征軍戰士,開始意識到這座山上的敵人不太簡單。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六月中旬,滇西進入雨季。由於掐住滇緬公路要衝的松山仍未攻克,渡過怒江的中國遠征軍分散到騰衝、松山、龍陵三大戰場作戰,彈藥補給日益困難。能否拿下松山,逐漸成為整個緬北戰局的關鍵。
炮兵閻啟志此時早已感覺不到絲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認識的很多步兵戰友再也沒有回來。面對我們的鏡頭,他回憶說:「屍體黑壓壓的,死了多少人啊!僅僅攻了一個月,慘得很!」此時的戰地上,遍佈著各式各樣的傷患,頭部受傷的、眼部受傷的、鼻子受傷的、嘴受傷的,還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個松山戰役期間,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共出動轟炸機數百架次,試圖炸毀阻擋中國軍隊前進的日軍工事。松山上的松樹被炸得一乾二淨,但由於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鋼板架起來的,所以大炮和炸彈轟炸對日軍工事根本發生不了絲毫的作用。
轟炸產生不了作用,面對似乎堅不可摧的日軍地堡,中國軍隊只能以士兵的生命為代價,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進。面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日軍拼死抵抗,遠征軍正面和側面遍佈日軍火力,再加上日軍大炮和轟炸機的配合,至六月二十日,遠征軍已傷亡近三千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軍手中。
在閻啟志的記憶裡,日軍非常兇悍,每射出一發子彈,必須要打死或打傷敵人,不然他們就絕不開槍。他說:「日本人那個頑抗勁就沒法說了,一個傷兵,守著個暗堡一天一夜。」
這個跟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內抗戰劇裡日軍窩囊、愚蠢的形象刻畫有些不同——反動至極的日軍為什麼會為軍國主義者拼死效忠?一個簡單而可以接受的解釋就是文化與倫理的解釋:日本是一個推崇集體主義獻身的國家。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專著《德川宗教》裡曾經講過,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種所謂「目標達成」的文化,為了達到自己國家的特定目標,個人可以毫不計較地犧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無論是非對錯。
六月三十日,新編第八軍接替七十一軍擔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協助部隊過江的工兵張羽富,他所裝備的美式火焰噴射器派上了大用場。他和戰友們先用火焰噴射器往日軍地道裡噴射,然後再扔入幾箱炸藥將它爆塌,最後用土將坑道掩埋,這樣即使燒不死日軍,也會悶死他們。
早間政則至今回憶起火焰噴射器來還害怕不已:「火焰噴射器很厲害,地道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呻吟聲,就如同地獄一般。」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松山戰鬥陷入僵局,攻防雙方都已筋疲力盡。
七月底,由於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國遠征軍決定利用坑道作業,在日軍主堡壘下方開挖地道放置炸藥,從而一次性炸毀日軍堡壘。八月三日,張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連,開始一天三班制地輪流挖掘坑道。一連挖左邊,二連挖右邊,兩邊一起挖。挖出來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敵人發現。戰士曹含經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敵人的碉堡下麵,然後再搬運兩三噸炸藥。」
與此同時,日軍也覺察到遠征軍進行坑道爆破的意圖,開始悄悄向鄰近陣地疏散兵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四十分,遠征軍司令衛立煌早早渡過怒江,來到隱蔽觀察所。九點十五分,第八軍軍長何紹周用電話下達起爆命令。刹那間,兩個坑道共計三噸重的烈性炸藥被同時引爆。張羽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轟隆一聲,泥巴石頭飛上去兩三百公尺,炸死大概四十多個人,這兩個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個人。」
成功爆破後,遠征軍戰士終於衝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犧牲卻並沒有結束。就在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鄰近陣地的日軍,突然向子高地發起兇猛反撲。雙方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瘋狂的肉搏。
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的崔化山回憶:
半夜裡,敵人不聲不響地衝上來,我們全都發了瘋,不顧死活;我一槍托打倒一個鬼子,他還在地上滾,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沒想到他一口咬來,我的三個手指就被咬斷了;我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右手摸出一顆手榴彈,連續砸了他七八下,硬將他的腦袋敲爛了。
九月一日,蔣介石下達命令,限第八軍在「九一八」國恥日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從事。為了在規定時間內消滅殘餘日軍,第八軍副軍長李彌親自帶領特務營衝上松山,一連激戰數日。九月六日,他被人從松山扶下。據目擊者描述,此時的他鬍子拉碴,眼眶充血,赤著雙腳,軍服爛成碎條狀,身上兩處負傷,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戰役終於宣告結束。
生存下來的遠征軍戰士將戰友們的屍體從松山子高地拖下來。雖然事隔多年,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的李文德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著說:「我的老天啊,因為打日本人,死了那麼多的人。」雙方的屍骨已經分辨不清了
松山戰役結束後,日本軍部發布「拉孟守備隊全員玉碎」的消息。事實上,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還是有一部分日軍士兵化整為零逃出了包圍圈,早見政則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早見政則被遣返回國,回到家後,他看到了日本軍部當年發給他家人的戰亡通知書。
松山之戰,在早見政則身上留下了永遠的記號。面對我們的鏡頭,他脫下衣服,露出渾身彈痕,一邊撫摸著其中的一個彈孔,一邊說:「這裡是被捷克式機槍打的,子彈直接將這裡打穿了,現在按上去還會覺得疼。」
早間政則出身於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從戰場上回來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看他,連他們家的牛也高興地一直跟著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幹活了。早間政則說:「終於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松山之戰是一場玉碎之戰,現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採訪中,早間政則還告訴我們,他記得松山戰役自己至少打死了六十五個中國人。有一次他正在戰壕裡獨自思鄉,外邊的一個炸彈突然打到了戰壕裡,將他炸傷,當時情況緊急,並沒有藥,醫療兵只好先給他打了一針獸醫的消炎藥,然後將他抬下了陣地。恰恰因為這樣,他逃過了高地爆破,撿回了一條命。松山戰役結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戰役結束後,工兵張羽富並沒有馬上跟隨大部隊離開松山。他們還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當時,犧牲的戰士們全部都沒有被妥善埋葬。張羽富回憶說:「到了十月份,已經留了幾百來斤的骨頭,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戰役共歷時九十五天,中國遠征軍先後投入十個團二萬餘人,總計傷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陣亡四千餘人,日軍陣亡人數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人。
隨著松山戰役的結束,滇西緬北會戰的僵局終於被打破。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國軍隊光復騰衝。十一月三日,龍陵戰役結束。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國駐印軍隊在緬甸芒友與遠征軍會師,滇西緬北會戰至此勝利結束。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後,曾救治過一個在松山守備的日本兵。上個世紀八○年代,在滇西緬北戰役中日老兵見面會上,他再一次見到這個日本兵,付心德回憶說:「我到那裡去以後,碰到那個當年的日本兵,他上來抱著我就哭。他說他來了這裡六次,每次來都是想找我。」
在我們找到付心德的時候,老人已經一百零五歲了。「文革」的時候,他被槍斃了八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開始的時候還很害怕,到第四次以後就無所謂了,反而覺得還不如早點槍斃了來得乾脆。這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一百零五歲老人,到現在還自己開門診維持生計。在我們去採訪的前幾天,他的門診剛剛被查封,原因是他沒有行醫執照。老人說,他當然沒有現在的行醫執照,當年給他頒發行醫執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們難以想像,對於一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人,和平年代的這些小苦惱,在老人心裡會有怎樣的波瀾。
騰衝的中國遠征軍國殤墓園裡,一排排的墓碑下長眠著為國捐軀的戰士。其實,犧牲的那些遠征軍將士們,一部分埋在了緬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後來被拆除了。很多已經找不到屍首,有些就是找到了屍首卻已經認不出是誰了。回憶起當年的那些事,張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說:「這些農民的兒子確實可憐。像我這樣還活著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進中國,我就不會出來當兵了。」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六十多年過去了,讀著穆旦這首詩的結尾部分,我們彷彿看到了當年那些浴血奮戰的年輕身影,他們的名字也許不為人知,但歷史將會永遠載下這壯烈的一筆。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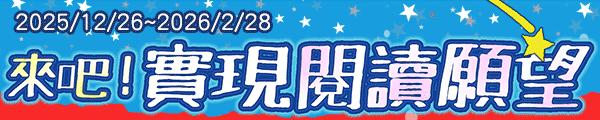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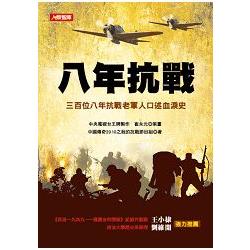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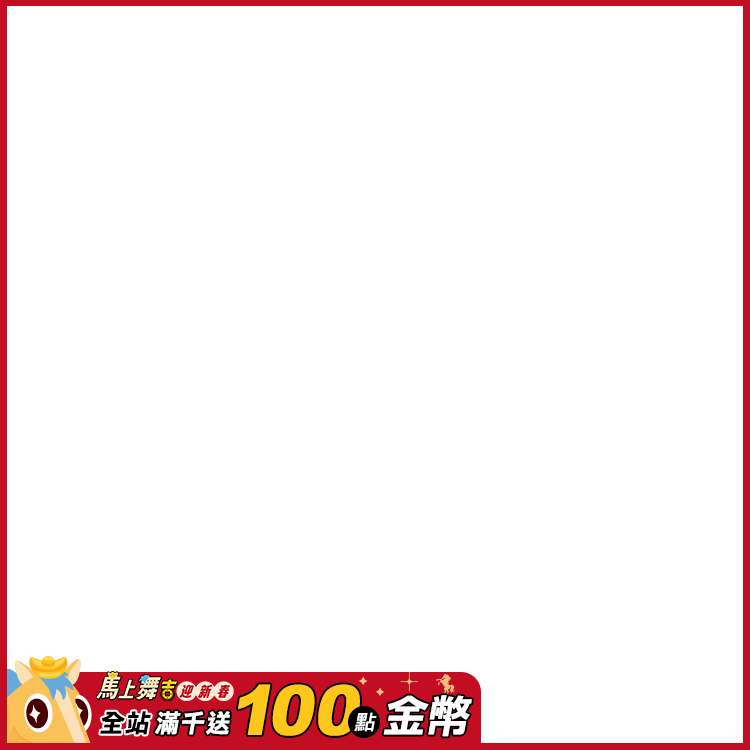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