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普發一萬放大術:滿千登記抽萬元好禮
大數據幫你找下一本愛書!今天填寫,隔天立刻揭曉!
聖誕節倒數!
500元以下禮物現貨,快速出貨專區→https://dks.tw/jmzos
用閱讀開啟視野,讓書成為照亮你人生的光
【金石堂選書】本月推薦您這些好書👉 快來看看
內容簡介
人人的衣食住行離不開城市,但你了解城市嗎?
看人們說起城市,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話要講。
易式品讀學 把中國城市品得入心入理、讓人讀得回味再三。
易中天教授將各個不同性格的中國城市作出分析和比較,包括地理、歷史淵源、文化和人民性格。看易中天這次怎樣以淵博的知識和活潑的文風來品讀城市!
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法。
人們喜歡談論城市,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個誰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話題,就像看完一部電視連續劇後,誰都可以發表一番議論一樣。城市之所以可讀,當然是因為它有個性、有魅力;城市街廓又因居民而氣韻生動,所以讀城又好比讀人,不同生活的人,就帶出相異的城市氛圍;比如:北京的大氣醇和、上海的開闊雅致、廣州的生猛鮮活、廈門的美麗溫馨、成都的悠閒灑脫、武漢的豪爽硬朗。
在《讀城記》裡,可以細細品味易中天觀察中國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他將城市特色收攏在精妙的譬喻與活潑的對比之下,活生生拉拔出每一城市的獨一質地。
看人們說起城市,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話要講。
易式品讀學 把中國城市品得入心入理、讓人讀得回味再三。
易中天教授將各個不同性格的中國城市作出分析和比較,包括地理、歷史淵源、文化和人民性格。看易中天這次怎樣以淵博的知識和活潑的文風來品讀城市!
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法。
人們喜歡談論城市,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個誰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話題,就像看完一部電視連續劇後,誰都可以發表一番議論一樣。城市之所以可讀,當然是因為它有個性、有魅力;城市街廓又因居民而氣韻生動,所以讀城又好比讀人,不同生活的人,就帶出相異的城市氛圍;比如:北京的大氣醇和、上海的開闊雅致、廣州的生猛鮮活、廈門的美麗溫馨、成都的悠閒灑脫、武漢的豪爽硬朗。
在《讀城記》裡,可以細細品味易中天觀察中國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他將城市特色收攏在精妙的譬喻與活潑的對比之下,活生生拉拔出每一城市的獨一質地。
序/導讀
易中天
一九四七年生,湖南長沙人,一九八一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
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帝國的惆悵》、《讀城記》、《黃與藍的交響──中西美學比較論》(與鄧曉芒合作)、《漢代風雲人物》等著作。近年撰寫出版了「易中天隨筆體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系列」四種:《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和《品人錄》。
因在電視臺開講三國歷史而迅速走紅,成為中國人氣最旺的「親民學者」。
一九四七年生,湖南長沙人,一九八一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
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帝國的惆悵》、《讀城記》、《黃與藍的交響──中西美學比較論》(與鄧曉芒合作)、《漢代風雲人物》等著作。近年撰寫出版了「易中天隨筆體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系列」四種:《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和《品人錄》。
因在電視臺開講三國歷史而迅速走紅,成為中國人氣最旺的「親民學者」。
試閱
第四章 廣州市
廣州是市。
廣州市很活很活。
廣州的活力讓人驚異。
用「生猛鮮活」四個字來概括廣州,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這些個性和風格雖然不能測定和量化,卻可以體會和玩味,也大體上可以用幾個字來描述和傳達,儘管不一定準確。廣州的個性和風格當然也不例外。如果說,北京的風格是「大氣醇和」,上海的風格是「開闊雅致」,廈門的風格是「美麗溫馨」,成都的風格是「灑脫閒適」,那麼,廣州的風格就是「生猛鮮活」。
廣州是一個不知疲倦、沒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保持著旺盛的生命活力。無論你在什麼時候(白天還是晚上)、從什麼方位(空中還是陸地)進入廣州,都立即能觸摸到它跳動的脈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機。這種「生猛鮮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亂跳地投入到廣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廣州的人常常會睡不著,尤其是逛過夜市之後。廣州的夜生活是那樣地豐富,能睡得著嗎?
廣州確實是一個「不夜城」。它似乎並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別人需要睡眠時(比方說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鮮活」。因此,當歷史在中原大地上演著一幕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時,它多少有點顯得默默無聞。但,如果歷史想要抽空打個盹,廣州便會活躍起來。由是之故,「生猛鮮活」的廣州似乎只屬於中國的近現代。
的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廣州無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個重要角色。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差不多有半數左右是由這三座城市書寫的。北京的一言九鼎當然毋庸置疑,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和廣州。廣州的歷史當然比上海久遠。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時秦將任囂在今廣州市中山路一帶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儘管那時的廣州並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現在的廣州。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州在「天朝大國」的版圖上,還是一個極不起眼的邊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過一個「超級大鎮」而已。然而,隨著古老的中國開始面對世界,走向現代,廣州突然變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強的頭顱,向著遙遠的北庭抗聲發言,乃至舉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盤踞北京的時代,南海岸的廣州和東海口的上海,輪番成為顛覆北方政權的革命策源地。後來,它似乎一度「退隱」了,只留下「廣交會」這個小小的「南風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繼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則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然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當上海成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陳舊落伍時,廣州卻重新顯示出它的「生猛鮮活」,而且勢頭正猛方興未艾。在短短十來年時間內,以廣州為中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先後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東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這塊原先的「蠻荒之地」變成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成為「淘金者」趨之若鶩的「金山」或「寶地」。儘管這些新興城市有不少在經濟發展水準和城市公共設施方面已經超過了廣州,但廣州畢竟還是它們的「老大」,是它們的歷史帶頭人和文化代言人。顯然,要瞭解這個地區活力的祕密,還得從廣州讀起。
更何況,廣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說啊!
那麼,讓我們走進廣州。(待續)一 怪異的城市
在中國,也許沒有哪個城市,會更像廣州這樣讓一個外地人感到怪異了。
乘火車從北京南下,一路上你會經過許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莊、邯鄲、鄭州、武漢、長沙、衡陽等等。這些城市多半不會使你感到奇異陌生,因為它們實在是大同小異。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飲食略有差異外,街道、建築、綠化、店面、商品、服務設施和新聞傳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堅持自己狹隘的地方文化習慣,那麼,你其實是很容易和這些城市認同的。
然而廣州卻不一樣。
改革開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進廣州,感覺往往都很強烈。第一是眼花繚亂,第二是暈頭轉向,第三是不得要領,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對於你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濕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何況廣州人的容貌是那樣的獨特,衣著是那樣的怪異,行色又是那樣匆匆,上前問路,會不會碰釘子呢?你心裡發怵。
當然,最困難的還是語言。廣州話雖然被稱作「白話」,然而一點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更難懂的是閩南話)。內地人稱之為「鳥語」,並說廣州的特點就是「鳥語花香」。語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廣州最感隔膜之處。因為語言不但是人際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個人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個人,如果被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所包圍,他心裡是不會自在的。幸虧只是「鳥語」啊!如果是「狼嚎」,那還得了?
廣州話聽不懂,廣州字也看不懂(儘管據說那也是「漢字」)。你能認出諸如「嘸」、「咁」、「?」,見過「?」、「叻」、「?」之類的字嗎?就算你認識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詞。比方說,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麼意思嗎?你當然也許會懂得什麼是「巴士」,什麼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卻不一定懂得「的士夠格」(絕非計程車很夠規格的意思)。至於其他那些「士」,比如什麼「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貼士」、「曬士」…。士多,買香菸、水果、罐頭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較固定的進行非法活動的地方。的士夠格,唱片夜總會或有小型樂隊伴奏的夜總會。多士,烤麵包片。卡士,演員表。菲士,面子。波士,老闆。甫士,明信片。貼士,小費。曬士,尺寸…之類,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讓人莫名其妙的是「鈒骨」。前些年,廣州滿街都是「鈒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現在不大能看見了),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廣州滿街都是骨科大夫,卻又不明白療傷正骨為什麼會「立等可取」,而廣州的骨傷又為什麼那麼多?其實所謂「鈒骨」,不過就是給裁好的衣料鎖邊,當然「立等可取」;而所謂「又靚又平」,則是「價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廣州人偏偏不按國內通行的方式來說、來寫,結果弄得外地人在廣州便變成了「識字的文盲」,聽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裡糊塗)啦」。
結果,一個外地人到了廣州,往往會連飯都吃不上,因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們的菜譜:豬手煲、牛腩粉、雲吞麵、魚生粥,這算是最大眾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領。至於「蠔油」、「焗」、「」之類,外地人更不知是怎麼回事,因而常常會面對菜單目瞪口呆,半天點不出一道菜來。有人曾在服務員的誘導下點了「牛奶」,結果端上來的卻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裡還再敢問津「瀨尿蝦」。
更為狼狽的是,外地人到了廣州,甚至可能連廁所也上不成。因為廣州廁所上寫的是「男界」、「女界」。所謂「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還是「禁止男人進入的界限」呢?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覷,不敢擅入。
於是,外地人就會納悶:我還在中國嗎?
當然是在中國,只不過有些特別罷了。(待續)的確,包括廣州在內,遠離中央政權的嶺南,歷來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話說:「千里同風不同俗」,廣東卻是連「風」也不同的。大庾、騎田、萌諸、都龐、越城這「五嶺」把北方吹來的風擋得嚴嚴實實,而南海的風又吹不過五嶺。於是嶺南嶺北,便既不同風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種」。嶺南人顴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膚色較深,與北方人在體質上確有較明顯的區別。再加上語言不通,衣食甚異,這就難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粵土,便會有身在異域的怪異之感了。
於是,在中原文化被視為華夏正宗的時代,嶺南文化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族文化」,嶺南人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野之人」。直到現在,不少北方人還把廣東人視為茹毛飲血的吃人生番,因為據說他們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離吃人也不太遠。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長蟲(蛇)、吃蛤蟆(青蛙)、吃螞蚱(實為禾蟲)、吃蟑螂(名曰龍虱,實為水蟑螂),吃貓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種北方人不吃的東西。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廣東人視為怪異而與之劃清界限。據說,當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時,弘忍便曾因他是「嶺南人」而不肯收留,說:「汝是嶺南人,怎生作佛?」誰知慧能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一句話,說得湖北人(一說江西人)弘忍暗自心驚,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缽也傳給了他。
慧能無疑是使北方人對嶺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禪宗衣缽後,連夜逃出湖北,回到嶺南,隱居十幾年,後來才在廣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脫穎而出,正式剃度受戒為僧,以後又到廣東曹溪開山傳教。不過,慧能開創的禪宗南宗雖然遠播中土,風靡華夏,成為中國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嶺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臉,但他傳播的,卻並不是「嶺南文化」。佛教和禪宗的主張,是「眾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麼會有「地域文化」的特徵?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們到中原去傳教時,說的一定不是「嶺南話」。
嶺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軍雖然是T恤衫、牛仔褲、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櫃等新潮商品,但讓文化人最感切膚之痛的還是那鋪天蓋地的粵語。今天,在中國一切追求「新潮」、「時髦」的地方,包括某些邊遠的城鎮,飯店改「酒樓」(同時特別注明「廣東名廚主理」),理髮店改「髮廊」(同時特別注明「特聘廣州名美容師」)已成為一時之風尚。(圖二十四)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樓」裡,不管飯桌上擺的是不是「正宗粵菜」,人們都會生硬地扣指為謝,或大叫「買單」。「打的」早已是通用語言,「鐳射」、「菲林」、「派對」、「拍拖」等粵語音譯或廣東土著名詞也頗為流行。一些內地傳媒也開始頻繁使用「爆棚」、「搶眼」之類的字眼,並以不使用為落伍、為土氣。至於「芝士圈」、「曲奇餅」之類大人們不知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為「中國小皇帝」們的愛物。
一句話,過去的怪異,已變成今日之時髦。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行動。如今,廣州人或廣東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愈來愈成為內地人們的仿效物件。人們仿效廣州人大興土木地裝修自己的住房,用電瓦煲湯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膽和蛇血泡進酒裡生吞,大大地抬起了當地的蛇價。這些生活方式當然並不一定都是從廣州人那裡學來的,但廣州的生活方式無疑是它們的「正宗」。總之人們的「活法」開始與前不同。除學會了喝早茶和過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說「哇」外,也學會了炒股票、炒期貨、炒「樓花」和「炒更」,自然也學會了「跳槽」,「炒」老闆的「魷魚」和被老闆「炒魷魚」,或把當國家公務員稱為「給政府打工」(廣州人自己則稱之為「打阿爺工」)。顯然,廣州文化或以廣州為代表的廣東文化對內地的影響已遠遠不止於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響到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勢頭比當年上海文化之影響內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說,上海人曾在全國造就了許許多多「小上海」,那麼,廣東人卻似乎要把全國都變成「大廣州」。
似乎誰也無法否認,廣州和廣東文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生猛鮮活」也最強勢的地域文化。(待續)但顯然,它又遠非是「地域」的。
以「擋不住的誘惑」風靡全國的廣州廣東文化,其真正魅力無疑在於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們爭相學說粵語,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粵語有多麼好聽;人們爭相請吃海鮮,也並非因為大家都覺得海鮮好吃,何況內地酒樓的海鮮也未必生猛。人們以此為時尚,完全因為這個地區在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成了國人羡慕的「首富之區」,這才使它們那怪異的生活方式和名詞術語沾光變成了時髦。因此,是改革開放成全了廣州廣東,而不是廣州廣東成就了改革開放。可以肯定,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廣州仍將只不過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南國都市,頂多和武漢、成都、西安、鄭州、南京、瀋陽平起平坐罷了,儘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粵菜和好聽的廣東音樂。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們當回事呢?
現在可就不一樣了。普天之下,真是何處不在粵語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們對於有著經濟優勢的地域及其文化總是羡慕的,而文化的傳播和接受又總是從表層的模仿開始的。當我們學著廣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聲地歡呼「哇」時,我們不是在學廣州,而是在學「先進」。似乎只要兩指在桌上輕輕一扣,就成了服務員不敢慢待的廣東「大款」,也就加入了現代化的潮流。看來,一種文化要想讓人刮目相看、趨之若鶩,就得有經濟實力作堅強後盾;而粵語文化的大舉北伐並大獲成功,則又首先因於這個地區經濟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開放在廣東首先獲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講話中曾感慨萬分地說,當年沒有選擇上海辦經濟特區是一大失誤。其實,這不但是時勢所使然,也是地勢所使然,甚至可以說是「別無選擇」。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只有廣東,才擔當得起這一偉大實驗的責任,也才有可能使這一實驗大告成功。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的。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全面啟動改革的進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鋪開的只有農村的改革,而可以並應該對外開放的也只有廣東、福建兩個省分。這兩個位於東南沿海又相對貧困的農業省分,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敗也不會影響大局,繼續閉關自守卻既不現實,也甚為可惜:港澳臺的經濟繁榮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棄與之合作的機會,放棄對其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利用,也等於坐失良機。
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廣東闖出了發達和繁榮,福建則要相對滯後一點。比如同期成為特區的廈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廈門卻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獲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臺灣對廈門的作用和影響遠不如香港之於深圳外,廣東有廣州而福州遠不能和廣州相比,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惜,這個因素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事實上,如果沒有廣州,僅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會如此成功。因為特區的成功不僅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廣東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廣州來創造和代表的。這是廣州和北京、上海、香港、臺北的不同之處。北京、上海、香港、臺北並不代表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臺文化,它們有許多並不屬於這些文化的個性的東西。北京、上海、香港、臺北的文化,是超越於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臺文化的,甚至還有某些抵觸之處(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歡上海人)。廣州卻是深深植根於廣東文化的。廣東人現在可以不喜歡廣州這個城市(太髒太擠太嘈雜),卻不會不喜歡廣州文化。事實上,廣州代表的,是廣東文化中現在看來比較優秀和先進的東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這些東西卻有不少要靠廈門而不是福州來代表。可以說,正是廣州,以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圍,為整個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廣州的祕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讀。
廣州,是連接過去(化外之地)和現在(經濟特區)的仲介點。
因此,儘管它的「生猛鮮活」是屬於現在時的,它的故事卻必須從古代說起。(待續)二 天高皇帝遠
廣州,從來就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
無論中央政府是在長安、洛陽、開封、南京或者北京,廣州都是一個邊遠的、偏僻的、鞭長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鎮。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規格,它顯然只能屬於最遠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長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嶺之隔,足以讓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視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然而從長安到成都,實在比到廣州近得多了。所以古人從未有過「粵道難」的說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到過廣州,也不大想到廣州。事實上,「蠻煙瘴雨」的嶺南,歷來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紀清廷官方規定的標準行程,從北京到廣州驛站,竟要五十六天(加急為二十七天),則對於所謂「天高皇帝遠」,便會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想想看吧,將近一兩個月的「時間差」,多少事情做不下來?
廣州距離中央政權既然有這樣遠的路程,那麼,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廣州,在事實上也心有餘而力不足,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樣,習慣了中央政府這種態度的廣州人,當然也早就學會了「看一隻眼不看另一隻眼」,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先斬後奏,甚至斬而不奏。
這種文化心理習慣在改革開放時期就表現為這樣一個「廣東經驗」:對於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夠、用足、用好、用活。具體說來,就是只要沒有明確規定不許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為可以做。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提倡改革,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地方許多省分,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廣東人看著的是那隻「閉著的眼」,福建人看著的是那隻「睜著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隻眼睜哪隻眼閉」,北京人則在議論「應該睜哪隻眼閉哪隻眼」。結果廣東上去了,福建滯後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則在不停地說話。看來,廣東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並非沒有文化上的原因。
廣州離「皇帝」很遠,離「外面的世界」卻很近。
廣州臨南海之濱,扼珠江之口,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有著天然的優勢。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就是於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廣州登陸,來到東土的。實際上,華南地區的出海口在晉時即已由徐聞、合浦一帶移至廣州。到了唐代,廣州便已以中國南海大港而著稱於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這時,廣州已設立「蕃坊」,城中外僑雜居,其所謂「蕃邦習俗」,對廣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可以說,從那時起,廣州人對於「蕃鬼」,便有些「見慣不怪」,習以為常。
不過那時的中國,的的確確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國。中國的文化,遠比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優越,尤其對於那時來華的「白蠻、赤蠻、大石、骨唐、昆侖」等國,就更是如此。總之,廣州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國文化的優越感為「底氣」的。這也是廣州與上海的不同之處。廣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而上海則是在「一張白紙」的情況下開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紀初,廣州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已大不如上海:廣州進出口的噸位數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租界大小則只有上海的一四七分之一。所以,上海的「西化」雖在廣州之後,卻比廣州「徹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車夫一類「苦力」說「洋徑?英語」外,一般來說只要肯學,英語說得都很好。廣州人卻喜歡把外來語言「本土化」,發明出諸如「打的」、「打波」之類「中外合資」的詞語,或諸如「佳士得」、「迷你」、「鐳射」之類中文色彩極濃的譯名。廣州給人的怪異感,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些話語的「不倫不類」引起的。
但這對於廣州人卻很正常。廣州人的「文化政策」,歷來就是「立足本土,兼收並容,合理改造,為我所用」。比方說,他們也用漢字,卻堅持讀粵音。當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他們是連「國語」都學不會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發明了一大堆只有他們自己才認識的「漢字」。廣州人對待中原文化的態度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其實,這也是「天高皇帝遠」所使然。(待續)所謂「天高皇帝遠」,顯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須自力更生。所以,廣州人的自強精神和自主意識也就特別強。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廣州和嶺南人民正是靠著自己的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自己闖開了一條生路,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獨創精神幾乎已成為他們的「文化無意識」。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廣州的文化,從飲食服飾、建築民居,到音樂美術、戲劇文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與內地大相異趣。自唐以降,優秀的嶺南詩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而近代崛起的「嶺南畫派」,更是銳意革新,獨樹一幟。嶺南畫派在繼承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相容西方攝影、透視等方法,終於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廣東音樂則在運用民族樂器的基礎上大膽採用外來樂器,於是便以其寬廣豐富的音域和優美嘹亮的音韻深得人們喜愛,享譽海內外。
實際上,即便廣州普通民眾的生活,也相當隨意和注重個性。廣州菜肴、點心、粥麵品種之多,堪稱中國之冠。除嶺南物產豐富、粵人注重飲食外,要求「吃出個性來」,也是原因之一。廣州人的穿著,更是五花八門。或講面料,或講款式,或講名牌,或講新潮,但更多的還是自己覺得怎麼好看就怎麼穿,或怎麼舒服就怎麼穿,比如穿西裝不打領帶,穿皮鞋不穿襪子等(此為廣州與深圳之不同處)。
相反,穿得過於一本正經,在廣州反倒會有怪異之感。一位廣州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單位一個同事西裝革履地走進來,大家便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改賣保險了?」原來,在廣州,只有推銷員才會穿得一本正經,其他人都穿得隨隨便便。(圖二十六)反正,在廣州,衣食住行均不妨個性化。不過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總和內地不一樣。內地人穿中山裝軍便服時,他們穿港式襯衫花衣服;內地人西裝領帶衣冠楚楚時,他們把西裝當茄克穿。內地人早上吃稀飯饅頭時,他們早上喝茶;內地人以「正宗粵菜生猛海鮮」為時尚時,他們卻對川菜湘菜東北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就使得外地人一進廣州,就覺得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實說怪也不怪。廣州既然是一個遠離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沒有什麼人來管他們和幫他們,他們當然就會按照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說三道四。事實上,即便有「北佬」評頭論足,廣州人也既聽不到又聽不懂。即便聽到了聽懂了,也「沒什麼所謂」。廣州人不喜歡爭論而喜歡實幹,而且喜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幹。在廣州人看來,北京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許多問題,都是「沒什麼所謂」的。或者借用一個哲學的說法,都是「假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要說爭不出什麼名堂,即便爭得出,也沒什麼實際效益。既然如此,爭論它幹什麼?顯然,廣州人廣東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的原則是「不爭論」,而廣州人也好廣東人也好,都不喜歡爭論。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廣州或廣東無思想。恰恰相反,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有著「思想搖籃」的美稱。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出了震驚全國的聲音,其影響極為深遠。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對本世紀中國的命運前途和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一個出在廣東,一個出在湖南,一個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尋味的。事實上,廣東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這其實也正是廣東文化或曰嶺南文化的特點,即「生猛鮮活」。生猛鮮活是和枯朽陳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生則猛,鮮則活。相反,枯則朽,陳則腐。這也正是一個古老帝國的古老文化可能會要遇到的問題。看來,嶺南文化能夠具有生猛鮮活的風格,或許就因為它「天高皇帝遠」!(待續)廣州與內地城市之最大區別,也許還在於其經濟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地城市,基本上是出於兩種目的而建立的,這就是「政治」和「軍事」。主要出於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於軍事目的而建立的則叫「鎮」。鎮,有重壓、安定、抑制、鎮服和武力據守等義。所以,重要或險要的地方叫鎮,在這些地方設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鎮。鎮以軍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軍事,故北京是「城」,武漢是「鎮」。城講「文治」,鎮重「武備」,它們都不會把商業和商品生產放在首位。
廣州卻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儘管廣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別名,但廣州的城市性質,卻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鎮」,而是「市」。由於「天高皇帝遠」,也由於歷代王朝對廣州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廣州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走的是與內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它不像「城」或「鎮」那樣看重政治和軍事,卻頗為重視商業和商業性的農業、手工業。早在漢初,它就已是我國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發展為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至宋時,則已成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兩代,廣州作為我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農業、手工業基地,商品經濟和海洋經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口增多,市場繁榮,與海外交往頻繁。據統計,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這九十年間,外輪抵港多達五一三○艘。鴉片戰爭時,廣州的進出口噸位數達二十八萬噸(同期上海只有九萬噸)。海洋經濟帶來的商業氣息,給廣州和整個嶺南地區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經濟活力,造成了一種新的氣象。與之相對應,整個珠江三角洲「棄田築塘,廢稻種桑」,成為商品性農業生產基地;而廣州則成為商品性手工業的中心,並以工藝精美而著稱於世,有所謂「蘇州樣,廣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廣州既然是「市」,則廣州之民風,也就自然會重財趨利。明清時有民謠云:「呼郎早趁大岡墟,妾理蠶繅已滿車。記取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可見亦農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風尚,市場、價格、交易等等也已成為人們的日常話題。至於經商貿易,當然也是廣州人競趨的職業。
廣州的這種民風,歷來頗受攻擊。但這些攻擊,顯然帶有文化上的偏見。要言之,他們是站在「城」和「鎮」的立場來攻擊「市」。「市」確乎是不同於「城」和「鎮」的。不論「城」也好,「鎮」也好,它們都主要是消費性的城市,其財政開支主要依賴農業稅收,部分依賴商業稅收,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即以清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八年)為例,是年北京七十萬人中,不事生產的八旗子弟和士紳官員就有二十八萬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這些人不必躬耕於壟畝,叫賣於街市,自然可以高談闊論於茶座,淺吟低唱於青樓,大講「義利之辨」或「逍遙之道」了。然而「市」卻是生產性的。什麼叫「市」?「市,買賣之所也。」既然是買賣,就必須不斷地買進賣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錢放在家裡,自己不會生兒子,老闆也不會有飯吃。因此,一個「市」,只要它一天不從事商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便立即會喪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義。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這就必須「生產」。生產,才有飯吃。所以,「城」與「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裡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異。要之,城多靜而市多動,城多雅而市多俗,城裡的人多會說而市上的人多會做,城裡的人多務虛而市上的人多務實。究其所以,大約也就是後者必須自己謀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廣州人為什麼不喜歡爭論,為什麼自主意識特別強,以及廣州為什麼會有生猛鮮活的風格,而且總是和內地不一樣了。就因為廣州是「市」,是中國最老也最大的一個市場。上海也有「市」的性質。但上海主要是外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當職員,廣州卻是廣州人自己當小老闆。所以,當中國諱言「市場經濟」時,以職員為主體的上海人很快就適應了計劃經濟,廣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經濟因數卻依然存在。結果,廣州和廣東人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上海人卻費了老半天才反應過來。廣州,畢竟是「老牌的市」啊!
廣州是市。
廣州市很活很活。
廣州的活力讓人驚異。
用「生猛鮮活」四個字來概括廣州,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這些個性和風格雖然不能測定和量化,卻可以體會和玩味,也大體上可以用幾個字來描述和傳達,儘管不一定準確。廣州的個性和風格當然也不例外。如果說,北京的風格是「大氣醇和」,上海的風格是「開闊雅致」,廈門的風格是「美麗溫馨」,成都的風格是「灑脫閒適」,那麼,廣州的風格就是「生猛鮮活」。
廣州是一個不知疲倦、沒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保持著旺盛的生命活力。無論你在什麼時候(白天還是晚上)、從什麼方位(空中還是陸地)進入廣州,都立即能觸摸到它跳動的脈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機。這種「生猛鮮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亂跳地投入到廣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廣州的人常常會睡不著,尤其是逛過夜市之後。廣州的夜生活是那樣地豐富,能睡得著嗎?
廣州確實是一個「不夜城」。它似乎並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別人需要睡眠時(比方說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鮮活」。因此,當歷史在中原大地上演著一幕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時,它多少有點顯得默默無聞。但,如果歷史想要抽空打個盹,廣州便會活躍起來。由是之故,「生猛鮮活」的廣州似乎只屬於中國的近現代。
的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廣州無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個重要角色。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差不多有半數左右是由這三座城市書寫的。北京的一言九鼎當然毋庸置疑,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和廣州。廣州的歷史當然比上海久遠。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時秦將任囂在今廣州市中山路一帶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儘管那時的廣州並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現在的廣州。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州在「天朝大國」的版圖上,還是一個極不起眼的邊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過一個「超級大鎮」而已。然而,隨著古老的中國開始面對世界,走向現代,廣州突然變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強的頭顱,向著遙遠的北庭抗聲發言,乃至舉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盤踞北京的時代,南海岸的廣州和東海口的上海,輪番成為顛覆北方政權的革命策源地。後來,它似乎一度「退隱」了,只留下「廣交會」這個小小的「南風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繼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則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然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當上海成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陳舊落伍時,廣州卻重新顯示出它的「生猛鮮活」,而且勢頭正猛方興未艾。在短短十來年時間內,以廣州為中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先後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東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這塊原先的「蠻荒之地」變成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成為「淘金者」趨之若鶩的「金山」或「寶地」。儘管這些新興城市有不少在經濟發展水準和城市公共設施方面已經超過了廣州,但廣州畢竟還是它們的「老大」,是它們的歷史帶頭人和文化代言人。顯然,要瞭解這個地區活力的祕密,還得從廣州讀起。
更何況,廣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說啊!
那麼,讓我們走進廣州。(待續)一 怪異的城市
在中國,也許沒有哪個城市,會更像廣州這樣讓一個外地人感到怪異了。
乘火車從北京南下,一路上你會經過許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莊、邯鄲、鄭州、武漢、長沙、衡陽等等。這些城市多半不會使你感到奇異陌生,因為它們實在是大同小異。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飲食略有差異外,街道、建築、綠化、店面、商品、服務設施和新聞傳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堅持自己狹隘的地方文化習慣,那麼,你其實是很容易和這些城市認同的。
然而廣州卻不一樣。
改革開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進廣州,感覺往往都很強烈。第一是眼花繚亂,第二是暈頭轉向,第三是不得要領,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對於你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濕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何況廣州人的容貌是那樣的獨特,衣著是那樣的怪異,行色又是那樣匆匆,上前問路,會不會碰釘子呢?你心裡發怵。
當然,最困難的還是語言。廣州話雖然被稱作「白話」,然而一點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更難懂的是閩南話)。內地人稱之為「鳥語」,並說廣州的特點就是「鳥語花香」。語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廣州最感隔膜之處。因為語言不但是人際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個人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個人,如果被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所包圍,他心裡是不會自在的。幸虧只是「鳥語」啊!如果是「狼嚎」,那還得了?
廣州話聽不懂,廣州字也看不懂(儘管據說那也是「漢字」)。你能認出諸如「嘸」、「咁」、「?」,見過「?」、「叻」、「?」之類的字嗎?就算你認識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詞。比方說,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麼意思嗎?你當然也許會懂得什麼是「巴士」,什麼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卻不一定懂得「的士夠格」(絕非計程車很夠規格的意思)。至於其他那些「士」,比如什麼「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貼士」、「曬士」…。士多,買香菸、水果、罐頭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較固定的進行非法活動的地方。的士夠格,唱片夜總會或有小型樂隊伴奏的夜總會。多士,烤麵包片。卡士,演員表。菲士,面子。波士,老闆。甫士,明信片。貼士,小費。曬士,尺寸…之類,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讓人莫名其妙的是「鈒骨」。前些年,廣州滿街都是「鈒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現在不大能看見了),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廣州滿街都是骨科大夫,卻又不明白療傷正骨為什麼會「立等可取」,而廣州的骨傷又為什麼那麼多?其實所謂「鈒骨」,不過就是給裁好的衣料鎖邊,當然「立等可取」;而所謂「又靚又平」,則是「價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廣州人偏偏不按國內通行的方式來說、來寫,結果弄得外地人在廣州便變成了「識字的文盲」,聽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裡糊塗)啦」。
結果,一個外地人到了廣州,往往會連飯都吃不上,因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們的菜譜:豬手煲、牛腩粉、雲吞麵、魚生粥,這算是最大眾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領。至於「蠔油」、「焗」、「」之類,外地人更不知是怎麼回事,因而常常會面對菜單目瞪口呆,半天點不出一道菜來。有人曾在服務員的誘導下點了「牛奶」,結果端上來的卻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裡還再敢問津「瀨尿蝦」。
更為狼狽的是,外地人到了廣州,甚至可能連廁所也上不成。因為廣州廁所上寫的是「男界」、「女界」。所謂「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還是「禁止男人進入的界限」呢?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覷,不敢擅入。
於是,外地人就會納悶:我還在中國嗎?
當然是在中國,只不過有些特別罷了。(待續)的確,包括廣州在內,遠離中央政權的嶺南,歷來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話說:「千里同風不同俗」,廣東卻是連「風」也不同的。大庾、騎田、萌諸、都龐、越城這「五嶺」把北方吹來的風擋得嚴嚴實實,而南海的風又吹不過五嶺。於是嶺南嶺北,便既不同風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種」。嶺南人顴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膚色較深,與北方人在體質上確有較明顯的區別。再加上語言不通,衣食甚異,這就難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粵土,便會有身在異域的怪異之感了。
於是,在中原文化被視為華夏正宗的時代,嶺南文化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族文化」,嶺南人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野之人」。直到現在,不少北方人還把廣東人視為茹毛飲血的吃人生番,因為據說他們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離吃人也不太遠。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長蟲(蛇)、吃蛤蟆(青蛙)、吃螞蚱(實為禾蟲)、吃蟑螂(名曰龍虱,實為水蟑螂),吃貓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種北方人不吃的東西。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廣東人視為怪異而與之劃清界限。據說,當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時,弘忍便曾因他是「嶺南人」而不肯收留,說:「汝是嶺南人,怎生作佛?」誰知慧能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一句話,說得湖北人(一說江西人)弘忍暗自心驚,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缽也傳給了他。
慧能無疑是使北方人對嶺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禪宗衣缽後,連夜逃出湖北,回到嶺南,隱居十幾年,後來才在廣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脫穎而出,正式剃度受戒為僧,以後又到廣東曹溪開山傳教。不過,慧能開創的禪宗南宗雖然遠播中土,風靡華夏,成為中國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嶺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臉,但他傳播的,卻並不是「嶺南文化」。佛教和禪宗的主張,是「眾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麼會有「地域文化」的特徵?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們到中原去傳教時,說的一定不是「嶺南話」。
嶺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軍雖然是T恤衫、牛仔褲、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櫃等新潮商品,但讓文化人最感切膚之痛的還是那鋪天蓋地的粵語。今天,在中國一切追求「新潮」、「時髦」的地方,包括某些邊遠的城鎮,飯店改「酒樓」(同時特別注明「廣東名廚主理」),理髮店改「髮廊」(同時特別注明「特聘廣州名美容師」)已成為一時之風尚。(圖二十四)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樓」裡,不管飯桌上擺的是不是「正宗粵菜」,人們都會生硬地扣指為謝,或大叫「買單」。「打的」早已是通用語言,「鐳射」、「菲林」、「派對」、「拍拖」等粵語音譯或廣東土著名詞也頗為流行。一些內地傳媒也開始頻繁使用「爆棚」、「搶眼」之類的字眼,並以不使用為落伍、為土氣。至於「芝士圈」、「曲奇餅」之類大人們不知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為「中國小皇帝」們的愛物。
一句話,過去的怪異,已變成今日之時髦。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行動。如今,廣州人或廣東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愈來愈成為內地人們的仿效物件。人們仿效廣州人大興土木地裝修自己的住房,用電瓦煲湯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膽和蛇血泡進酒裡生吞,大大地抬起了當地的蛇價。這些生活方式當然並不一定都是從廣州人那裡學來的,但廣州的生活方式無疑是它們的「正宗」。總之人們的「活法」開始與前不同。除學會了喝早茶和過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說「哇」外,也學會了炒股票、炒期貨、炒「樓花」和「炒更」,自然也學會了「跳槽」,「炒」老闆的「魷魚」和被老闆「炒魷魚」,或把當國家公務員稱為「給政府打工」(廣州人自己則稱之為「打阿爺工」)。顯然,廣州文化或以廣州為代表的廣東文化對內地的影響已遠遠不止於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響到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勢頭比當年上海文化之影響內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說,上海人曾在全國造就了許許多多「小上海」,那麼,廣東人卻似乎要把全國都變成「大廣州」。
似乎誰也無法否認,廣州和廣東文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生猛鮮活」也最強勢的地域文化。(待續)但顯然,它又遠非是「地域」的。
以「擋不住的誘惑」風靡全國的廣州廣東文化,其真正魅力無疑在於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們爭相學說粵語,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粵語有多麼好聽;人們爭相請吃海鮮,也並非因為大家都覺得海鮮好吃,何況內地酒樓的海鮮也未必生猛。人們以此為時尚,完全因為這個地區在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成了國人羡慕的「首富之區」,這才使它們那怪異的生活方式和名詞術語沾光變成了時髦。因此,是改革開放成全了廣州廣東,而不是廣州廣東成就了改革開放。可以肯定,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廣州仍將只不過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南國都市,頂多和武漢、成都、西安、鄭州、南京、瀋陽平起平坐罷了,儘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粵菜和好聽的廣東音樂。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們當回事呢?
現在可就不一樣了。普天之下,真是何處不在粵語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們對於有著經濟優勢的地域及其文化總是羡慕的,而文化的傳播和接受又總是從表層的模仿開始的。當我們學著廣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聲地歡呼「哇」時,我們不是在學廣州,而是在學「先進」。似乎只要兩指在桌上輕輕一扣,就成了服務員不敢慢待的廣東「大款」,也就加入了現代化的潮流。看來,一種文化要想讓人刮目相看、趨之若鶩,就得有經濟實力作堅強後盾;而粵語文化的大舉北伐並大獲成功,則又首先因於這個地區經濟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開放在廣東首先獲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講話中曾感慨萬分地說,當年沒有選擇上海辦經濟特區是一大失誤。其實,這不但是時勢所使然,也是地勢所使然,甚至可以說是「別無選擇」。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只有廣東,才擔當得起這一偉大實驗的責任,也才有可能使這一實驗大告成功。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的。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全面啟動改革的進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鋪開的只有農村的改革,而可以並應該對外開放的也只有廣東、福建兩個省分。這兩個位於東南沿海又相對貧困的農業省分,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敗也不會影響大局,繼續閉關自守卻既不現實,也甚為可惜:港澳臺的經濟繁榮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棄與之合作的機會,放棄對其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利用,也等於坐失良機。
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廣東闖出了發達和繁榮,福建則要相對滯後一點。比如同期成為特區的廈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廈門卻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獲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臺灣對廈門的作用和影響遠不如香港之於深圳外,廣東有廣州而福州遠不能和廣州相比,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惜,這個因素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事實上,如果沒有廣州,僅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會如此成功。因為特區的成功不僅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廣東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廣州來創造和代表的。這是廣州和北京、上海、香港、臺北的不同之處。北京、上海、香港、臺北並不代表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臺文化,它們有許多並不屬於這些文化的個性的東西。北京、上海、香港、臺北的文化,是超越於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臺文化的,甚至還有某些抵觸之處(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歡上海人)。廣州卻是深深植根於廣東文化的。廣東人現在可以不喜歡廣州這個城市(太髒太擠太嘈雜),卻不會不喜歡廣州文化。事實上,廣州代表的,是廣東文化中現在看來比較優秀和先進的東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這些東西卻有不少要靠廈門而不是福州來代表。可以說,正是廣州,以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圍,為整個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廣州的祕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讀。
廣州,是連接過去(化外之地)和現在(經濟特區)的仲介點。
因此,儘管它的「生猛鮮活」是屬於現在時的,它的故事卻必須從古代說起。(待續)二 天高皇帝遠
廣州,從來就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
無論中央政府是在長安、洛陽、開封、南京或者北京,廣州都是一個邊遠的、偏僻的、鞭長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鎮。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規格,它顯然只能屬於最遠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長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嶺之隔,足以讓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視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然而從長安到成都,實在比到廣州近得多了。所以古人從未有過「粵道難」的說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到過廣州,也不大想到廣州。事實上,「蠻煙瘴雨」的嶺南,歷來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紀清廷官方規定的標準行程,從北京到廣州驛站,竟要五十六天(加急為二十七天),則對於所謂「天高皇帝遠」,便會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想想看吧,將近一兩個月的「時間差」,多少事情做不下來?
廣州距離中央政權既然有這樣遠的路程,那麼,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廣州,在事實上也心有餘而力不足,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樣,習慣了中央政府這種態度的廣州人,當然也早就學會了「看一隻眼不看另一隻眼」,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先斬後奏,甚至斬而不奏。
這種文化心理習慣在改革開放時期就表現為這樣一個「廣東經驗」:對於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夠、用足、用好、用活。具體說來,就是只要沒有明確規定不許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為可以做。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提倡改革,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地方許多省分,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廣東人看著的是那隻「閉著的眼」,福建人看著的是那隻「睜著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隻眼睜哪隻眼閉」,北京人則在議論「應該睜哪隻眼閉哪隻眼」。結果廣東上去了,福建滯後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則在不停地說話。看來,廣東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並非沒有文化上的原因。
廣州離「皇帝」很遠,離「外面的世界」卻很近。
廣州臨南海之濱,扼珠江之口,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有著天然的優勢。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就是於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廣州登陸,來到東土的。實際上,華南地區的出海口在晉時即已由徐聞、合浦一帶移至廣州。到了唐代,廣州便已以中國南海大港而著稱於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這時,廣州已設立「蕃坊」,城中外僑雜居,其所謂「蕃邦習俗」,對廣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可以說,從那時起,廣州人對於「蕃鬼」,便有些「見慣不怪」,習以為常。
不過那時的中國,的的確確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國。中國的文化,遠比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優越,尤其對於那時來華的「白蠻、赤蠻、大石、骨唐、昆侖」等國,就更是如此。總之,廣州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國文化的優越感為「底氣」的。這也是廣州與上海的不同之處。廣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而上海則是在「一張白紙」的情況下開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紀初,廣州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已大不如上海:廣州進出口的噸位數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租界大小則只有上海的一四七分之一。所以,上海的「西化」雖在廣州之後,卻比廣州「徹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車夫一類「苦力」說「洋徑?英語」外,一般來說只要肯學,英語說得都很好。廣州人卻喜歡把外來語言「本土化」,發明出諸如「打的」、「打波」之類「中外合資」的詞語,或諸如「佳士得」、「迷你」、「鐳射」之類中文色彩極濃的譯名。廣州給人的怪異感,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些話語的「不倫不類」引起的。
但這對於廣州人卻很正常。廣州人的「文化政策」,歷來就是「立足本土,兼收並容,合理改造,為我所用」。比方說,他們也用漢字,卻堅持讀粵音。當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他們是連「國語」都學不會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發明了一大堆只有他們自己才認識的「漢字」。廣州人對待中原文化的態度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其實,這也是「天高皇帝遠」所使然。(待續)所謂「天高皇帝遠」,顯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須自力更生。所以,廣州人的自強精神和自主意識也就特別強。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廣州和嶺南人民正是靠著自己的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自己闖開了一條生路,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獨創精神幾乎已成為他們的「文化無意識」。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廣州的文化,從飲食服飾、建築民居,到音樂美術、戲劇文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與內地大相異趣。自唐以降,優秀的嶺南詩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而近代崛起的「嶺南畫派」,更是銳意革新,獨樹一幟。嶺南畫派在繼承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相容西方攝影、透視等方法,終於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廣東音樂則在運用民族樂器的基礎上大膽採用外來樂器,於是便以其寬廣豐富的音域和優美嘹亮的音韻深得人們喜愛,享譽海內外。
實際上,即便廣州普通民眾的生活,也相當隨意和注重個性。廣州菜肴、點心、粥麵品種之多,堪稱中國之冠。除嶺南物產豐富、粵人注重飲食外,要求「吃出個性來」,也是原因之一。廣州人的穿著,更是五花八門。或講面料,或講款式,或講名牌,或講新潮,但更多的還是自己覺得怎麼好看就怎麼穿,或怎麼舒服就怎麼穿,比如穿西裝不打領帶,穿皮鞋不穿襪子等(此為廣州與深圳之不同處)。
相反,穿得過於一本正經,在廣州反倒會有怪異之感。一位廣州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單位一個同事西裝革履地走進來,大家便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改賣保險了?」原來,在廣州,只有推銷員才會穿得一本正經,其他人都穿得隨隨便便。(圖二十六)反正,在廣州,衣食住行均不妨個性化。不過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總和內地不一樣。內地人穿中山裝軍便服時,他們穿港式襯衫花衣服;內地人西裝領帶衣冠楚楚時,他們把西裝當茄克穿。內地人早上吃稀飯饅頭時,他們早上喝茶;內地人以「正宗粵菜生猛海鮮」為時尚時,他們卻對川菜湘菜東北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就使得外地人一進廣州,就覺得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實說怪也不怪。廣州既然是一個遠離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沒有什麼人來管他們和幫他們,他們當然就會按照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說三道四。事實上,即便有「北佬」評頭論足,廣州人也既聽不到又聽不懂。即便聽到了聽懂了,也「沒什麼所謂」。廣州人不喜歡爭論而喜歡實幹,而且喜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幹。在廣州人看來,北京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許多問題,都是「沒什麼所謂」的。或者借用一個哲學的說法,都是「假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要說爭不出什麼名堂,即便爭得出,也沒什麼實際效益。既然如此,爭論它幹什麼?顯然,廣州人廣東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的原則是「不爭論」,而廣州人也好廣東人也好,都不喜歡爭論。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廣州或廣東無思想。恰恰相反,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有著「思想搖籃」的美稱。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出了震驚全國的聲音,其影響極為深遠。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對本世紀中國的命運前途和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一個出在廣東,一個出在湖南,一個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尋味的。事實上,廣東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這其實也正是廣東文化或曰嶺南文化的特點,即「生猛鮮活」。生猛鮮活是和枯朽陳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生則猛,鮮則活。相反,枯則朽,陳則腐。這也正是一個古老帝國的古老文化可能會要遇到的問題。看來,嶺南文化能夠具有生猛鮮活的風格,或許就因為它「天高皇帝遠」!(待續)廣州與內地城市之最大區別,也許還在於其經濟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地城市,基本上是出於兩種目的而建立的,這就是「政治」和「軍事」。主要出於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於軍事目的而建立的則叫「鎮」。鎮,有重壓、安定、抑制、鎮服和武力據守等義。所以,重要或險要的地方叫鎮,在這些地方設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鎮。鎮以軍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軍事,故北京是「城」,武漢是「鎮」。城講「文治」,鎮重「武備」,它們都不會把商業和商品生產放在首位。
廣州卻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儘管廣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別名,但廣州的城市性質,卻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鎮」,而是「市」。由於「天高皇帝遠」,也由於歷代王朝對廣州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廣州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走的是與內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它不像「城」或「鎮」那樣看重政治和軍事,卻頗為重視商業和商業性的農業、手工業。早在漢初,它就已是我國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發展為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至宋時,則已成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兩代,廣州作為我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農業、手工業基地,商品經濟和海洋經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口增多,市場繁榮,與海外交往頻繁。據統計,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這九十年間,外輪抵港多達五一三○艘。鴉片戰爭時,廣州的進出口噸位數達二十八萬噸(同期上海只有九萬噸)。海洋經濟帶來的商業氣息,給廣州和整個嶺南地區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經濟活力,造成了一種新的氣象。與之相對應,整個珠江三角洲「棄田築塘,廢稻種桑」,成為商品性農業生產基地;而廣州則成為商品性手工業的中心,並以工藝精美而著稱於世,有所謂「蘇州樣,廣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廣州既然是「市」,則廣州之民風,也就自然會重財趨利。明清時有民謠云:「呼郎早趁大岡墟,妾理蠶繅已滿車。記取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可見亦農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風尚,市場、價格、交易等等也已成為人們的日常話題。至於經商貿易,當然也是廣州人競趨的職業。
廣州的這種民風,歷來頗受攻擊。但這些攻擊,顯然帶有文化上的偏見。要言之,他們是站在「城」和「鎮」的立場來攻擊「市」。「市」確乎是不同於「城」和「鎮」的。不論「城」也好,「鎮」也好,它們都主要是消費性的城市,其財政開支主要依賴農業稅收,部分依賴商業稅收,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即以清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八年)為例,是年北京七十萬人中,不事生產的八旗子弟和士紳官員就有二十八萬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這些人不必躬耕於壟畝,叫賣於街市,自然可以高談闊論於茶座,淺吟低唱於青樓,大講「義利之辨」或「逍遙之道」了。然而「市」卻是生產性的。什麼叫「市」?「市,買賣之所也。」既然是買賣,就必須不斷地買進賣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錢放在家裡,自己不會生兒子,老闆也不會有飯吃。因此,一個「市」,只要它一天不從事商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便立即會喪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義。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這就必須「生產」。生產,才有飯吃。所以,「城」與「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裡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異。要之,城多靜而市多動,城多雅而市多俗,城裡的人多會說而市上的人多會做,城裡的人多務虛而市上的人多務實。究其所以,大約也就是後者必須自己謀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廣州人為什麼不喜歡爭論,為什麼自主意識特別強,以及廣州為什麼會有生猛鮮活的風格,而且總是和內地不一樣了。就因為廣州是「市」,是中國最老也最大的一個市場。上海也有「市」的性質。但上海主要是外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當職員,廣州卻是廣州人自己當小老闆。所以,當中國諱言「市場經濟」時,以職員為主體的上海人很快就適應了計劃經濟,廣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經濟因數卻依然存在。結果,廣州和廣東人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上海人卻費了老半天才反應過來。廣州,畢竟是「老牌的市」啊!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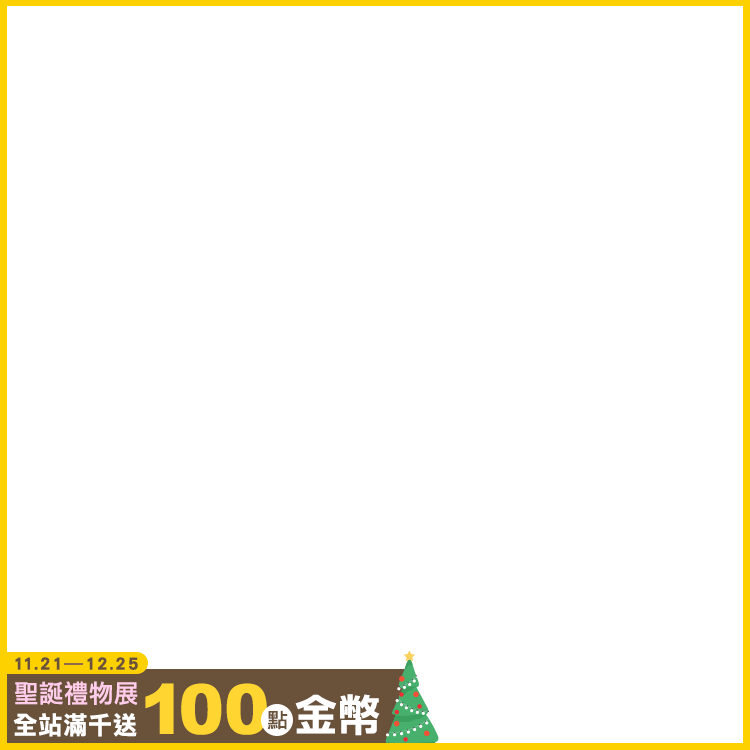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