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家,即回家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離家才認識故鄉,是我近年的心情。
這些年我在兩岸三城移動,台北、上海和北京,幾乎每月繞行一次。我常自我調侃,說自己是狡兔三窟,過著一種離家就是回家的日子。
北京號稱「帝都」,上海又名「魔都」,台北則是我出生的地方。這三個城市幾乎天天出現在兩岸的媒體上,是兩岸民眾最熟悉的城市。這三城也有個共同點,即都是移民城市。台北居民多半是明、清時代移居者,也有不少是1949年來台的上海人、北平人(北京的原名)。上海和北京則是大陸各省移民的重鎮,長住的台胞不在少數,更有大量來自各地的流動人口在此生活。
過客抑或歸人?距離縮短彼此
移民城市,送往迎來的聚會特別頻繁,當然少不了來自三城的人同桌共餐。「你這次什麼時候回來?這次待多久?下次什麼時候回來?」是三個城市友人聚會時,最常問我的幾個問題。這時,我是他們中的一夥,是當地的自己人。我在上海是新上海人,在北京是「北漂」,在台北是自大陸返台的台灣人。
此外,我也往往成為當地友人閒聊其他二城的主角――當北京人討論台灣的政治、電視名嘴,上海人閒聊台灣的旅遊、房價,這時我是台北來的台胞;當上海人批評北京的交通、空氣,這時我是在北京的「北漂」;當北京人議論上海人冷漠、不講普通話,這時我成為新上海人了;回台灣參加老友聚會,一談到兩岸議題時,我又成為移居大陸的歸人。
「離家就是回家,回家卻是客人」,是我這些年往返兩岸,常住三城的生活寫照。這三座城市幾乎在同一經度上,只是緯度有差,南北差距二千多公里。距離或許不算遠,但不同的緯度,卻足以形成不同的地理風貌。
在城市季節間悠遊,數字轉換
冬末早春是季節轉換的日子。對於長居四季如春的台北人,很難感受季節的更迭變化。如果,你有興致體驗南北氣候的差異,我推薦下面這趟三城行走的溫差行程。今年初春三月,你或許就可體驗一下。
前年三月,我從攝氏15度的台北直飛上海,下機時攝氏5度,大衣、圍巾、外套一樣不少。三月的上海細雨紛紛,置身在溼冷但清淨的空氣中,走在初吐新芽的梧桐樹下,恰是春寒料峭。七天後,我又飛到零下5度的北京,走出機場大門,我幾乎將行李箱帶來的衣服全部都套上,從頭到腳包裡得密不透風。那時雖是日正當中,屋外依然凍人。天寒地凍一周後,我再從北京直飛台北,下機又回到宜人的攝氏20度,正是春暖花開的台北四月天了。這三城走一趟,你肯定能體會季節轉換的情趣。
台北地方小,大眾交通十分便捷,約30分鐘內可到達多數地區,出租車費用一般不超過台幣300元;但上海和北京就完全不同,是絕對的大都市。台北面積只有271.8平方公里,上海面積有台北的24倍大(6340平方公里),北京更有62倍大(16410平方公里);台北人口267萬,北京則超過2100萬人,是台北的8倍;上海更有2500萬人口,超過台北9倍。
大城堵車試煉,難得氣定神閒
2008年,我開始長住上海時,最初的困擾就是交通。上海出租車據說是全大陸最有規範的,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尖峰時間叫不到車、塞車還是必然的,動輒一、二小時的車程總是令我心煩意亂,尤其是東西橫跨黃浦江的晚餐聚會,至少要提前一個半小時出發,才能確保不會遲到太久。
直到2009年我開始在北京長住,經歷了「首堵」之都的考驗後,終於練就搭車如同打坐般氣定神閒的功夫。這兩年,堵車已成為北京的日常生活,下班後同事的晚餐聚會也大都盡量約在辦公樓附近、或是地鐵可達之處。但北京地鐵下班時段的擁擠場面,就如同跨年煙火散場時的台北捷運一樣,非一般外來人能適應。何況北京地方大,地鐵站不夠密集,出了地鐵站,距離目的地動輒近二公里,更是常有的情況。尤其是冬天,在雪地上行走二公里,對南方遊客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在北京的日子,隨身攜帶地圖,先規劃出行路線,交叉搭配運用出租車和地鐵,提前二小時出門,已是日常功課了。歷經上海、北京「地大車堵出行難」的鍛鍊後,如今我每次回到台北,搭計程車,再無堵車的感覺了。
東風西風夾吹,上海地球村
此外,三城的發展歷史的不同,也醞釀出不同的城市風格。他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心靈的提升與成長,和經濟成長同等重要,並且相信這才是真正的幸福,他允諾人民將落實世界上最為獨到且進化的哲學和政策。與其他不擇手段只為提高所得要人民犧牲個人的幸福、影響家人感情的開發國家相比,這的確是很不一樣的政策。
不丹國王的政見讓人感受到他將朝著國民個人最幸福的方向而樹立國家政策的強烈意志。除此之外,像是不丹人有義務平時也要穿著不丹傳統服飾、規定建築物必須採用傳統的工法使用混凝土或是磚頭建造,規定用木頭做窗戶時不能使用釘子只能採用榫卯結構、規定國土的三分之二作為山林保護區,規定外來遊客必須按日繳納規定的金額作為國家收入來源(用來提供不丹國民免費的醫療和教育費用)部分用途的觀光法規。
不丹的憲法著重的是永續公平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清廉良好的統治。人民對此有什麼樣的感受、幸福指數是否在下滑、什麼樣的環境能夠造就幸福感等國家設有幸福檢測機關,並且將測定的結果反應在政治上。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國家能像這樣把國人的幸福指數積極反應在政策之上?
人們之所以開始注意到不丹這個國家,一方面絕對是因為不丹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王自願放下王權導入民主主義的國家。第4代國王是傳位於現任國王之前世界上唯一自願放下所有的王權並且親自拜訪、說服人民,導入人民主導選舉的民主主義的國王。直到現在他依然是人民心目中的聖君,是世界上史無前例深受人民景仰的一位真正的領導者。
不丹最叫人好奇的莫過於是家家戶戶的屋簷或大門口會掛著男性陽具的象徵物。尤其是通往奇美拉康寺(Chimi Lhakhang,俗稱為瘋喇嘛的廟)的村落入口,沿路的牆上都畫滿了陽具的圖畫。陽具被認為是助生、祈福、趨吉避兇的吉祥物,而非一般人所認為的性象徵。見到這些陽具掛飾,有些人會直覺認為不丹是一個男性主義的社會,其實正好相反。婦女懷孕時甚至都期望懷的是女兒,不丹就是一個如此重視女性的母系社會。
以在企業和政府機關各地工作的女性員工數來說,不但人數接近男性,待遇方面也與男性相等。
相較於韓國,高學歷的單身女性因結婚或為了育兒需要放棄工作或是繼續上班、與男性相比難以升遷或是受差別待遇,不丹女性則是令人艷羨。另外,一夫多妻制與一妻多夫制的共存制度,使得不丹人的男女角色關係很不一樣。男女關係開放,婚前性關係和離婚的情形也很普遍。忠於自己的情感,不以制度來為愛情畫界線,更不會想要佔有彼此,不丹就是這樣的社會。
此外,婚後男方住進女方家是很正常的事,萬一要離婚,女方一樣比較強勢。當女方要求離婚時,男方必須無條件接受,而男方要求離婚,女方有權拒絕。雙方在協議離婚時,男方必須將一半的財產分給女方,且女方優先擁有子女的扶養權。離婚婦女多半是由娘家一起照顧子女,男方則是必須按子女人數將月薪的20%(多個子女的情況下,最多40%)交給女方作為子女的養育費。
再回頭看看韓國女性的情況,離婚後即使是獨自辛苦扶養子女,也很少會跟前夫拿贍養費。從女性的立場而言,不丹在各方面都令人十分羨慕。戀愛自由奔放,但卻也在法律上嚴格規範父母親應盡的責任。
從不丹回來之後,腦海裡一直有個想法。在不停追求個人的發展和成長之際,是否有很多重要的人事物已經被我們遺忘了呢?慢活的悠閒、對他人的友善、明朗的笑容、與大自然共存的快樂、寶貴的傳統、生活的幸福指數……。不丹,擁有我們早已失去的某樣重要的東西。我了解到一個國家抱持著明確的意識,不去瘋狂追求發展與成長,這一趟不丹之旅的體驗讓我覺得值回票價。
在首都廷布市區裡往來穿梭的公車後面可以看到這樣的標語:
「Take a ride, and be happy!」
不丹果然是地球上僅存的香格里拉(理想國)!上海是三城中最國際化的都會。任何人置身在浦東陸家嘴的金融區,放眼盡是國際500強企業的高樓大廈,很難不把它和紐約相比較。上海的白領,無論是在外資或國企上班,也不論是中國人、港台或外國人,大都有英文名字。即使是最需要向本土口味妥協的外國餐飲業,也能堅持原汁原味。上海有家法國餐廳只優先提供法文菜單,一般由點菜員口頭翻譯、解說,除非是顧客要求,否則不會主動提供英文或中文菜單。我知道的一家德國藝廊,在上海多年,一直用德文的公司名字經營,只有少數人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多數外國人在上海,就是如此賓至如歸地生活;上海人對外來的洋玩意,也見怪不怪。
上海的國際化,是直接的、徹底的、毫不本地化的。有位台商在上海經營一家複合式高檔餐廳,他自豪地說我的員工來自世界各地,紐約、莫斯科、香港、曼谷、倫敦……本地人只占少數。這家餐廳的消費者和服務人員來自世界各地,最通用的語言是英語,但無論講英語、法語、日語、俄語、甚至泰語,都有服務員能溝通,即便是台語也能通。這家餐廳的消費也很紐約,埋單時看到帳單的人民幣金額會令人心驚,只有私自在心裡換算成美元的數字才稍稍覺得釋懷些。
處處可見外國人,北京仍然很中國
在地上海人是大陸各省最喜歡出國旅遊,聚會時也愛談論國外事物,他們樂於在生活中引進外國經驗。大陸正在努力要向國際接軌,當今上海絕對是大陸最國際化的城市,也最能接受國際化的標準。
北京則是國際注目的焦點城市,長安街上不時有插著各國國旗的車隊,在前導車引領下呼嘯而過。但是,北京的國際化是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不同於上海的原汁原味。北京的外國人不少,外國使館、企業、餐廳也不少,但是仍然是很中國。
北京的外國人多半能講幾句中文,不少人有中文名字,甚至喜歡住在本地人聚集的胡同巷弄。北京酒吧的表演樂團用中國樂器演奏西方熱門音樂,外國歌手唱中國歌曲是常有的現象。可是這些外國的元素,就像沾在豬血糕表層的花生粉,未能真正融合進北京城的骨子裡。五星飯店大門前的交通動線,是典型的北京特色。飯店正門緊鄰大馬路的車道,平時用活動柵欄隔離,所有車子均須繞行到側門,再迴轉到飯店大廳正門。只有領導車子蒞臨時,才撤除柵欄空出直通正門的車道。不只是交通有中國特色,事無大小,幾乎任何事都有其獨有特色。套句老外在北京發牢騷時的慣用語:「TIC」(This is China)!因為這是中國,北京是所謂的「帝都」,自有其中國特色的標準。
去政治化,台北樂活
台北沒有上海的國際化,也沒有北京的中國化。台北是怎樣的城市呢?
某位常與我討論台灣電視政論節目的北京學者,首次來台旅遊,驚訝地發現「去政治化的台北」。他發現,台北人為小吃排隊,搭捷運去泡湯,電視名嘴聲嘶力竭的控訴,似乎離一般人很遙遠。兩位偕伴來台北旅遊的上海白領,愛上台北茶館、咖啡館的閒淡氛圍,這是「向錢衝」的上海無法想像的生活。
開放大陸自由行後,為接待來台的大陸友人,我在台北的時間越來越長,也越來越能感受到樂活的台北生活。或許台北的日常生活,太平常、太一般,不容易有感;上海的國際化,北京的中國化,反而凸顯了台北的生活化。最終台北人,要遠從對岸的上海、北京,才看見樂活的台北。
空間不是距離,時間留下回憶。我在三城間的移動,離家就是回家,回家就是歸人!何處是家?有人等待就是家。所以,最後也要提醒三城的朋友們,如果讀到這篇文章,下次替我接風時不要問我:「待多久?」當我離去時,你的一句「什麼時候回來?」就是最好的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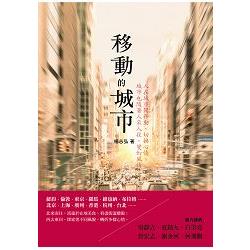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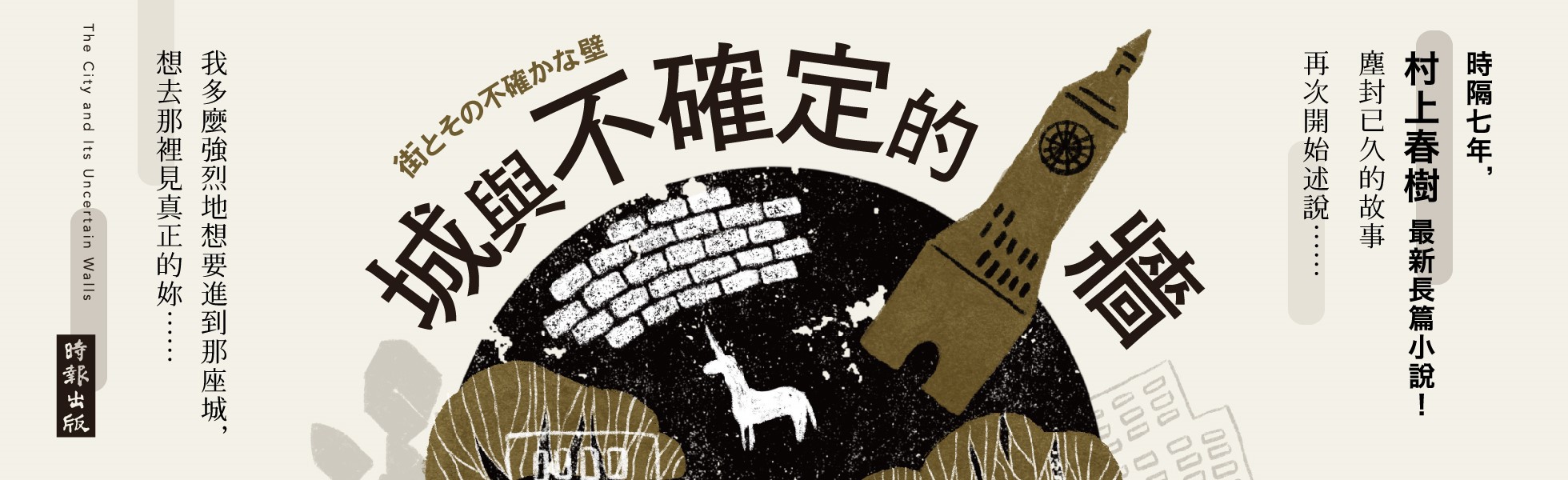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