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王朝 第七部 淬鏡 (下)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教訓了姜家堡一眾愚昧之人,
儘管眼前還有白家一關要過,
已是互訴衷腸的冷寧芳與孫副官,
決定攜手一起走下去。
然而要過白家大關的,
卻不只這一對。
歷經路途辛苦,
宣懷風跟著白雪嵐,
終是踏進了白府大宅。
而相較起沿路上剽悍的匪徒,
眼前的白家三太太,
竟是更讓宣懷風感到戰戰兢兢。
深知那人不惜一切也要護住他的脾性,
宣懷風知道他得先穩住自己。
唯有如此,在這風雨前夕的白府,
他與白雪嵐才能,並肩齊行。
試閱
第四十二章
宣懷風回到房裡,見宋壬帶著兩個護兵正提著裝衣服的行李箱子出去,卻不知白雪嵐去了哪裡。便問宋壬。
宋壬也正打算和宣懷風說一件事,叫護兵先把東西搬出去,自己留下來答說,「總長到酒窖裡去了。說這窮地方,別的好東西想必沒有,陳年老酒也許藏著幾罈。宣副官,您不知道,鄉下古法釀的老酒,藏在土窖裡幾十年,一打開封蓋,那個香啊。」
一邊說,一邊便像勾起了饞蟲一樣,嚥了一口口水。
宣懷風低頭想了想,歎道,「找酒就找酒罷,只別一時使起性子,把人家的酒窖給砸了。」
不料宋壬這粗獷的山東漢子,也有心細的時候,竟聽出一點意思來,便問,「怎麼?您和總長吵嘴了?」
自己和宣懷風夜裡的事情,宣懷風哪能拿來和宋壬講,微微笑道,「並沒有吵嘴那樣嚴重。不過是今天早上,我為那位老太太順口說了兩句好話,不合他的意思。恐怕他臨走前要去找姜家堡一個麻煩。等他回來,要是心裡的氣還沒有平,大概究竟還是要來找我的麻煩。」
宋壬咧嘴笑道,「宣副官,你們這些喝過洋墨水的,肚子裡彎彎就是多。照我說呢,總長對上您,就是一頭強騾子,心裡再大的氣,只要您順著毛,捋一捋,也就樂乎起來了。天底下,一物降一物,您說,是不是這道理。」
宣懷風被逗樂了,「怪不得總長抱怨,說你們這些人去了首都後,都不學好了。當著他的面老實,背著他,敢把他比作騾子。你不怕他拿鞭子抽你?」
宋壬把胸膛拍得砰地一響,「跟著總長辦事的人,還挨不起那幾鞭子嗎?我也不是傻子,這些話只在宣副官跟前說。您我是知道的,從不在總長面前嚼舌頭。」
說完,左右看看,把聲音壓低著說,「宣副官,我想求您一件事。」
宣懷風說,「我就說,你不去忙你的,站這和我說閒話,該是有些古怪。什麼事?你說來聽聽。」
宋壬那蒲扇般的大手,在剃得短短的半寸頭髮上,難為情地摸來摸去,「宣副官,這不是快到總長老家了?總長的老家,離我老家也不多大遠。」
宣懷風說,「我知道了。你記掛著媳婦孩子,想請幾天假回家裡看看,是不是?」
宋壬說,「也是,也不是。我若只是請幾天假,總長總不會不答允,又何必勞動您?」
宣懷風看他張手張腳地站著,很不得自在的樣子,打個手勢,請他在自己對面的椅子坐下,溫和地說,「看你這樣,是打算談一件正經事?恕我直言,你這樣大漢子,很不適合繞彎彎說話,這也是也不是,聽得我難受呢。還是請你直腸直肚地說。不管什麼事,我要是能辦,一定幫你辦了。要是不能辦,我也告訴你為何不能辦,這樣豈不是大家都痛快?」
宋壬得到他的鼓勵,果然痛快起來,竹筒倒豆子一般,「宣副官,也是這幾日看著姜家堡遇土匪,才興起來的想頭。我本想著,婆娘帶著幾個毛孩子在老家,等著我寄餉銀回家養活,他們吃的吃,穿的穿,日子很不錯了。可是您瞧瞧,這次回來,世道更亂了。姜家堡有著許多堡丁,還有許多火槍,都要受土匪的禍害,別的鄉下村子又如何?要是來了土匪,家裡男人不在,女人孩子怎麼處?一想起這個,我夜裡就睡不著。我總想,要去央求總長,讓他答允我把婆娘孩子接到城裡來才好。」
宣懷風說,「原來如此。可你開始為什麼作出那鬼鬼祟祟怕人知道的樣子?想老婆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並沒有不可見人之處。如今社會進步了,以後再有這種想法,你大大方方地直說就是。」
宋壬牛高馬大的,竟也有皮不厚的時候,一張大臉紅脹起來,晃著腦袋解釋,「實在沒想婆娘,要說想,也就是想幾個毛孩子。」
宣懷風笑道,「是的,是的,我說錯了。你只想這幾個,沒想那一個。」
又爽快地說,「只管安心。你這個事,我和總長說。其實,我也就奇怪,你跟著總長,每個月的餉銀加上額外賞錢,總該是不差的。既然不缺錢,把家裡人接到城裡,只管租個地方住下來就是,怎麼還非要經總長同意呢?」
宋壬嘖嘖搖頭,「您是住在天宮裡的人,不知道老百姓的門道。如今別說首都,就算濟南城,也開始實行那勞什子良民管理了。鄉下人到城裡,總要每人辦理一張良民證,若是辦不來這張證,就是流民,在街上讓巡警看見,問你要良民證,你要是拿不出來,是要馬上被警棍打一頓,趕出城去的,或者你拿幾個錢給巡警,他就饒過你。如今逃荒入城的人太多,那良民證就金貴了,尋常人花上許多錢,也未必辦得來。但要在總長那裡,也就是一句話的事。」
宣懷風大為驚訝,「我從前剛到首都,也拿過一張良民證。可我在路上,從沒有被巡警攔住問話,沒有用它的時候,總覺得拿著不過廢紙一張罷了。原來它不大好弄嗎?」
宋壬打量宣懷風兩眼,嘿笑道,「巡警也長眼睛,您這樣的人,穿著洋裝在大街上一站,誰會來對你檢查?這張廢紙用處大著呢,但凡任職、讀書,都要憑著良民證辦手續,連娶個老婆,也必須拿著良民證,才能在城裡辦下一張結婚證明。就拿您來說,您到海關衙門當差,難道不用辦手續?其實一定有辦的,只不過不用您親自去,總長色色都給您安排好了,吩咐了底下人跑腿。那首都的良民證,當初恐怕不是您自己去辦的,否則,絕不會說出這樣輕易的話。」
宣懷風便沉默了。
當日從英國匆匆趕回奔父喪,被姨娘奪去所剩不多的家業,只好再從廣州轉赴首都。兩袖空空,千里奔波,直到和姐姐見了面,才吃了一顆定心丸。
住處、穿著、飲食……處處都是姐姐使了勁的花錢張羅,無一處不周到。
那張良民證,自然也是姐姐給他辦了來,輕鬆交到他手上,其中有什麼周折難處,竟是一個字也沒透露。
宣懷風想著他姐姐,往日那般關懷厚愛,如今又是另一番不堪景象,眼角怔怔地一陣微熱,忙裝做眼裡進了灰塵,用指頭輕輕揉了兩下,對宋壬淡笑著說,「我總以為你只知道打槍,不懂這些衙門裡的事。沒想到你竟是個行家。」
宋壬忙說,「哪的事。我和戴小姐閒話,一個不妨頭,讓她知道了我把婆娘孩子帶到城裡的打算。戴小姐就提醒了我。她真是個好人,知道我不懂這些道道,很仔細地和我說了半日。她說,我閨女還小,可我那三個毛崽子,也該學幾個字了。如今不興私塾,都興送到學校去識字。要進城裡的學校,也一定要良民證的。其實,戴小姐也說了,她那學校收學生倒很鬆動,不指著要這要那。但我辛辛苦苦想把家裡人帶到城裡,就是想早晚見一見孩子,寧願多花幾個錢,在城裡正經學校讀書,不要到城外老遠……」
還沒說完,就聽見樓下響亮的哨子聲。
又有人在大聲吆喝,「到點了!」
宋壬哎呦一聲,彈簧似的從椅上起來,「都怪我,一說起那幾個毛崽子就忘了點。宣副官,路上風大,您加一件披風才好下樓。」
宣懷風攤開兩手問,「你不是叫人把箱子都拿走了嗎?這時候我到哪變出一件披風來?」
宋壬一拍腦袋,「果然不錯,怎麼倒忘了這個。我叫他們再把箱子拎上來。」
宣懷風攔著說,「上上下下的瞎忙什麼?到路上覺得冷了再說。快走罷,不然,有人要生氣了。」
這時行李早叫護兵拿了去,宣懷風便兩手空空地和宋壬一起走出房間。
下樓到了院子裡,藍鬍子早把人召集齊全,都在等著。
白雪嵐也不知何時從酒窖裡回了來,卻站在院裡,沒上樓回房,存心要看宣懷風著急不著急。
等了半日,才見宣懷風從樓梯下來,竟是半點也不著急,一邊走,一邊和宋壬說說笑笑。
白雪嵐心裡更為憋悶,等宣懷風到了面前,也不和宣懷風說話,轉過頭,喝著底下人說,「斷了手嗎?還不牽馬來?就為你磨磨蹭蹭,耽擱了上路!」
宣懷風本想和他先說一句軟和話,聽這不好的聲息,不由生出一分氣來,便也不和白雪嵐說話,抬起頭,只裝做很悠閒地看天色。
不多時,兩個騎兵牽了兩匹馬來。
其中一匹,自然是白雪嵐專騎的白將軍。
宣懷風接了騎兵送上的韁繩,對著自己的坐騎仔細看了兩眼,問那騎兵說,「怎麼我看這一匹,不像我昨天騎的?昨天那匹就好,還是照舊給我牽過來罷。」
那年輕騎兵臉上的笑容,像有些躲閃,又不馬上答應下來。
宣懷風正覺得奇怪,藍大鬍子大步地走過來,順手就拿著馬鞭,往騎兵背上刷地抽了一下。
第四十三章
宣懷風見他這樣凶狠,正在吃驚,藍大鬍子卻已把臉轉過來對著他,換了笑容,對他解釋說,「都是這蠢東西,沒有一點記性。早提醒過,軍長的白將軍絕不能和別的馬同槽,他昨晚倒把宣副官你騎的馬和白將軍栓了一處。大半夜的,聽見馬叫喚得厲害,過去一看,已經讓白將軍把後腿給咬出血了。那一匹是沒法子騎了,您今天將就一下,換這一匹罷。」
宣懷風這才明白事由,不由轉頭去看旁邊那匹白將軍。
那白將軍體態矯健,兩眼黑亮,脖子高昂著,彷彿總有一種瞧不起人似的驕傲神情,倒很像他熟悉的那個人。
宣懷風笑道,「原來這馬裡頭,也有這麼橫行霸道的。同一個槽,就要把人家咬傷了去,你也太蠻橫了些……」
他心裡其實是喜愛這匹神駿馬兒的,一邊說話,一邊伸過手去,想撫牠漂亮的鬃毛。
白將軍天生的性子暴戾,又因為是白雪嵐的坐騎,早被嬌縱壞了,陡然見一個陌生人敢伸手過來,扭過脖子來,不聲不響地張開牙口。
白雪嵐見宣懷風和騎兵說話,和藍大鬍子說話,甚至和一匹馬說話,偏自己就像不存在似的,偏偏故意地不和自己說話,心裡正生氣。他是馬主人,見白將軍忽然低頭,哪能不知道這畜生要幹什麼,嚇得一個箭步竄上來,啪地一下,把宣懷風的手猛打下去,對宣懷風吼道,「吃了豹子膽!這是你能碰的?」
急切之下,這一吼,是十分用力的,扯得脖子上青筋都起來了。
偌大的院子,頓時一片寂靜。
白雪嵐心裡也咯?一下。
剛才打得宣懷風手背啪地一聲脆響,他已知打重了,再一吼,發覺院中死寂一般,人人都偷瞧著自己,又知吼得急了。
心裡越在意,越是沒了平日的從容,見宣懷風怔怔地瞅著自己,白雪嵐一時心也亂了,臉上卻還是擺著一副生氣的表情。
若在平時,總有一個伶俐的孫副官,來給二人打圓場,偏生孫副官因為受傷,早被安排坐了大篷車。那十幾輛大篷車因為不方便,不曾停到院裡來,因而此時,孫副官也不在跟前。
白雪嵐積威深重,他僵在那裡,別人哪裡敢說話。
宣懷風窘迫得俊臉通紅,但心知這樣下去,場面越發要不好看了,因此反而強擠出一個淡笑來,「總長說的是。總長的坐騎,我以後不碰就是。」
說罷,回過頭去,對藍大鬍子說,「我就騎這一匹罷。」
翻身上了馬。
白雪嵐還只管站著,宋壬上前試探著問,「總長,該出發了?」
白雪嵐彷彿回過神來,才喝了一聲,「出發。」
也騎上白將軍,領著眾人上路。
這次上路和昨日大有不同,走的不再是狹窄的側門,而是正經大門。何況那種被帶著雙二十響的殼子槍的騎兵們前呼後擁的氣勢,是特別的威嚴懾人。
姜家堡的人早被嚇破了膽,縮頭縮腦地藏在牆後,眼瞅著閻王似的白十三少去得遠了,騎著高頭大馬的身影消失在山林深處,才趕緊把敞開的大門關上,自去哭天搶地,悲悼哀哭。
離了姜家堡,白雪嵐帶著自己親手調教的這支虎狼近衛營,看似威風凜凜,踏雪而去,其實滿心裡不是滋味,彷彿腸子被扯著似的,一路上,常常拿眼角偷瞥宣懷風的所在,唯恐宣懷風騎著馬,不聲響地離了自己。
宣懷風面上倒很平靜,策馬總在白雪嵐右邊,偶然慢一點,落下白雪嵐七、八步,白雪嵐必慢下來,磨蹭到宣懷風馬匹跟上了才走。
如此拖拖拉拉,雖是人強馬壯的猛虎之師,大半個上午的時光,竟只走了一小段山路。老天爺似乎也生起氣來,早上還露著晴臉,到了中午,漸漸的烏雲堆積起來,有再來一場雪的意味。
冷寧芳在大篷車裡坐得氣悶,掀開簾子透氣,被冷風吹得頓時打了一個哆嗦,這才知道天要變了。
再一看前面,宣懷風和眾人一樣,騎著馬上趕路。
冷寧芳忙叫著白雪嵐說,「十三弟,這樣刺骨的風,你怎麼還讓宣副官騎馬?眼見著要下雪了,快到車上來罷。」
白雪嵐早想招呼宣懷風,只是見宣懷風騎著馬目不斜視的模樣,竟是很心虛,三番兩次地開不了口。這時巴不得冷寧芳一句,直如領了太后的懿旨一般,趕緊應道,「姐姐教訓得很是。」
冷寧芳還不曾見過他這樣恭順的態度,還在發怔。
白雪嵐哪理會冷寧芳想什麼,揮手叫停隊伍,跳下馬,給宣懷風牽著韁繩,用很尋常的口氣說,「你也聽見姐姐的話了。這樣的天,不好騎馬,到車裡去罷。」
回頭吩咐藍大鬍子,「給我預備的車呢?快拉過來。」
不一會,便有護兵吆喝著,駕了一輛馬車過來。
白雪嵐在地上站著,抬著頭,伸著手,擺出一個要扶宣懷風下馬的姿勢。心裡琢磨著,宣懷風大概是要對自己耍一下性子的。
不料,宣懷風臉色雖是淡淡的,眼神也不肯和他對上,但在身體上,卻順應著白雪嵐的動作,安靜地下了馬,跟著白雪嵐上馬車。
那馬車的簾子是羊毛製的,十分厚重擋風,人到了裡面,立即和風雪隔開了,彷彿到了一個極安靜的小世界裡。
白雪嵐見宣懷風肯跟自己上車,宛如中了巨獎一般,到了車廂裡,便一伸手把宣懷風抱住了。
宣懷風見此處沒有外人,才做出不配合的態度來,拿右手的肘部向後搡他,冷冷地說,「這有什麼意思?請你離遠些。」
白雪嵐越發抱得緊了,耍起很擅長的無賴伎倆來,反問他說,「要我離遠些,剛才你怎麼又跟我來?」
宣懷風說,「你是我的上司,當著眾人,不得不照顧你的面子。到了這裡,你再胡攪蠻纏,就是欺負人了。」
白雪嵐只怕宣懷風不和自己說話,既然肯說話,那總是一件叫人高興的事,因此他竟把一路上的心虛忐忑,都放到了一邊,仗著自己力氣大,宣懷風再也掙脫不過的,嘴唇只在他臉頰、脖子上混親混蹭,柔聲央道,「是我的錯。我真該死,也不欺負別個,只欺負你了。親親,別生氣,我給你賠罪,好不好?」
見宣懷風不答話,便抓著宣懷風的手背,再三給他揉,嘴裡不住地說,「疼不疼?我打重了,真不是故意的。我見白將軍要咬你,我才急的。」
宣懷風掙了幾次,越發讓他八爪魚一般纏得緊了,脹紅了臉罵道,「白雪嵐,你還要不要臉?」
白雪嵐想也不想地說,「要臉做何用?我為了你,連命都不要,更不要臉。」
宣懷風心忖,自己吃他這無賴的虧,總不能吃一輩子,便一低頭,發狠地咬在白雪嵐手腕上。
白雪嵐反而叫好,笑著說,「只管咬,咬下一塊肉來,你吃了去,這就是你中有我了。」
宣懷風只以為咬得疼了,他總要縮回手去的,自己得了脫身,就趕緊下車,避到外頭去。
沒想到狠咬了一氣,白雪嵐仍抱得死牢,手勁一點沒有鬆動。
反而是嘴裡,似乎嘗到淡淡腥味。
宣懷風心頭一驚,不要真咬出血來了?趕緊鬆口去看。
果然,手腕上一圈齒印裡,隱隱地滲出鮮紅顏色。宣懷風看著那沁出來的一滴血珠,不知什麼滋味。再要繼續咬,是絕不忍心了,可若要幫他拭傷止血,又十分地不服氣。
原本一肚子氣,讓白雪嵐耍無賴地一番水磨,竟是只能憋著。
宣懷風不由灰了心,也不掙扎了,由白雪嵐兩根胳膊,宛如牢籠似的圈著。
半晌,歎了一口氣說,「你放手,好不好?」
白雪嵐說,「當然是不好。」
宣懷風說,「我也不到別處去,你放開我,我們面對面的談一談,也不成嗎?若連這也不成,那以後,也不要再想我和你說什麼話了。」
白雪嵐聽他的語氣,是很認真的,不敢再嬉笑敷衍,只好鬆了手,在他面前盤膝坐了,擺出一個面談的姿態,搶先說,「先前是我太急切。白將軍那嘴利牙,一口下去,能把你手指咬斷兩、三根。因此我才失了態,並不是存心當著眾人的面,讓你下不了臺。有一個字撒謊,叫我天打雷劈。」
舉起兩根手指,做個很鄭重的發誓。
宣懷風說,「白將軍碰不得,你說是為著我考量,我姑且表示理解。可今天早上,無端無故的,你十分不待見我,又作何解釋?」
白雪嵐說,「何曾不待見,我也只是向你做一番抗議罷了。」
宣懷風問,「抗議什麼?」
白雪嵐反問,「你答應了的事,不肯兌現,讓我活活吃個啞巴虧。」
宣懷風問,「把話說明白了,我答應了你什麼不肯兌現?」
白雪嵐很不含糊,就問他,「孫副官挨打那一天的事,你還記得不記得?」
宣懷風說,「這才多久前的事,當然記得。」
白雪嵐說,「你既然記得,那就能做個對證了。那天晚上,我們在床上,你不讓我近身。我和你打商量,說你狠著心將我餓一個晚上,到了時候,我要補償回來。你滿口答應,有沒有這回事?」
宣懷風不由回想,那天晚上自己迷迷糊糊,似乎是曾聽過這麼一句,這是不好否認的,只好說,「當時我睏得緊,究竟怎麼答應你的,實在記不清了。可就算我答應過什麼,也不過昨夜睡得早,把你這不正經的賠償,再拖欠一個晚上罷了,為什麼要生我這樣大的氣?」
白雪嵐訕訕道,「哪裡生老大的氣了?也就早上一個小小的起床氣,對你冷淡些,沒往日那樣殷勤罷了。」
宣懷風搖頭說,「我不信,一定還有什麼,你瞞著不肯說。再不說實話,我就下去了。」
說著就要起身,到車外頭去。
白雪嵐連忙一伸手,把他擒羊似的擒住了,順勢一扳,兩人摟做一團,歪倒在車廂裡鋪著的厚厚的褥子上。
白雪嵐咬著宣懷風耳朵,低聲說,「要我說實話也行,可你先做個承諾,不拿這事笑話人。」
宣懷風聽他這樣遮遮掩掩,倒生出好奇心來,痛快地說,「好,我做一個承諾。你快說出來。」
白雪嵐說,「這要怪張大勝。」
宣懷風說,「這就奇了,我們的事,如何扯到他身上去?」
白雪嵐說,「我昨日,不是叫他給你打野味?這滿山都是肥?子的地方,就他憨,沒打著?子,偏拖了一頭野鹿回來。野鹿也罷了,叫他宰了給你烤著做宵夜,他又跑來問我,那老大的一根鹿鞭……」
宣懷風被白雪嵐無法無天地混鬧了一、兩年,也不是當初那個清純簡單的留洋學子了,至此便明白幾分,臉頰微熱,截住白雪嵐的話道,「快住嘴。打個野味也能扯到這上頭,這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虧你這個做總長的,還有臉怪手下人。」
又不禁好奇起來,低聲問,「那個東西,你難道就真的吃了?何必去吃那種古怪東西,你平日就很……」
說到一半,忽然就剎住了。
白雪嵐被他這只說了一半的話,撩撥得心窩發癢,慢慢地壓上身體的重量來,一下一下地擠著他問,「我平日就很如何?就很讓你吃不消,是不是?」
宣懷風哪有臉回答這樣下流的問題,被白雪嵐邪氣地擠迫著,便蜷起身體,儘管避讓著。
宣懷風回到房裡,見宋壬帶著兩個護兵正提著裝衣服的行李箱子出去,卻不知白雪嵐去了哪裡。便問宋壬。
宋壬也正打算和宣懷風說一件事,叫護兵先把東西搬出去,自己留下來答說,「總長到酒窖裡去了。說這窮地方,別的好東西想必沒有,陳年老酒也許藏著幾罈。宣副官,您不知道,鄉下古法釀的老酒,藏在土窖裡幾十年,一打開封蓋,那個香啊。」
一邊說,一邊便像勾起了饞蟲一樣,嚥了一口口水。
宣懷風低頭想了想,歎道,「找酒就找酒罷,只別一時使起性子,把人家的酒窖給砸了。」
不料宋壬這粗獷的山東漢子,也有心細的時候,竟聽出一點意思來,便問,「怎麼?您和總長吵嘴了?」
自己和宣懷風夜裡的事情,宣懷風哪能拿來和宋壬講,微微笑道,「並沒有吵嘴那樣嚴重。不過是今天早上,我為那位老太太順口說了兩句好話,不合他的意思。恐怕他臨走前要去找姜家堡一個麻煩。等他回來,要是心裡的氣還沒有平,大概究竟還是要來找我的麻煩。」
宋壬咧嘴笑道,「宣副官,你們這些喝過洋墨水的,肚子裡彎彎就是多。照我說呢,總長對上您,就是一頭強騾子,心裡再大的氣,只要您順著毛,捋一捋,也就樂乎起來了。天底下,一物降一物,您說,是不是這道理。」
宣懷風被逗樂了,「怪不得總長抱怨,說你們這些人去了首都後,都不學好了。當著他的面老實,背著他,敢把他比作騾子。你不怕他拿鞭子抽你?」
宋壬把胸膛拍得砰地一響,「跟著總長辦事的人,還挨不起那幾鞭子嗎?我也不是傻子,這些話只在宣副官跟前說。您我是知道的,從不在總長面前嚼舌頭。」
說完,左右看看,把聲音壓低著說,「宣副官,我想求您一件事。」
宣懷風說,「我就說,你不去忙你的,站這和我說閒話,該是有些古怪。什麼事?你說來聽聽。」
宋壬那蒲扇般的大手,在剃得短短的半寸頭髮上,難為情地摸來摸去,「宣副官,這不是快到總長老家了?總長的老家,離我老家也不多大遠。」
宣懷風說,「我知道了。你記掛著媳婦孩子,想請幾天假回家裡看看,是不是?」
宋壬說,「也是,也不是。我若只是請幾天假,總長總不會不答允,又何必勞動您?」
宣懷風看他張手張腳地站著,很不得自在的樣子,打個手勢,請他在自己對面的椅子坐下,溫和地說,「看你這樣,是打算談一件正經事?恕我直言,你這樣大漢子,很不適合繞彎彎說話,這也是也不是,聽得我難受呢。還是請你直腸直肚地說。不管什麼事,我要是能辦,一定幫你辦了。要是不能辦,我也告訴你為何不能辦,這樣豈不是大家都痛快?」
宋壬得到他的鼓勵,果然痛快起來,竹筒倒豆子一般,「宣副官,也是這幾日看著姜家堡遇土匪,才興起來的想頭。我本想著,婆娘帶著幾個毛孩子在老家,等著我寄餉銀回家養活,他們吃的吃,穿的穿,日子很不錯了。可是您瞧瞧,這次回來,世道更亂了。姜家堡有著許多堡丁,還有許多火槍,都要受土匪的禍害,別的鄉下村子又如何?要是來了土匪,家裡男人不在,女人孩子怎麼處?一想起這個,我夜裡就睡不著。我總想,要去央求總長,讓他答允我把婆娘孩子接到城裡來才好。」
宣懷風說,「原來如此。可你開始為什麼作出那鬼鬼祟祟怕人知道的樣子?想老婆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並沒有不可見人之處。如今社會進步了,以後再有這種想法,你大大方方地直說就是。」
宋壬牛高馬大的,竟也有皮不厚的時候,一張大臉紅脹起來,晃著腦袋解釋,「實在沒想婆娘,要說想,也就是想幾個毛孩子。」
宣懷風笑道,「是的,是的,我說錯了。你只想這幾個,沒想那一個。」
又爽快地說,「只管安心。你這個事,我和總長說。其實,我也就奇怪,你跟著總長,每個月的餉銀加上額外賞錢,總該是不差的。既然不缺錢,把家裡人接到城裡,只管租個地方住下來就是,怎麼還非要經總長同意呢?」
宋壬嘖嘖搖頭,「您是住在天宮裡的人,不知道老百姓的門道。如今別說首都,就算濟南城,也開始實行那勞什子良民管理了。鄉下人到城裡,總要每人辦理一張良民證,若是辦不來這張證,就是流民,在街上讓巡警看見,問你要良民證,你要是拿不出來,是要馬上被警棍打一頓,趕出城去的,或者你拿幾個錢給巡警,他就饒過你。如今逃荒入城的人太多,那良民證就金貴了,尋常人花上許多錢,也未必辦得來。但要在總長那裡,也就是一句話的事。」
宣懷風大為驚訝,「我從前剛到首都,也拿過一張良民證。可我在路上,從沒有被巡警攔住問話,沒有用它的時候,總覺得拿著不過廢紙一張罷了。原來它不大好弄嗎?」
宋壬打量宣懷風兩眼,嘿笑道,「巡警也長眼睛,您這樣的人,穿著洋裝在大街上一站,誰會來對你檢查?這張廢紙用處大著呢,但凡任職、讀書,都要憑著良民證辦手續,連娶個老婆,也必須拿著良民證,才能在城裡辦下一張結婚證明。就拿您來說,您到海關衙門當差,難道不用辦手續?其實一定有辦的,只不過不用您親自去,總長色色都給您安排好了,吩咐了底下人跑腿。那首都的良民證,當初恐怕不是您自己去辦的,否則,絕不會說出這樣輕易的話。」
宣懷風便沉默了。
當日從英國匆匆趕回奔父喪,被姨娘奪去所剩不多的家業,只好再從廣州轉赴首都。兩袖空空,千里奔波,直到和姐姐見了面,才吃了一顆定心丸。
住處、穿著、飲食……處處都是姐姐使了勁的花錢張羅,無一處不周到。
那張良民證,自然也是姐姐給他辦了來,輕鬆交到他手上,其中有什麼周折難處,竟是一個字也沒透露。
宣懷風想著他姐姐,往日那般關懷厚愛,如今又是另一番不堪景象,眼角怔怔地一陣微熱,忙裝做眼裡進了灰塵,用指頭輕輕揉了兩下,對宋壬淡笑著說,「我總以為你只知道打槍,不懂這些衙門裡的事。沒想到你竟是個行家。」
宋壬忙說,「哪的事。我和戴小姐閒話,一個不妨頭,讓她知道了我把婆娘孩子帶到城裡的打算。戴小姐就提醒了我。她真是個好人,知道我不懂這些道道,很仔細地和我說了半日。她說,我閨女還小,可我那三個毛崽子,也該學幾個字了。如今不興私塾,都興送到學校去識字。要進城裡的學校,也一定要良民證的。其實,戴小姐也說了,她那學校收學生倒很鬆動,不指著要這要那。但我辛辛苦苦想把家裡人帶到城裡,就是想早晚見一見孩子,寧願多花幾個錢,在城裡正經學校讀書,不要到城外老遠……」
還沒說完,就聽見樓下響亮的哨子聲。
又有人在大聲吆喝,「到點了!」
宋壬哎呦一聲,彈簧似的從椅上起來,「都怪我,一說起那幾個毛崽子就忘了點。宣副官,路上風大,您加一件披風才好下樓。」
宣懷風攤開兩手問,「你不是叫人把箱子都拿走了嗎?這時候我到哪變出一件披風來?」
宋壬一拍腦袋,「果然不錯,怎麼倒忘了這個。我叫他們再把箱子拎上來。」
宣懷風攔著說,「上上下下的瞎忙什麼?到路上覺得冷了再說。快走罷,不然,有人要生氣了。」
這時行李早叫護兵拿了去,宣懷風便兩手空空地和宋壬一起走出房間。
下樓到了院子裡,藍鬍子早把人召集齊全,都在等著。
白雪嵐也不知何時從酒窖裡回了來,卻站在院裡,沒上樓回房,存心要看宣懷風著急不著急。
等了半日,才見宣懷風從樓梯下來,竟是半點也不著急,一邊走,一邊和宋壬說說笑笑。
白雪嵐心裡更為憋悶,等宣懷風到了面前,也不和宣懷風說話,轉過頭,喝著底下人說,「斷了手嗎?還不牽馬來?就為你磨磨蹭蹭,耽擱了上路!」
宣懷風本想和他先說一句軟和話,聽這不好的聲息,不由生出一分氣來,便也不和白雪嵐說話,抬起頭,只裝做很悠閒地看天色。
不多時,兩個騎兵牽了兩匹馬來。
其中一匹,自然是白雪嵐專騎的白將軍。
宣懷風接了騎兵送上的韁繩,對著自己的坐騎仔細看了兩眼,問那騎兵說,「怎麼我看這一匹,不像我昨天騎的?昨天那匹就好,還是照舊給我牽過來罷。」
那年輕騎兵臉上的笑容,像有些躲閃,又不馬上答應下來。
宣懷風正覺得奇怪,藍大鬍子大步地走過來,順手就拿著馬鞭,往騎兵背上刷地抽了一下。
第四十三章
宣懷風見他這樣凶狠,正在吃驚,藍大鬍子卻已把臉轉過來對著他,換了笑容,對他解釋說,「都是這蠢東西,沒有一點記性。早提醒過,軍長的白將軍絕不能和別的馬同槽,他昨晚倒把宣副官你騎的馬和白將軍栓了一處。大半夜的,聽見馬叫喚得厲害,過去一看,已經讓白將軍把後腿給咬出血了。那一匹是沒法子騎了,您今天將就一下,換這一匹罷。」
宣懷風這才明白事由,不由轉頭去看旁邊那匹白將軍。
那白將軍體態矯健,兩眼黑亮,脖子高昂著,彷彿總有一種瞧不起人似的驕傲神情,倒很像他熟悉的那個人。
宣懷風笑道,「原來這馬裡頭,也有這麼橫行霸道的。同一個槽,就要把人家咬傷了去,你也太蠻橫了些……」
他心裡其實是喜愛這匹神駿馬兒的,一邊說話,一邊伸過手去,想撫牠漂亮的鬃毛。
白將軍天生的性子暴戾,又因為是白雪嵐的坐騎,早被嬌縱壞了,陡然見一個陌生人敢伸手過來,扭過脖子來,不聲不響地張開牙口。
白雪嵐見宣懷風和騎兵說話,和藍大鬍子說話,甚至和一匹馬說話,偏自己就像不存在似的,偏偏故意地不和自己說話,心裡正生氣。他是馬主人,見白將軍忽然低頭,哪能不知道這畜生要幹什麼,嚇得一個箭步竄上來,啪地一下,把宣懷風的手猛打下去,對宣懷風吼道,「吃了豹子膽!這是你能碰的?」
急切之下,這一吼,是十分用力的,扯得脖子上青筋都起來了。
偌大的院子,頓時一片寂靜。
白雪嵐心裡也咯?一下。
剛才打得宣懷風手背啪地一聲脆響,他已知打重了,再一吼,發覺院中死寂一般,人人都偷瞧著自己,又知吼得急了。
心裡越在意,越是沒了平日的從容,見宣懷風怔怔地瞅著自己,白雪嵐一時心也亂了,臉上卻還是擺著一副生氣的表情。
若在平時,總有一個伶俐的孫副官,來給二人打圓場,偏生孫副官因為受傷,早被安排坐了大篷車。那十幾輛大篷車因為不方便,不曾停到院裡來,因而此時,孫副官也不在跟前。
白雪嵐積威深重,他僵在那裡,別人哪裡敢說話。
宣懷風窘迫得俊臉通紅,但心知這樣下去,場面越發要不好看了,因此反而強擠出一個淡笑來,「總長說的是。總長的坐騎,我以後不碰就是。」
說罷,回過頭去,對藍大鬍子說,「我就騎這一匹罷。」
翻身上了馬。
白雪嵐還只管站著,宋壬上前試探著問,「總長,該出發了?」
白雪嵐彷彿回過神來,才喝了一聲,「出發。」
也騎上白將軍,領著眾人上路。
這次上路和昨日大有不同,走的不再是狹窄的側門,而是正經大門。何況那種被帶著雙二十響的殼子槍的騎兵們前呼後擁的氣勢,是特別的威嚴懾人。
姜家堡的人早被嚇破了膽,縮頭縮腦地藏在牆後,眼瞅著閻王似的白十三少去得遠了,騎著高頭大馬的身影消失在山林深處,才趕緊把敞開的大門關上,自去哭天搶地,悲悼哀哭。
離了姜家堡,白雪嵐帶著自己親手調教的這支虎狼近衛營,看似威風凜凜,踏雪而去,其實滿心裡不是滋味,彷彿腸子被扯著似的,一路上,常常拿眼角偷瞥宣懷風的所在,唯恐宣懷風騎著馬,不聲響地離了自己。
宣懷風面上倒很平靜,策馬總在白雪嵐右邊,偶然慢一點,落下白雪嵐七、八步,白雪嵐必慢下來,磨蹭到宣懷風馬匹跟上了才走。
如此拖拖拉拉,雖是人強馬壯的猛虎之師,大半個上午的時光,竟只走了一小段山路。老天爺似乎也生起氣來,早上還露著晴臉,到了中午,漸漸的烏雲堆積起來,有再來一場雪的意味。
冷寧芳在大篷車裡坐得氣悶,掀開簾子透氣,被冷風吹得頓時打了一個哆嗦,這才知道天要變了。
再一看前面,宣懷風和眾人一樣,騎著馬上趕路。
冷寧芳忙叫著白雪嵐說,「十三弟,這樣刺骨的風,你怎麼還讓宣副官騎馬?眼見著要下雪了,快到車上來罷。」
白雪嵐早想招呼宣懷風,只是見宣懷風騎著馬目不斜視的模樣,竟是很心虛,三番兩次地開不了口。這時巴不得冷寧芳一句,直如領了太后的懿旨一般,趕緊應道,「姐姐教訓得很是。」
冷寧芳還不曾見過他這樣恭順的態度,還在發怔。
白雪嵐哪理會冷寧芳想什麼,揮手叫停隊伍,跳下馬,給宣懷風牽著韁繩,用很尋常的口氣說,「你也聽見姐姐的話了。這樣的天,不好騎馬,到車裡去罷。」
回頭吩咐藍大鬍子,「給我預備的車呢?快拉過來。」
不一會,便有護兵吆喝著,駕了一輛馬車過來。
白雪嵐在地上站著,抬著頭,伸著手,擺出一個要扶宣懷風下馬的姿勢。心裡琢磨著,宣懷風大概是要對自己耍一下性子的。
不料,宣懷風臉色雖是淡淡的,眼神也不肯和他對上,但在身體上,卻順應著白雪嵐的動作,安靜地下了馬,跟著白雪嵐上馬車。
那馬車的簾子是羊毛製的,十分厚重擋風,人到了裡面,立即和風雪隔開了,彷彿到了一個極安靜的小世界裡。
白雪嵐見宣懷風肯跟自己上車,宛如中了巨獎一般,到了車廂裡,便一伸手把宣懷風抱住了。
宣懷風見此處沒有外人,才做出不配合的態度來,拿右手的肘部向後搡他,冷冷地說,「這有什麼意思?請你離遠些。」
白雪嵐越發抱得緊了,耍起很擅長的無賴伎倆來,反問他說,「要我離遠些,剛才你怎麼又跟我來?」
宣懷風說,「你是我的上司,當著眾人,不得不照顧你的面子。到了這裡,你再胡攪蠻纏,就是欺負人了。」
白雪嵐只怕宣懷風不和自己說話,既然肯說話,那總是一件叫人高興的事,因此他竟把一路上的心虛忐忑,都放到了一邊,仗著自己力氣大,宣懷風再也掙脫不過的,嘴唇只在他臉頰、脖子上混親混蹭,柔聲央道,「是我的錯。我真該死,也不欺負別個,只欺負你了。親親,別生氣,我給你賠罪,好不好?」
見宣懷風不答話,便抓著宣懷風的手背,再三給他揉,嘴裡不住地說,「疼不疼?我打重了,真不是故意的。我見白將軍要咬你,我才急的。」
宣懷風掙了幾次,越發讓他八爪魚一般纏得緊了,脹紅了臉罵道,「白雪嵐,你還要不要臉?」
白雪嵐想也不想地說,「要臉做何用?我為了你,連命都不要,更不要臉。」
宣懷風心忖,自己吃他這無賴的虧,總不能吃一輩子,便一低頭,發狠地咬在白雪嵐手腕上。
白雪嵐反而叫好,笑著說,「只管咬,咬下一塊肉來,你吃了去,這就是你中有我了。」
宣懷風只以為咬得疼了,他總要縮回手去的,自己得了脫身,就趕緊下車,避到外頭去。
沒想到狠咬了一氣,白雪嵐仍抱得死牢,手勁一點沒有鬆動。
反而是嘴裡,似乎嘗到淡淡腥味。
宣懷風心頭一驚,不要真咬出血來了?趕緊鬆口去看。
果然,手腕上一圈齒印裡,隱隱地滲出鮮紅顏色。宣懷風看著那沁出來的一滴血珠,不知什麼滋味。再要繼續咬,是絕不忍心了,可若要幫他拭傷止血,又十分地不服氣。
原本一肚子氣,讓白雪嵐耍無賴地一番水磨,竟是只能憋著。
宣懷風不由灰了心,也不掙扎了,由白雪嵐兩根胳膊,宛如牢籠似的圈著。
半晌,歎了一口氣說,「你放手,好不好?」
白雪嵐說,「當然是不好。」
宣懷風說,「我也不到別處去,你放開我,我們面對面的談一談,也不成嗎?若連這也不成,那以後,也不要再想我和你說什麼話了。」
白雪嵐聽他的語氣,是很認真的,不敢再嬉笑敷衍,只好鬆了手,在他面前盤膝坐了,擺出一個面談的姿態,搶先說,「先前是我太急切。白將軍那嘴利牙,一口下去,能把你手指咬斷兩、三根。因此我才失了態,並不是存心當著眾人的面,讓你下不了臺。有一個字撒謊,叫我天打雷劈。」
舉起兩根手指,做個很鄭重的發誓。
宣懷風說,「白將軍碰不得,你說是為著我考量,我姑且表示理解。可今天早上,無端無故的,你十分不待見我,又作何解釋?」
白雪嵐說,「何曾不待見,我也只是向你做一番抗議罷了。」
宣懷風問,「抗議什麼?」
白雪嵐反問,「你答應了的事,不肯兌現,讓我活活吃個啞巴虧。」
宣懷風問,「把話說明白了,我答應了你什麼不肯兌現?」
白雪嵐很不含糊,就問他,「孫副官挨打那一天的事,你還記得不記得?」
宣懷風說,「這才多久前的事,當然記得。」
白雪嵐說,「你既然記得,那就能做個對證了。那天晚上,我們在床上,你不讓我近身。我和你打商量,說你狠著心將我餓一個晚上,到了時候,我要補償回來。你滿口答應,有沒有這回事?」
宣懷風不由回想,那天晚上自己迷迷糊糊,似乎是曾聽過這麼一句,這是不好否認的,只好說,「當時我睏得緊,究竟怎麼答應你的,實在記不清了。可就算我答應過什麼,也不過昨夜睡得早,把你這不正經的賠償,再拖欠一個晚上罷了,為什麼要生我這樣大的氣?」
白雪嵐訕訕道,「哪裡生老大的氣了?也就早上一個小小的起床氣,對你冷淡些,沒往日那樣殷勤罷了。」
宣懷風搖頭說,「我不信,一定還有什麼,你瞞著不肯說。再不說實話,我就下去了。」
說著就要起身,到車外頭去。
白雪嵐連忙一伸手,把他擒羊似的擒住了,順勢一扳,兩人摟做一團,歪倒在車廂裡鋪著的厚厚的褥子上。
白雪嵐咬著宣懷風耳朵,低聲說,「要我說實話也行,可你先做個承諾,不拿這事笑話人。」
宣懷風聽他這樣遮遮掩掩,倒生出好奇心來,痛快地說,「好,我做一個承諾。你快說出來。」
白雪嵐說,「這要怪張大勝。」
宣懷風說,「這就奇了,我們的事,如何扯到他身上去?」
白雪嵐說,「我昨日,不是叫他給你打野味?這滿山都是肥?子的地方,就他憨,沒打著?子,偏拖了一頭野鹿回來。野鹿也罷了,叫他宰了給你烤著做宵夜,他又跑來問我,那老大的一根鹿鞭……」
宣懷風被白雪嵐無法無天地混鬧了一、兩年,也不是當初那個清純簡單的留洋學子了,至此便明白幾分,臉頰微熱,截住白雪嵐的話道,「快住嘴。打個野味也能扯到這上頭,這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虧你這個做總長的,還有臉怪手下人。」
又不禁好奇起來,低聲問,「那個東西,你難道就真的吃了?何必去吃那種古怪東西,你平日就很……」
說到一半,忽然就剎住了。
白雪嵐被他這只說了一半的話,撩撥得心窩發癢,慢慢地壓上身體的重量來,一下一下地擠著他問,「我平日就很如何?就很讓你吃不消,是不是?」
宣懷風哪有臉回答這樣下流的問題,被白雪嵐邪氣地擠迫著,便蜷起身體,儘管避讓著。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金玉王朝 第八部 潛熱 (下)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金玉王朝 第八部 潛熱 (中)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金玉王朝 第八部 潛熱 (上)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金玉王朝 第七部 淬鏡 (下)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金玉王朝 第七部 淬鏡 (中)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金玉王朝 第七部 淬鏡 (上)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防水卡貼組-金玉王朝
特價89元
貨到通知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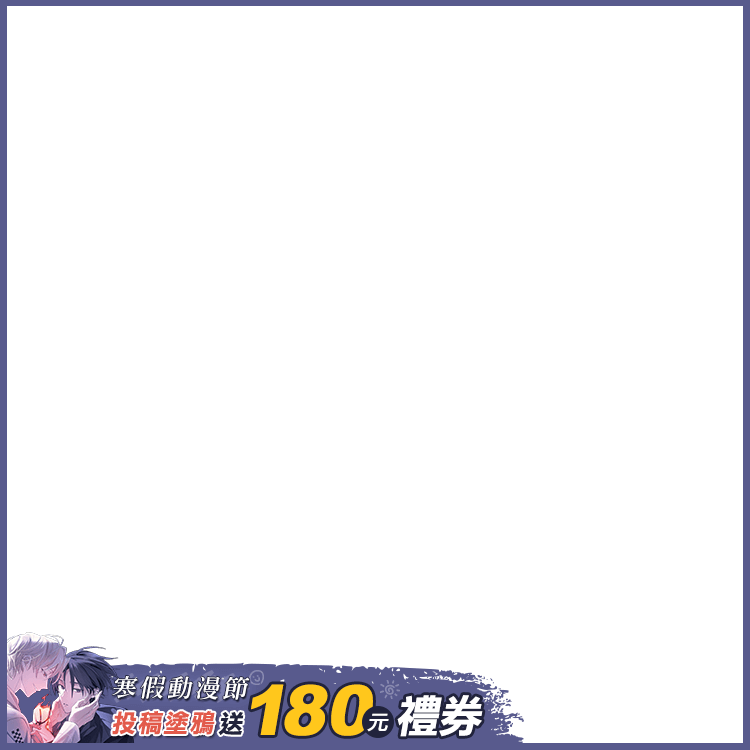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