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1)
眼下最重要的卻非這些兒女情長,三年一度的大衍試,開考在即!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在薛睿的幫助下,劫船一案順利解決,
而薛睿更託人帶余舒進太史書苑,讓她得以查閱大衍試的歷年試卷,
誰想就在藏書樓裡,她竟意外發現了黃霜石的下落!
可不巧的是,石頭卻偏偏是在同她有過節的紀星璇身上。
不過這點麻煩豈能難倒余舒,
有景塵同她配合,擋厄石還不物歸原主?
可饒是余舒再聰慧狡黠,碰上感情問題一樣得傷透腦筋,
她曉得薛睿待她好,以及為何待她這般好,
但景塵一路以來的陪伴和患難與共卻更為牽動她的心,
可薛睿的態度卻讓余舒感覺到,這事兒,還沒完。
但眼下最重要的卻非這些兒女情長,
三年一度的大衍試,開考在即!
本書特色
《新唐遺玉》作者三月果歷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大作!
奇門遁甲這類學問在此時代竟有如此大用?
且看小女子余舒如何運用精算師頭腦配合易學,谷底翻身、出人頭地!
上輩子,她昧著良心賺錢;
這一世,她要活得乾淨自在!
試閱
第一章
「徒兒,你此番下山,是為尋找破命人,切記在此之前,不可妄動道心,一旦……」
夜深了,景塵又從夢中驚醒,睜開眼是一片寂靜的黑暗,他抬起手臂壓在汗濕的額頭上,紊亂的呼吸漸漸平復下來。
依稀回憶著夢裡模糊的情境,半晌後下了床,披上外衫,坐在書桌邊點了燈,一手鋪開紙張,提筆在紙上寫下:破命人、道心。
翻來覆去看著這五個字,景塵就這麼靜靜坐在桌前沉思,一直到窗外微微見了天亮,聽到了大屋房門開響,他將紙折疊壓在一本道經中,重回到床上躺下。
冬日的天白得遲,儘管薛睿那頭還沒有消息,但余舒照樣為大衍做起準備,每天比平日早起半個時辰,起來背書練字,等天再亮些,就出門到街上雜食鋪子秤上半斤餅子,挑二兩鹹菜豆,打上一壺油茶回來做早點。
天冷了,白天下廚房做飯要沾水,容易凍手,余舒持家有道,不會省這點早飯錢。
去敲了敲景塵房門,余舒回屋把余修叫起來,擺上碗筷,三個人吃了早飯,余修去上學,余舒就收拾了桌子,到景塵房裡給他換藥。
景塵手上的傷口長了幾日,縫兒都差不多合上了,分別橫在手指關節和掌心處的兩道刀口子深深的還是肉眼可辨,顯得可怖,余舒小心翼翼地拿棉布沾著熱水清理了一遍,一邊撒上藥粉,一邊問道:「還疼嗎?」
景塵搖搖頭,想了想,又道:「有些癢。」
余舒叮囑道:「癢是好事,慢慢就長好了,千萬別隨便亂撓,知道嗎?」
「嗯。」
景塵低頭,看著正專心拿棉布一圈圈給他包手的余舒,突然開口道:「小魚,我以前同你提起過,我下山入世是為何而來嗎?」
余舒手上動作一頓,若無其事地道:「怎麼好好地問起這個,我記得在船上時我就同你說過,我對你的事知道得不多。」
若是她沒記錯,他曾對她提起過,他此次下山是為了尋找能破他計都星命格的人。
「我昨晚夢到,似是我在山門中的師父告訴我,我下山是為了尋找……破命人。」
余舒猛地抬頭看著景塵。
「你知道什麼是破命人嗎?」景塵面色困惑,對於這夢中的提醒,他想了半夜都無解,還有……道心又是指的什麼?
余舒心中驚疑,他夢什麼不好,怎麼就偏偏夢見了這個,這要她怎麼對他解釋,難道要把他命犯計都星,會時時禍累旁人的真相告訴他?
余舒拿不定主意,之前不告訴景塵,是因為怕他一知道真相就避開她,好像當初在義陽城一樣,但總這麼瞞著他也不是個事兒啊。
要說他們都相處了這麼久,字據也讓他立了,他也親口答應過,她就算真和他說明白,他未必就會一走了之。但是,真和他說了又有什麼用,只要他一日不想起來,知道了破命人是什麼,也無處去找尋,這種事在他恢復記憶之前說出來,只能讓他白受一場打擊,未必就是對他好。倒不如一瞞到底,就算日後他想起來會責怪她,她也認了。
景塵不是不會看人臉色,余舒的猶豫,讓他察覺到,她似乎在瞞著自己什麼,有關他的事。
「小魚,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我……」余舒歪歪脖子,讓她編謊話容易,說真話卻彆扭:「景塵,實話說,我是知道你一些事,但是不方便對你講,還是等你自己想起來吧,啊?」
景塵看著余舒侷促的樣子,到底是不想為難她。
這時候,院外門敲響了,余舒怕景塵再問,趕緊將他手上紗布打了結,「我去開門。」
余舒小跑出去,一拉開門,看到門外一襲雪緞灰裘的俊俏男人,差點手一抖又把門甩上去。
「怎麼著,這副樣子,是見到我不歡迎嗎?」
「哈哈,哪有,是沒想到你這麼一大早就上門。」余舒乾笑兩聲,那天晚上在巷子口,薛睿不清不楚地答了她一句話,讓她到現在心裡頭還犯著彆扭。
「來給妳送好消息,能不早嗎?」薛睿將手裡拎的一盒點心遞給余舒,繞過她進了門,路過景塵房門口,不忘停下打個招呼。
「景公子,手上的傷好些了嗎?」
「嗯,小魚剛給我換過藥。」
「那就好,我同阿舒有正事說,先進去了。」
兩人每回見到也就這麼幾句話,翻來覆去說不厭。
余舒關上門,整理了一下表情,才跟著薛睿進了大屋,放下點心盒子,道:「你先坐,天冷,我去給你沏壺熱茶。」
「別忙了,我說幾句話就走,轎子在外頭等著。」薛睿抬手示意余舒坐下,先是掃了眼屋裡,沒見到過冬用的火爐火炭,暗自記下了,想著下回再來要稍帶什麼。
他不賣關子,直接伸手從裘絨領子裡翻出一直信封,放在桌上,推給她:「妳的事辦成了,這裡是妳入考的文牒,仔細收著千萬不要弄丟,屆時就憑著它去參考,試後還要拿它去接榜。」 余舒面色一喜,撿起了信封,抽出裡面的文書,這是一張相當講究的紙箋,紙張略硬,呈瑩白色,底有印花,正反兩面都寫有字,一面書著入考時年等字樣,下頭蓋有一枚大印,是「司天監」的章,一面書著姓名籍貫等字樣,下頭蓋有兩枚小印,是「太承司」、和「會記司」的章。
余舒瞧見她名字「余舒」下頭,還特意用紅圈印了一個「女」字,心想這大概就是夏明明說的,大衍試用來區分男女考生的方法。
這就相當於是古代的准考證了,余舒心想。
薛睿道:「第一科慣來是易理,臘月初一開考,當天只要帶著紙筆和卜具去太承司,有別於科舉,男女分院而試,當日考當日畢,唯一一點,中午妳得餓著肚子,太承院是不許帶吃食入內的,但有水供應,屆時只要搖鈴喚監考即可。」
余舒之前已經在一位大易師處打聽了大衍試入考事宜,但聽薛睿說的更詳細,便認真記下。
「這頭一科後,再三天是第二科,按順序應當是風水科、星象科、面相科、奇術科,最後才是算科,前面四科不一定是筆試,也有時會考時事,我會派人到太承司打聽,有什麼變動再來通知妳,妳只需安心等候即可。」
余舒點頭,知道這事兒有個人幫襯著最好,便不推辭:「那就有勞你代我留心了。」
「說這客氣話是做什麼,我今天來還有一件事要找妳幫忙。」薛睿這回從袖口裡抽出了一張紙,遞給余舒,「這上面有兩副八字,妳這兩天抽空幫我算一下,看這兩人近日是否有難,可行?」
余舒接過去,並不打聽這上頭是誰的八字,只是笑道:「你託的事還有什麼不行的,你要是不急著走,我現在就給你算,省得你再跑一趟路。」
薛睿看一眼外面,搖頭道:「上午我要到衙門去一趟,看看泰亨商會那起案子審理得如何,不能多待,後天我再來找妳。」
余舒一聽這事,便正了色:「好,我還想說怎麼沒聽動靜,正好你去看看,回頭來告訴我。」
裘彪和畢青一日不被問罪,她一日睡不踏實,這案子最好是盡快了了,別再拖到大衍試時。
余舒起身送薛睿出去,景塵就在院子裡給牆角的菜地澆水,回頭看他們出來,道:「要走了嗎?」
薛睿看著他閒適的樣子,心中不覺有幾分羡慕,這種日子他也曾有過,觀書度日,掃地理舍,還有,同某個缺心少肺的丫頭朝夕相處。
「還有旁的事,改日再來。」過幾日他忙完了手頭上的事,看看在這附近找座空宅,不能再叫他們這麼混住下去,一來不方便,二來他不放心。
「慢走。」
「我出去送送他。」余舒對景塵道,送著薛睿出了門,不忘將院門帶上。
景塵看著被關上的院門,臉上才露出幾分落寞,還有誰似他這般無所事事。
◎
余舒把薛睿送到巷子口,才想起來忘說一件事,正想著要不要同薛睿提一提紀星璇前天來找她的事,薛睿便先看出她有話要說:「怎麼了?」
「唔,也沒什麼,你且走吧,別誤了時辰。」算了,紀星璇也沒能把她怎麼地,反倒是她,逗弄了人家一回,學這嘴沒意思。
薛睿失笑:「不差這麼一兩句話的工夫,妳說。」
余舒也笑,衝他擺擺手攆道:「怎麼就這麼好事呢,真沒什麼,快走快走。」
薛睿看她不願說,想來不是什麼緊要事,便搖搖頭走了,出去十幾步,回頭看一眼,見她還站在巷子口目送,而不是沒良心地轉頭就走,他心情一好,步子也不由輕快了幾分。
殊不知,余舒那頭正望著街對面的豆油鋪子,心琢磨著家裡的油還夠不夠吃,要不要待會兒出來打一壺,壓根沒注意到他走哪兒去了。
薛睿說是去打聽泰亨商會一案審理的情況,當天晚上就有衙門的差役上門來通知,要她準備明天上堂過審,余舒滿口答應了。
余修和景塵都很關心這件案子,前者就怕畢青和裘彪再被放出來,後者倒是想陪余舒一起去過堂聽審。
「我去就好,聽薛少說,畢青裘彪他們當初是把劫船那件案子推到了中途救上船的人身上,那不就是說的你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案子了結之前你最好是不要露面。」
余舒打消了景塵陪同的念頭,又同余修唏噓回憶了當時在船上被逼得走投無路跳江自保的情形,把那裘畢二人恨得是牙癢癢,只想著明天就讓他們被處決了才夠解恨。
吃罷晚飯,各自回房休息,余舒因為明天要上公堂興奮得睡不著,躺了一會兒就乾脆爬起來做算數。 這幾日準備考試,尋找黃霜石的演算法剛有了眉目就被她擱置到一旁,今夜撿起來繼續研究,就算出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奇怪,怎麼照這麼算,那石頭應該就在我身邊兒上啊,明明丟了的……」
余舒摸著下巴,想來想去,只能說是又算錯了步驟,這種法子行不通,得另尋出路。
暗道一聲可惜,將算好大半的結果隨手放在一旁,余舒又抽了紙,重新將有關黃霜石的理數都羅列出來,再一個個套用八門生死的術數口訣,尋找合適的公式反推。
◎
余舒昨晚半夜才睡,第二天不用雞打鳴就醒了,純粹是過於興奮睡不著,收拾好只等著衙門來喊人。
不多久就有官差上門,審案的公堂設在城南衙門,倒是不多遠,走有少半個時辰的路就到了地方,剛一進門,就聽見了喝狀聲:「啟稟大人,義陽人證,余舒帶到!」
余舒還在想著薛睿今天會不會來,一走到了大廳門口便往裡打量,只見公案後海生明月的背景,下坐著一個頭戴烏紗的京官兒,而那側旁又特意列一張木案,後頭坐的正是一身朱紅官服的薛睿。
余舒不是頭一回見到他公服打扮,但回回都覺得他在穿著這身衣裳時,就像是換了一個人,一絲不苟又正經八百的樣子,頗有威嚴。
見他在場,余舒不覺多了幾分心安,想必這案子不出什麼意外,是定了。
薛睿看見余舒被帶上來,對她不著痕跡地微微一點頭,扭臉對公案後的官員道:「徐大人,正是此人,泰亨商會七月進京的商船遇劫時,曾僥倖逃生,且目睹了畢裘幾人同水匪裡應外合,謀財害命的經過。」
余舒這才將視線落在前頭跪在地上穿著囚服,披頭散髮的幾人身上,這幾個人也都正在扭頭看她,認出那大鬍子的裘彪不難,另外一個正死死盯著她的長臉男人,該是畢青無疑了。
他們顯然是在獄中受過刑,個個臉上都有傷處,手腳上的鐐銬露有血色,不過被關了幾日就餓得面黃肌瘦,正該如此,沒了泰亨商會做後臺,他們這等重犯在獄中怎會好過。
時隔多日,再瞧見這舊仇如此形狀,余舒除了痛快,就只一個痛快,不怕那畢青裘彪惡眼相像,冷笑相對:「畢老闆,沒想到吧,我那晚從船上跳江逃生,在林子裡餐風飲露,吃了半個月的麻雀肉,還是撐著活了下來。」
畢青想來是還存著一絲苟活之願,並未在余舒這激怒下反唇相譏,咬破嘴皮忍了回去。
「啪!」
「堂下可是義陽余舒?」
聽到驚堂木聲,余舒上前躬身,做小民狀:「回稟大人,正是在下。」
「妳可認得這下跪幾人?」
「他們化成灰我都認得。」余舒套了句經典的臺詞兒,伸手指著畢青裘彪,抬頭做出忿忿之色:「就是這二人暗通款曲,為私吞商貨,勾結匪徒謀害整條船上旅人的性命!我僥倖逃出生天躲藏到京城,前不久又被他們撞見,他們怕我告破他們的惡行,不光帶人趁夜潛入我宅中企圖加害與我,還買凶殺人,要將我滅口!」
余舒脹紅臉,對著薛睿一拱手,感激道:「多虧了薛大人明察秋毫,將這幾個惡人當場捉拿,不然我便是早晚一死,他們就逍遙法外了。」
薛睿看著余舒在那裡表演,差點忍不住笑場,壓下嘴角,點點頭,對那徐大人道:「泰亨商會已將畢青此人徹查,帳目方才徐大人也過目了,那幾個同犯都已招認,證明這七月劫船一案,同三年前另一起發生在西南的商禍劫財案,皆是畢裘二人帶頭所為,如今人證物證俱在,請徐大人定罪吧。」
在余舒來之前,這案子審得已經差不多,開堂之前供詞都已收齊了,她來也就是走個過場,除她之外,這在場還有兩個泰亨商會的管事,是被東家派來提供物證,聽候審訊的。
而薛睿之所以會在這裡聽堂,則是因著律法中有明文一條,罪若當判死刑,則須有大理寺和刑部的批文,且要兩部職官在場,所以說這起案子,薛睿是下了大功夫,才能在開審之前就申請到了上頭的批文,一旦成刑,則可以直接判決,過後複奏即可。
「啪!」
「堂下義陽縣畢青、裘彪、徐六、周五等人,因於七月間在開封縣內上江段峽處劫禍商船,監守自盜,殺人害命,取利謀財,致死二十六條人命,占數萬之財,經查實確為其事……罪大惡極,故本官判令,剝汝等家財,處畢青、裘彪、徐六、周五四人極刑,臘月三日,斬首示眾,午時行刑!」
「啪!」
「來人啊,拖下去收入死牢!」
那坐堂的徐大人厲聲丟了火籤,畢裘幾人方知劫數難逃,有的立刻就鬼哭狼嚎了起來,大聲討饒,裘彪是面如土灰,反觀畢青,見大勢已去,方露了癲狂,粗喘著氣,措不及防地轉身面向余舒,心想到半生積蓄,苦苦經營就栽在這麼個無名小卒手上,大悔大恨,雙目赤紅,手裡重重的鐐銬高舉砸向她頭頂——「死也要拉妳作數!」 兩邊衙役阻攔不及,只看他撲向余舒,薛睿大驚失色,來不及多想,便抓起了案上玉石紙鎮就要朝著畢青手上擲去,試圖阻攔,然有人比他動作更快——「哼!」
余舒今早上出門算過一卦,早有著防備不測,一直盯著裘彪畢青,一見到畢青發作,眼裡便露了狠色,在他舉手敲來時,抬起一腳,厚底硬邦邦的靴子狠狠照著對方胸腹踹去,半點餘力不留!
「噗咚!」
畢青在獄裡吃苦幾日,怎及她每日幹活吃飽力大十足,被她一腳踹到,悶哼一聲,直愣愣地向後栽倒在地上,腦袋重重一磕,嘴裡湧出一口瘀血,翻了白眼,便暈死過去。
在場的眾人看到這一幕,包括薛睿在內,皆是傻眼,誰曾想一個人證會在明鏡高懸的公堂上把犯人給一腳踹得吐血,片刻後,還是薛睿先回過神,厲聲道:「還不把犯人拖下去!」
余舒輕輕跺了跺發麻的腿,低下頭,對著幾步外瞠目結舌看著她的裘彪微微露了一撇冷笑,頓時便叫後者打了個冷顫,看著被拽著胳膊拖下去的畢青,兩腿發軟地被衙役拉了下去,一點掙扎都沒有。
薛睿正好瞧見了余舒的臉色,眼神一閃,方知道她是早有防備,剛才那一腳賣力只怕是積勢已久,故而見到危險不躲反擊,對她這賊膽,他心中是又氣又樂,面上未做表情,將手裡的紙鎮輕輕放回了桌上,拂平袖口,對著徐大人道:「徐大人明斷,本官這便回大理寺錄案,請你派人前往開封府知會。」
「薛大人放心,下官自會處理妥當。」
薛睿接過師爺複抄的一份口供,帶著兩個官差離去,路過余舒身邊時候,頓了頓腳步,低聲道:「事後再找妳算帳。」
余舒正沉浸在那一腳洩憤的痛快中,耳朵尖傳來這一句,抖抖眉毛,莫名其妙地扭過頭,看著大步帶人離去的薛睿,納悶著:算什麼帳?
衙門外稀稀拉拉的看客裡,有個小廝模樣的見案子落定,一轉身小跑走,在街頭轉角停下,攀了一輛馬車,在車窗邊小聲回報:「二老爺,案子了了,人被判了死刑。」
馬車裡的人似是出了一口長氣:「嗯,走吧。」
不論如何,當日劫船一案事了,畢青裘彪罪有應得,余舒高高興興地回了家,一開門就把這好消息告訴了景塵。
「臘月初三斬首,正好日子,我那天不用考試可以去看。」余舒拉著景塵袖子進了他屋裡,正好桌上有現成的筆墨,便拿起筆在紙上寫下「臘月初三」,又重重畫了一圈。
景塵看看那圈圈,想了想,問道:「我能去嗎?」
余舒頭一歪:「殺人你也想看啊,要見血掉腦袋的你不怕嗎?」
景塵反問道:「那你不怕嗎?」
余舒收起笑,沉聲道:「當然怕了,不過再怎麼可怕,也不比咱們那時候逃生見到的血腥場面更可怕,不過,我要親眼瞧見他們是怎麼死的。」
好讓她牢牢記住那一次船行遇險的慘痛教訓,不可輕信人心。
她對過頭,問景塵道:「你是不是也想看看這兩個惡人如何惡報?」
景塵搖搖頭,誠實地說:「我只是想陪你做個伴。」假如她害怕,身邊至少還有個人在。
余舒眨了眨眼睛,會心一笑:「好,那就一起去,到時候咱們找個高處觀刑,聽說看殺頭的人可多了。」
「嗯。」
「徒兒,你此番下山,是為尋找破命人,切記在此之前,不可妄動道心,一旦……」
夜深了,景塵又從夢中驚醒,睜開眼是一片寂靜的黑暗,他抬起手臂壓在汗濕的額頭上,紊亂的呼吸漸漸平復下來。
依稀回憶著夢裡模糊的情境,半晌後下了床,披上外衫,坐在書桌邊點了燈,一手鋪開紙張,提筆在紙上寫下:破命人、道心。
翻來覆去看著這五個字,景塵就這麼靜靜坐在桌前沉思,一直到窗外微微見了天亮,聽到了大屋房門開響,他將紙折疊壓在一本道經中,重回到床上躺下。
冬日的天白得遲,儘管薛睿那頭還沒有消息,但余舒照樣為大衍做起準備,每天比平日早起半個時辰,起來背書練字,等天再亮些,就出門到街上雜食鋪子秤上半斤餅子,挑二兩鹹菜豆,打上一壺油茶回來做早點。
天冷了,白天下廚房做飯要沾水,容易凍手,余舒持家有道,不會省這點早飯錢。
去敲了敲景塵房門,余舒回屋把余修叫起來,擺上碗筷,三個人吃了早飯,余修去上學,余舒就收拾了桌子,到景塵房裡給他換藥。
景塵手上的傷口長了幾日,縫兒都差不多合上了,分別橫在手指關節和掌心處的兩道刀口子深深的還是肉眼可辨,顯得可怖,余舒小心翼翼地拿棉布沾著熱水清理了一遍,一邊撒上藥粉,一邊問道:「還疼嗎?」
景塵搖搖頭,想了想,又道:「有些癢。」
余舒叮囑道:「癢是好事,慢慢就長好了,千萬別隨便亂撓,知道嗎?」
「嗯。」
景塵低頭,看著正專心拿棉布一圈圈給他包手的余舒,突然開口道:「小魚,我以前同你提起過,我下山入世是為何而來嗎?」
余舒手上動作一頓,若無其事地道:「怎麼好好地問起這個,我記得在船上時我就同你說過,我對你的事知道得不多。」
若是她沒記錯,他曾對她提起過,他此次下山是為了尋找能破他計都星命格的人。
「我昨晚夢到,似是我在山門中的師父告訴我,我下山是為了尋找……破命人。」
余舒猛地抬頭看著景塵。
「你知道什麼是破命人嗎?」景塵面色困惑,對於這夢中的提醒,他想了半夜都無解,還有……道心又是指的什麼?
余舒心中驚疑,他夢什麼不好,怎麼就偏偏夢見了這個,這要她怎麼對他解釋,難道要把他命犯計都星,會時時禍累旁人的真相告訴他?
余舒拿不定主意,之前不告訴景塵,是因為怕他一知道真相就避開她,好像當初在義陽城一樣,但總這麼瞞著他也不是個事兒啊。
要說他們都相處了這麼久,字據也讓他立了,他也親口答應過,她就算真和他說明白,他未必就會一走了之。但是,真和他說了又有什麼用,只要他一日不想起來,知道了破命人是什麼,也無處去找尋,這種事在他恢復記憶之前說出來,只能讓他白受一場打擊,未必就是對他好。倒不如一瞞到底,就算日後他想起來會責怪她,她也認了。
景塵不是不會看人臉色,余舒的猶豫,讓他察覺到,她似乎在瞞著自己什麼,有關他的事。
「小魚,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我……」余舒歪歪脖子,讓她編謊話容易,說真話卻彆扭:「景塵,實話說,我是知道你一些事,但是不方便對你講,還是等你自己想起來吧,啊?」
景塵看著余舒侷促的樣子,到底是不想為難她。
這時候,院外門敲響了,余舒怕景塵再問,趕緊將他手上紗布打了結,「我去開門。」
余舒小跑出去,一拉開門,看到門外一襲雪緞灰裘的俊俏男人,差點手一抖又把門甩上去。
「怎麼著,這副樣子,是見到我不歡迎嗎?」
「哈哈,哪有,是沒想到你這麼一大早就上門。」余舒乾笑兩聲,那天晚上在巷子口,薛睿不清不楚地答了她一句話,讓她到現在心裡頭還犯著彆扭。
「來給妳送好消息,能不早嗎?」薛睿將手裡拎的一盒點心遞給余舒,繞過她進了門,路過景塵房門口,不忘停下打個招呼。
「景公子,手上的傷好些了嗎?」
「嗯,小魚剛給我換過藥。」
「那就好,我同阿舒有正事說,先進去了。」
兩人每回見到也就這麼幾句話,翻來覆去說不厭。
余舒關上門,整理了一下表情,才跟著薛睿進了大屋,放下點心盒子,道:「你先坐,天冷,我去給你沏壺熱茶。」
「別忙了,我說幾句話就走,轎子在外頭等著。」薛睿抬手示意余舒坐下,先是掃了眼屋裡,沒見到過冬用的火爐火炭,暗自記下了,想著下回再來要稍帶什麼。
他不賣關子,直接伸手從裘絨領子裡翻出一直信封,放在桌上,推給她:「妳的事辦成了,這裡是妳入考的文牒,仔細收著千萬不要弄丟,屆時就憑著它去參考,試後還要拿它去接榜。」 余舒面色一喜,撿起了信封,抽出裡面的文書,這是一張相當講究的紙箋,紙張略硬,呈瑩白色,底有印花,正反兩面都寫有字,一面書著入考時年等字樣,下頭蓋有一枚大印,是「司天監」的章,一面書著姓名籍貫等字樣,下頭蓋有兩枚小印,是「太承司」、和「會記司」的章。
余舒瞧見她名字「余舒」下頭,還特意用紅圈印了一個「女」字,心想這大概就是夏明明說的,大衍試用來區分男女考生的方法。
這就相當於是古代的准考證了,余舒心想。
薛睿道:「第一科慣來是易理,臘月初一開考,當天只要帶著紙筆和卜具去太承司,有別於科舉,男女分院而試,當日考當日畢,唯一一點,中午妳得餓著肚子,太承院是不許帶吃食入內的,但有水供應,屆時只要搖鈴喚監考即可。」
余舒之前已經在一位大易師處打聽了大衍試入考事宜,但聽薛睿說的更詳細,便認真記下。
「這頭一科後,再三天是第二科,按順序應當是風水科、星象科、面相科、奇術科,最後才是算科,前面四科不一定是筆試,也有時會考時事,我會派人到太承司打聽,有什麼變動再來通知妳,妳只需安心等候即可。」
余舒點頭,知道這事兒有個人幫襯著最好,便不推辭:「那就有勞你代我留心了。」
「說這客氣話是做什麼,我今天來還有一件事要找妳幫忙。」薛睿這回從袖口裡抽出了一張紙,遞給余舒,「這上面有兩副八字,妳這兩天抽空幫我算一下,看這兩人近日是否有難,可行?」
余舒接過去,並不打聽這上頭是誰的八字,只是笑道:「你託的事還有什麼不行的,你要是不急著走,我現在就給你算,省得你再跑一趟路。」
薛睿看一眼外面,搖頭道:「上午我要到衙門去一趟,看看泰亨商會那起案子審理得如何,不能多待,後天我再來找妳。」
余舒一聽這事,便正了色:「好,我還想說怎麼沒聽動靜,正好你去看看,回頭來告訴我。」
裘彪和畢青一日不被問罪,她一日睡不踏實,這案子最好是盡快了了,別再拖到大衍試時。
余舒起身送薛睿出去,景塵就在院子裡給牆角的菜地澆水,回頭看他們出來,道:「要走了嗎?」
薛睿看著他閒適的樣子,心中不覺有幾分羡慕,這種日子他也曾有過,觀書度日,掃地理舍,還有,同某個缺心少肺的丫頭朝夕相處。
「還有旁的事,改日再來。」過幾日他忙完了手頭上的事,看看在這附近找座空宅,不能再叫他們這麼混住下去,一來不方便,二來他不放心。
「慢走。」
「我出去送送他。」余舒對景塵道,送著薛睿出了門,不忘將院門帶上。
景塵看著被關上的院門,臉上才露出幾分落寞,還有誰似他這般無所事事。
◎
余舒把薛睿送到巷子口,才想起來忘說一件事,正想著要不要同薛睿提一提紀星璇前天來找她的事,薛睿便先看出她有話要說:「怎麼了?」
「唔,也沒什麼,你且走吧,別誤了時辰。」算了,紀星璇也沒能把她怎麼地,反倒是她,逗弄了人家一回,學這嘴沒意思。
薛睿失笑:「不差這麼一兩句話的工夫,妳說。」
余舒也笑,衝他擺擺手攆道:「怎麼就這麼好事呢,真沒什麼,快走快走。」
薛睿看她不願說,想來不是什麼緊要事,便搖搖頭走了,出去十幾步,回頭看一眼,見她還站在巷子口目送,而不是沒良心地轉頭就走,他心情一好,步子也不由輕快了幾分。
殊不知,余舒那頭正望著街對面的豆油鋪子,心琢磨著家裡的油還夠不夠吃,要不要待會兒出來打一壺,壓根沒注意到他走哪兒去了。
薛睿說是去打聽泰亨商會一案審理的情況,當天晚上就有衙門的差役上門來通知,要她準備明天上堂過審,余舒滿口答應了。
余修和景塵都很關心這件案子,前者就怕畢青和裘彪再被放出來,後者倒是想陪余舒一起去過堂聽審。
「我去就好,聽薛少說,畢青裘彪他們當初是把劫船那件案子推到了中途救上船的人身上,那不就是說的你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案子了結之前你最好是不要露面。」
余舒打消了景塵陪同的念頭,又同余修唏噓回憶了當時在船上被逼得走投無路跳江自保的情形,把那裘畢二人恨得是牙癢癢,只想著明天就讓他們被處決了才夠解恨。
吃罷晚飯,各自回房休息,余舒因為明天要上公堂興奮得睡不著,躺了一會兒就乾脆爬起來做算數。 這幾日準備考試,尋找黃霜石的演算法剛有了眉目就被她擱置到一旁,今夜撿起來繼續研究,就算出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奇怪,怎麼照這麼算,那石頭應該就在我身邊兒上啊,明明丟了的……」
余舒摸著下巴,想來想去,只能說是又算錯了步驟,這種法子行不通,得另尋出路。
暗道一聲可惜,將算好大半的結果隨手放在一旁,余舒又抽了紙,重新將有關黃霜石的理數都羅列出來,再一個個套用八門生死的術數口訣,尋找合適的公式反推。
◎
余舒昨晚半夜才睡,第二天不用雞打鳴就醒了,純粹是過於興奮睡不著,收拾好只等著衙門來喊人。
不多久就有官差上門,審案的公堂設在城南衙門,倒是不多遠,走有少半個時辰的路就到了地方,剛一進門,就聽見了喝狀聲:「啟稟大人,義陽人證,余舒帶到!」
余舒還在想著薛睿今天會不會來,一走到了大廳門口便往裡打量,只見公案後海生明月的背景,下坐著一個頭戴烏紗的京官兒,而那側旁又特意列一張木案,後頭坐的正是一身朱紅官服的薛睿。
余舒不是頭一回見到他公服打扮,但回回都覺得他在穿著這身衣裳時,就像是換了一個人,一絲不苟又正經八百的樣子,頗有威嚴。
見他在場,余舒不覺多了幾分心安,想必這案子不出什麼意外,是定了。
薛睿看見余舒被帶上來,對她不著痕跡地微微一點頭,扭臉對公案後的官員道:「徐大人,正是此人,泰亨商會七月進京的商船遇劫時,曾僥倖逃生,且目睹了畢裘幾人同水匪裡應外合,謀財害命的經過。」
余舒這才將視線落在前頭跪在地上穿著囚服,披頭散髮的幾人身上,這幾個人也都正在扭頭看她,認出那大鬍子的裘彪不難,另外一個正死死盯著她的長臉男人,該是畢青無疑了。
他們顯然是在獄中受過刑,個個臉上都有傷處,手腳上的鐐銬露有血色,不過被關了幾日就餓得面黃肌瘦,正該如此,沒了泰亨商會做後臺,他們這等重犯在獄中怎會好過。
時隔多日,再瞧見這舊仇如此形狀,余舒除了痛快,就只一個痛快,不怕那畢青裘彪惡眼相像,冷笑相對:「畢老闆,沒想到吧,我那晚從船上跳江逃生,在林子裡餐風飲露,吃了半個月的麻雀肉,還是撐著活了下來。」
畢青想來是還存著一絲苟活之願,並未在余舒這激怒下反唇相譏,咬破嘴皮忍了回去。
「啪!」
「堂下可是義陽余舒?」
聽到驚堂木聲,余舒上前躬身,做小民狀:「回稟大人,正是在下。」
「妳可認得這下跪幾人?」
「他們化成灰我都認得。」余舒套了句經典的臺詞兒,伸手指著畢青裘彪,抬頭做出忿忿之色:「就是這二人暗通款曲,為私吞商貨,勾結匪徒謀害整條船上旅人的性命!我僥倖逃出生天躲藏到京城,前不久又被他們撞見,他們怕我告破他們的惡行,不光帶人趁夜潛入我宅中企圖加害與我,還買凶殺人,要將我滅口!」
余舒脹紅臉,對著薛睿一拱手,感激道:「多虧了薛大人明察秋毫,將這幾個惡人當場捉拿,不然我便是早晚一死,他們就逍遙法外了。」
薛睿看著余舒在那裡表演,差點忍不住笑場,壓下嘴角,點點頭,對那徐大人道:「泰亨商會已將畢青此人徹查,帳目方才徐大人也過目了,那幾個同犯都已招認,證明這七月劫船一案,同三年前另一起發生在西南的商禍劫財案,皆是畢裘二人帶頭所為,如今人證物證俱在,請徐大人定罪吧。」
在余舒來之前,這案子審得已經差不多,開堂之前供詞都已收齊了,她來也就是走個過場,除她之外,這在場還有兩個泰亨商會的管事,是被東家派來提供物證,聽候審訊的。
而薛睿之所以會在這裡聽堂,則是因著律法中有明文一條,罪若當判死刑,則須有大理寺和刑部的批文,且要兩部職官在場,所以說這起案子,薛睿是下了大功夫,才能在開審之前就申請到了上頭的批文,一旦成刑,則可以直接判決,過後複奏即可。
「啪!」
「堂下義陽縣畢青、裘彪、徐六、周五等人,因於七月間在開封縣內上江段峽處劫禍商船,監守自盜,殺人害命,取利謀財,致死二十六條人命,占數萬之財,經查實確為其事……罪大惡極,故本官判令,剝汝等家財,處畢青、裘彪、徐六、周五四人極刑,臘月三日,斬首示眾,午時行刑!」
「啪!」
「來人啊,拖下去收入死牢!」
那坐堂的徐大人厲聲丟了火籤,畢裘幾人方知劫數難逃,有的立刻就鬼哭狼嚎了起來,大聲討饒,裘彪是面如土灰,反觀畢青,見大勢已去,方露了癲狂,粗喘著氣,措不及防地轉身面向余舒,心想到半生積蓄,苦苦經營就栽在這麼個無名小卒手上,大悔大恨,雙目赤紅,手裡重重的鐐銬高舉砸向她頭頂——「死也要拉妳作數!」 兩邊衙役阻攔不及,只看他撲向余舒,薛睿大驚失色,來不及多想,便抓起了案上玉石紙鎮就要朝著畢青手上擲去,試圖阻攔,然有人比他動作更快——「哼!」
余舒今早上出門算過一卦,早有著防備不測,一直盯著裘彪畢青,一見到畢青發作,眼裡便露了狠色,在他舉手敲來時,抬起一腳,厚底硬邦邦的靴子狠狠照著對方胸腹踹去,半點餘力不留!
「噗咚!」
畢青在獄裡吃苦幾日,怎及她每日幹活吃飽力大十足,被她一腳踹到,悶哼一聲,直愣愣地向後栽倒在地上,腦袋重重一磕,嘴裡湧出一口瘀血,翻了白眼,便暈死過去。
在場的眾人看到這一幕,包括薛睿在內,皆是傻眼,誰曾想一個人證會在明鏡高懸的公堂上把犯人給一腳踹得吐血,片刻後,還是薛睿先回過神,厲聲道:「還不把犯人拖下去!」
余舒輕輕跺了跺發麻的腿,低下頭,對著幾步外瞠目結舌看著她的裘彪微微露了一撇冷笑,頓時便叫後者打了個冷顫,看著被拽著胳膊拖下去的畢青,兩腿發軟地被衙役拉了下去,一點掙扎都沒有。
薛睿正好瞧見了余舒的臉色,眼神一閃,方知道她是早有防備,剛才那一腳賣力只怕是積勢已久,故而見到危險不躲反擊,對她這賊膽,他心中是又氣又樂,面上未做表情,將手裡的紙鎮輕輕放回了桌上,拂平袖口,對著徐大人道:「徐大人明斷,本官這便回大理寺錄案,請你派人前往開封府知會。」
「薛大人放心,下官自會處理妥當。」
薛睿接過師爺複抄的一份口供,帶著兩個官差離去,路過余舒身邊時候,頓了頓腳步,低聲道:「事後再找妳算帳。」
余舒正沉浸在那一腳洩憤的痛快中,耳朵尖傳來這一句,抖抖眉毛,莫名其妙地扭過頭,看著大步帶人離去的薛睿,納悶著:算什麼帳?
衙門外稀稀拉拉的看客裡,有個小廝模樣的見案子落定,一轉身小跑走,在街頭轉角停下,攀了一輛馬車,在車窗邊小聲回報:「二老爺,案子了了,人被判了死刑。」
馬車裡的人似是出了一口長氣:「嗯,走吧。」
不論如何,當日劫船一案事了,畢青裘彪罪有應得,余舒高高興興地回了家,一開門就把這好消息告訴了景塵。
「臘月初三斬首,正好日子,我那天不用考試可以去看。」余舒拉著景塵袖子進了他屋裡,正好桌上有現成的筆墨,便拿起筆在紙上寫下「臘月初三」,又重重畫了一圈。
景塵看看那圈圈,想了想,問道:「我能去嗎?」
余舒頭一歪:「殺人你也想看啊,要見血掉腦袋的你不怕嗎?」
景塵反問道:「那你不怕嗎?」
余舒收起笑,沉聲道:「當然怕了,不過再怎麼可怕,也不比咱們那時候逃生見到的血腥場面更可怕,不過,我要親眼瞧見他們是怎麼死的。」
好讓她牢牢記住那一次船行遇險的慘痛教訓,不可輕信人心。
她對過頭,問景塵道:「你是不是也想看看這兩個惡人如何惡報?」
景塵搖搖頭,誠實地說:「我只是想陪你做個伴。」假如她害怕,身邊至少還有個人在。
余舒眨了眨眼睛,會心一笑:「好,那就一起去,到時候咱們找個高處觀刑,聽說看殺頭的人可多了。」
「嗯。」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萬事如易 第肆卷 天下易得,成敗誰何(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一卷 福禍易算,人心難卜(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一卷 福禍易算,人心難卜(2)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2)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3)完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三卷 生死易破,情仇難解(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三卷 生死易破,情仇難解(2)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一卷 福禍易算,人心難卜(3)完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三卷 生死易破,情仇難解(3)完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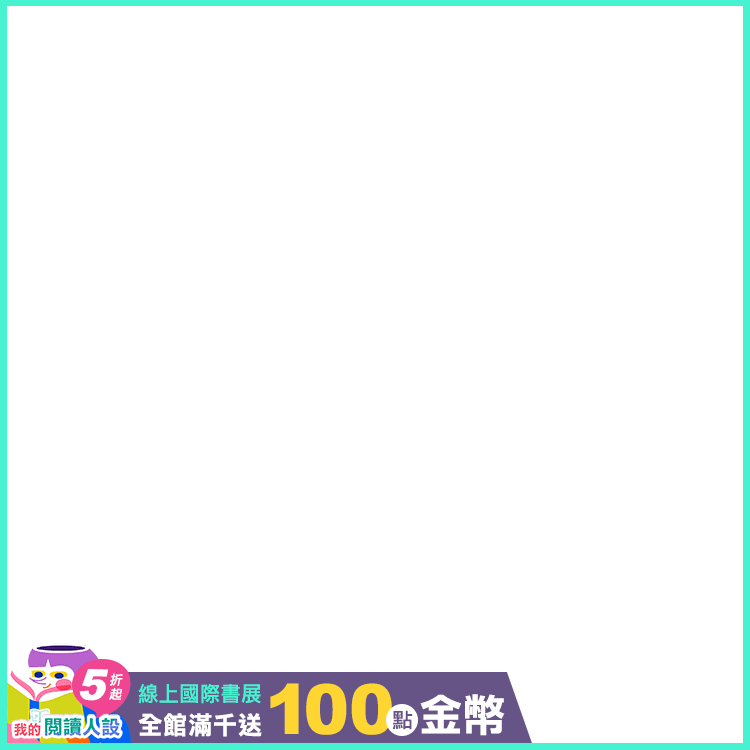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