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陽光 (下)
一無所有了,卻仍須挺直脊梁,深深地愛著,原來,是這樣艱難嗎……內容簡介
以為肉體折磨可怕的人,
其實是因為未受過精神折磨。
高高在上獨攬大權的安燃一句「不想活」,
被搓圓按扁的何君悅,
頓時成了呼風喚雨的接班人。
安燃失蹤了,狩獵的掠奪者已然消失,
備受煎熬的小魚,真的自由了嗎?
江湖的糜爛虛偽,人後血淋淋的決策,
再沒有了爸爸、大哥、或者安燃,
現實的重擔,頭一次落在了何大少爺的肩膀上。
一無所有了,卻仍須挺直脊梁,
深深地愛著,
原來,是這樣艱難嗎……
試閱
第一章
經過這麼多的教訓,我已經懶得再期待什麼奇蹟。
不是頹喪,做人該識趣。
安燃覆蓋的範圍內,怎麼可能有奇蹟?
如果有,那就是陷阱。
我知道,應保持這個警覺。
我做到了,才發現後果沒什麼不同。
該倒楣的時候,一樣倒楣;該死無全屍的時侯,索性痛快點死無全屍,萬萬不要死去活來,還保持清醒,暈不過去。
真的。
夜深人靜,那麼幾個來回,落個熱汗淋漓,我竟然還出奇清醒。
如果不是被壓在下面的那人是我,哭著叫著救命的人是我,我一定萬分激賞營養針、爬山、補品的綜合功效。
安燃的體能極限到底如何,我不知道。
當然,更不想知道。
這樣又冷又熱,又動人又絕望,不是什麼好滋味。筋疲力盡之際,我叫夠了徒勞無功的救命,便開始無骨氣的哭。
這幾招用得多了,連我都覺得厭煩。可惜沒有新招,不得不用。
哭得厲害了,安燃往我臉上輕輕吹一口氣,柔聲問,「哭什麼?」
我說,「安燃,好難受。」
安燃不置可否,「是嗎?」
他還是那麼懂說話,口氣恰到好處,不尖酸刻薄,那份視你如螻蟻的淡漠,從尊貴從容裡直透出來。
有時候,我真奇怪他的血統。
安家的人,怎麼出這樣一個異類?
隔一會,安燃又問,「誰難受?」
我愣看著他。
他說,「你剛剛說安燃,好難受。誰難受?君悅,你?還是我?」
很心平氣和的語調,彷佛談心。
我這個經常被修理的,卻恍如驚弓之鳥,不敢亂說一個字。
安燃目光,盯在我臉上。
他忽然壓低聲音,「君悅,你怕我?」
好問題。
至少這個問題,我知道答案。
我連忙點頭,以表臣服,表情一百二十分配合,唯恐他覺得我不夠誠懇。
安燃只是笑。
他笑得又那麼溫柔,挨近來,對我耳語,「君悅,我們再來。」
我倒抽一口涼氣。
他要取我小命,我知道。
看見我的神色,安燃竟然體貼入微,行事前,還問一句,「有話要說?」
反正都要完蛋,我想,還是不要死得不明不白。
我斗膽,問他,「寧舒到底是什麼人?」
別說何君悅一點都不懂兵法,這個怎麼也算新招,叫置於死地。
惹毛惡魔,是否可以後生,希望不大。
只盼他一時惱了,下手稍微失個輕重,不小心給了我一個痛快,真的一了百了。
本來是這樣打算的,結果證明,論兵法,十個君悅都不是安燃的對手。
安燃不但沒有惱,他還笑。
忍俊不禁的笑,看著我,如看一個笑話。
他問,「君悅,你以為我吃醋?」
如果我膽子夠大,一定反問「你說呢?」。不過膽子不夠大,我只能搖頭,虛偽到十成,回答得很違心,「沒有。」
說得多,錯得就多。
話一出口,安燃就斂了笑,悠然地,歎氣,搖頭,露無奈之色,「君悅,你又說謊。」
這個「又」字,絕對毒辣。
提醒我已經錯過百萬次,現在再度咎由自取,就算被人拆骨煎皮,也是自作孽,不可活。
精彩。
我雖然沒有昏,但體力消耗過多,面對這麼強大的對手,還要遭他翻來覆去戲弄,一加二加三,早到了欲暈未暈,眼冒金星的勝境。
於是,不但又說謊,而且,又開始犯錯。
我說,「安燃,對不起。」
這句話,當然錯。安燃何等人物,得寸進尺,從不放過,我主動退一步,他立即侵前三步。
果然,安燃立即問,「為什麼說對不起?」那語氣,還很無辜。
每次和他玩對白遊戲,我就痛苦不堪。
偏偏躲不過。
我思考。
與其一句一句被逼問,不如化長痛為短痛,一次到位。
所以我也來個痛快坦白,「因為我痴心妄想,以為你還像從前那樣愛我,以為你會為我吃醋。對不起,我作了好美一個,白日夢。」
這句話,也是錯的。
本來地位就不高,還要妄想期盼,這種人,連我自己也不屑。我知道,那些營養針、爬山、補品、娛樂中心管理權,通通不算什麼,代表不了什麼。
安燃一直提醒我不要以為過去能重來,我卻仍盼望。
這不能怪安燃,只能怪我,他的的確確,一直提醒我,用各種方法。
安燃看來早猜到答案,居高臨下俯視我,目光絲毫未變。
他不惱,也不高興,甚至不鄙夷。
他只憐憫輕歎,「君悅,既然是白日夢,就不該去做。」
這人一開口,總如寶劍出鞘。
若是冰冷的話,則如冷刃,寒透人心;若不冰冷反而柔情萬分,則如抹毒的溫柔一劍,輕輕插進去,抽出來時還不沾血,不太痛,只是要了你的命。
來來去去,都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一開口,我便又哭了。
傷心欲絕,抱著他哭得毫無矜持。
太可悲,到如今,要哭的時候,我還只能抱著他。一邊尊嚴喪盡,一邊還要問,「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明白。」
這樣的悲情鏡頭,在我和安燃之間演到爛了,沒能感動安燃,反傷盡了我自己。安燃聽著我問,一成不變的沉默,任我抱著他,揮霍此生眼淚。
我知道他不會答,每逢這時,開口的只有我而已。
他寶劍已經出鞘,功成身退,剩下的,只能我孤零零演繹。
抱著他,哭給自己聽,問給自己聽。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我什麼都願意,為什麼還是死路一條?」
「應該怎麼做?你教我,安燃。」「為什麼?為什麼變成如今這樣?我不明白,死也不明白。」
我問多久,安燃就沉默多久。
等我哭夠問夠,不做聲了,安燃才反抱了我,反問了那麼一句話。
他問,「君悅,為什麼你不明白?」
匪夷所思。
他說什麼毒辣的話,都不會比這句更讓我怔住。
我怔住,怔在他如鐵鑄的懷裡。
不曾料到,我問過之後,他罕見地接過了戲份。
緊抱著我,語氣低沉。
「為什麼你不懂?」
「為什麼你總不明白?」
「君悅,什麼時候,你才能明白?」
一聲,一聲,再一聲。
比我的更令人心痛,更令人絕望。
我怔得徹底,簡直痴了,心底明白安燃真是常勝將軍,無人可敵,輕輕一個反擊,何君悅什麼鬥志都被瓦解了。
我愣了半天,心中剩下的都是灰色,輕飄飄,卻仍會不忍。最終只是索然歎氣,不知第多少次舉手投降,閉上眼說,「安燃,你要做就做。」
做吧。
不要哭了。
再不要哭了。
我投降,服了。
以為肉體折磨可怕的人,其實是因為未受過精神折磨。
本希望得一個喘息,不用見識安燃的體能極限,後來才知道,頑抗得來的下場,還不如早點讓安燃如願以償。
可惜,我後悔的又遲了。
當安燃要做的時候,我沒有讓他盡興;當我企圖讓他盡興的時候,他也理所當然沒讓我得逞。
我放鬆身體,他反而抱得我更緊。
鐵臂收勒,很用力。
我忍著,希望那傳過來的顫慄只是因為用力,而不是因為他真的在顫慄。
兩個大男人,我抱著他哭,已經很可笑;他抱著我哭,只能更可笑。
太不可思議,局勢莫名其妙逆轉,前一秒還算正常,下一秒,那心平氣和的角色就忽然落我頭上了。
我半帶驚惶,餘下一半,也只有盡量心平氣和,低聲問這個幾乎把我勒到無法呼吸,又絕望到令人心痛的男人,「安燃,你幹什麼?」
安燃久久不回答。
秒針從容移動,夜仍深沉。
他不回答,我便一同沉默。
雖然不好受,但剎那間,會有那麼一絲希望時光永存此刻的奢望閃過心頭。因為他抱得好緊,彷彿懷裡的極珍貴,生怕失去。
如果我是一件瓷器,會希望被他用臂力勒碎在胸前。
但,安燃不是我,他當然不會哭著睡去。
沉默夠了,他終於說話。
「君悅,」他把臉埋在我頸窩,慢慢說,「我不想活。」
這麼一句,驚出我一身冷汗。
我受驚地問,「安燃,你說什麼?」
沒道理,太沒道理。
我這個被搓圓按扁的尚且沒死透,你這個高高在上的反而不想活?
什麼天理?
他不回答,我迫切追問,「為什麼?安燃,你說清楚。」
若不是他依然體重驚人,臂力驚人,勒得我透不過氣來,我說不定已經拽起他的衣領,盯著他的眼睛。
很無奈,如今卻要當個忍氣吞聲的抱枕,還一邊追問為什麼。
安燃在我頸窩裡喃喃,「太艱難,太絕望……」
我追問,「什麼艱難?什麼東西絕望?」
你比誰艱難?
你比我還活得絕望?
我真憤怒。
我還是問那一句,「為什麼?」
安燃長歎,回答一句,「我一無所有。」
我啼笑皆非。
虧他那麼認真感歎,說的卻是個彌天大謊。
我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要安慰他,笨拙得如獵物反去安慰獵人,竟然真心實意,「安燃,你怎會一無所有,今非昔比,你什麼都得到了,應該知足。」
很快我就發現,這句安慰是我今夜犯的最大錯誤。
話一出口,那個脆弱得不想活的男人就消失了。
安燃變身的速度,快得好可怕。
我才心裡微覺不妥,已聽見安燃不屑的嗤笑。
他冷笑的聲音令人難受,笑著,有趣地問我,「你真這麼想?」
不等我回答,他吐出一聲「好」,然後說,「君悅,不妨讓你像我一樣,什麼都得到。」
最後,加一句鋒刃似的祝福,「希望你比我知足。」
聽他那語氣,我就知道又一次的大事不好。
但不好在什麼地方,卻猜不出來。
玄機未露,空琢磨,反正琢磨不出來。
只能先睡了。
次日,我被阿旗禮貌的叫醒。睜開眼,安燃已經不在屋內。安大公子自由來去,沒人有資格過問,我更不會自取禍端,便在床上睡眼惺忪,看著阿旗。
阿旗說,「君悅少爺,安老大吩咐,你今天可以去娛樂中心上班,那邊各級主管已接到通知。君悅少爺到了之後,會議就開始。」
昨晚不知道究竟幾點才入睡,任誰像我這樣一夜又驚又嚇還要傷心,都會精神不濟。
何況,還消耗了大量體力。
阿旗說的,我勉強聽得明白,回應起來卻不容易。人未醒時大腦最難使喚,我挨在枕旁,看他半天,才迷糊問了一句頗關鍵的,「安燃有規定幾點必須到嗎?」
阿旗一絲不苟地答,「沒有。」
好答案。
我放心下來,倦意湧上,倒下繼續大睡。
這一覺無夢,倒是睡得不錯。肆意睡夠了,才有精力生出些許懼意,想起安燃那個惡魔般的脾氣,除非萬不得已,不可招惹,我勉強自己醒來,爬起,收拾自己。
打開門,發現阿旗領著幾個西裝筆挺的男人,似乎一直等在外面。
若論耐性,阿旗在黑道中真是難得的,難怪安燃看得上他。
明明在走廊上等了大半日,他那臉色卻正常到如我按時赴約,讓開一條路,把手一送,「君悅少爺,車已經準備好。」
我點頭。
一車送到娛樂中心,又是前呼後擁呼嘯入門。
這次身邊少了安燃,四面八方更多注視自然集中在我身上。
對這樣張狂的出場,我只能無可奈何,恨不得從哪翻出幾張白紙,上書淋漓兩個大字──獄卒,貼在這些冒牌保鑣額上。
阿旗輕車熟路,領著我們一干人等招招搖搖,直上最高層。
到了樓層,合金門兩扇左右打開,水晶燈的反射光芒迎面撲來,璀璨得令人呼吸一窒。
「君悅少爺來了。」
在門前那麼一停,才看清一屋子的人。
很多是生面孔,高矮肥瘦不一,不過眼神氣度都算不錯,看我來了,個個肅然起立。
林信儼然也在其中。
我真不得不愕然。
安燃不愧是安燃,連玩個遊戲,手筆也夠大。遊樂場之後,索性丟出個娛樂中心。
這梟雄如此有魄力,江山多嬌,鬥爭激烈,理應忙到不堪。他哪來那麼多餘的心機,一點也不吝嗇,通通花在對付我上頭?
我冷冷環視這一屋子人。
林信看來是裡頭頗有地位的,率先打破僵局,問我,「會議可以開始了嗎?」
我問,「你們在等我?」
林信說,「對,從今天早上八點正開始。」
我了然。
怪不得滿屋怨氣。
原來我這個新官懵懂一覺,已經燒了第一把火。不用說,這裡十個人裡面,十個都會認為我姍姍來遲,是在施下馬威。
真是個無可解釋的誤會。
但這威下都已經下了,只能硬著頭皮繼續。
我領著阿旗一干獄卒進門,起碼看起來威風凜凜,穿過站立的眾人,順理成章坐在大書桌後面。
背靠椅上,擺個子勢,輕描淡寫,「大家坐,開會吧。」
什麼都是裝的,只有那輕描淡寫不是。
反正只是個擺設、事不關己,要緊張也輪不到我。
會議開始,林信自動自覺當了主持。大家輪流發言,一切很有順序。
我恪守本分,在書桌前托著半邊腮,扮做思考,為免單調,偶爾還點個頭,發個模糊的單音。
若有人侃侃而談到一半,用詢問的目光看向我,我就說五個字萬無一失的字,「我在聽,繼續。」
聽什麼?真可笑。
供應商資金流云云,我壓根不懂。他們說得越專業,君悅少爺我越雲裡霧裡,那些老成持重的建議,用盡心力組織的詞句,對我的意義還不如一首三流KTV。
左耳入右耳出,我倒是略有餘力觀察林信。
機會難得,安燃不在,又是會議這樣冠冕堂皇的場合,林信這個主持會議的就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翹著二郎腿,在眾人間居中調和,主導氣氛。
他真的長大了,那般駕輕就熟。
我打量他半天,找不到當初的影子,那些癲狂放肆的色彩呢?那些醉酒當歌無病呻吟的幼稚呢?全不見。
人人都會變,變得我根本不認得。
阿旗在旁邊提醒一聲,「君悅少爺。」
我才低頭去看送到眼前的厚厚大本,翻一翻,前面每頁都用端正筆跡記得密密麻麻。
一邊亂翻,我一邊忍著笑。
大哥如果在天有靈,此刻應該也會哈哈大笑。
何君悅端坐桌前,認真翻看大帳本的鏡頭,怎麼想像,怎麼滑稽。
別人不知道我底細,林信是知道的。但偏偏是他,站在我桌前,等候我翻得差不多,還那麼沉著地問上一句,「君悅,覺得怎樣?」
他真不該問。
我已經忍得很辛苦,被他語氣認真地一問,頓時情不自禁,笑出聲來。
雖然只有一聲,但想必人人都已聽見。
屋裡這群西裝革履的管理級精英,個個目光聚焦,都定在我身上。
我總不能學他們一樣盯著自己,只有抬頭,去盯林信,唇邊還帶著方才殘餘的一絲苦笑。
林信反應敏捷得令我吃驚,一接觸我的視線,立即點頭,「是,我明白了。」
我自己都懵了。
明白什麼?我自己都沒弄明白。
林信轉過身,指了一人出來,純熟地發出指使,「帳本再重頭對一次。」
只聽見連聲應是,一個陌生人到我桌前,半彎腰,雙手取下面前的帳本,迅速退下去。
我恍然,心底大歎,繼而大樂。
於是,枯燥的會議忽然充滿樂趣,這是我開始絕沒想到的。
安燃是個天才,林信原來也不遜色。
我每個莫名其妙的表情,小動作,都能被他解釋成某個充滿玄機的決定,他一解釋,就立即有人領命執行,效率之高,配合之精密,令人歎為觀止。
這齣好戲,我看得不亦樂乎,邊演邊看,可惜後來得意忘形,伸了個過於愜意的懶腰,林信便不打招呼奏響了結束音樂,宣布,「說的夠多了,會議結束,都去幹活吧。」
眾人收拾文件,肅然而去,腳步匆忙。
好戲落幕,一屋人氣散去九成。
安靜了幾分鐘,我才確定真的曲終人散。
打個哈欠,懶懶趴下,伏在書桌,下巴墊在手臂上,看著面前的林信,有趣地笑。
林信並不配合,筆直地站在書桌前,低頭和我對視半天,才說,「君悅,你還是老樣子。」
我問,「嗯?」
林信用八個字給我的老樣子下評斷,「不學無術,無責任心。」
我放聲大笑,不可自抑。
世界真奇妙,可以毫無預兆,某日忽然把所有人都變得面目全非,面孔翻轉過來,你才糊裡糊塗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千夫所指,罪惡根源。
林信冷眼看我大笑,半日,才搖頭,「你還笑?」
我奇怪了,問他,「我不笑?難道要哭?」
哭本來也沒什麼。
不過我的眼淚,已經通通給了安燃,哪裡還有多餘的留給林信?
林信說我不學無術,無責任心。
安燃怎麼說的?對,頑劣不堪,冥頑不靈,不可救藥。
都說了不可救藥,林信又能奈我何?他也就只能歎氣,搖頭,退回沙發,收拾他帶來的文件。
我看著他彎腰的背影,忽然問,「你走了?」
他甚至懶得回頭,冷冷說,「我並不是你,總要做點事。」
好深明大義的回答,正氣凜然。
不用說,一定是安燃調教出來的。
走了林信,我更加無聊。
辦公室後面整牆的落地玻璃,不放下窗簾時,能直接看到下方的賭場。我發呆地看了半日,被阿旗喚醒過來。
阿旗問,「君悅少爺,餓嗎?想吃點什麼?」
我驚訝,「可以點餐?」
阿旗點頭,「當然,怎麼會不可以?」
那神情,一貫的充滿欺騙性,彷彿我從來就擁有這項權利,從前被逼著吃光指定食物的日子都是作夢。
不過,這怎麼說,也畢竟是一項恩賜。
如果可以一直恩賜下去,我倒是寧願跪下三呼萬歲,真心實意謝主隆恩的。
我問,「有什麼選擇?」
阿旗型的敏捷再現,立即不知從哪裡變出一迭菜單。菜單各種各樣,設計十分錆美,一看就知道檔次不錯。泰國菜、法國菜、中餐、義大利菜、印度菜……各國美食俱備,不但有娛樂中心內設餐廳的點菜單,恐怕這附近可以送餐的高級餐廳都在其中。
經過這麼多的教訓,我已經懶得再期待什麼奇蹟。
不是頹喪,做人該識趣。
安燃覆蓋的範圍內,怎麼可能有奇蹟?
如果有,那就是陷阱。
我知道,應保持這個警覺。
我做到了,才發現後果沒什麼不同。
該倒楣的時候,一樣倒楣;該死無全屍的時侯,索性痛快點死無全屍,萬萬不要死去活來,還保持清醒,暈不過去。
真的。
夜深人靜,那麼幾個來回,落個熱汗淋漓,我竟然還出奇清醒。
如果不是被壓在下面的那人是我,哭著叫著救命的人是我,我一定萬分激賞營養針、爬山、補品的綜合功效。
安燃的體能極限到底如何,我不知道。
當然,更不想知道。
這樣又冷又熱,又動人又絕望,不是什麼好滋味。筋疲力盡之際,我叫夠了徒勞無功的救命,便開始無骨氣的哭。
這幾招用得多了,連我都覺得厭煩。可惜沒有新招,不得不用。
哭得厲害了,安燃往我臉上輕輕吹一口氣,柔聲問,「哭什麼?」
我說,「安燃,好難受。」
安燃不置可否,「是嗎?」
他還是那麼懂說話,口氣恰到好處,不尖酸刻薄,那份視你如螻蟻的淡漠,從尊貴從容裡直透出來。
有時候,我真奇怪他的血統。
安家的人,怎麼出這樣一個異類?
隔一會,安燃又問,「誰難受?」
我愣看著他。
他說,「你剛剛說安燃,好難受。誰難受?君悅,你?還是我?」
很心平氣和的語調,彷佛談心。
我這個經常被修理的,卻恍如驚弓之鳥,不敢亂說一個字。
安燃目光,盯在我臉上。
他忽然壓低聲音,「君悅,你怕我?」
好問題。
至少這個問題,我知道答案。
我連忙點頭,以表臣服,表情一百二十分配合,唯恐他覺得我不夠誠懇。
安燃只是笑。
他笑得又那麼溫柔,挨近來,對我耳語,「君悅,我們再來。」
我倒抽一口涼氣。
他要取我小命,我知道。
看見我的神色,安燃竟然體貼入微,行事前,還問一句,「有話要說?」
反正都要完蛋,我想,還是不要死得不明不白。
我斗膽,問他,「寧舒到底是什麼人?」
別說何君悅一點都不懂兵法,這個怎麼也算新招,叫置於死地。
惹毛惡魔,是否可以後生,希望不大。
只盼他一時惱了,下手稍微失個輕重,不小心給了我一個痛快,真的一了百了。
本來是這樣打算的,結果證明,論兵法,十個君悅都不是安燃的對手。
安燃不但沒有惱,他還笑。
忍俊不禁的笑,看著我,如看一個笑話。
他問,「君悅,你以為我吃醋?」
如果我膽子夠大,一定反問「你說呢?」。不過膽子不夠大,我只能搖頭,虛偽到十成,回答得很違心,「沒有。」
說得多,錯得就多。
話一出口,安燃就斂了笑,悠然地,歎氣,搖頭,露無奈之色,「君悅,你又說謊。」
這個「又」字,絕對毒辣。
提醒我已經錯過百萬次,現在再度咎由自取,就算被人拆骨煎皮,也是自作孽,不可活。
精彩。
我雖然沒有昏,但體力消耗過多,面對這麼強大的對手,還要遭他翻來覆去戲弄,一加二加三,早到了欲暈未暈,眼冒金星的勝境。
於是,不但又說謊,而且,又開始犯錯。
我說,「安燃,對不起。」
這句話,當然錯。安燃何等人物,得寸進尺,從不放過,我主動退一步,他立即侵前三步。
果然,安燃立即問,「為什麼說對不起?」那語氣,還很無辜。
每次和他玩對白遊戲,我就痛苦不堪。
偏偏躲不過。
我思考。
與其一句一句被逼問,不如化長痛為短痛,一次到位。
所以我也來個痛快坦白,「因為我痴心妄想,以為你還像從前那樣愛我,以為你會為我吃醋。對不起,我作了好美一個,白日夢。」
這句話,也是錯的。
本來地位就不高,還要妄想期盼,這種人,連我自己也不屑。我知道,那些營養針、爬山、補品、娛樂中心管理權,通通不算什麼,代表不了什麼。
安燃一直提醒我不要以為過去能重來,我卻仍盼望。
這不能怪安燃,只能怪我,他的的確確,一直提醒我,用各種方法。
安燃看來早猜到答案,居高臨下俯視我,目光絲毫未變。
他不惱,也不高興,甚至不鄙夷。
他只憐憫輕歎,「君悅,既然是白日夢,就不該去做。」
這人一開口,總如寶劍出鞘。
若是冰冷的話,則如冷刃,寒透人心;若不冰冷反而柔情萬分,則如抹毒的溫柔一劍,輕輕插進去,抽出來時還不沾血,不太痛,只是要了你的命。
來來去去,都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一開口,我便又哭了。
傷心欲絕,抱著他哭得毫無矜持。
太可悲,到如今,要哭的時候,我還只能抱著他。一邊尊嚴喪盡,一邊還要問,「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明白。」
這樣的悲情鏡頭,在我和安燃之間演到爛了,沒能感動安燃,反傷盡了我自己。安燃聽著我問,一成不變的沉默,任我抱著他,揮霍此生眼淚。
我知道他不會答,每逢這時,開口的只有我而已。
他寶劍已經出鞘,功成身退,剩下的,只能我孤零零演繹。
抱著他,哭給自己聽,問給自己聽。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我什麼都願意,為什麼還是死路一條?」
「應該怎麼做?你教我,安燃。」「為什麼?為什麼變成如今這樣?我不明白,死也不明白。」
我問多久,安燃就沉默多久。
等我哭夠問夠,不做聲了,安燃才反抱了我,反問了那麼一句話。
他問,「君悅,為什麼你不明白?」
匪夷所思。
他說什麼毒辣的話,都不會比這句更讓我怔住。
我怔住,怔在他如鐵鑄的懷裡。
不曾料到,我問過之後,他罕見地接過了戲份。
緊抱著我,語氣低沉。
「為什麼你不懂?」
「為什麼你總不明白?」
「君悅,什麼時候,你才能明白?」
一聲,一聲,再一聲。
比我的更令人心痛,更令人絕望。
我怔得徹底,簡直痴了,心底明白安燃真是常勝將軍,無人可敵,輕輕一個反擊,何君悅什麼鬥志都被瓦解了。
我愣了半天,心中剩下的都是灰色,輕飄飄,卻仍會不忍。最終只是索然歎氣,不知第多少次舉手投降,閉上眼說,「安燃,你要做就做。」
做吧。
不要哭了。
再不要哭了。
我投降,服了。
以為肉體折磨可怕的人,其實是因為未受過精神折磨。
本希望得一個喘息,不用見識安燃的體能極限,後來才知道,頑抗得來的下場,還不如早點讓安燃如願以償。
可惜,我後悔的又遲了。
當安燃要做的時候,我沒有讓他盡興;當我企圖讓他盡興的時候,他也理所當然沒讓我得逞。
我放鬆身體,他反而抱得我更緊。
鐵臂收勒,很用力。
我忍著,希望那傳過來的顫慄只是因為用力,而不是因為他真的在顫慄。
兩個大男人,我抱著他哭,已經很可笑;他抱著我哭,只能更可笑。
太不可思議,局勢莫名其妙逆轉,前一秒還算正常,下一秒,那心平氣和的角色就忽然落我頭上了。
我半帶驚惶,餘下一半,也只有盡量心平氣和,低聲問這個幾乎把我勒到無法呼吸,又絕望到令人心痛的男人,「安燃,你幹什麼?」
安燃久久不回答。
秒針從容移動,夜仍深沉。
他不回答,我便一同沉默。
雖然不好受,但剎那間,會有那麼一絲希望時光永存此刻的奢望閃過心頭。因為他抱得好緊,彷彿懷裡的極珍貴,生怕失去。
如果我是一件瓷器,會希望被他用臂力勒碎在胸前。
但,安燃不是我,他當然不會哭著睡去。
沉默夠了,他終於說話。
「君悅,」他把臉埋在我頸窩,慢慢說,「我不想活。」
這麼一句,驚出我一身冷汗。
我受驚地問,「安燃,你說什麼?」
沒道理,太沒道理。
我這個被搓圓按扁的尚且沒死透,你這個高高在上的反而不想活?
什麼天理?
他不回答,我迫切追問,「為什麼?安燃,你說清楚。」
若不是他依然體重驚人,臂力驚人,勒得我透不過氣來,我說不定已經拽起他的衣領,盯著他的眼睛。
很無奈,如今卻要當個忍氣吞聲的抱枕,還一邊追問為什麼。
安燃在我頸窩裡喃喃,「太艱難,太絕望……」
我追問,「什麼艱難?什麼東西絕望?」
你比誰艱難?
你比我還活得絕望?
我真憤怒。
我還是問那一句,「為什麼?」
安燃長歎,回答一句,「我一無所有。」
我啼笑皆非。
虧他那麼認真感歎,說的卻是個彌天大謊。
我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要安慰他,笨拙得如獵物反去安慰獵人,竟然真心實意,「安燃,你怎會一無所有,今非昔比,你什麼都得到了,應該知足。」
很快我就發現,這句安慰是我今夜犯的最大錯誤。
話一出口,那個脆弱得不想活的男人就消失了。
安燃變身的速度,快得好可怕。
我才心裡微覺不妥,已聽見安燃不屑的嗤笑。
他冷笑的聲音令人難受,笑著,有趣地問我,「你真這麼想?」
不等我回答,他吐出一聲「好」,然後說,「君悅,不妨讓你像我一樣,什麼都得到。」
最後,加一句鋒刃似的祝福,「希望你比我知足。」
聽他那語氣,我就知道又一次的大事不好。
但不好在什麼地方,卻猜不出來。
玄機未露,空琢磨,反正琢磨不出來。
只能先睡了。
次日,我被阿旗禮貌的叫醒。睜開眼,安燃已經不在屋內。安大公子自由來去,沒人有資格過問,我更不會自取禍端,便在床上睡眼惺忪,看著阿旗。
阿旗說,「君悅少爺,安老大吩咐,你今天可以去娛樂中心上班,那邊各級主管已接到通知。君悅少爺到了之後,會議就開始。」
昨晚不知道究竟幾點才入睡,任誰像我這樣一夜又驚又嚇還要傷心,都會精神不濟。
何況,還消耗了大量體力。
阿旗說的,我勉強聽得明白,回應起來卻不容易。人未醒時大腦最難使喚,我挨在枕旁,看他半天,才迷糊問了一句頗關鍵的,「安燃有規定幾點必須到嗎?」
阿旗一絲不苟地答,「沒有。」
好答案。
我放心下來,倦意湧上,倒下繼續大睡。
這一覺無夢,倒是睡得不錯。肆意睡夠了,才有精力生出些許懼意,想起安燃那個惡魔般的脾氣,除非萬不得已,不可招惹,我勉強自己醒來,爬起,收拾自己。
打開門,發現阿旗領著幾個西裝筆挺的男人,似乎一直等在外面。
若論耐性,阿旗在黑道中真是難得的,難怪安燃看得上他。
明明在走廊上等了大半日,他那臉色卻正常到如我按時赴約,讓開一條路,把手一送,「君悅少爺,車已經準備好。」
我點頭。
一車送到娛樂中心,又是前呼後擁呼嘯入門。
這次身邊少了安燃,四面八方更多注視自然集中在我身上。
對這樣張狂的出場,我只能無可奈何,恨不得從哪翻出幾張白紙,上書淋漓兩個大字──獄卒,貼在這些冒牌保鑣額上。
阿旗輕車熟路,領著我們一干人等招招搖搖,直上最高層。
到了樓層,合金門兩扇左右打開,水晶燈的反射光芒迎面撲來,璀璨得令人呼吸一窒。
「君悅少爺來了。」
在門前那麼一停,才看清一屋子的人。
很多是生面孔,高矮肥瘦不一,不過眼神氣度都算不錯,看我來了,個個肅然起立。
林信儼然也在其中。
我真不得不愕然。
安燃不愧是安燃,連玩個遊戲,手筆也夠大。遊樂場之後,索性丟出個娛樂中心。
這梟雄如此有魄力,江山多嬌,鬥爭激烈,理應忙到不堪。他哪來那麼多餘的心機,一點也不吝嗇,通通花在對付我上頭?
我冷冷環視這一屋子人。
林信看來是裡頭頗有地位的,率先打破僵局,問我,「會議可以開始了嗎?」
我問,「你們在等我?」
林信說,「對,從今天早上八點正開始。」
我了然。
怪不得滿屋怨氣。
原來我這個新官懵懂一覺,已經燒了第一把火。不用說,這裡十個人裡面,十個都會認為我姍姍來遲,是在施下馬威。
真是個無可解釋的誤會。
但這威下都已經下了,只能硬著頭皮繼續。
我領著阿旗一干獄卒進門,起碼看起來威風凜凜,穿過站立的眾人,順理成章坐在大書桌後面。
背靠椅上,擺個子勢,輕描淡寫,「大家坐,開會吧。」
什麼都是裝的,只有那輕描淡寫不是。
反正只是個擺設、事不關己,要緊張也輪不到我。
會議開始,林信自動自覺當了主持。大家輪流發言,一切很有順序。
我恪守本分,在書桌前托著半邊腮,扮做思考,為免單調,偶爾還點個頭,發個模糊的單音。
若有人侃侃而談到一半,用詢問的目光看向我,我就說五個字萬無一失的字,「我在聽,繼續。」
聽什麼?真可笑。
供應商資金流云云,我壓根不懂。他們說得越專業,君悅少爺我越雲裡霧裡,那些老成持重的建議,用盡心力組織的詞句,對我的意義還不如一首三流KTV。
左耳入右耳出,我倒是略有餘力觀察林信。
機會難得,安燃不在,又是會議這樣冠冕堂皇的場合,林信這個主持會議的就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翹著二郎腿,在眾人間居中調和,主導氣氛。
他真的長大了,那般駕輕就熟。
我打量他半天,找不到當初的影子,那些癲狂放肆的色彩呢?那些醉酒當歌無病呻吟的幼稚呢?全不見。
人人都會變,變得我根本不認得。
阿旗在旁邊提醒一聲,「君悅少爺。」
我才低頭去看送到眼前的厚厚大本,翻一翻,前面每頁都用端正筆跡記得密密麻麻。
一邊亂翻,我一邊忍著笑。
大哥如果在天有靈,此刻應該也會哈哈大笑。
何君悅端坐桌前,認真翻看大帳本的鏡頭,怎麼想像,怎麼滑稽。
別人不知道我底細,林信是知道的。但偏偏是他,站在我桌前,等候我翻得差不多,還那麼沉著地問上一句,「君悅,覺得怎樣?」
他真不該問。
我已經忍得很辛苦,被他語氣認真地一問,頓時情不自禁,笑出聲來。
雖然只有一聲,但想必人人都已聽見。
屋裡這群西裝革履的管理級精英,個個目光聚焦,都定在我身上。
我總不能學他們一樣盯著自己,只有抬頭,去盯林信,唇邊還帶著方才殘餘的一絲苦笑。
林信反應敏捷得令我吃驚,一接觸我的視線,立即點頭,「是,我明白了。」
我自己都懵了。
明白什麼?我自己都沒弄明白。
林信轉過身,指了一人出來,純熟地發出指使,「帳本再重頭對一次。」
只聽見連聲應是,一個陌生人到我桌前,半彎腰,雙手取下面前的帳本,迅速退下去。
我恍然,心底大歎,繼而大樂。
於是,枯燥的會議忽然充滿樂趣,這是我開始絕沒想到的。
安燃是個天才,林信原來也不遜色。
我每個莫名其妙的表情,小動作,都能被他解釋成某個充滿玄機的決定,他一解釋,就立即有人領命執行,效率之高,配合之精密,令人歎為觀止。
這齣好戲,我看得不亦樂乎,邊演邊看,可惜後來得意忘形,伸了個過於愜意的懶腰,林信便不打招呼奏響了結束音樂,宣布,「說的夠多了,會議結束,都去幹活吧。」
眾人收拾文件,肅然而去,腳步匆忙。
好戲落幕,一屋人氣散去九成。
安靜了幾分鐘,我才確定真的曲終人散。
打個哈欠,懶懶趴下,伏在書桌,下巴墊在手臂上,看著面前的林信,有趣地笑。
林信並不配合,筆直地站在書桌前,低頭和我對視半天,才說,「君悅,你還是老樣子。」
我問,「嗯?」
林信用八個字給我的老樣子下評斷,「不學無術,無責任心。」
我放聲大笑,不可自抑。
世界真奇妙,可以毫無預兆,某日忽然把所有人都變得面目全非,面孔翻轉過來,你才糊裡糊塗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千夫所指,罪惡根源。
林信冷眼看我大笑,半日,才搖頭,「你還笑?」
我奇怪了,問他,「我不笑?難道要哭?」
哭本來也沒什麼。
不過我的眼淚,已經通通給了安燃,哪裡還有多餘的留給林信?
林信說我不學無術,無責任心。
安燃怎麼說的?對,頑劣不堪,冥頑不靈,不可救藥。
都說了不可救藥,林信又能奈我何?他也就只能歎氣,搖頭,退回沙發,收拾他帶來的文件。
我看著他彎腰的背影,忽然問,「你走了?」
他甚至懶得回頭,冷冷說,「我並不是你,總要做點事。」
好深明大義的回答,正氣凜然。
不用說,一定是安燃調教出來的。
走了林信,我更加無聊。
辦公室後面整牆的落地玻璃,不放下窗簾時,能直接看到下方的賭場。我發呆地看了半日,被阿旗喚醒過來。
阿旗問,「君悅少爺,餓嗎?想吃點什麼?」
我驚訝,「可以點餐?」
阿旗點頭,「當然,怎麼會不可以?」
那神情,一貫的充滿欺騙性,彷彿我從來就擁有這項權利,從前被逼著吃光指定食物的日子都是作夢。
不過,這怎麼說,也畢竟是一項恩賜。
如果可以一直恩賜下去,我倒是寧願跪下三呼萬歲,真心實意謝主隆恩的。
我問,「有什麼選擇?」
阿旗型的敏捷再現,立即不知從哪裡變出一迭菜單。菜單各種各樣,設計十分錆美,一看就知道檔次不錯。泰國菜、法國菜、中餐、義大利菜、印度菜……各國美食俱備,不但有娛樂中心內設餐廳的點菜單,恐怕這附近可以送餐的高級餐廳都在其中。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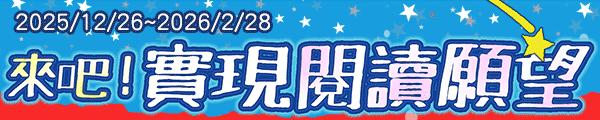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