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如易 第肆卷 天下易得,成敗誰何(1)
是誰重傷了景塵卻存心留他一命?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新唐遺玉》作者三月果歷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大作!
奇門遁甲這類學問在此時代竟有如此大用?
且看小女子余舒如何運用精算師頭腦配合易學,谷底翻身、出人頭地!
上輩子,她昧著良心賺錢;
這一世,她要活得乾淨自在!
在水陸大會上一舉挽回大安易師名譽,深獲聖心的余舒,
頂著御賜「淼靈使者」的封號,可謂是順風順水,
然她身為坤翎局女御,現不光是前朝的官員們搶著巴結,
後宮的妃嬪們也坐不住了。
為了侍寢一事,眾妃們輪番召見,
後宮裡的心機城府,向來不比朝堂遜色。
而余舒雖事事處理得宜,但背後的隱患仍在──
針對景塵,尋找破命人並殺害無辜的幕後主使。
是誰意圖阻撓當今皇上與司天監?
是誰重傷了景塵卻存心留他一命?
余舒與正查辦湛雪元命案的薛睿層層推敲,
這個既不想殺害景塵,又想盡辦法從中破壞的人,
莫非,竟是二十年前「已故」的那位……?!
本書另收錄未公開番外〈前世〉
試閱
第一章
安頓好辛瀝山,余舒心事重重地回到房間,吩咐門外侍婢誰都不許打擾,在書房暗處找出上次她為辛酉先生推算死期的記錄,翻來覆去地確認了幾遍。
這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辛家父子要她卜算之人的生辰八字絲毫不差。
眾所周知,雲華易子是在麓月長公主病逝之後,為妻殉情,余舒從辛瀝山那裡套了不少話,當年對外人稱,麓月是在誕下景塵之後,不到半個月就撒手人寰,雲華緊隨其後,死於寶太十三年的四月之後。而辛雅告訴她,辛酉先生的死期大概是在二月份到五月份之間,他聽到死訊,也是在四月之後。
父子兩人的說法不謀而合,很顯然,雲華易子就是辛酉先生不會錯。
再來看她的推算——辛酉先生在寶太十三年遇到兩件禍事。
第一件,是二月裡,一場火災,可是他活了下來,沒有於此喪命。
第二件,是五月初,喪親之痛,他死了一個親人,這個親人,無疑就是他的妻子,麓月長公主了。
在世人眼中,雲華已經是死去多年的傳說,他的死期倒也是個特殊的日子,五月初五,端午節。然而余舒計算到這一天,卻沒發現丁點禍事,毫無死到臨頭的預兆,顯然雲華是「假死」的。
可是所有人都以為他是真的死了,不管是覺得他是被害的,還是覺得他是殉情的。
她極力去揣測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她猜雲華是在那場火災之後就失蹤了,所以辛雅說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二月。她猜雲華失蹤以後,皇室中人找不到他,就在麓月長公主死後,編造了他殉情的假象,讓他「死」去了。
那麼雲華現在還活著嗎?
余舒不敢肯定,只有等她用禍時法則為他卜算出這二十年的禍事,才能確認,他是生是死。
「二十年,這可不是一天兩天能算清楚的,至少得費上半個月的工夫。」余舒發愁地揉了揉額頭,忽然手指一頓,猛地睜開眼睛,面露喜色。「對了,可以用六爻啊!」
六爻術是不能斷生死的,但是六爻有一篇吉凶,可以用子女的生辰八字,來應克父母的身體康泰與否,爻眼只需取得父母的生辰八字即可。
景塵的生辰八字,早在他恢復記憶之後,她就問過了,現在又得知了雲華的八字,只要她卜一卦吉凶,算景塵父母如何,麓月公主已經去世了,若不成卦,就證明他雙親皆亡故,若是成卦,豈不證明雲華還活著!
余舒說做就做,興匆匆地從書櫃的暗格裡取出小青爐和醍醐香。
下午,向郭槐安回稟了太史書苑新出的人命案的調查進展之後,薛睿獨自走出大理寺。頭頂的太陽,照得人頭腳發昏,巡邏的護衛早就汗流浹背了,薛睿慢慢搖著手中的慕江扇,倒不覺得熱。
此時他腦子裡想的卻不是案情,而是郭槐安剛才對他說的那幾句題外話——「剛好趕上這起命案,水陸大會那兩天你沒能來,聽說了司天監的余女官被聖上封做淼靈使者的事嗎?那一天倒真把我這老頭子給驚著了,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能親眼看到凡人呼風喚雨的法術,你這位義妹的本事真能通天了。」
薛睿確是還沒聽說余舒被賜封號的消息,他這兩天都泡在太史書苑查案,家都沒回去,壓根不知道余舒不聲不響地出了這樣的風頭。
讓他都吃了一驚。
驚訝過後,便是深思。
薛睿敢說除了余舒本人,他是最清楚她底細的一個,什麼呼風喚雨,她會不會用,他還不清楚嗎?
料想與斷死奇術一樣,都是她投機取巧擺出來的陣仗。而迫使她急於「表現」的誘因,大概就是湛雪元的慘死吧。
「唉。」薛睿輕嘆一聲,闔上扇頁,抵了抵額頭,他就知道她不會「安分守己」地等著他出謀劃策。可才幾天不見,她就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當真是雷厲風行,讓他既放心,又不安心啊。
◎
薛睿回到忘機樓,聽說後院來了「客人」,沒去叨擾,在樓底下換了便服,便上二樓去。
一進門,就看到坐在客廳裡端著茶盅發愣的余舒,不由停下腳步,打量起她。大概是思慮過重了,她這兩天分明瘦減,杏色的綢衫服貼著腰肩,越發襯得人從頭到腳的清顯,那張素淨得不見多少女色的臉龐,總有用不完的精神,即便是發呆,也不會渙散。
等余舒回過神來發現門口的薛睿,他已不知站在那裡看了她多久,眼神那樣的專注,叫她頓時不好意思起來。
「咳,大哥回來了。」余舒清清嗓子,站了起來,挪了挪發麻的腿腳,又坐了回去。
薛睿幾步來到她身邊,收起扇子,坐在她對面。「昨晚沒睡好嗎?」
余舒搖搖頭。
薛睿抬起手指從她眼下掠過,道:「眼睛都是紅的,還說沒有。」
余舒笑笑,道:「不是熬夜鬧的,剛才香熏著了,不礙事。」
薛睿鼻翼翕動,挑起眉:「妳用了醍醐香?」
「你好靈的鼻子。」余舒抬起袖子聞了聞,是有一點味道,只是兩人隔著幾尺遠,他這都能聞見。
她哪裡清楚,薛睿從小被薛凌南親自撫養,學的可不只是心性謀略,為防薛家的長子嫡孫被人暗害了,薛凌南的教育,可謂是方方面面。香料藥草,該是什麼味道,不該是什麼味道,薛睿聞過一次,便會記在心裡。
「何事需要用到六爻卜算?」薛睿疑問。
余舒兩手交與腹間,眼神變幻:「上午我到辛府去拜訪,門前大街上你猜我遇見了誰?」
薛睿搖頭道:「聽說妳帶了個人回來,在客房歇著。」
「是辛家那位被逐出門的五老爺,兩榜魁首辛瀝山。」
「嗯?」薛睿一聽便有蹊蹺,身體微向前傾,兩眼盯著她:「怎麼回事?」
余舒嘴唇嚅動了兩下,忽地站身,上前關嚴了房門,回到座位上,咬著牙低聲告訴他:「大哥,我說了你別太驚訝,我算出來,我那無緣見面的大師兄,雲華易子他還好端端的活著呢。」
余舒將辛家父子分別拜託她卜算雲華之死一事,細說給薛睿聽。
薛睿的反應與其說是驚訝,倒不如說是迷茫,「原來他還活著麼。」
「不會錯的,我用景塵的八字算了三遍,卦象上都是同一個結果,麓月長公主二十年前就過世了,要是雲華也死了,那六爻根本就不成卦。」
余舒說完,半晌不見薛睿回話,看著他飄忽不定的眼神,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大哥?你在想什麼。」
薛睿收起了跑遠的思緒,對她道:「我有些猜疑,尚不能確認,暫不與妳說了。」
余舒沒所謂地點點頭,又接著方才的話,有些高興道:「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雲華是我大師兄,他當年進京的目的想來與我一致,都是為了毀掉《玄女六壬書》,只是不知他如今藏身在何處,不然我們找到他,便能問個清楚。」
薛睿看著她,問道:「這件事,妳打算和景塵說嗎?」
余舒之前倒沒想過這個問題,稍加思索,輕輕點了下頭,「我約了他今天晚上到忘機樓來,到時候就告訴他。」
薛睿慢吞吞地說道:「景塵聽到這個消息,想必會是個驚喜吧。」
余舒道:「我告訴他,卻不是為了要給他什麼驚喜。只當還報了他未對我隱瞞破命人一事,況且——雲華是景塵的生父,是他至親,他有理由知道他爹還活著,而我身為知情者,有什麼資格瞞著他呢。」
薛睿眼色深了幾許,自言自語:「他有理由知道麼……」
「怎麼,你覺得不妥嗎?」
薛睿搖頭:「告訴他也好,讓他知道雲華易子當年『死』得蹊蹺,他便不會一味地聽從那一邊的安排,叫他疑心越重越好。」
余舒忽就想到昨天早上,在坤翎局,景塵向她保證的話,猶豫了來回,沒有在薛睿面前提起。無關乎她信與不信景塵的保證,而是覺得在現任相好面前,嚼前任男友的舌根,是件蠢事。
同薛睿分享了這個驚人的發現,余舒也從雲華活著的倉皇中冷靜下來,有了心情說及其他:「大哥可是聽說了我在水陸大會上的英勇。」
薛睿一笑,「妳是指妳扯了皇上的虎皮,糊弄了一群人的事嗎?」
「什麼糊弄,我那是真才實學。」余舒嘟囔一聲,卻沒多少底氣,薛睿最清楚她底細,信了她真能呼風喚雨才有鬼。
「妳也真夠膽大。」薛睿操心道:「騙人都騙到皇上跟前了,就不怕日後騎虎難下嗎?若是逢上乾旱,皇上派妳到地方上去降雨,妳待如何?」
余舒又得意起來:「我早想好了,所以當天就告訴了他們,我這本事用起來是要夭壽的,不能保證回回都靈。」
薛睿這才放了心,抬手在她額上輕彈一記,輕聲笑道:「算妳狡猾。」
◎
傍晚的時候,景塵來了。
余舒聽夥計稟報辛瀝山還在屋裡呼呼大睡,為免他醒過來同景塵撞見了,事先派了貴八在辛瀝山門外頭守著。
小晴將景塵帶上了略顯冷清的三樓,余舒和薛睿正在茶廳等著。
茶座兩旁立著兩盞青瓷長燈,照亮一室。
景塵看到一襲竹色長衫,閒適在座的薛睿,腳步在門前停住了,表情有些困頓地看向了余舒。
薛睿闔上茶蓋,起身道:「景兄請進,今天是薛某人要見你,有事相商。」
景塵看著余舒在燈下淡淡的臉色,眸光明滅,舉步而入。侍婢在他身後將門掩上了。
三人同處一室,空氣中流動著一股詭怪的靜謐,最先打破沉寂的卻是景塵:「我與你的事,你全都告訴他了嗎?」
這句話問的當然是余舒,他話裡沒有責問的意思,眼神卻一動不動地望著她。
余舒沉默了一下,正要開口作答,就聽身側說話:「你若是指大安禍子與破命人的話,我都知道了。」
景塵這才將目光轉向薛睿,看著這個總在余舒身邊出現的男人,心中有些說不出來的滋味。他知道這種感覺,是因為許多本該是他來做的事情——陪伴她,保護她,不讓她被人欺負,他沒能做到,卻被眼前這個人做了。
薛睿坦率地對上景塵的目光,曾幾何時,他羨慕過這個人,他的身世或許比自己還要不幸一些,但是他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值得付出的人,可惜的是,他沒能珍重,錯過了她。
「你今日找我前來,想說什麼?」
「恕我直言。」薛睿收起了客套,聲音冷下來:「景兄高義,能為大安社稷以身作則,薛某佩服。景兄良善,為報答師門養育之恩,忍辱負重,薛某理解。可是敢問景兄,我義妹對你有何虧欠,讓你不顧惜她性命,擅自將她捲入危局。」
這番話,他早就想當面質問景塵,憑什麼他想要恩斷義絕就可以一刀兩斷,他想要重歸舊好,就以為余舒應該乖乖就範。哪怕他的理由再是冠冕堂皇,也掩蓋不了利用的本質。
男人總有這樣自以為是的弊病,以為他們可以決定一切,一個自私的男人,要比一個自私的女人,更加獨斷。
看到景塵,就讓他聯想到三年前的自己,一心求娶十公主,卻未考慮過她人是否情願,最終落得一個不可挽回的下場。同樣身為男人,薛睿不以為自己有資格責備景塵,但是身為余舒的男人,他不能容忍景塵的覬覦之心。
「還是景兄真的天真地以為,只要阿舒答應了與你成婚生子,就相安無事了嗎?」
景塵饒是習慣了余舒的冷言冷語,面對薛睿的直言不諱,還是覺得有些刺耳。一直以來他想要自欺欺人的東西,反倒越發的清晰了。
在皇陵墓底的那一日,他不是沒有疑慮,可他還是選擇了相信大提點的話,告訴了他破命人是誰,除卻恩情與大義,他私心裡,到底是歡喜那個人就是小魚。他歡喜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好與她重新在一起。
「她沒有虧欠我什麼,是我對不起她。」
「你沒有對不起我,我說過的,你與我兩清了。」余舒的聲音毫無起伏,她早過了憤怒與不甘的時期,現在的景塵對她來說,不再是朋友,卻也不是敵人。
景塵聞言,只是轉頭看她,俊逸的臉上並未流露太多的情緒。
薛睿見狀,點到即止,沒有再咄咄逼人下去,而是話題一轉,帶到了太史書苑的命案上頭:「殺害湛雪元的凶手尚未確認,很顯然那些人的目的是在針對身為大安禍子的你,所以與你親近的女子,才會被殃及,恐怕對方下一個目標就是阿舒,為了她的安全著想,我想麻煩景兄一件事。」
「何事,你講。」
「近日聖上或許會加派人手保護阿舒,若是他們在你面前提起,我希望你能代阿舒拒絕。至於藉口,我已幫你想好了,就說阿舒會用斷死奇術,並無性命之虞,你也會從旁保護,不必多此一舉。」
本來薛睿要請景塵合作的不是這件事——湛雪元一死,他怕皇上不顧余舒死活,提前安排景塵與她的婚事,先利用她破命。所以他原先是要提醒景塵不要答應他們的婚事,拖延下去。但是現在情況又有了轉機,余舒在水陸大會上的表現,讓兆慶帝重估了她的分量,一個御賜的封號就說明了問題。
他們不會著急讓余舒去送命,相反的,會加派人手保護她的安
全。
「我不懂。」景塵蹙眉,「為何要拒絕?」
余舒同樣不懂薛睿這是為什麼,多幾個人保護她的小命不是件好事嗎?
但是她沒有提出質疑,她相信薛睿這樣要求,一定有他的原因。
薛睿很快就給出了這個原因:「歷來大安國君都有一支秘而不宣的親衛,隨行護駕,不受軍部調遣,人員不過數十,但論及武功,當中不乏有人能與景兄一較高低,且他們極擅隱匿,忠心不二。所以我大安開國至今,雖多有行刺之事,卻從無一起得手的先例。若我猜的不錯,皇上這次要加派人手暗中保護阿舒,一定會從這些親衛當中撥人。」薛睿說著,看了一眼余舒,道:「妳若不想吃飯睡覺如廁都有人盯著,將妳的一舉一動彙報給皇上聽,最好還是拒絕。」
余舒身上的秘密太多,隨便一個洩露出來,都夠她掉腦袋的。
這些親衛對她來說不是保護符,而是催命符。
余舒臉色變了變,不自覺地換了個姿勢,看向景塵,那臉色擺明了就是抗拒。
景塵低頭想了想,道:「好,我會留意,不論皇上與大提點是否對我提起,一旦我發現她身邊有高手監視,便會出面阻攔。」
「最好如此。」
薛睿言盡於此,轉頭對余舒道:「妳不是有事要告訴景兄嗎?」
余舒沒想到這麼快就輪到她了,深吸了一口氣,兩眼看向被蒙蔽了十幾年的景塵,心中不禁跑出來一些憐憫,聲音不自覺地壓低:「雲華易子,也就是令尊,他尚在人世。」
余舒沒對景塵細講辛家父子的事,只將一切推到了「斷死奇術」上。
「我無意間得知了雲華易子的生辰八字,以斷死奇術卜後,發現他還活著,我反覆算過幾遍,不會出錯。」
景塵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面有怔忡,整個人似乎凝固了,余舒後面的解釋,不知他聽沒聽進去。
余舒可以想像到他所受到的衝擊,從小到大就知道自己是個「禍胎」,身邊的所有人都告訴他,父母都是被他的計都星「剋」死的。就這樣在自責中長大的人,孤零零地活了將近二十年,突然有一天被人告知他爹還好好的活著,想必一時間不能接受。
余舒扭過頭去,想和薛睿對個眼色,卻見他看著景塵一臉思索,不知在想什麼。
半晌過去,景塵才開口,壓抑的聲音帶著一抹沙啞:「多謝妳告訴我。」
按說這是個往兆慶帝和大提點身上潑髒水的好機會,可余舒見到他這副倍受打擊的模樣,嘴唇動了動,話到嘴邊就變成了:「不必,你不懷疑我是騙你的就好。」
景塵搖了搖頭,按著扶手站起來,「恕我不便久留,先告辭了。」
余舒點點頭,轉頭看了一眼薛睿,猶豫後,起身道:「我送你到門口。」
「景兄慢走。」薛睿坐著沒動,目送著他們兩個出去了。
從三樓下來,到樓梯轉角處,景塵突然站住,也沒回頭,低聲道:「他們為何一個個都要騙我呢。」
他從幼至今所聞所見,究竟還有什麼是真的。
余舒不知怎麼回答,饒是她心裡裝的那個人不再是他,卻也不禁替他難過。「或許是為了達到某些目的,也或許是有什麼苦衷。」
「……」
前面樓階下那個人背影落寞極了,余舒抬起手,方要落到他肩上,一頓又放下,她不大會安慰人,勉強找出一句話:「不論如何,他人還活著,不是件好事嗎?」
「呵,是啊。」一聲若有似無地輕笑,景塵回過頭,神色不明地望著她:「至少他活著不是嗎。」
◎
余舒送了景塵回到院中,一抬頭便看到立在一樓走廊下面等著她的薛睿,腳下不由快了幾步走上去。
「人走了嗎?」
「嗯,走了。」
薛睿伸出手來,牽住了她略顯冰涼的手掌,輕輕一握,轉身拉著她進屋。
「妳原諒他了麼?」
「啊?」
「阿舒,不要裝傻。」
「景塵他,其實很可憐。」
「嗯,我也這樣覺得。」
兩人相攜的身形消失在了闔起的房門後。
◎
水陸大會過後,拜帖像是雪花一樣飄進了余舒家的大門,有些人不知從哪兒打聽到余舒的新宅子建在寶昌街上,兩頭圍堵,一天到晚都有人登門求見。
余舒有了上回在芙蓉宴出名的經驗,一早就吩咐了兩府,帖子收著,禮也收著,客人們都請進來喝茶,問起她,就說不在家。
可是她東躲西躲,躲不過一些奇葩。
這不,這一天,她天不亮就出了門,卻在自家大門口被攔了路,不知從哪兒衝出來兩道人影,撲通兩聲就給她跪下了,要不是陸鴻和徐青眼快攔在她身前,非撞到她腳底下。
「小生周民,仰慕余先生已久,願拜您為師,求您不嫌收下,日後定當奉恩師為再生父母,孝順您老人家。」
「弟子王生,祖上三代學易,吃得苦耐得勞,求請淼靈使者收我為徒,弟子定然勤苦向學,傳您衣缽,發揚光大。」
余舒額頭上冒出來兩條黑線,心說這打哪兒來的兩個不要臉的,那個年紀看著都有三十了,還敢說要給她當兒子,還有那個祖上三代學易的,誰要他繼承衣缽啊!
陸鴻和徐青顯然也是頭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不知如何處理,扭頭看向余舒,等她發話。
「咳咳,二位起來吧,家師有令,不許我收徒的。」
兩人面面相覷,猶不死心——
「那記名弟子呢?」
「那您認乾兒子嗎?」
◎
好不容易打發了那兩個不要臉的,余舒來到司天監,已是天白大亮了,差點沒趕上點卯。
從進大門起,便不斷有人熱情地與她問候,還有個別臉皮厚的,從鐘樓底下,一路攀談到了坤翎局樓外面,才意猶未盡地離開了。
余舒擦了把虛汗,進門就坐下了,謝蘭眼明手快地奉了一杯茶,立在她跟前道:「大人今天是出門晚了嗎,不必急的,下回您來得遲了,沒點得上,下官去同會計司的同窗招呼一聲即是。」
「唉,別提了,我本來早早就起來了……」余舒就將早上出門遭堵的事同他說了,末了還有感慨:「得虧我跑得快,不然今天就多了兩個乾兒子了。」
「哈哈。」謝蘭失笑,又給她續了一杯茶,道:「這等癡心妄想之徒,比比皆是,不肯腳踏實地,只想著一步登天呢,大人日後再遇著了,無須給他們好臉色,直接轟了就是。」說罷,又請示她:「您身邊還空著一員佐吏的名額,可是挑好人了?眼瞅著要到月底了,下官緊快補錄上去,還能趕得上這個月發俸。」
余舒道:「有了,我這就修書一封,你派人到太史書苑去找他來吧。」
「是。」
余舒起身走向她辦公的書齋,扭頭掃了一眼樓梯上,問謝蘭:
「右令大人來了嗎?」
「景大人今日請了休,似乎身體不適,早上派人來支應過了。」
「哦。」
安頓好辛瀝山,余舒心事重重地回到房間,吩咐門外侍婢誰都不許打擾,在書房暗處找出上次她為辛酉先生推算死期的記錄,翻來覆去地確認了幾遍。
這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辛家父子要她卜算之人的生辰八字絲毫不差。
眾所周知,雲華易子是在麓月長公主病逝之後,為妻殉情,余舒從辛瀝山那裡套了不少話,當年對外人稱,麓月是在誕下景塵之後,不到半個月就撒手人寰,雲華緊隨其後,死於寶太十三年的四月之後。而辛雅告訴她,辛酉先生的死期大概是在二月份到五月份之間,他聽到死訊,也是在四月之後。
父子兩人的說法不謀而合,很顯然,雲華易子就是辛酉先生不會錯。
再來看她的推算——辛酉先生在寶太十三年遇到兩件禍事。
第一件,是二月裡,一場火災,可是他活了下來,沒有於此喪命。
第二件,是五月初,喪親之痛,他死了一個親人,這個親人,無疑就是他的妻子,麓月長公主了。
在世人眼中,雲華已經是死去多年的傳說,他的死期倒也是個特殊的日子,五月初五,端午節。然而余舒計算到這一天,卻沒發現丁點禍事,毫無死到臨頭的預兆,顯然雲華是「假死」的。
可是所有人都以為他是真的死了,不管是覺得他是被害的,還是覺得他是殉情的。
她極力去揣測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她猜雲華是在那場火災之後就失蹤了,所以辛雅說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二月。她猜雲華失蹤以後,皇室中人找不到他,就在麓月長公主死後,編造了他殉情的假象,讓他「死」去了。
那麼雲華現在還活著嗎?
余舒不敢肯定,只有等她用禍時法則為他卜算出這二十年的禍事,才能確認,他是生是死。
「二十年,這可不是一天兩天能算清楚的,至少得費上半個月的工夫。」余舒發愁地揉了揉額頭,忽然手指一頓,猛地睜開眼睛,面露喜色。「對了,可以用六爻啊!」
六爻術是不能斷生死的,但是六爻有一篇吉凶,可以用子女的生辰八字,來應克父母的身體康泰與否,爻眼只需取得父母的生辰八字即可。
景塵的生辰八字,早在他恢復記憶之後,她就問過了,現在又得知了雲華的八字,只要她卜一卦吉凶,算景塵父母如何,麓月公主已經去世了,若不成卦,就證明他雙親皆亡故,若是成卦,豈不證明雲華還活著!
余舒說做就做,興匆匆地從書櫃的暗格裡取出小青爐和醍醐香。
下午,向郭槐安回稟了太史書苑新出的人命案的調查進展之後,薛睿獨自走出大理寺。頭頂的太陽,照得人頭腳發昏,巡邏的護衛早就汗流浹背了,薛睿慢慢搖著手中的慕江扇,倒不覺得熱。
此時他腦子裡想的卻不是案情,而是郭槐安剛才對他說的那幾句題外話——「剛好趕上這起命案,水陸大會那兩天你沒能來,聽說了司天監的余女官被聖上封做淼靈使者的事嗎?那一天倒真把我這老頭子給驚著了,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能親眼看到凡人呼風喚雨的法術,你這位義妹的本事真能通天了。」
薛睿確是還沒聽說余舒被賜封號的消息,他這兩天都泡在太史書苑查案,家都沒回去,壓根不知道余舒不聲不響地出了這樣的風頭。
讓他都吃了一驚。
驚訝過後,便是深思。
薛睿敢說除了余舒本人,他是最清楚她底細的一個,什麼呼風喚雨,她會不會用,他還不清楚嗎?
料想與斷死奇術一樣,都是她投機取巧擺出來的陣仗。而迫使她急於「表現」的誘因,大概就是湛雪元的慘死吧。
「唉。」薛睿輕嘆一聲,闔上扇頁,抵了抵額頭,他就知道她不會「安分守己」地等著他出謀劃策。可才幾天不見,她就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當真是雷厲風行,讓他既放心,又不安心啊。
◎
薛睿回到忘機樓,聽說後院來了「客人」,沒去叨擾,在樓底下換了便服,便上二樓去。
一進門,就看到坐在客廳裡端著茶盅發愣的余舒,不由停下腳步,打量起她。大概是思慮過重了,她這兩天分明瘦減,杏色的綢衫服貼著腰肩,越發襯得人從頭到腳的清顯,那張素淨得不見多少女色的臉龐,總有用不完的精神,即便是發呆,也不會渙散。
等余舒回過神來發現門口的薛睿,他已不知站在那裡看了她多久,眼神那樣的專注,叫她頓時不好意思起來。
「咳,大哥回來了。」余舒清清嗓子,站了起來,挪了挪發麻的腿腳,又坐了回去。
薛睿幾步來到她身邊,收起扇子,坐在她對面。「昨晚沒睡好嗎?」
余舒搖搖頭。
薛睿抬起手指從她眼下掠過,道:「眼睛都是紅的,還說沒有。」
余舒笑笑,道:「不是熬夜鬧的,剛才香熏著了,不礙事。」
薛睿鼻翼翕動,挑起眉:「妳用了醍醐香?」
「你好靈的鼻子。」余舒抬起袖子聞了聞,是有一點味道,只是兩人隔著幾尺遠,他這都能聞見。
她哪裡清楚,薛睿從小被薛凌南親自撫養,學的可不只是心性謀略,為防薛家的長子嫡孫被人暗害了,薛凌南的教育,可謂是方方面面。香料藥草,該是什麼味道,不該是什麼味道,薛睿聞過一次,便會記在心裡。
「何事需要用到六爻卜算?」薛睿疑問。
余舒兩手交與腹間,眼神變幻:「上午我到辛府去拜訪,門前大街上你猜我遇見了誰?」
薛睿搖頭道:「聽說妳帶了個人回來,在客房歇著。」
「是辛家那位被逐出門的五老爺,兩榜魁首辛瀝山。」
「嗯?」薛睿一聽便有蹊蹺,身體微向前傾,兩眼盯著她:「怎麼回事?」
余舒嘴唇嚅動了兩下,忽地站身,上前關嚴了房門,回到座位上,咬著牙低聲告訴他:「大哥,我說了你別太驚訝,我算出來,我那無緣見面的大師兄,雲華易子他還好端端的活著呢。」
余舒將辛家父子分別拜託她卜算雲華之死一事,細說給薛睿聽。
薛睿的反應與其說是驚訝,倒不如說是迷茫,「原來他還活著麼。」
「不會錯的,我用景塵的八字算了三遍,卦象上都是同一個結果,麓月長公主二十年前就過世了,要是雲華也死了,那六爻根本就不成卦。」
余舒說完,半晌不見薛睿回話,看著他飄忽不定的眼神,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大哥?你在想什麼。」
薛睿收起了跑遠的思緒,對她道:「我有些猜疑,尚不能確認,暫不與妳說了。」
余舒沒所謂地點點頭,又接著方才的話,有些高興道:「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雲華是我大師兄,他當年進京的目的想來與我一致,都是為了毀掉《玄女六壬書》,只是不知他如今藏身在何處,不然我們找到他,便能問個清楚。」
薛睿看著她,問道:「這件事,妳打算和景塵說嗎?」
余舒之前倒沒想過這個問題,稍加思索,輕輕點了下頭,「我約了他今天晚上到忘機樓來,到時候就告訴他。」
薛睿慢吞吞地說道:「景塵聽到這個消息,想必會是個驚喜吧。」
余舒道:「我告訴他,卻不是為了要給他什麼驚喜。只當還報了他未對我隱瞞破命人一事,況且——雲華是景塵的生父,是他至親,他有理由知道他爹還活著,而我身為知情者,有什麼資格瞞著他呢。」
薛睿眼色深了幾許,自言自語:「他有理由知道麼……」
「怎麼,你覺得不妥嗎?」
薛睿搖頭:「告訴他也好,讓他知道雲華易子當年『死』得蹊蹺,他便不會一味地聽從那一邊的安排,叫他疑心越重越好。」
余舒忽就想到昨天早上,在坤翎局,景塵向她保證的話,猶豫了來回,沒有在薛睿面前提起。無關乎她信與不信景塵的保證,而是覺得在現任相好面前,嚼前任男友的舌根,是件蠢事。
同薛睿分享了這個驚人的發現,余舒也從雲華活著的倉皇中冷靜下來,有了心情說及其他:「大哥可是聽說了我在水陸大會上的英勇。」
薛睿一笑,「妳是指妳扯了皇上的虎皮,糊弄了一群人的事嗎?」
「什麼糊弄,我那是真才實學。」余舒嘟囔一聲,卻沒多少底氣,薛睿最清楚她底細,信了她真能呼風喚雨才有鬼。
「妳也真夠膽大。」薛睿操心道:「騙人都騙到皇上跟前了,就不怕日後騎虎難下嗎?若是逢上乾旱,皇上派妳到地方上去降雨,妳待如何?」
余舒又得意起來:「我早想好了,所以當天就告訴了他們,我這本事用起來是要夭壽的,不能保證回回都靈。」
薛睿這才放了心,抬手在她額上輕彈一記,輕聲笑道:「算妳狡猾。」
◎
傍晚的時候,景塵來了。
余舒聽夥計稟報辛瀝山還在屋裡呼呼大睡,為免他醒過來同景塵撞見了,事先派了貴八在辛瀝山門外頭守著。
小晴將景塵帶上了略顯冷清的三樓,余舒和薛睿正在茶廳等著。
茶座兩旁立著兩盞青瓷長燈,照亮一室。
景塵看到一襲竹色長衫,閒適在座的薛睿,腳步在門前停住了,表情有些困頓地看向了余舒。
薛睿闔上茶蓋,起身道:「景兄請進,今天是薛某人要見你,有事相商。」
景塵看著余舒在燈下淡淡的臉色,眸光明滅,舉步而入。侍婢在他身後將門掩上了。
三人同處一室,空氣中流動著一股詭怪的靜謐,最先打破沉寂的卻是景塵:「我與你的事,你全都告訴他了嗎?」
這句話問的當然是余舒,他話裡沒有責問的意思,眼神卻一動不動地望著她。
余舒沉默了一下,正要開口作答,就聽身側說話:「你若是指大安禍子與破命人的話,我都知道了。」
景塵這才將目光轉向薛睿,看著這個總在余舒身邊出現的男人,心中有些說不出來的滋味。他知道這種感覺,是因為許多本該是他來做的事情——陪伴她,保護她,不讓她被人欺負,他沒能做到,卻被眼前這個人做了。
薛睿坦率地對上景塵的目光,曾幾何時,他羨慕過這個人,他的身世或許比自己還要不幸一些,但是他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值得付出的人,可惜的是,他沒能珍重,錯過了她。
「你今日找我前來,想說什麼?」
「恕我直言。」薛睿收起了客套,聲音冷下來:「景兄高義,能為大安社稷以身作則,薛某佩服。景兄良善,為報答師門養育之恩,忍辱負重,薛某理解。可是敢問景兄,我義妹對你有何虧欠,讓你不顧惜她性命,擅自將她捲入危局。」
這番話,他早就想當面質問景塵,憑什麼他想要恩斷義絕就可以一刀兩斷,他想要重歸舊好,就以為余舒應該乖乖就範。哪怕他的理由再是冠冕堂皇,也掩蓋不了利用的本質。
男人總有這樣自以為是的弊病,以為他們可以決定一切,一個自私的男人,要比一個自私的女人,更加獨斷。
看到景塵,就讓他聯想到三年前的自己,一心求娶十公主,卻未考慮過她人是否情願,最終落得一個不可挽回的下場。同樣身為男人,薛睿不以為自己有資格責備景塵,但是身為余舒的男人,他不能容忍景塵的覬覦之心。
「還是景兄真的天真地以為,只要阿舒答應了與你成婚生子,就相安無事了嗎?」
景塵饒是習慣了余舒的冷言冷語,面對薛睿的直言不諱,還是覺得有些刺耳。一直以來他想要自欺欺人的東西,反倒越發的清晰了。
在皇陵墓底的那一日,他不是沒有疑慮,可他還是選擇了相信大提點的話,告訴了他破命人是誰,除卻恩情與大義,他私心裡,到底是歡喜那個人就是小魚。他歡喜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好與她重新在一起。
「她沒有虧欠我什麼,是我對不起她。」
「你沒有對不起我,我說過的,你與我兩清了。」余舒的聲音毫無起伏,她早過了憤怒與不甘的時期,現在的景塵對她來說,不再是朋友,卻也不是敵人。
景塵聞言,只是轉頭看她,俊逸的臉上並未流露太多的情緒。
薛睿見狀,點到即止,沒有再咄咄逼人下去,而是話題一轉,帶到了太史書苑的命案上頭:「殺害湛雪元的凶手尚未確認,很顯然那些人的目的是在針對身為大安禍子的你,所以與你親近的女子,才會被殃及,恐怕對方下一個目標就是阿舒,為了她的安全著想,我想麻煩景兄一件事。」
「何事,你講。」
「近日聖上或許會加派人手保護阿舒,若是他們在你面前提起,我希望你能代阿舒拒絕。至於藉口,我已幫你想好了,就說阿舒會用斷死奇術,並無性命之虞,你也會從旁保護,不必多此一舉。」
本來薛睿要請景塵合作的不是這件事——湛雪元一死,他怕皇上不顧余舒死活,提前安排景塵與她的婚事,先利用她破命。所以他原先是要提醒景塵不要答應他們的婚事,拖延下去。但是現在情況又有了轉機,余舒在水陸大會上的表現,讓兆慶帝重估了她的分量,一個御賜的封號就說明了問題。
他們不會著急讓余舒去送命,相反的,會加派人手保護她的安
全。
「我不懂。」景塵蹙眉,「為何要拒絕?」
余舒同樣不懂薛睿這是為什麼,多幾個人保護她的小命不是件好事嗎?
但是她沒有提出質疑,她相信薛睿這樣要求,一定有他的原因。
薛睿很快就給出了這個原因:「歷來大安國君都有一支秘而不宣的親衛,隨行護駕,不受軍部調遣,人員不過數十,但論及武功,當中不乏有人能與景兄一較高低,且他們極擅隱匿,忠心不二。所以我大安開國至今,雖多有行刺之事,卻從無一起得手的先例。若我猜的不錯,皇上這次要加派人手暗中保護阿舒,一定會從這些親衛當中撥人。」薛睿說著,看了一眼余舒,道:「妳若不想吃飯睡覺如廁都有人盯著,將妳的一舉一動彙報給皇上聽,最好還是拒絕。」
余舒身上的秘密太多,隨便一個洩露出來,都夠她掉腦袋的。
這些親衛對她來說不是保護符,而是催命符。
余舒臉色變了變,不自覺地換了個姿勢,看向景塵,那臉色擺明了就是抗拒。
景塵低頭想了想,道:「好,我會留意,不論皇上與大提點是否對我提起,一旦我發現她身邊有高手監視,便會出面阻攔。」
「最好如此。」
薛睿言盡於此,轉頭對余舒道:「妳不是有事要告訴景兄嗎?」
余舒沒想到這麼快就輪到她了,深吸了一口氣,兩眼看向被蒙蔽了十幾年的景塵,心中不禁跑出來一些憐憫,聲音不自覺地壓低:「雲華易子,也就是令尊,他尚在人世。」
余舒沒對景塵細講辛家父子的事,只將一切推到了「斷死奇術」上。
「我無意間得知了雲華易子的生辰八字,以斷死奇術卜後,發現他還活著,我反覆算過幾遍,不會出錯。」
景塵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面有怔忡,整個人似乎凝固了,余舒後面的解釋,不知他聽沒聽進去。
余舒可以想像到他所受到的衝擊,從小到大就知道自己是個「禍胎」,身邊的所有人都告訴他,父母都是被他的計都星「剋」死的。就這樣在自責中長大的人,孤零零地活了將近二十年,突然有一天被人告知他爹還好好的活著,想必一時間不能接受。
余舒扭過頭去,想和薛睿對個眼色,卻見他看著景塵一臉思索,不知在想什麼。
半晌過去,景塵才開口,壓抑的聲音帶著一抹沙啞:「多謝妳告訴我。」
按說這是個往兆慶帝和大提點身上潑髒水的好機會,可余舒見到他這副倍受打擊的模樣,嘴唇動了動,話到嘴邊就變成了:「不必,你不懷疑我是騙你的就好。」
景塵搖了搖頭,按著扶手站起來,「恕我不便久留,先告辭了。」
余舒點點頭,轉頭看了一眼薛睿,猶豫後,起身道:「我送你到門口。」
「景兄慢走。」薛睿坐著沒動,目送著他們兩個出去了。
從三樓下來,到樓梯轉角處,景塵突然站住,也沒回頭,低聲道:「他們為何一個個都要騙我呢。」
他從幼至今所聞所見,究竟還有什麼是真的。
余舒不知怎麼回答,饒是她心裡裝的那個人不再是他,卻也不禁替他難過。「或許是為了達到某些目的,也或許是有什麼苦衷。」
「……」
前面樓階下那個人背影落寞極了,余舒抬起手,方要落到他肩上,一頓又放下,她不大會安慰人,勉強找出一句話:「不論如何,他人還活著,不是件好事嗎?」
「呵,是啊。」一聲若有似無地輕笑,景塵回過頭,神色不明地望著她:「至少他活著不是嗎。」
◎
余舒送了景塵回到院中,一抬頭便看到立在一樓走廊下面等著她的薛睿,腳下不由快了幾步走上去。
「人走了嗎?」
「嗯,走了。」
薛睿伸出手來,牽住了她略顯冰涼的手掌,輕輕一握,轉身拉著她進屋。
「妳原諒他了麼?」
「啊?」
「阿舒,不要裝傻。」
「景塵他,其實很可憐。」
「嗯,我也這樣覺得。」
兩人相攜的身形消失在了闔起的房門後。
◎
水陸大會過後,拜帖像是雪花一樣飄進了余舒家的大門,有些人不知從哪兒打聽到余舒的新宅子建在寶昌街上,兩頭圍堵,一天到晚都有人登門求見。
余舒有了上回在芙蓉宴出名的經驗,一早就吩咐了兩府,帖子收著,禮也收著,客人們都請進來喝茶,問起她,就說不在家。
可是她東躲西躲,躲不過一些奇葩。
這不,這一天,她天不亮就出了門,卻在自家大門口被攔了路,不知從哪兒衝出來兩道人影,撲通兩聲就給她跪下了,要不是陸鴻和徐青眼快攔在她身前,非撞到她腳底下。
「小生周民,仰慕余先生已久,願拜您為師,求您不嫌收下,日後定當奉恩師為再生父母,孝順您老人家。」
「弟子王生,祖上三代學易,吃得苦耐得勞,求請淼靈使者收我為徒,弟子定然勤苦向學,傳您衣缽,發揚光大。」
余舒額頭上冒出來兩條黑線,心說這打哪兒來的兩個不要臉的,那個年紀看著都有三十了,還敢說要給她當兒子,還有那個祖上三代學易的,誰要他繼承衣缽啊!
陸鴻和徐青顯然也是頭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不知如何處理,扭頭看向余舒,等她發話。
「咳咳,二位起來吧,家師有令,不許我收徒的。」
兩人面面相覷,猶不死心——
「那記名弟子呢?」
「那您認乾兒子嗎?」
◎
好不容易打發了那兩個不要臉的,余舒來到司天監,已是天白大亮了,差點沒趕上點卯。
從進大門起,便不斷有人熱情地與她問候,還有個別臉皮厚的,從鐘樓底下,一路攀談到了坤翎局樓外面,才意猶未盡地離開了。
余舒擦了把虛汗,進門就坐下了,謝蘭眼明手快地奉了一杯茶,立在她跟前道:「大人今天是出門晚了嗎,不必急的,下回您來得遲了,沒點得上,下官去同會計司的同窗招呼一聲即是。」
「唉,別提了,我本來早早就起來了……」余舒就將早上出門遭堵的事同他說了,末了還有感慨:「得虧我跑得快,不然今天就多了兩個乾兒子了。」
「哈哈。」謝蘭失笑,又給她續了一杯茶,道:「這等癡心妄想之徒,比比皆是,不肯腳踏實地,只想著一步登天呢,大人日後再遇著了,無須給他們好臉色,直接轟了就是。」說罷,又請示她:「您身邊還空著一員佐吏的名額,可是挑好人了?眼瞅著要到月底了,下官緊快補錄上去,還能趕得上這個月發俸。」
余舒道:「有了,我這就修書一封,你派人到太史書苑去找他來吧。」
「是。」
余舒起身走向她辦公的書齋,扭頭掃了一眼樓梯上,問謝蘭:
「右令大人來了嗎?」
「景大人今日請了休,似乎身體不適,早上派人來支應過了。」
「哦。」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萬事如易 第肆卷 天下易得,成敗誰何(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一卷 福禍易算,人心難卜(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一卷 福禍易算,人心難卜(2)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2)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二卷 善惡易知,是非難說(3)完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三卷 生死易破,情仇難解(1)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三卷 生死易破,情仇難解(2)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一卷 福禍易算,人心難卜(3)完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萬事如易 第三卷 生死易破,情仇難解(3)完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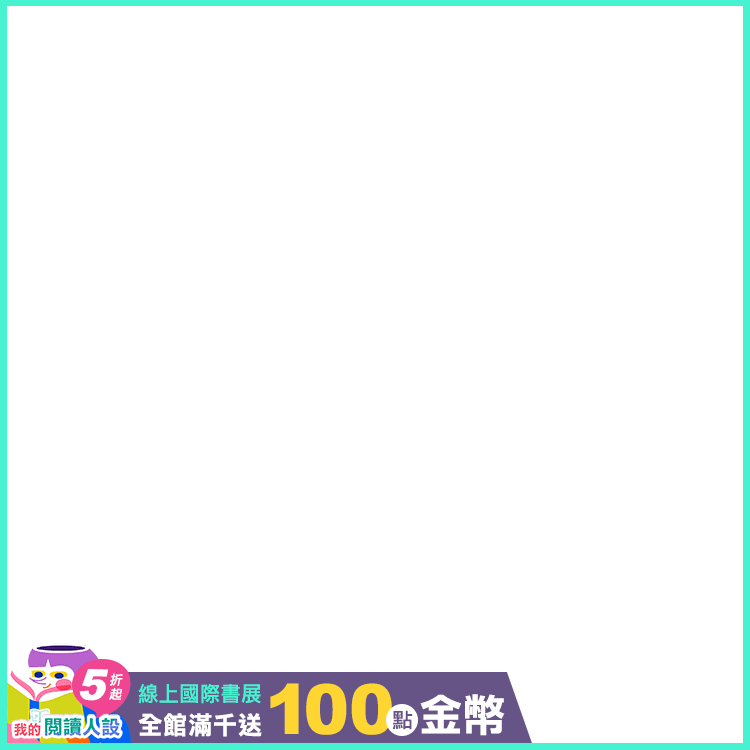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