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探討日本殖民時期東亞文學與文化的跨境交流
為深陷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人文學提供靈感,並建構批判性的亞際史觀
自甲午戰後到冷戰體系形成之前,殖民主義在東亞掀起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與文化混雜,迫使我們至今猶須不斷回溯東亞現代文化生成的種種假設,挖掘東亞內部的文化傳承與變異形態,探討戰爭與變局、體制與資本、中心與邊陲、主體與他者、族群與帝國、語言與翻譯、藝術與互文,如何影響文藝的表現與傳播,又如何形成多維的文學史競合。
《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一書,聚焦於20世紀前半期東亞變局中活躍一時的跨文化流動現象,探討「滿洲國」、台灣、朝鮮、中國淪陷區的文藝生產經驗。此時期的跨文化流動過去分屬各國的文學史範疇,不易被置於一個視野下關注。然而,剛脫離污名化階段的滿洲國文學、淪陷區文學,或者隸屬殖民地文學的台、韓文學,十分有必要置於同一個視野下進行後殖民省思。透過複數文學史的交叉觀察,重新解釋文化殖民現象,尋覓其中的思想資源,有其當代意義。
為深陷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人文學提供靈感,並建構批判性的亞際史觀
自甲午戰後到冷戰體系形成之前,殖民主義在東亞掀起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與文化混雜,迫使我們至今猶須不斷回溯東亞現代文化生成的種種假設,挖掘東亞內部的文化傳承與變異形態,探討戰爭與變局、體制與資本、中心與邊陲、主體與他者、族群與帝國、語言與翻譯、藝術與互文,如何影響文藝的表現與傳播,又如何形成多維的文學史競合。
《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一書,聚焦於20世紀前半期東亞變局中活躍一時的跨文化流動現象,探討「滿洲國」、台灣、朝鮮、中國淪陷區的文藝生產經驗。此時期的跨文化流動過去分屬各國的文學史範疇,不易被置於一個視野下關注。然而,剛脫離污名化階段的滿洲國文學、淪陷區文學,或者隸屬殖民地文學的台、韓文學,十分有必要置於同一個視野下進行後殖民省思。透過複數文學史的交叉觀察,重新解釋文化殖民現象,尋覓其中的思想資源,有其當代意義。
目錄
序一 東亞殖民地文學跨國研究的基石/陳萬益
序二 正確歷史認識的共享/岡田英樹
序三 東亞殖民場文學研究的跨度思維/張泉
序四 滿洲國的研究新視野/施淑
序五 前進的台灣文學/林瑞明
導言 東亞文學場的跨境交流與研究動能
反帝國主義國際主義與解殖文學
全球非殖民化論與東亞殖民地文學研究展望/金在湧
中國淪陷區文藝研究的方法問題──以杜贊奇的「滿洲國」想像為中心/張泉
解殖性內在於殖民地文學──以偽滿洲國文壇為中心的考察/劉曉麗
偽滿洲國抵抗文學的地下書寫/蔣蕾
話語與抵抗
從鄉土文學到殖民地文學──本格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文化轉向與文藝創新主軸/郭誌光
超越意識與新京文壇──以《大同報》副刊為中心的考察/劉恆興
何謂「滿洲國語」?──考察雜誌《滿洲國語》的創刊及其言說/大久保明男
聲與光的短暫交匯──「滿洲國」的電影廣播劇/代珂
原住民、少數者與帝國
「蕃婦」形象中的二元對立與殖民地問題──以真杉靜枝的台灣原住民族關係作品為主/簡中昊
沉默之境──佐藤春夫未竟之行與王家祥小說中的布農族傳統領域/柳書琴
「發現」滿洲──拜闊夫小說中的密林與虎王意象/蔡佩均
撫順煤礦與韓中小說──以韓雪野的〈合宿所的夜〉和王秋螢的〈礦坑〉為中心/金昌鎬
世變、文化媒介與記憶
台灣古典文人的文化經營──新竹北門鄭氏家族與一九二九年全島書畫展覽會/徐淑賢
三○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作家的關係──以台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王惠珍
歷史記憶與成長敘事──論馬尋的《風雨關東》/岡田英樹
心的戰爭──蕭金堆〈命運的洋娃娃〉中的戰爭記憶與台韓友誼/崔末順
安壽吉解放前後「滿洲」敘事中的民族認識──以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為中心/李海英
序二 正確歷史認識的共享/岡田英樹
序三 東亞殖民場文學研究的跨度思維/張泉
序四 滿洲國的研究新視野/施淑
序五 前進的台灣文學/林瑞明
導言 東亞文學場的跨境交流與研究動能
反帝國主義國際主義與解殖文學
全球非殖民化論與東亞殖民地文學研究展望/金在湧
中國淪陷區文藝研究的方法問題──以杜贊奇的「滿洲國」想像為中心/張泉
解殖性內在於殖民地文學──以偽滿洲國文壇為中心的考察/劉曉麗
偽滿洲國抵抗文學的地下書寫/蔣蕾
話語與抵抗
從鄉土文學到殖民地文學──本格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文化轉向與文藝創新主軸/郭誌光
超越意識與新京文壇──以《大同報》副刊為中心的考察/劉恆興
何謂「滿洲國語」?──考察雜誌《滿洲國語》的創刊及其言說/大久保明男
聲與光的短暫交匯──「滿洲國」的電影廣播劇/代珂
原住民、少數者與帝國
「蕃婦」形象中的二元對立與殖民地問題──以真杉靜枝的台灣原住民族關係作品為主/簡中昊
沉默之境──佐藤春夫未竟之行與王家祥小說中的布農族傳統領域/柳書琴
「發現」滿洲──拜闊夫小說中的密林與虎王意象/蔡佩均
撫順煤礦與韓中小說──以韓雪野的〈合宿所的夜〉和王秋螢的〈礦坑〉為中心/金昌鎬
世變、文化媒介與記憶
台灣古典文人的文化經營──新竹北門鄭氏家族與一九二九年全島書畫展覽會/徐淑賢
三○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作家的關係──以台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王惠珍
歷史記憶與成長敘事──論馬尋的《風雨關東》/岡田英樹
心的戰爭──蕭金堆〈命運的洋娃娃〉中的戰爭記憶與台韓友誼/崔末順
安壽吉解放前後「滿洲」敘事中的民族認識──以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為中心/李海英
序/導讀
序一(節錄)
東亞殖民地文學跨國研究的基石/陳萬益/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退休教授
日本在脫亞入歐、明治維新以後,成為亞洲近代化的強國,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打敗清廷,獲取第一個殖民地台灣;一九一○年強迫朝鮮簽約合併;一九三二年軍國主義者扶持中國東北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二十世紀東亞「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就是上述地區或國家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式與名稱淪陷被統治;再擴大來說,還可包括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以後先後占領的地區。迄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放棄所有日本領土以外統轄或占領的土地,「殖民地」因此擺脫了被殖民的情境。
一九四○年代前期太平洋戰爭熾烈,日本帝國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號召,日本文學報國會聲援所謂「聖戰」,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分別在東京、南京召開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來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學者齊聚一堂交流,當然,事後來看,在戰爭陰影和法西斯脅迫下,交流不是喊口號,就是言不由衷,虛情假意。不過,客觀說來,在「大東亞文學者」名義下,來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學者卻開啟了當今所謂的跨文化交流,雖然參與大會的殖民地文學者當時或事後多不齒或避免言及此一輝煌。
二戰結束以後,冷戰結構的對立,以及台、中、日、韓等國家自身政經形勢的發展,「殖民地」的歷史都成為禁忌和恥辱,在各自國家政治宰制與言論控制下,長期湮沒不彰。大概是二十世紀後期,對帝國和殖民主義的反思和批判成為舉世文化研究的重大課題,而前述「殖民地」也先後獲得民主化的言論空間,殖民地的文學文獻才得以陸續出土,得到研究,也因此在自身歷史的考察之下,深深覺得東亞跨國、跨文化、跨語和跨種族連結研究的必要。
前述的研究團隊成員,從二○○五年五月十日在首爾延世大學「殖民主義與文學」國際論壇,中經上海華東師大,至二○一六年在台灣清華大學召開的「東亞文學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十幾年不斷對話、深化此一學術領域,同時進行《東亞殖民地文學事典》的編纂作為具體而微的跨國研究成果,與學術新領域的極具參考性的工具書,供後進奠基以超越研究,主事者的堅持與宏圖,不能不令人佩服,而跨國團隊長期合作的模式亦大可垂範來者,可以效倣。
此會議論文集的台灣主事者柳書琴教授希望我寫篇序文共襄盛舉,並且希望我對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在戰後長期沉埋以至復活的歷程稍作陳述,以供參照比較。茲再費筆墨簡述如下:
總體說來,戰後台灣由國民黨來台接收統治,長期在戒嚴體制(一九四九—一九八七)「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類殖民式的文化教育,尤其「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和一九五○年代反共的「白色恐怖」,將「台灣」污名化,幾乎所有的台灣歷史文化都成為禁忌,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歷史文獻多數被禁毀,在深仇大恨的抗日情結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長期從台灣土地上消失。
大概可以從三個時段來考察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在戰後的復活歷程:
首先是戰後初期,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府戒嚴之前,雖然中間曾發生二二八流血事變,相對來說,言論比較寬鬆,台灣作家以光復的心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雖已去世,其「台灣新文學之父」的榮寵地位得到肯定,報紙雜誌重登舊作,發表〈獄中日記〉等,此一現象可與魯迅作品的翻譯出版互相輝映;楊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戰後更活躍一時,由於他的小說〈送報伕〉戰前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因而得與戰後來台文化人交往,編輯報刊雜誌,譯介魯迅、沈從文等人作品、參與「台灣新文學重建問題」的論爭,最後,在一九四九年因為〈和平宣言〉事件成為政治受難者,送綠島管訓十二年;另外一位曾經擁有文學版圖的是龍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九四六年任職《中華日報》日文版,介紹世界文學名著,可惜只有短暫的十個月,即在政府廢止日文報刊後噤默;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戰後即拒絕用日語創作,積極學習中文,陸續發表中文小說四篇,卻於二二八事件後從事反政府行動,一九五○年代被毒蛇咬死;張文環(一九○八—一九七八)作為戰前《台灣文學》雜誌的主導者,一九四四年在時局艱難下即離開台北文壇,戰後初期捲入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半年,雖倖免於難,也無法創作。
戰後台灣新文學復活的契機在一九七○年代,美國將釣魚台移交日本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重挫了國府的外交及其治台的國策,後來的台日、台美的斷交,以至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十年間,政治的孤立、經濟的繁榮,台灣受歐美反戰及保釣學生運動影響,呈現一波左翼的回歸現實的鄉土思潮與民族主義論爭,以一九七○年代中期為代表「鄉土文學論戰」和校園民歌流行為具體標識,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乃乘勢復活。
首先揭開序幕的是楊逵,一九六一年服刑完畢返台的他,隱居躬耕於台中東海大學對面,經營花園,遺世獨立,十年無人聞問。東海大學的學生無意間接觸老農,發現他竟然是一九三四年以日文小說〈新聞配達夫〉(中譯〈送報伕〉)在東京獲獎的普羅文學作家與社會運動者,這一頁傳奇既經揭開,台灣的作家、學生、甚至政治人物,從南北各地前來參訪,也鼓舞作家復出,一九七五年首度結集出版中文小說集《鵝媽媽出嫁》,也開始參與各類社會活動,其老而彌堅、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壓不扁的玫瑰」(同名作品被選為中學教材的範文)的意象成為典範,校園民歌則傳唱他作詞的〈愚公移山〉,並以〈老鼓手〉之名歌頌他;在此一氛圍底下,戰後出生的台灣青年開始探問「賴和是誰?」爭取言論自由的黨外雜誌之一的《夏潮》雜誌陸續重刊賴和、呂赫若、吳新榮等作家作品;葉石濤、鍾肇政則持續譯介、評論戰前日文作家作品;《大學雜誌》舉辦「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更於鄉土文學論戰正酣時出版《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這股熱潮延續到一九七○年代後期,在鍾理和、吳濁流、吳新榮等作家全集之後,一九七九年《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和《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兩大套書的出版集其大成,卻也隨著年底「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和隨後的司法審判,因社會氛圍改變而偃旗息鼓。
第三個時段在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後的一九九○年代,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大大解放了言論的空間,左翼歷史和統獨議題,不再成為禁忌;而中國大陸在文革之後的開放改革、引介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兩岸交流以至於「六四事件」和隨後的「蘇東波」共產主義的解體,這個大背景提供了台灣人反思自身主體的歷史文化的契機,一九八七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雖然只是輪廓性的敘述,他所強調的台灣文學發展歷史的「自主意願」和「台灣性格」的史觀,則強烈導引了一九九○年代台灣文學的發展,改變了戰後台灣學院中文系教研「只有中國,沒有台灣;只有古典,沒有現代」的體制。而這一波被稱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運動,主要還是以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復活為表徵:先是以左翼和武裝反叛政府至終以遭蛇咬傳聞消失四十年的呂赫若的復活,他的日文小說由林至潔逐篇翻譯,於報紙副刊發表,一九九五年結集《呂赫若小說全集》,被冠以「台灣第一才子」的美名,隨後更在台北和北京舉辦兩場以其生平和文學為主題的研討會,更促成他僅有的遺物《呂赫若日記(1942-1944)》的出版,這一股研讀呂赫若的熱情貫穿一九九○年代,可與前述楊逵現象相互比美。
序二(節錄)
正確歷史認識的共享/岡田英樹/日本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
日本的亞洲侵略戰爭與殖民地化、再加上戰後的冷戰結構,讓東亞的國家與地域留下深深的傷痕,直到現在也未能確保這個區域的和平與安定。再加上以日本人的立場來說,安倍政權之下的四年半,政治急速地右傾、且將過去的侵略戰爭粉飾成為解放亞洲的歷史、強辯說過去的殖民地是因著日本才能現代化,橫行著這樣的歷史修正主義。應對這個風潮,殖民地、占領地實際情況的正確歷史認識能夠被明辨,是我們所期望的。
這次的研討會裡,加入了無產階級文學中的國際主義、抵抗文學與親日文學、童話文學、民族比較文學、台灣原住民文學、滿洲國的抗日地下文學、雜誌、新聞、廣播等媒體、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書畫博覽會、萬國博覽會、台灣的媽祖信仰等多樣的主題,成為充實的研究發表場。超越各式各樣的國家與地域的框架,成為共享「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珍貴機會。
序三(節錄)
東亞殖民場文學研究的跨度思維/張泉/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
東亞殖民場文學的學術研究發展到今天,我覺得有關語言的問題,值得引起進一步的重視。主要的原因在於,在近代東亞日本統治區的不同區域,「語言」議題有著不同的發展形態。
日本東方殖民主義構想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地理/文化疆域,細分為「自主圈」、「共榮圈」和「文化圈」三個層面(參見拙著《殖民主義與離散文學— 「滿洲國」、「滿系」作家/文學的跨域流動》第一章〈日據區文學跨域流動政治研究關鍵詞〉中的第三節〈「大東亞共榮圈」〉,二○一七),其中的自主圈界定為中、日、滿,是日本經營有年的體制殖民核心區:中,即中國內地汪精衛偽政權名義上的轄地(淪陷區);日,包括被割據被侵占的台灣、朝鮮半島;滿,中國東北淪陷區「滿洲國」。語言殖民(同化)是強化和維繫外來殖民統治的基礎之一。台灣和朝鮮半島被殖民的歷史漫長,宗主國的語言殖民得以實現。比如台灣,從一八九五年開始,在經歷了四十二年的殖民教化之後,得以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廢止報刊上的漢文欄,日語成為官方語言,日語成為台灣作家的通行創作語言。「滿洲國」一九三二年成立,到一九三七年才開始實行與殖民主日本統一的「新學制」,到一九四一年才顧及到日語在東北的推廣,發文要求官吏修習日語並開展群眾性的普及日語的活動。由於時間短,日語未能累積起能夠改變東北淪陷區文學生態的足夠的比重,倒是大量在滿日本人、朝鮮人、俄羅斯人等僑民、移民文學,形成了殖民期東北獨特的多語言文學生態景觀。至於廣袤的蒙疆、華北、南京、廣州、上海等中國內地,這些地區完全淪陷期大多不超過八年,日語語言殖民的累積遠為不夠,其效果微乎其微。但宗主國語言對殖民地在地語言的影響和滲透,在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總之,語言殖民在不同日據區所呈現出來的差異性,是由各地所累積的殖民教化的程度所決定的。殖民地台灣/「滿洲國」/淪陷區三種統治模式間的共時殖民體制差異維度,是我近年來反覆申說的東亞殖民研究中的四個宏觀背景或方法中的一個,它或可作為考察語言殖民差異化的原因或依據之一。
語言是殖民文化統制的基礎內容。文學又是語言的藝術。因此,在東亞殖民場研究領域,文學曾長期遭冷落、被誤解,就是現在,全盤污名化殖民期在地民族文學的認知,也時有所見。因此,作為語言藝術研究的東亞殖民場文學研究,值得我們堅持不懈地持續投入。
從本質上看,「文學」不同於政論時評和大眾傳媒,是一種很獨立、很奇特的反映外在現實世界和內在主觀感受的樣式。文學在本體上是反抗的、自在的。通過研究,有可能將那些看似沒有明確目的的文學文本中隱藏的目的彰顯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比歷史更真實。而這正是從事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價值所在。比如「滿洲國」的古丁。他一向被認為是與日本政權合作的作家,但透過作品細讀和分析,卻能夠發現與殖民體制相對的社會發展面向和民心所向,是文學研究能夠發掘出與政治表象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判斷的個案。又如朝鮮親日作家張赫宙。他曾撰文表達這樣的心跡:自己無論如何要進入日本中央文壇,因為只有用日文才能夠將悲慘的朝鮮民族的命運展現給世界。從中,我們再次看到,作家利用文學的特殊性來達到自身目的與追求的敏感度與可能性。
這樣的個案所展現的意義與價值,顯現了殖民地語言和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的拓展空間。雖然政治環境對作家的影響巨大,但通過文學研究,卻能夠發掘出與政治研究結論完全不同的取向。進入這樣的研究空間,需要奠基於對語言與文學之特殊性的理解與把握,以及對殖民地文學及文學生產的時間、地點等場域關係的縝密追蹤與客觀查考。這也是我一直呼籲在相關研究中必須謹慎、用心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反覆申說東亞文學研究中的四個與殖民相關的宏觀維度背景或方法的原因所在。
序五(節錄)
前進的台灣文學/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楊雲萍老師(一九○六—二○○○)出生於日治初期,是一九二○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一九二六年就率先以白話文發表了〈光臨〉、〈黃昏的蔗園〉等小說,描寫殖民地封建社會、性別壓迫與糖業資本主義等等。戰後他在台大歷史系任教、以一名歷史學者聞名,但是在台灣史的第一堂課都會自稱:「老師是一名詩人」。當時學生們都不當一回事,聽過即忘,但一位老教授反覆自豪地自詡自己是詩人,卻意外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天,我跑到當時位於台北市八德路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借出那本出版於一九四三年戰火煙硝之中的日文詩集《山河》。靠著大學修過兩年的微薄日文能力,努力翻查字典,終於讀完了這本詩集。我的第一個感覺是,老師的日文詩歌充滿了現代感。
一九七○年代當時,台灣的現代詩盛行引用中國古典詩詞,詩壇祭酒余光中先生在現代詩中嵌入古典修辭與意象,更風靡一時。然而我卻偏好楊老師那種不復古亦沒有典故的詩歌。他描寫生活,新鮮、簡練而真實,富含情感,也充滿詩性。譬如,他曾這樣讚美妻子:「你用彈鋼琴的手,洗了尿布,拔了蘿蔔」。簡單幾句話便把一位日本時代受過高女教育的優雅少女之手,因婚後操持家計、張羅生活的變化浮現出來。我想,師母讀到這首詩時,也會為所愛之人的疼惜而感動吧?楊師母確實是我見過的人們當中,對自己先生最悅服的一位,而老師一生也非常信靠她、倚賴她。
我研究生時期接觸的,就是這樣一位老教授與日語詩人。楊老師其人其詩其學問視野,都在當時主流的中國感覺、中國意象之外,非常有世界性。實際歷經台灣新文學運動從萌芽期、成熟期到戰爭期多種進程的楊老師,經常告訴我們:一九二○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啟動之後,納進各種海外文藝潮流,形成本地獨特個性,絕對不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或亞流。我牢牢記住了這句話。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懷抱印證這句話的好奇心,一個人到各地圖書館尋找日治時期的舊雜誌與舊作品,依憑著粗淺的日文程度一點一滴走入那個時代,靠向不為人知的作家。在這樣極度缺乏外部支援的克難情況下,時代的魅影把我帶向往後數十年的台灣新文學研究。
我對這位台灣第一代作家的研究歷時約十年,期間整理了賴和的詩文,並出版作家全集,雖然今日看來仍有諸多缺點,但已是窮盡我當時的洪荒之力、盡我所能了!在資源和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做到這樣的程度,這是我命,我心甘情願,因為在我心裡只有一個聲音:我要為台灣死去的文學前輩發出聲音。這個信念支持著我在當時完全排斥台灣文學的社會環境下,堅持從事台灣文學這個被認為須冒極大政治風險而又非常寂寞的學術工作。
數十年來,台灣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很幸運地,從前我認為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達成的目標,現在都一一達到了,包括成立國立台灣文學館及促進大專院校設立台灣文學系所。迄今台灣文學系所甚至已成為衡量一間大學是否與台灣社會隔離的指標之一。能達到這樣的成果,不只是我一人的努力,而是許許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奮鬥而來的,譬如陳萬益、呂興昌……等人。
東亞殖民地文學跨國研究的基石/陳萬益/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退休教授
日本在脫亞入歐、明治維新以後,成為亞洲近代化的強國,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打敗清廷,獲取第一個殖民地台灣;一九一○年強迫朝鮮簽約合併;一九三二年軍國主義者扶持中國東北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二十世紀東亞「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就是上述地區或國家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式與名稱淪陷被統治;再擴大來說,還可包括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以後先後占領的地區。迄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放棄所有日本領土以外統轄或占領的土地,「殖民地」因此擺脫了被殖民的情境。
一九四○年代前期太平洋戰爭熾烈,日本帝國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號召,日本文學報國會聲援所謂「聖戰」,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分別在東京、南京召開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來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學者齊聚一堂交流,當然,事後來看,在戰爭陰影和法西斯脅迫下,交流不是喊口號,就是言不由衷,虛情假意。不過,客觀說來,在「大東亞文學者」名義下,來自不同殖民地的文學者卻開啟了當今所謂的跨文化交流,雖然參與大會的殖民地文學者當時或事後多不齒或避免言及此一輝煌。
二戰結束以後,冷戰結構的對立,以及台、中、日、韓等國家自身政經形勢的發展,「殖民地」的歷史都成為禁忌和恥辱,在各自國家政治宰制與言論控制下,長期湮沒不彰。大概是二十世紀後期,對帝國和殖民主義的反思和批判成為舉世文化研究的重大課題,而前述「殖民地」也先後獲得民主化的言論空間,殖民地的文學文獻才得以陸續出土,得到研究,也因此在自身歷史的考察之下,深深覺得東亞跨國、跨文化、跨語和跨種族連結研究的必要。
前述的研究團隊成員,從二○○五年五月十日在首爾延世大學「殖民主義與文學」國際論壇,中經上海華東師大,至二○一六年在台灣清華大學召開的「東亞文學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十幾年不斷對話、深化此一學術領域,同時進行《東亞殖民地文學事典》的編纂作為具體而微的跨國研究成果,與學術新領域的極具參考性的工具書,供後進奠基以超越研究,主事者的堅持與宏圖,不能不令人佩服,而跨國團隊長期合作的模式亦大可垂範來者,可以效倣。
此會議論文集的台灣主事者柳書琴教授希望我寫篇序文共襄盛舉,並且希望我對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在戰後長期沉埋以至復活的歷程稍作陳述,以供參照比較。茲再費筆墨簡述如下:
總體說來,戰後台灣由國民黨來台接收統治,長期在戒嚴體制(一九四九—一九八七)「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類殖民式的文化教育,尤其「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和一九五○年代反共的「白色恐怖」,將「台灣」污名化,幾乎所有的台灣歷史文化都成為禁忌,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歷史文獻多數被禁毀,在深仇大恨的抗日情結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長期從台灣土地上消失。
大概可以從三個時段來考察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在戰後的復活歷程:
首先是戰後初期,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府戒嚴之前,雖然中間曾發生二二八流血事變,相對來說,言論比較寬鬆,台灣作家以光復的心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雖已去世,其「台灣新文學之父」的榮寵地位得到肯定,報紙雜誌重登舊作,發表〈獄中日記〉等,此一現象可與魯迅作品的翻譯出版互相輝映;楊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戰後更活躍一時,由於他的小說〈送報伕〉戰前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因而得與戰後來台文化人交往,編輯報刊雜誌,譯介魯迅、沈從文等人作品、參與「台灣新文學重建問題」的論爭,最後,在一九四九年因為〈和平宣言〉事件成為政治受難者,送綠島管訓十二年;另外一位曾經擁有文學版圖的是龍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九四六年任職《中華日報》日文版,介紹世界文學名著,可惜只有短暫的十個月,即在政府廢止日文報刊後噤默;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戰後即拒絕用日語創作,積極學習中文,陸續發表中文小說四篇,卻於二二八事件後從事反政府行動,一九五○年代被毒蛇咬死;張文環(一九○八—一九七八)作為戰前《台灣文學》雜誌的主導者,一九四四年在時局艱難下即離開台北文壇,戰後初期捲入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半年,雖倖免於難,也無法創作。
戰後台灣新文學復活的契機在一九七○年代,美國將釣魚台移交日本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重挫了國府的外交及其治台的國策,後來的台日、台美的斷交,以至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十年間,政治的孤立、經濟的繁榮,台灣受歐美反戰及保釣學生運動影響,呈現一波左翼的回歸現實的鄉土思潮與民族主義論爭,以一九七○年代中期為代表「鄉土文學論戰」和校園民歌流行為具體標識,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乃乘勢復活。
首先揭開序幕的是楊逵,一九六一年服刑完畢返台的他,隱居躬耕於台中東海大學對面,經營花園,遺世獨立,十年無人聞問。東海大學的學生無意間接觸老農,發現他竟然是一九三四年以日文小說〈新聞配達夫〉(中譯〈送報伕〉)在東京獲獎的普羅文學作家與社會運動者,這一頁傳奇既經揭開,台灣的作家、學生、甚至政治人物,從南北各地前來參訪,也鼓舞作家復出,一九七五年首度結集出版中文小說集《鵝媽媽出嫁》,也開始參與各類社會活動,其老而彌堅、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壓不扁的玫瑰」(同名作品被選為中學教材的範文)的意象成為典範,校園民歌則傳唱他作詞的〈愚公移山〉,並以〈老鼓手〉之名歌頌他;在此一氛圍底下,戰後出生的台灣青年開始探問「賴和是誰?」爭取言論自由的黨外雜誌之一的《夏潮》雜誌陸續重刊賴和、呂赫若、吳新榮等作家作品;葉石濤、鍾肇政則持續譯介、評論戰前日文作家作品;《大學雜誌》舉辦「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更於鄉土文學論戰正酣時出版《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這股熱潮延續到一九七○年代後期,在鍾理和、吳濁流、吳新榮等作家全集之後,一九七九年《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和《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兩大套書的出版集其大成,卻也隨著年底「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和隨後的司法審判,因社會氛圍改變而偃旗息鼓。
第三個時段在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後的一九九○年代,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大大解放了言論的空間,左翼歷史和統獨議題,不再成為禁忌;而中國大陸在文革之後的開放改革、引介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兩岸交流以至於「六四事件」和隨後的「蘇東波」共產主義的解體,這個大背景提供了台灣人反思自身主體的歷史文化的契機,一九八七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雖然只是輪廓性的敘述,他所強調的台灣文學發展歷史的「自主意願」和「台灣性格」的史觀,則強烈導引了一九九○年代台灣文學的發展,改變了戰後台灣學院中文系教研「只有中國,沒有台灣;只有古典,沒有現代」的體制。而這一波被稱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運動,主要還是以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復活為表徵:先是以左翼和武裝反叛政府至終以遭蛇咬傳聞消失四十年的呂赫若的復活,他的日文小說由林至潔逐篇翻譯,於報紙副刊發表,一九九五年結集《呂赫若小說全集》,被冠以「台灣第一才子」的美名,隨後更在台北和北京舉辦兩場以其生平和文學為主題的研討會,更促成他僅有的遺物《呂赫若日記(1942-1944)》的出版,這一股研讀呂赫若的熱情貫穿一九九○年代,可與前述楊逵現象相互比美。
序二(節錄)
正確歷史認識的共享/岡田英樹/日本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
日本的亞洲侵略戰爭與殖民地化、再加上戰後的冷戰結構,讓東亞的國家與地域留下深深的傷痕,直到現在也未能確保這個區域的和平與安定。再加上以日本人的立場來說,安倍政權之下的四年半,政治急速地右傾、且將過去的侵略戰爭粉飾成為解放亞洲的歷史、強辯說過去的殖民地是因著日本才能現代化,橫行著這樣的歷史修正主義。應對這個風潮,殖民地、占領地實際情況的正確歷史認識能夠被明辨,是我們所期望的。
這次的研討會裡,加入了無產階級文學中的國際主義、抵抗文學與親日文學、童話文學、民族比較文學、台灣原住民文學、滿洲國的抗日地下文學、雜誌、新聞、廣播等媒體、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書畫博覽會、萬國博覽會、台灣的媽祖信仰等多樣的主題,成為充實的研究發表場。超越各式各樣的國家與地域的框架,成為共享「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珍貴機會。
序三(節錄)
東亞殖民場文學研究的跨度思維/張泉/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
東亞殖民場文學的學術研究發展到今天,我覺得有關語言的問題,值得引起進一步的重視。主要的原因在於,在近代東亞日本統治區的不同區域,「語言」議題有著不同的發展形態。
日本東方殖民主義構想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地理/文化疆域,細分為「自主圈」、「共榮圈」和「文化圈」三個層面(參見拙著《殖民主義與離散文學— 「滿洲國」、「滿系」作家/文學的跨域流動》第一章〈日據區文學跨域流動政治研究關鍵詞〉中的第三節〈「大東亞共榮圈」〉,二○一七),其中的自主圈界定為中、日、滿,是日本經營有年的體制殖民核心區:中,即中國內地汪精衛偽政權名義上的轄地(淪陷區);日,包括被割據被侵占的台灣、朝鮮半島;滿,中國東北淪陷區「滿洲國」。語言殖民(同化)是強化和維繫外來殖民統治的基礎之一。台灣和朝鮮半島被殖民的歷史漫長,宗主國的語言殖民得以實現。比如台灣,從一八九五年開始,在經歷了四十二年的殖民教化之後,得以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廢止報刊上的漢文欄,日語成為官方語言,日語成為台灣作家的通行創作語言。「滿洲國」一九三二年成立,到一九三七年才開始實行與殖民主日本統一的「新學制」,到一九四一年才顧及到日語在東北的推廣,發文要求官吏修習日語並開展群眾性的普及日語的活動。由於時間短,日語未能累積起能夠改變東北淪陷區文學生態的足夠的比重,倒是大量在滿日本人、朝鮮人、俄羅斯人等僑民、移民文學,形成了殖民期東北獨特的多語言文學生態景觀。至於廣袤的蒙疆、華北、南京、廣州、上海等中國內地,這些地區完全淪陷期大多不超過八年,日語語言殖民的累積遠為不夠,其效果微乎其微。但宗主國語言對殖民地在地語言的影響和滲透,在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總之,語言殖民在不同日據區所呈現出來的差異性,是由各地所累積的殖民教化的程度所決定的。殖民地台灣/「滿洲國」/淪陷區三種統治模式間的共時殖民體制差異維度,是我近年來反覆申說的東亞殖民研究中的四個宏觀背景或方法中的一個,它或可作為考察語言殖民差異化的原因或依據之一。
語言是殖民文化統制的基礎內容。文學又是語言的藝術。因此,在東亞殖民場研究領域,文學曾長期遭冷落、被誤解,就是現在,全盤污名化殖民期在地民族文學的認知,也時有所見。因此,作為語言藝術研究的東亞殖民場文學研究,值得我們堅持不懈地持續投入。
從本質上看,「文學」不同於政論時評和大眾傳媒,是一種很獨立、很奇特的反映外在現實世界和內在主觀感受的樣式。文學在本體上是反抗的、自在的。通過研究,有可能將那些看似沒有明確目的的文學文本中隱藏的目的彰顯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比歷史更真實。而這正是從事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價值所在。比如「滿洲國」的古丁。他一向被認為是與日本政權合作的作家,但透過作品細讀和分析,卻能夠發現與殖民體制相對的社會發展面向和民心所向,是文學研究能夠發掘出與政治表象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判斷的個案。又如朝鮮親日作家張赫宙。他曾撰文表達這樣的心跡:自己無論如何要進入日本中央文壇,因為只有用日文才能夠將悲慘的朝鮮民族的命運展現給世界。從中,我們再次看到,作家利用文學的特殊性來達到自身目的與追求的敏感度與可能性。
這樣的個案所展現的意義與價值,顯現了殖民地語言和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的拓展空間。雖然政治環境對作家的影響巨大,但通過文學研究,卻能夠發掘出與政治研究結論完全不同的取向。進入這樣的研究空間,需要奠基於對語言與文學之特殊性的理解與把握,以及對殖民地文學及文學生產的時間、地點等場域關係的縝密追蹤與客觀查考。這也是我一直呼籲在相關研究中必須謹慎、用心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反覆申說東亞文學研究中的四個與殖民相關的宏觀維度背景或方法的原因所在。
序五(節錄)
前進的台灣文學/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楊雲萍老師(一九○六—二○○○)出生於日治初期,是一九二○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一九二六年就率先以白話文發表了〈光臨〉、〈黃昏的蔗園〉等小說,描寫殖民地封建社會、性別壓迫與糖業資本主義等等。戰後他在台大歷史系任教、以一名歷史學者聞名,但是在台灣史的第一堂課都會自稱:「老師是一名詩人」。當時學生們都不當一回事,聽過即忘,但一位老教授反覆自豪地自詡自己是詩人,卻意外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有一天,我跑到當時位於台北市八德路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借出那本出版於一九四三年戰火煙硝之中的日文詩集《山河》。靠著大學修過兩年的微薄日文能力,努力翻查字典,終於讀完了這本詩集。我的第一個感覺是,老師的日文詩歌充滿了現代感。
一九七○年代當時,台灣的現代詩盛行引用中國古典詩詞,詩壇祭酒余光中先生在現代詩中嵌入古典修辭與意象,更風靡一時。然而我卻偏好楊老師那種不復古亦沒有典故的詩歌。他描寫生活,新鮮、簡練而真實,富含情感,也充滿詩性。譬如,他曾這樣讚美妻子:「你用彈鋼琴的手,洗了尿布,拔了蘿蔔」。簡單幾句話便把一位日本時代受過高女教育的優雅少女之手,因婚後操持家計、張羅生活的變化浮現出來。我想,師母讀到這首詩時,也會為所愛之人的疼惜而感動吧?楊師母確實是我見過的人們當中,對自己先生最悅服的一位,而老師一生也非常信靠她、倚賴她。
我研究生時期接觸的,就是這樣一位老教授與日語詩人。楊老師其人其詩其學問視野,都在當時主流的中國感覺、中國意象之外,非常有世界性。實際歷經台灣新文學運動從萌芽期、成熟期到戰爭期多種進程的楊老師,經常告訴我們:一九二○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啟動之後,納進各種海外文藝潮流,形成本地獨特個性,絕對不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或亞流。我牢牢記住了這句話。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懷抱印證這句話的好奇心,一個人到各地圖書館尋找日治時期的舊雜誌與舊作品,依憑著粗淺的日文程度一點一滴走入那個時代,靠向不為人知的作家。在這樣極度缺乏外部支援的克難情況下,時代的魅影把我帶向往後數十年的台灣新文學研究。
我對這位台灣第一代作家的研究歷時約十年,期間整理了賴和的詩文,並出版作家全集,雖然今日看來仍有諸多缺點,但已是窮盡我當時的洪荒之力、盡我所能了!在資源和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做到這樣的程度,這是我命,我心甘情願,因為在我心裡只有一個聲音:我要為台灣死去的文學前輩發出聲音。這個信念支持著我在當時完全排斥台灣文學的社會環境下,堅持從事台灣文學這個被認為須冒極大政治風險而又非常寂寞的學術工作。
數十年來,台灣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很幸運地,從前我認為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達成的目標,現在都一一達到了,包括成立國立台灣文學館及促進大專院校設立台灣文學系所。迄今台灣文學系所甚至已成為衡量一間大學是否與台灣社會隔離的指標之一。能達到這樣的成果,不只是我一人的努力,而是許許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奮鬥而來的,譬如陳萬益、呂興昌……等人。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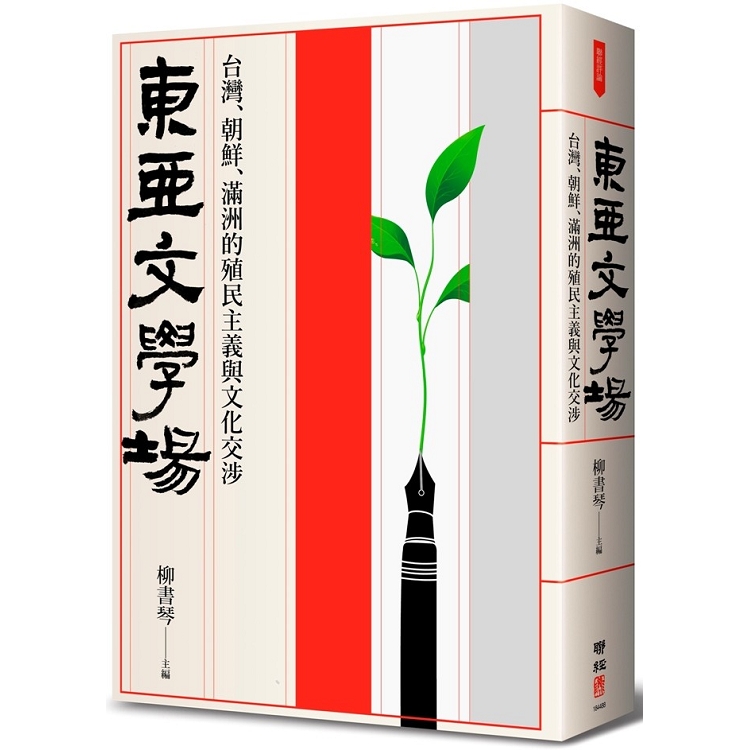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