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吧,群青( 全)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失去的東西是什麼?
撞擊內心的青春懸疑小說。
11月19日早上6點42分,我與她重逢了。比任何人都還要率真、正直、凜然的少女──真邊由宇。理應不該發生的相逢使我安定的高中生活驟然一變。奇妙的島嶼、連續性塗鴉事件,其中隱藏的謎題是……我為何會在這裡?她為何會來到這裡?最終揭曉的真相將殘酷的現實推入我倆的青春。「階梯島」系列就此拉開序幕。
撞擊內心的青春懸疑小說。
11月19日早上6點42分,我與她重逢了。比任何人都還要率真、正直、凜然的少女──真邊由宇。理應不該發生的相逢使我安定的高中生活驟然一變。奇妙的島嶼、連續性塗鴉事件,其中隱藏的謎題是……我為何會在這裡?她為何會來到這裡?最終揭曉的真相將殘酷的現實推入我倆的青春。「階梯島」系列就此拉開序幕。
試閱
這是階梯島的故事。
生活在島上的居民約有兩千人。商店數目不多,因此也時常令人感到不方便,但這裡既不會發生能稱得上案件的案件,晴朗的夜晚又能看到充滿震撼的星空,我們在此過著平淡安穩的日常生活,沒有人能離開這座小島。
沒有人知道我們為何會來到這座島上,所有人都把當時的記憶忘得一乾二淨。
以我為例,我大概喪失了四天的記憶。
我來到這座島的時間是八月底。我還記得自己二十五號走出家門,為了前往書店而穿過附近的一座公園,然後記憶在此戛然而止,之後恢復意識時是二十九號,那天我已莫名其妙地站在階梯島的海岸上,追兔子追到掉進洞穴裡的愛麗絲還比較能令人接受。這座島上的居民都是跳過過程,不知不覺間迷失在這座島上。
這裡似乎是被丟棄的人才會前來的島嶼,人們如此口耳相傳。
不知道究竟是被誰、以怎樣的方式丟棄,也很難想像用來丟棄人的島嶼真的存在於現代社會之中。
不過,在聽到「這裡是被丟棄的人的島嶼」時,我卻不可思議地坦然接受了這個說明,並沒有特別感到難過或混亂,只是恍然大悟「啊,原來我被丟棄了」。接下來,甚至還一副事不關己地思考到才只有十六歲卻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這樣的人生真是相當艱苦啊。大概是因為缺乏真實感吧。
事實上,來到島上後,我幾乎都沒有遇到有關住的地方、食物等現實面的問題。之後的三個月,我悠然自得地過著平穩的生活。到島上唯一一間學校上課,住在位於山腳的宿舍,心血來潮時還可以稍微打點零工,偶爾到屋頂上和活了一百萬次的貓聊天。回想起來,日子反倒過得比我造訪這座島之前還來得更安定。
階梯島這個地方當然充滿謎團。
這裡的由來?是個怎樣的地方?沒有人能正確回答得出來,甚至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個即使並不正確但具有說服力的說法。
有人忿忿地表示這裡是死後的世界,又有人一臉興奮地揚言這裡是政府祕密建立的實驗設施,還有傳言說這裡是高價收購廢人的企業擁有的島嶼,也有人把這一切歸咎成一場夢,無論哪一種都是缺乏根據的說法。
關於這座島,我持有一種假說。
那是個跟死後的世界相同,不,或許還更偏離現實的假說,跟高價收購廢人的企業這種傳言能成立相比,我的假說更令人絕望。
我至今都沒有對其他人提過這個假說。
今後恐怕也不會對任何人說起吧。
我不打算解開這座島的真相。活了一百萬次的貓說過,移動才是幸福的本質,可是我並不討厭安定下來的停滯。也許就幸福而言,這裡是個距離遙遠的地方,可是同時也是遠離不幸的地方,只要並非不幸,我就能夠堅稱這是幸福。
至少這座島目前正處於安定的停滯之中,所以我才不會去追尋什麼階梯島的真相,我是如此打算。
我的奇妙但安定的日常生活則在十一月十九日,早上六點四十二分崩潰,正當即將入冬的夜晚翻出魚肚白不久,呼出的空氣開始變白的早上,我一見到她的臉,就感覺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那是我不願看到的變化。
真邊由宇。
這則故事就在無可奈何下,從與她相遇的那一刻開始。
第一話,唯一無法容忍的事
第一話,唯一無法容忍的事
1
這場重逢之中想必沒有什麼命運的成分混在裡頭。
再說階梯島上的學校只有一所,她最後也只能到那裡上學,儘管會遲一些,但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究會碰到面吧,所以一切都能夠用偶然這兩個字來解釋。
事情的開端不過是因為我久違地夢見自己在海邊仰望夜空,只是這點程度的契機而已。
做了個有點感傷的夢,我比平常都還要早醒來,也無意再重回被窩的懷抱,於是我穿上外套走出了宿舍,就為了一時心血來潮想一個人在清晨裡走走。像這樣想嘗試看看的舉動至今也實行過好幾次。島上的黎明除了颳強風的日子之外都像早晨的圖書館一樣安靜,空氣清新,正適合散步。
大概是受到夢境的影響,我挑了沿海的小路漫步。
雖然沿海,但這裡並沒有沙灘,不適合泳裝,只有浪濤嘩啦嘩啦地打在跟我胸口差不多高的沿海堤防,是條毫無風情可言的路,但我偏偏喜歡它的毫無風情,從以前就這樣。例如我認為價格昂貴且美麗大顆的鑽石會受人喜愛是理所當然的事,覺得對路旁的小石頭或有點凹陷的空罐加以青睞的情感才算貨真價實,「古樸閑寂」這個詞讓我有種被救贖的感覺。
太陽從海平面探出頭來,到了朝霞迎曦的時間。看起來像在山的對面的西方天空仍殘留著夜色的痕跡,影子長而濃,不過光線並不像薄暮時那般張揚,我很喜歡這段時間,就跟喜歡沿海毫無風情的小路一樣。
眼睛在無意間瞄向手錶,指針指著六點四十二分,口中呼出的氣息染上了白色,我意識到冬天已經近了。
就在這時候。
「七草。」
聽到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於是我抬起了頭。
堤防上站著一名少女。
那少女穿著看起來眼熟的水手制服。肩上斜背著款式簡單的深藍色書包。微弱的朝陽在她白皙的肌膚上淡淡地渲染出顏色。柔順的黑髮隨著來自海上的徐風飄動。
她就站在堤防上,筆直地望著我。這樣的身影看起來頗具戲劇性,就像昏暗朦朧的景色之中,唯獨有個人鮮明地浮現出來似的,為何直到剛才我都沒有注意到這麼顯眼的少女?我經常會漏看重要的事物。
「真邊?」
我下意識地停下腳步,心裡非常震驚,感覺全身的血液瞬間被抽走──那女孩是真邊由宇,真的嗎?這怎麼可能!
真邊毫不猶豫地沿著堤防朝我這邊走來。
「好久不見,七草。」
「啊,嗯,好久不見。」
「有兩年沒見了?」
「差不多吧。」
「七草一點都沒變呢,我一眼就認出你了。」
我才想這麼說呢。
真邊由宇還是真邊由宇,跟我記憶中的她一模一樣,聲音、步調、表情,一切都還是這麼筆直。現實中才沒有完美的直線,除了她之外,其他人都在某些地方偏了歪了,所以她看起來才會這麼突兀,就像拙劣的合成照一樣,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她從堤防上跳下來,來到我眼前。咚!宛如斷音的著地聲在清晨睡得迷迷糊糊的景色中作響。
「我有事想問你。」她說。
「嗯?」
「這裡是哪裡?」
「階梯島。」
「沒聽過的地方啊。」
「似乎也沒有標記在地圖上喔。」
「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方?」
「我怎麼知道?」
「那七草你呢?」
「這我也不知道。」
「明明是你自己的事你卻不知道?」
「妳不也一樣。」
為什麼自己會在這座島上,真邊本身也無法理解。
不過她點了點頭,大概是因為不得不接受吧。
「話說回來,我不想上學遲到。」
「是喔。」
「這裡是橫濱嗎?」
「是嗎?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然而也有弄清楚的事。
真邊由宇對階梯島一無所知,今天早上才新來乍到。
「有點儀式性的事要進行,妳可以配合一下嗎?」我向她問道。
「需要花多少時間?」
「不用幾分鐘就結束了。」
「我明白了,可以啊。」
階梯島上有幾條規則。
按慣例,這些規則得由剛造訪這座島的人遇上的第一位島民來說明,我當時也是這樣。
「妳叫什麼名字?」
「真邊由宇。你忘了嗎?」
「當然沒忘啊,只是這也是儀式的一部分。」
說明規則時首先必須詢問對方的名字,肯定沒有設想過原本就認識的人會在這裡碰面的情形吧。
「這裡是被丟棄的人的島嶼,想離開這座島,真邊由宇就必須找出失去的東西。」我說。
這是階梯島上最基本的規則,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說的,通常認為是住在山上的魔女,不過魔女之類的誰知道是否真的存在?
「被丟棄的人的島?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待在這裡的人全都是被丟棄的人。」
真邊皺起臉龐,連扭曲的臉看起來都很直,我心想這還真是矛盾啊。
「丟棄人類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不過人們很常說吧,像是被戀人拋棄啊、被公司拋棄等等。」
「七草也被丟棄了嗎?」
「嗯,妳也是喔。」
「被誰?」
「誰知道啊。」
「被不認識的人丟棄,這種事有可能嗎?」
真邊由宇生性就是無法將疑問放到一旁。
只要有什麼事她無法理解,她就會不斷地發問,無論何時都追求著完美正確的答案,相信它確實存在於這個世界。
然而現實中的確有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像我這種人,目前為止都沒有對哪件事給過正經的答案。
「很有意思的疑問,不過妳不想上學遲到吧?我們邊走邊說?」
「要去哪裡?」
「去找一個比我更了解詳情的人。」
「什麼樣的人?」
「見了妳就知道。」
真邊點了點頭,我們開始移動。
「話說你不覺得今早的氣溫太奇怪了?」
「妳以為現在是幾月?」
「不是八月嗎?不過就快進入九月了。」
「不,其實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了。」
看來真邊最近三個月的記憶都沒了。造訪階梯島的人全部都會喪失來之前的記憶。
「莫名其妙。」真邊表示。
「我也有同感。」我回答。
我在心底偷偷地嘆了一口氣。與她重逢讓我升起焦慮、煩躁、憤怒等等的負面情緒,但我握著拳頭,忍著不讓這些表露出來。
在早晨的海邊與她碰到面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一切都可以歸結給偶然,但令我無法接受的是更根本的事情。
──為什麼真邊由宇會在這座島上?
不明白為什麼,也不想去明白。既沒道理,也不應該發生。
老實說,唯有她的臉是我絕對不想再看見的。
第一次見到真邊由宇是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不,嚴格來說,第一次相遇應該是在更早之前。我和她上同一所小學,如果把簡短的對話也算進去,想必在更早之前我們就已經交談過,話雖如此,但我是在小學四年級那個冬日的回家路上,才明確地意識到真邊由宇這個人的存在。
簡單來說,當時的真邊由宇是個遭到欺凌的孩子。小學生一到四年級就多少懂得一些社會性的常識,班級內部開始出現派系,在交談中察言觀色的技巧也變得很重要。
真邊由宇是個對這部分很生疏的孩子。
雖然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什麼,但她被班級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女學生──名字已經想不起來了──給盯上。小孩子的惡意都很直接,因此也曾發生一些就連我這個旁觀者都覺得看不下去的事情。
無論受到多少不講道理、單方面的惡意,真邊由宇都沒有將任何情緒顯現在外,也不會哭喪著臉。即使她的體育服裝被扔進水窪、室內拖鞋被人用麥克筆塗鴉,她都只是一臉不可思議地偏頭納悶。
當時我以為那是她竭盡所能裝出來的逞強。
如今則知道其實不是那樣。
真邊由宇真的純粹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體育服裝非得被扔進水窪不可呢?她無法順利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感受不到惡意的她既無法悲傷也無法動怒,所以她才會偏頭感到不解。
我並非正義的夥伴,所以也沒有想過要為她做點什麼,就連視而不見的態度也沒能讓我心生罪惡感,我似乎還曾經想像過幾次,倘若她向我求助,難道我真能為她做點什麼?一些細節我已經記不得了。
不管怎樣,小學生雖然具有如此陰暗的一面,但同時畢竟還是擁有純真的地方,比方說牛奶這個例子。
牛奶是一隻白色幼犬。
牠應該是一隻棄犬,脖子上雖然沒有項圈,但毛色很乾淨。牛奶三不五時會出現在校園中,每次都讓班上同學歡欣無比,我也曾經餵牛奶吃過幾次營養午餐剩下來的麵包。在牛奶的面前,教室內的階級制度等等都毫不重要,班上同學都會變成大人理想中的純真孩童,這種兩面性想想還真滑稽。
在我們這個小規模的世界中,牛奶是和平的象徵。難以用言語表示的某種秩序具體呈現在這隻白色幼犬上,就像另一方面,真邊由宇具體呈現了什麼叫做沒道理一樣。
如此人見人愛的牛奶流著血倒在地上。
就在一個冬天的回家路上。
一眼就看得出來牠被車撞了,後腳的部分似乎被壓碎,牠肚子上柔軟的毛還在上下起伏,那緩慢的動作很不可思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當時剛好是放學時間,大批孩子站得遠遠地圍觀牛奶。「好可憐。」有人毫無責任感地喃喃道,我也有同樣的想法。
在場的每個人都只是旁觀者。
我們沒人打算成為牛奶車禍的當事者。
可是偏偏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真邊由宇。
她跑到牛奶身邊,毫不猶豫地抱起牠,血跡在白色制服上暈染開,紅得非常鮮明。我記得有人嘟噥了一句「好髒」,但這點我實在無法認同,在我看來,她很美。
真邊由宇邁步就跑。
我不假思索地追著她跑。如今我已經想不起來當時是什麼樣的心情,總之,我就在她後面追著。
真邊由宇筆直地跑著。
她的表情並不悲愴,只是一臉認真,專心地看著前方。似乎壓根就沒有想過她懷中的牛奶已經快要一命嗚呼了。
「沒問題。」她喃喃說道。
「絕對沒問題。」
回想起來,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
不過到達動物醫院時,牛奶已經沒有呼吸了。
醫生搖了搖頭,那一刻,我才見識到真邊由宇哭泣的臉龐。
她皺起臉來放聲大哭,猶如野獸的嚎哮。制服依舊血跡斑斑,眼淚滾滾滴落,她用盡全身力氣痛哭。
我應該沒有哭,不過也可能哭了,記不清楚。
她的身影太過鮮明,以至於我如今已經想不起自己當時的模樣。
真邊由宇和我是從那天才開始變得熟稔起來。
從那天一直到她在國中二年級的暑假搬家為止,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行動。
越了解就越發現她很特殊。她眼中的世界似乎充滿希望,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理想就一定會實現,她對此深信不疑。
為什麼呢?
牛奶明明就死了。
為何她還是能夠如此堅信這世界是合理的呢?
雖然好幾次都浮現這個疑問,但我終究還是什麼都沒問她。
生活在島上的居民約有兩千人。商店數目不多,因此也時常令人感到不方便,但這裡既不會發生能稱得上案件的案件,晴朗的夜晚又能看到充滿震撼的星空,我們在此過著平淡安穩的日常生活,沒有人能離開這座小島。
沒有人知道我們為何會來到這座島上,所有人都把當時的記憶忘得一乾二淨。
以我為例,我大概喪失了四天的記憶。
我來到這座島的時間是八月底。我還記得自己二十五號走出家門,為了前往書店而穿過附近的一座公園,然後記憶在此戛然而止,之後恢復意識時是二十九號,那天我已莫名其妙地站在階梯島的海岸上,追兔子追到掉進洞穴裡的愛麗絲還比較能令人接受。這座島上的居民都是跳過過程,不知不覺間迷失在這座島上。
這裡似乎是被丟棄的人才會前來的島嶼,人們如此口耳相傳。
不知道究竟是被誰、以怎樣的方式丟棄,也很難想像用來丟棄人的島嶼真的存在於現代社會之中。
不過,在聽到「這裡是被丟棄的人的島嶼」時,我卻不可思議地坦然接受了這個說明,並沒有特別感到難過或混亂,只是恍然大悟「啊,原來我被丟棄了」。接下來,甚至還一副事不關己地思考到才只有十六歲卻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這樣的人生真是相當艱苦啊。大概是因為缺乏真實感吧。
事實上,來到島上後,我幾乎都沒有遇到有關住的地方、食物等現實面的問題。之後的三個月,我悠然自得地過著平穩的生活。到島上唯一一間學校上課,住在位於山腳的宿舍,心血來潮時還可以稍微打點零工,偶爾到屋頂上和活了一百萬次的貓聊天。回想起來,日子反倒過得比我造訪這座島之前還來得更安定。
階梯島這個地方當然充滿謎團。
這裡的由來?是個怎樣的地方?沒有人能正確回答得出來,甚至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個即使並不正確但具有說服力的說法。
有人忿忿地表示這裡是死後的世界,又有人一臉興奮地揚言這裡是政府祕密建立的實驗設施,還有傳言說這裡是高價收購廢人的企業擁有的島嶼,也有人把這一切歸咎成一場夢,無論哪一種都是缺乏根據的說法。
關於這座島,我持有一種假說。
那是個跟死後的世界相同,不,或許還更偏離現實的假說,跟高價收購廢人的企業這種傳言能成立相比,我的假說更令人絕望。
我至今都沒有對其他人提過這個假說。
今後恐怕也不會對任何人說起吧。
我不打算解開這座島的真相。活了一百萬次的貓說過,移動才是幸福的本質,可是我並不討厭安定下來的停滯。也許就幸福而言,這裡是個距離遙遠的地方,可是同時也是遠離不幸的地方,只要並非不幸,我就能夠堅稱這是幸福。
至少這座島目前正處於安定的停滯之中,所以我才不會去追尋什麼階梯島的真相,我是如此打算。
我的奇妙但安定的日常生活則在十一月十九日,早上六點四十二分崩潰,正當即將入冬的夜晚翻出魚肚白不久,呼出的空氣開始變白的早上,我一見到她的臉,就感覺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那是我不願看到的變化。
真邊由宇。
這則故事就在無可奈何下,從與她相遇的那一刻開始。
第一話,唯一無法容忍的事
第一話,唯一無法容忍的事
1
這場重逢之中想必沒有什麼命運的成分混在裡頭。
再說階梯島上的學校只有一所,她最後也只能到那裡上學,儘管會遲一些,但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究會碰到面吧,所以一切都能夠用偶然這兩個字來解釋。
事情的開端不過是因為我久違地夢見自己在海邊仰望夜空,只是這點程度的契機而已。
做了個有點感傷的夢,我比平常都還要早醒來,也無意再重回被窩的懷抱,於是我穿上外套走出了宿舍,就為了一時心血來潮想一個人在清晨裡走走。像這樣想嘗試看看的舉動至今也實行過好幾次。島上的黎明除了颳強風的日子之外都像早晨的圖書館一樣安靜,空氣清新,正適合散步。
大概是受到夢境的影響,我挑了沿海的小路漫步。
雖然沿海,但這裡並沒有沙灘,不適合泳裝,只有浪濤嘩啦嘩啦地打在跟我胸口差不多高的沿海堤防,是條毫無風情可言的路,但我偏偏喜歡它的毫無風情,從以前就這樣。例如我認為價格昂貴且美麗大顆的鑽石會受人喜愛是理所當然的事,覺得對路旁的小石頭或有點凹陷的空罐加以青睞的情感才算貨真價實,「古樸閑寂」這個詞讓我有種被救贖的感覺。
太陽從海平面探出頭來,到了朝霞迎曦的時間。看起來像在山的對面的西方天空仍殘留著夜色的痕跡,影子長而濃,不過光線並不像薄暮時那般張揚,我很喜歡這段時間,就跟喜歡沿海毫無風情的小路一樣。
眼睛在無意間瞄向手錶,指針指著六點四十二分,口中呼出的氣息染上了白色,我意識到冬天已經近了。
就在這時候。
「七草。」
聽到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於是我抬起了頭。
堤防上站著一名少女。
那少女穿著看起來眼熟的水手制服。肩上斜背著款式簡單的深藍色書包。微弱的朝陽在她白皙的肌膚上淡淡地渲染出顏色。柔順的黑髮隨著來自海上的徐風飄動。
她就站在堤防上,筆直地望著我。這樣的身影看起來頗具戲劇性,就像昏暗朦朧的景色之中,唯獨有個人鮮明地浮現出來似的,為何直到剛才我都沒有注意到這麼顯眼的少女?我經常會漏看重要的事物。
「真邊?」
我下意識地停下腳步,心裡非常震驚,感覺全身的血液瞬間被抽走──那女孩是真邊由宇,真的嗎?這怎麼可能!
真邊毫不猶豫地沿著堤防朝我這邊走來。
「好久不見,七草。」
「啊,嗯,好久不見。」
「有兩年沒見了?」
「差不多吧。」
「七草一點都沒變呢,我一眼就認出你了。」
我才想這麼說呢。
真邊由宇還是真邊由宇,跟我記憶中的她一模一樣,聲音、步調、表情,一切都還是這麼筆直。現實中才沒有完美的直線,除了她之外,其他人都在某些地方偏了歪了,所以她看起來才會這麼突兀,就像拙劣的合成照一樣,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她從堤防上跳下來,來到我眼前。咚!宛如斷音的著地聲在清晨睡得迷迷糊糊的景色中作響。
「我有事想問你。」她說。
「嗯?」
「這裡是哪裡?」
「階梯島。」
「沒聽過的地方啊。」
「似乎也沒有標記在地圖上喔。」
「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方?」
「我怎麼知道?」
「那七草你呢?」
「這我也不知道。」
「明明是你自己的事你卻不知道?」
「妳不也一樣。」
為什麼自己會在這座島上,真邊本身也無法理解。
不過她點了點頭,大概是因為不得不接受吧。
「話說回來,我不想上學遲到。」
「是喔。」
「這裡是橫濱嗎?」
「是嗎?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然而也有弄清楚的事。
真邊由宇對階梯島一無所知,今天早上才新來乍到。
「有點儀式性的事要進行,妳可以配合一下嗎?」我向她問道。
「需要花多少時間?」
「不用幾分鐘就結束了。」
「我明白了,可以啊。」
階梯島上有幾條規則。
按慣例,這些規則得由剛造訪這座島的人遇上的第一位島民來說明,我當時也是這樣。
「妳叫什麼名字?」
「真邊由宇。你忘了嗎?」
「當然沒忘啊,只是這也是儀式的一部分。」
說明規則時首先必須詢問對方的名字,肯定沒有設想過原本就認識的人會在這裡碰面的情形吧。
「這裡是被丟棄的人的島嶼,想離開這座島,真邊由宇就必須找出失去的東西。」我說。
這是階梯島上最基本的規則,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說的,通常認為是住在山上的魔女,不過魔女之類的誰知道是否真的存在?
「被丟棄的人的島?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待在這裡的人全都是被丟棄的人。」
真邊皺起臉龐,連扭曲的臉看起來都很直,我心想這還真是矛盾啊。
「丟棄人類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不過人們很常說吧,像是被戀人拋棄啊、被公司拋棄等等。」
「七草也被丟棄了嗎?」
「嗯,妳也是喔。」
「被誰?」
「誰知道啊。」
「被不認識的人丟棄,這種事有可能嗎?」
真邊由宇生性就是無法將疑問放到一旁。
只要有什麼事她無法理解,她就會不斷地發問,無論何時都追求著完美正確的答案,相信它確實存在於這個世界。
然而現實中的確有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像我這種人,目前為止都沒有對哪件事給過正經的答案。
「很有意思的疑問,不過妳不想上學遲到吧?我們邊走邊說?」
「要去哪裡?」
「去找一個比我更了解詳情的人。」
「什麼樣的人?」
「見了妳就知道。」
真邊點了點頭,我們開始移動。
「話說你不覺得今早的氣溫太奇怪了?」
「妳以為現在是幾月?」
「不是八月嗎?不過就快進入九月了。」
「不,其實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了。」
看來真邊最近三個月的記憶都沒了。造訪階梯島的人全部都會喪失來之前的記憶。
「莫名其妙。」真邊表示。
「我也有同感。」我回答。
我在心底偷偷地嘆了一口氣。與她重逢讓我升起焦慮、煩躁、憤怒等等的負面情緒,但我握著拳頭,忍著不讓這些表露出來。
在早晨的海邊與她碰到面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一切都可以歸結給偶然,但令我無法接受的是更根本的事情。
──為什麼真邊由宇會在這座島上?
不明白為什麼,也不想去明白。既沒道理,也不應該發生。
老實說,唯有她的臉是我絕對不想再看見的。
第一次見到真邊由宇是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不,嚴格來說,第一次相遇應該是在更早之前。我和她上同一所小學,如果把簡短的對話也算進去,想必在更早之前我們就已經交談過,話雖如此,但我是在小學四年級那個冬日的回家路上,才明確地意識到真邊由宇這個人的存在。
簡單來說,當時的真邊由宇是個遭到欺凌的孩子。小學生一到四年級就多少懂得一些社會性的常識,班級內部開始出現派系,在交談中察言觀色的技巧也變得很重要。
真邊由宇是個對這部分很生疏的孩子。
雖然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什麼,但她被班級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女學生──名字已經想不起來了──給盯上。小孩子的惡意都很直接,因此也曾發生一些就連我這個旁觀者都覺得看不下去的事情。
無論受到多少不講道理、單方面的惡意,真邊由宇都沒有將任何情緒顯現在外,也不會哭喪著臉。即使她的體育服裝被扔進水窪、室內拖鞋被人用麥克筆塗鴉,她都只是一臉不可思議地偏頭納悶。
當時我以為那是她竭盡所能裝出來的逞強。
如今則知道其實不是那樣。
真邊由宇真的純粹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體育服裝非得被扔進水窪不可呢?她無法順利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感受不到惡意的她既無法悲傷也無法動怒,所以她才會偏頭感到不解。
我並非正義的夥伴,所以也沒有想過要為她做點什麼,就連視而不見的態度也沒能讓我心生罪惡感,我似乎還曾經想像過幾次,倘若她向我求助,難道我真能為她做點什麼?一些細節我已經記不得了。
不管怎樣,小學生雖然具有如此陰暗的一面,但同時畢竟還是擁有純真的地方,比方說牛奶這個例子。
牛奶是一隻白色幼犬。
牠應該是一隻棄犬,脖子上雖然沒有項圈,但毛色很乾淨。牛奶三不五時會出現在校園中,每次都讓班上同學歡欣無比,我也曾經餵牛奶吃過幾次營養午餐剩下來的麵包。在牛奶的面前,教室內的階級制度等等都毫不重要,班上同學都會變成大人理想中的純真孩童,這種兩面性想想還真滑稽。
在我們這個小規模的世界中,牛奶是和平的象徵。難以用言語表示的某種秩序具體呈現在這隻白色幼犬上,就像另一方面,真邊由宇具體呈現了什麼叫做沒道理一樣。
如此人見人愛的牛奶流著血倒在地上。
就在一個冬天的回家路上。
一眼就看得出來牠被車撞了,後腳的部分似乎被壓碎,牠肚子上柔軟的毛還在上下起伏,那緩慢的動作很不可思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當時剛好是放學時間,大批孩子站得遠遠地圍觀牛奶。「好可憐。」有人毫無責任感地喃喃道,我也有同樣的想法。
在場的每個人都只是旁觀者。
我們沒人打算成為牛奶車禍的當事者。
可是偏偏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真邊由宇。
她跑到牛奶身邊,毫不猶豫地抱起牠,血跡在白色制服上暈染開,紅得非常鮮明。我記得有人嘟噥了一句「好髒」,但這點我實在無法認同,在我看來,她很美。
真邊由宇邁步就跑。
我不假思索地追著她跑。如今我已經想不起來當時是什麼樣的心情,總之,我就在她後面追著。
真邊由宇筆直地跑著。
她的表情並不悲愴,只是一臉認真,專心地看著前方。似乎壓根就沒有想過她懷中的牛奶已經快要一命嗚呼了。
「沒問題。」她喃喃說道。
「絕對沒問題。」
回想起來,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
不過到達動物醫院時,牛奶已經沒有呼吸了。
醫生搖了搖頭,那一刻,我才見識到真邊由宇哭泣的臉龐。
她皺起臉來放聲大哭,猶如野獸的嚎哮。制服依舊血跡斑斑,眼淚滾滾滴落,她用盡全身力氣痛哭。
我應該沒有哭,不過也可能哭了,記不清楚。
她的身影太過鮮明,以至於我如今已經想不起自己當時的模樣。
真邊由宇和我是從那天才開始變得熟稔起來。
從那天一直到她在國中二年級的暑假搬家為止,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行動。
越了解就越發現她很特殊。她眼中的世界似乎充滿希望,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理想就一定會實現,她對此深信不疑。
為什麼呢?
牛奶明明就死了。
為何她還是能夠如此堅信這世界是合理的呢?
雖然好幾次都浮現這個疑問,但我終究還是什麼都沒問她。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消失吧,群青 Fragile Light of Pistol Star 02
95折
特價124元
加入購物車
消失吧,群青 Fragile Light of Pistol Star 01
95折
特價124元
加入購物車
凶器是毀壞之黑的呼喊 (全)
79折
特價205元
貨到通知
名為戀情的不潔之紅
79折
特價205元
貨到通知
消失吧,群青( 全)
79折
特價198元
貨到通知
北野坂偵探舍:人物心理描寫不足
9折
特價269元
加入購物車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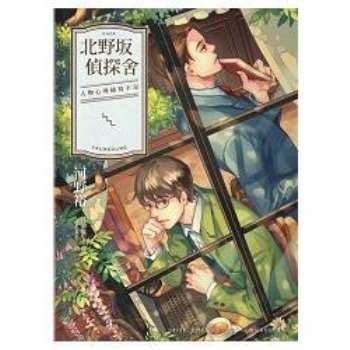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