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一層透明的膜
芥川奬得主李琴峰首部散文集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以肉身與世界對峙
直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芥川奬得主李琴峰首部散文集
若說小說是一種「提問」的語言,散文或許便可說是一種「解答」。
本書展現李琴峰從一名剛出道的新手作家,到成為首位臺籍芥川獎得主之間四年半間的思索與風景變化。全書以「聲、生、性、省、星、靜」六個篇章展開:談語言,也談愛與性;談創作,也談生與死;談成名的代價,也談成為人本身的勇氣。
這是一名性格乖僻彆扭的人類,拒絕被強行貼上任何標籤,試圖捕捉「世界」與「他者」的巨大瞬間所飛散的細微花火,用文字刻劃自己的精神星圖,只為尋找那即使「隔著一層透明的膜」也能抵達的,屬於自己的語言。
這是李琴峰獻給世界與自我,既迫切又有勇無謀的「解答」。
這些文字裡潛藏的是我的精神,不論是輾轉難眠的深夜,或是煢然孤孑的黃昏,我都是靠著書寫與刻劃文字來度過的。如今,且讓我放手讓這些篇章流傳於世,祈願這些文字、這些精神的碎片,在徬徨於活字之海後不致輕易消失於虛空之中,而能被誰的雙掌接住,成為誰的精神支柱。若能如此,我心已足。
──李琴峰
本書繁體中文版仍由作者本人親自譯寫而成。
目錄
目次
一種創世:代序
第一章 聲:往返於語言之間
隔著一層透明的膜
取得日本語籍的那一天
中間╱非中間的風景
就像兩臺獨立的機器
創作的源泉‧中二病
笑一笑就被反日
第二章 生:降生於攘攘人世
我之所以想要一了百了──三十歲生日紀念散文
夢境
國中的夢
死與生的隨想──《生之祝禱》出版紀念散文
微小的敘事,或是對自由的信仰
剛啟程的旅途,未酬的壯志──追悼翻譯家‧天野健太郎
第三章 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星光下的電影節
沒生產性的初戀
像樣的戀愛
親愛的疼痛
有分量的小說──性少數書寫之我見
發芽前便死去的戀愛種子
第四章 省:旅行、歷史、省察
最後的海外旅行
濃霧深處的霓虹
夏天、煙火、時間碎片
在你稱呼我為外人之前
可愛的日本、可悲的歧視
日本人用刺刀殺了好多小孩
永無止境的「越境」之旅──紀念東山彰良《越境》臺灣版出版
所以我才必須和珍珠奶茶說再見
新宿二丁目的熠耀輝煌──《北極星灑落之夜》出版紀念散文
單車邂逅記
第五章 星:芥川獎相關篇章
十年一覺文學夢
虛構的力量
崩潰的深夜
芥獎三日
日語戀歌
筆名的由來
執筆四春秋
賴以生存的奇蹟──芥川獎頒獎典禮演說全文
第六章 靜:書與電影
長大成人的王寺滿與她的愛之國──中山可穗《王寺滿三部曲》
單車是時間的魔法──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完美而不完美的我們──王谷晶《不?完美的我們》
逸脫者們的風景──今村夏子《變成樹的亞沙》
「多樣性」的多音複旨──朝井遼《正欲》
道德世界的非道德之光──電影《單袖之魚》
賦島以光──電影《我們的青春,在臺灣》
雪何時才要停呢?──電影《致潤熙》
齒牙閒話
後記:隔著薄膜的傳話遊戲
試閱
文摘
隔著一層透明的膜
十二年前,我是住在臺灣鄉下的女國中生,不認得一個平假名;十二年後,我是住在日本大都市的上班族,得到了「群像新人文學獎」。驀然回首,這一路走來可真是走得夠遠了。
為什麼妳會想學日語?這問題被問過幾次,我已經數不清了,每次被問,我都只能皺起眉頭煩惱──因為我學日語根本沒有什麼足以對人道的,那種好懂的契機,就只是某天突然想到,「啊,我想學學看日語」,一切就開始了。既不是為了就業,也不是為了趕流行,就像砸中牛頓腦袋的那顆蘋果,那是一種天啟一般的念頭。
之後我就邊唱著動漫歌,邊把假名文字一個個敲進了腦海中。在那考上明星高中即是人生唯一目標的極其高壓的國中生活裡,文學與日語是我培養出的小小興趣。日語是種學了愈久,便愈能感受箇中妙味的語言,流麗的平假名之海如寶石般鑲嵌著顆顆漢字,月光撒下,整片海就幽靜地閃閃發光起來。
不是每個人都懂我的興趣。雖然沒有明講,但當時的班導顯然對我自學日語感到不大痛快,心裡恐怕想著「為什麼要學殖民過臺灣的民族的語言」;他也在課堂上說過「假名不過是在模仿漢字」這種話。我可不在乎班導怎麼想,反正我生性喜好反抗,頂撞權威可說是家常便飯。
不久,我就上了大學、研究所,開始把日語、日本文學與日語教育學當成專業修習,不知不覺間竟還用日文得了文學獎,成了作家。都走到這裡了,想必我的日語已經到了爐火純青、駕輕就熟的境界──但現實不見得如此美好。雖然我的確是所謂的雙語者──以第二語言學習論的術語來講,是「添加性雙語者」(additive bilingual)──,但我是在過了語言學習的臨界期(critical period)後才開始學日語的,因此日語絕無法等同於第一語言。雖然聽起來有點矛盾,但我的日語愈是精進──或愈是被認為精進──,我便愈是深切感受到日語並不是我的第一語言這個事實。
有時,我會說出一個單字後才發現自己弄錯了重音,只能在心裡暗自懊悔;有時,我明明知道有個詞能精確表達我所想表達的概念,翻找腦中的字典卻總找不到能對應那個詞的語音結構,只能一直說「那個──」來拖時間;有時,我感覺彷彿有人把連接我大腦與舌頭的神經切斷了那般,即使大腦發出關於發音的指令,舌頭卻怎麼也不夠靈活。若是生了病情況就更糟了,一點小感冒都可能使我產生類似失語症的症狀。許多時候,我也會深感外語副作用(foreign language side effect )的影響,的確讓我的思考能力下降不少。
有個慣用的講法是「語言的高牆」,我常會想,若屏障在語言之間的事物真的是堵牆,那該有多好,牆這種東西,翻過去就是了。然而阻隔在我和日語之間的與其說是牆,不如說是一層透明的薄膜,這膜貼在天地之間,無法翻越,平時眼不可見,甚至感覺不到,因此常會忘了它的存在。但它確實在那裡,時而亮起顏色宣示它存在,時而突然硬化阻絕越境。即使我伸手掬起膜的另一頭那散落一地的語言寶石,總也像戴著一隻塑膠手套,難以赤手檢視寶石的手感。
隔著膜也是有好處的,這樣才可以以解析的角度觀看日語這種語言,我常因此注意到許多母語人士所未能發現的盲點,而受誇讚說我對語言的感覺敏銳。但這種語言敏銳度對一名作家而言不過是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罷了,就像公車司機必須看得懂道路標示一樣。
所以直到今天,我依舊不斷地自問自答:這樣的我究竟能對日本(語)文學貢獻些什麼。可惜目前我還沒有答案,也不知道會不會找到答案。即使如此,我仍毫無根據地相信,肯定有某種語言,是即使是我,不,正因為是我──以自己的意志接納了日本與日語,也為日本與日語所接納的我──,才能寫得出來的。那種語言究竟長什麼樣子,我現在還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今後也會為了尋找那屬於我自己的語言,而持續這趟旅程。
所以我今天也隔著一層透明的膜,繼續用日文書寫著世界。
(二○一七年八月)
取得日本語籍的那一天
就在幾天前,我以日文書寫的小說《独り舞》繁體中文版《獨舞》,正式在臺灣上市。作者和譯者是同一人的文學作品,雖算不上空前絕後,卻也相當罕見吧。正如宣傳句「臺灣首位獲日本群像新人文學獎優秀作」所說的,我是一名以日中雙語進行創作的臺籍作家。
談起以日文創作小說的臺籍作家,溫又柔和東山彰良堪稱前輩。但他們都是從小便移居日本,是在日語裡長大的作家。
我卻不然。雖然我現居日本,但移居日本卻還只是幾年前的事。那時我還只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日本一個親戚家人都沒有。在我的親戚和家人裡,別說是日籍人士或旅居日本了,就連懂日文的人,也一個都沒有。
所以在我的孩提時代,我幾乎是沒有機會接觸日語的。在國中歷史課教到「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形成經過以前,我甚至連「平假名」與「片假名」這兩個詞都沒聽過。我還記得在品客洋芋片外罐的多語食品標示上看到「召し上がる」這個日文詞彙時,由於當時只看得懂漢字,便望漢字生意,以為是「向上召喚」的意思。的確,想吃品客洋芋片,得將洋芋片從筒狀容器裡向上拿出才行,難道在日文裡這種行為就稱作「召喚」嗎?那時的我覺得相當有趣。
包括我在內,大概誰也沒想到,那個連「あいうえお」都看不懂的女國中生,十二年後竟會獲得日本純文學代表性的文學獎「群像新人文學獎」,成為日本文學的作家吧。
為什麼妳會想學日語呢?
打從旅居日本,這問題我已被問了不下百遍,而我總是歪著頭,煩惱著不知該如何回答。
若有什麼易於理解的動機,比如說為了就業啊,或因為喜歡日本動漫什麼的,那倒是不難回答,難就難在,我並沒有這類動機。以結果而論,我的確在日本就業了,也的確喜歡日本動漫,但我覺得這些都只是我學習日語的結果,而非理由或契機。
所以我也只好回答:其實沒什麼契機耶。十五歲的某天,不知為何突然有個念頭,「不然來學個日語吧」,從天而降打中了我,從此開啟了我的日語學習之路。若說世上真有天啟這回事,或許就是如此吧。
但當然,一個人不大可能憑著天啟就學一門語言十幾年。雖然剛開始只是某種沒來由的念頭,但實際學過日語後,我便為日文之美所魅惑,從此欲罷不能,轉瞬之間竟已過了十幾年。
你問我美在哪裡?
首先是文字,日文文字夾雜漢字與假名,密度不均看來像是某種斑點花紋,這就有一種美感,彷彿是漢字的寶石鑲嵌在平假名的大海裡,或是漢字的花瓣點綴在平假名的樹梢上,當月光照下,大海便閃閃發亮,風一吹過,櫻瓣便紛紛飄落。
接著是音韻,日語的音節基本上是「開音節」,也就是「子音+母音」的組合,比如說「こ」是「k」+「o」而「と」是「t」+「o」。並非所有語言都是如此的。「子音+母音」的構造持續發音,聽起來便有如機關槍,噠噠噠噠噠,極富節奏與韻律感,使人(使我)不由得想出聲重複朗誦。啊,在閃耀的海面和飄落的櫻瓣後突然掏出機關槍這種譬喻,真是抱歉。
總之,在那之後我便循著初級、中級、高級的順序,一階一階爬上了日語的階梯,不知不覺便開始用日語自言自語,就連夢境裡的角色也開始講日語了。我來到日本,在日本企業就職,然後突發奇想地開始用日文寫小說,而那竟也僥倖得了獎。對現在的我而言,日語已經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事物。
沒什麼特別的契機,不過就是一時興起,我開始學習日語,而那卻大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但倘若當初我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帶著某種明確目的接觸日語的呢?恐怕我就無法走到今天了。我真心如此認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若是帶有具體目的,那麼日語也只是純然的工具手段,一旦達成目的,工具便棄之可也。對我而言日語並非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嗯,多像戀愛。
若有人問我為何能把日語學得這麼好,我大概也只能說,因為我愛上日語了。
在我還在以中文練習寫小說的那段時間裡,我從沒想過自己有天竟能用日文寫小說。
無疑,我是喜歡語言表達的,因此即便當時日語仍破破爛爛,我仍盡力想用日語表達些高深的什麼。在初級階段的作文課裡,我就偏偏愛用「厳寒」「酷暑」「耽溺」這種任哪個出版社的初級教科書都絕不會收錄的詞語。在練習日語演講時,我甚至當場背誦藤村操〈辭世文〉這種日文古文的文章。下課時間我也老是纏著老師,問些五段活用、四字熟語、漢文訓讀的問題,想必讓老師相當頭疼。
同時,我也練習聽寫動畫和日劇的臺詞,閱讀日文小說,自學漢文訓讀,想方設法試圖拓展自己的日語表達能力。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所擁有的日文詞彙和句法,在質與量上都無法表達我所想表達的事物與心緒(嚴格來講其實現在也仍無法)。何況文學作品,這種需要高度、多樣且精準表達的藝術,我一直覺得自己身為非母語人士,是寫不出來的。
文學既是「語言的藝術」,同時也承擔著「拓展語言本身的可能性」此一任務。那麼對一個不屬於我的語言,我是否真有辦法做到這種事?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是做不到的。
這樣的想法其實相當詭異:語言之為物,本就不該屬於特定個人或群體,而該是更加開放性的存在,為不同時空的人類所共享,與歷史一同演化的事物。即使如此,我依舊顧忌著自己非母語人士的身分,不敢將不是自己母語的語言,當作是「自己的東西」,不遵從某種既定規範(如語法、詞語在辭典上的語意、母語人士的語感等等),而妄自尊大地嘗試「拓展其可能性」。
非母語人士是語言世界的難民,一旦離開兒時所習得的第一語言的領域,其語言使用的正統性便不被承認。其實即便同是母語人士,也有語感大相逕庭的時候,但若非母語人士和母語人士的語感不同了,總是母語人士的語感會被認為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非母語人士對於該語言,是沒有解釋權的,這就好像移民往往不被認為有權利開口干預移居國家的內政一樣。
做為一個非母語人士,便必須時時刻刻誠惶誠恐,恐懼著有人會指著自己說:「你的日語很奇怪,不自然」。而非母語人士自身,也往往無法完全信賴自己的語感。
所以當我獲得「群像新人文學獎」時,固然喜悅自己作為作家出道,同時也相當開心,自己「作為一個日文使用者受到了承認」。我以不甚熟稔的手勢,一邊參照辭典和網路資訊,一邊戰戰兢兢寫下的第一篇日文小說,那正是我恬不知恥的,對「拓展語言可能性」的嘗試。本來寫小說這回事便有如走鋼索,若使用的是第二語言,那鋼索更是脆弱如蛛絲。我知道自己一個不小心便可能墜落而摔得粉身碎骨,卻仍奮不顧身地用力一跳。所幸這個跳躍沒有導致墜落,就像是有人接住了我,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交給我一枝筆,溫柔地告訴我:「沒事的,妳就放心地待在這裡,放心地寫吧。」
這正是我期盼已久的話語。歷經了嘔心瀝血的學習,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名為「日語」的筆,我終於知道自己能信任這支筆,這讓我感到相當安心,就好像得到了「日本語籍」──不是「日本國籍」──一樣。
國籍是封閉的,必須達成規定的條件、按照規定的手續、通過規定的審查才能入手,有時想拿到新國籍還得先放棄舊國籍。但「語籍」卻是開放的,任誰都可以在任意時刻入手,若有那個心,甚至也可以保有雙重,甚至三重語籍。取得國籍需要繳交厚得像電話簿般的申請資料,但取得語籍只消有對語言的愛,以及一支筆便可。國籍在國家滅亡之時便會消滅,但語籍卻直到疾病帶來遺忘,或是死亡造訪的那天為止,任誰也無法剝奪。
終於取得日本語籍的那一天,我走出講談社大樓,抬頭望向濃密漆黑的夜空,深吸了一口大氣,然後在心裡默默做了個決定。
我要用自己手中所握的這支雙重語籍的筆,來彩繪出自己所看到的世界。
(二○一九年二月)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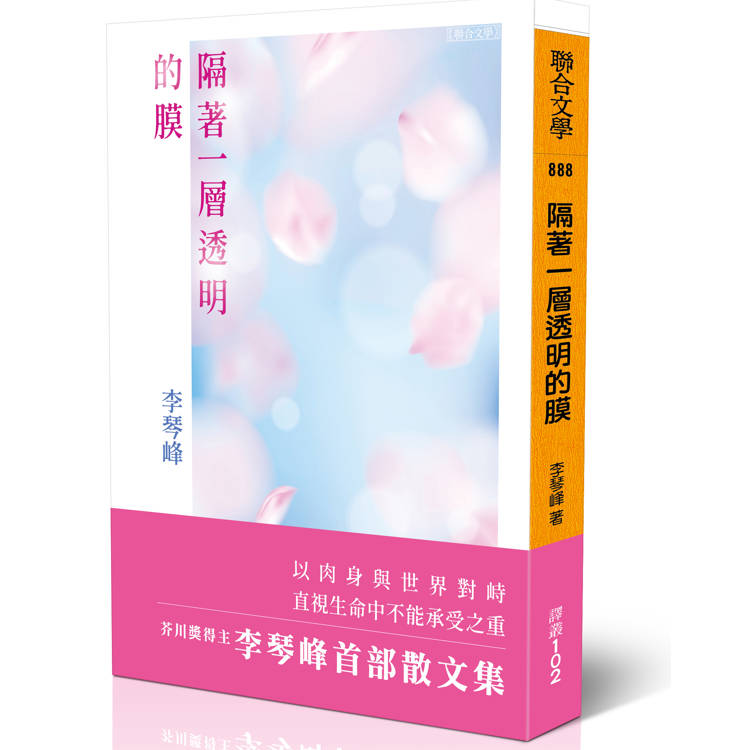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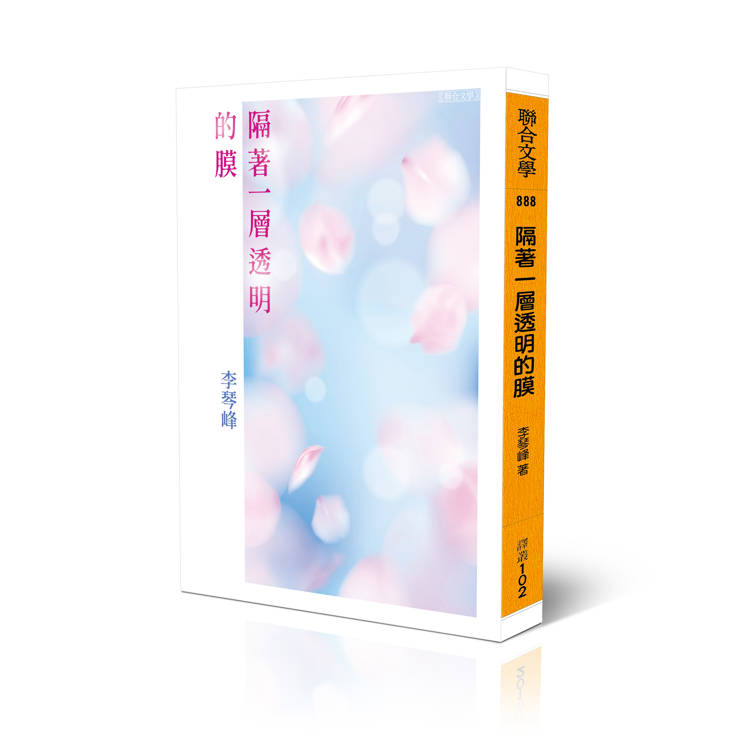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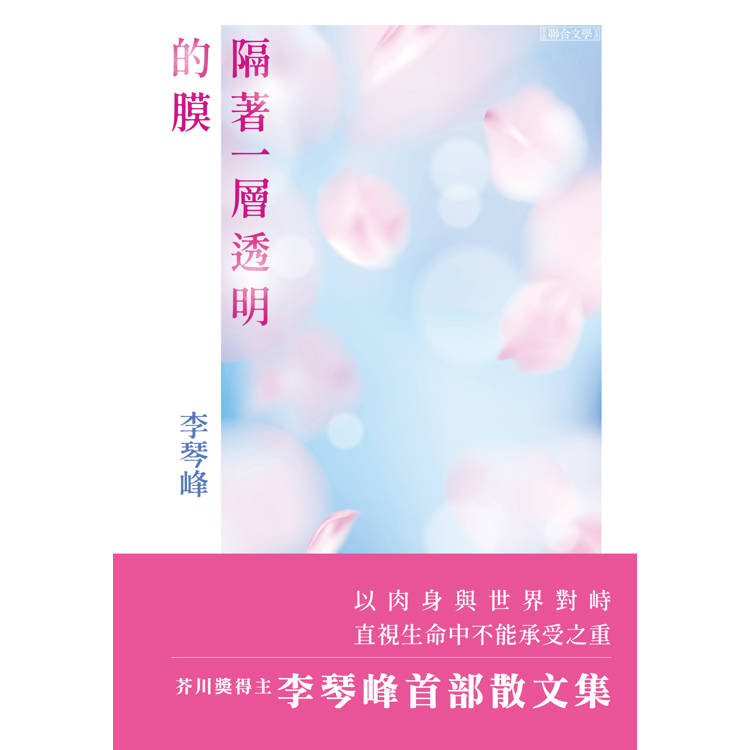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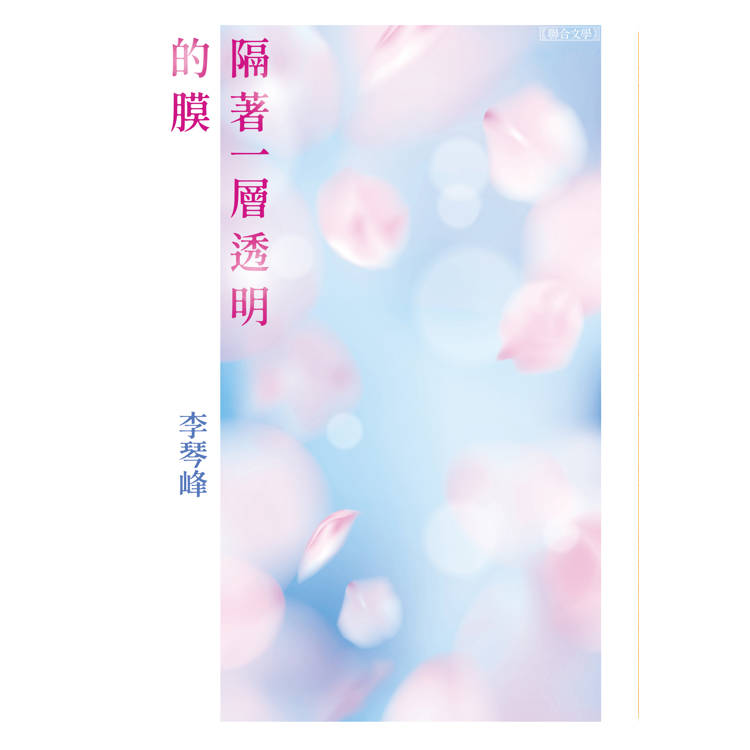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