綾羅歌.卷二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書法大師董陽孜女士親筆題字,氣韻奔騰,剛柔並濟,豪放恣意※
亞洲最暢銷武俠女作家──鄭丰
風起雲湧,覆手繁華,玄妙壯闊重磅力作登場!
***
在巫童羅欽的夢境觀望之下,沈綾被主母趕去南方大梁京城建康長住,
並在「沈緞」舖頭充當學徒,認真勤奮,頗受賞識;
一次因緣際會下,他結交了王謝家的子弟,視野大開,自信漸增。
北方洛陽卻陷入了空前的動盪,兵災不斷,
沈家父子不得不攜帶大批絲綢金銀離城,打算南下建康避禍……
長年在村中格格不入的巫童羅欽,驚然得知童年玩伴柔然公主阿郁將遠嫁魏國和親,並指名自己隨行。
他生平第一次離開磈磊村,來到西魏首都長安,
好奇夢中的沈綾究竟是不是真實存在的人……
庶子沈綾和巫童羅欽之間,究竟有著何種特異的連結?
身處天涯海角的兩個少年,又將在南北朝的亂世之中,有著何等動蕩起伏的際遇?
試閱
【第一部 洛陽沈緞】
第一章 豎子
「備車,備馬!主人、主母、郎君和小娘子們要出門啦!」 洛陽城阜財里東沈氏大宅中,大廳門外上馬堂前,一個身形微胖、頭頂微禿的中年宅院管事,一疊聲地呼喊催促著。數十名衣著鮮淨齊整的馬夫和僕人奔趨來去,忙中有序地備好了兩輛簇新的馬車,馬車車身為紅柚木,車輪為青榆木,車轅則為水曲柳所製;車壁漆成紅色,車頂鑲金,飾以五彩纓絡。每輛車前各套著兩匹高大健壯的北方駿馬,馬轡繫環皆以真金實銀打造,鎏金上綴著銀錢、寶珠、飛燕和駿馬等裝飾,在日頭下閃閃發光。四名馬夫牽著四匹駿馬來到正屋門外,駐馬等候;幾個童僕快手在兩輛馬車門旁的青石板地上放置了半尺高的純銀踏腳凳,各自用衣袖快速將銀凳擦得潔淨光亮。 那宅院管事來到馬車之旁,上下左右仔細檢視,又伸出胖胖的手指,小心梳理從車頂懸掛而下的五色琉璃纓絡,接著探頭入內審視,拍去繡金錦緞座褥上的些許灰塵。眼見一切安排妥當,宅院管事才對馬夫和僕人點點頭,說道:「可以了。主母的坐騎呢?」 後方一個馬夫高聲答道:「主母的『踏燕』在這兒,已上好鞍鞬轡頭了。」牽過一匹高大的青驄花斑馬而來。這匹馬不但矯健雄駿,身上裝飾更是奪目,金帶扣、銀帶箍、鎏金鐵馬銜、鑲玉銀馬籠頭,配上嵌有馬形玉飾的鞍帶、銀馬鐙,馬鞍上鋪著大紅繡花錦緞,光鮮燦爛至極。 宅院管事點點頭,說道:「甚好。我這便去稟報主人。」快步趨入正廳,在門口躬身稟報道:「啟稟阿郎,馬車已備妥了。」 大廳正中,一個華服男子盤膝坐在金銀錦墊之上,正低頭查閱身前几上一本厚厚的帳冊。男子衣著雖華貴,一雙手卻頗為粗糙,撫著帳冊的指節上長滿了繭子。一個留著山羊鬍子的老者捧著幾本帳冊,恭敬地跪在一旁伺候。 華服男子聽見門外宅院管事的稟報,並不抬頭,只擺手道:「知道了。冉管事,派人去請夫人、郎君和兩位小娘子。」 那姓冉的宅院管事應了,立即吩咐僕人婢女去恭請主母、郎君、小娘子等人。 華服男子闔上了帳冊,對那山羊鬍子道:「桑園的帳可以了。絲坊的帳,我明日再看吧。」 山羊鬍子答道:「謹遵東家之命。」小心翼翼地闔上帳冊,疊放整齊,捧在懷裡,起身向華服男子躬身行禮,退出正廳。 華服男子站起身,走到大廳門口。他約莫四十來歲年紀,身穿赭色團虎紋錦袍,體形略瘦而結實,腳步沉穩,黑瘦清俊的臉上透出精明警醒之色。若看服色裝扮,這人顯然是這座大宅的主人;若看他的體態舉止,卻似個飽經風霜的江湖人。 華服男子望向垂手立在門外伺候的冉管事,問道:「壽禮可備妥了?」 冉管事答道:「回稟阿郎,都已齊備。老奴方才與大郎一道,再次檢視過了給駙馬準備的壽禮。」 華服男子道:「可是我上回交代的,雙蝠萬壽紋大紅織錦?」 冉管事道:「正是。昨日大郎和李大掌櫃一同挑撿了極品雙蝠萬壽紋大紅織錦一百疋,已裝入十只檀木箱子,安置在馬車上了。」 華服男子露出滿意之色,點頭道:「甚好。」 這時,一個身穿碧綠綾羅繡衫、紫紗長裙的貴婦從廳中快步走出,身後跟著一名僕婦、一名年輕侍女。貴婦望了望門外的馬車,皺眉對冉管事道:「我的馬呢?」 冉管事連忙躬身道:「啟稟娘子,您的『踏燕』已備好了,就在門外。」 華服男子揚起眉毛,望向妻子,脫口道:「妳要騎馬?」 貴婦三十來歲年紀,一張橢圓臉,眉目間英氣十足。這時她挑起雙眉,高聲對丈夫道:「我出門時,哪回不騎馬了?」 華服男子露出微笑,安撫地道:「不、不,我可無意阻止娘子騎馬。咱們這回去給駙馬拜六十大壽,公主想必樂意見到娘子騎馬的英姿,就只怕..只怕駙馬不喜我等唐突。」 貴婦一笑,說道:「我在大門之外下馬,駙馬又怎會知道我是騎馬去的?」轉頭問冉管事道:「大娘和二娘的馬都備好了麼?」 冉管事還未回答,華服男子已皺起眉頭,插口道:「雁兒剛剛訂親,怎能騎馬上街?盧家可是有著百年傳承的漢人世家大族,絕不樂見未進門的新婦如此拋頭露面。」 貴婦「哼」了一聲,撇嘴道:「你們漢人,偏有這許多規矩!好吧,大娘就乘車好了。冉管事,快給二娘備馬!」冉管事連聲答應了,自去吩咐。 華服男子見妻子堅持自己和小女兒要騎馬出門,只能苦笑,不再爭辯。 這華服男子姓沈名拓,正是這座沈家大宅的主人。沈家乃是洛陽首屈一指的絲綢大賈,富可敵國;沈氏原為南方漢人,三十多年前隨齊朝大臣王肅背齊歸魏,定居洛陽。王肅出身琅琊王家,父親王奐曾任雍州刺史,後遭齊武帝蕭賾殺害,王肅憤而歸降北魏。王肅初投魏時,高祖方遷都洛陽,見王肅博學多才、通曉舊事,因此大加重用,封為尚書令,呼其「王生」,延請他為營建新都出計獻策,更將自己的妹妹陳留長公主嫁給了他。高祖並命將作大匠在洛陽城東南興建巨園華宅,供王肅和公主居住,並將該里命名為「延賢里」。 王肅為了討好公主,並炫耀南方絲織技巧,於是讓出身絲綢世家的屬僚沈譽養蠶取絲、染織成綢,製出花樣新穎的綢緞,獻給公主揀選。公主一見之下,果然喜歡非常,愛不釋手。王肅甚是滿意,將沈家所製綢緞命名為「沈緞」,令沈譽大量製造,除了供公主選用,亦進貢北魏皇室。洛陽城初興,數萬皇族貴宦受命遷入城中,時值魏高祖極力漢化,下令人人改穿漢族衣裳,絲綢需求因而大增。沈譽覷見商機,於是在洛陽城外購入數十頃桑園,廣植桑樹,採桑養蠶,煮繭取絲;又建造了百餘座絲坊、染坊和織坊,巧用南方絲織之法,織出圖案精緻多變、質地輕軟細柔、色彩鮮豔亮麗,獨樹一幟的「沈緞」,更與山東的「大文綾」、「連珠孔雀羅」和阿縣的「縞」齊名。「沈緞」得長公主青睞有加,很快便受到其他皇族富宦的重視,爭相採購,舖頭從此門庭若市、生意興隆,不過一代之間,便致暴富一方。 到沈拓時,已是沈家第二代;由於高祖鼓勵胡漢通婚,因此沈譽讓獨子沈拓娶了鮮卑女子羅氏為妻。高祖遷都洛陽後,敕令胡姓一律改為漢姓;羅姓原為叱羅,羅氏的祖上叱羅鑒曾為大魏名將,戰功彪炳,惟傳到羅氏時,再無男丁,家族已趨式微。遷洛的鮮卑貴族雖大抵漢化,人人說漢語、著漢服,但羅氏一族仍未脫粗獷勇武之風,羅氏自幼便騎馬射箭,勇健豪邁,英姿颯爽;在她心中,女子騎馬射箭、在外出行遊走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與漢人禮俗大相逕庭。沈拓和妻子羅氏雖結褵多年,卻仍不時因漢胡習俗差異而小起爭執;而羅氏性情強悍,大多時候都以沈拓讓步遷就收場。 正當羅氏點頭表示滿意時,一個少女跨入大廳。她一出現,整個大廳似乎陡然亮了起來;那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女,天生麗質,容顏明媚無方,讓人一見便難以移開視線。她身著絳色冰羅霧縠長裙,腰間束著水綠繡纈腰帶,纖腰如柳,體態婀娜,正是沈拓和羅氏的長女沈雁。她在廳外聽見了父母的對答,笑盈盈地走上前,攬住父親的手臂,撒嬌道:「阿爺,怎地阿娘和小妹都能騎馬,唯獨我不能騎馬出門?」 沈拓疼愛地望向長女,拍拍她的手臂,輕笑道:「妳就要嫁入江北的世家大族啦,還問阿爺為甚麼?」 沈雁道:「誰曉得?說不定盧五郎就喜歡新婦騎馬呢?」 羅氏揚眉道:「盧五郎要是不讓妳騎馬,妳就回家來,阿娘讓妳騎個夠!」 沈雁嘻嘻一笑,說道:「還是阿娘疼我!」 羅氏笑著向女兒招手,說道:「來,讓阿娘看看妳的新衫裙。」 沈雁放開了父親的手臂,走向母親。羅氏牽著女兒的手,母女倆一起來到大廳東壁上一面巨大的銅鏡之前。羅氏言語舉止雖爽快率直,對女兒的關懷可是細緻入微;她細細檢視女兒身著的嶄新冰羅霧縠衣裙,臉上神色愛憐橫溢,點頭讚賞道:「剪裁功夫不錯,馮裁縫的手藝確實了得!咱們挑一疋上好的『沈緞』,就請織室的馮裁縫給妳做大婚之日的嫁裳吧!」轉頭對身後的侍女道:「婇兒,妳說如何?」 卻說羅欽獨自離開了磈磊村,往西方行去。這是他第一次離開磈磊村,又是獨自出行,無人帶路,連馬也沒有,不禁大感茫然,才走出村口數丈,心頭便感到一陣驚慌,擔心自己已經迷路了。 他定下神,從懷中取出牛皮地圖,翻來覆去地觀看,勉強辨明了方位,又抬頭看看初升的太陽,辨別方向,這才收好地圖,吸了一口氣,舉步往西方行去。 他孤身行路,甚是寂寞無聊,心頭更大感恐懼不安,只能對自己說道:「你已不是個孩童啦,即使不具巫術,但你瞧那些牧童們趕著牛羊走遍整個大草原,也不見他們害怕,怎地你獨自出行,便驚慌害怕得要命,如此無用?」 但他畢竟年輕,又毫無單獨行旅的經驗,心中實在不安,於是只好低下頭,開始對著石鏡說話: 「岩瑪薩滿,是我羅欽。我已離開磈磊村口,正往西邊走去,已經走出五千步了。」 「我已經走了半天了,現在停下休息一會兒,吃點乾糧。」 「我渴了,停下喝水。」 「前面那座山尖尖的,可能就是日月山了,也不知是不是?」 「地圖上說,日月山是天的樞紐,最高的主峰叫吳姖天門山。」 「咦,前面有條河,彎彎曲曲的,似乎和地圖上畫的一樣。我正好可以在牛皮袋裡加點兒飲水。」 「前面有一群牧人,放著幾十頭羊,有黑的,也有白的。嘿,那些牧人見到我,好像很害怕,避得遠遠地,還向我躬身行禮。是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巫者麼?哈哈,其實我比他們更加害怕哩!」 岩瑪薩滿也不知能否聽見他的自言自語,即使能聽見,也並不回應,那石鏡就如一塊尋常的石頭一般安靜。 羅欽心想:「他想必能聽見我說話,否則當我遇上危險時,高聲呼救,他若聽不見,又怎能出手保護我呢?他並沒有嫌我囉嗦,要我閉嘴,那我就一直說下去也沒關係。」 他步行了一整日,天黑後,便用毛氈包著身子,在草原上睡倒;天亮後吃些乾糧,續往西行。 三日之後,羅欽來到了一座山的山腳。他抬頭望去,但見山巔隱沒在雲霧之中,中間一座山峰高高聳起,想來便是日月神山的最高峰吳姖天門山了。 他想起自己的小獸曾經住在這兒,心中不禁一酸,暗暗祝禱:「小獸啊小獸,十幾年前你被大長老捉住,來到磈磊村做我的守護獸,最後卻因保護我而死。能跟你一起長大,是我的幸運,卻是你的不幸啊!」 羅欽舉步往山上行去,一路只見到一些不知名的奇樹怪草,卻沒見到任何會動的蟲魚鳥獸。 約莫正午,來到山腰時,剛轉過一個山坳,一個巨物忽然出現在面前。羅欽嚇了一跳,趕緊往後退出幾步。定睛看去,但見那巨物說是人,卻又完全不像人;他有頭有身,卻沒有胳膊,兩條大腿直接從頭的兩旁伸出,腿下是兩隻生毛的大腳,穩穩地踏在地上,赤裸的身子垂掛在頭之下,有著圓滾滾的肚子,身下沒有腿,只有一叢亂毛;這人的臉上滿是皺紋,一頭亂髮披垂在胸前。 羅欽從未見過長相如此古怪之物,不禁呆了一呆,還未想到該如何反應,那「人」已跨著大步向他走來,因他雙腿長在頭邊,每走一步,大頭都跟著晃動。怪人大步來到羅欽身前,睜著一對細長的眼睛瞪著他,張口喝道:「來者何人?」 來到近前,羅欽才發現這怪人巨大無比,比自己高出兩倍有餘,心頭驚怕,連忙行禮說道:「這位神人,我是來自磈磊村的巫童,叫作羅欽。請問神人如何稱呼?」 那人仍舊冷冷地瞪著他,臉上露出不悅之色,質問道:「小子,你是巫者,竟不識得我?」 羅欽心頭發慌,只能老實答道:「我不識得神人......」 那人發出吼吼之聲,顯得又是憤怒,又是驕傲,昂首道:「我是黎之子!」 羅欽「嗯」了一聲,心想:「黎之子?那是甚麼人?黎又是誰?」 那人見他不言語,豎起眉毛,喝道:「你既知道我是黎之子,為何不跪倒膜拜?」 羅欽嚇了一跳,趕緊跪下膜拜,說道:「小巫拜見黎之子。」 那人哼道:「我是黎的兒子,卻不叫黎之子。我叫作噓。」 羅欽心想:「原來他叫『噓』,是黎的兒子。黎是甚麼人?我該認識他麼?」 噓晃了晃赤裸的身子,抬起右腳往地上一踩,整座山似乎都震動起來。他高喝道:「你自稱巫童,卻甚麼也不知道!村裡的薩滿都沒教過你麼?你給我聽好了!古帝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二子;古帝顓頊命重托天,命黎撐地,以分開天地;又命重主天,黎主地。我是大地之主黎之子,掌管日月星辰運行的次序。」 羅欽從未聽說過這些遠古神話,只道:「原來如此。日月每天都得升起落下,你想必忙碌得很。」 噓「哼」了一聲,說道:「可不是?我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不能歇息。你既然知道我如此忙碌,又為何來日月山上擾我清眠?」 羅欽甚感歉疚,說道:「我才剛剛來到這兒,打擾到神人,真正對不住。我來日月山,是想找一頭神獸做我的保護獸。」 噓搖起頭來,他的頭夾在兩條大腿之間,搖起來頗為不易。他一邊搖頭,一邊說道:「沒用的,沒用的。日月山早已沒有神獸啦!」 羅欽奇道:「我們村子的大長老說,他十多年前曾來過這兒,替我捉回了一頭小獸。現在這山上怎會沒有神獸了呢?」 噓低頭望向自己鼓起的肚子,說道:「我父命我在此管理日月星辰,已有數萬個年頭了。但他始終未曾給我送食物來,因此我便將這山上的神獸全吃光了。」 羅欽望著他凸起的肚子,心想:「不知他究竟吃了多少頭神獸?小獸當年若未曾被大長老捉走,或許也已被他吃了。」又想:「這山上既沒有神獸,那我得趕緊去下一座山尋找了。」於是說道:「既然如此,那我便不打擾神人,就此拜別。」 噓卻嘿嘿冷笑起來,說道:「你以為自己可以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平安無事地下山去麼?」 羅欽惶恐地問道:「請問噓神人,我該做甚麼,才能下山?」 噓晃晃頭,說道:「至少也該替我梳個頭吧!你瞧,我沒有胳膊,只有兩條腿,因此從來沒法給自己梳頭。你有胳膊也有手,既然來到我日月山上,便該替我梳個頭,順便幫我洗個臉,才說得過去。」 羅欽心想:「那倒不難。」當即答應道:「好,我這就替神人梳頭洗臉。」跨步上前,來到噓的身前。噓的身子龐大,站直身時足有丈八高。 羅欽仰頭望向他,說道:「你的頭離地這麼遠,我該怎麼替你梳頭呢?」 噓低頭望向他,慢慢地彎下膝蓋,坐倒在山石上,又將自己夾在兩腿間的頭慢慢垂低,靠近羅欽。 羅欽感到一股難聞至極的臭味撲面而來,趕緊掩住了口鼻,心想:「這位神人可能有幾萬年未曾洗頭洗臉了,味道難聞得緊。」 他心想自己既已答應了,便該將事情做好,於是對噓道:「我先替你洗臉,請神人等一會兒,我去取水。」奔去一旁的山泉,取出包袱中的衣衫,在山泉中浸濕了,回來替噓洗臉。 噓的臉非常大,從下巴到額頭,總有羅欽的整個人那麼高。羅欽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將他的整張臉都擦過一遍,那件用來擦臉的衣衫全都成了黑色。 噓點點頭,噓出一口氣,說道:「好!好!洗過臉之後,清爽多了。」側過頭,說道:「小巫者,那我的頭髮呢?」 羅欽還未想過該如何替這巨大的神人梳理頭髮,抬頭往他的頭上打量去,但見他的頭髮甚粗,一根根如繩索一般,心想:「一般的梳子,可沒法梳理這麼粗的頭髮。」問道:「請問神人可有一把大梳子麼?」 噓搖了搖頭,說道:「我沒有手,無法拿梳子梳頭,又怎會有梳子?」 羅欽點頭道:「那也有理。但沒有梳子,我卻該如何替你梳頭?」 噓發怒道:「我怎麼知道?我就是要你幫我想辦法啊!」 羅欽見他一發怒,整個天都黑暗了,日月山的土地也震動起來,心下恐懼,暗想:「大長老上回來日月山,不知是否見過這個神人噓?是否也曾替他洗臉梳頭?噓說自己是顓頊的孫子,掌管日月出入,神通廣大,那可是位大大了不起的神人。大長老即使身為大巫,想必也不敢不聽從噓的話,替他洗臉梳頭。」又想:「應當不曾,噓的臉總有幾千年沒洗過了。大長老十多年前若曾替他洗過臉,他的臉便不會這麼骯髒了。」 其實他卻不知,大長老當然知道噓住在日月山上,因此趁著噓忙著指揮日月升降,也就是黎明和黃昏之時,才上山尋找神獸,如此便可避開噓。此事大長老雖未曾向羅欽交代,但都寫在了地圖之上,只是字跡太小,又兼模糊,羅欽並未細讀,因此不知道自己應該在黎明或黃昏時上山,而選在正午之時來此,一上山就正正撞見了這個難纏的神人。 羅欽這時只能快速動念,籌思:「若是換成大長老或岩瑪薩滿撞見了神人噓,他們會怎麼做?他們定能使動甚麼奇特巫術來替噓梳頭,但我可不懂得甚麼梳頭的巫術啊!」靈機一動,說道:「神人請等一會兒,我試試用樹枝來做把梳子。」 噓瞇起眼睛,說道:「你說甚麼樹枝?你想逃走麼?」 羅欽忙道:「不、不,我不敢逃走。我是想出了個主意,看能不能用樹枝做出一把大梳子給你梳頭。我也不知道是否使得,不如讓我試試吧!」 噓冷冷地瞪著他,低喝道:「好,你便試試!你若敢欺騙我,我將你撕成四塊!」 羅欽心想:「他沒有手,只有兩條腿,如何將我撕成四塊?」但想歸想,畢竟不敢以身嘗試,於是趕緊來到一株大樹下,取出多它給他帶上的短刀,劈下十餘根粗樹枝,又剝下樹皮,搓成繩索,將樹枝綁在一起,固定於兩株大樹之間。 噓睜著一雙細細的眼睛,望著他的一舉一動,滿面好奇懷疑之色。 羅欽忙完之後,回頭對噓一笑,得意地道:「這是我專門替神人製作的巨大梳子,快來試試吧。」 噓懷疑道:「怎麼試?」 羅欽道:「你沒有手,不能拿梳子給自己梳頭,因此我將這把梳子固定在兩株大樹之間,你只需走近前,將頭湊在梳子上,讓頭髮甩上這些梳牙,慢慢拖過,便可以梳理頭髮了。快來試試吧!」 噓從未梳過頭,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將頭湊到樹枝上;他巨大的頭一甩,立即便將一頭髒亂的頭髮甩在了梳牙之上。 羅欽用手扶著「梳子」,將噓的一頭粗髮壓在梳牙之間,說道:「好了,慢慢往前走,將頭移開。」 噓開始舉步往前走,但他的頭髮實在太過骯髒糾結,立即便卡住了,再也無法拖動。 羅欽見了,腦子急速動念,快速說道:「且莫著急,神人多年來第一次梳頭,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就梳通。我知道啦,待我給神人洗洗頭髮,將汙垢沖去了,想來便能夠梳動頭髮了。請等一會兒,我去那邊的山泉取水來。」 噓的頭髮仍卡在樹枝之上,無法移動,頓時急了,怒吼道:「不准走!你騙我,讓我卡在這兒動彈不得,你使詐!我定要捉住你,將你撕成四塊,一塊一塊活活吃了!」說著奮力掙扎,想扯回自己的頭髮,但他的頭髮糾結得極為密實,一時扯之不開,兩株大樹被噓扯得左搖右晃,整座山似乎都震動了起來。 羅欽心想:「你若把我撕成四塊,我早就死了,你又怎能一塊塊活活吃了?」但他畢竟不想被撕成四塊吃掉,於是趕忙安撫道:「我沒有騙你,我是真心在想辦法替你梳頭啊!你瞧,我不是已經幫你洗好臉了麼?我現在正在想辦法給你梳頭啊!請相信我,耐心等一會兒,我去取水來清給你洗頭髮。神人請想想,你只要我梳頭,我卻還願意替你清洗頭髮哩!世間曾有人答應替你清洗頭髮麼?想必沒有吧。請耐心等候一會兒,我很快就回來。」 噓似乎聽信了他的言語,怒氣略息,說道:「好吧!你去,快去快回!」 於是羅欽快步奔去之前山泉,再次用自己的衣衫沾滿了泉水,回來澆在噓的頭髮上;但這一點兒山泉並不足夠,他來回跑了幾趟,才終於將噓的頭髮全都沾濕了。之後他便用力搓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將糾結的亂髮稍稍理順了些。他對噓道:「好啦,頭髮洗過一遍了,神人再試試梳頭吧!」 這回噓慢慢往前跨步,將頭移開,頭髮滑過梳牙,果然能夠拖動了。但是走出幾步,便又卡住了。羅欽只好再次試圖幫他清洗頭髮,但噓的頭髮許多地方緊緊糾結成一團,甚難扯開。 羅欽忙了半天,仍舊徒勞無功,喘著氣道:「沒辦法了,不如讓我砍斷這團亂髮,你說成麼?」 噓的頭卡在樹枝之上,扯了幾回都無法移動,頭皮疼痛得緊,忙叫道:「砍吧,砍吧!我總不能永遠卡在這兒啊!就要天黑了,我得去叫太陽下山啊!不然太陽今日下不了山,天下可就亂了!」 羅欽心想:「我若將他留在這兒,讓太陽留在天上一整夜,豈不有趣?」 但他畢竟不敢太過胡鬧,於是拔出多它給他帶上的短刀,向著噓的亂髮砍下。豈知才一砍下,噓便慘叫起來:「疼啊!」 羅欽一驚,立即停手,問道:「哪兒疼?」那侍女名叫陸婇兒,約莫十五、六歲年紀,月圓臉上總掛著討喜的微笑,一雙細眼透出機靈之色;她身形矮小而豐腴,衣著比一般婢女鮮亮得多。她是羅氏一個遠房表妹的獨女,因父母早逝,自幼便隨羅氏住在沈家,身分處於婢女和外甥女之間,乃是羅氏的貼身親信。 陸婇兒上下打量沈雁一身奢華鮮麗的簇新衣裙,和她裊娜多姿的體態身形,臉上露出難掩的豔羨之色,搖頭笑道:「大娘這身新裝,就連天上仙女也不如啊!依我說,大娘大婚那日,可要羨煞全城的女兒了!」 羅氏聽了,不禁得意地笑了,說道:「婇兒,妳這張嘴可真甜!」 沈雁甜笑著對母親道:「既然要給我做嫁裳,不如阿娘也做一套,婚禮那日我們母女穿一個樣式的,好不?」 羅氏笑斥道:「雁兒胡說!我若打扮得跟新嫁娘一般,可不成了老妖婆了!」 陸婇兒在旁說道:「倒是該選一疋和大娘同款的冰羅霧縠,給二娘也做套新衣裙。」 羅氏喜道:「這主意好!」眼光掃向廳內,問道:「雒兒呢?」 沈雁對著銅鏡左顧右盼,伸手輕抿髮鬢,扶正髮髻上的飛雁金簪,說道:「我方才忙著裝扮,沒見到小妹。」 羅氏皺起眉頭,轉身道:「嵇嫂,妳讓人去找找二娘,咱們趕著出門哩!」 羅氏的陪嫁婢女嵇嫂答應了,陸婇兒插口道:「姨母,我今朝見二娘去了桑園看蠶兒,只怕人還在園子裡呢。」 羅氏點頭道:「還是婇兒有心。嵇嫂,妳快讓人去桑園找二娘,叫王乳娘趕緊替她梳頭更衣!都甚麼時候了,還在園子裡瘋玩兒!」嵇嫂連忙吩咐婢女,婢女快步趕往桑園去了。 就在這時,沈拓忽然抬起頭,問道:「二郎呢?」 此言一出,全場一靜,羅氏臉色頓時沉下,廳中的冉管事、嵇嫂、陸婇兒等都低下了頭不作聲。 就在這一片靜默中,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從門外進來,他身形挺拔,容貌俊美,對沈拓道:「阿爺,駙馬的壽禮都已備妥了。」 沈拓點點頭,說道:「大郎,還是你辦事妥貼。」 這青年正是沈家長子沈維。他留意到母親和冉管事、嵇嫂、陸婇兒個個臉色古怪,微笑問道:「怎麼了?臨出門卻找不著小妹,是麼?」 羅氏淡淡地道:「嵇嫂已遣婢女去桑園裡喚她了。」 沈維望望母親,又望望大妹沈雁,說道:「等小妹到來,我等便即出發,是麼?」 沈拓咳嗽一聲,對冉管事道:「還不快去尋二郎?駙馬爺是知道他的。今日我們全家去給駙馬爺拜賀六十大壽,少攜一子,殊為不恭。」 冉管事低下頭,唯唯答應而去。 沈維恍然大悟:「原來是為了小弟。」他知道父母感情融洽,相敬如賓,唯一不和之事,便是這個庶出的弟弟。北人重嫡輕庶,正出和庶出之子的地位往往有天壤之別;正妻的子女錦衣玉食、僕從成群,庶子女則粗布陋食,地位與奴僕相去不遠。然而沈家祖上遷自南方,南方習俗不似北方這般輕庶,因此沈拓一直將這庶子放在心上,雖因長年在外奔波生意,家中內外大事皆多交由羅氏主導,心知羅氏不待見庶子,卻也難以時時迴護,偶爾為此與羅氏有所爭執。而由於駙馬爺王肅也是來自南方的漢人,並不在意嫡庶之分,此番沈氏舉家造訪駙馬府邸給駙馬拜壽,少攜一子,確屬失禮。 羅氏冷冷地道:「他自己遲了,咱們何必等他?再說,駙馬爺倘若問起,就說他病了,留在家中休養,有何不可?」 沈拓皺起眉搖搖頭,只揮手催促冉管事趕緊去尋二郎。 廳中陷入一片尷尬的沉默。沈拓夫婦坐在織錦坐墊上等候,沈維、沈雁兄妹則一個垂手肅立,一個對鏡顧盼,目光各不相對。 陸婇兒跪在羅氏身邊,輕聲勸解道:「姨母,咱們今兒去給駙馬拜壽,還能見到公主殿下呢,怎好為了這點兒瑣事鬧心呢?」 羅氏聽了,眉頭略舒,臉色也緩和了些。 沈拓見婇兒好言勸解,妻子怒氣略消,心中暗暗鬆了口氣。
不多時,王乳娘領著一個六、七歲的女童來到廳上,女童顯然剛剛梳好頭,紮著雙辮,穿著一身桃紅繡花綢緞衫褲,紅撲撲的圓臉上仍綴著不少汗珠子。女孩兒面貌與羅氏極為相似,英氣十足,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她彷彿全然不覺自己來遲了,也未留意父母兄姊神態有異,滿臉歡快地撲入父親懷中,甜笑道:「阿爺!今年的蠶兒可大了!有一籃子的蠶兒已經跟我的手指兒一般粗了!」 羅氏心下微惱,卻不忍心斥責小女兒,只對王乳娘埋怨道:「不是跟妳說了今兒要出門,讓妳早些給二娘梳洗打扮麼?」 王乳娘委屈地道:「娘子,奴婢提醒二娘好多回了,但她在蠶舍裡忙著餵飼蠶兒,全不聽奴婢的話啊!」 沈拓最最疼愛這個小女兒,伸手將她攬在懷裡,笑著道:「乖雒兒,妳愛惜蠶兒,阿爺很歡喜。不過咱們不該遲到、惹阿娘生氣,這得趕著去給駙馬拜壽啦!」 沈雒全沒聽出父親言語中的教訓之意,笑嘻嘻地著指向角落,說道:「還要多謝小兄每日爬上樹梢,幫我採最嫩的桑葉餵蠶兒,蠶兒才能長得這麼好!」 眾人聽小娘沈雒這麼說,都是一呆,一齊轉頭望去。
但見一個七、八歲的童子靜悄悄地站在廳中角落。在此之前,眾人都未曾發現他,直到二娘沈雒伸手指向他,沈拓和羅氏等才忽然留意到他立在該處。至於他是從哪道門進來的,何時進來的,進來了多久,廳上人竟誰也不知。 此時人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這童子身上。沈家上下,不論主僕,見到這童子的衣著形貌,都不禁暗暗搖頭。只見他安靜退縮地立在廳角,低頭望向自己腳上一雙顯然太小的破布鞋,頭髮又髒又亂,一身布衣布褲不但汙穢陳舊,膝頭和手肘處還打著幾個補丁,其卑微猥瑣、上不得檯盤之態,比之沈府的奴僕都還不如。 沈拓深皺眉頭,問道:「綾兒,你的乳娘呢?怎地未曾給你梳頭更衣?」 那童子名叫沈綾,正是沈家唯一的庶子。 他低下頭,囁嚅答道:「回阿爺的話……趙姊姊兩年前便辭去了。」 沈拓一呆,沒想到自己竟疏漏至此,小兒子的乳娘辭去了兩年,自己卻全不知情!但沈家絲綢生意越做越大,他長年帶著長子沈維在外奔波買賣,忙碌不堪,確也無暇顧及家中這等小事。沈拓不禁望了妻子羅氏一眼,心想:「家裡自然不缺聘請乳娘的銀錢,趙乳娘多半是娘子蓄意辭退的。這等瑣事,我若不過問,她自不會主動跟我提起。」他不好向妻子發作,當下咳嗽一聲,轉向小女兒的王乳娘,說道:「王姊姊,妳快帶二郎下去梳洗一下,換身新衣。」
王乳娘「欸」了一聲,但卻站在當地,並不移動,猶豫地搓著雙手,滿面為難之色,也不知是不屑幫這庶出之子梳洗更衣,還是不敢得罪主母羅氏? 沈拓見狀心中不悅,正打算開口催促王乳娘,羅氏忽然站起身,往門外走去,不耐煩地道:「還梳洗甚麼?你瞧他這個邋遢樣,不知要梳洗多久才見得人,咱們可要遲到啦!不必梳洗更衣了,就這麼去吧!」 沈拓更加鎖緊了眉頭,他決不願讓外人見到自己的幼子如此不體面,尤其這孩子上有長兄,旁有姊妹,個個容貌出眾,衣著光鮮亮麗,偏生這幼子卻如此形容骯髒,看在外人眼中,定將引發街談巷議,令沈家大失臉面。於是沈拓不顧妻子的不快,堅持道:「不成。咱們這是去造訪駙馬府邸,人人都必須換裝打扮,整肅儀容,否則可是大不敬。綾兒,你趕緊去換了新衣來。」 沈綾答道:「是,阿爺。」卻遲疑不動。 沈拓見了頗感惱怒,呵叱道:「怎不快去?」沈綾低下頭,支支吾吾地道:「回阿爺的話,小子沒有……沒有新衣可換。」 沈拓大感驚怒,高聲道:「我們沈家做的是絲綢生意,隨從僕婦都皆穿綢著緞,家中二郎怎會連件可換上的新衣都沒有?」他轉頭望向羅氏,眼中頗有責怪之意。 羅氏卻不甘示弱,立即揚起眉毛,冷冷地道:「你望我做甚麼,這關我何事?」 沈拓平日對妻子好生恭敬禮讓,這時卻當真惱火了,大聲道:「妳是家中主母,孩子的事情自然都歸妳管。大兒和兩個女兒個個錦衣華服、穿金戴玉,妳卻任由小兒整日穿著一身破爛布衣,連件能換上的新衣都沒有?」 羅氏乃是出名的火爆脾氣,聽丈夫責怪自己,頓時雙眉倒豎,雙手叉腰,也提高了聲音,瞪眼道:「我日日在總舖照顧生意、招呼主顧,忙得焦頭爛額,哪有工夫理會家中這等瑣事?這些衣衫鞋子的小事兒,自有管事和僕婦照料。這庶子的飲食起居,怎會是該我管的事兒!」 沈拓駁道:「就算妳忙,內宅的人事總歸妳管吧!他的乳娘何時辭去了,妳竟不曾跟我提起,也不曾替他另請一個?他才幾歲哪,怎能連個乳娘也沒有?平日誰照顧他?」 羅氏怒道:「甚麼乳娘不乳娘,他的乳娘是誰,我根本不知道!當初那乳娘可不是我請的。她何時辭去,為何辭去,我半點兒也不知情,又怎會想到要另請一個?更加不會跟你提起!再說,他也有八歲了,年紀夠大了,早就不喝奶了,也該能夠照看自己了。你竟為了這卑微庶子有沒有乳娘的瑣碎事兒怪起我來?」 夫妻倆當著僕從子女的面,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在大廳中爭吵起來。
長子沈維看在眼中,露出擔憂之色,走上一步,想試圖勸解,卻見母親身後的陸婇兒向自己連連搖手,示意莫要介入,只好打消了念頭,退開一步。 正僵持間,站在銅鏡前的沈雁忽然對沈綾招招手,語音清脆地說道:「小弟,你跟我來。我屋中留了幾件大兄年幼時的衣衫,應當合你身。我帶你去換上了,咱們好趕緊出門。」 沈拓一聽大女兒這麼說,吁了口氣,向她投去欣慰的目光,說道:「那敢情好。綾兒,快跟你大姊去更衣吧。」 沈雁回頭對父親嫣然一笑,向沈綾瞥了一眼,回身走去,沈綾連忙趨前跟上。小妹沈雒見父母大起口角,不敢留在廳中,立即道:「我也一起去。」舉步追上大姊沈雁和小兄沈綾。 沈拓和羅氏留在廳中,但兩人怒氣未消,立即又針鋒相對地繼續爭執起來,吵了一陣子,羅氏氣得滿臉通紅,拂袖怒道:「這事兒我當年便說明白了,我絕不理會。此前不理會,往後也不理會!你莫要再在我面前提起那低賤的豎子!」隨手將廳中一只琉璃花瓶掃到地上,哐噹一聲,砸得粉碎。 沈拓露出驚怒之色,那只花瓶乃是他五年前赴西域大秦國販售絲綢時,特意以千金買下,千里迢迢帶回洛陽,送給妻子的禮物,豈知羅氏一怒之下,竟輕易砸碎了這無價之寶!他臉上黑氣一閃,握緊了拳頭,指節突出,身子微微顫抖,顯然須得用盡全力,才能按捺下心頭的怒火。 沈家眾管事、僕婦、婢女、家丁們見慣了羅氏的剛烈脾氣,倒也並不驚訝,只個個低頭屏息,不想觸怒主母將一口惡氣發洩在自己身上,也不敢去望主人,免得他因在奴僕面前失了顏面倍感尷尬。只有羅氏的外甥女陸婇兒神色沉穩,抬頭望向羅氏,滿面關懷擔憂。 羅氏怒氣未歇,伸腳狠狠地往地上的琉璃碎片踢去,只踢得碎屑到處亂飛。她踢了一陣後,往地上啐了一口,頭也不回,起身大步出門而去。陸婇兒站起追上幾步,又停下腳步,回頭望了主人沈拓一眼。沈拓對她擺擺手,說道:「去!快去勸勸她。」陸婇兒點頭答應,快速向沈拓行了個禮,快步追出門外,口中急喚道:「姨母!」 冉管事畢竟在沈家服侍了三十餘年,經驗老道,這時維持鎮靜,暗中對兩個婢女示意。婢女連忙奔去取了掃帚畚箕等物,匆匆進廳,清理琉璃花瓶的碎片,又悄悄退出;一個僕婦立即捧出了另一只花瓶,放在原處。那是主人沈拓從南方帶回來的青釉仰覆蓮花尊,雖不及那只大秦國琉璃花瓶奇麗美觀,也是件稀世之寶。沈家乃大富之家,種種珍貴擺設不計其數,倉房中甚麼沒有?一番清理轉換之後,廳中便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一般。 沈拓將奴僕的舉止都看在眼中,不發一言,鐵青著臉,轉過身去。 這時長子沈維咳嗽一聲,緩步來到父親身旁,低聲道:「阿爺,阿娘平日不只須照料家務,還得兼顧總舖的生意,確實忙碌得很。我和阿爺又常常出門,總舖的經營全落在阿娘一人身上,日日何等分身乏術!家中之事,她自不免有些許難全之處,阿爺何必苛責?」 沈拓吁出一口氣,臉色平緩下來,說道:「你說得是。我不該對你阿娘發脾氣。只是我長年不在家,照看不上你弟弟妹妹的生活起居,自不免擔憂。你看看你小弟,都八歲了,一身穿著竟如同乞兒似的,外人見了怎麼想?」 沈維安慰父親道:「小弟年紀還小,從不出門,想來不曾被外人見到。如今我們知曉了此事,只需交代冉管事,命織室的裁縫給他做上幾套全新的衣褲鞋襪,那便是了。他年紀也大了,乳娘不必另請,不如就指派個僕人,專門服侍他吧。」 沈拓點了點頭,說道:「就這麼辦吧。」叫了冉管事近前,交代了一番,又吩咐道:「你靜靜去做便是,別讓主母知道了。」 冉管事垂手道:「謹遵阿郎吩咐。」 沈綾和沈雒跟著大姊沈雁來到她的居處「飛雁居」。雖是同住一宅的親姊弟,這卻是沈綾第一回來到沈雁的居處。飛雁居乃是一座獨立的院子,佔地寬廣;沈拓夫婦寵愛長女,在她出生百日後,便開始替她營造這座飛雁居,全供沈雁一人居住;飛雁居中配有三十名僕婦婢女,負責打掃、烹飪及各項雜務,專職服侍沈雁這位沈家大娘。 此時沈雁領著弟弟沈綾和妹妹沈雒跨入飛雁居,入門先是一座庭園,右首是個巨大的花圃,圃中萬紫千紅,種滿了百合、甘菊、蘭蕙等名花珍卉;左首是個葫蘆型的池塘,池水碧綠,池旁連香、銀杏和山白芍圍繞,濃郁成蔭。通過一條鋪滿碎石子的小徑後,便來到一間寬敞的花廳,廳旁分出三條閣道,分別連接到沈雁的書房、起居室和寢室。這花廳四面開敞,窗明几淨,楠木櫃上陳設著各種玩物擺飾,有白玉辟邪、青瓷花瓶、石雕胡馬、青銅壽龜等,還有不少沈拓從西域各國帶回來的珍品,包括琉璃珠串、石雕佛像、花卉紋金盤等。沈綾從未見過這等珍奇寶貝,只看得眼花撩亂,暗暗稱奇。
沈雁對婢女于洛道:「我往年騎馬時慣穿的大兄衣衫收在何處?妳快快替我找了出來。」 于洛答應了,連忙去衣物房翻箱倒櫃,找了好一會兒,才找出了一套童子衫褲,看來還有八分新。 沈雒拍手笑道:「大姊,妳怎地還留著大兄小時候的衣衫?」 沈雁道:「我六、七歲時剛學騎馬,嫌裙裝不方便,因此向大兄討了幾套他的衣褲來穿,後來就留在屋裡了。」從于洛手中接過,往沈綾身上比了比,蹙眉道:「大了些。沒法子,將就著換上吧。」 沈綾忙道:「多謝大娘。」恭敬接過,趕緊去衣物間更衣。 沈雁又吩咐婢女于洛道:「妳去給他梳個頭,要快。」于洛答應了,忙跟入衣物間。 隨後她斜倚在花廳窗邊,懶洋洋地道:「你們快些吧!阿爺和阿娘還在大廳上等著呢。」沈綾連忙隔空應道:「是,大娘。」 沈雒側過頭,擔憂地問道:「大姊,妳說阿爺阿娘還在爭吵麼?」 沈雁似乎並不在意,只淡淡地道:「應該吵完了吧?阿娘就是這般性情,不高興了便板起臉、高聲訓斥人,我在總舖可是見得多了。但她和阿爺當著奴僕之面大動肝火,這可是頭一回。」 沈雒吐吐舌頭,說道:「是啊,我從未見過阿爺阿娘這般紅臉相對哩!」 沈雁道:「妳年紀小,沒見過的事兒可多著呢。阿爺成日在外奔波,在家的時候原本不多。況且他們即便意見不合,也不會在妳面前爭持不下。」 沈雒嘟起嘴道:「那今兒是怎麼回事?阿爺阿娘怎地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爭成這樣?」 沈雁閒散地笑笑,說道:「當然是因為在裡面更衣的這一位啦。他若不快些換好,只怕阿爺阿娘還得繼續爭下去哩。」 沈綾在裡面聽著大姊的言語,好生焦急,快手快腳換好了衣衫,發現袖子褲腳都太長了些,只能趕緊捲上了。這時于洛也已飛快替他梳好了頭髮,沈綾便快步走出衣物間,說道:「大娘,換好了。」 沈雒見他換上一身新的衫褲,頭髮齊整,顯得精神煥發許多,拍手笑道:「小兄,你穿上大兄這身衣褲,可好看得很哪!」 沈雁望向沈綾,說道:「你總低著頭,誰也看不清你臉面。你抬起頭來。」 沈綾依言抬起頭;沈雁望向他的臉龐,微微一怔,但見他膚色白淨,鼻挺眼細,容貌端俊,心想:「小弟平日畏畏縮縮,今日換上一身整齊衣衫,才看得出他一張臉竟然還挺俊秀的!雖沒有大兄的英氣,但絕對是上得檯盤的。」她微微點頭,說道:「換了身衣衫,人可就不同了。」神情轉為嚴肅,說道:「小弟,你給我聽好了,我幫你找衣衫更換,可不是對你存著什麼好心。我只是不願見到阿爺阿娘為你互起齟齬,不想你穿得邋邋遢遢地出門去丟人現眼,也別誤了咱們一家拜壽的時辰。聽清楚了麼?」 沈綾原也奇怪大姊沈雁何以忽然出頭幫助自己,聽她如此說來,倒也在情理之內;沈家的兩位長兄長姊年紀比自己大上許多,在家中的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自不必紆尊降貴,對自己示好,於是連忙回答道:「是,大娘,小子聽清楚了。」 沈雒噘起嘴,對姊姊道:「大姊,妳怎地這般說話?妳明明對小兄很好,卻故意說自己對他不存好心?」 沈雁一笑,「我就是不存好心,爽快說出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甚麼不對了?」又向沈綾打量去,目光停留在他腳上那對過小的破布鞋上,微微皺眉,對于洛道:「大兄當年那對馬靴呢?應當還不太舊,快找出來了。」 于洛趕緊答應了,再次去衣物間翻箱倒櫃,沈雒也興沖沖地跟著去幫忙翻找,一會兒後,終於找出一對男童的騎馬皮靴,拿出來給沈綾試穿。沈綾穿上了,倒是剛好合腳。沈雒高興地道:「衣衫大了些,靴子倒是剛剛好。」 但聽外面僕人連聲催促,姊弟妹三人快步回到大廳上,見母親羅氏已立於上馬堂前,正撫摸著愛馬「踏燕」的鬃毛,神色已恢復平靜;沈拓則獨自坐在大廳之中,臉色仍有些不豫,但已無明顯怒色。大兄沈維見他們回來,連忙催促道:「快些、快些,咱們得趕緊出門啦!」 這時馬夫已替小娘沈雒備好了她的愛駒「踏雪」,那是一匹通體黑色、四蹄雪白的母馬,身上鞍轡也是金銀鑲玉,十分華麗。沈雒和母親羅氏分別騎上了馬,沈拓坐上第一輛馬車,長子沈維、長女沈雁和幼子沈綾則坐上第二輛馬車。眾人一坐定,馬夫便喝叱揮鞭,兩輛馬車緩緩駛出沈家大門。 在沈家主人的馬匹和馬車之後,另跟了三輛裝飾較為樸實的楠木馬車,前兩輛承載著給駙馬的十箱壽禮,第三輛則乘坐了沈家主人們的貼身僕婢,包括跟隨主人沈拓多年的親信喬五、主母羅氏身邊的嵇嫂和陸婇兒、大娘沈雁的婢女于洛、二娘沈雒的婢女于沱,以及日常供大郎沈維使喚的兩個小奴;另有十餘名勁裝結束的健僕跨著駿馬,簇擁在馬車和雙馬旁,充作護衛。一行人浩浩蕩蕩,策馳在洛陽城大街之上。
第一章 豎子
「備車,備馬!主人、主母、郎君和小娘子們要出門啦!」 洛陽城阜財里東沈氏大宅中,大廳門外上馬堂前,一個身形微胖、頭頂微禿的中年宅院管事,一疊聲地呼喊催促著。數十名衣著鮮淨齊整的馬夫和僕人奔趨來去,忙中有序地備好了兩輛簇新的馬車,馬車車身為紅柚木,車輪為青榆木,車轅則為水曲柳所製;車壁漆成紅色,車頂鑲金,飾以五彩纓絡。每輛車前各套著兩匹高大健壯的北方駿馬,馬轡繫環皆以真金實銀打造,鎏金上綴著銀錢、寶珠、飛燕和駿馬等裝飾,在日頭下閃閃發光。四名馬夫牽著四匹駿馬來到正屋門外,駐馬等候;幾個童僕快手在兩輛馬車門旁的青石板地上放置了半尺高的純銀踏腳凳,各自用衣袖快速將銀凳擦得潔淨光亮。 那宅院管事來到馬車之旁,上下左右仔細檢視,又伸出胖胖的手指,小心梳理從車頂懸掛而下的五色琉璃纓絡,接著探頭入內審視,拍去繡金錦緞座褥上的些許灰塵。眼見一切安排妥當,宅院管事才對馬夫和僕人點點頭,說道:「可以了。主母的坐騎呢?」 後方一個馬夫高聲答道:「主母的『踏燕』在這兒,已上好鞍鞬轡頭了。」牽過一匹高大的青驄花斑馬而來。這匹馬不但矯健雄駿,身上裝飾更是奪目,金帶扣、銀帶箍、鎏金鐵馬銜、鑲玉銀馬籠頭,配上嵌有馬形玉飾的鞍帶、銀馬鐙,馬鞍上鋪著大紅繡花錦緞,光鮮燦爛至極。 宅院管事點點頭,說道:「甚好。我這便去稟報主人。」快步趨入正廳,在門口躬身稟報道:「啟稟阿郎,馬車已備妥了。」 大廳正中,一個華服男子盤膝坐在金銀錦墊之上,正低頭查閱身前几上一本厚厚的帳冊。男子衣著雖華貴,一雙手卻頗為粗糙,撫著帳冊的指節上長滿了繭子。一個留著山羊鬍子的老者捧著幾本帳冊,恭敬地跪在一旁伺候。 華服男子聽見門外宅院管事的稟報,並不抬頭,只擺手道:「知道了。冉管事,派人去請夫人、郎君和兩位小娘子。」 那姓冉的宅院管事應了,立即吩咐僕人婢女去恭請主母、郎君、小娘子等人。 華服男子闔上了帳冊,對那山羊鬍子道:「桑園的帳可以了。絲坊的帳,我明日再看吧。」 山羊鬍子答道:「謹遵東家之命。」小心翼翼地闔上帳冊,疊放整齊,捧在懷裡,起身向華服男子躬身行禮,退出正廳。 華服男子站起身,走到大廳門口。他約莫四十來歲年紀,身穿赭色團虎紋錦袍,體形略瘦而結實,腳步沉穩,黑瘦清俊的臉上透出精明警醒之色。若看服色裝扮,這人顯然是這座大宅的主人;若看他的體態舉止,卻似個飽經風霜的江湖人。 華服男子望向垂手立在門外伺候的冉管事,問道:「壽禮可備妥了?」 冉管事答道:「回稟阿郎,都已齊備。老奴方才與大郎一道,再次檢視過了給駙馬準備的壽禮。」 華服男子道:「可是我上回交代的,雙蝠萬壽紋大紅織錦?」 冉管事道:「正是。昨日大郎和李大掌櫃一同挑撿了極品雙蝠萬壽紋大紅織錦一百疋,已裝入十只檀木箱子,安置在馬車上了。」 華服男子露出滿意之色,點頭道:「甚好。」 這時,一個身穿碧綠綾羅繡衫、紫紗長裙的貴婦從廳中快步走出,身後跟著一名僕婦、一名年輕侍女。貴婦望了望門外的馬車,皺眉對冉管事道:「我的馬呢?」 冉管事連忙躬身道:「啟稟娘子,您的『踏燕』已備好了,就在門外。」 華服男子揚起眉毛,望向妻子,脫口道:「妳要騎馬?」 貴婦三十來歲年紀,一張橢圓臉,眉目間英氣十足。這時她挑起雙眉,高聲對丈夫道:「我出門時,哪回不騎馬了?」 華服男子露出微笑,安撫地道:「不、不,我可無意阻止娘子騎馬。咱們這回去給駙馬拜六十大壽,公主想必樂意見到娘子騎馬的英姿,就只怕..只怕駙馬不喜我等唐突。」 貴婦一笑,說道:「我在大門之外下馬,駙馬又怎會知道我是騎馬去的?」轉頭問冉管事道:「大娘和二娘的馬都備好了麼?」 冉管事還未回答,華服男子已皺起眉頭,插口道:「雁兒剛剛訂親,怎能騎馬上街?盧家可是有著百年傳承的漢人世家大族,絕不樂見未進門的新婦如此拋頭露面。」 貴婦「哼」了一聲,撇嘴道:「你們漢人,偏有這許多規矩!好吧,大娘就乘車好了。冉管事,快給二娘備馬!」冉管事連聲答應了,自去吩咐。 華服男子見妻子堅持自己和小女兒要騎馬出門,只能苦笑,不再爭辯。 這華服男子姓沈名拓,正是這座沈家大宅的主人。沈家乃是洛陽首屈一指的絲綢大賈,富可敵國;沈氏原為南方漢人,三十多年前隨齊朝大臣王肅背齊歸魏,定居洛陽。王肅出身琅琊王家,父親王奐曾任雍州刺史,後遭齊武帝蕭賾殺害,王肅憤而歸降北魏。王肅初投魏時,高祖方遷都洛陽,見王肅博學多才、通曉舊事,因此大加重用,封為尚書令,呼其「王生」,延請他為營建新都出計獻策,更將自己的妹妹陳留長公主嫁給了他。高祖並命將作大匠在洛陽城東南興建巨園華宅,供王肅和公主居住,並將該里命名為「延賢里」。 王肅為了討好公主,並炫耀南方絲織技巧,於是讓出身絲綢世家的屬僚沈譽養蠶取絲、染織成綢,製出花樣新穎的綢緞,獻給公主揀選。公主一見之下,果然喜歡非常,愛不釋手。王肅甚是滿意,將沈家所製綢緞命名為「沈緞」,令沈譽大量製造,除了供公主選用,亦進貢北魏皇室。洛陽城初興,數萬皇族貴宦受命遷入城中,時值魏高祖極力漢化,下令人人改穿漢族衣裳,絲綢需求因而大增。沈譽覷見商機,於是在洛陽城外購入數十頃桑園,廣植桑樹,採桑養蠶,煮繭取絲;又建造了百餘座絲坊、染坊和織坊,巧用南方絲織之法,織出圖案精緻多變、質地輕軟細柔、色彩鮮豔亮麗,獨樹一幟的「沈緞」,更與山東的「大文綾」、「連珠孔雀羅」和阿縣的「縞」齊名。「沈緞」得長公主青睞有加,很快便受到其他皇族富宦的重視,爭相採購,舖頭從此門庭若市、生意興隆,不過一代之間,便致暴富一方。 到沈拓時,已是沈家第二代;由於高祖鼓勵胡漢通婚,因此沈譽讓獨子沈拓娶了鮮卑女子羅氏為妻。高祖遷都洛陽後,敕令胡姓一律改為漢姓;羅姓原為叱羅,羅氏的祖上叱羅鑒曾為大魏名將,戰功彪炳,惟傳到羅氏時,再無男丁,家族已趨式微。遷洛的鮮卑貴族雖大抵漢化,人人說漢語、著漢服,但羅氏一族仍未脫粗獷勇武之風,羅氏自幼便騎馬射箭,勇健豪邁,英姿颯爽;在她心中,女子騎馬射箭、在外出行遊走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與漢人禮俗大相逕庭。沈拓和妻子羅氏雖結褵多年,卻仍不時因漢胡習俗差異而小起爭執;而羅氏性情強悍,大多時候都以沈拓讓步遷就收場。 正當羅氏點頭表示滿意時,一個少女跨入大廳。她一出現,整個大廳似乎陡然亮了起來;那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女,天生麗質,容顏明媚無方,讓人一見便難以移開視線。她身著絳色冰羅霧縠長裙,腰間束著水綠繡纈腰帶,纖腰如柳,體態婀娜,正是沈拓和羅氏的長女沈雁。她在廳外聽見了父母的對答,笑盈盈地走上前,攬住父親的手臂,撒嬌道:「阿爺,怎地阿娘和小妹都能騎馬,唯獨我不能騎馬出門?」 沈拓疼愛地望向長女,拍拍她的手臂,輕笑道:「妳就要嫁入江北的世家大族啦,還問阿爺為甚麼?」 沈雁道:「誰曉得?說不定盧五郎就喜歡新婦騎馬呢?」 羅氏揚眉道:「盧五郎要是不讓妳騎馬,妳就回家來,阿娘讓妳騎個夠!」 沈雁嘻嘻一笑,說道:「還是阿娘疼我!」 羅氏笑著向女兒招手,說道:「來,讓阿娘看看妳的新衫裙。」 沈雁放開了父親的手臂,走向母親。羅氏牽著女兒的手,母女倆一起來到大廳東壁上一面巨大的銅鏡之前。羅氏言語舉止雖爽快率直,對女兒的關懷可是細緻入微;她細細檢視女兒身著的嶄新冰羅霧縠衣裙,臉上神色愛憐橫溢,點頭讚賞道:「剪裁功夫不錯,馮裁縫的手藝確實了得!咱們挑一疋上好的『沈緞』,就請織室的馮裁縫給妳做大婚之日的嫁裳吧!」轉頭對身後的侍女道:「婇兒,妳說如何?」 卻說羅欽獨自離開了磈磊村,往西方行去。這是他第一次離開磈磊村,又是獨自出行,無人帶路,連馬也沒有,不禁大感茫然,才走出村口數丈,心頭便感到一陣驚慌,擔心自己已經迷路了。 他定下神,從懷中取出牛皮地圖,翻來覆去地觀看,勉強辨明了方位,又抬頭看看初升的太陽,辨別方向,這才收好地圖,吸了一口氣,舉步往西方行去。 他孤身行路,甚是寂寞無聊,心頭更大感恐懼不安,只能對自己說道:「你已不是個孩童啦,即使不具巫術,但你瞧那些牧童們趕著牛羊走遍整個大草原,也不見他們害怕,怎地你獨自出行,便驚慌害怕得要命,如此無用?」 但他畢竟年輕,又毫無單獨行旅的經驗,心中實在不安,於是只好低下頭,開始對著石鏡說話: 「岩瑪薩滿,是我羅欽。我已離開磈磊村口,正往西邊走去,已經走出五千步了。」 「我已經走了半天了,現在停下休息一會兒,吃點乾糧。」 「我渴了,停下喝水。」 「前面那座山尖尖的,可能就是日月山了,也不知是不是?」 「地圖上說,日月山是天的樞紐,最高的主峰叫吳姖天門山。」 「咦,前面有條河,彎彎曲曲的,似乎和地圖上畫的一樣。我正好可以在牛皮袋裡加點兒飲水。」 「前面有一群牧人,放著幾十頭羊,有黑的,也有白的。嘿,那些牧人見到我,好像很害怕,避得遠遠地,還向我躬身行禮。是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巫者麼?哈哈,其實我比他們更加害怕哩!」 岩瑪薩滿也不知能否聽見他的自言自語,即使能聽見,也並不回應,那石鏡就如一塊尋常的石頭一般安靜。 羅欽心想:「他想必能聽見我說話,否則當我遇上危險時,高聲呼救,他若聽不見,又怎能出手保護我呢?他並沒有嫌我囉嗦,要我閉嘴,那我就一直說下去也沒關係。」 他步行了一整日,天黑後,便用毛氈包著身子,在草原上睡倒;天亮後吃些乾糧,續往西行。 三日之後,羅欽來到了一座山的山腳。他抬頭望去,但見山巔隱沒在雲霧之中,中間一座山峰高高聳起,想來便是日月神山的最高峰吳姖天門山了。 他想起自己的小獸曾經住在這兒,心中不禁一酸,暗暗祝禱:「小獸啊小獸,十幾年前你被大長老捉住,來到磈磊村做我的守護獸,最後卻因保護我而死。能跟你一起長大,是我的幸運,卻是你的不幸啊!」 羅欽舉步往山上行去,一路只見到一些不知名的奇樹怪草,卻沒見到任何會動的蟲魚鳥獸。 約莫正午,來到山腰時,剛轉過一個山坳,一個巨物忽然出現在面前。羅欽嚇了一跳,趕緊往後退出幾步。定睛看去,但見那巨物說是人,卻又完全不像人;他有頭有身,卻沒有胳膊,兩條大腿直接從頭的兩旁伸出,腿下是兩隻生毛的大腳,穩穩地踏在地上,赤裸的身子垂掛在頭之下,有著圓滾滾的肚子,身下沒有腿,只有一叢亂毛;這人的臉上滿是皺紋,一頭亂髮披垂在胸前。 羅欽從未見過長相如此古怪之物,不禁呆了一呆,還未想到該如何反應,那「人」已跨著大步向他走來,因他雙腿長在頭邊,每走一步,大頭都跟著晃動。怪人大步來到羅欽身前,睜著一對細長的眼睛瞪著他,張口喝道:「來者何人?」 來到近前,羅欽才發現這怪人巨大無比,比自己高出兩倍有餘,心頭驚怕,連忙行禮說道:「這位神人,我是來自磈磊村的巫童,叫作羅欽。請問神人如何稱呼?」 那人仍舊冷冷地瞪著他,臉上露出不悅之色,質問道:「小子,你是巫者,竟不識得我?」 羅欽心頭發慌,只能老實答道:「我不識得神人......」 那人發出吼吼之聲,顯得又是憤怒,又是驕傲,昂首道:「我是黎之子!」 羅欽「嗯」了一聲,心想:「黎之子?那是甚麼人?黎又是誰?」 那人見他不言語,豎起眉毛,喝道:「你既知道我是黎之子,為何不跪倒膜拜?」 羅欽嚇了一跳,趕緊跪下膜拜,說道:「小巫拜見黎之子。」 那人哼道:「我是黎的兒子,卻不叫黎之子。我叫作噓。」 羅欽心想:「原來他叫『噓』,是黎的兒子。黎是甚麼人?我該認識他麼?」 噓晃了晃赤裸的身子,抬起右腳往地上一踩,整座山似乎都震動起來。他高喝道:「你自稱巫童,卻甚麼也不知道!村裡的薩滿都沒教過你麼?你給我聽好了!古帝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二子;古帝顓頊命重托天,命黎撐地,以分開天地;又命重主天,黎主地。我是大地之主黎之子,掌管日月星辰運行的次序。」 羅欽從未聽說過這些遠古神話,只道:「原來如此。日月每天都得升起落下,你想必忙碌得很。」 噓「哼」了一聲,說道:「可不是?我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不能歇息。你既然知道我如此忙碌,又為何來日月山上擾我清眠?」 羅欽甚感歉疚,說道:「我才剛剛來到這兒,打擾到神人,真正對不住。我來日月山,是想找一頭神獸做我的保護獸。」 噓搖起頭來,他的頭夾在兩條大腿之間,搖起來頗為不易。他一邊搖頭,一邊說道:「沒用的,沒用的。日月山早已沒有神獸啦!」 羅欽奇道:「我們村子的大長老說,他十多年前曾來過這兒,替我捉回了一頭小獸。現在這山上怎會沒有神獸了呢?」 噓低頭望向自己鼓起的肚子,說道:「我父命我在此管理日月星辰,已有數萬個年頭了。但他始終未曾給我送食物來,因此我便將這山上的神獸全吃光了。」 羅欽望著他凸起的肚子,心想:「不知他究竟吃了多少頭神獸?小獸當年若未曾被大長老捉走,或許也已被他吃了。」又想:「這山上既沒有神獸,那我得趕緊去下一座山尋找了。」於是說道:「既然如此,那我便不打擾神人,就此拜別。」 噓卻嘿嘿冷笑起來,說道:「你以為自己可以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平安無事地下山去麼?」 羅欽惶恐地問道:「請問噓神人,我該做甚麼,才能下山?」 噓晃晃頭,說道:「至少也該替我梳個頭吧!你瞧,我沒有胳膊,只有兩條腿,因此從來沒法給自己梳頭。你有胳膊也有手,既然來到我日月山上,便該替我梳個頭,順便幫我洗個臉,才說得過去。」 羅欽心想:「那倒不難。」當即答應道:「好,我這就替神人梳頭洗臉。」跨步上前,來到噓的身前。噓的身子龐大,站直身時足有丈八高。 羅欽仰頭望向他,說道:「你的頭離地這麼遠,我該怎麼替你梳頭呢?」 噓低頭望向他,慢慢地彎下膝蓋,坐倒在山石上,又將自己夾在兩腿間的頭慢慢垂低,靠近羅欽。 羅欽感到一股難聞至極的臭味撲面而來,趕緊掩住了口鼻,心想:「這位神人可能有幾萬年未曾洗頭洗臉了,味道難聞得緊。」 他心想自己既已答應了,便該將事情做好,於是對噓道:「我先替你洗臉,請神人等一會兒,我去取水。」奔去一旁的山泉,取出包袱中的衣衫,在山泉中浸濕了,回來替噓洗臉。 噓的臉非常大,從下巴到額頭,總有羅欽的整個人那麼高。羅欽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將他的整張臉都擦過一遍,那件用來擦臉的衣衫全都成了黑色。 噓點點頭,噓出一口氣,說道:「好!好!洗過臉之後,清爽多了。」側過頭,說道:「小巫者,那我的頭髮呢?」 羅欽還未想過該如何替這巨大的神人梳理頭髮,抬頭往他的頭上打量去,但見他的頭髮甚粗,一根根如繩索一般,心想:「一般的梳子,可沒法梳理這麼粗的頭髮。」問道:「請問神人可有一把大梳子麼?」 噓搖了搖頭,說道:「我沒有手,無法拿梳子梳頭,又怎會有梳子?」 羅欽點頭道:「那也有理。但沒有梳子,我卻該如何替你梳頭?」 噓發怒道:「我怎麼知道?我就是要你幫我想辦法啊!」 羅欽見他一發怒,整個天都黑暗了,日月山的土地也震動起來,心下恐懼,暗想:「大長老上回來日月山,不知是否見過這個神人噓?是否也曾替他洗臉梳頭?噓說自己是顓頊的孫子,掌管日月出入,神通廣大,那可是位大大了不起的神人。大長老即使身為大巫,想必也不敢不聽從噓的話,替他洗臉梳頭。」又想:「應當不曾,噓的臉總有幾千年沒洗過了。大長老十多年前若曾替他洗過臉,他的臉便不會這麼骯髒了。」 其實他卻不知,大長老當然知道噓住在日月山上,因此趁著噓忙著指揮日月升降,也就是黎明和黃昏之時,才上山尋找神獸,如此便可避開噓。此事大長老雖未曾向羅欽交代,但都寫在了地圖之上,只是字跡太小,又兼模糊,羅欽並未細讀,因此不知道自己應該在黎明或黃昏時上山,而選在正午之時來此,一上山就正正撞見了這個難纏的神人。 羅欽這時只能快速動念,籌思:「若是換成大長老或岩瑪薩滿撞見了神人噓,他們會怎麼做?他們定能使動甚麼奇特巫術來替噓梳頭,但我可不懂得甚麼梳頭的巫術啊!」靈機一動,說道:「神人請等一會兒,我試試用樹枝來做把梳子。」 噓瞇起眼睛,說道:「你說甚麼樹枝?你想逃走麼?」 羅欽忙道:「不、不,我不敢逃走。我是想出了個主意,看能不能用樹枝做出一把大梳子給你梳頭。我也不知道是否使得,不如讓我試試吧!」 噓冷冷地瞪著他,低喝道:「好,你便試試!你若敢欺騙我,我將你撕成四塊!」 羅欽心想:「他沒有手,只有兩條腿,如何將我撕成四塊?」但想歸想,畢竟不敢以身嘗試,於是趕緊來到一株大樹下,取出多它給他帶上的短刀,劈下十餘根粗樹枝,又剝下樹皮,搓成繩索,將樹枝綁在一起,固定於兩株大樹之間。 噓睜著一雙細細的眼睛,望著他的一舉一動,滿面好奇懷疑之色。 羅欽忙完之後,回頭對噓一笑,得意地道:「這是我專門替神人製作的巨大梳子,快來試試吧。」 噓懷疑道:「怎麼試?」 羅欽道:「你沒有手,不能拿梳子給自己梳頭,因此我將這把梳子固定在兩株大樹之間,你只需走近前,將頭湊在梳子上,讓頭髮甩上這些梳牙,慢慢拖過,便可以梳理頭髮了。快來試試吧!」 噓從未梳過頭,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將頭湊到樹枝上;他巨大的頭一甩,立即便將一頭髒亂的頭髮甩在了梳牙之上。 羅欽用手扶著「梳子」,將噓的一頭粗髮壓在梳牙之間,說道:「好了,慢慢往前走,將頭移開。」 噓開始舉步往前走,但他的頭髮實在太過骯髒糾結,立即便卡住了,再也無法拖動。 羅欽見了,腦子急速動念,快速說道:「且莫著急,神人多年來第一次梳頭,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就梳通。我知道啦,待我給神人洗洗頭髮,將汙垢沖去了,想來便能夠梳動頭髮了。請等一會兒,我去那邊的山泉取水來。」 噓的頭髮仍卡在樹枝之上,無法移動,頓時急了,怒吼道:「不准走!你騙我,讓我卡在這兒動彈不得,你使詐!我定要捉住你,將你撕成四塊,一塊一塊活活吃了!」說著奮力掙扎,想扯回自己的頭髮,但他的頭髮糾結得極為密實,一時扯之不開,兩株大樹被噓扯得左搖右晃,整座山似乎都震動了起來。 羅欽心想:「你若把我撕成四塊,我早就死了,你又怎能一塊塊活活吃了?」但他畢竟不想被撕成四塊吃掉,於是趕忙安撫道:「我沒有騙你,我是真心在想辦法替你梳頭啊!你瞧,我不是已經幫你洗好臉了麼?我現在正在想辦法給你梳頭啊!請相信我,耐心等一會兒,我去取水來清給你洗頭髮。神人請想想,你只要我梳頭,我卻還願意替你清洗頭髮哩!世間曾有人答應替你清洗頭髮麼?想必沒有吧。請耐心等候一會兒,我很快就回來。」 噓似乎聽信了他的言語,怒氣略息,說道:「好吧!你去,快去快回!」 於是羅欽快步奔去之前山泉,再次用自己的衣衫沾滿了泉水,回來澆在噓的頭髮上;但這一點兒山泉並不足夠,他來回跑了幾趟,才終於將噓的頭髮全都沾濕了。之後他便用力搓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將糾結的亂髮稍稍理順了些。他對噓道:「好啦,頭髮洗過一遍了,神人再試試梳頭吧!」 這回噓慢慢往前跨步,將頭移開,頭髮滑過梳牙,果然能夠拖動了。但是走出幾步,便又卡住了。羅欽只好再次試圖幫他清洗頭髮,但噓的頭髮許多地方緊緊糾結成一團,甚難扯開。 羅欽忙了半天,仍舊徒勞無功,喘著氣道:「沒辦法了,不如讓我砍斷這團亂髮,你說成麼?」 噓的頭卡在樹枝之上,扯了幾回都無法移動,頭皮疼痛得緊,忙叫道:「砍吧,砍吧!我總不能永遠卡在這兒啊!就要天黑了,我得去叫太陽下山啊!不然太陽今日下不了山,天下可就亂了!」 羅欽心想:「我若將他留在這兒,讓太陽留在天上一整夜,豈不有趣?」 但他畢竟不敢太過胡鬧,於是拔出多它給他帶上的短刀,向著噓的亂髮砍下。豈知才一砍下,噓便慘叫起來:「疼啊!」 羅欽一驚,立即停手,問道:「哪兒疼?」那侍女名叫陸婇兒,約莫十五、六歲年紀,月圓臉上總掛著討喜的微笑,一雙細眼透出機靈之色;她身形矮小而豐腴,衣著比一般婢女鮮亮得多。她是羅氏一個遠房表妹的獨女,因父母早逝,自幼便隨羅氏住在沈家,身分處於婢女和外甥女之間,乃是羅氏的貼身親信。 陸婇兒上下打量沈雁一身奢華鮮麗的簇新衣裙,和她裊娜多姿的體態身形,臉上露出難掩的豔羨之色,搖頭笑道:「大娘這身新裝,就連天上仙女也不如啊!依我說,大娘大婚那日,可要羨煞全城的女兒了!」 羅氏聽了,不禁得意地笑了,說道:「婇兒,妳這張嘴可真甜!」 沈雁甜笑著對母親道:「既然要給我做嫁裳,不如阿娘也做一套,婚禮那日我們母女穿一個樣式的,好不?」 羅氏笑斥道:「雁兒胡說!我若打扮得跟新嫁娘一般,可不成了老妖婆了!」 陸婇兒在旁說道:「倒是該選一疋和大娘同款的冰羅霧縠,給二娘也做套新衣裙。」 羅氏喜道:「這主意好!」眼光掃向廳內,問道:「雒兒呢?」 沈雁對著銅鏡左顧右盼,伸手輕抿髮鬢,扶正髮髻上的飛雁金簪,說道:「我方才忙著裝扮,沒見到小妹。」 羅氏皺起眉頭,轉身道:「嵇嫂,妳讓人去找找二娘,咱們趕著出門哩!」 羅氏的陪嫁婢女嵇嫂答應了,陸婇兒插口道:「姨母,我今朝見二娘去了桑園看蠶兒,只怕人還在園子裡呢。」 羅氏點頭道:「還是婇兒有心。嵇嫂,妳快讓人去桑園找二娘,叫王乳娘趕緊替她梳頭更衣!都甚麼時候了,還在園子裡瘋玩兒!」嵇嫂連忙吩咐婢女,婢女快步趕往桑園去了。 就在這時,沈拓忽然抬起頭,問道:「二郎呢?」 此言一出,全場一靜,羅氏臉色頓時沉下,廳中的冉管事、嵇嫂、陸婇兒等都低下了頭不作聲。 就在這一片靜默中,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從門外進來,他身形挺拔,容貌俊美,對沈拓道:「阿爺,駙馬的壽禮都已備妥了。」 沈拓點點頭,說道:「大郎,還是你辦事妥貼。」 這青年正是沈家長子沈維。他留意到母親和冉管事、嵇嫂、陸婇兒個個臉色古怪,微笑問道:「怎麼了?臨出門卻找不著小妹,是麼?」 羅氏淡淡地道:「嵇嫂已遣婢女去桑園裡喚她了。」 沈維望望母親,又望望大妹沈雁,說道:「等小妹到來,我等便即出發,是麼?」 沈拓咳嗽一聲,對冉管事道:「還不快去尋二郎?駙馬爺是知道他的。今日我們全家去給駙馬爺拜賀六十大壽,少攜一子,殊為不恭。」 冉管事低下頭,唯唯答應而去。 沈維恍然大悟:「原來是為了小弟。」他知道父母感情融洽,相敬如賓,唯一不和之事,便是這個庶出的弟弟。北人重嫡輕庶,正出和庶出之子的地位往往有天壤之別;正妻的子女錦衣玉食、僕從成群,庶子女則粗布陋食,地位與奴僕相去不遠。然而沈家祖上遷自南方,南方習俗不似北方這般輕庶,因此沈拓一直將這庶子放在心上,雖因長年在外奔波生意,家中內外大事皆多交由羅氏主導,心知羅氏不待見庶子,卻也難以時時迴護,偶爾為此與羅氏有所爭執。而由於駙馬爺王肅也是來自南方的漢人,並不在意嫡庶之分,此番沈氏舉家造訪駙馬府邸給駙馬拜壽,少攜一子,確屬失禮。 羅氏冷冷地道:「他自己遲了,咱們何必等他?再說,駙馬爺倘若問起,就說他病了,留在家中休養,有何不可?」 沈拓皺起眉搖搖頭,只揮手催促冉管事趕緊去尋二郎。 廳中陷入一片尷尬的沉默。沈拓夫婦坐在織錦坐墊上等候,沈維、沈雁兄妹則一個垂手肅立,一個對鏡顧盼,目光各不相對。 陸婇兒跪在羅氏身邊,輕聲勸解道:「姨母,咱們今兒去給駙馬拜壽,還能見到公主殿下呢,怎好為了這點兒瑣事鬧心呢?」 羅氏聽了,眉頭略舒,臉色也緩和了些。 沈拓見婇兒好言勸解,妻子怒氣略消,心中暗暗鬆了口氣。
不多時,王乳娘領著一個六、七歲的女童來到廳上,女童顯然剛剛梳好頭,紮著雙辮,穿著一身桃紅繡花綢緞衫褲,紅撲撲的圓臉上仍綴著不少汗珠子。女孩兒面貌與羅氏極為相似,英氣十足,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她彷彿全然不覺自己來遲了,也未留意父母兄姊神態有異,滿臉歡快地撲入父親懷中,甜笑道:「阿爺!今年的蠶兒可大了!有一籃子的蠶兒已經跟我的手指兒一般粗了!」 羅氏心下微惱,卻不忍心斥責小女兒,只對王乳娘埋怨道:「不是跟妳說了今兒要出門,讓妳早些給二娘梳洗打扮麼?」 王乳娘委屈地道:「娘子,奴婢提醒二娘好多回了,但她在蠶舍裡忙著餵飼蠶兒,全不聽奴婢的話啊!」 沈拓最最疼愛這個小女兒,伸手將她攬在懷裡,笑著道:「乖雒兒,妳愛惜蠶兒,阿爺很歡喜。不過咱們不該遲到、惹阿娘生氣,這得趕著去給駙馬拜壽啦!」 沈雒全沒聽出父親言語中的教訓之意,笑嘻嘻地著指向角落,說道:「還要多謝小兄每日爬上樹梢,幫我採最嫩的桑葉餵蠶兒,蠶兒才能長得這麼好!」 眾人聽小娘沈雒這麼說,都是一呆,一齊轉頭望去。
但見一個七、八歲的童子靜悄悄地站在廳中角落。在此之前,眾人都未曾發現他,直到二娘沈雒伸手指向他,沈拓和羅氏等才忽然留意到他立在該處。至於他是從哪道門進來的,何時進來的,進來了多久,廳上人竟誰也不知。 此時人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這童子身上。沈家上下,不論主僕,見到這童子的衣著形貌,都不禁暗暗搖頭。只見他安靜退縮地立在廳角,低頭望向自己腳上一雙顯然太小的破布鞋,頭髮又髒又亂,一身布衣布褲不但汙穢陳舊,膝頭和手肘處還打著幾個補丁,其卑微猥瑣、上不得檯盤之態,比之沈府的奴僕都還不如。 沈拓深皺眉頭,問道:「綾兒,你的乳娘呢?怎地未曾給你梳頭更衣?」 那童子名叫沈綾,正是沈家唯一的庶子。 他低下頭,囁嚅答道:「回阿爺的話……趙姊姊兩年前便辭去了。」 沈拓一呆,沒想到自己竟疏漏至此,小兒子的乳娘辭去了兩年,自己卻全不知情!但沈家絲綢生意越做越大,他長年帶著長子沈維在外奔波買賣,忙碌不堪,確也無暇顧及家中這等小事。沈拓不禁望了妻子羅氏一眼,心想:「家裡自然不缺聘請乳娘的銀錢,趙乳娘多半是娘子蓄意辭退的。這等瑣事,我若不過問,她自不會主動跟我提起。」他不好向妻子發作,當下咳嗽一聲,轉向小女兒的王乳娘,說道:「王姊姊,妳快帶二郎下去梳洗一下,換身新衣。」
王乳娘「欸」了一聲,但卻站在當地,並不移動,猶豫地搓著雙手,滿面為難之色,也不知是不屑幫這庶出之子梳洗更衣,還是不敢得罪主母羅氏? 沈拓見狀心中不悅,正打算開口催促王乳娘,羅氏忽然站起身,往門外走去,不耐煩地道:「還梳洗甚麼?你瞧他這個邋遢樣,不知要梳洗多久才見得人,咱們可要遲到啦!不必梳洗更衣了,就這麼去吧!」 沈拓更加鎖緊了眉頭,他決不願讓外人見到自己的幼子如此不體面,尤其這孩子上有長兄,旁有姊妹,個個容貌出眾,衣著光鮮亮麗,偏生這幼子卻如此形容骯髒,看在外人眼中,定將引發街談巷議,令沈家大失臉面。於是沈拓不顧妻子的不快,堅持道:「不成。咱們這是去造訪駙馬府邸,人人都必須換裝打扮,整肅儀容,否則可是大不敬。綾兒,你趕緊去換了新衣來。」 沈綾答道:「是,阿爺。」卻遲疑不動。 沈拓見了頗感惱怒,呵叱道:「怎不快去?」沈綾低下頭,支支吾吾地道:「回阿爺的話,小子沒有……沒有新衣可換。」 沈拓大感驚怒,高聲道:「我們沈家做的是絲綢生意,隨從僕婦都皆穿綢著緞,家中二郎怎會連件可換上的新衣都沒有?」他轉頭望向羅氏,眼中頗有責怪之意。 羅氏卻不甘示弱,立即揚起眉毛,冷冷地道:「你望我做甚麼,這關我何事?」 沈拓平日對妻子好生恭敬禮讓,這時卻當真惱火了,大聲道:「妳是家中主母,孩子的事情自然都歸妳管。大兒和兩個女兒個個錦衣華服、穿金戴玉,妳卻任由小兒整日穿著一身破爛布衣,連件能換上的新衣都沒有?」 羅氏乃是出名的火爆脾氣,聽丈夫責怪自己,頓時雙眉倒豎,雙手叉腰,也提高了聲音,瞪眼道:「我日日在總舖照顧生意、招呼主顧,忙得焦頭爛額,哪有工夫理會家中這等瑣事?這些衣衫鞋子的小事兒,自有管事和僕婦照料。這庶子的飲食起居,怎會是該我管的事兒!」 沈拓駁道:「就算妳忙,內宅的人事總歸妳管吧!他的乳娘何時辭去了,妳竟不曾跟我提起,也不曾替他另請一個?他才幾歲哪,怎能連個乳娘也沒有?平日誰照顧他?」 羅氏怒道:「甚麼乳娘不乳娘,他的乳娘是誰,我根本不知道!當初那乳娘可不是我請的。她何時辭去,為何辭去,我半點兒也不知情,又怎會想到要另請一個?更加不會跟你提起!再說,他也有八歲了,年紀夠大了,早就不喝奶了,也該能夠照看自己了。你竟為了這卑微庶子有沒有乳娘的瑣碎事兒怪起我來?」 夫妻倆當著僕從子女的面,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在大廳中爭吵起來。
長子沈維看在眼中,露出擔憂之色,走上一步,想試圖勸解,卻見母親身後的陸婇兒向自己連連搖手,示意莫要介入,只好打消了念頭,退開一步。 正僵持間,站在銅鏡前的沈雁忽然對沈綾招招手,語音清脆地說道:「小弟,你跟我來。我屋中留了幾件大兄年幼時的衣衫,應當合你身。我帶你去換上了,咱們好趕緊出門。」 沈拓一聽大女兒這麼說,吁了口氣,向她投去欣慰的目光,說道:「那敢情好。綾兒,快跟你大姊去更衣吧。」 沈雁回頭對父親嫣然一笑,向沈綾瞥了一眼,回身走去,沈綾連忙趨前跟上。小妹沈雒見父母大起口角,不敢留在廳中,立即道:「我也一起去。」舉步追上大姊沈雁和小兄沈綾。 沈拓和羅氏留在廳中,但兩人怒氣未消,立即又針鋒相對地繼續爭執起來,吵了一陣子,羅氏氣得滿臉通紅,拂袖怒道:「這事兒我當年便說明白了,我絕不理會。此前不理會,往後也不理會!你莫要再在我面前提起那低賤的豎子!」隨手將廳中一只琉璃花瓶掃到地上,哐噹一聲,砸得粉碎。 沈拓露出驚怒之色,那只花瓶乃是他五年前赴西域大秦國販售絲綢時,特意以千金買下,千里迢迢帶回洛陽,送給妻子的禮物,豈知羅氏一怒之下,竟輕易砸碎了這無價之寶!他臉上黑氣一閃,握緊了拳頭,指節突出,身子微微顫抖,顯然須得用盡全力,才能按捺下心頭的怒火。 沈家眾管事、僕婦、婢女、家丁們見慣了羅氏的剛烈脾氣,倒也並不驚訝,只個個低頭屏息,不想觸怒主母將一口惡氣發洩在自己身上,也不敢去望主人,免得他因在奴僕面前失了顏面倍感尷尬。只有羅氏的外甥女陸婇兒神色沉穩,抬頭望向羅氏,滿面關懷擔憂。 羅氏怒氣未歇,伸腳狠狠地往地上的琉璃碎片踢去,只踢得碎屑到處亂飛。她踢了一陣後,往地上啐了一口,頭也不回,起身大步出門而去。陸婇兒站起追上幾步,又停下腳步,回頭望了主人沈拓一眼。沈拓對她擺擺手,說道:「去!快去勸勸她。」陸婇兒點頭答應,快速向沈拓行了個禮,快步追出門外,口中急喚道:「姨母!」 冉管事畢竟在沈家服侍了三十餘年,經驗老道,這時維持鎮靜,暗中對兩個婢女示意。婢女連忙奔去取了掃帚畚箕等物,匆匆進廳,清理琉璃花瓶的碎片,又悄悄退出;一個僕婦立即捧出了另一只花瓶,放在原處。那是主人沈拓從南方帶回來的青釉仰覆蓮花尊,雖不及那只大秦國琉璃花瓶奇麗美觀,也是件稀世之寶。沈家乃大富之家,種種珍貴擺設不計其數,倉房中甚麼沒有?一番清理轉換之後,廳中便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一般。 沈拓將奴僕的舉止都看在眼中,不發一言,鐵青著臉,轉過身去。 這時長子沈維咳嗽一聲,緩步來到父親身旁,低聲道:「阿爺,阿娘平日不只須照料家務,還得兼顧總舖的生意,確實忙碌得很。我和阿爺又常常出門,總舖的經營全落在阿娘一人身上,日日何等分身乏術!家中之事,她自不免有些許難全之處,阿爺何必苛責?」 沈拓吁出一口氣,臉色平緩下來,說道:「你說得是。我不該對你阿娘發脾氣。只是我長年不在家,照看不上你弟弟妹妹的生活起居,自不免擔憂。你看看你小弟,都八歲了,一身穿著竟如同乞兒似的,外人見了怎麼想?」 沈維安慰父親道:「小弟年紀還小,從不出門,想來不曾被外人見到。如今我們知曉了此事,只需交代冉管事,命織室的裁縫給他做上幾套全新的衣褲鞋襪,那便是了。他年紀也大了,乳娘不必另請,不如就指派個僕人,專門服侍他吧。」 沈拓點了點頭,說道:「就這麼辦吧。」叫了冉管事近前,交代了一番,又吩咐道:「你靜靜去做便是,別讓主母知道了。」 冉管事垂手道:「謹遵阿郎吩咐。」 沈綾和沈雒跟著大姊沈雁來到她的居處「飛雁居」。雖是同住一宅的親姊弟,這卻是沈綾第一回來到沈雁的居處。飛雁居乃是一座獨立的院子,佔地寬廣;沈拓夫婦寵愛長女,在她出生百日後,便開始替她營造這座飛雁居,全供沈雁一人居住;飛雁居中配有三十名僕婦婢女,負責打掃、烹飪及各項雜務,專職服侍沈雁這位沈家大娘。 此時沈雁領著弟弟沈綾和妹妹沈雒跨入飛雁居,入門先是一座庭園,右首是個巨大的花圃,圃中萬紫千紅,種滿了百合、甘菊、蘭蕙等名花珍卉;左首是個葫蘆型的池塘,池水碧綠,池旁連香、銀杏和山白芍圍繞,濃郁成蔭。通過一條鋪滿碎石子的小徑後,便來到一間寬敞的花廳,廳旁分出三條閣道,分別連接到沈雁的書房、起居室和寢室。這花廳四面開敞,窗明几淨,楠木櫃上陳設著各種玩物擺飾,有白玉辟邪、青瓷花瓶、石雕胡馬、青銅壽龜等,還有不少沈拓從西域各國帶回來的珍品,包括琉璃珠串、石雕佛像、花卉紋金盤等。沈綾從未見過這等珍奇寶貝,只看得眼花撩亂,暗暗稱奇。
沈雁對婢女于洛道:「我往年騎馬時慣穿的大兄衣衫收在何處?妳快快替我找了出來。」 于洛答應了,連忙去衣物房翻箱倒櫃,找了好一會兒,才找出了一套童子衫褲,看來還有八分新。 沈雒拍手笑道:「大姊,妳怎地還留著大兄小時候的衣衫?」 沈雁道:「我六、七歲時剛學騎馬,嫌裙裝不方便,因此向大兄討了幾套他的衣褲來穿,後來就留在屋裡了。」從于洛手中接過,往沈綾身上比了比,蹙眉道:「大了些。沒法子,將就著換上吧。」 沈綾忙道:「多謝大娘。」恭敬接過,趕緊去衣物間更衣。 沈雁又吩咐婢女于洛道:「妳去給他梳個頭,要快。」于洛答應了,忙跟入衣物間。 隨後她斜倚在花廳窗邊,懶洋洋地道:「你們快些吧!阿爺和阿娘還在大廳上等著呢。」沈綾連忙隔空應道:「是,大娘。」 沈雒側過頭,擔憂地問道:「大姊,妳說阿爺阿娘還在爭吵麼?」 沈雁似乎並不在意,只淡淡地道:「應該吵完了吧?阿娘就是這般性情,不高興了便板起臉、高聲訓斥人,我在總舖可是見得多了。但她和阿爺當著奴僕之面大動肝火,這可是頭一回。」 沈雒吐吐舌頭,說道:「是啊,我從未見過阿爺阿娘這般紅臉相對哩!」 沈雁道:「妳年紀小,沒見過的事兒可多著呢。阿爺成日在外奔波,在家的時候原本不多。況且他們即便意見不合,也不會在妳面前爭持不下。」 沈雒嘟起嘴道:「那今兒是怎麼回事?阿爺阿娘怎地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爭成這樣?」 沈雁閒散地笑笑,說道:「當然是因為在裡面更衣的這一位啦。他若不快些換好,只怕阿爺阿娘還得繼續爭下去哩。」 沈綾在裡面聽著大姊的言語,好生焦急,快手快腳換好了衣衫,發現袖子褲腳都太長了些,只能趕緊捲上了。這時于洛也已飛快替他梳好了頭髮,沈綾便快步走出衣物間,說道:「大娘,換好了。」 沈雒見他換上一身新的衫褲,頭髮齊整,顯得精神煥發許多,拍手笑道:「小兄,你穿上大兄這身衣褲,可好看得很哪!」 沈雁望向沈綾,說道:「你總低著頭,誰也看不清你臉面。你抬起頭來。」 沈綾依言抬起頭;沈雁望向他的臉龐,微微一怔,但見他膚色白淨,鼻挺眼細,容貌端俊,心想:「小弟平日畏畏縮縮,今日換上一身整齊衣衫,才看得出他一張臉竟然還挺俊秀的!雖沒有大兄的英氣,但絕對是上得檯盤的。」她微微點頭,說道:「換了身衣衫,人可就不同了。」神情轉為嚴肅,說道:「小弟,你給我聽好了,我幫你找衣衫更換,可不是對你存著什麼好心。我只是不願見到阿爺阿娘為你互起齟齬,不想你穿得邋邋遢遢地出門去丟人現眼,也別誤了咱們一家拜壽的時辰。聽清楚了麼?」 沈綾原也奇怪大姊沈雁何以忽然出頭幫助自己,聽她如此說來,倒也在情理之內;沈家的兩位長兄長姊年紀比自己大上許多,在家中的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自不必紆尊降貴,對自己示好,於是連忙回答道:「是,大娘,小子聽清楚了。」 沈雒噘起嘴,對姊姊道:「大姊,妳怎地這般說話?妳明明對小兄很好,卻故意說自己對他不存好心?」 沈雁一笑,「我就是不存好心,爽快說出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甚麼不對了?」又向沈綾打量去,目光停留在他腳上那對過小的破布鞋上,微微皺眉,對于洛道:「大兄當年那對馬靴呢?應當還不太舊,快找出來了。」 于洛趕緊答應了,再次去衣物間翻箱倒櫃,沈雒也興沖沖地跟著去幫忙翻找,一會兒後,終於找出一對男童的騎馬皮靴,拿出來給沈綾試穿。沈綾穿上了,倒是剛好合腳。沈雒高興地道:「衣衫大了些,靴子倒是剛剛好。」 但聽外面僕人連聲催促,姊弟妹三人快步回到大廳上,見母親羅氏已立於上馬堂前,正撫摸著愛馬「踏燕」的鬃毛,神色已恢復平靜;沈拓則獨自坐在大廳之中,臉色仍有些不豫,但已無明顯怒色。大兄沈維見他們回來,連忙催促道:「快些、快些,咱們得趕緊出門啦!」 這時馬夫已替小娘沈雒備好了她的愛駒「踏雪」,那是一匹通體黑色、四蹄雪白的母馬,身上鞍轡也是金銀鑲玉,十分華麗。沈雒和母親羅氏分別騎上了馬,沈拓坐上第一輛馬車,長子沈維、長女沈雁和幼子沈綾則坐上第二輛馬車。眾人一坐定,馬夫便喝叱揮鞭,兩輛馬車緩緩駛出沈家大門。 在沈家主人的馬匹和馬車之後,另跟了三輛裝飾較為樸實的楠木馬車,前兩輛承載著給駙馬的十箱壽禮,第三輛則乘坐了沈家主人們的貼身僕婢,包括跟隨主人沈拓多年的親信喬五、主母羅氏身邊的嵇嫂和陸婇兒、大娘沈雁的婢女于洛、二娘沈雒的婢女于沱,以及日常供大郎沈維使喚的兩個小奴;另有十餘名勁裝結束的健僕跨著駿馬,簇擁在馬車和雙馬旁,充作護衛。一行人浩浩蕩蕩,策馳在洛陽城大街之上。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綾羅歌.卷一
79折
特價300元
加入購物車
綾羅歌.卷二
79折
特價300元
加入購物車
綾羅歌.卷三
79折
特價300元
加入購物車
綾羅歌.卷四(完結篇)
79折
特價300元
加入購物車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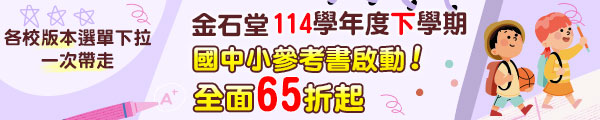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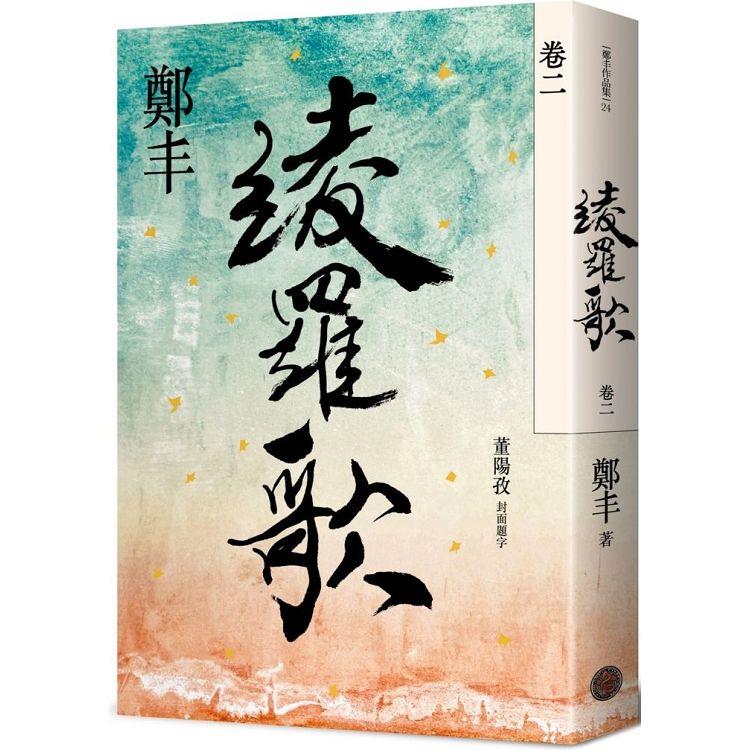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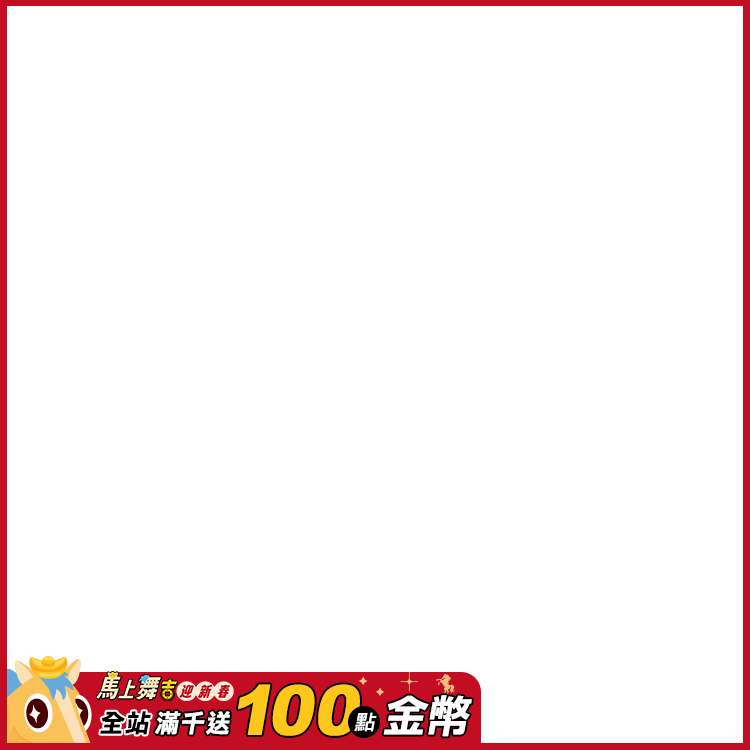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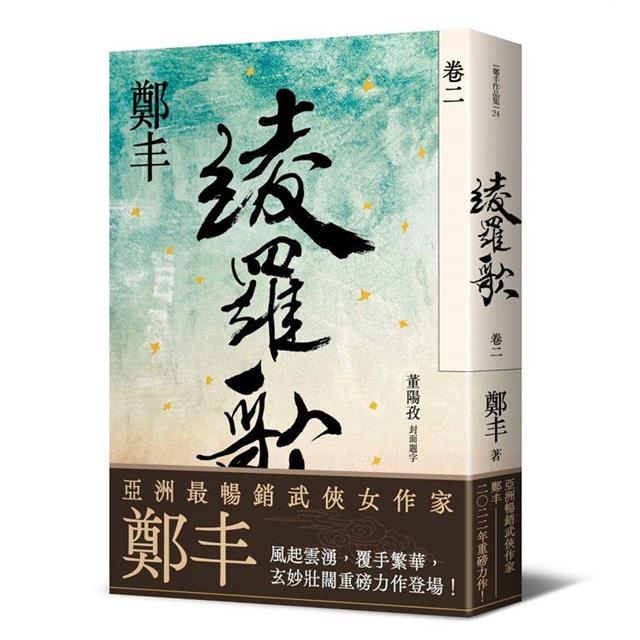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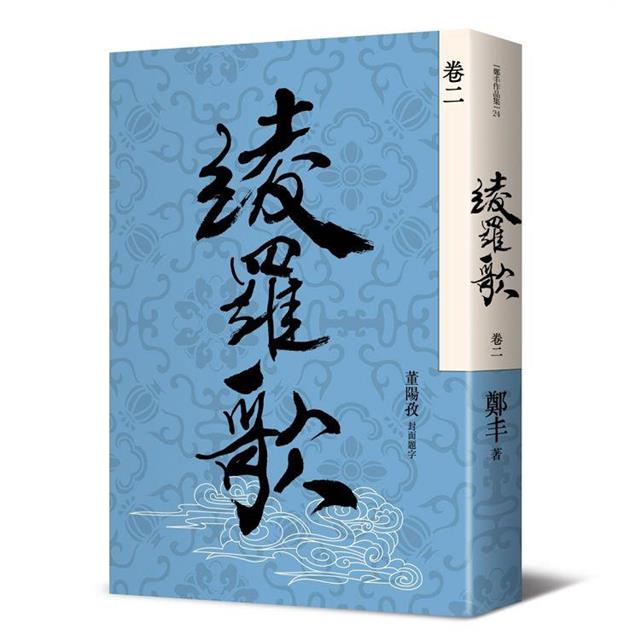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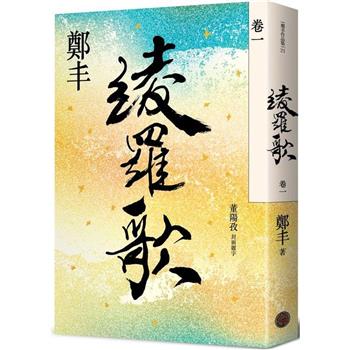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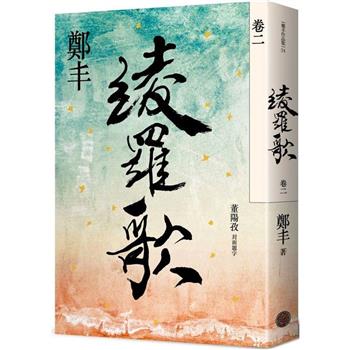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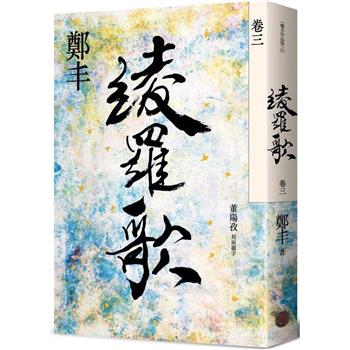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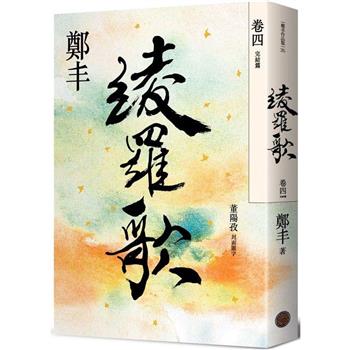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