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詩在沉默裡發生,神在沉默時降臨。
思想、知識和情感,都在沉默中凝定。
生命在沉默裡開鑿意義,靈魂在沉默裡取得質量。
而我沉默如缽,盛滿自己的祕密。
二十五年後,當我們從「柯南唐捐」(或他多次自我解構的「唐損」)重新回到這部集結了他九○年代整整十年的散文集,書中那些繁複得近乎奇觀的喻體與喻依,濃稠的感官書寫與象徵系統,以及他所招喚來的一批白堊紀式的上古蟲魚鳥獸……,熟悉唐捐的讀者或都可以在這些語言的抽搐痙攣處,見證了一種創世紀式的開天闢地。那會是一個碑記嗎?如同書中反覆出現的那個場景:童年的村落已被湖水淹沒在水庫底下。滄海桑田。末日的景觀招喚出一種創世的出逃。面對眼前每時每瞬皆在消逝的風景,唯有大規模的沉默是為記?
──言叔夏
詩在沉默裡發生,神在沉默時降臨。
思想、知識和情感,都在沉默中凝定。
生命在沉默裡開鑿意義,靈魂在沉默裡取得質量。
而我沉默如缽,盛滿自己的祕密。
二十五年後,當我們從「柯南唐捐」(或他多次自我解構的「唐損」)重新回到這部集結了他九○年代整整十年的散文集,書中那些繁複得近乎奇觀的喻體與喻依,濃稠的感官書寫與象徵系統,以及他所招喚來的一批白堊紀式的上古蟲魚鳥獸……,熟悉唐捐的讀者或都可以在這些語言的抽搐痙攣處,見證了一種創世紀式的開天闢地。那會是一個碑記嗎?如同書中反覆出現的那個場景:童年的村落已被湖水淹沒在水庫底下。滄海桑田。末日的景觀招喚出一種創世的出逃。面對眼前每時每瞬皆在消逝的風景,唯有大規模的沉默是為記?
──言叔夏
目錄
目次
【導讀】魚有兩張臉:讀唐捐《大規模的沉默》╱言叔夏
【自序】
魚語搜異誌
螢河榮枯錄
福壽綿綿
口腹因緣品
少年遊
黑色素
養神
暗中
脫身
毛血篇
有人被家門吐出
紅花園索隱
墓室內的子宮
感應
十日痰
不在場證明
大規模的沉默
血肉稿
喔,機械狼
調用遠方無聲鴿
後記
索引
【導讀】魚有兩張臉:讀唐捐《大規模的沉默》╱言叔夏
【自序】
魚語搜異誌
螢河榮枯錄
福壽綿綿
口腹因緣品
少年遊
黑色素
養神
暗中
脫身
毛血篇
有人被家門吐出
紅花園索隱
墓室內的子宮
感應
十日痰
不在場證明
大規模的沉默
血肉稿
喔,機械狼
調用遠方無聲鴿
後記
索引
序/導讀
推薦序
只有少年Q知道,魚們都有左右兩張不相屬的臉,會微笑,更會大聲地嚎啕。只因鎮日在水中游動,即使流了淚亦不自知,笑了,亦無從鑑照。只有在離水的剎那,才看到自我的形象;只有在離水的剎那,才知道隨身攜帶淚水以潤膚爽身之必要。
──唐捐,〈魚語搜異誌〉
不知二○二六年的今天,已在現代詩的領域裡練成無堅不摧「金臂勾」、甚或熟練地配戴起柯南「蝴蝶結變聲器」、大玩迷因與諧音梗的唐捐,會如何看待這部遠在上世紀末的「沉默的少作」?(套句書中他所自述的:「人就是他所吃喝的。」不禁讓人想問:這二十幾年來他究竟嗑了什麼……?)在各種意義上,出版於上世紀一九九九年的《大規模的沉默》,對時年三十一歲的青年唐捐而言,既是他第一部散文集,同時或許也是他對他自身「現代主義時代」的告別。以沉默的手勢。此後的唐捐少再有那種「魚的流淚時刻」。取而代之的是「笑」。如同魚有兩張臉。魚的左臉,會知道右臉的表情嗎?又或者魚僅願意對人們展示牠的左臉,而將右臉隱密地藏匿起來?二十五年後,當我們從「柯南唐捐」(或他多次自我解構的「唐損」)重新回到這部集結了他九○年代整整十年的散文集,書中那些繁複得近乎奇觀的喻體與喻依,濃稠的感官書寫與象徵系統,以及他所招喚來的一批白堊紀式的上古蟲魚鳥獸……,熟悉唐捐的讀者或都可以在這些語言的抽搐痙攣處,見證了一種創世紀式的開天闢地。那會是一個碑記嗎?如同書中反覆出現的那個場景:童年的村落已被湖水淹沒在水庫底下。滄海桑田。末日的景觀招喚出一種創世的出逃。面對眼前每時每瞬皆在消逝的風景,唯有大規模的沉默是為記?
《大規模的沉默》裡,也有一個按圖索驥、沿著被大水沖沒的水庫沿岸,去追索童年時住過的村落的少年。少年依稀記得舊家村落的名字叫做「紅花園」。多年後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找到了《台灣地名手冊》上一行看不出背景身世的小字:「紅花園:23°17’-20°34’,小村。」在這個只剩下一行經緯度的地名裡,他所招喚來的回憶竟是幼時與姊姊提著餿水餵豬、雙雙摔進豬圈裡,被豬蹄與糞便、飼料蹂躪成爛泥的記憶。
這些場景顯然離抒情詩的世界有些遙遠,而且拒絕給出救贖的啟示與靈光。彷彿這些斷片,就僅僅是斷片本身,再無法從時間裡要求任何索賠。換言之,它們都沒有「後來」,而只是個人活過的時間裡所剩下的「鬼」。作為黃錦樹所編列的、從余光中、楊牧以降的「現代散文」╱「詩化散文」隊伍下游之一員,《大規模的沉默》自有其從現代主義的譜系之處承接過來的抒情血緣──只是那「血」,可能還混摻了一些「不純」的什麼──出身嘉義大埔偏鄉山村的唐捐不見得飲過那正統的抒情血緣,但必然喝過他那筍農父親在竹寮裡捕到的山鼠之血:「……父親買來十幾個鼠斬置於田間。隔天果然捕得數隻,隻隻腦滿腸肥,顯然吃了許多民脂民膏。父親把牠們宰了下鍋,肉質堅韌,使人脾胃大開。」(〈毛血篇〉)
〈毛血篇〉裡接過父親殺鼠利刃的唐捐,劃開鼠腹,將手掌伸探進內臟的深處,一時間在山鼠的血裡感到「彷彿就要被鼠同化」;忽而恍然大悟:「我們宰魚的時候,聽不到魚的哀鳴與抽搐,惟見冰冷的血滴默默流落。而蟑螂蒼蠅之屬就更等而下之了,連血都沒有,當然更不容易引發加害者的同情與悔吝。」這會是他貫串整部《大規模的沉默》最顯而易見的秘密嗎?在古老的抒情傳統裡,「情」作為一種引譬連類的觸媒引信,將抒情主體與其所處的外部世界,串聯成一種隱喻與象徵系統的宇宙。這種意識形態自成一種內嵌於詩學內部的階級意識,與文化資本幣值,並且進而圈限出了「文」的傳統領域──因此那詩學的盡頭,必有靈。然而,《大規模的沉默》顯然是抒情詩的一種變體?或者根本是另條路數──在唐捐筆下,那淹沒家屋與田地的水庫大水不啻是一種遠古山洪景觀,類近志怪筆記或《山海經》(如此旁門左道、掉出六經之外的「邪典」──):在那荒僻、猶如被世界遺棄的山村裡,父親提刀上山採摘竹筍、削水波石,回到山村養瑰麗妖豔的粉紅福壽螺,且在母親營生的山產店裡,捕鼠殺羌,開腸剖肚,且令人怵目地掏心掏肺。這些《詩經》甚或《楚辭》裡的蟲魚鳥獸不再只是抒情詩裡的一個名字,而是為了生存,一切皆必須成為可吃之物──父親總是說:「吃吃看就知道。」一切事物都要落入口腹,被我消化吸收,才算是徹頭徹尾的理解。(〈口腹因緣品〉)
口腹先於語言。舌頭從一種語言的發音部位,先成為了消化系統的前端器官。唐捐儼然創造出了一種獨屬於他那荒山野嶺經驗裡的「抒情路數」,以殘酷的階級現實作為起點,透過宰殺放血所形成的食物鏈:每個被吃的,都將成為那牠所被吃的;而每個吃下牠的,也都將代替死去的牠而成為牠。這是他超克死亡的抒情方法嗎?又或者,在《大規模的沉默》裡,無處不在的「死亡」其實是無法被超克的,尤其在階級的現實裡,無暇被美學化的「死」,才是「生」的地基。某種意義上,當年茹毛飲血的唐捐非但走踏出了一條有別於中文系抒情傳統的大雅之路,走向被湖水淹沒的野墳與廢村。在那裡,未知死,焉知生?他其實已在這部嚴肅的少作裡,示範也暗示了一種顛覆叛離,回應了二十年後投向解構歧路(與戴上蝴蝶結變聲器)的自己。魚有兩張臉。一張是自己。還有一張,也是自己。
只有少年Q知道,魚們都有左右兩張不相屬的臉,會微笑,更會大聲地嚎啕。只因鎮日在水中游動,即使流了淚亦不自知,笑了,亦無從鑑照。只有在離水的剎那,才看到自我的形象;只有在離水的剎那,才知道隨身攜帶淚水以潤膚爽身之必要。
──唐捐,〈魚語搜異誌〉
不知二○二六年的今天,已在現代詩的領域裡練成無堅不摧「金臂勾」、甚或熟練地配戴起柯南「蝴蝶結變聲器」、大玩迷因與諧音梗的唐捐,會如何看待這部遠在上世紀末的「沉默的少作」?(套句書中他所自述的:「人就是他所吃喝的。」不禁讓人想問:這二十幾年來他究竟嗑了什麼……?)在各種意義上,出版於上世紀一九九九年的《大規模的沉默》,對時年三十一歲的青年唐捐而言,既是他第一部散文集,同時或許也是他對他自身「現代主義時代」的告別。以沉默的手勢。此後的唐捐少再有那種「魚的流淚時刻」。取而代之的是「笑」。如同魚有兩張臉。魚的左臉,會知道右臉的表情嗎?又或者魚僅願意對人們展示牠的左臉,而將右臉隱密地藏匿起來?二十五年後,當我們從「柯南唐捐」(或他多次自我解構的「唐損」)重新回到這部集結了他九○年代整整十年的散文集,書中那些繁複得近乎奇觀的喻體與喻依,濃稠的感官書寫與象徵系統,以及他所招喚來的一批白堊紀式的上古蟲魚鳥獸……,熟悉唐捐的讀者或都可以在這些語言的抽搐痙攣處,見證了一種創世紀式的開天闢地。那會是一個碑記嗎?如同書中反覆出現的那個場景:童年的村落已被湖水淹沒在水庫底下。滄海桑田。末日的景觀招喚出一種創世的出逃。面對眼前每時每瞬皆在消逝的風景,唯有大規模的沉默是為記?
《大規模的沉默》裡,也有一個按圖索驥、沿著被大水沖沒的水庫沿岸,去追索童年時住過的村落的少年。少年依稀記得舊家村落的名字叫做「紅花園」。多年後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找到了《台灣地名手冊》上一行看不出背景身世的小字:「紅花園:23°17’-20°34’,小村。」在這個只剩下一行經緯度的地名裡,他所招喚來的回憶竟是幼時與姊姊提著餿水餵豬、雙雙摔進豬圈裡,被豬蹄與糞便、飼料蹂躪成爛泥的記憶。
這些場景顯然離抒情詩的世界有些遙遠,而且拒絕給出救贖的啟示與靈光。彷彿這些斷片,就僅僅是斷片本身,再無法從時間裡要求任何索賠。換言之,它們都沒有「後來」,而只是個人活過的時間裡所剩下的「鬼」。作為黃錦樹所編列的、從余光中、楊牧以降的「現代散文」╱「詩化散文」隊伍下游之一員,《大規模的沉默》自有其從現代主義的譜系之處承接過來的抒情血緣──只是那「血」,可能還混摻了一些「不純」的什麼──出身嘉義大埔偏鄉山村的唐捐不見得飲過那正統的抒情血緣,但必然喝過他那筍農父親在竹寮裡捕到的山鼠之血:「……父親買來十幾個鼠斬置於田間。隔天果然捕得數隻,隻隻腦滿腸肥,顯然吃了許多民脂民膏。父親把牠們宰了下鍋,肉質堅韌,使人脾胃大開。」(〈毛血篇〉)
〈毛血篇〉裡接過父親殺鼠利刃的唐捐,劃開鼠腹,將手掌伸探進內臟的深處,一時間在山鼠的血裡感到「彷彿就要被鼠同化」;忽而恍然大悟:「我們宰魚的時候,聽不到魚的哀鳴與抽搐,惟見冰冷的血滴默默流落。而蟑螂蒼蠅之屬就更等而下之了,連血都沒有,當然更不容易引發加害者的同情與悔吝。」這會是他貫串整部《大規模的沉默》最顯而易見的秘密嗎?在古老的抒情傳統裡,「情」作為一種引譬連類的觸媒引信,將抒情主體與其所處的外部世界,串聯成一種隱喻與象徵系統的宇宙。這種意識形態自成一種內嵌於詩學內部的階級意識,與文化資本幣值,並且進而圈限出了「文」的傳統領域──因此那詩學的盡頭,必有靈。然而,《大規模的沉默》顯然是抒情詩的一種變體?或者根本是另條路數──在唐捐筆下,那淹沒家屋與田地的水庫大水不啻是一種遠古山洪景觀,類近志怪筆記或《山海經》(如此旁門左道、掉出六經之外的「邪典」──):在那荒僻、猶如被世界遺棄的山村裡,父親提刀上山採摘竹筍、削水波石,回到山村養瑰麗妖豔的粉紅福壽螺,且在母親營生的山產店裡,捕鼠殺羌,開腸剖肚,且令人怵目地掏心掏肺。這些《詩經》甚或《楚辭》裡的蟲魚鳥獸不再只是抒情詩裡的一個名字,而是為了生存,一切皆必須成為可吃之物──父親總是說:「吃吃看就知道。」一切事物都要落入口腹,被我消化吸收,才算是徹頭徹尾的理解。(〈口腹因緣品〉)
口腹先於語言。舌頭從一種語言的發音部位,先成為了消化系統的前端器官。唐捐儼然創造出了一種獨屬於他那荒山野嶺經驗裡的「抒情路數」,以殘酷的階級現實作為起點,透過宰殺放血所形成的食物鏈:每個被吃的,都將成為那牠所被吃的;而每個吃下牠的,也都將代替死去的牠而成為牠。這是他超克死亡的抒情方法嗎?又或者,在《大規模的沉默》裡,無處不在的「死亡」其實是無法被超克的,尤其在階級的現實裡,無暇被美學化的「死」,才是「生」的地基。某種意義上,當年茹毛飲血的唐捐非但走踏出了一條有別於中文系抒情傳統的大雅之路,走向被湖水淹沒的野墳與廢村。在那裡,未知死,焉知生?他其實已在這部嚴肅的少作裡,示範也暗示了一種顛覆叛離,回應了二十年後投向解構歧路(與戴上蝴蝶結變聲器)的自己。魚有兩張臉。一張是自己。還有一張,也是自己。
試閱
內文選摘
魚語搜異誌
魚臉
湖裡浮現一對慘白的月亮,如溺者泡水數日的乳房,點綴著一塊塊深褐色的屍斑。夜裡的湖泊凝滯如果凍,少年Q蹲踞在湖畔,讓鳥的啼鳴蟲的聒噪獸的叫喊滋潤他枯乾的耳膜。他困惑著,月亮,怎麼會是成雙成對的呢?揉揉痠麻的雙眼,眼皮裡流洩出許多令人駭異的影像。許許多多虛幻縹緲的魚群游到他的跟前,張開蒼白的嘴唇,發送喃喃不止的音波。那些細微的聲響夾雜著起滅不定的泡沫,一旦流入Q的腦髓,竟然漸漸凝成一粒粒滾動的語音,色明味濃,可以提鍊出斷斷續續的意義。如同海水,衝入鹽田,留下大片結晶的粗鹽。
啊,少年Q竟然聽懂了魚的語言。
他忽然發現魚也是有頭有臉的,由於頭部緊緊接契著身體,伸展不出去,使人誤以為牠們只是一塊塊游動的骨肉。牠們的聲帶長在鼻孔之內,液態的語音總是在水中湮沒,因此又被誤為天生的啞者。牠們的眼睛長在兩側,不斷從左右邊逼壓過來的兩片視域,總是無法在腦海裡完整地統合,如同兩張溼濡的畫片黏疊在一起,相互滲透渲染,造成迷離恍惚的圖象。更可悲的是,頭的正前方竟然沒有眼睛,只有一張凸出而寬闊的大嘴,不斷地開合吞食,再加上連昆蟲那樣的觸鬚也沒有,只好以口代眼,以食物決定去來的時機與方向。這就注定了觸網銜鉤的命運,給了釣者無限的樂趣。
只有少年Q知道,魚們都有左右兩張不相連屬的臉,會微笑,更會大聲地嚎啕。只因鎮日在水中游動,即使流了淚亦不自知,笑了,亦無從鑑照。只有在離水的剎那,俯身下望,才看到自我的形象;只有在離水的剎那,才知道隨身攜帶淚水以潤膚爽身之必要。
腸肚
少年的故鄉僻處郊野,距城百里,四面環山,懷抱著島內最大的湖泊。滿水位二百二十五公尺,面積十七平方公里,總蓄水量七億零八百萬立方公尺。每到星期假日,城裡的人們總會乘著汽車,來到這裡,如螞蟻聚向一攤糖水或蟲屍。人人都愛湖,愛湖從肚子裡吐出一尾一尾肥美的魚蝦。
街上於是興起一種叫作「筏釣」的行業,以膠筏載客到湖心釣魚。原本靠山吃飯的少年Q的父親,如今也在湖裡營生了。
所有的魚都像孩童一樣,用嘴巴來認識世界,用唾腺來思考。當牠們在蒼茫水波中,嗅聞芳香的魚料,便要義無反顧地游向釣客預設的陷阱。被鐵鉤穿透的蚯蚓,仍能輕輕地扭身,美好的血腥味一點一點在水裡流行。這時會有一隻幸運的魚兒,用有力的尾巴甩開朋伴,張開嘴唇,狠狠吞食。銳利的鐵鉤立即貫穿牠的嘴唇,愈是掙扎,傷口就鑿得愈深。離水的剎那,湖底彷彿也有一隻手在挽留著牠,但巨大的痛楚使牠不得不服從釣線,終於甩甩尾巴,慘然離開永恆的家園。
每日黃昏,魚們就搭乘著堆滿冰塊的鐵箱,駛向岸上。釣客們手裡吃力地提著一尾二三十斤的大頭鰱,咧著唇齒,站在湖邊拍照。父親蹲踞在水龍頭下,替客人殺魚。他用長刃切開魚腹,像拉開胯下的拉鍊那般流利,血水嘩嘩地噴洩出來,紅紫交雜的腸肚擲落一地。
少年Q發現,垂死的魚最大的娛樂便是模仿釣客的臉。但是淚水總會刺破生硬的笑臉,悽慘的啼哭只有少年Q聽得見。父親手握魚刮,吋吋刨掉貼身的魚鱗,淡淡的血絲滑入眼眶,與淚水相互碰撞,暗暗地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響。離水的魚目具有一種神奇的透視的能力,牠們看見每個人的腸肚都像池塘,游著無數的魚魂,牠們看見天空的底部埋著鳥的骨骸,牠們看見自己的腸肚化入昆蟲的腸肚,在草叢裡蹦蹦跳跳。
血緣
「魚乃水之花。」少年Q聽過這種說法。那麼,湖水也是一種泥土了。少年Q看到許多細小的魚苗被播入湖裡,在豐饒養份的滋潤下,慢慢生根發芽、成長茁壯,開出肥美燦爛的花朵。於是人們動手從水裡將牠們拔出,一條條看不見的臍帶在空中斷裂,濕答答的血水悄悄地流淌。絕對不是花,Q想,魚可能更像是湖的鱗片。當人們取走任何一尾魚,湖便承受一次刮鱗剔肉的痛楚。
少年Q含淚凝視著湖面。他知道,每隻魚從湖裡被拔走,都會留下一個永不結痂的瘡孔,表面上雖然風平浪靜,其實不斷流出黏稠的膿汁。Q想,那些瘡孔是魚的出口,同時也是人的入口。短短一個暑假,湖泊已吞食了本地三名少年,吞食且加以咀嚼、消化,不吐一根骨頭。奇怪的是,從來不曾聽說外來的釣客失足落水。這樣看來,湖也是挑食的吧!他夢見那些少年的魂魄化作浮藻流菌,滋養著魚蝦,使水色長保碧綠。
湖跟少年之間,其實是有血緣關係的。他出生的村落就在湖底,人工造湖的計劃才把村人趕上高處。湖底飽含著童年的記憶:水井。阡陌。泡著水牛的池塘。土地祠。祖父母的舊墳。他總是覺得自己與湖之間原來也有一條臍帶相連,跟魚一樣。這樣想時,他忽然發現湖水和血肉竟是同質同色,交感互通。當人們把釣線垂入湖裡,他的肌膚感到痛楚痠疼,像被針灸一樣。當釣鉤從湖裡被拉出,他感覺精氣流失,腦海裡湧出昏黑的氣體,全身虛弱不堪。
輪迴
少年Q在路邊撿到一本善書,《鳥語搜異誌》,公冶長先生奉天公之命,降鸞寫下的著作。據說,他本是孔夫子的學生兼女婿,生來通曉鳥語,死後昇天成仙。書中共訊問了三十四隻鳥,歷數前世今生的因緣。墮落的孌童被罰作牡孔雀,永世無聊地炫耀著毛羽。夜間晃蕩不眠,四處偷竊的男子變成貓頭鷹,再也無力承受明亮的日光。苛薄刁鑽的酷吏化作嘴硬的啄木鳥,日復一日,敲打著樹木。販女求財的賭徒,九十九世廁身羽族,轉世為百靈、樹喜、八哥之屬,供人玩賞殺戮……。
這樣的話,天上的鳥禽無一不是帶著罪孽飛行的惡人了。少年Q想,那麼,整座湖便是一個大囚籠,龜鱉魚蝦不斷地泅泳著,以洗滌前世積累的惡業。當牠們最後被人釣起、剖殺、吞食,也算是罪有應得了。可是,蒙昧無知的魚鳥日日夜夜讓慾念催動著,飢則食,倦則眠,飽暖則交配以求繁殖,既已忘卻前世種種繁複的枝節,又怎能體會今生失卻人身的緣由與意義呢?或許,Q想,讓牠們不明不白地承受苦難,正是最嚴厲的處分吧!
這天他躺在竹筏上睡著,湖伸出白晰的指掌輕輕撫弄他的胸膛。
夢裡,他感覺體內的水份嘩嘩地向下滲落,湖水重新注滿他的心湖和腦海。於是他看到了,一尾武昌魚急切地游到足下,雙眼浮腫,彷彿長期被PH值七的強酸的淚水浸泡著,惶惶然將要潰爛。牠搖動著孱弱的尾部,輕聲地哀求著:「釣起我吧!拜託。無法再忍受湖的統治、水的拴囚,但無手以自盡,無腳以逃亡,唯一的希望是釣鉤。釣起我吧!拜託拜託。」少年Q駭然坐起,像搶救溺者般,急急甩出釣竿。那魚立刻咬餌不放,催促少年快快提起。當牠離水的剎那,拚命地扭腰,彷彿真是那麼那麼地亢奮。
水孕
少年Q裸身在湖裡游泳,夕陽暖暖,湖水發出一種淫蕩的聲響,水質香滑甜軟,如同少女初初成熟的肌膚。少年Q滑泳著,忽潛忽浮,感覺自己像個嬰孩在羊水中快樂地蠕動。波浪在搓揉他的感官,陽光在激發他的綺想。少年生猛地泳動,在湖心與岩岸間不斷來回,感覺到無數魚目在水底窺探,無數魚唇在礁石藻草間唼喋。湖水愈來愈冰涼,少女已發育為少婦,散發迷人的芳香。夕陽更用力地將最後一道殘光洩入湖泊,湖水頓時劇烈地顫抖搖晃。少年Q從勃發的身體裡,射出一道腥臊的白漿。水溫陡然昇高了三度,母魚全都聚攏過來,同時急切地排卵。
這時湖面漸漸向上凸起,渾圓,飽滿,如孕。
虛弱地躺在岩上。湖裡慢慢浮現那對乳房般的月亮。少年Q彷彿看到他灑下的種子在水裡長成美麗的魚苗,搖動稚嫩的鰭翅,追逐起滅不定的泡沫,自由地嬉戲笑鬧。他把雙手垂入水底,讓幼魚吸吭著指頭,於是十指都成了乳頭,泌出濃濃的汁液,享受哺育的快感。魚在悠游中成熟膨脹,但少年Q知道,有一天牠們也將相吞互併,同歸於盡,或者陷入網罟鉤叉,魂斷砧板。想到這裡,他發覺指甲裡滲出的不再是乳汁,而是淚水。水裡的手指已經被泡得慘白而皺褶,少年一下子老去了許多。
那天晚上,餐桌上照樣有一盤煮熟的魚屍。被蒸爛的白眼彷彿還能瞪人,家人的竹筷起落頻頻,很快就剔光了白嫩的肉。少年Q折下魚頭,仔細端詳,忽然他發現魚頭左右兩面的表情竟然不同:一面充滿悲哀,唇部下凹,生前未流盡的淚水繼續滑落,因而顯得特別濕潤;另一面則掛著淺淺的笑容,彷彿在享受死亡的歡欣。少年Q想,從湖泊游向餐桌,究竟是蒙難,還是解脫?他剝開魚頭,吮食甜甜軟軟的魚髓,細細體會積蓄在其中的美夢與惡魘,於是他看到了濃濃的影像:扭腰的武昌魚。鸞書。湖泊下的祖墳。白漿。
一九九八年七月
魚語搜異誌
魚臉
湖裡浮現一對慘白的月亮,如溺者泡水數日的乳房,點綴著一塊塊深褐色的屍斑。夜裡的湖泊凝滯如果凍,少年Q蹲踞在湖畔,讓鳥的啼鳴蟲的聒噪獸的叫喊滋潤他枯乾的耳膜。他困惑著,月亮,怎麼會是成雙成對的呢?揉揉痠麻的雙眼,眼皮裡流洩出許多令人駭異的影像。許許多多虛幻縹緲的魚群游到他的跟前,張開蒼白的嘴唇,發送喃喃不止的音波。那些細微的聲響夾雜著起滅不定的泡沫,一旦流入Q的腦髓,竟然漸漸凝成一粒粒滾動的語音,色明味濃,可以提鍊出斷斷續續的意義。如同海水,衝入鹽田,留下大片結晶的粗鹽。
啊,少年Q竟然聽懂了魚的語言。
他忽然發現魚也是有頭有臉的,由於頭部緊緊接契著身體,伸展不出去,使人誤以為牠們只是一塊塊游動的骨肉。牠們的聲帶長在鼻孔之內,液態的語音總是在水中湮沒,因此又被誤為天生的啞者。牠們的眼睛長在兩側,不斷從左右邊逼壓過來的兩片視域,總是無法在腦海裡完整地統合,如同兩張溼濡的畫片黏疊在一起,相互滲透渲染,造成迷離恍惚的圖象。更可悲的是,頭的正前方竟然沒有眼睛,只有一張凸出而寬闊的大嘴,不斷地開合吞食,再加上連昆蟲那樣的觸鬚也沒有,只好以口代眼,以食物決定去來的時機與方向。這就注定了觸網銜鉤的命運,給了釣者無限的樂趣。
只有少年Q知道,魚們都有左右兩張不相連屬的臉,會微笑,更會大聲地嚎啕。只因鎮日在水中游動,即使流了淚亦不自知,笑了,亦無從鑑照。只有在離水的剎那,俯身下望,才看到自我的形象;只有在離水的剎那,才知道隨身攜帶淚水以潤膚爽身之必要。
腸肚
少年的故鄉僻處郊野,距城百里,四面環山,懷抱著島內最大的湖泊。滿水位二百二十五公尺,面積十七平方公里,總蓄水量七億零八百萬立方公尺。每到星期假日,城裡的人們總會乘著汽車,來到這裡,如螞蟻聚向一攤糖水或蟲屍。人人都愛湖,愛湖從肚子裡吐出一尾一尾肥美的魚蝦。
街上於是興起一種叫作「筏釣」的行業,以膠筏載客到湖心釣魚。原本靠山吃飯的少年Q的父親,如今也在湖裡營生了。
所有的魚都像孩童一樣,用嘴巴來認識世界,用唾腺來思考。當牠們在蒼茫水波中,嗅聞芳香的魚料,便要義無反顧地游向釣客預設的陷阱。被鐵鉤穿透的蚯蚓,仍能輕輕地扭身,美好的血腥味一點一點在水裡流行。這時會有一隻幸運的魚兒,用有力的尾巴甩開朋伴,張開嘴唇,狠狠吞食。銳利的鐵鉤立即貫穿牠的嘴唇,愈是掙扎,傷口就鑿得愈深。離水的剎那,湖底彷彿也有一隻手在挽留著牠,但巨大的痛楚使牠不得不服從釣線,終於甩甩尾巴,慘然離開永恆的家園。
每日黃昏,魚們就搭乘著堆滿冰塊的鐵箱,駛向岸上。釣客們手裡吃力地提著一尾二三十斤的大頭鰱,咧著唇齒,站在湖邊拍照。父親蹲踞在水龍頭下,替客人殺魚。他用長刃切開魚腹,像拉開胯下的拉鍊那般流利,血水嘩嘩地噴洩出來,紅紫交雜的腸肚擲落一地。
少年Q發現,垂死的魚最大的娛樂便是模仿釣客的臉。但是淚水總會刺破生硬的笑臉,悽慘的啼哭只有少年Q聽得見。父親手握魚刮,吋吋刨掉貼身的魚鱗,淡淡的血絲滑入眼眶,與淚水相互碰撞,暗暗地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響。離水的魚目具有一種神奇的透視的能力,牠們看見每個人的腸肚都像池塘,游著無數的魚魂,牠們看見天空的底部埋著鳥的骨骸,牠們看見自己的腸肚化入昆蟲的腸肚,在草叢裡蹦蹦跳跳。
血緣
「魚乃水之花。」少年Q聽過這種說法。那麼,湖水也是一種泥土了。少年Q看到許多細小的魚苗被播入湖裡,在豐饒養份的滋潤下,慢慢生根發芽、成長茁壯,開出肥美燦爛的花朵。於是人們動手從水裡將牠們拔出,一條條看不見的臍帶在空中斷裂,濕答答的血水悄悄地流淌。絕對不是花,Q想,魚可能更像是湖的鱗片。當人們取走任何一尾魚,湖便承受一次刮鱗剔肉的痛楚。
少年Q含淚凝視著湖面。他知道,每隻魚從湖裡被拔走,都會留下一個永不結痂的瘡孔,表面上雖然風平浪靜,其實不斷流出黏稠的膿汁。Q想,那些瘡孔是魚的出口,同時也是人的入口。短短一個暑假,湖泊已吞食了本地三名少年,吞食且加以咀嚼、消化,不吐一根骨頭。奇怪的是,從來不曾聽說外來的釣客失足落水。這樣看來,湖也是挑食的吧!他夢見那些少年的魂魄化作浮藻流菌,滋養著魚蝦,使水色長保碧綠。
湖跟少年之間,其實是有血緣關係的。他出生的村落就在湖底,人工造湖的計劃才把村人趕上高處。湖底飽含著童年的記憶:水井。阡陌。泡著水牛的池塘。土地祠。祖父母的舊墳。他總是覺得自己與湖之間原來也有一條臍帶相連,跟魚一樣。這樣想時,他忽然發現湖水和血肉竟是同質同色,交感互通。當人們把釣線垂入湖裡,他的肌膚感到痛楚痠疼,像被針灸一樣。當釣鉤從湖裡被拉出,他感覺精氣流失,腦海裡湧出昏黑的氣體,全身虛弱不堪。
輪迴
少年Q在路邊撿到一本善書,《鳥語搜異誌》,公冶長先生奉天公之命,降鸞寫下的著作。據說,他本是孔夫子的學生兼女婿,生來通曉鳥語,死後昇天成仙。書中共訊問了三十四隻鳥,歷數前世今生的因緣。墮落的孌童被罰作牡孔雀,永世無聊地炫耀著毛羽。夜間晃蕩不眠,四處偷竊的男子變成貓頭鷹,再也無力承受明亮的日光。苛薄刁鑽的酷吏化作嘴硬的啄木鳥,日復一日,敲打著樹木。販女求財的賭徒,九十九世廁身羽族,轉世為百靈、樹喜、八哥之屬,供人玩賞殺戮……。
這樣的話,天上的鳥禽無一不是帶著罪孽飛行的惡人了。少年Q想,那麼,整座湖便是一個大囚籠,龜鱉魚蝦不斷地泅泳著,以洗滌前世積累的惡業。當牠們最後被人釣起、剖殺、吞食,也算是罪有應得了。可是,蒙昧無知的魚鳥日日夜夜讓慾念催動著,飢則食,倦則眠,飽暖則交配以求繁殖,既已忘卻前世種種繁複的枝節,又怎能體會今生失卻人身的緣由與意義呢?或許,Q想,讓牠們不明不白地承受苦難,正是最嚴厲的處分吧!
這天他躺在竹筏上睡著,湖伸出白晰的指掌輕輕撫弄他的胸膛。
夢裡,他感覺體內的水份嘩嘩地向下滲落,湖水重新注滿他的心湖和腦海。於是他看到了,一尾武昌魚急切地游到足下,雙眼浮腫,彷彿長期被PH值七的強酸的淚水浸泡著,惶惶然將要潰爛。牠搖動著孱弱的尾部,輕聲地哀求著:「釣起我吧!拜託。無法再忍受湖的統治、水的拴囚,但無手以自盡,無腳以逃亡,唯一的希望是釣鉤。釣起我吧!拜託拜託。」少年Q駭然坐起,像搶救溺者般,急急甩出釣竿。那魚立刻咬餌不放,催促少年快快提起。當牠離水的剎那,拚命地扭腰,彷彿真是那麼那麼地亢奮。
水孕
少年Q裸身在湖裡游泳,夕陽暖暖,湖水發出一種淫蕩的聲響,水質香滑甜軟,如同少女初初成熟的肌膚。少年Q滑泳著,忽潛忽浮,感覺自己像個嬰孩在羊水中快樂地蠕動。波浪在搓揉他的感官,陽光在激發他的綺想。少年生猛地泳動,在湖心與岩岸間不斷來回,感覺到無數魚目在水底窺探,無數魚唇在礁石藻草間唼喋。湖水愈來愈冰涼,少女已發育為少婦,散發迷人的芳香。夕陽更用力地將最後一道殘光洩入湖泊,湖水頓時劇烈地顫抖搖晃。少年Q從勃發的身體裡,射出一道腥臊的白漿。水溫陡然昇高了三度,母魚全都聚攏過來,同時急切地排卵。
這時湖面漸漸向上凸起,渾圓,飽滿,如孕。
虛弱地躺在岩上。湖裡慢慢浮現那對乳房般的月亮。少年Q彷彿看到他灑下的種子在水裡長成美麗的魚苗,搖動稚嫩的鰭翅,追逐起滅不定的泡沫,自由地嬉戲笑鬧。他把雙手垂入水底,讓幼魚吸吭著指頭,於是十指都成了乳頭,泌出濃濃的汁液,享受哺育的快感。魚在悠游中成熟膨脹,但少年Q知道,有一天牠們也將相吞互併,同歸於盡,或者陷入網罟鉤叉,魂斷砧板。想到這裡,他發覺指甲裡滲出的不再是乳汁,而是淚水。水裡的手指已經被泡得慘白而皺褶,少年一下子老去了許多。
那天晚上,餐桌上照樣有一盤煮熟的魚屍。被蒸爛的白眼彷彿還能瞪人,家人的竹筷起落頻頻,很快就剔光了白嫩的肉。少年Q折下魚頭,仔細端詳,忽然他發現魚頭左右兩面的表情竟然不同:一面充滿悲哀,唇部下凹,生前未流盡的淚水繼續滑落,因而顯得特別濕潤;另一面則掛著淺淺的笑容,彷彿在享受死亡的歡欣。少年Q想,從湖泊游向餐桌,究竟是蒙難,還是解脫?他剝開魚頭,吮食甜甜軟軟的魚髓,細細體會積蓄在其中的美夢與惡魘,於是他看到了濃濃的影像:扭腰的武昌魚。鸞書。湖泊下的祖墳。白漿。
一九九八年七月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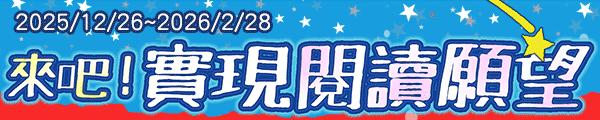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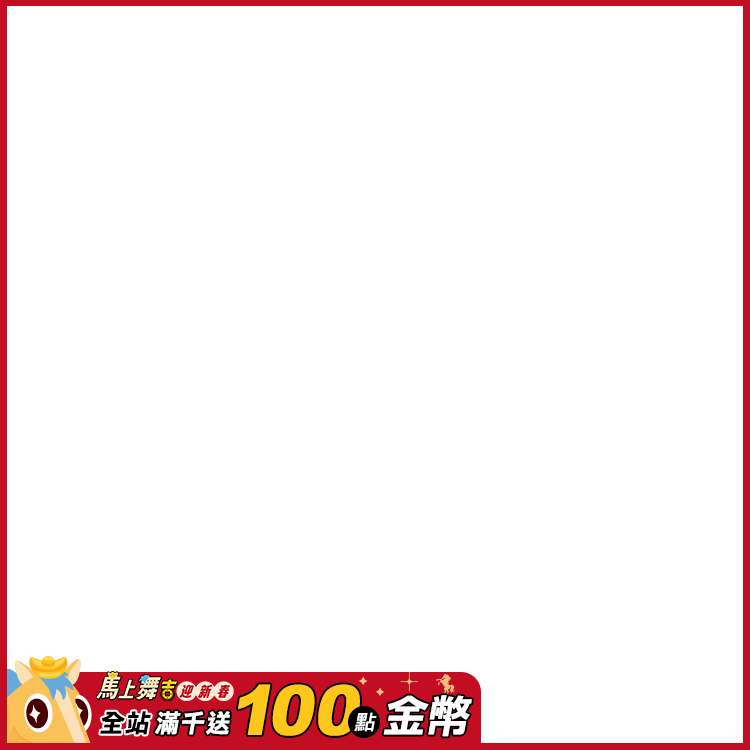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