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世界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三個人此生錯過的愛
一場充滿心碎、煎熬與希望的愛戀!
袁瓊瓊 鍾文音鄭重推薦
在我知道的這個世界底下,就在夏日蔓生的草坪底下,在門前階梯的巨大厚石板下面,埋藏著另一個世界:
三個人、愛意洶湧的秘密世界。
本書透過描寫紐約的一個捷克移民家庭,慢慢地拼出了這場愛情的全貌。主角在紐約成長時,發現了家中詭異的氣氛,所有話語到了嘴邊都只能講一半,彷彿有許多不該講的秘密,存在於鬱鬱寡歡的父親、謎般的母親、不存在第三者的心裡。於是他回到了故鄉布拉格,循著父母親往日的足跡,在灰飛煙滅的歷史餘燼中,撿拾殘缺的事實,一點一滴地解開了藏在母親心中十五年的祕密。原來母親與情人的烽火戀情,還有父親荒謬的等待,都在他們的內心占有不為人知的角落:我們內心相信的愛情,不一定是被世界允許的情感;我們只能選擇要相信哪一個眼中世界。
名人推薦
普立茲獎得主理查‧福特 (Richard Ford):這本小說的力量蘊藏在作者極富想像力的描述中,他描寫過去所失去的像回音一般不斷被繼承、承受,讓耳朵只聽得見回憶的聲音。這本書真是扣人心弦。
華盛頓郵報:很少有小說會剖開故事的幻覺──就像在十七世紀的解剖圖裡,屍體有效地抑制自己胃部的跳動──顯露出底層的創作技巧、回憶和渴望。更少見的是,像這樣微妙的書能打進你的心坎裡。但馬克‧史洛卡的第二本小說《眼中世界》不光是質疑說故事的目的,以及過往和現在的關連,也是個撼動人心的愛情故事。
書商雜誌:《眼中世界》的主要情節圍繞著捷克反抗軍刺殺海德里希的事件,調製了一杯感情的甜酒。裡頭加入了命中注定的愛情,還有老一輩移民擺脫不了過去的悲哀,有些人失敗了,另一些人挺身奮戰。寫得非常出色。
歐普拉雜誌:只要能掌握回憶和語言善變的特質、哀傷慢慢的侵蝕和愛情令人喜愛的力量,那麼當故事真的發生時,任何人都應該能夠述說出來。這是本文采豐富、具啟發性的小說
週日泰晤士報:一個精心編織的故事令人難以忘懷。
出版人週刊:書中安排的懸疑節奏流暢,動作場面描寫得栩栩如生。史洛卡的小說洋溢著熱情。
◆柯倫‧麥肯 (Colum McCann):一句句,一字字,馬克‧史洛卡證明了自己是這時代最優秀的作家:他令人想起伯格(Berger)、塞伯德(Sebald)、艾芮綺(Erdrich)、翁達傑(Ondaatje)。《眼中世界》是個非凡的愛情故事,描述隱藏在底下的世界……這本書可以遠遠流傳。
◆觀察家:書中沒有英雄也沒有浪漫的結局,但史洛卡仍然征服了人心。」
◆週日電訊報:本書避開一般的陳腔濫調,很有技巧地傳達了對戰爭愛情故事的反諷,最後以急轉直下的情節作為結束,引出我們心中純真的浪漫,風格有如米蘭‧昆德拉和麥可‧翁達傑。然而《眼中世界》最大的成就是,讓真相和小說勢均力敵,成功地融合為一體。
◆《故事》:史洛卡是位非常敏銳的作家,他非常擅長刻畫人物,而且對於模擬兩可的人的行為觀察入微。這是本成功的小說。
◆芝加哥論壇報:文字精簡,內容豐富,值得沉思、充滿懸疑,《眼中世界》探索了父母親神秘的一生,以及在戰爭期間做出的讓步與犧牲。更重要的是,本書探索了說故事這個動作本身,達成完全瞭解我們所愛的人這項艱難、必須的工作,透過瞭解他們,我們也盡自己所能地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舊金山紀事報:他的散文特色是嚴謹,他的計畫更是野心勃勃……我們記下的所有物質細節構成了《眼中世界》,但在我們生活的表面底下有道深層的水流在流動。要讀懂微妙、具有啟示性的細節需要一顆富含詩意的心靈,而要重組這些細節則需要詩人吹毛求疵的性格。史洛卡對心靈智慧的執著證明他有以上兩種特質。」
◆作家伊莉莎白‧伯格:一本精彩出色的小說。《眼中世界》是敘述渴望的故事。充滿智慧和詩意的細節,證明了為何馬克‧史洛卡是當代最佳的小說家之一。他讓我們思考;帶我們去感覺;因為他的作品不僅僅是在說故事而是藝術,所以在閱讀他的書時,我們的層次也提昇了。
◆斯溫‧伯克茨 (Sven Birkerts):灰暗但令人神往,《眼中世界》探討了絕對的愛情和不可避免的悲劇。史洛卡學會了小說家的秘密暗號,掌握了難以捉摸的故事脈絡,他能夠穿過一切時髦的反諷直抵故事的源頭。以戰爭為背景,用回憶的光芒來點亮,他的小說真是引人入勝,叫人愛不釋手。
編輯推薦
目錄
在闃黑中躺著,我心想,沒錯,正是如此:在我知道的這個世界底下(一個對我如此熟悉、如此美式的世界),就在夏日蔓生的草坪底下,或門前階梯的巨大厚石板下面,埋藏著另一個世界。
我認為,我父親是個正派的好人,他會對他所處的世界忿忿不平,但他對理性的信仰就像有些人對上帝或愛的信仰一樣,始終堅定不移,即使他的一生已使這個信念顯得荒謬可笑。
布拉格間奏曲
灰暗的一天。一陣風,暖和的氣息,吹動了樹葉,揚起覆在玩滑板小孩眼睛上骯髒的捲髮,讓紙袋沿著人行道滑行了一小段距離。坐在廣場上,我突然感覺到那些事實、日期、故事、坐在教堂墓地長椅上的情侶,都如同鐵屑環繞著看不見的磁鐵聚集在一起,慢慢浮現出一個模糊的形狀出來。
母親將自己抹除得一乾二淨,所以她過世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在任何地方都無法找到她的蹤影。六個月後父親也過世了,兩年後我辭去工作搬到布拉格。當時我三十一歲,不曾有過意外的好運氣,也不特別期待。或許我正在尋找運氣,我不知道──人就是會做各種蠢事。或許我希望能找出屬於我家的獨特故事,到底是如何嵌進時代的大故事中,雖然我對我家的故事所知不多。或許與過往、布拉格、戰爭這個已知的大拼圖面對面,我就能看出屬於我們的那塊空白,能認出它的形狀。然後我就能明白。
一九四二小說
當他快要溺死的時候,她會是垂到井裡的繩索。他知道這是毫無疑問的,如同他確定一生中所知道的所有事情。這不是感情用事,只是個事實。就像紙會燃燒、白晝會帶來亮光、活著的萬物終究難免一死。她會救他,只因為她就是她。因為專斷的世界之神決定了事情該如此發展。因為她的聲音、她的身體──如果喜歡的話,還可以說她的靈魂──在跟他說話。
試閱
我的雙親於一九三九年相識於布爾諾,在捷克被佔領的四個月後,父親寫了一封情書給母親,那是別人花十克朗的酬勞請他代寫的。他告訴我,這種事他經常做,靠這個工作,日子過得還挺不錯的。他說,寫情書不算什麼,只要掌握幾個特色,還有一些信手拈來的陳腔濫調就夠了。然而這回,當他幫客戶送信時,事情卻走了樣。「這不是弘札寫的,」後來成為我母親的年輕女子一開始看信就斬釘截鐵地說。她大笑,然後高聲朗讀:「『……在我心中空蕩蕩的房間和庭院裡』?喔,上帝。」父親開口說了些話。「停,」她說。「弘札是個可愛的男生,但寫不出含有隱喻的文字,就算隱喻在街上從他身上輾過去,他也認不出來。」她看著我父親。「哪種人會幫其他男人寫情書?」她問。「沒錢的人,」父親說。
他們開始聊起天來,等他步出位於札波梅努塔街上的糕餅店時(那是父親找到母親跟女性朋友坐在一起的地方,後來他們兩人移到靠近後頭的桌子私下談),她答應第二天跟他一起散步。這是有原因的。父親一表人才,也不是個傻子。他身上有種漫不經心的憂傷,似乎不太在意別人怎麼看他。還有,他有膽量。那天他們見過面後,他跑去練習足球(那時校門還沒關),最後在健身房的更衣室找到弘札,把信還給他。父親說,他決定了,自己要跟那個女孩交往。事情變成這樣也難怪弘札會生氣,他夥同兩個朋友將父親狠狠揍了一頓。父親用袖子擦掉臉上的血,想辦法站起來從口袋掏出十克朗的硬幣。「拿去,」他說,把錢丟在更衣室的地板上。「全額退費。」
整個夏天和秋天他們經常見面。他跟她約在鋼鐵火車站外頭碰面,兩人手挽著手走到瑪薩瑞科瓦街(占領後改名為赫曼戈林街),然後穿過廣場,沿著安靜的小街道往下走到城堡區,就跟其他情侶一樣,他們也在偌大的城堡庭園裡迷了路。我可以想像他們躺在那裡的草坪上,母親仰望深淺不一的藍天,父親在她身邊支著手肘,叨絮著一些瑣事,臉上帶著他特有的微笑,讓故事轉動得像旋轉盤上的燭台。
我喜歡想像他們兩人手挽著手漫步在裡頭的小徑上,遠離市區,像新婚夫婦第一次走進他們將要住上一輩子的房子裡,幸福洋溢地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空房間,好像從此可以輕易避開所有的事情,彷彿可以找到一個地方,或許就在這段樓梯上,或許就在這面牆的後頭或在房間大小的花園裡,讓時間找不到他們。
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我的雙親在史皮爾柏城堡沒有走平常的第一道階梯,而是不小心從第二道階梯往下走,結果來到了通往舊聖方濟修道院地窖的入口。母親從來沒到過那裡。地窖在十五分鐘內就要關閉。
一個淚眼汪汪、白髮長到下巴的老婦人坐在階梯頂端的椅子上,旁邊擺了張歪斜的牌桌和裝了三個硬幣的碗。顯而易見地,他們是最後的遊客。如果那天有學校團體造訪的話,也都已經離開了。為了一睹死了幾百年的僧侶屍體,階梯上曾經擠滿了遊客,因為戰爭遊客變少了。這地方有種被遺棄的古怪感覺。老婦人或許已經在那裡等了好幾年。
「孩子,下面很冷喔。」她看著他們。「要穿暖和點。」
事實上,他們也感覺到一股地底的濕冷寒氣從樓梯間竄了上來。父親用手環抱住母親的肩膀。婦人給了他們兩張黃色的門票。
「那樣是沒有用的。」她笑著說。
雖然沒有人收門票,父親還是拿著門票,然後兩人一起走下陡峭、彎曲的階梯。走到一半,談笑間,聽到老婦人沿著通道往下對著他們喊:「孩子,你們得快點。沒剩多少時間了。」
底下的氣氛丕變,或許是因為進入天花板低矮的昏暗房間後突如其來的寂靜,或是黏土的味道;也可能跟沒有點燈的低矮走廊有關,這走廊太矮,父親牽著母親走到隔壁點著蠟燭的房間時,還得低著頭;也可能是其他林林總總的原因。總之,這不重要。在外面的世界裡,大學紛紛關校了,工廠轉而做戰爭的生意。在上面的世界,報紙的黑色細長方格裡羅列著死者的名字,宛如在做水龍頭或皮鞋的廣告。(待續)
**
那天下午哈努斯先生跟我解釋,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事情發生。沒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正是因為沒事。「連續好幾個世代,」他說,「一切都沒變,看起來都一樣,沒有東西改變。廚房裡邊掛著日曆,一直都保持一樣,走道上有張毛又細又長的紅色絨毯,浴室的門邊總是會捲縮起來。你必須想像。我們假設是六月的某個黃昏,一個僅穿著襯衫的男人探出廚房窗口,抽著菸,手肘靠在斑駁的窗台上。下面的中庭,一切靜止不動:成堆潮濕的沙和磚、疊靠在北面牆上的兔籠、停放在屋簷下的腳踏車。花園裡的大頭菜在黑暗中不斷往上推擠。四周很安靜:你可以聽見突如其來的聲響、尖細的鍋盆碰撞聲、小孩啼哭聲。那一年是一九二三年。這男人(順便告訴你,他就是你祖父)從戰場回來已經五年了,在戰爭中他比一些人受更多的苦,也比其他人少受一點苦。
「現在有個男孩走進房間,不到三歲,膝蓋先跨到椅子上再爬上去。『你洗手了沒?』女人的聲音說道。站在窗口的男人沒有回頭,他分心在聽中庭傳來的聲音。襯衫裹著的背感覺很好、很強壯。他吸了最後一口菸,然後在窗台下方的外牆上把菸捻熄。
「歲月流逝,一切還是沒有改變。走廊上又細又長的絨毯或許比以前薄了一點,但成堆的沙和磚、停靠在車棚的腳踏車都還在,兔籠還是像公寓房子一樣堆靠在磚頭上。所有東西都是濕的。空氣聞起來有鐵或銅的味道。你可以聽見遠處傳來電車細微的鈴聲,恍若來自另一個世界。
「同一個男人探出窗口,看著雨。『安東尼,』他頭也沒回地喊道,『把煤拿來,』而你父親,現在已經十二歲,剛剛在房間裡背誦拉丁文動詞或假裝在背,他從房裡走出來,拿起煤桶消失在走廊上。
「一年過一年。這男人,你的祖父,用腳撫平絨毯上起伏劇烈的皺折無數次。馮德拉科娃太太無數次拿著薪柴,拖著腳步走到兔籠。濕潤的雪花下在沙和磚堆成的小山上,看起來像地窖門上的糖霜。然後時序再回到六月,午後的太陽照到東面牆的一半,空氣聞起來像剛翻過的土壤。在暖和的夜晚,窗戶朝中庭旋轉開來。花園裡大頭菜的頭往上鼓起,再次頂破土壤,像一排排綠色的小頭蓋骨。這是你熟知的世界。你清楚這個世界,就像現在你熟悉自己的房間一樣。
「這就是我想要跟你說的: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發生任何事。然後事情就發生了。」
「在一個叫做貝希特斯加登的地方,有個叫張伯倫的高大英國人,留著花白小鬍子從豪華轎車上現身。中間有些爭執,也喝了些茶。大人物的手指戳在擦得發亮的桌面上。『你們必須……我們變成……先生,要喝點什麼茶嗎?』在巴特哥德斯堡,這個英國人用右手撫順頭髮,然後說:『我接受你的論點,里賓特洛甫先生。然而,如果我可以……我們覺得……關於……我可以把這當成是你最後的立場嗎?』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哈努斯先生微笑著。「貝希特斯加登、巴特哥德斯堡、柏林。全都是ㄅ。」
「但你看看四周。那邊有個餐具架是你母親以前用的,還有你父親的皮革裝訂書,安全地鎖在玻璃後面。事情還沒有發生。年輕的女孩依舊躺在後院裡,讀小說打發冗長的午後;德沃斯基的舞曲依然在電台播放。沒有任何事情改變。
「突然間他們出現了,猶如三月大風雪中的晴天霹靂,用馬毛填充座墊的賓士豪華轎車開到國家大道上,越過雕塑和結凍的聖徒像到河邊去。整座城市闐靜無聲。沒有人,沒有電車。軌道動也不動,雪在鵝卵石上形成大理石花紋,就像你母親在皇后大道熟食店為你買的蛋糕一樣。建築物上吐著長舌的怪獸雕刻,從山形牆下的凹穴往外凝望。你跟其他每個人一樣,在自己的公寓裡,透過窗簾上的縫隙往外看。當他們在遠遠的底下經過時,你可以聽到旗幟發出劈哩啪啦的聲響。
「已經無計可施了,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列車陣行駛過伏爾塔瓦河。雷得卡尼城堡的城牆幾乎看不見了;射箭口空蕩蕩的。佩特辛山的林子也如同沙漠般,只剩下雪席捲過果園的風嘯聲。報紙上說,政府已經被解散。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區域內的森林、田野、城鎮、你熟知的小徑、你游泳的池塘,現在改名為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哈努斯先生笑著說:「『先生,要喝點什麼茶嗎?』
「即便是現在,在你心中仍然不覺得有什麼東西改變了。日子還是繼續過,他們繼續這樣過日子,直到有東西停頓下來的那一刻,所有這些年來平靜無事的日子,如卡在釘子上的窗簾一樣被撕裂。也許是看見有人在街上受到攻擊,也或許是收音機傳來的某種聲音,一種以前從來不曾聽過的聲音,像是毆打的聲音。無論是什麼,忽然間你明白一切東西都已經改變,沒有東西跟以前一樣了。」(待續)
父親曾經告訴我,人是像螃蟹一樣倒退著走進英雄行為,或因為太笨拙而不小心跌進去。他們衝進火裡,被榮耀遮蔽了雙眼,好不容易莫名其妙地存活下來接受大街上的遊行,或是愚蠢地遊走在事物的表面,想辦法靠著物理學和運氣度過,事後回頭看看,稱自己的行為是勇敢。
他說,無數代的英雄,這整個大隊人馬其實都是普通人,他們只是突然被捲進事件中,沒有多想就做了他們所做的事情,就像狗的尾巴被門夾住時自然會張口咬,是一樣的道理。人一旦尾巴解脫、意識甦醒之後,就會覺得像是自己人生的旁觀者。
然而,重點來了,與所有人類行為準則相牴觸的事情三不五時還是會發生:一樁英雄行動是事先計畫好,為了正當理由而執行,並對可能涉及的風險有充分的認知,甚至可說是悲痛的認知,卻仍然堅持要完成。這樣的事情簡直像下蟾蜍雨一樣令人難以置信。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你無法相信。但事實就擺在眼前,蟾蜍在路面上蹦蹦跳跳。
當那種事情發生時,他說,你只能嘆服,脫下帽子致敬。
我問父親他是否當過英雄。他說沒有,完全談不上。因為他是我父親,所以我相信他。
**
走下長而直的道路,四面沉寂,耳裡只剩下風吹過高高的樹梢發出細微的響聲,還有風停時,從灌木樹籬裡傳來疲累蟲子的聲音。她有點驚訝地發現,她變得連自己都覺得陌生。她還是同一個人,腦子裡還是裝著同樣的心思──想著還要多遠才會走到岔路;她該不該繼續走大路,或者抄捷徑穿越牧場。只是現在的她,還會跟他對話,彷彿有第三者進入原本只有她跟自己分享的空間。她想要跟他說話,大聲地跟他一起思考。她很清楚,他的闖入取代了某種根本的東西,一部分的她不見了;帶著某種快感,她也哀傷地了解到,她已經等了他一輩子,一切將永遠不會再跟以前一樣,但她不在乎,對過去毫不留戀。
郵局是間小小的石造建築,離中央廣場不遠。她打開厚重的門進入涼爽、昏暗的內部。窗口鐵欄杆後面的男人看起來就像是被關在金絲雀籠裡,他用像鸚鵡的長長指頭遞一張電報表格給她。
她沒有猶豫。她仍記得他的臉,他們在一起散步,還有在城堡花園那些漫長的午後時光;卻感覺那是很遙遠的人與事了。他是個好人,正派的男人,甚至是個勇敢的人。她送出消息,這個消息對他來說衝擊應該很大。但那也沒有辦法,她並不覺得抱歉或遺憾。在她一生中,從來沒有像這時候這麼篤定。她從磨損的木頭表面拿了零錢,走出郵局到外面的酷熱中,兩個小時後,她看見他背靠著松樹,坐在她離開他的地方,等著她。
那天晚上下雨了,事先沒有任何徵兆。或許是他們沒留意到。他們在樹枝低垂的松樹下面睡著了,頭幾乎碰到了粗糙的樹幹,樹幹上流淌著一條條結晶的樹液。一聲長而沉悶的轟隆聲,一道安靜的閃電,然後雨就來了。
他們在更深沉的黑暗中醒來,周遭盡是雨水和小樹枝斷裂的聲音。突然颳來一陣強風,又一陣。他們依偎著坐在一起,有那麼一下子,頭上成千上萬的松針讓他們分不清是否下了雨;直到枝頭開始滴水。」森林管理員的小屋,「她說,喊聲蓋過了雨聲。他記得嗎?」要一個小時,「他說。」說不定更久。我找得到,母親說。
這是她記得最清楚的事情:他們兩人身上已經水流成河,他把兩人的衣服塞進他的背包裡,希望衣服不要淋濕,然後兩人全身赤裸,只穿著鞋子就衝進暴風雨中。她肩上揹的愚蠢手提袋不斷從一角淌下水來,好像長了根水龍頭,他們在傾盆大雨和黑暗中,尋找樵夫的簡陋小屋。他幫她爬上一座小坡時,陷進了泥巴裡,雨水潑濺在他身上形成一條條的紋路,他站在那裡看起來十分強悍,像精瘦的夜行性動物,然後他甩開身上的雨水,就像狗剛從水裡爬出來。他們衝過雨中白茫茫的田野,跑下平坦的草地、滑溜的山坡,穿過水不停滴落、沙沙作響、咕噥低語的林子,在林子裡前進時,他們必須把手臂橫在臉前來保護眼睛。他們牽著彼此濕透的手,大聲喊叫蓋過紛沓的雨聲,他取笑她的方向感,說靠著上次閃電的光,他確定看見了雷得卡尼尖塔,布拉格想必就在前方,或是華沙。(待續)
結果,她當然找到了,一間簡陋小屋,猶如森林牆上的洞,深深藏在延伸入林地的狹長草地上,這片牧草地,看起來跟連日來在各處所見的其他牧草地一模一樣。黑色木板上覆滿了青苔,小玄關處有張粗陋的桌子,一張木長椅靠牆放著。一個杯子鉤在鐵絲上,在風裡上下來回擺盪。
「門鎖上了,」她聽見他喊,就上前幫忙。他用手指摸索著鉸鍊四周,推推門再摸摸看。金屬從牆上鬆脫,他用一根螺絲釘把其他螺絲從濕透的木頭上撬開,突然他們就可以進去了。他們在有黴味的黑暗中到處摸索,如同盲人在演啞劇,然後他劃了根火柴,拿開骯髒的玻璃燈罩,把冒著煙的燈芯放了進去。幾片木頭層板,兩扇窗戶,一張狹窄飄著黴味的吊床,上面擺著老鼠弄髒的床單和一條棕色的薄毯。矮胖的黑色火爐上頭有個鍋子,還有一把生鏽的銼刀,用來打開火爐的門和拿起鍋子,可能還用來攪拌鍋子裡的食物。他把沉重的木門關上擋風。
她記得這一切,留有斑斑蒼蠅屎的小屋和屋裡所有的東西:他們拿來擦乾身體的破布,她穿的男用藍襯衫的左胸上破了個洞,還有裝著釘子的那只鐵罐上所寫的名字。他們清出鐵罐裡的釘子,把罐子放在地板上接屋頂漏下來的雨水,她還記得鐵罐是深紅色的,也記得在火爐左邊有個三層木架;而在鐵床的正前方,有兩塊地板的聲音聽起來是空心的,原來地板下還藏著食物儲藏室:地裡挖了個高度及胸的凹洞,有個籃子掛在繩索上可以把東西放下去或拿上來。她也記得發現了放在外頭窗台上的鑰匙,還有在第三層木架上找到一碗胡桃,他們把胡桃跟雨中撿來的覆盆子一起吃,她仍然記得當時胡桃的滋味。他躺在她身邊看起來像睡著了,天亮時,雨水飄離玄關像極了窗簾,偶爾拉開露出雨簾後的森林,然後又再度闔上。這一切的一切都留在她的記憶裡。
他們認定沒有人會走進這片滴著水的陰暗林子裡,所以就留了下來。他們的想法沒錯。他找到一個扁平的黃銅箱子,裡頭有些工具和幾盒螺絲釘,他用工具把鉸鍊挪到比較硬的木頭上。興致一來他們就做愛,經常是突然停下手邊的事來做,幾乎任何事都得往後延個一小時或更長的時間。早晨當水影往牆上移動時,兩人雙腿交纏在一起坐著,」我能借用你的湯匙嗎?「她說,手指在碗下面撫摸他的大腿,他看著面帶笑容的她,笑得如此自信、美麗,完全屬於她的獨特笑容,他說:」請自便,「有一兩分鐘他試著不要亂動,讓她自己動手,看著她對他微笑──」先生,可以再來點奶油嗎,拜託?「──等他們再回到餐桌上時,茶早就涼了,他把茶拿到玄關,潑到長長的草叢裡,隨後全身赤裸地走出去,然後勸她一起出來,她會邊跑邊笑,跟他一起走進濕淋淋的野地,身上仍然又黏又熱,當風把世界耙過來圍繞在他們身邊時,她抱住他。沒做愛的時候,他們忙著收集可以當食物的材料,或是在玄關相互依偎地坐著,背靠在牆上兩腳蜷縮起來,一邊看著松樹枝頭滴水、擺動,看風吹過長長的青草,一邊聊天。她告訴他一些事情:關於她的村莊、父母親、她跟母親在貝徹瓦河度過的夏天,還有八歲時走失的狗。她跟他提起一年前在布爾諾遇到的男人,那人長什麼樣子,以及他們曾提過要結婚的事。
他們每天都有些小小的儀式。一天三次,他們移開地板,把籃子拉上來,裡頭裝著一點點縮水的起司和四分之一條麵包,那是她用僅剩的錢從鎮上買來的,再把籃子放下去,用木板把地洞像祕密一樣掩蓋起來。一天兩次,他們走出去,在雨中撿拾能找到的半乾木頭,從長滿刺的松木心折下小樹枝,在懸垂的枝葉下尋找松果。有一天他們偶然看見一扇門平躺在牧場的草地上,接著又一扇破碎的窗戶,明白他們找到了幾年前倒塌的舊小屋。有些沒掉在地上的木頭看起來還可以燒。他們拿起窗戶,假裝從窗口看外頭的天氣如何,然後一起扶起那扇門,門放在牧場中間看起來很奇怪,好像要紀念些什麼。他們把門拖回去,穿越濕透的林子到他們的小屋,用他在火爐邊牆上找到的斧頭把門給拆了。斧柄有點鬆脫,不過有人在頂端打了根釘子進去。他們在爐口的左邊堆了一小疊木板和木條,每天晚上他們會在火爐生火,木頭燒得霹啪作響,臨睡前,她會看著火爐門邊的細縫透出橘紅色的火光,像是黑暗中一道微弱、原始的光環。(待續)
第五天,他們坐在玄關地板上,喝著用粗麻布過濾過的甘菊茶時,她告訴他,那天早晨和她父親一起走去埋葬她弟弟的事。弟弟像蠹蛾,她說,在世界上只活了幾個小時,被放在一條麵包大小的棺材裡。她永遠不可能認識他,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在她記憶中的那天早晨是溫暖而不是悲傷的。
那是個迷人的早晨。往墓園的路上,父親牽著她的手,跟她說關於托巴斯力克小精靈的奇妙故事,小精靈知道山坡上有道門──一扇不比鐵鎚大的門,父親說,門檻上懸吊著一叢青草,這扇門可以通往另一個世界,一個在池底的世界。
父親告訴她,住在池底的人像天文學家,每天抬頭往上看,觀察上面世界的各種徵象,哀悼他們失落的東西。漁夫的紅色浮標碰到天空,小狗粉紅色的舌頭舔著地平線,孩子們包在銀色泡泡裡像青蛙蛋,當他們踢腿游到水面時,泡泡會從身上脫落漂在後頭……上面世界的一切是他們生活的目標,漫長的冬季他們會在冰冷的黑暗中,坐在水裡點燃的綠色蠟燭旁,拿他們看到的、誤解的事情,一點一滴來編織奇妙的故事。
父親說,可是托巴斯力克知道上面世界是什麼樣子,清楚它雖美麗卻腐敗,因此他為池底的人感到難過。他不了解他們就是愛這種悲傷,也不明白真相會像毒藥一樣殘害他們,所以決定告訴他們自己知道的一切。有一天,托巴斯力克深吸一口特別長的氣──父親說,托巴斯力克可以憋氣將近一個小時──打開祕密之門,走下窄長的階梯,直到腳下的泥土變鬆軟,他看見在前面遠遠的地方有個微弱的光圈,周邊鑲著植物的根,標示出池塘的入口。
他跟往常一樣找到他們。他們在輕柔的水流中如水草般地搖擺,眼角含淚地仰望水汪汪的天空。他想,他能拯救他們。於是他開始說起上面世界的真正樣子,但是他們聽了以後,臉上卻出現更哀傷的神情,一種跟他以往所見完全不同的哀傷。他們彷彿十分痛苦地彎下了腰,拚命用柔軟青綠的手摀住耳朵,當他們發覺無法堵住托巴斯力克述說真相的聲音時,他們就用手纏住他的喉嚨掐住他,直到他不能說話為止。當托巴斯力克醒過來時,父親說,他的心裡充塞了一股全新的痛苦和愛,那是他不曾有過的,他抬頭望向天空那片他不明白的水水亮光,心想如果能夠永遠看著那亮光,他將再也一無所求了。
她看著外面濕淋淋的牧草地,她說她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這麼喜愛這個故事,也不知道為何那天早晨的回憶對她來說如此重要,但她就是想要告訴他這個故事。她想要告訴他所有事情,她說,甚至連她不知道的事情也想說。
***
同一天下午,目送班姆轉身消失在往梅爾科維斯的轉彎處後,不到六個小時,我母親就站在阿達莫夫的斯克達車廠外面等。
天色越來越陰沉。車廠大門前裝置著倒鉤鐵絲網,婦女們人手一碗維他命錠,已經在門內站好位置,等著上晚班。她聽見哨音,沒多久工人就一身疲憊地魚貫湧出。她在人群中認出他來,看著他走上寬敞的大道,兩旁像飛機棚的黑色建築似乎要把中間的小巷道填滿。然後他轉彎走向安全門,他一個人走,身上穿著工廠的藍色制服及短夾克,手上提著午餐桶。
父親看見她站在對街底部崩裂的人行道上,馬上就停下了腳步。人群在他身邊推擠著。她看見有人撞到他,他的肩膀往前晃了一下,然後他就走過鋪著卵石的路,路面上停著一排帆布車篷的大卡車,正等著前往火車站的人潮通過。
他停在幾公尺外。母親看見他瞄了一眼人行道旁一小塊枯黃的草地,然後繼續上路。他微微點著頭,彷彿想起誰說過的話。直到那一刻,母親才了解父親有多愛她。
「妳還好嗎?」他終於開口。
她點點頭。「我需要跟你談談,」她說。
「不需要。」
「我知道,可是我還是想。」
他再點頭。她了解他。他不會在大庭廣眾下吵架,也不會泫然欲泣地紅著眼眶。他有他的驕傲,他不會讓她難堪。(待續)
「妳幾時回來的?」他問。
「昨天。」
「我愛妳,」他說。「這對妳來說重要嗎?」
「很重要,」她說。
他笑了,笑得很扭曲。「但,還是不夠。」
「不夠。」
父親點點頭,然後把午餐桶輕輕放在人行道上,拿下眼鏡,開始用手帕擦拭鏡片。他的眼裡看不出情緒。她把視線移開。工廠大門口有個婦人拿著裝有維他命的碗,正在檢查鞋跟。
「我們還得一起工作,」他說。
「我知道。」
「妳有辦法嗎?」
「我可以,」她說。「那你呢?」
他拿起午餐桶。「艾娃娜,這是妳想要的嗎?」
「是的,」她看著他說。「沒錯。」
「妳這麼愛他?」
「對。」
「我明白了。」父親重新戴上眼鏡,小心翼翼地把眼鏡掛到耳朵上。「我該走了,」他說。「妳會沒事吧?」
「我沒事,」母親說。
「那好吧……」他笑著,笑的方式就像是有人從他手臂拔出了一根長刺。「我一直在想,我該跟妳吻別。」
當她聽見他喊她的名字時,她已經走下人行道。他站在長椅旁,椅背上的橫條掉了兩片。她太了解這個男人了。「有件事妳該知道,」他說。
她等他說下去。
「我要妳知道我會在這裡,」他說。
「不要……,」她開口。「我不會……」
「我知道妳不會,」父親說。「但他離開時,我會在這裡。」說完後,他轉身走下人行道。
那天晚上父親走出布爾諾火車站。他穿過大街到電車站搭車回家,在已經關門的肉店轉角下車,然後往上坡走,去他父母親那間可以俯瞰中庭的公寓。清晨四點他醒過來,把整個過程倒帶了一遍:沒有燈光的街道,漆黑的車廂,乘客像瞎子一樣摸索著座位在哪裡。那天傍晚當他走出工廠,穿越崗哨和鐵絲網的大門,經過警衛和拿著維他命碗的婦人,他不由自主地往對街看去,看看她是否在那裡,接著跟其他人一起轉向火車站。
他無法停止回想,也不想停。不管是走到他們以前經常一起散步的廣場,或是經過通往城堡區那條有斜坡的小巷,他們曾在城堡花園裡一起計畫未來,他一直都在想著她。一整個秋天,眼看冬天也快過去了,他努力地要穿越過從愛的地基上冒生出來的荊棘。這些事早在他預料之中。生氣?對什麼生氣?你要如何為愛奮鬥?或是如何對抗愛?
他每隔幾個禮拜就會看到她。開會時,或在大街上。他們沒有多談。但不要緊。他看得出來那個人,不管是誰,沒跟她在一起,他知道那個人不在,而她在等他回來。
父親並不希望那人生病,除了這點之外什麼都可以。不,他希望那頭野獸還活著,好讓他殺了它。健健康康地活著,百無聊賴地過日子。坐在床邊,踩著拖鞋,晚餐時爭論新家具的價錢。他想,就讓那個人活著吧,然後跟其他人一樣,在每天生活的戰場上一點一滴老去死去。他可以等。(待續)
不管怎麼說,還是有其他事情讓他可以分心,工作就是其一。他不喜歡工廠的工作,每天把鋼粉撒到軸承裡的儀式讓人神經緊繃。年長些的工人盡忠職守,是守法的叛國賊,他們基於幾個理由而討厭他跟少數幾個同伴:因為他們是學生,是新人,只會礙手礙腳。
工廠以外的世界也好不到哪裡去。沒有什麼事情是確定的。沒有人知道事情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或者什麼時候結束。有些事情跟往前一樣,有些改變了。報上登的或透過擴音器宣布的不平等條約,每天都帶來一些新訊息。學校要在這天或那天關校;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的所有電台都由當局壟斷。所有具猶太血統的人,從今以後禁止出入劇院、電影院、餐廳……等公共場所;收聽外國頻道是犯罪行為,可判處死刑。荒謬。這不是戰爭,這是疾病。他們無所不在,車子裡、角落裡或大步走在卵石路上,彷彿是潛伏在身體裡的傳染病。
一些症狀出現得正是時候,就像泛黃的指甲或容易斷裂的頭髮一樣。他一一記錄這些症狀的進展當消遣。就拿回答命令的方式為例,就出現了林林總總的各種姿勢,不僅用以表示承認現狀(誰又能否認呢?),也表示心悅臣服,更重要的是絕對地服從:視線朝下,頭微微向前彎,臉上帶著小心翼翼的笑,把袋子或公事包像小孩一樣緊緊抱在胸前。
就某方面來說,這些畫面相當有意思。面對力量完全壓制過自己的人,大多數的人會發現自己下意識地想要取悅對方。你會看見他們想盡辦法找出恰當的表情、正確的態度,如同曠野中的動物會出自本能地在尊嚴與怯懦之間找到安身之處並待在那裡,不隨便移動。他們在身旁四周畫上中立色彩當成保護色,這像是一種遊戲。認可他人對你的討厭,但不助長這種情緒;玩弄雜種狗,卻不致過份到讓牠反咬你一口。
當然,這算是比較容易的部分。更具挑戰性的部分是,如何不讓外在的公開行為滲透進個人的私生活,如何將兩個自我給一切為二。這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夠切割得乾乾淨淨。沒有任何一個人。你活在世上的每個鐘頭,從黑暗中醒來的那一刻起,你就為了活下去而改造自己。
這變成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你角色扮演得越好,你越擁有假扮的才能,你就越有可能活下來,同時,也越有可能在途中迷失自己。
恨幫得上忙,它可以幫你釐清事情。然而恨是一把任何人都能耍弄的鐵鎚,在幫助你的同時,也能用完全一樣的方式為別人所用。(2009.01.06出版)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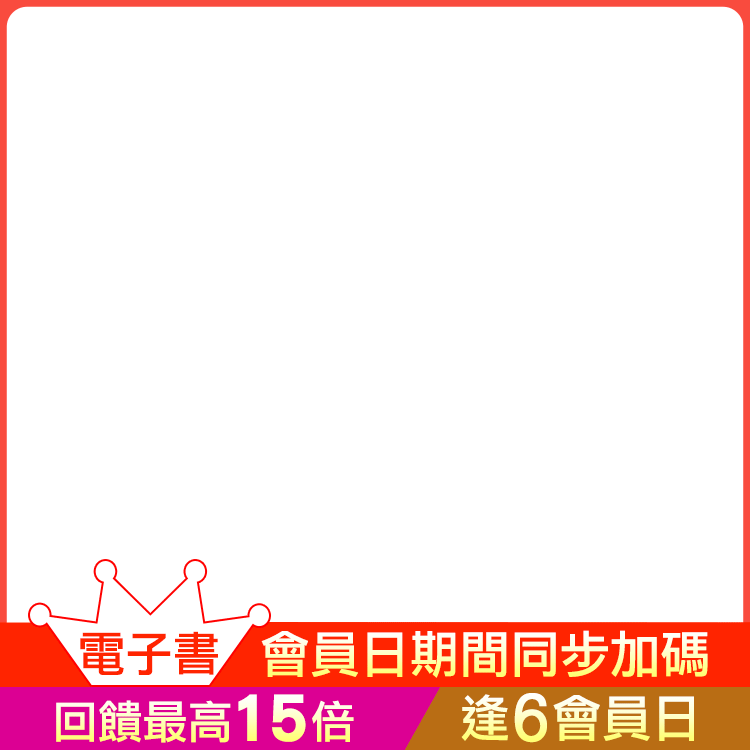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