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 她說:「因為羞恥,我才開始寫作。」
◎ 當愛成為禁忌,情感與信仰拉扯,身體便成了靈魂的角力場。
◎ 榮獲法國《不羈》(Les Inrockuptibles)文學獎最佳首作獎。
◎ 坎城影展得獎電影原著小說。
◎ 張亦絢:「這本書在小溪流淌的外貌下,字字都如驚濤駭浪——甚至,一浪還有一浪高。」
林杏鴻(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創辦人)
邱常婷(小說家)
張亦絢(作家)
楊佳嫻(詩人)
——推薦
我是法蒂瑪,我擁有聖徒的名字,
卻是在真主與禁忌愛欲間流浪的靈魂。
我叫法蒂瑪,我有伊斯蘭教中象徵性人物的名字,一個不能「玷汙」的名字。我是家裡最小的女兒,那個誰都沒有準備好迎接的孩子。
我是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人。我是虔誠的穆斯林。我是每天得花三個多小時通勤到巴黎的克里希鎮居民。我像個觀光客,從郊區觀察著巴黎人的舉手投足。
我是騙子,我是罪人。青少年時期,我是問題學生;成年後,我是個極度格格不入的邊緣人。我寫故事,是為了逃避自己的人生。我接受了四年的心理諮商——這竟是我維持過最長久的一段關係。
在我們家,愛是禁忌,溫柔也是,性更是如此。我曾以為自己追求的是多重伴侶關係。直到妮娜闖入我的生命,我才發現自己再也無法辨認:究竟我需要什麼?又缺少了什麼?⋯⋯
小說透過法蒂瑪對父母、姊姊、情人妮娜以及真主的對話,深刻探討了多重身分交織下的矛盾與掙扎。她在醫院的氣喘噴霧與清真寺的禱告聲中尋找出口,試圖在教義禁止的欲望與對家庭的忠誠之間,築起一道通往自我的橋梁。
這不僅是一部關於性傾向認同的作品,更是一場關於語言、族裔與宗教的深層辯證。作者以其獨特的「多元交織女性主義」視角,撕開了移民二代在現代法國社會中那層看不見的隱形隔閡 。
這是一份誠實到令人心痛的告解,也是一首獻給所有「格格不入者」的勇氣之歌。
「法蒂瑪・達斯的獨白由碎片構築,彷彿以羅蘭・巴特與法蘭索瓦・莫里亞克這兩位大作家,為當代的克里希鎮進行了『更新』。她如同耐心且專注的雕塑家,細細雕琢出人物肖像⋯⋯又像是一位拆彈專家,深知每個詞彙都可能引爆一切,必須以極致的謹慎來精挑細選。
「在這裡,書寫試圖創造出不可能:如何讓一切得以調和?如何在羞恥之中呼吸?如何在死胡同裡跳舞,直到在牆上開出一扇門?在這裡,書寫以低調姿態獲勝,不求喧嘩,卻對至親之人傾注了前所未有的溫柔;法蒂瑪・達斯正是憑藉其細膩敏銳的風格,鑿開了屬於她的突圍之路。」
——維吉妮・德龐特(Virginie Despentes,作家、電影導演)
各界好評
「作者以一種對立交織的筆觸與敘事,確立了獨特風格。她將句子像重拳般甩出,卻又灌注滿滿溫柔。她坦誠剖白,卻從不矯情啜泣;她一一指陳各種醜惡、不義與愛的匱乏,卻不自憐,反而以幽默加倍回應……文字在震動、在鳴響、在躍動,直擊肺腑。」
——瑪汀娜・拉瓦爾(Martine Laval),《天使名冊》(Le Matricule des anges)
「節奏強烈,句句鏗鏘;章節如吟誦般低迴,皆以同一句話開場,卻總把人帶往不同的遠方。重複、縫補,開拓新的紋理,揭開全新面向,為這幅破碎卻震撼人心的自畫像添加新的元素:一個真正屬於當下的女孩,尋找自己,也尋找——在他人、父母、伊斯蘭、郊區、法國與愛情強加的種種『真理』之中,某種平衡與真相。這正是我們期盼已久、代表當代的聲音。」
——內莉・卡普列里安(Nelly Kaprièlian),《不羈》(Les Inrockuptibles)
「寫就了一部既是女同志成長小說,也是一場與真主近身肉搏的作品。」
——讓・比恩鮑姆(Jean Birnbaum),《世界報》書評(Le Monde des livres)
「我從未想過,能在小說中感受到如此絕對且衝擊肉體的情感。」
——丹尼爾・皮庫利(Daniel Picouly),《閱讀文學雜誌》(Lire Magazine littéraire)
「藉由碎片化的結構,以及在阿拉伯語與法語之間的流動,其幽默既帶著溫柔亦不乏自嘲,《最小的女兒》擁有真正的文學素養。這段獨白連結了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與平民運動的變革,正是其最精確的表達。」
——皮耶・貝內蒂(Pierre Benetti),法國獨立調查新聞網Mediapart
「法蒂瑪・達斯首部作品展現了震撼的抒情力道,敘事者行走在『禁忌』與欲望交界的稜線上。」
——尚・J・羅斯(Sean J. Rose),《圖書週刊》(Livres Hebdo)
「《最小的女兒》是一枚碎片彈,細緻且熱切地審視了身分認同的議題。」
——克萊曼婷・戈札爾(Clémentine Goldszal),《Elle》雜誌
「這份剖白伴隨口語化、生動且大膽的書寫,堪稱瑰寶。當文學敢於活得像生活本身,懂得跨越框架並撼動我們時,是多麼幸福的事!」
——安・布欽斯基(Anne Burzynski),《Page》雜誌
「儘管身負社會、性別與宗教的種種枷鎖,這位年輕作家仍展現出渴望自由生活的驚人熱忱。⋯⋯這部以碎片獨白構成的首作,憑藉其犀利、強勁且節律鮮明的風格,從一開始便令人著迷。」
——穆麗葉・史坦梅茲(Muriel Steinmetz),《人道報》(L’Humanité)
◎ 當愛成為禁忌,情感與信仰拉扯,身體便成了靈魂的角力場。
◎ 榮獲法國《不羈》(Les Inrockuptibles)文學獎最佳首作獎。
◎ 坎城影展得獎電影原著小說。
◎ 張亦絢:「這本書在小溪流淌的外貌下,字字都如驚濤駭浪——甚至,一浪還有一浪高。」
林杏鴻(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創辦人)
邱常婷(小說家)
張亦絢(作家)
楊佳嫻(詩人)
——推薦
我是法蒂瑪,我擁有聖徒的名字,
卻是在真主與禁忌愛欲間流浪的靈魂。
我叫法蒂瑪,我有伊斯蘭教中象徵性人物的名字,一個不能「玷汙」的名字。我是家裡最小的女兒,那個誰都沒有準備好迎接的孩子。
我是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人。我是虔誠的穆斯林。我是每天得花三個多小時通勤到巴黎的克里希鎮居民。我像個觀光客,從郊區觀察著巴黎人的舉手投足。
我是騙子,我是罪人。青少年時期,我是問題學生;成年後,我是個極度格格不入的邊緣人。我寫故事,是為了逃避自己的人生。我接受了四年的心理諮商——這竟是我維持過最長久的一段關係。
在我們家,愛是禁忌,溫柔也是,性更是如此。我曾以為自己追求的是多重伴侶關係。直到妮娜闖入我的生命,我才發現自己再也無法辨認:究竟我需要什麼?又缺少了什麼?⋯⋯
小說透過法蒂瑪對父母、姊姊、情人妮娜以及真主的對話,深刻探討了多重身分交織下的矛盾與掙扎。她在醫院的氣喘噴霧與清真寺的禱告聲中尋找出口,試圖在教義禁止的欲望與對家庭的忠誠之間,築起一道通往自我的橋梁。
這不僅是一部關於性傾向認同的作品,更是一場關於語言、族裔與宗教的深層辯證。作者以其獨特的「多元交織女性主義」視角,撕開了移民二代在現代法國社會中那層看不見的隱形隔閡 。
這是一份誠實到令人心痛的告解,也是一首獻給所有「格格不入者」的勇氣之歌。
「法蒂瑪・達斯的獨白由碎片構築,彷彿以羅蘭・巴特與法蘭索瓦・莫里亞克這兩位大作家,為當代的克里希鎮進行了『更新』。她如同耐心且專注的雕塑家,細細雕琢出人物肖像⋯⋯又像是一位拆彈專家,深知每個詞彙都可能引爆一切,必須以極致的謹慎來精挑細選。
「在這裡,書寫試圖創造出不可能:如何讓一切得以調和?如何在羞恥之中呼吸?如何在死胡同裡跳舞,直到在牆上開出一扇門?在這裡,書寫以低調姿態獲勝,不求喧嘩,卻對至親之人傾注了前所未有的溫柔;法蒂瑪・達斯正是憑藉其細膩敏銳的風格,鑿開了屬於她的突圍之路。」
——維吉妮・德龐特(Virginie Despentes,作家、電影導演)
各界好評
「作者以一種對立交織的筆觸與敘事,確立了獨特風格。她將句子像重拳般甩出,卻又灌注滿滿溫柔。她坦誠剖白,卻從不矯情啜泣;她一一指陳各種醜惡、不義與愛的匱乏,卻不自憐,反而以幽默加倍回應……文字在震動、在鳴響、在躍動,直擊肺腑。」
——瑪汀娜・拉瓦爾(Martine Laval),《天使名冊》(Le Matricule des anges)
「節奏強烈,句句鏗鏘;章節如吟誦般低迴,皆以同一句話開場,卻總把人帶往不同的遠方。重複、縫補,開拓新的紋理,揭開全新面向,為這幅破碎卻震撼人心的自畫像添加新的元素:一個真正屬於當下的女孩,尋找自己,也尋找——在他人、父母、伊斯蘭、郊區、法國與愛情強加的種種『真理』之中,某種平衡與真相。這正是我們期盼已久、代表當代的聲音。」
——內莉・卡普列里安(Nelly Kaprièlian),《不羈》(Les Inrockuptibles)
「寫就了一部既是女同志成長小說,也是一場與真主近身肉搏的作品。」
——讓・比恩鮑姆(Jean Birnbaum),《世界報》書評(Le Monde des livres)
「我從未想過,能在小說中感受到如此絕對且衝擊肉體的情感。」
——丹尼爾・皮庫利(Daniel Picouly),《閱讀文學雜誌》(Lire Magazine littéraire)
「藉由碎片化的結構,以及在阿拉伯語與法語之間的流動,其幽默既帶著溫柔亦不乏自嘲,《最小的女兒》擁有真正的文學素養。這段獨白連結了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與平民運動的變革,正是其最精確的表達。」
——皮耶・貝內蒂(Pierre Benetti),法國獨立調查新聞網Mediapart
「法蒂瑪・達斯首部作品展現了震撼的抒情力道,敘事者行走在『禁忌』與欲望交界的稜線上。」
——尚・J・羅斯(Sean J. Rose),《圖書週刊》(Livres Hebdo)
「《最小的女兒》是一枚碎片彈,細緻且熱切地審視了身分認同的議題。」
——克萊曼婷・戈札爾(Clémentine Goldszal),《Elle》雜誌
「這份剖白伴隨口語化、生動且大膽的書寫,堪稱瑰寶。當文學敢於活得像生活本身,懂得跨越框架並撼動我們時,是多麼幸福的事!」
——安・布欽斯基(Anne Burzynski),《Page》雜誌
「儘管身負社會、性別與宗教的種種枷鎖,這位年輕作家仍展現出渴望自由生活的驚人熱忱。⋯⋯這部以碎片獨白構成的首作,憑藉其犀利、強勁且節律鮮明的風格,從一開始便令人著迷。」
——穆麗葉・史坦梅茲(Muriel Steinmetz),《人道報》(L’Humanité)
目錄
推薦序——八百萬種「自我介紹」 (張亦絢)
譯序——跨越郊區的小女兒 (嚴慧瑩)
最小的女兒
譯序——跨越郊區的小女兒 (嚴慧瑩)
最小的女兒
序/導讀
推薦序
八百萬種「自我介紹」
(張亦絢)
我一打開《最小的女兒》就停不下來。是因為作者能夠用字簡潔又行文流暢嗎?不完全是。這本書在小溪流淌的外貌下,字字都如驚濤駭浪——甚至,一浪還有一浪高。
我的法國同學C說過一個小故事,他的某女生朋友F的父母,得知C是F朋友後,大加讚賞,認為F總算交了個沒移民背景的朋友。移民有等級,我的同學裡就有義大利、羅馬尼亞、俄國與北非三國的後裔——北非移民承受的社會拒斥最為嚴重。F的雙親如果知道C是男同志,不知是否又要收回讚賞。歧視五花八門,有些惡待移民但友善同志,有些擁抱移民卻憎恨同志——逐漸取得優勢的法國極右派的政治綱領,則是「兩者皆斥」。我在南特的某女同志會議上,見過一對手拉手的北非拉子。會中滔滔不絕的是位直女,我當時有過這類感覺,「直女當然容易開口啦」。北非情侶提前離開,我追出去,她們說了在會議中,很難開口的感受——彼時我初涉法國社會,但對弱勢者「越『是』越『難言』」的狀況,印象深刻。
二○○五年,達斯成長的克里希(Clichy-Sous-Bois),爆發劇烈騷亂與反抗。起因是警方包圍躲進變電所中的未成年人,導致青少年誤觸高壓電死亡。「郊區」成為集各種汙名的所在。強調其危險貧困有之,揭露其為執法者種族主義受害區有之,也有視其為殖民遺緒與錯誤都市計畫的失敗綜合體。
在對達斯的訪談中,穆斯林、女同志與郊區仔常成焦點。地理的負面烙印大概較為法國本土熟知,其他國家可能會略微錯失「郊區仔」現身的重大意涵,但未必找不到自己國家可資對照、會「另眼看待」的「標章壞區」。也出自郊區的饒舌歌手,在文化節目中道,外人常對郊區青年遊晃抱以偏見,視為治安威脅。他說道:「現在我有資源了,在同樣情況下,我自然會花幾歐在咖啡廳見朋友。但當我沒資源,家中空間不夠,那時我也總和朋友成群在街邊聊天。」證言充滿啟發。——首先是「內部視角詮釋」的重要性,其次是「以記憶重寫標籤」——這兩者正是《最小的女兒》充滿力量的原因——這些意識與技巧,使得「自我介紹」這個看似最普通的日常行為,成為突觸生滅蔓延的蛛網,或說層層複寫的羊皮紙圖層——每段固定的「首字(串/段)」(我叫作法蒂瑪),不僅形構文本的周而復始感,也賦予了圍繞錨定原點放射狀的意象。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讀者,或許會看到某種「自我民族誌」的呈現,透過顯現、磋商與對話,進行的流變政治。自我介紹是語言實踐,也是社會介入。所有對「自畫像」藝術策略有興趣的讀者,應都會為本書的意味深長震動。因為它是如此如此的「第一步」,比自傳更低調,卻也更具簡約與形式的基本美感。
「逆風前行」與「頗有肩膀」,是我最強烈的印象。然而,在尤瑟娜與莫虛金1活躍的國度裡,LGBTSQQ+的自我確立,依然如斯艱難,仍教我感慨。有些困惑是青春期到成年不免的,在這階段因為「自我恐同」做傻事,假裝喜歡異性、逃避同性親密等,不少人都經歷過。某些錯誤嘗試,無可厚非。然而,當達斯描述自己假託「朋友的狀況」(當「自我介紹」都太危險),尋求宗教社群建議時,一律被「捨棄不顧」——就讓我們看到「像法蒂瑪這樣的生命體」面臨的危機有多嚴苛,所需承受的自我匿跡壓力,又有多複雜。——法蒂瑪最有歸屬感的世界,卻會抹煞其性欲人格。
《最小的女兒》衝擊我的另一刻,是法蒂瑪表示「我想成為伊瑪目!」——有何不可?據說丹麥已有女伊瑪目,南非則有酷兒伊瑪目2。——儘管實際阻力應不小。要知道,二次大戰期間,哈佛法律碩士班還不讓女性入學呢3。從靈性到宗教,從寬泛到特定,人們如何選擇不同的精神之路?不見得都有清晰答案。信徒、異端、無神論者、懷疑論者或想得到的任何定位——沒有誰可以凌駕誰,或迫害非我族類——這是法國這樣的民主共和的原則與課題。對於輕易將伊斯蘭教與反同打上等號而不檢討伊斯蘭恐懼者,我們有必要提醒,無神論(比如蘇聯時期)或非宗教的恐同紀錄,也沒多好看。——更別說當今與某些基督教教派關係匪淺的極右派。法蒂瑪對伊斯蘭教的情感真摯,就如同其同性情欲也非虛幻——難道「真誠不欺」不是所有宗教與酷兒共通的價值嗎?就算沒有類似信仰,我們也能察覺「只能二選一」對人性的挫傷。
法蒂瑪對家人有種溫情的態度,但父親暴打家人,也導致法蒂瑪斥其為「惡棍」。在逐次發出的「自我介紹卡」中,還有許多大標籤以外的諸面貌。比如哮喘病患——我曾因為切・格拉瓦患有此疾,而注意過——慢性病患,一般會比其他人更注意互賴的存在。因為一旦缺乏社會接觸,生命就可能不保。「種種小歷程」中,「問題學生」與「性別鑲嵌狀」兩項,也殊有況味。「鄉下的」、「工廠的」、「浪蕩壞媽媽」的同志,都曾是台灣同志運動著手正視內部差異的面向。這本書,則給予憶起「非行邊緣同志」(比如香妲.艾克曼4)更多契機。歷史來看,「性別二元兩極」如同「貧富差距」,都更是「政治方案」而非「天造地設」。對其適應不良,也許反而更合理。性別學者應會直指法蒂瑪「就是跨(性別)」——但法蒂瑪更在意以自己的話,寫出「不識性別二元專制真面目」的自由態——這種細緻化,可說是女性主義與文學相得益彰的「語言手工藝絕活」。
我稱《最小的女兒》為「八百萬種自我介紹」。這個稱號確實脫自也演繹性別主題的小說家卜洛克:《八百萬種死法》——但願《最小的女兒》在讀者手中,能如「八百萬種死而復生」。
--
1瑪格麗特.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亞莉安.莫虛金(Ariane Mnouchkine, 1939-)被視為巨擘的LGBT+的作家與劇場導演。
2穆辛.亨德里克斯(Muhsin Hendricks, 1967-2025),在主持女同志婚禮時,遭兩名槍手射殺身亡。
3參考保利.莫瑞(Pauli Murray, 1910-1985)生平。莫瑞為美國律師、民權與女權運動者。為歷史研究者追加「跨性別者」,因為在莫瑞當代,這類名稱應用尚不廣泛。。
4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 1950-2015)在成為國際知名的導演前,曾為竊賊。
譯序
跨越郊區的小女兒
(嚴慧瑩)
所謂的「郊區」
很多年前剛到巴黎要租房子,學姊善意提醒:「無論如何都不要住到郊區啊!」她還加了一句:「『它』是個形容詞。」
語言有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就是弦外之音,學姊短短一個詞彙可能代表背後龐大的意思。在法文裡,「郊區」這個字是具體的例子。說到郊區,相對的是城市中心,但它指的絕不僅是地理方位,而代表了歷史、社會、人文、都市規畫、治安等等多層含義。
以巴黎而言,分為市區的「小巴黎」,以及包含整個外圍郊區的「大巴黎」,前者居民約兩百萬,後者一千兩百萬,比台灣人口的總數一半還多,也是歐洲國家人口密度數一數二高的地區。
巴黎市面積出奇的小,只有一百零五平方公里,然而呈圓形往外延伸的郊區幾近一萬兩千平方公里。 圍著市中心有一圈環城快速道路,因此,市區與郊區涇渭分明,隔著一條三十五公尺寬的八線道快速道路。
在巴黎城鄉發展史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戰後重建、發展工業都需要大量人工,法國積極引進外來移工,其中以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以及保護地突尼西亞、摩洛哥人最多。這些北非阿拉伯人來到巴黎,住不起市中心,最先是在外圍郊區蓋了一些貧民窟居住,到了一九五○、六○年代,政府緊急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安置這些移工。一九七四年開放依親政策,更大舉增加了住在巴黎郊區的北非阿拉伯移民人口(僅有極少數的郊區維持原來獨棟房屋,不再此列 )。
社會住宅雖解了燃眉之急,但很快衍生出問題,倉促建成建材粗糙,管理不當,加上大量的外國人聚居,貧窮、宗教傾向、教育程度、文化活動貧瘠、交通受阻、毒品、暴力、犯罪率,使郊區變得惡名昭彰。一九八○年代頻頻出現的「郊區危機」讓這些問題浮上檯面,二○○五年在克里希鎮爆發的警民衝突暴動更是法國現代史上最嚴重的人民暴動(二○二三年在北郊南泰爾的警民衝突又引爆一次激烈的暴動,蔓延全國,震驚國際)。
這一段對巴黎郊區的描述,是因為這是本書的重要背景,對郊區的既定印象,成了一個符碼。短短一句:「我叫作法蒂瑪。我是阿爾及利亞人。」「我是克里希鎮居民,跨過環城大道到另一邊的巴黎求學。」「我是克里希鎮民,每天花在通勤的時間超過三個鐘頭。」「我是克里希鎮民,要轉三次車去大學上課。」立刻勾勒出主人翁的成長背景與環境。帶著這個「原罪」,書中描述就讀國高中時在學校裡的混亂、通勤交通途中的觀察、在大學裡受到歧視這些片段,都妥妥地鑲嵌在這個背景裡。
郊區居民相對於巴黎人(「我是那個觀察巴黎人行為舉止的郊區女孩」),「穿著像男生的女兒」相對於父母親沒等到的兒子(「我是個錯誤,一個意外」),同志性取向相對於不容許同性戀的伊斯蘭(「我是個罪人」),法國相對於祖國阿爾及利亞(「我感覺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阿爾及利亞,但是每一次探完親,我都告訴自己不會再回去了」),法蒂瑪永遠是在邊緣,永遠是渴望被認可的「最小的女兒」。(又何嘗不是「法國的小女兒」?)
「郊區文學」
郊區既然具有這樣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很自然孕育了藝術的呈現。
八○年代開始,誕生了所謂的「法籍北非裔文學」(littérature beur),由梅迪‧夏夫(Mehdi Charef)打響第一炮,鼓舞了更多生活在法國的北非移民二代書寫。
在此以前,記者、社會學家、紀錄工作者都是以外人視角來呈現郊區樣貌、討論郊區問題。這是第一次位居城市邊緣的移民二代,以「在地人」的視野見證自己「異鄉人」的情境。
九○年代後期,「法籍北非裔文學」發展為「郊區文學」(littérature des banlieues),加入了相同地域性的各裔移民二代作者,但其中還是以北非裔為主。
貧窮、居住環境狹隘髒亂、交通不便引起的封閉隔離、失業、毒品、暴力,郊區年輕人欠缺娛樂活動,沒有疏通管道,看不見未來,內心的無奈轉換成叛逆與不滿,與體制、公權力產生尖銳對立。壓力與叛逆也引爆了藝術呈現,文學、音樂、歌曲、舞蹈、穿著、繪畫都成了抒發宣洩的管道,蔚為流行(嘻哈、電音舞、饒舌、詩歌吟唱、街頭塗鴉等等),興起了相對於「布爾喬亞文化」的「郊區文化」,多元、顛覆傳統、直白、融合原生國文化的魅力,造成可觀的傳播力,進入主流文化。
郊區文學的作者們大多年紀輕,以真切簡單的語句描繪周遭生活環境,參雜郊區年輕人的用語,大多是第一人稱自傳式的敘述,短促的句子,接地氣的對話,單刀直入不多修飾的詞彙,形成一個特別的音樂性節奏。
這種社會寫實的筆調,吸引了愈來愈多的讀者與評論,引起主流文化的注意,二○○○年之後甚至出現「郊區文學出版潮」。由邊緣社會現象書寫進入了文學殿堂,由「法語系文學」(littérarure francophone)融入了「法國文學」(littérature française)。其中許多作家如阿祖‧貝加(Azouz Begag)、法依莎‧桂尼(Faïza Guène)都成了暢銷明星。而這股出版潮一直持續至今,隨著社群、媒體,更增加推廣度。
時隔數十年,郊區文學依然活躍,並且一路改變。從最開始對居住環境、暴力、對未來徬徨的描寫,漸漸擴展到更寬廣更深層的議題。去殖民化、女權、身分認同、宗教、性取向,郊區這塊複雜多元的沃土正好培植了舉世最受討論的文化議題。郊區文學作者由「我為我的族群說話」到「我們為我們這一代說話」,再到「我為我自己說話」。從邊緣出發,進入中心,從反叛吶喊到審視省思,由呈現問題到尋求答案,由移民的失根到在客國扎根。無怪今日人們已將「郊區文學」納入「都市文學」(littérature urbaine)。
《最小的女兒》從邊緣郊區出發,主角法蒂瑪游移在形而上、形而下的邊緣與中心的辯證,無畏地向讀者坦露她掙扎的最深處。她的掙扎化作語言,以直白而強勁的力道,向各種偏見、歧視、禁忌、爭議迎去,由邊緣扣向中心、反省中心,即使在小說中她對這個「靠近」的歷程注入了反思。
一本書是一個世界,不論郊區或是都市,作者永遠是中心,不是邊緣。
八百萬種「自我介紹」
(張亦絢)
我一打開《最小的女兒》就停不下來。是因為作者能夠用字簡潔又行文流暢嗎?不完全是。這本書在小溪流淌的外貌下,字字都如驚濤駭浪——甚至,一浪還有一浪高。
我的法國同學C說過一個小故事,他的某女生朋友F的父母,得知C是F朋友後,大加讚賞,認為F總算交了個沒移民背景的朋友。移民有等級,我的同學裡就有義大利、羅馬尼亞、俄國與北非三國的後裔——北非移民承受的社會拒斥最為嚴重。F的雙親如果知道C是男同志,不知是否又要收回讚賞。歧視五花八門,有些惡待移民但友善同志,有些擁抱移民卻憎恨同志——逐漸取得優勢的法國極右派的政治綱領,則是「兩者皆斥」。我在南特的某女同志會議上,見過一對手拉手的北非拉子。會中滔滔不絕的是位直女,我當時有過這類感覺,「直女當然容易開口啦」。北非情侶提前離開,我追出去,她們說了在會議中,很難開口的感受——彼時我初涉法國社會,但對弱勢者「越『是』越『難言』」的狀況,印象深刻。
二○○五年,達斯成長的克里希(Clichy-Sous-Bois),爆發劇烈騷亂與反抗。起因是警方包圍躲進變電所中的未成年人,導致青少年誤觸高壓電死亡。「郊區」成為集各種汙名的所在。強調其危險貧困有之,揭露其為執法者種族主義受害區有之,也有視其為殖民遺緒與錯誤都市計畫的失敗綜合體。
在對達斯的訪談中,穆斯林、女同志與郊區仔常成焦點。地理的負面烙印大概較為法國本土熟知,其他國家可能會略微錯失「郊區仔」現身的重大意涵,但未必找不到自己國家可資對照、會「另眼看待」的「標章壞區」。也出自郊區的饒舌歌手,在文化節目中道,外人常對郊區青年遊晃抱以偏見,視為治安威脅。他說道:「現在我有資源了,在同樣情況下,我自然會花幾歐在咖啡廳見朋友。但當我沒資源,家中空間不夠,那時我也總和朋友成群在街邊聊天。」證言充滿啟發。——首先是「內部視角詮釋」的重要性,其次是「以記憶重寫標籤」——這兩者正是《最小的女兒》充滿力量的原因——這些意識與技巧,使得「自我介紹」這個看似最普通的日常行為,成為突觸生滅蔓延的蛛網,或說層層複寫的羊皮紙圖層——每段固定的「首字(串/段)」(我叫作法蒂瑪),不僅形構文本的周而復始感,也賦予了圍繞錨定原點放射狀的意象。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讀者,或許會看到某種「自我民族誌」的呈現,透過顯現、磋商與對話,進行的流變政治。自我介紹是語言實踐,也是社會介入。所有對「自畫像」藝術策略有興趣的讀者,應都會為本書的意味深長震動。因為它是如此如此的「第一步」,比自傳更低調,卻也更具簡約與形式的基本美感。
「逆風前行」與「頗有肩膀」,是我最強烈的印象。然而,在尤瑟娜與莫虛金1活躍的國度裡,LGBTSQQ+的自我確立,依然如斯艱難,仍教我感慨。有些困惑是青春期到成年不免的,在這階段因為「自我恐同」做傻事,假裝喜歡異性、逃避同性親密等,不少人都經歷過。某些錯誤嘗試,無可厚非。然而,當達斯描述自己假託「朋友的狀況」(當「自我介紹」都太危險),尋求宗教社群建議時,一律被「捨棄不顧」——就讓我們看到「像法蒂瑪這樣的生命體」面臨的危機有多嚴苛,所需承受的自我匿跡壓力,又有多複雜。——法蒂瑪最有歸屬感的世界,卻會抹煞其性欲人格。
《最小的女兒》衝擊我的另一刻,是法蒂瑪表示「我想成為伊瑪目!」——有何不可?據說丹麥已有女伊瑪目,南非則有酷兒伊瑪目2。——儘管實際阻力應不小。要知道,二次大戰期間,哈佛法律碩士班還不讓女性入學呢3。從靈性到宗教,從寬泛到特定,人們如何選擇不同的精神之路?不見得都有清晰答案。信徒、異端、無神論者、懷疑論者或想得到的任何定位——沒有誰可以凌駕誰,或迫害非我族類——這是法國這樣的民主共和的原則與課題。對於輕易將伊斯蘭教與反同打上等號而不檢討伊斯蘭恐懼者,我們有必要提醒,無神論(比如蘇聯時期)或非宗教的恐同紀錄,也沒多好看。——更別說當今與某些基督教教派關係匪淺的極右派。法蒂瑪對伊斯蘭教的情感真摯,就如同其同性情欲也非虛幻——難道「真誠不欺」不是所有宗教與酷兒共通的價值嗎?就算沒有類似信仰,我們也能察覺「只能二選一」對人性的挫傷。
法蒂瑪對家人有種溫情的態度,但父親暴打家人,也導致法蒂瑪斥其為「惡棍」。在逐次發出的「自我介紹卡」中,還有許多大標籤以外的諸面貌。比如哮喘病患——我曾因為切・格拉瓦患有此疾,而注意過——慢性病患,一般會比其他人更注意互賴的存在。因為一旦缺乏社會接觸,生命就可能不保。「種種小歷程」中,「問題學生」與「性別鑲嵌狀」兩項,也殊有況味。「鄉下的」、「工廠的」、「浪蕩壞媽媽」的同志,都曾是台灣同志運動著手正視內部差異的面向。這本書,則給予憶起「非行邊緣同志」(比如香妲.艾克曼4)更多契機。歷史來看,「性別二元兩極」如同「貧富差距」,都更是「政治方案」而非「天造地設」。對其適應不良,也許反而更合理。性別學者應會直指法蒂瑪「就是跨(性別)」——但法蒂瑪更在意以自己的話,寫出「不識性別二元專制真面目」的自由態——這種細緻化,可說是女性主義與文學相得益彰的「語言手工藝絕活」。
我稱《最小的女兒》為「八百萬種自我介紹」。這個稱號確實脫自也演繹性別主題的小說家卜洛克:《八百萬種死法》——但願《最小的女兒》在讀者手中,能如「八百萬種死而復生」。
--
1瑪格麗特.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亞莉安.莫虛金(Ariane Mnouchkine, 1939-)被視為巨擘的LGBT+的作家與劇場導演。
2穆辛.亨德里克斯(Muhsin Hendricks, 1967-2025),在主持女同志婚禮時,遭兩名槍手射殺身亡。
3參考保利.莫瑞(Pauli Murray, 1910-1985)生平。莫瑞為美國律師、民權與女權運動者。為歷史研究者追加「跨性別者」,因為在莫瑞當代,這類名稱應用尚不廣泛。。
4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 1950-2015)在成為國際知名的導演前,曾為竊賊。
譯序
跨越郊區的小女兒
(嚴慧瑩)
所謂的「郊區」
很多年前剛到巴黎要租房子,學姊善意提醒:「無論如何都不要住到郊區啊!」她還加了一句:「『它』是個形容詞。」
語言有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就是弦外之音,學姊短短一個詞彙可能代表背後龐大的意思。在法文裡,「郊區」這個字是具體的例子。說到郊區,相對的是城市中心,但它指的絕不僅是地理方位,而代表了歷史、社會、人文、都市規畫、治安等等多層含義。
以巴黎而言,分為市區的「小巴黎」,以及包含整個外圍郊區的「大巴黎」,前者居民約兩百萬,後者一千兩百萬,比台灣人口的總數一半還多,也是歐洲國家人口密度數一數二高的地區。
巴黎市面積出奇的小,只有一百零五平方公里,然而呈圓形往外延伸的郊區幾近一萬兩千平方公里。 圍著市中心有一圈環城快速道路,因此,市區與郊區涇渭分明,隔著一條三十五公尺寬的八線道快速道路。
在巴黎城鄉發展史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戰後重建、發展工業都需要大量人工,法國積極引進外來移工,其中以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以及保護地突尼西亞、摩洛哥人最多。這些北非阿拉伯人來到巴黎,住不起市中心,最先是在外圍郊區蓋了一些貧民窟居住,到了一九五○、六○年代,政府緊急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安置這些移工。一九七四年開放依親政策,更大舉增加了住在巴黎郊區的北非阿拉伯移民人口(僅有極少數的郊區維持原來獨棟房屋,不再此列 )。
社會住宅雖解了燃眉之急,但很快衍生出問題,倉促建成建材粗糙,管理不當,加上大量的外國人聚居,貧窮、宗教傾向、教育程度、文化活動貧瘠、交通受阻、毒品、暴力、犯罪率,使郊區變得惡名昭彰。一九八○年代頻頻出現的「郊區危機」讓這些問題浮上檯面,二○○五年在克里希鎮爆發的警民衝突暴動更是法國現代史上最嚴重的人民暴動(二○二三年在北郊南泰爾的警民衝突又引爆一次激烈的暴動,蔓延全國,震驚國際)。
這一段對巴黎郊區的描述,是因為這是本書的重要背景,對郊區的既定印象,成了一個符碼。短短一句:「我叫作法蒂瑪。我是阿爾及利亞人。」「我是克里希鎮居民,跨過環城大道到另一邊的巴黎求學。」「我是克里希鎮民,每天花在通勤的時間超過三個鐘頭。」「我是克里希鎮民,要轉三次車去大學上課。」立刻勾勒出主人翁的成長背景與環境。帶著這個「原罪」,書中描述就讀國高中時在學校裡的混亂、通勤交通途中的觀察、在大學裡受到歧視這些片段,都妥妥地鑲嵌在這個背景裡。
郊區居民相對於巴黎人(「我是那個觀察巴黎人行為舉止的郊區女孩」),「穿著像男生的女兒」相對於父母親沒等到的兒子(「我是個錯誤,一個意外」),同志性取向相對於不容許同性戀的伊斯蘭(「我是個罪人」),法國相對於祖國阿爾及利亞(「我感覺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阿爾及利亞,但是每一次探完親,我都告訴自己不會再回去了」),法蒂瑪永遠是在邊緣,永遠是渴望被認可的「最小的女兒」。(又何嘗不是「法國的小女兒」?)
「郊區文學」
郊區既然具有這樣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很自然孕育了藝術的呈現。
八○年代開始,誕生了所謂的「法籍北非裔文學」(littérature beur),由梅迪‧夏夫(Mehdi Charef)打響第一炮,鼓舞了更多生活在法國的北非移民二代書寫。
在此以前,記者、社會學家、紀錄工作者都是以外人視角來呈現郊區樣貌、討論郊區問題。這是第一次位居城市邊緣的移民二代,以「在地人」的視野見證自己「異鄉人」的情境。
九○年代後期,「法籍北非裔文學」發展為「郊區文學」(littérature des banlieues),加入了相同地域性的各裔移民二代作者,但其中還是以北非裔為主。
貧窮、居住環境狹隘髒亂、交通不便引起的封閉隔離、失業、毒品、暴力,郊區年輕人欠缺娛樂活動,沒有疏通管道,看不見未來,內心的無奈轉換成叛逆與不滿,與體制、公權力產生尖銳對立。壓力與叛逆也引爆了藝術呈現,文學、音樂、歌曲、舞蹈、穿著、繪畫都成了抒發宣洩的管道,蔚為流行(嘻哈、電音舞、饒舌、詩歌吟唱、街頭塗鴉等等),興起了相對於「布爾喬亞文化」的「郊區文化」,多元、顛覆傳統、直白、融合原生國文化的魅力,造成可觀的傳播力,進入主流文化。
郊區文學的作者們大多年紀輕,以真切簡單的語句描繪周遭生活環境,參雜郊區年輕人的用語,大多是第一人稱自傳式的敘述,短促的句子,接地氣的對話,單刀直入不多修飾的詞彙,形成一個特別的音樂性節奏。
這種社會寫實的筆調,吸引了愈來愈多的讀者與評論,引起主流文化的注意,二○○○年之後甚至出現「郊區文學出版潮」。由邊緣社會現象書寫進入了文學殿堂,由「法語系文學」(littérarure francophone)融入了「法國文學」(littérature française)。其中許多作家如阿祖‧貝加(Azouz Begag)、法依莎‧桂尼(Faïza Guène)都成了暢銷明星。而這股出版潮一直持續至今,隨著社群、媒體,更增加推廣度。
時隔數十年,郊區文學依然活躍,並且一路改變。從最開始對居住環境、暴力、對未來徬徨的描寫,漸漸擴展到更寬廣更深層的議題。去殖民化、女權、身分認同、宗教、性取向,郊區這塊複雜多元的沃土正好培植了舉世最受討論的文化議題。郊區文學作者由「我為我的族群說話」到「我們為我們這一代說話」,再到「我為我自己說話」。從邊緣出發,進入中心,從反叛吶喊到審視省思,由呈現問題到尋求答案,由移民的失根到在客國扎根。無怪今日人們已將「郊區文學」納入「都市文學」(littérature urbaine)。
《最小的女兒》從邊緣郊區出發,主角法蒂瑪游移在形而上、形而下的邊緣與中心的辯證,無畏地向讀者坦露她掙扎的最深處。她的掙扎化作語言,以直白而強勁的力道,向各種偏見、歧視、禁忌、爭議迎去,由邊緣扣向中心、反省中心,即使在小說中她對這個「靠近」的歷程注入了反思。
一本書是一個世界,不論郊區或是都市,作者永遠是中心,不是邊緣。
試閱
我叫作法蒂瑪。
我有一個伊斯蘭教象徵性人物的名字。
我有一個大家都必須尊敬的名字。
就像我們那兒說的,一個不能「玷汙」的名字。
我們那兒,玷汙,就是汙辱,阿爾及利亞阿拉伯字是wassekh。
我們那兒的地方方言說作darja或darija。
wassekh:玷汙,塗上屎,染黑。
就像法文中的「靠近」,是個多重意思的字。
我母親用這個字跟我說我弄髒了衣服,當她回家發現她的王國亂七八糟時,也是用這個字。
她的王國:廚房。
沒有人能動手或涉足的地方。
我母親痛恨東西不在它該在的地方。
廚房裡有規範,就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樣,必須知道、尊重、遵守它。
如果我們做不到,就應該離王國遠一點。
我母親經常說的句子裡面,有這句:Makènch li ghawèn, fi hadi dar, izzèdolèk.
這在我耳朵裡敲擊像個爆點。
「在這家裡不但沒有人會幫妳,反而還拖累妳。」
我腳趾頭在高統襪裡亂動,每每這樣頂她嘴:
「需要幫忙妳得說啊,我又不是通靈者,猜不到。」
我母親一律立即回嗆說她不需要「我們的」幫忙。她特別說「我們的」,是把責備變成集體,免得我以為是針對我個人,避免我覺得受到抨擊。
我母親十四歲就開始做飯。
最初料理的是她所謂的sahline:簡單的。
庫斯庫斯小米飯、tchouktchouka、djouwèz、李子乾羊肉塔吉鍋、橄欖雞肉塔吉鍋。
十四歲,我連床都不會整理。
二十歲,我連襯衫都不會燙。
二十八歲,我連義大利麵拌奶油都不會煮。
除了吃飯,我不喜歡出現在廚房裡。
我喜歡吃,但不是什麼都喜歡。
母親煮全家人的飯。
她會隨著我們的任性研究出菜單。
我不肯吃肉,我就會有魚吃;我父親無肉不歡,他盤裡絕不缺肉。
當我大姊度妮雅不想吃傳統餐點,想吃薯條,她就會有薯條。
從我有記憶以來,就看到母親在廚房裡,雙手被凍壞,臉頰凹陷,正用番茄醬在我的義大利麵上畫小人兒、裝飾甜點、泡茶、把平底鍋收進烤箱裡。
我眼前只留下一個畫面:我們腳伸在桌下,頭伸在盤子上。
母親在爐前,最後一個上桌。
那是卡瑪.達斯的王國,不是我的地方。
我叫作法蒂瑪.達斯。
我是克里希鎮人,跨過環城大道到另一邊的巴黎求學。
在杭西-維勒蒙博車站搭八點三十三分的火車之前,我抓一份《即時新聞》免費報紙。我手指沾沾口水方便翻閱報紙。第三十一頁,大標題:放鬆自己。
氣象報告下方,我找到我的星座預測。
在月台上,我讀著我今日和本週星座運勢。
你若要忍受生命,就得準備好接受死亡(佛洛伊德)。
您的星座運勢:不要難過自己無法幫助所有向您求助的人,先想到您自己!在著手一項重大計畫之前請先三思,不要太樂觀太逞強。
工作:必須大膽地下決定。您的腳踏實地將是您今日最佳強項。
愛情:您若已有伴侶,注意不要因無理的要求讓對方灰心。您若還單身一人,可以夢想白馬王子,但不要誤以為會在街角遇到他。
接著我瀏覽世界上的不幸消息,試著按捺下觀察車內乘客的欲望。
沒有例外,每一天乘客都拒絕往前移動到走道中央。每天早上,我重複著這句不具神奇效果的句子:「麻煩可以請往裡面走嗎?很多人跟您一樣想去上班。」
到了晚上,我改變口氣。
我特意減去句子裡的禮貌用詞。
那些不願往裡走的乘客,是那些再過兩站要下車的人:邦迪鎮或諾西勒塞克鎮。
他們的竅門:緊靠車門,以免來不及下車。
在公車裡,我會注意讓帶孩子的婦女、懷孕婦女、年長婦女能有座位。
我的注意力只放在女性身上。
我要求自己扮演伸張正義的角色,捍衛其他人,為其他人喉舌,為其發言,讓她們安心,拯救她們。
我誰都沒救成,沒救成妮娜,也沒救成我母親。
甚至連我自己也沒救成。
妮娜說得很有道理。
想拯救世界是變態的想法。
我叫作法蒂瑪.達斯,但我出生在法國,七十八省,聖傑曼昂雷鎮。
我在傑哈男爵夫人街上的聖傑曼診所剖腹出生。
剖腹生產,拉丁文字源是caedere:「切開」、「割開」。
切開子宮。
生完我之後,我三十歲的母親發生心肌梗塞。
我怨恨自己出生。
拂曉時分我從母親肚子裡被拉出來。
出生時我並沒有哮喘。
是後來才發病的。
兩歲時,我被正式歸入過敏性哮喘的分類。
青少年時期,我第一次聽到以「嚴重」這個字眼判定我的病情。
十七歲時,我明瞭到我身上帶著一個看不見的疾病。
我在醫院裡待得最長的一次持續了六個星期。
我姊姊度妮雅說我像一塊海綿。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我呼吸道發作也可能是情緒引發。
我必須按時用藥,一輩子。
使肺泰(Seretide):一天兩次,早上噴一次,晚上噴一次。
類固醇片(Inorial):早上一錠。
欣流膜衣錠(Singulair):晚上一錠。
泛得林(Ventoline):呼吸阻礙時噴。
我叫作法蒂瑪。
法蒂瑪是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Salla Allah alayhi wa salam,恭祝其平安——和第一任妻子哈蒂嘉(Khadidja)所生的最小的女兒。
我叫作法蒂瑪。
唯有神知道我是否對得起這個名字。
我是否玷汙了它。
法蒂瑪的含義是「斷奶的小雌駱駝」。
斷奶的阿拉伯文:fatm。
停止給嬰兒或幼年動物餵奶,讓其開始新的一種進食方式。另一個定義是戒斷,感覺沮喪,讓某人戒離某物,或讓某物分離某人,或讓某人斷離某人。
跟伊斯蘭教裡的法蒂瑪一樣,我本來應該有三個姊姊。
我的一個姊姊出生幾個鐘頭後就早夭了。
她叫作順雅。
法蒂瑪被她父親指認為是天堂裡最尊貴的女人。
先知穆罕默德——祈祝他擁有真主所降臨的平安與恩典——有一天說:「法蒂瑪是我的一部分,冒犯她就是冒犯我。」
我父親不會跟我說這樣的話。
我父親不太和我說話。
我有一個伊斯蘭教象徵性人物的名字。
我有一個大家都必須尊敬的名字。
就像我們那兒說的,一個不能「玷汙」的名字。
我們那兒,玷汙,就是汙辱,阿爾及利亞阿拉伯字是wassekh。
我們那兒的地方方言說作darja或darija。
wassekh:玷汙,塗上屎,染黑。
就像法文中的「靠近」,是個多重意思的字。
我母親用這個字跟我說我弄髒了衣服,當她回家發現她的王國亂七八糟時,也是用這個字。
她的王國:廚房。
沒有人能動手或涉足的地方。
我母親痛恨東西不在它該在的地方。
廚房裡有規範,就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樣,必須知道、尊重、遵守它。
如果我們做不到,就應該離王國遠一點。
我母親經常說的句子裡面,有這句:Makènch li ghawèn, fi hadi dar, izzèdolèk.
這在我耳朵裡敲擊像個爆點。
「在這家裡不但沒有人會幫妳,反而還拖累妳。」
我腳趾頭在高統襪裡亂動,每每這樣頂她嘴:
「需要幫忙妳得說啊,我又不是通靈者,猜不到。」
我母親一律立即回嗆說她不需要「我們的」幫忙。她特別說「我們的」,是把責備變成集體,免得我以為是針對我個人,避免我覺得受到抨擊。
我母親十四歲就開始做飯。
最初料理的是她所謂的sahline:簡單的。
庫斯庫斯小米飯、tchouktchouka、djouwèz、李子乾羊肉塔吉鍋、橄欖雞肉塔吉鍋。
十四歲,我連床都不會整理。
二十歲,我連襯衫都不會燙。
二十八歲,我連義大利麵拌奶油都不會煮。
除了吃飯,我不喜歡出現在廚房裡。
我喜歡吃,但不是什麼都喜歡。
母親煮全家人的飯。
她會隨著我們的任性研究出菜單。
我不肯吃肉,我就會有魚吃;我父親無肉不歡,他盤裡絕不缺肉。
當我大姊度妮雅不想吃傳統餐點,想吃薯條,她就會有薯條。
從我有記憶以來,就看到母親在廚房裡,雙手被凍壞,臉頰凹陷,正用番茄醬在我的義大利麵上畫小人兒、裝飾甜點、泡茶、把平底鍋收進烤箱裡。
我眼前只留下一個畫面:我們腳伸在桌下,頭伸在盤子上。
母親在爐前,最後一個上桌。
那是卡瑪.達斯的王國,不是我的地方。
我叫作法蒂瑪.達斯。
我是克里希鎮人,跨過環城大道到另一邊的巴黎求學。
在杭西-維勒蒙博車站搭八點三十三分的火車之前,我抓一份《即時新聞》免費報紙。我手指沾沾口水方便翻閱報紙。第三十一頁,大標題:放鬆自己。
氣象報告下方,我找到我的星座預測。
在月台上,我讀著我今日和本週星座運勢。
你若要忍受生命,就得準備好接受死亡(佛洛伊德)。
您的星座運勢:不要難過自己無法幫助所有向您求助的人,先想到您自己!在著手一項重大計畫之前請先三思,不要太樂觀太逞強。
工作:必須大膽地下決定。您的腳踏實地將是您今日最佳強項。
愛情:您若已有伴侶,注意不要因無理的要求讓對方灰心。您若還單身一人,可以夢想白馬王子,但不要誤以為會在街角遇到他。
接著我瀏覽世界上的不幸消息,試著按捺下觀察車內乘客的欲望。
沒有例外,每一天乘客都拒絕往前移動到走道中央。每天早上,我重複著這句不具神奇效果的句子:「麻煩可以請往裡面走嗎?很多人跟您一樣想去上班。」
到了晚上,我改變口氣。
我特意減去句子裡的禮貌用詞。
那些不願往裡走的乘客,是那些再過兩站要下車的人:邦迪鎮或諾西勒塞克鎮。
他們的竅門:緊靠車門,以免來不及下車。
在公車裡,我會注意讓帶孩子的婦女、懷孕婦女、年長婦女能有座位。
我的注意力只放在女性身上。
我要求自己扮演伸張正義的角色,捍衛其他人,為其他人喉舌,為其發言,讓她們安心,拯救她們。
我誰都沒救成,沒救成妮娜,也沒救成我母親。
甚至連我自己也沒救成。
妮娜說得很有道理。
想拯救世界是變態的想法。
我叫作法蒂瑪.達斯,但我出生在法國,七十八省,聖傑曼昂雷鎮。
我在傑哈男爵夫人街上的聖傑曼診所剖腹出生。
剖腹生產,拉丁文字源是caedere:「切開」、「割開」。
切開子宮。
生完我之後,我三十歲的母親發生心肌梗塞。
我怨恨自己出生。
拂曉時分我從母親肚子裡被拉出來。
出生時我並沒有哮喘。
是後來才發病的。
兩歲時,我被正式歸入過敏性哮喘的分類。
青少年時期,我第一次聽到以「嚴重」這個字眼判定我的病情。
十七歲時,我明瞭到我身上帶著一個看不見的疾病。
我在醫院裡待得最長的一次持續了六個星期。
我姊姊度妮雅說我像一塊海綿。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我呼吸道發作也可能是情緒引發。
我必須按時用藥,一輩子。
使肺泰(Seretide):一天兩次,早上噴一次,晚上噴一次。
類固醇片(Inorial):早上一錠。
欣流膜衣錠(Singulair):晚上一錠。
泛得林(Ventoline):呼吸阻礙時噴。
我叫作法蒂瑪。
法蒂瑪是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Salla Allah alayhi wa salam,恭祝其平安——和第一任妻子哈蒂嘉(Khadidja)所生的最小的女兒。
我叫作法蒂瑪。
唯有神知道我是否對得起這個名字。
我是否玷汙了它。
法蒂瑪的含義是「斷奶的小雌駱駝」。
斷奶的阿拉伯文:fatm。
停止給嬰兒或幼年動物餵奶,讓其開始新的一種進食方式。另一個定義是戒斷,感覺沮喪,讓某人戒離某物,或讓某物分離某人,或讓某人斷離某人。
跟伊斯蘭教裡的法蒂瑪一樣,我本來應該有三個姊姊。
我的一個姊姊出生幾個鐘頭後就早夭了。
她叫作順雅。
法蒂瑪被她父親指認為是天堂裡最尊貴的女人。
先知穆罕默德——祈祝他擁有真主所降臨的平安與恩典——有一天說:「法蒂瑪是我的一部分,冒犯她就是冒犯我。」
我父親不會跟我說這樣的話。
我父親不太和我說話。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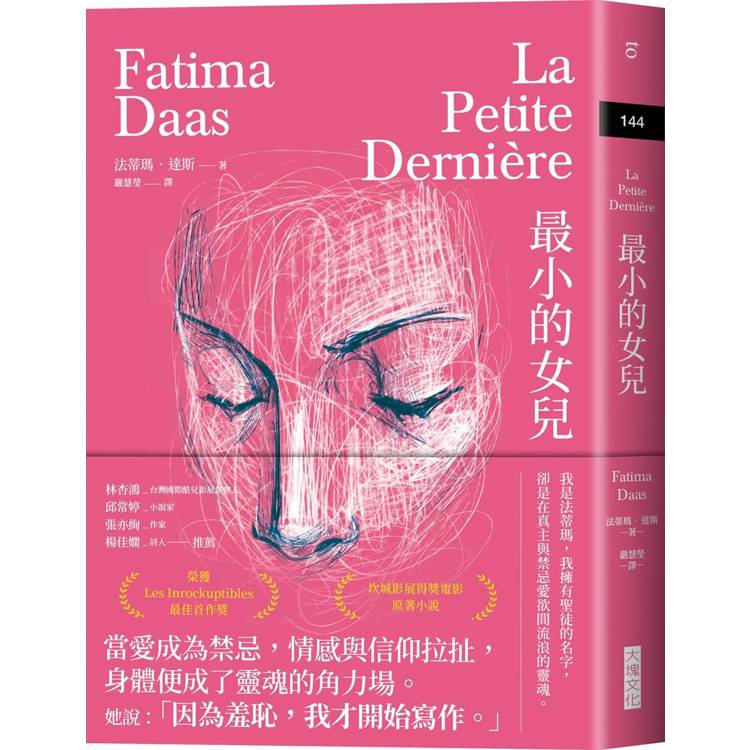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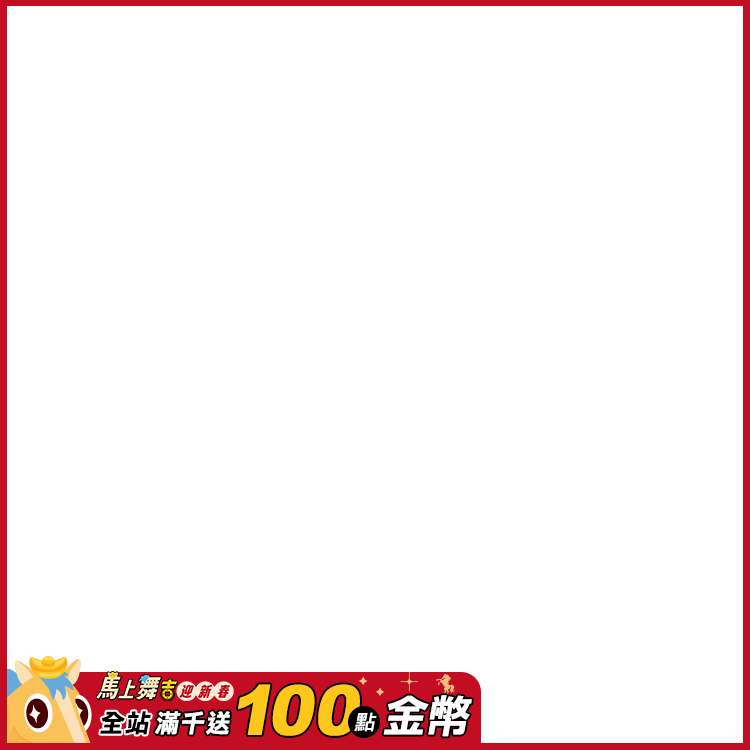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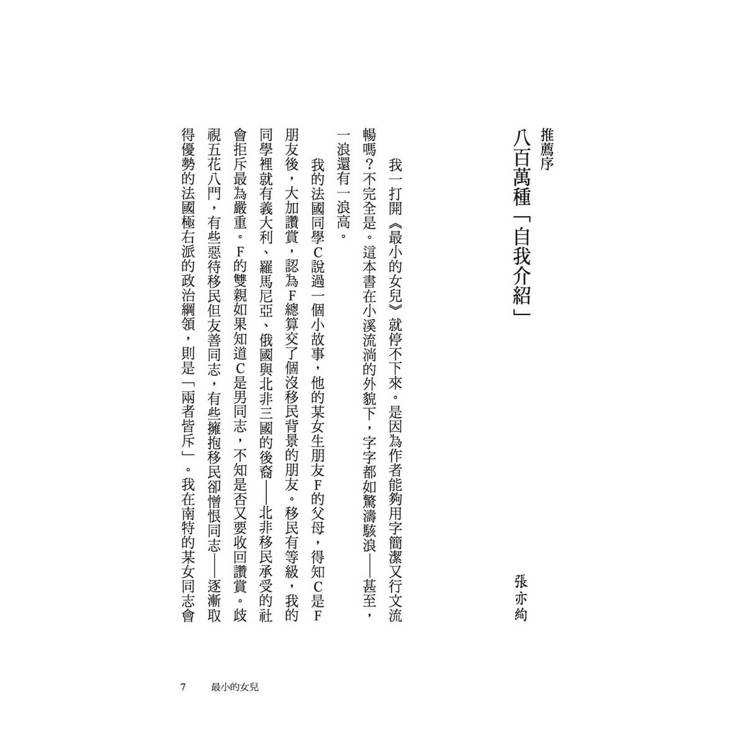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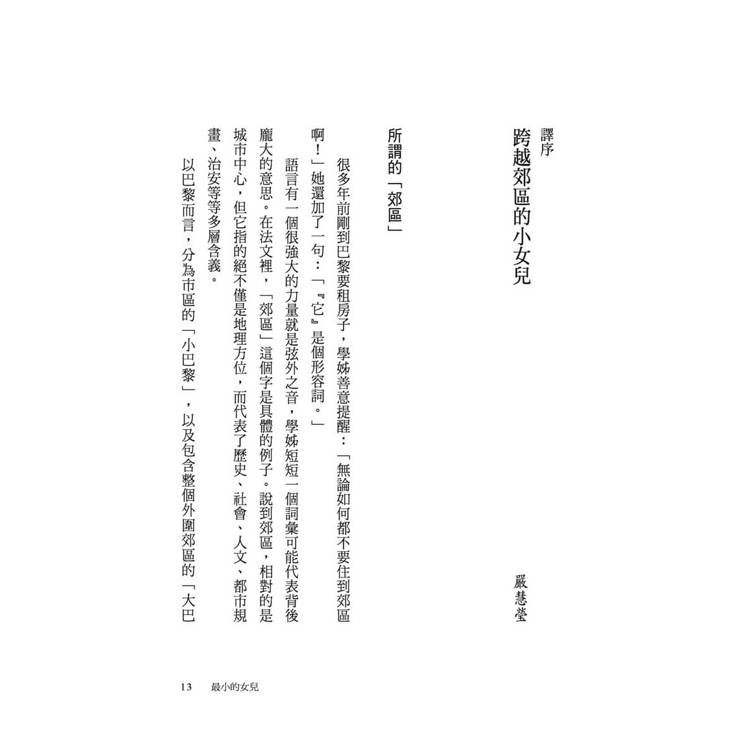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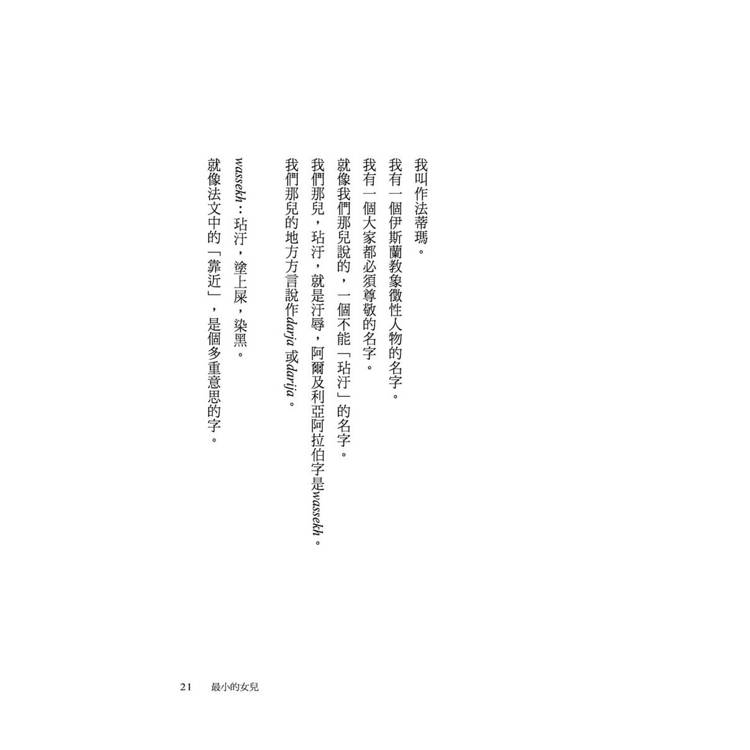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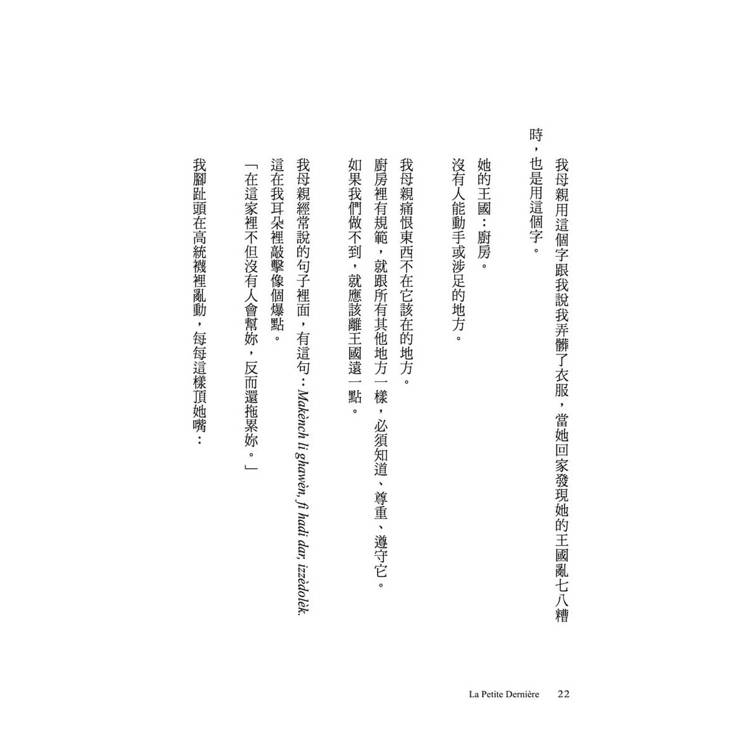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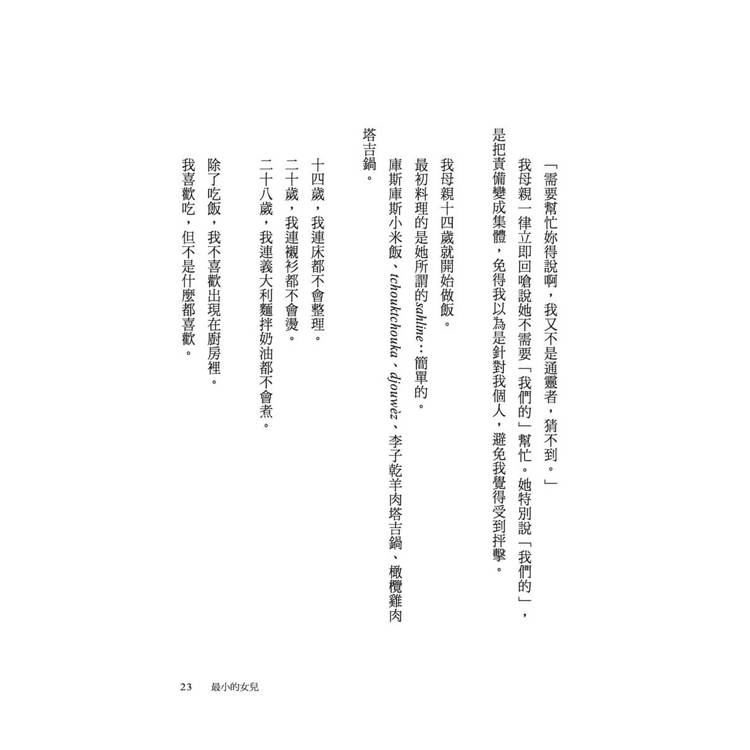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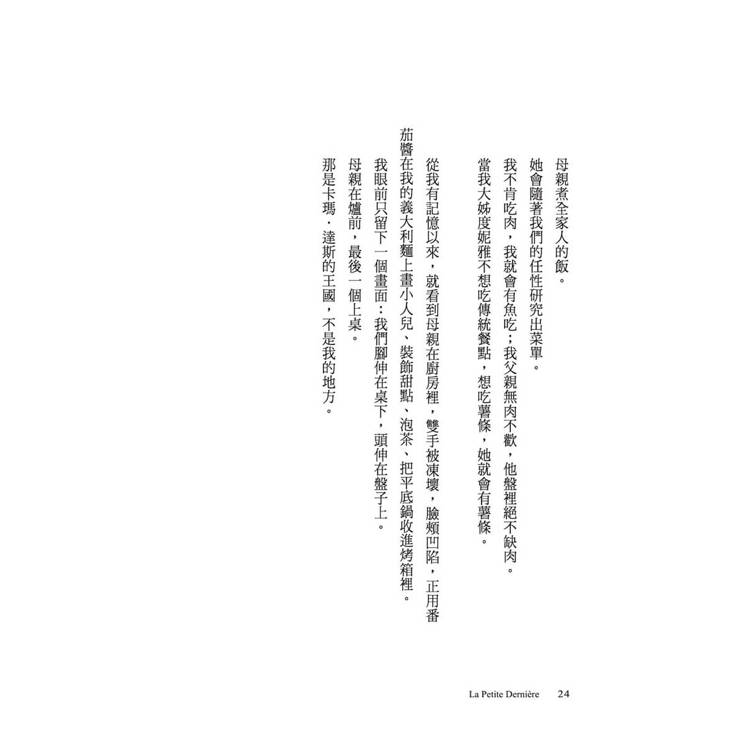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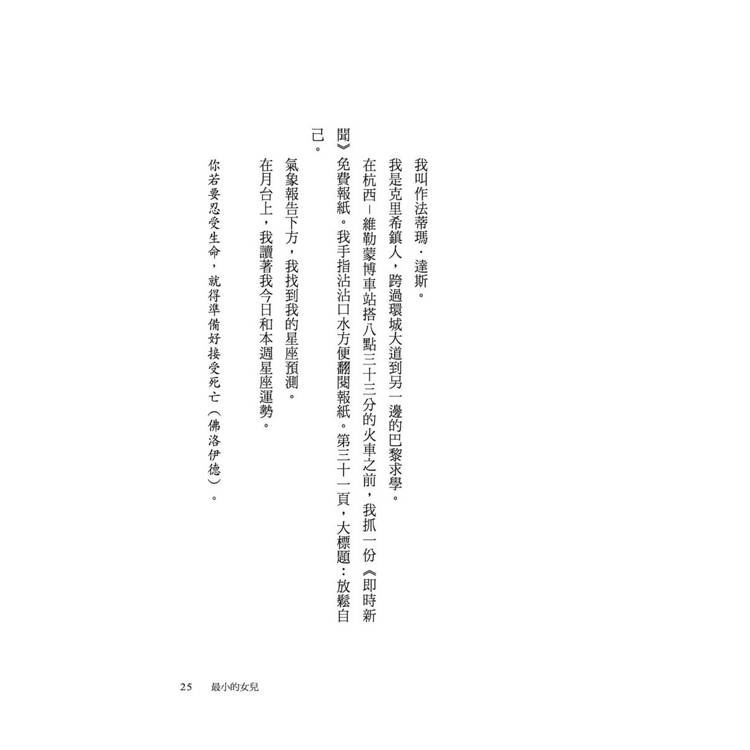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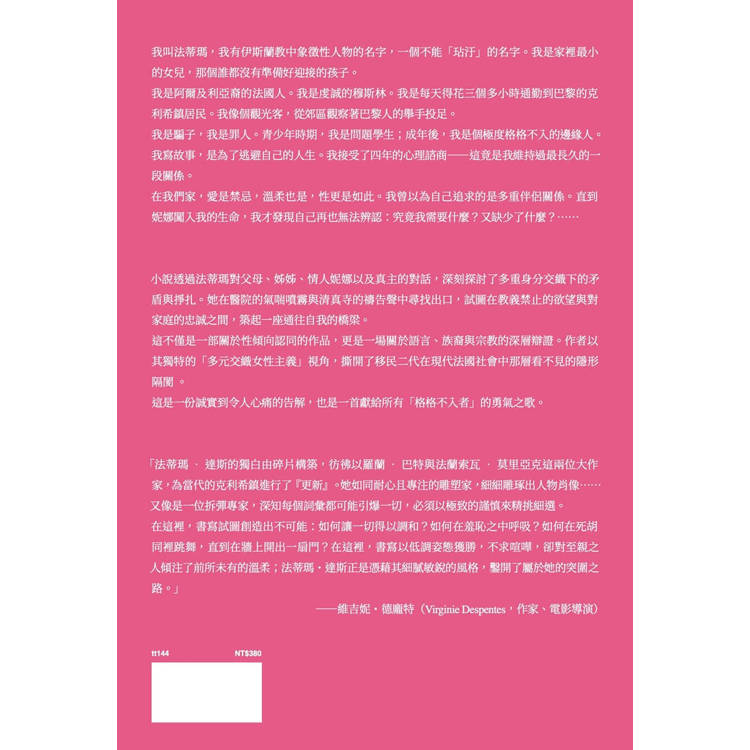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