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
Bookseller of Kabul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你是否有勇氣逼視真相?女記者揭露《追風箏的孩子》、《燦爛千陽》幕後阿富汗驚人真貌,家庭專制監獄中,妻女的哀愁與絕望,無限的希冀與掙扎。
他的書,蘇聯人來了禁,聖戰者來了搶,塔利班來了燒。
他的女人,平日只能穿藍色,結婚那天必須穿綠色。兩種顏色之間,是女人的希望與絕望。
「那個十一月的下午,宗教警察們在蘇爾坦的書店裡恪盡職守地工作。任何描繪著有生命的活物的書,不管是描寫人還是描寫動物的,都被拿下書架,扔到火堆裡。」
蘇爾坦是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一個書商,三十多年來,他反抗著政府的思想箝制,而提供各類書籍給他的同胞。因為害怕被搜查,他把一萬冊的書籍藏在喀布爾各處的閣樓裡,他有個秘密的夢想:將來,要把它們全部無償捐給城裡被洗劫一空的圖書館。
然而,對於自己的家人,蘇爾坦卻完全不是如此的慷慨。他執意要迎娶一位十六歲的女孩作二房,只因為大太太年老色衰;他要三個兒子輟學,每天十二小時拴在他的書店裡工作,只為了成就自己的圖書志業;他干預家中每位女眷的婚姻大事,因為婚姻是椿買賣,愛情只是笑話。
二00二年的春天,挪威女記者奧斯娜.塞厄斯塔,到書商家裡與他的家人共同居住了四個月。她以客觀的角度,小說的筆法,讓書中角色們訴說自己的故事。在作者細密生動文筆的描摹下,我們彷彿聞到了布卡裡蒸騰的汗味、油煙味、與塵土味,彷彿也經歷了同樣的哀愁與絕望。回過頭來,我們才赫然明白,自己擁有的哪怕是再微小的幸福,竟是如此珍貴美好。
本書特色
*全球銷量超過200萬冊
*北歐地區有史以來最暢銷圖書之一
*英國2004年引進版年度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書
*榮登美、法、德、意、西、俄、日、韓等多國年度暢銷書榜
獲美國書店協會、英國書店協會、法國書店協會年度最佳圖書推薦
*榮膺十多項國際性大獎、版權轉授近40個國家(瑞典、丹、荷、英、美、德、冰、拉脫維亞、希臘、法、義、芬蘭、西、葡、波蘭、韓、斯洛文尼亞、日、孟、以、印尼、土、保、巴西、愛沙尼亞、捷、匈、泰、羅馬尼亞、立陶宛、烏克蘭、印度、俄)
他的書,蘇聯人來了禁,聖戰者來了搶,塔利班來了燒。
他的女人,平日只能穿藍色,結婚那天必須穿綠色。兩種顏色之間,是女人的希望與絕望。
「那個十一月的下午,宗教警察們在蘇爾坦的書店裡恪盡職守地工作。任何描繪著有生命的活物的書,不管是描寫人還是描寫動物的,都被拿下書架,扔到火堆裡。」
蘇爾坦是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一個書商,三十多年來,他反抗著政府的思想箝制,而提供各類書籍給他的同胞。因為害怕被搜查,他把一萬冊的書籍藏在喀布爾各處的閣樓裡,他有個秘密的夢想:將來,要把它們全部無償捐給城裡被洗劫一空的圖書館。
然而,對於自己的家人,蘇爾坦卻完全不是如此的慷慨。他執意要迎娶一位十六歲的女孩作二房,只因為大太太年老色衰;他要三個兒子輟學,每天十二小時拴在他的書店裡工作,只為了成就自己的圖書志業;他干預家中每位女眷的婚姻大事,因為婚姻是椿買賣,愛情只是笑話。
二00二年的春天,挪威女記者奧斯娜.塞厄斯塔,到書商家裡與他的家人共同居住了四個月。她以客觀的角度,小說的筆法,讓書中角色們訴說自己的故事。在作者細密生動文筆的描摹下,我們彷彿聞到了布卡裡蒸騰的汗味、油煙味、與塵土味,彷彿也經歷了同樣的哀愁與絕望。回過頭來,我們才赫然明白,自己擁有的哪怕是再微小的幸福,竟是如此珍貴美好。
本書特色
*全球銷量超過200萬冊
*北歐地區有史以來最暢銷圖書之一
*英國2004年引進版年度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書
*榮登美、法、德、意、西、俄、日、韓等多國年度暢銷書榜
獲美國書店協會、英國書店協會、法國書店協會年度最佳圖書推薦
*榮膺十多項國際性大獎、版權轉授近40個國家(瑞典、丹、荷、英、美、德、冰、拉脫維亞、希臘、法、義、芬蘭、西、葡、波蘭、韓、斯洛文尼亞、日、孟、以、印尼、土、保、巴西、愛沙尼亞、捷、匈、泰、羅馬尼亞、立陶宛、烏克蘭、印度、俄)
名人推薦
◎「直擊阿富汗人民生活的隱秘,擅長讓人物自己述說,講述在新聞報導中看不到的他們的真實故事。」——英國《泰晤士報》
◎「精彩絕倫的描繪……塞厄斯塔對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著迷,她的好奇心加上敏銳的觀察使得本書每一頁都引人入勝。」——英國《獨立報》
◎「非同凡響……筆觸誠實公正而富於智慧。」——英國《星期日電訊報》
◎「引人入勝……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人們在最殘暴的環境下如何苦苦掙扎。」 ——英國《每日電訊報》
◎「對於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塞厄斯塔是一個敏銳而富於感情色彩的觀察者……《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讀上去像一本非常吸引人的具有報導體色彩的小說……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觀點來看,《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是一幅關於一個十分不幸的阿富汗家庭的肖像畫,毫無疑問這是西方記者對一個阿富汗家庭所曾作過的最細緻入微的描繪。」——美國《紐約時報》
◎「對一個華盛頓宣稱業已解放,但卻所知甚少的國家,精巧而又發人深省的描繪出其日常生活的細節,塞厄斯塔書寫的是不同的個體,但是她傳達的資訊卻要深遠得多……」——美國《華盛頓郵報》
◎「(塞厄斯塔)對於一個家庭日常生活的細緻入微的觀察,惟妙惟肖的描寫,尤其是對女性奴隸地位的深刻揭示,這一切預示著,對全體阿富汗人來說,前進的步伐是何等的艱難……每一個閱讀此書的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 ——美國《華盛頓郵報》
◎「對於一個處於十字路口的國家的引人入勝的描繪。」 ——美國《波士頓環球時報》
◎「塞厄斯塔直指人心的描繪既引人入勝,又動人心弦,一本令人震撼的國際暢銷書,必將成為描寫塔利班垮臺後阿富汗人民生活的最精彩絕倫的書籍之一。」 ——美國《出版家週刊》
◎「今日阿富汗的天才洋溢的寫照,文筆冷峻優美,充滿異域情調……。」 ——美國《科克斯評論》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蘇爾坦冒著被捕的危險出售書籍和其他印刷物,但是在家裡,在那棟他與母親、兄弟姐妹、妻子、兒子和侄子共同居住的飽受戰火摧殘的狹小公寓裡,他是個暴君……塞厄斯塔將塔利班垮臺後這個家庭的並不十分令人樂觀的場景,非常逼真地呈現在了讀者面前。」 ——美國《圖書館月刊》
◎「客觀公正地描繪面紗後面真實生活的作品——第一次將阿富汗婦女的境遇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一定會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追捧。」——美國Jackson’s Books書友協會網評
◎「精彩絕倫的描繪……塞厄斯塔對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著迷,她的好奇心加上敏銳的觀察使得本書每一頁都引人入勝。」——英國《獨立報》
◎「非同凡響……筆觸誠實公正而富於智慧。」——英國《星期日電訊報》
◎「引人入勝……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人們在最殘暴的環境下如何苦苦掙扎。」 ——英國《每日電訊報》
◎「對於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塞厄斯塔是一個敏銳而富於感情色彩的觀察者……《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讀上去像一本非常吸引人的具有報導體色彩的小說……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觀點來看,《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是一幅關於一個十分不幸的阿富汗家庭的肖像畫,毫無疑問這是西方記者對一個阿富汗家庭所曾作過的最細緻入微的描繪。」——美國《紐約時報》
◎「對一個華盛頓宣稱業已解放,但卻所知甚少的國家,精巧而又發人深省的描繪出其日常生活的細節,塞厄斯塔書寫的是不同的個體,但是她傳達的資訊卻要深遠得多……」——美國《華盛頓郵報》
◎「(塞厄斯塔)對於一個家庭日常生活的細緻入微的觀察,惟妙惟肖的描寫,尤其是對女性奴隸地位的深刻揭示,這一切預示著,對全體阿富汗人來說,前進的步伐是何等的艱難……每一個閱讀此書的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 ——美國《華盛頓郵報》
◎「對於一個處於十字路口的國家的引人入勝的描繪。」 ——美國《波士頓環球時報》
◎「塞厄斯塔直指人心的描繪既引人入勝,又動人心弦,一本令人震撼的國際暢銷書,必將成為描寫塔利班垮臺後阿富汗人民生活的最精彩絕倫的書籍之一。」 ——美國《出版家週刊》
◎「今日阿富汗的天才洋溢的寫照,文筆冷峻優美,充滿異域情調……。」 ——美國《科克斯評論》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蘇爾坦冒著被捕的危險出售書籍和其他印刷物,但是在家裡,在那棟他與母親、兄弟姐妹、妻子、兒子和侄子共同居住的飽受戰火摧殘的狹小公寓裡,他是個暴君……塞厄斯塔將塔利班垮臺後這個家庭的並不十分令人樂觀的場景,非常逼真地呈現在了讀者面前。」 ——美國《圖書館月刊》
◎「客觀公正地描繪面紗後面真實生活的作品——第一次將阿富汗婦女的境遇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一定會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追捧。」——美國Jackson’s Books書友協會網評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神秘的求婚者
第二章 焚書
第三章 一切由阿拉裁決
第四章 自殺與哀歌
第五章 商務之旅
第六章 你要惹我生氣嗎?
第七章 時代開始了
第八章 布卡吞沒的臉
第九章 三流的婚禮
第十章 一家之主
第十一章 少女的誘惑
第十二章 阿里的召喚
第十三章 塵埃的氣味
第十四章 無法跨越的半小時
第十五章 真主會死嗎?
第十六章 陰鬱的房間
第十七章 木匠
第十八章 我的母親「奧薩馬」
第十九章 破碎的心
尾聲
第一章 神秘的求婚者
第二章 焚書
第三章 一切由阿拉裁決
第四章 自殺與哀歌
第五章 商務之旅
第六章 你要惹我生氣嗎?
第七章 時代開始了
第八章 布卡吞沒的臉
第九章 三流的婚禮
第十章 一家之主
第十一章 少女的誘惑
第十二章 阿里的召喚
第十三章 塵埃的氣味
第十四章 無法跨越的半小時
第十五章 真主會死嗎?
第十六章 陰鬱的房間
第十七章 木匠
第十八章 我的母親「奧薩馬」
第十九章 破碎的心
尾聲
試閱
Migozarad!(一切皆如過眼雲煙)——喀布爾一家茶室牆上的塗鴉
前 言
二○○一年十一月,當我抵達喀布爾時,蘇爾坦‧汗是我遇到的第一批人之一。在那之前,我和北方聯盟的突擊隊一起相處了六個星期——在靠近塔吉克斯坦邊界的沙漠中,在興都庫什山脈間,在潘傑希爾山谷裡,在喀布爾以北的懸崖絕壁上。緊隨他們對塔利班發動攻勢的步伐,我睡過石頭地,住過小土屋,在硝煙彌漫的前線搭乘貨車、軍用車,還騎過馬,也步行過。
塔利班垮臺以後,我和北方聯盟一起開進喀布爾。在一家書店裡,我碰巧遇到了這位舉止優雅、頭髮花白的人。在槍林彈雨和亂石間度過了幾個星期,整天談論的是戰略戰術和軍事進攻,現在卻能翻著一頁頁的書籍,高談闊論歷史和文化,的確是一件再愜意不過的事。蘇爾坦的書架上擺滿了多種語言的書籍,有詩集、阿富汗民間傳說、歷史書,和小說。他是個優秀的推銷員,第一次從他的書店離開時,我買了七本書。後來一有空閒時間,我就會光顧他的書店,隨便翻一翻書,跟這位有趣的書商聊一聊。儘管阿富汗總是不斷令他感到失望,但他依然深愛著這個國家。
「一開始是蘇聯支持的共產黨人燒了我的書,接著是聖戰者組織肆無忌憚地掠奪與搶劫,最後是塔利班把一切全部燒得精光。」他告訴我。
我花了許多個小時聆聽這位書商講述的故事,他講起自己如何應對不同政權及其檢查人員,如何僅憑一己之力與員警展開周旋,要嘛把書藏起來,要嘛把它們寄放到別處——最後怎樣因此而入獄。他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又一個的獨裁者竭盡全力摧毀他的國家的文化藝術,他卻想盡辦法拯救它們。從他的談話中,我深深意識到,他本身就是阿富汗文化史的一個生動寫照:一本有著兩條腿的歷史書。
有一天他邀請我去他們家共進晚餐,他的家人——一個妻子、兒子們、妹妹們、弟弟、母親、幾個堂弟堂妹——圍坐在地上,為我準備了一場非常豐盛的晚宴。
蘇爾坦不斷地講故事,他的兒子們又笑又鬧,席間的氣氛十分熱烈,這與我和突擊隊員在山中所吃的克難餐點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是我很快注意到,他們家的女眷很少說話,蘇爾坦年輕漂亮的妻子懷抱著小孩靜靜坐在靠近門的地方,他的大太太那天晚上沒有露面。其他女人只是對向她們提出的問題予以回答,或者默默接受客人對食物的讚美,但卻從不主動引起話題。
離開時我告訴自己:「這就是阿富汗。如果能寫一本有關這個家庭的書,那一定十分有意思。」
第二天,我去蘇爾坦的書店拜訪他,並且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
「謝謝你。」這是他的全部回答。
「但是,這意味著我必須和你們住在一起。」
「歡迎你。」
「我將和你一起四處走動,按照你的方式生活,和你以及你的妻子、妹妹、兒子一起生活。」
「歡迎你。」他重複道。
*
在二月一個霧氣沉沉的日子裡,我搬進了他家,我隨身攜帶的只有我的電腦、幾本筆記本、幾支鉛筆、一支手機和身上穿的衣服,所有別的東西都在旅途中遺失了,掉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某個地方。他們一家人敞開雙臂歡迎我,我也漸漸習慣於穿戴他們借給我的阿富汗服飾。
他們在蕾拉旁邊的地上給我鋪了一個墊子,蕾拉是蘇爾坦最小的妹妹,她被安排來照顧我的飲食起居。
「你是我的小娃娃,」這位十九歲的姑娘第一天晚上對我說,「我會好好照看你的。」她向我保證。每次我一起床,她立刻就跳起身來。
蘇爾坦要求家人提供我所需的一切,我後來瞭解到,無論是誰,如果不按照這個要求做,就會受到他的處罰。
我整天都有茶喝、有東西吃,我慢慢融入這個家庭的生活中,即使我不主動問,他們有時也願意告訴我一些事情。當我手裡拿著筆記本的時候,他們的談話有些不太自在,但是如果是去逛市場、在公共汽車上,或是深夜躺在墊子上,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無論我提出何種難以想像的問題,他們的回答大都自然而然,絕少有什麼掩飾。
*
我這本書是以小說的形式寫成的,但它是根據真實的事件,或這些事件的參與者的親口講述為藍本。當我描述思想和情感時,我依照著人們告訴我的他們在某個場景下的所思所想。讀者會問我:「你怎麼能知道每個不同家庭成員的頭腦裡是如何想的?」我當然不是全知全能,內心深處的話語和情感完全是以家庭成員對我所作的描述為基礎。
蘇爾坦家人所說的波斯方言「達里語」,我始終沒能學好,但是有幾個家庭成員會說英語。不尋常嗎?確實如此。我所講述的喀布爾故事是一個最不尋常的阿富汗家庭的故事,當一個國家四分之三的人口不能讀或寫的時候,一個書商之家自然而然就是非比尋常的了。
在教一名外交官「達里」方言的過程中,蘇爾坦學會了一種形式華麗和冗長的英語。他妹妹蕾拉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在阿富汗時曾上過九年學校,在巴基斯坦流亡時也曾上過英語夜校。蘇爾坦的大兒子曼蘇爾在巴基斯坦上過幾年學校,他的英語也很好。他能夠向我講述他的恐懼、愛戀以及他和真主的討論。他解釋自己想全身全心投入宗教洗滌的渴望,並且容許我做為看不見的第四個人和他們一起去馬札里沙里夫朝聖。我應邀和蘇爾坦同行去了白沙瓦和拉合爾,加入搜捕基地組織的行列中,還陪伴女人們逛過市場,去過浴室,參加過婚禮儀式及其前期的準備工作,並且訪問了學校、教育部、警察局及監獄。
我沒有親眼目睹嘉米拉的悲慘命運或拉赫瑪尼的越軌行為,蘇爾坦向桑雅求婚的事我也只是從相關的人的故事中側面聽說的,這些人包括:蘇爾坦、桑雅以及他的母親、妹妹、弟弟和沙里法。
蘇爾坦不容許任何家庭成員以外的人住在他家裡,因此我的口譯就只有他、曼蘇爾和蕾拉,這使得他們對有關他們家的故事施加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對有出入的地方都再三確認,我會向三個口譯提出同樣的問題,而他們恰好各自代表了家庭成員中鮮明的對比。
所有家庭成員都知道,我和他們住在一起的目的是為了寫一本書,如果有什麼他們不願意我寫的,他們會告訴我。儘管如此,我還是儘量避免令蘇爾坦的家人及其他我所描繪的人感到難堪。
我的日常起居和家裡其他人完全一樣。每天拂曉,我在孩子們的哭號聲和大人們的勒令聲中起床,我等候輪到我如廁的時間,或者等每個人都解決後再悄悄溜進去。運氣好的日子裡會剩下些熱水,但是我很快發現用一杯冷水洗臉更令人神清氣爽。一天中剩餘的時間裡,我和女人們一起待在家裡、到親戚家串門子、去市場買東西,或是陪蘇爾坦和他的兒子去書店、在城裡閒逛、或是去哪裡旅行。晚上我和一家人一起用餐喝綠茶,一直到睡覺的時間。
我是個客人,但很快就感到賓至如歸。他們對我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家人都很慷慨大方。我們分享了許多美好時光,但是我這輩子很少像在蘇爾坦家裡時那樣生氣過,也很少像在那裡時那樣激烈爭吵過,甚至從未有過那麼想揍一個人的強烈衝動。同樣的事情持續不斷地刺激著我的神經:男人對待女人的方式。男人的優越感是如此根深蒂固,卻沒有人提出質疑。
我猜想他們把我當成了某種類型的「雙性人」,身為一個西方人,我可以是男人和女人的混合。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就永遠不會有機會如此近距離地和家庭婦女接觸交流;與此同時,身為一個女人,我在男人的世界裡也不存在任何障礙。當宴會分成兩半,男人和女人分別待在不同的房間時,我是唯一能夠在兩邊自由穿梭的人。
我不用遵從阿富汗婦女極為嚴格的穿衣規範,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儘管如此,我還是經常穿布卡,僅僅是為了不被干擾。西方女性在喀布爾街頭經常會招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關注,罩在布卡下面,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東張西望,而又不至於招致回視的目光。在我們外出時,我可以靜靜觀察其他的家庭成員,而不會被路人盯著瞧。蒙著臉成為一種解脫,布卡成了我唯一的隱蔽角落,這樣安靜的處所在喀布爾是極難找到的。
我穿布卡也是為了親自體驗一下阿富汗婦女究竟是什麼樣子,體驗一下當半個車廂都空著的時候用力往擁擠的後座擠的焦慮,體驗一下因為一個男人佔據著計程車後座因而只好擠在後車廂裡的痛苦,體驗做為一名高挑迷人的「布卡」而受人關注,並在大街上得到男人恭維時的得意。
但是我很快就開始討厭布卡了。它把頭部束得那麼緊,令人頭暈眼花;從視孔中要想把一切都看清楚是多麼的困難;它是那麼的密不透風,要不了多久你就開始冒汗;由於看不見腳,走起路來你不得不小心翼翼,舉步維艱;它的上面佈滿了灰塵,既骯髒又礙事;當你回到家裡將布卡拋到一邊時,是多麼的如釋重負。
我穿布卡也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當我和蘇爾坦行走在通往賈拉拉巴德的危險道路時,當我們不得不在骯髒的邊界哨所過夜時,或是當我們深夜出門時。阿富汗婦女一般不會隨身攜帶一捆美鈔和一台電腦,因此公路上的攔路強盜常常會放過罩著布卡的女人。
有一點必須著重強調一下,這是有關一個阿富汗家庭的故事,還有成百萬的別的家庭,比起這些家庭,我所描述的這個家庭算不上非常典型。這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如果這個詞也可用於阿富汗的話。這個家庭中有些人受過教育,有好幾個人能讀會寫,他們有足夠多的錢,從來不會挨餓。
假使我是住在一個典型的阿富汗家庭,那一定會是一個生活在鄉村的大家庭,家裡沒有一個人能讀會寫,對他們來說,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戰鬥。我選擇這個家庭並不是因為我想用它來代表其他所有家庭,而是因為它激發了我的創作動機。
*
我在塔利班逃跑後的第一個春天居住在喀布爾,希望的微光已經在這個春天裡浮現。塔利班的垮臺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不會再有人擔心在大街上受到宗教警察的盤問,婦女們又可以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進城去,她們可以學習,女孩子可以去上學。但是以往數十年留存下來的種種不如意,依然如揮之不去的陰影一樣存在。現在這一切何必改變呢?
在這個春天裡,隨著相對和平時期的到來,一種更為樂觀的情緒隨處可見。藍圖已經繪就,越來越多的婦女將布卡扔在了家裡,有些還找到了工作,難民也陸續回家了。
政府搖擺不定——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在軍閥和部族首領之間。在一片混亂之中,新領導人哈米德‧卡爾札伊(Hamid Karzai)採取一種平衡的策略,並以此來把握政治進程的方向。他非常受歡迎,但是他既沒有軍隊,也沒有政黨——在一個武器氾濫、敵對派別林立的國度。
儘管有兩位部長被殺,還有一位暗殺未遂,喀布爾的局勢整體來說還算平靜。居民們依舊心懷不安,許多人寄希望於大街上巡邏的外國士兵。「沒有他們內戰又會爆發。」他們說。
我記錄下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並試著把我對喀布爾春天的印象採集在一起。在這樣一個春天裡,一些人努力將冬天拋在身後,就像花兒似的默默生長,含苞欲放;另一些人則命中註定要繼續過一種「含垢忍辱」的生活,就像蕾拉所形容的那樣。
奧斯娜‧塞厄斯塔二○○二年八月一日,奧斯陸
第一章:神秘的求婚者
蘇爾坦‧汗覺得,是到了給自己再找一個老婆的時候了,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他。他先去和母親商量。
「你還是跟你現在的老婆好好過日子吧。」這是母親的回答。
他又去找大姊。「我喜歡你的第一個太太。」大姊說。他的妹妹們回答他的口吻也都完全一樣。
「這是對沙里法的羞辱。」嬸嬸的話說得更直白。
蘇爾坦需要幫助,求婚者不能自己跑到女方家去提親。按照阿富汗的風俗,這事要由男方家裡的女眷來轉達,她要先看一眼那個女孩子,以確定她是否能幹,是否有家教,是不是做妻子的材料。可是在蘇爾坦的女性近親裡,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面幫他促成這樁婚事。
蘇爾坦已經挑出了三個他認為合乎他條件的女孩子。她們都身體健康,人也長得漂亮,而且還都和他出身於同一個部族。在蘇爾坦家裡,很少有人和其他家族通婚——和親戚,尤其是表兄弟姊妹結婚被認為比較穩妥和可靠。
蘇爾坦的第一個候選新娘是十六歲的桑雅。她有一雙黑漆漆的杏仁眼,烏溜溜的頭髮閃閃發亮,身材姣好,一舉一動都很討人喜歡,據說幹起活來也很能幹。她的家裡很窮,而且他們之間還算得上是親戚——她母親的祖母和蘇爾坦母親的祖母是親姊妹。
當蘇爾坦還在琢磨著怎樣可以不透過家裡的女人,而向他心儀的候選新娘求婚時,謝天謝地,他的第一個妻子完全沒有意識到,蘇爾坦的心已經被一個小丫頭牢牢佔據了——這個小丫頭是他們結婚那一年出生的。沙里法已經慢慢變老了,和蘇爾坦一樣,她已經年過四十,她替他生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像蘇爾坦這樣身份的男人,也確實該找個新妻子了。
「你自己看著辦吧。」他弟弟最後說。
蘇爾坦想了想,這大概也是他唯一的辦法了。一天清早,他出發到那個十六歲女孩的家裡去。女孩的父母張開雙臂歡迎了他,在他們心目中,蘇爾坦是一個慷慨大方的人,對於他的每一次來訪,他們都會表示歡迎。桑雅的母親趕快燒水沏茶,他們斜倚在土屋裡的平扁墊子上,談了些輕鬆愉快的話題。末了,蘇爾坦想,該提出他的求婚請求了。
「我有個朋友想娶桑雅。」他對女孩子的父母說。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向他們的女兒求婚了,她既漂亮又勤快,但是他們認為她還有點兒小。桑雅的父親已經不能工作了,他在一場爭執中被人用刀子割斷了背部的幾根神經。他美麗的女兒可以成為婚姻交易上的籌碼,他和他太太總是期待著下一次的下注會更高。
「他很有錢,」蘇爾坦說,「他跟我做同樣的生意,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三個兒子,只是他的太太開始變老了。」
「他的牙齒怎麼樣?」女孩的父母馬上問道,暗示他們想知道這個人的年齡。
「跟我差不多吧。」蘇爾坦說。
老了點,女孩的父母想,不過也不一定是件壞事。男人年紀越大,他們的女兒越值錢。新娘的價碼是根據年齡、美貌、才幹以及家庭狀況來計算的。
果然不出所料,在蘇爾坦‧汗表達了他的求婚之意後,女孩子的父母說:「她太小了。」
對於蘇爾坦如此熱心推薦的這位富有的、不知名的求婚者來說,任何其他的回答都等於使他們賣不出好價錢,過於熱情的表現不會對事情的發展產生有益的影響,但是他們知道蘇爾坦會回來的,因為桑雅既年輕又美麗。
蘇爾坦第二天果真又回來了,重複了他的求婚。同樣的對話,同樣的回答,但這一次他得以見到桑雅。自從她出落成一個年輕少女之後,他還從未見過她。
按照傳統,她吻了他的手,這是向年長的親戚表示尊敬的意思,他則吻了她的額頭以示祝福。桑雅意識到眼前令人窒息的氛圍,蘇爾坦叔叔緊盯不放的熱切目光,讓她有些畏縮。
「我給你找了個有錢的男人,你覺得如何?」蘇爾坦問她。桑雅低頭看著地板,女孩子是沒有權利對一個求婚者有任何意見的。
蘇爾坦第三天又回來了。這次他帶來了求婚者的聘禮單:一枚戒指、一條項鍊、耳環和手鐲,全都是純金的。還有她想要的所有衣服、三百公斤米和一百五十公斤油、一頭牛和幾隻羊,還有一千五百萬阿富汗尼(約三百英鎊)。
桑雅的父親對這份禮單喜出望外,他要求見一見這位肯為他女兒出這麼大價錢的神秘求婚者。按照蘇爾坦的說法,這個人還和他們是同一部族的,但他們卻想不出這個人會是誰,也不記得曾經和他見過面。
「明天吧,」蘇爾坦說,「我會帶一張他的照片過來。」
又過了一天,在收了他的好處後,蘇爾坦的嬸嬸同意來向桑雅的父母挑明這個求婚者的身份。她帶了一張照片—— 一張蘇爾坦本人的照片──並且帶來一個絕無商量餘地的口信,要求他們在一個小時內做出決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將不勝感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們之間也不會產生任何的不愉快。他可不願意在也許行、也許不行的模棱兩可狀況中,沒完沒了地討價還價。
桑雅的父母在一個小時內同意了。他們對蘇爾坦本人以及他的財富和地位極為賞識。桑雅坐在閣樓裡等著,當求婚者的身份之謎被解開而她父母也決定接受的時候,她父親的弟弟來到閣樓上。「蘇爾坦叔叔就是你的追求者,」他說,「你同意嗎?」
桑雅沒吭聲,她躲在長長的頭巾後面,低著頭,滿眼淚花。
「你父母已經接受了求婚,」叔叔說,「現在是你唯一表達意見的機會了。」
桑雅恐懼極了,全身動彈不得。她不想要這個男人,但她知道她必須遵從她的父母。作為蘇爾坦的妻子,她在阿富汗的社會地位會大大提高,這份彩禮也可以為她家解決很多問題,幫助她的父母為兒子們買到好太太。
桑雅始終雙唇緊閉,她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沉默不語代表她同意了,協定達成了,甚至連日期也確定了。
蘇爾坦回到家裡,把這一消息通知了家人。太太沙里法、他的母親和妹妹們正圍坐著盛有米飯和菠菜的碟子用餐。沙里法以為他在開玩笑,她放聲大笑,忍不住也回敬了他幾句玩笑話。母親開心地笑著,說什麼也不相信,未經她的首肯,他居然去向人求婚了。而他的妹妹們則楞在那裡摸不著頭緒。
誰都不相信他,直到他給她們看了新娘的父母交給他的定親信物:一塊頭巾以及一些蜜餞。
沙里法一連哭了二十天。「我做錯了什麼呀?多丟人哪!你對我究竟有什麼不滿?」
蘇爾坦叫她自己振作起精神來。家裡沒有一個人支持他,甚至他自己的兒子也是如此。即便這樣,家裡卻沒有人敢出面反對他——他總是能得到他想要的。沙里法肝腸寸斷,最讓她傷心欲絕的是,她丈夫挑的人居然是個連托兒所也沒上完的文盲,而她自己是個擁有資格證書的波斯語教師。「她有什麼是我沒有的?」她抽噎著說。
蘇爾坦對妻子的眼淚無動於衷。沒有人願意參加他的訂婚宴,但沙里法最終還是不得不咬緊牙關吞下屈辱,把自己打扮起來出席宴會。
「我希望讓所有人看到你同意並支持我。將來我們都將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你必須得表現出桑雅是受歡迎的。」他要求道。沙里法一貫對丈夫百依百順,這次也不例外。儘管這次的情形糟透了,她將把他拱手讓給別人,可是沙里法還是屈從了。蘇爾坦甚至要求她把戒指戴在他和桑雅的手上。
求婚的二十天後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沙里法設法打起精神,強作歡顏。她家的女眷卻淨說些令她心煩意亂的話。「太可怕了!」她們說,「他對你怎麼這麼狠?你一定要吃苦頭了。」
婚禮在訂婚兩個月之後的穆斯林新年除夕舉行。這一次,沙里法拒絕參加。
「我辦不到。」她告訴她丈夫說。
家裡的女眷再一次支持了她,她們都沒有置辦新衣服,也沒有像參加一般婚禮那樣穿金戴銀,只是簡單打理了一下頭髮,帶著僵硬的微笑來出席典禮——她們以此來聲援那位事實上被休掉的妻子,因為從今以後,她再也不可能和蘇爾坦同床共枕——那張床現在是為那個年輕而驚慌失措的新娘預備的。儘管如此,她們將會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一直到死才能分開。
前 言
二○○一年十一月,當我抵達喀布爾時,蘇爾坦‧汗是我遇到的第一批人之一。在那之前,我和北方聯盟的突擊隊一起相處了六個星期——在靠近塔吉克斯坦邊界的沙漠中,在興都庫什山脈間,在潘傑希爾山谷裡,在喀布爾以北的懸崖絕壁上。緊隨他們對塔利班發動攻勢的步伐,我睡過石頭地,住過小土屋,在硝煙彌漫的前線搭乘貨車、軍用車,還騎過馬,也步行過。
塔利班垮臺以後,我和北方聯盟一起開進喀布爾。在一家書店裡,我碰巧遇到了這位舉止優雅、頭髮花白的人。在槍林彈雨和亂石間度過了幾個星期,整天談論的是戰略戰術和軍事進攻,現在卻能翻著一頁頁的書籍,高談闊論歷史和文化,的確是一件再愜意不過的事。蘇爾坦的書架上擺滿了多種語言的書籍,有詩集、阿富汗民間傳說、歷史書,和小說。他是個優秀的推銷員,第一次從他的書店離開時,我買了七本書。後來一有空閒時間,我就會光顧他的書店,隨便翻一翻書,跟這位有趣的書商聊一聊。儘管阿富汗總是不斷令他感到失望,但他依然深愛著這個國家。
「一開始是蘇聯支持的共產黨人燒了我的書,接著是聖戰者組織肆無忌憚地掠奪與搶劫,最後是塔利班把一切全部燒得精光。」他告訴我。
我花了許多個小時聆聽這位書商講述的故事,他講起自己如何應對不同政權及其檢查人員,如何僅憑一己之力與員警展開周旋,要嘛把書藏起來,要嘛把它們寄放到別處——最後怎樣因此而入獄。他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又一個的獨裁者竭盡全力摧毀他的國家的文化藝術,他卻想盡辦法拯救它們。從他的談話中,我深深意識到,他本身就是阿富汗文化史的一個生動寫照:一本有著兩條腿的歷史書。
有一天他邀請我去他們家共進晚餐,他的家人——一個妻子、兒子們、妹妹們、弟弟、母親、幾個堂弟堂妹——圍坐在地上,為我準備了一場非常豐盛的晚宴。
蘇爾坦不斷地講故事,他的兒子們又笑又鬧,席間的氣氛十分熱烈,這與我和突擊隊員在山中所吃的克難餐點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是我很快注意到,他們家的女眷很少說話,蘇爾坦年輕漂亮的妻子懷抱著小孩靜靜坐在靠近門的地方,他的大太太那天晚上沒有露面。其他女人只是對向她們提出的問題予以回答,或者默默接受客人對食物的讚美,但卻從不主動引起話題。
離開時我告訴自己:「這就是阿富汗。如果能寫一本有關這個家庭的書,那一定十分有意思。」
第二天,我去蘇爾坦的書店拜訪他,並且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
「謝謝你。」這是他的全部回答。
「但是,這意味著我必須和你們住在一起。」
「歡迎你。」
「我將和你一起四處走動,按照你的方式生活,和你以及你的妻子、妹妹、兒子一起生活。」
「歡迎你。」他重複道。
*
在二月一個霧氣沉沉的日子裡,我搬進了他家,我隨身攜帶的只有我的電腦、幾本筆記本、幾支鉛筆、一支手機和身上穿的衣服,所有別的東西都在旅途中遺失了,掉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某個地方。他們一家人敞開雙臂歡迎我,我也漸漸習慣於穿戴他們借給我的阿富汗服飾。
他們在蕾拉旁邊的地上給我鋪了一個墊子,蕾拉是蘇爾坦最小的妹妹,她被安排來照顧我的飲食起居。
「你是我的小娃娃,」這位十九歲的姑娘第一天晚上對我說,「我會好好照看你的。」她向我保證。每次我一起床,她立刻就跳起身來。
蘇爾坦要求家人提供我所需的一切,我後來瞭解到,無論是誰,如果不按照這個要求做,就會受到他的處罰。
我整天都有茶喝、有東西吃,我慢慢融入這個家庭的生活中,即使我不主動問,他們有時也願意告訴我一些事情。當我手裡拿著筆記本的時候,他們的談話有些不太自在,但是如果是去逛市場、在公共汽車上,或是深夜躺在墊子上,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無論我提出何種難以想像的問題,他們的回答大都自然而然,絕少有什麼掩飾。
*
我這本書是以小說的形式寫成的,但它是根據真實的事件,或這些事件的參與者的親口講述為藍本。當我描述思想和情感時,我依照著人們告訴我的他們在某個場景下的所思所想。讀者會問我:「你怎麼能知道每個不同家庭成員的頭腦裡是如何想的?」我當然不是全知全能,內心深處的話語和情感完全是以家庭成員對我所作的描述為基礎。
蘇爾坦家人所說的波斯方言「達里語」,我始終沒能學好,但是有幾個家庭成員會說英語。不尋常嗎?確實如此。我所講述的喀布爾故事是一個最不尋常的阿富汗家庭的故事,當一個國家四分之三的人口不能讀或寫的時候,一個書商之家自然而然就是非比尋常的了。
在教一名外交官「達里」方言的過程中,蘇爾坦學會了一種形式華麗和冗長的英語。他妹妹蕾拉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在阿富汗時曾上過九年學校,在巴基斯坦流亡時也曾上過英語夜校。蘇爾坦的大兒子曼蘇爾在巴基斯坦上過幾年學校,他的英語也很好。他能夠向我講述他的恐懼、愛戀以及他和真主的討論。他解釋自己想全身全心投入宗教洗滌的渴望,並且容許我做為看不見的第四個人和他們一起去馬札里沙里夫朝聖。我應邀和蘇爾坦同行去了白沙瓦和拉合爾,加入搜捕基地組織的行列中,還陪伴女人們逛過市場,去過浴室,參加過婚禮儀式及其前期的準備工作,並且訪問了學校、教育部、警察局及監獄。
我沒有親眼目睹嘉米拉的悲慘命運或拉赫瑪尼的越軌行為,蘇爾坦向桑雅求婚的事我也只是從相關的人的故事中側面聽說的,這些人包括:蘇爾坦、桑雅以及他的母親、妹妹、弟弟和沙里法。
蘇爾坦不容許任何家庭成員以外的人住在他家裡,因此我的口譯就只有他、曼蘇爾和蕾拉,這使得他們對有關他們家的故事施加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對有出入的地方都再三確認,我會向三個口譯提出同樣的問題,而他們恰好各自代表了家庭成員中鮮明的對比。
所有家庭成員都知道,我和他們住在一起的目的是為了寫一本書,如果有什麼他們不願意我寫的,他們會告訴我。儘管如此,我還是儘量避免令蘇爾坦的家人及其他我所描繪的人感到難堪。
我的日常起居和家裡其他人完全一樣。每天拂曉,我在孩子們的哭號聲和大人們的勒令聲中起床,我等候輪到我如廁的時間,或者等每個人都解決後再悄悄溜進去。運氣好的日子裡會剩下些熱水,但是我很快發現用一杯冷水洗臉更令人神清氣爽。一天中剩餘的時間裡,我和女人們一起待在家裡、到親戚家串門子、去市場買東西,或是陪蘇爾坦和他的兒子去書店、在城裡閒逛、或是去哪裡旅行。晚上我和一家人一起用餐喝綠茶,一直到睡覺的時間。
我是個客人,但很快就感到賓至如歸。他們對我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家人都很慷慨大方。我們分享了許多美好時光,但是我這輩子很少像在蘇爾坦家裡時那樣生氣過,也很少像在那裡時那樣激烈爭吵過,甚至從未有過那麼想揍一個人的強烈衝動。同樣的事情持續不斷地刺激著我的神經:男人對待女人的方式。男人的優越感是如此根深蒂固,卻沒有人提出質疑。
我猜想他們把我當成了某種類型的「雙性人」,身為一個西方人,我可以是男人和女人的混合。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就永遠不會有機會如此近距離地和家庭婦女接觸交流;與此同時,身為一個女人,我在男人的世界裡也不存在任何障礙。當宴會分成兩半,男人和女人分別待在不同的房間時,我是唯一能夠在兩邊自由穿梭的人。
我不用遵從阿富汗婦女極為嚴格的穿衣規範,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儘管如此,我還是經常穿布卡,僅僅是為了不被干擾。西方女性在喀布爾街頭經常會招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關注,罩在布卡下面,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東張西望,而又不至於招致回視的目光。在我們外出時,我可以靜靜觀察其他的家庭成員,而不會被路人盯著瞧。蒙著臉成為一種解脫,布卡成了我唯一的隱蔽角落,這樣安靜的處所在喀布爾是極難找到的。
我穿布卡也是為了親自體驗一下阿富汗婦女究竟是什麼樣子,體驗一下當半個車廂都空著的時候用力往擁擠的後座擠的焦慮,體驗一下因為一個男人佔據著計程車後座因而只好擠在後車廂裡的痛苦,體驗做為一名高挑迷人的「布卡」而受人關注,並在大街上得到男人恭維時的得意。
但是我很快就開始討厭布卡了。它把頭部束得那麼緊,令人頭暈眼花;從視孔中要想把一切都看清楚是多麼的困難;它是那麼的密不透風,要不了多久你就開始冒汗;由於看不見腳,走起路來你不得不小心翼翼,舉步維艱;它的上面佈滿了灰塵,既骯髒又礙事;當你回到家裡將布卡拋到一邊時,是多麼的如釋重負。
我穿布卡也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當我和蘇爾坦行走在通往賈拉拉巴德的危險道路時,當我們不得不在骯髒的邊界哨所過夜時,或是當我們深夜出門時。阿富汗婦女一般不會隨身攜帶一捆美鈔和一台電腦,因此公路上的攔路強盜常常會放過罩著布卡的女人。
有一點必須著重強調一下,這是有關一個阿富汗家庭的故事,還有成百萬的別的家庭,比起這些家庭,我所描述的這個家庭算不上非常典型。這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如果這個詞也可用於阿富汗的話。這個家庭中有些人受過教育,有好幾個人能讀會寫,他們有足夠多的錢,從來不會挨餓。
假使我是住在一個典型的阿富汗家庭,那一定會是一個生活在鄉村的大家庭,家裡沒有一個人能讀會寫,對他們來說,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戰鬥。我選擇這個家庭並不是因為我想用它來代表其他所有家庭,而是因為它激發了我的創作動機。
*
我在塔利班逃跑後的第一個春天居住在喀布爾,希望的微光已經在這個春天裡浮現。塔利班的垮臺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不會再有人擔心在大街上受到宗教警察的盤問,婦女們又可以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進城去,她們可以學習,女孩子可以去上學。但是以往數十年留存下來的種種不如意,依然如揮之不去的陰影一樣存在。現在這一切何必改變呢?
在這個春天裡,隨著相對和平時期的到來,一種更為樂觀的情緒隨處可見。藍圖已經繪就,越來越多的婦女將布卡扔在了家裡,有些還找到了工作,難民也陸續回家了。
政府搖擺不定——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在軍閥和部族首領之間。在一片混亂之中,新領導人哈米德‧卡爾札伊(Hamid Karzai)採取一種平衡的策略,並以此來把握政治進程的方向。他非常受歡迎,但是他既沒有軍隊,也沒有政黨——在一個武器氾濫、敵對派別林立的國度。
儘管有兩位部長被殺,還有一位暗殺未遂,喀布爾的局勢整體來說還算平靜。居民們依舊心懷不安,許多人寄希望於大街上巡邏的外國士兵。「沒有他們內戰又會爆發。」他們說。
我記錄下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並試著把我對喀布爾春天的印象採集在一起。在這樣一個春天裡,一些人努力將冬天拋在身後,就像花兒似的默默生長,含苞欲放;另一些人則命中註定要繼續過一種「含垢忍辱」的生活,就像蕾拉所形容的那樣。
奧斯娜‧塞厄斯塔二○○二年八月一日,奧斯陸
第一章:神秘的求婚者
蘇爾坦‧汗覺得,是到了給自己再找一個老婆的時候了,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他。他先去和母親商量。
「你還是跟你現在的老婆好好過日子吧。」這是母親的回答。
他又去找大姊。「我喜歡你的第一個太太。」大姊說。他的妹妹們回答他的口吻也都完全一樣。
「這是對沙里法的羞辱。」嬸嬸的話說得更直白。
蘇爾坦需要幫助,求婚者不能自己跑到女方家去提親。按照阿富汗的風俗,這事要由男方家裡的女眷來轉達,她要先看一眼那個女孩子,以確定她是否能幹,是否有家教,是不是做妻子的材料。可是在蘇爾坦的女性近親裡,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面幫他促成這樁婚事。
蘇爾坦已經挑出了三個他認為合乎他條件的女孩子。她們都身體健康,人也長得漂亮,而且還都和他出身於同一個部族。在蘇爾坦家裡,很少有人和其他家族通婚——和親戚,尤其是表兄弟姊妹結婚被認為比較穩妥和可靠。
蘇爾坦的第一個候選新娘是十六歲的桑雅。她有一雙黑漆漆的杏仁眼,烏溜溜的頭髮閃閃發亮,身材姣好,一舉一動都很討人喜歡,據說幹起活來也很能幹。她的家裡很窮,而且他們之間還算得上是親戚——她母親的祖母和蘇爾坦母親的祖母是親姊妹。
當蘇爾坦還在琢磨著怎樣可以不透過家裡的女人,而向他心儀的候選新娘求婚時,謝天謝地,他的第一個妻子完全沒有意識到,蘇爾坦的心已經被一個小丫頭牢牢佔據了——這個小丫頭是他們結婚那一年出生的。沙里法已經慢慢變老了,和蘇爾坦一樣,她已經年過四十,她替他生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像蘇爾坦這樣身份的男人,也確實該找個新妻子了。
「你自己看著辦吧。」他弟弟最後說。
蘇爾坦想了想,這大概也是他唯一的辦法了。一天清早,他出發到那個十六歲女孩的家裡去。女孩的父母張開雙臂歡迎了他,在他們心目中,蘇爾坦是一個慷慨大方的人,對於他的每一次來訪,他們都會表示歡迎。桑雅的母親趕快燒水沏茶,他們斜倚在土屋裡的平扁墊子上,談了些輕鬆愉快的話題。末了,蘇爾坦想,該提出他的求婚請求了。
「我有個朋友想娶桑雅。」他對女孩子的父母說。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向他們的女兒求婚了,她既漂亮又勤快,但是他們認為她還有點兒小。桑雅的父親已經不能工作了,他在一場爭執中被人用刀子割斷了背部的幾根神經。他美麗的女兒可以成為婚姻交易上的籌碼,他和他太太總是期待著下一次的下注會更高。
「他很有錢,」蘇爾坦說,「他跟我做同樣的生意,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三個兒子,只是他的太太開始變老了。」
「他的牙齒怎麼樣?」女孩的父母馬上問道,暗示他們想知道這個人的年齡。
「跟我差不多吧。」蘇爾坦說。
老了點,女孩的父母想,不過也不一定是件壞事。男人年紀越大,他們的女兒越值錢。新娘的價碼是根據年齡、美貌、才幹以及家庭狀況來計算的。
果然不出所料,在蘇爾坦‧汗表達了他的求婚之意後,女孩子的父母說:「她太小了。」
對於蘇爾坦如此熱心推薦的這位富有的、不知名的求婚者來說,任何其他的回答都等於使他們賣不出好價錢,過於熱情的表現不會對事情的發展產生有益的影響,但是他們知道蘇爾坦會回來的,因為桑雅既年輕又美麗。
蘇爾坦第二天果真又回來了,重複了他的求婚。同樣的對話,同樣的回答,但這一次他得以見到桑雅。自從她出落成一個年輕少女之後,他還從未見過她。
按照傳統,她吻了他的手,這是向年長的親戚表示尊敬的意思,他則吻了她的額頭以示祝福。桑雅意識到眼前令人窒息的氛圍,蘇爾坦叔叔緊盯不放的熱切目光,讓她有些畏縮。
「我給你找了個有錢的男人,你覺得如何?」蘇爾坦問她。桑雅低頭看著地板,女孩子是沒有權利對一個求婚者有任何意見的。
蘇爾坦第三天又回來了。這次他帶來了求婚者的聘禮單:一枚戒指、一條項鍊、耳環和手鐲,全都是純金的。還有她想要的所有衣服、三百公斤米和一百五十公斤油、一頭牛和幾隻羊,還有一千五百萬阿富汗尼(約三百英鎊)。
桑雅的父親對這份禮單喜出望外,他要求見一見這位肯為他女兒出這麼大價錢的神秘求婚者。按照蘇爾坦的說法,這個人還和他們是同一部族的,但他們卻想不出這個人會是誰,也不記得曾經和他見過面。
「明天吧,」蘇爾坦說,「我會帶一張他的照片過來。」
又過了一天,在收了他的好處後,蘇爾坦的嬸嬸同意來向桑雅的父母挑明這個求婚者的身份。她帶了一張照片—— 一張蘇爾坦本人的照片──並且帶來一個絕無商量餘地的口信,要求他們在一個小時內做出決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將不勝感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們之間也不會產生任何的不愉快。他可不願意在也許行、也許不行的模棱兩可狀況中,沒完沒了地討價還價。
桑雅的父母在一個小時內同意了。他們對蘇爾坦本人以及他的財富和地位極為賞識。桑雅坐在閣樓裡等著,當求婚者的身份之謎被解開而她父母也決定接受的時候,她父親的弟弟來到閣樓上。「蘇爾坦叔叔就是你的追求者,」他說,「你同意嗎?」
桑雅沒吭聲,她躲在長長的頭巾後面,低著頭,滿眼淚花。
「你父母已經接受了求婚,」叔叔說,「現在是你唯一表達意見的機會了。」
桑雅恐懼極了,全身動彈不得。她不想要這個男人,但她知道她必須遵從她的父母。作為蘇爾坦的妻子,她在阿富汗的社會地位會大大提高,這份彩禮也可以為她家解決很多問題,幫助她的父母為兒子們買到好太太。
桑雅始終雙唇緊閉,她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沉默不語代表她同意了,協定達成了,甚至連日期也確定了。
蘇爾坦回到家裡,把這一消息通知了家人。太太沙里法、他的母親和妹妹們正圍坐著盛有米飯和菠菜的碟子用餐。沙里法以為他在開玩笑,她放聲大笑,忍不住也回敬了他幾句玩笑話。母親開心地笑著,說什麼也不相信,未經她的首肯,他居然去向人求婚了。而他的妹妹們則楞在那裡摸不著頭緒。
誰都不相信他,直到他給她們看了新娘的父母交給他的定親信物:一塊頭巾以及一些蜜餞。
沙里法一連哭了二十天。「我做錯了什麼呀?多丟人哪!你對我究竟有什麼不滿?」
蘇爾坦叫她自己振作起精神來。家裡沒有一個人支持他,甚至他自己的兒子也是如此。即便這樣,家裡卻沒有人敢出面反對他——他總是能得到他想要的。沙里法肝腸寸斷,最讓她傷心欲絕的是,她丈夫挑的人居然是個連托兒所也沒上完的文盲,而她自己是個擁有資格證書的波斯語教師。「她有什麼是我沒有的?」她抽噎著說。
蘇爾坦對妻子的眼淚無動於衷。沒有人願意參加他的訂婚宴,但沙里法最終還是不得不咬緊牙關吞下屈辱,把自己打扮起來出席宴會。
「我希望讓所有人看到你同意並支持我。將來我們都將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你必須得表現出桑雅是受歡迎的。」他要求道。沙里法一貫對丈夫百依百順,這次也不例外。儘管這次的情形糟透了,她將把他拱手讓給別人,可是沙里法還是屈從了。蘇爾坦甚至要求她把戒指戴在他和桑雅的手上。
求婚的二十天後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沙里法設法打起精神,強作歡顏。她家的女眷卻淨說些令她心煩意亂的話。「太可怕了!」她們說,「他對你怎麼這麼狠?你一定要吃苦頭了。」
婚禮在訂婚兩個月之後的穆斯林新年除夕舉行。這一次,沙里法拒絕參加。
「我辦不到。」她告訴她丈夫說。
家裡的女眷再一次支持了她,她們都沒有置辦新衣服,也沒有像參加一般婚禮那樣穿金戴銀,只是簡單打理了一下頭髮,帶著僵硬的微笑來出席典禮——她們以此來聲援那位事實上被休掉的妻子,因為從今以後,她再也不可能和蘇爾坦同床共枕——那張床現在是為那個年輕而驚慌失措的新娘預備的。儘管如此,她們將會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一直到死才能分開。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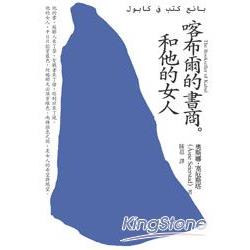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