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實相與再現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比較建築學,空間裡的新語言,跨區域與跨文化的多元建築對話!
我們常常說新化老街的街屋是「巴洛克建築」,而巴洛克建築這詞源指的是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那麼,新化老街的街屋和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兩者有直接的關係嗎?
「日式極簡禪風」、「新古典式的低調奢華」……這些字眼與形式的搭配,在建築實踐與歸類上是適當且合理的嗎?如此弔詭的新名詞組合在東、西方現代文化中時常可見,尤其是面對後殖民、跨文化、跨領域的多元建築研究時,西方自19世紀以來所建立的建築史架構顯現左支右絀的窘境。
建築為實相的再現,意旨建築以其外顯的形式來「呈現」人類對於真實事物與精神文化的理解、認知與信念。本書以諸多建築實例為主角,從新穎的「比較建築學」的空間新語言,提出一些傳統建築史架構下無力探討的議題,從傳統與現代的虛構藩籬、精神與意念的認同、形式的移植與複製,最後結合人、建築與心靈建構來做分析。
例如:荷蘭人在磚材的使用,包含著人們對荷蘭建築從傳統到現代的情感,及其中所發生的爭辯與質疑;從歐洲的猶太隔離區與猶太會堂的建築與空間,呈現出猶太人在離散歷史中的身分認同、以及壓抑到解放的過程;而飄洋過海到中國泉州的蔥形拱式建築、德國特里爾的城市結構,是否為印度蒙兀兒帝國和羅馬帝國的文化移植或混血複製……等等,嶄新的切入角度、跨區域與跨文化的多元建築對話,提供你我另一種不同的建築風景與思考。
目錄
前言
主題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虛構藩籬
Ⅰ 揮之不去的傳統──磚在荷蘭建築發展中的角色
Ⅱ 前現代中的現代──印度齋普爾的占塔曼塔天文台建築群
主題貳:建築與認同
Ⅲ 菁英的自白──建築語法中的建築細部
Ⅳ 離散歷史中的自我認同──歐洲的猶太人、猶太隔離區與猶太會堂
主題參:形式的移植與複製
Ⅴ 飄洋過海的形式移植──中國泉州街屋的印度蒙兀兒拱式
Ⅵ 在北方複製羅馬──德國特里爾的城市空間與建築
主題肆:建築與宇宙實相
Ⅶ 相同的實相,不同的再現──漢人儀式空間中的「左尊右卑」與印度儀式空間中的「順時針繞行」
Ⅷ 由神廟變教堂──歐洲城市中心的神聖性延續
序/導讀
對於大部分常見的主題來說,這樣的歸類並不成問題,然而當面對某些特殊的主題時,如台灣日治時期的街屋與公共建築,或是台灣戰後的中國復古式樣建築等等,如何將它們適當地歸類卻時常令我們頭痛。舉例來說,我們常常說新化老街的街屋是「巴洛克建築」,而巴洛克建築這個詞所指涉的乃是源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我們必須要想想,新化老街街屋所呈現的形式與內容,和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的形式與內容,兩者有直接的關係嗎?如果這它們沒有直接的關係,卻將新化老街街屋貼上「巴洛克」的標籤,這樣是否會太過唐突?更者,這樣的歸類是否會導向一個沒有合理分析基礎的研究結論?然而,若我們因此迴避「歸類」這個動作,我們又如何在適當的脈絡下進行對它們的分析?
類似的問題除了出現在建築史研究的領域,也同樣出現在建築實踐的領域。如我們所見,不少台灣房地產建築在推案時,往往會冠上一些充滿想像並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有關的建築史詞彙,而它們的呈現也往往會是一些有趣的排列組合,如「日式極簡禪風」、「新古典式的低調奢華」或「文藝復興雅典豪宅」等等,有時候還會看到「Art Deco」被誤寫成「Art de Core」(誰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們不禁要問,國人對於建築史的認知,是否有一大半都是來自這些房地產領域的想像?隨著國人的生活與知識水準逐漸提高,不少人也對世界建築文化產生興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該用何種方式向他們介紹豐富的建築文化卻又不誤導他們呢?
2004年起,筆者進入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藝術史系建築史研究所就讀後,才赫然發現這種歸類與命名的問題不僅出現在台灣,卻也出現在建築史研究體系形成的西方世界。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所建立的建築史體系,在面對後殖民、跨文化與跨地域的多元建築研究主題時,早已出現左支右拙的窘境,既有的建築史架構早已不堪使用。面對這種窘境,不少西方的建築史學者已開始思考對策,萊頓大學的建築史教授麥金(Aart J. J. Mekking)是其中之一。麥金教授在分析傳統建築史研究「典範」(paradigm)的侷限性後,提出了一套新的研究典範,並發展出所謂的「比較建築學」(Comparative Architecture Studies),藉此,我們將有機會討論那些在既有建築史架構下無力討論的建築主題。
2007年夏天,由黃健敏老師領隊,台灣的公共藝術專家們至歐洲各國考察,筆者也才有機會在荷蘭向他介紹自己所學。因此,關於本書的出版,筆者必須向黃健敏老師致上誠摯的感謝。雖然本書所有的主題皆以「比較建築學」的方法切入分析,但筆者已盡量避免讓內文出現太多理論性的討論,僅希望讀者能以輕鬆的態度,拋去那些傳統建築分類法的沈重包袱,以一個新的視野來接觸世界上各種有趣的建築文化與現象。
2009年4月於荷蘭萊頓
試閱
泉州以及鄰近地區的拱式
在中國泉州的老城區,我們往往可以發現一種普遍出現的拱式,通常作為街屋窗子上方的裝飾。它們可能是石造、磚造或是木造,雖然有的較為高聳、有的較為扁平,但都具備相仿的形式特徵。其形式上大致有著兩點特徵:一、中央為一尖拱,尖拱兩側沿著上凹的弧線向下,經過反曲點後再成為下凹的弧線,而形成蔥形的拱式,依照建築學的形式分類,其可稱為「蔥形拱式」(Ogee Arch);二、蔥形拱式的兩側通常還會再搭配上一或多組的連續對稱拱圈。除了在泉州,我們亦可以發現這樣的拱式出現在其鄰近地區,如漳州、廈門或是金門,甚至一些偏遠的小村鎮。
這些以蔥形拱式搭配著連續對稱拱圈作為裝飾的建築,大多興建於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有些居民可以確切指出其中某幾棟是由海外華僑所興建的,另有些居民認為,這種拱式可能和過去泉州的外國穆斯林有關。據此我們可以大略知道,這種拱式應是由海外輸入,而非源自中國本土的形式語彙。然而,這種拱式究竟源自哪裡?它為何會移植到泉州等地呢?它在泉州的現身代表了什麼意義?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再進一步討論。
「蔥形拱式」與「連續對稱拱圈」的起源與發展
這些於泉州及其周邊地區觀察到的拱式,第一個特徵無非其中央的蔥形拱式。根據有限的建築史資料,我們無法確切指出這種蔥形拱式的起源,但我們可以大致知道,其最早可能出現於古代波斯(今伊朗)。部分考古學家推測,西元前六世紀所興建的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之墓,其屋頂即有著蔥形拱式的造型,只可惜此頂蓋保留不夠完整,以致於其原貌的推測仍眾說紛紜。不過,透過其他較晚的建築遺跡則可發現,這種蔥形拱式早已在古波斯以及其周邊地區出現。當伊斯蘭教興起後,此拱式更進一步被吸納成為伊斯蘭建築的特徵之一。隨著日後伊斯蘭勢力的擴散,蔥形拱式也跟著成為各地清真寺的普遍元素。
在與波斯接壤的印度,亦有此蔥形拱式早期出現的遺跡。例如在著名的阿旖陀(Ajanta)佛教石窟群當中,有幾個建於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後二世紀之間的石窟,其入口亦雕刻著蔥形拱式的裝飾。到了十五世紀時,印度西北部已是伊斯蘭勢力範圍,當地的清真寺也都有著蔥形拱式的裝飾造型;更者,除了蔥形拱式,連續拱圈的裝飾亦在這些建築上出現。如在印度艾哈邁達巴德市(Ahmedabad)的大清真寺(Jami Masjid,十五世紀)上,我們可以發現其石造的主要大門有著蔥形拱式的造型,進入大門後的兩根對柱上方,亦有著一組連續拱圈。只是其大門上方的蔥形拱式並未直接搭配多組的連續對稱拱圈,且此對柱上方的連續對稱拱圈的中心點亦非蔥形拱式。在這個時候,蔥形拱式與連續拱圈兩者尚未結合在一起,它們仍是兩種獨立存在的元素。
蔥形拱式與連續拱圈在印度的結合,成為「蒙兀兒拱式」
到了十六世紀,印度進入了蒙兀兒帝國時期,其統治者為穆斯林。蒙兀兒帝國極盛時期的領土,涵蓋今日大部分的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等地,西接薩非王朝(Safavids Dynasty)所統治的波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首度見到蔥形拱式與連續對稱拱圈的結合,其被命名為「蒙兀兒拱式」(Mughal Arch)。
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這種蒙兀兒拱式發展為為印度普遍出現的建築元素。在蒙兀兒帝國時期的各類型建築上,無論是城堡、陵墓、宮殿或是清真寺,我們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蹤影。如在阿格拉的城堡(Agra Fort,十六世紀)和泰姬瑪哈陵(Taj Mahal,十七世紀)以及德里的紅堡(Red Fort,十七世紀)和大清真寺(Jama Masjid,十七世紀),蒙兀兒拱式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顯然地,這種拱式不但由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兀兒帝國大量使用,更被其他非伊斯蘭信仰的印度人們所接受。如鄰近德里的齋普爾王國,其統治者雖然是傳統印度教徒,但其亦大量使用此蒙兀兒拱式作為各類型建築的裝飾。在王國首都齋普爾城(Jaipur,建於十八世紀初)我們即可明顯看到,無論是宮殿、印度教廟宇或是街屋,都有以此拱式的蹤影。而今日的印度,雖然蒙兀兒帝國的輝煌已成過去,但一般印度人們仍不掩其對蒙兀兒帝國拱式的喜愛,繼續以蒙兀兒拱式裝飾著各種新建的建築物。
同在世界貿易網路上的印度與中國泉州
這種印度蒙兀兒拱式和中國泉州等地所見到的拱式,有著極類似的特徵,它們的中心都是一組蔥形尖拱,其兩側亦搭配著一組至多組的連續對稱拱圈。基於印度蒙兀兒拱式出現的年代早於中國泉州拱式出現的年代,我們或許可以大膽推測,如同蔥形拱式藉由陸路由波斯輸入至印度,印度形成的蒙兀兒拱式有可能再藉由別的管道輸入至中國泉州。不過在下定論之前,我們仍須從貿易、文化或宗教的交流往來,檢視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諸如各種史料所證,全球的貿易活動在古老的年代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所熟悉的古代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串起了東亞、南亞、西亞至歐洲等地區,藉此,除了商品得以往來之外,各種的文化交流也隨之展開。而在這個貿易網絡中,印度正好位於中央的位置,我們可以想像,在漫漫的歷史中,印度文明的一切必定曾藉此網絡傳遞至其他地區,甚至包括中國,佛教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十六世紀之後,由於西方各國紛紛以強大的海上勢力至亞洲開拓市場,此古老的貿易網絡進一步被強化,許多印度的海港貿易城市亦隨之興起(Van Veen, 2005: 11-14)。就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在十七與十八世紀間,他們曾在印度東岸與孟加拉等地建立了十多個港口據點(Jacobs, 2006: 91-100)。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取而代之,成為對印度貿易的獨佔勢力,他們在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基礎上,設立了更多的港口據點,這些據點也在日後發展成重要的貿易城市,這些城市都非常有可能是印度蒙兀兒拱式輸出至泉州的源頭。
在中國方面,各種史料亦記載了泉州在中國與海外之商業與文化交流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十一世紀(宋代)的時候,官府甚至在泉州設立了市舶司,專管貿易稅收等事務(宋峴,2007: 159)。而從義大利的猶太商人雅各(Jacob D’Ancona)所著的《光明之城》(City of Light)中,我們更可以見到,宋末時期的泉州甚至有著義大利熱那亞人的商會,以及各種來自印度的商品(Jacobs, 2007: 235&282)。且宋代官府恐市內的外國人不易控制,更規定這些外國人不得居住城內,只能居住於鎮南門以外,這也因此讓泉州城南地區形成了外國人的集居地(戴泉明,2007: 62)。
到了十四世紀的元代,泉州已成為東亞最大的港口貿易城市。無論是從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或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的遊記中都可得知,泉州有著驚人尺度的大港,大港內停泊無法計數的船隻,泉州城內亦有著大量外國人的活動,以及各種外來的宗教。十五世紀的明代,當鄭和準備第五次下西洋時,他先來到泉州靈山的三賢與四賢伊斯蘭聖墓前行香,祈求神靈庇佑(宋峴,2007: 186),這也證實了伊斯蘭教在泉州的興盛。到了明末與清代,中國朝廷雖然實施海禁政策,但民間對外的私商貿易仍相當活絡(陳高華,2007: 27),十七世紀鄭氏家族的海上事業即為一明顯的例子。大批華人亦在明清年間,由泉州等地移居至台灣或東南亞,泉州自此也成為中國重要的僑鄉之一。簡而言之,自唐宋以後,無論朝廷的政策如何改變,泉州作為中國與海外交流的重要城市,其地位未曾改變。
位處同一個世界貿易網絡下的泉州與印度,其兩者之間的往來有著許多直接的證據。前述的伊本白圖泰,即是以印度穆斯林蘇丹的使節身分來到了中國泉州等地(李玉昆,2007: 141-142)。泉州市內更有著許多受印度文化影響所遺留下的痕跡,如在古老的泉州開元寺裡面,我們可以發現數根具有印度教風格的石柱。除此之外,大批與印度教有關的文物也陸續於泉州出土,如濕婆神(Shiva)的「宇宙之舞」(Nataraja)石刻,以及象徵濕婆神與其配偶結合的「林伽與約尼」(Linga & Yoni)石刻。我們甚至可以想像,當時在清靜寺(泉州最古老的清真寺)裡面作禮拜的人們,必定有大量來自印度的穆斯林。
在泉州落地生根的蒙兀兒拱式
據此我們已可大膽推論,泉州街屋上所觀察到的拱式,應是由印度傳入的蒙兀兒拱式。雖然泉州等地具有蒙兀兒拱式的街屋都出現在十八世紀以後,但從其它的證據可發現,蒙兀兒拱式傳入泉州的時間可能比十八世紀更早。透過泉州城南地區的考古挖掘,發現了許多以蒙兀兒拱式為造型的墓碑與墓蓋,它們的年代皆早於十八世紀,且證明了大量外國穆斯林與基督徒曾在泉州世居的事實。這說明了在蒙兀兒拱式確實是外國人帶入的外來形式,且在其運用於當地建築之前,即曾以其他方式出現。
除此之外,這也說明了在泉州的外國人,無論他們是來自哪裡,無論他們信奉伊斯蘭教或是基督教,都期望藉此外來形式以表達其外來的身分與宗教,區別他們和當地漢人的差異。這種藉蒙兀兒拱式作為自我認同的方式,在今日的泉州仍舊可見。例如在泉州清靜寺的明善堂(禮拜堂)裡面,人們即以蒙兀兒拱式裝飾著朝向麥加的牆面(Qibla Wall)。甚至在一些泉州穆斯林後代的新墓,蒙兀兒拱式仍是其主要特徵。
泉州城南除了是蒙兀兒拱式墓碑與墓蓋發現的主要地區之外,亦是此拱式運用於建築上最密集的地區,幾乎平均每兩、三間街屋,就有一間使用蒙兀兒拱式作為裝飾,也些地方甚至連續好幾棟房子都有這種裝飾。這也說明了,在泉州城南,蒙兀兒拱式首先運用於外國人的墓碑與墓蓋之後,亦逐漸運用於建築之上。一開始或許是外國人首先將此拱式運用於他們的住家裝飾上,隨後當地漢人亦起而仿效之,甚至此拱式再進一步傳至泉州周邊的各個城市與村鎮。至此我們仍須再討論一個問題:為何泉州當地的漢人肯接受這種代表不同身分與宗教的外來形式呢?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綜觀世界建築史,各種建築形式總是不斷地移植與融合。人們常常將某種形式帶至另一個地方,只要這些形式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財富、地位與權力上的優勢,或者反映出所欲追求的身分認同,當地人即往往會接納這個外來的形式,並將這個新形式融入既有的傳統之中。
泉州的漢人在十九世紀之前接納了來自印度的蒙兀兒拱式,其心態或許就類似於東亞各國在十九世紀末之後接納了來自歐洲的建築語彙。當十九世紀下半西方勢力大舉入侵東亞時,東亞的人們不得不接受西方人所帶來技術、制度與觀念,而使用歐洲的建築語彙,即可滿足他們追求進步以及對自身未來的想像。而在這些西方列強於十九世紀下半入侵東亞之前,最令泉州漢人所欽羨的,恐怕就是那些外國商人所帶來的財富,以及這些財富替他們帶來的地位與權力。對當時的泉州漢人來說,或許沒多少人能弄清楚蒙兀兒拱式究竟來自哪裡,但他們知道,這個形式足以代表著財富、地位與權力。華麗的蒙兀兒拱式不但容易模仿,更可滿足他們對未來的想像,這也是為何大部分的蒙兀兒拱式都出現在商人居住的街屋以及富裕的華僑所興建的洋樓上。此外,這種蒙兀兒拱式亦滲入漢人建築以外的領域,例如在泉州開元寺裡的部分石柱,即有著蒙兀兒拱式的雕刻。
這些案例述說著,蒙兀兒拱式已在泉州等地落地生根,成為當地漢人可以普遍接受的形式。對於泉州的穆斯林或是印度僑民來說,蒙兀兒拱式是自我認同的堅持,但對於泉州的漢人或返鄉華僑來說,卻是追求生涯成功的象徵。也因此這種跨越地區、族群與宗教的形式移植,非但沒有成為禁忌,反而豐富了此形式的意義內涵。
蒙兀兒拱式在世界各地的移植
既然此蒙兀兒拱式能夠千里迢迢地由印度傳至中國泉州,它自然也會透過各種管道傳至世界其他地方。如在鄰近印度的斯里蘭卡,我們即可見到由印度穆斯林移民所興建的清真寺上,使用著蒙兀兒拱式;除了清真寺,位於斯里蘭卡中部康提附近山區中的恩貝卡寺廟(裡面同時供奉著印度教神祇、當地神祇與佛陀)中,我們亦可以發現蒙兀兒拱式的蹤影,其並與斯里蘭卡的傳統龍形拱(Dragon Arch)相互結合。在印度東北喜馬拉雅山的另外一頭,這種拱式也跨越了地域與宗教的隔閡,成為藏傳佛教神龕的形式語彙。而在新加坡,隨著到此地的印度移民,這種蒙兀兒拱式也大量被使用在印度教廟宇或清真寺建築上。
除此之外,在遙遠的歐洲似乎也有著蒙兀兒拱式影響的痕跡。例如義大利的威尼斯,自中世紀開始即與東方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亦吸收了許多來自東方的事物,並反映在其當地的建築形式上。而在威尼斯眾多的街屋建築上,即大量出現類似來自印度的蒙兀兒拱式。然而比起其他地方,這種在威尼斯出現的拱式,卻更不容易釐清其形式的來源,因為歐洲自身存在著另一種強烈的拱式傳統-歌德式尖拱。
雖然蒙兀兒拱式上的蔥形尖不同於與歌德式尖拱(後者自最高點往下呈下凹的曲線),但在歐洲不少地方,我們仍可見到歌德式尖拱與蔥形拱式的混和呈現,如德國明斯特(Münster)聖保羅主教座堂(Sankt Paulus Dom,十三世紀)。我們也難以推測這種歐洲出現的蔥形拱式是發源自歐洲本身,亦或受到東方的影響,畢竟在1096至1291年間十字軍東征時,確實讓歐洲人從東方帶回許多事物。
再看幾座不同年代的威尼斯建築,如聖喬萬尼與保羅教堂(Basilica di Santi Giovanni e Paolo,十二至十五世紀)與公爵府(Palazzo Ducale,十四至十五世紀),它們上面所呈現的拱式更令人疑惑。究竟這些威尼斯街屋、教堂與公爵府上的拱式,代表的是歌德式尖拱的傳統?還是波斯蔥形拱式的傳統?還是印度蒙兀兒拱式的傳統?雖然我們無法在短時間內釐清這些問題,但基於歐洲與東方曾密切交流的歷史事實,至少我們可以保守地推測,這些威尼斯出現的拱式是各種東西方形式傳統混和後的結果,即便可能與十六世紀後出現的蒙兀兒拱式無關,但我們亦不能排除其或許與更早的波斯蔥形拱式有關。
在世界建築史裡,蒙兀兒拱式只是眾多形式移植故事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常常可以發現,某種特定的形式一開始可能僅出現於某地,或者同時出現於完全不相關的兩、三地。但透過人類的活動,這些形式將會被移植至不同地方,有些與當地形式產生衝突,但有些則被接納,進而與當地形式融合。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往往會賦予這些形式新的意義,無論是直接承襲舊的意義,或是疊加於舊的意義之上,甚至是完全取代舊的意義。而這種意義的增生與轉變,正是建築形式移植過程中必須探討的地方。
當蒙兀兒尖拱能夠跨越時空、跨越族群並跨越宗教被不同的人們廣泛使用時,或許我們應該意識到,建築裡沒有絕對的「本土形式」或「外來形式」。建築作為身分認同的投射或表現,則是流動而非固定的。而形式與意義之間,從未曾也將不會是永恆的等號。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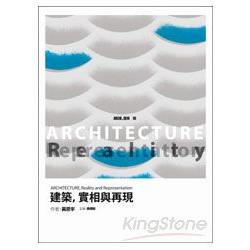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