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人以死亡做為根部
人就突然地安定下來
開始對自己有限的生命一有一分珍惜
甚至產生一種了斷的感覺
只有站在這種情況下去活
才是比較真誠的活。
死亡對每個人絕不是假設,更不是理論,而是無人可以逃避的事實。這原本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我們卻不曾真正認識這必然的命運在每人的身上會出現什麼景觀。一旦我們避問這「生死大事」,或不正視大限的必然性,我們就會像孤魂野鬼一樣,成天東飄西盪,找不到自己的根。
我們的生命史裡,其實是由一連串「進」、「出」所完成的,我們經歷過「入學」與「畢業」,我們找到新的工作,離開工作退休;我們結婚、離婚;我們戀愛與分手;而最大的「生死大事」則是終極的「進」與「出」。
人就突然地安定下來
開始對自己有限的生命一有一分珍惜
甚至產生一種了斷的感覺
只有站在這種情況下去活
才是比較真誠的活。
死亡對每個人絕不是假設,更不是理論,而是無人可以逃避的事實。這原本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我們卻不曾真正認識這必然的命運在每人的身上會出現什麼景觀。一旦我們避問這「生死大事」,或不正視大限的必然性,我們就會像孤魂野鬼一樣,成天東飄西盪,找不到自己的根。
我們的生命史裡,其實是由一連串「進」、「出」所完成的,我們經歷過「入學」與「畢業」,我們找到新的工作,離開工作退休;我們結婚、離婚;我們戀愛與分手;而最大的「生死大事」則是終極的「進」與「出」。
序/導讀
作者序
人的時間是直線地朝向死亡,但他的書卻進入了迴旋時間,隨著讀者的閱讀而決定它的生死;決定它的生死,與作者無涉。
多年前的作品再版,我決定說說它背後的故事,這是我從來未曾說過的。
三十幾年前(一九七七年吧?)我承宋公的慨允與安屯兄(編註:宋時選、劉安屯)的支持,將《張老師簡訊》改成《張老師月刊》,本來想做為輔導專業人員的雜誌,但是當時輔導人員不多,訂戶太少,無以為繼,遂改成生活心理雜誌,仿當年美國的”Psychology Today”,做了許多以問卷調查為主的專題。其間,一九八七年我赴美做博士後研究,一年待在柏克萊的人類學系,後來又承潘英海兄的引介轉往奧立岡大學人類學系,還赴大陸廣州做了幾個月的田野,覺得人類學方法頗能切近生活,所以在返國之後,著手將《張老師月刊》改編成深入台灣社會的生命故事。
就在改版的第一期,編輯們覺得好似少了什麼,要求我寫一篇刊頭文章,讓整本雜誌有個起身炮。結果一寫就寫了十年。每隔一段時間,出版總編王桂花覺得夠出一本書,就將之輯成冊。
剛從美國回到台灣,對台灣的生活感到十分厭煩,燥熱、吵鬧,加上時差的緣故,晚上完全無法入睡,身心備受煎熬。我只記得自己處在這樣的狀態中寫著刊頭文章,從中慢慢發現只有在寫刊頭文章的時候,心才安定下來。當時並不了解寫作做為療癒的意思,只知道在每個月的某段時間,我必須將自己沉潛下來,好好把五六千字的文章趕出來。透過這樣的寫作過程,我一片一片地掙脫掉對台北的厭煩。慢慢地,寫文章成為每個月某段時間固定的儀式,我可以在非常忙碌的狀態下把事情擱置、抽身,專心地寫稿;我的許多稿子可能是在候機室或是火車上寫就的,也可能是在某家咖啡館,甚至MTV的小房間也曾經變成我的書房。
曾經有書評批評這些刊頭文章只不過是一堆他人話語的拼貼圖樣,不怎麼有創意,但對我來說,串連別人話語對我卻深具意義。我對他人的經驗充滿好奇心,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經驗相當有限,在個人的能力範圍內不可能有這般多樣的人生體驗,所以必須倚靠閱讀他人經驗細細體會當中某些可能的脈絡。這就是一個非常富有療癒性的追索過程,主要是因為我對一些深刻的經驗相當敏感,無論這些人是哲學家、藝術家、詩人、作家,甚至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他們在自己的生命脈絡或在特殊事件機緣之下所說出令人感到心動的經驗描述,常常讓我有一種通電的感覺。每當遇到這些經驗敘說,我就忍不住將之擷取下來,用我的感覺將某份深刻性重新說一遍。所以也許某一句話在某本書上只是淡淡的一句話,但到了我的心裡頭卻成為閃耀的寶石,跟我內心裡的某個部分互相照映。
我想,可能因為內心過於黑暗吧!在寫作過程透過與他人經驗交互串連,我總感覺到亮晶晶的什麼在我的意象裡繞來繞去,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裡頭我才發現自身已然脫離現實世界,進入令人迷醉的文學空間。當初的我並不曉得這個文學空間的存在,直到後來讀到布朗肖(註)的文學空間,他提到,寫作之人常不自覺地跌宕至此神祕氛圍,布朗肖提到卡夫卡與里爾克幾乎都是活在異於現實的世界裡。當我讀完布朗肖的書,我才想起那個空間也正是我進行心靈療癒的場所。心理學領域也有閱讀或寫作治療,而這樣的方式具有效果的前提是跌宕進文學空間裡。我當然無法教導讀者如何跌宕進去的方法,對我個人而言,我可能是躺在床上發呆一段時間、在街上遊蕩,或者在書局瀏覽書籍,我從不預設主題,也從不知道將寫出什麼,只有等待感覺到了,五、六千字的文章自然汩汩而動。
我還記得當年寫這些文章時,一定要用台大的實驗紙,大約是八十磅,上面畫滿了細格子,加上一定要用我的鋼筆來寫,如果不是鋼筆,也一定要用細字的墨水筆,如果是滾珠原子筆就無法下筆。鋼筆在紙面上的滑動是引領我進入文學空間的一個小小旋轉軌道,只要我手握著鋼筆開始在紙上沙沙的滑動,就可以感覺到文學空間的魔力召喚,開始發揮它的作用,也就是一般所謂的靈感泉湧。原來我也不敢使用「靈感」這個詞彙,但在布朗肖的文學空間特有一章在談靈感,我才知道靈感確有其真實的意義──凝視著看不見的空間,那裡居住著寫作者的靈魂,感覺到文學空間存在的同時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或許我就是在這樣的時光中暫時地脫離生活中的苦悶,讓自己沉浸在這靈感的狀態。那麼,靈感就不是一種形容詞,而是一份道地的感覺,帶有深刻的詩意乃至哲學的味道,去除了凡俗間的懊熱、煩憂、操勞,乃至於焦慮、不安。
這是一個很弔詭的現象。我的編輯經常抱怨,只要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就會覺得寫不出東西,好像每個月的寫稿只會把文思榨光,常常寫完一個月的稿子卻不知下個月的文思在哪裡,不知該如何是好。當初並沒有察覺到是怎麼一回事,就讓編輯們多參與一些工作坊或研討會,或者鼓勵他們多讀點書。這樣的建議顯然對編輯並不足夠,甚至常因交不出稿子常常半夜驚醒、哭泣,充滿了焦慮不安。這對我來說相當不解,對我來說,我的經驗剛好相反,每次寫文章好像從疲乏的現實裡頭拾回一些活潑的感覺,寫作對我來講完全沒有負擔,甚至常常自願承擔額外的寫作量。
所以,寫作不一定會造成療癒,如果我們心中的文學空間依舊是緊閉的狀態,任何寫作都可能是最艱難的負擔或引起大量的焦慮。一旦文學空間打開,將會發現極大的快樂、舒服、感動,使得心情像潺潺的流水一樣,不斷地流著、流著,就這樣不知不覺寫了幾十本書,自己也從來不覺得在做苦工,甚至會覺得這是當年張老師文化賜給我的恩情。所以當年離開張老師文化之際,我把大部分書籍的版權都捐給張老師文化,如今張老師文化重新整理我的作品加以出版,說來說去,就說是文學空間帶來的殊緣吧。
人的時間是直線地朝向死亡,但他的書卻進入了迴旋時間,隨著讀者的閱讀而決定它的生死;決定它的生死,與作者無涉。
多年前的作品再版,我決定說說它背後的故事,這是我從來未曾說過的。
三十幾年前(一九七七年吧?)我承宋公的慨允與安屯兄(編註:宋時選、劉安屯)的支持,將《張老師簡訊》改成《張老師月刊》,本來想做為輔導專業人員的雜誌,但是當時輔導人員不多,訂戶太少,無以為繼,遂改成生活心理雜誌,仿當年美國的”Psychology Today”,做了許多以問卷調查為主的專題。其間,一九八七年我赴美做博士後研究,一年待在柏克萊的人類學系,後來又承潘英海兄的引介轉往奧立岡大學人類學系,還赴大陸廣州做了幾個月的田野,覺得人類學方法頗能切近生活,所以在返國之後,著手將《張老師月刊》改編成深入台灣社會的生命故事。
就在改版的第一期,編輯們覺得好似少了什麼,要求我寫一篇刊頭文章,讓整本雜誌有個起身炮。結果一寫就寫了十年。每隔一段時間,出版總編王桂花覺得夠出一本書,就將之輯成冊。
剛從美國回到台灣,對台灣的生活感到十分厭煩,燥熱、吵鬧,加上時差的緣故,晚上完全無法入睡,身心備受煎熬。我只記得自己處在這樣的狀態中寫著刊頭文章,從中慢慢發現只有在寫刊頭文章的時候,心才安定下來。當時並不了解寫作做為療癒的意思,只知道在每個月的某段時間,我必須將自己沉潛下來,好好把五六千字的文章趕出來。透過這樣的寫作過程,我一片一片地掙脫掉對台北的厭煩。慢慢地,寫文章成為每個月某段時間固定的儀式,我可以在非常忙碌的狀態下把事情擱置、抽身,專心地寫稿;我的許多稿子可能是在候機室或是火車上寫就的,也可能是在某家咖啡館,甚至MTV的小房間也曾經變成我的書房。
曾經有書評批評這些刊頭文章只不過是一堆他人話語的拼貼圖樣,不怎麼有創意,但對我來說,串連別人話語對我卻深具意義。我對他人的經驗充滿好奇心,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經驗相當有限,在個人的能力範圍內不可能有這般多樣的人生體驗,所以必須倚靠閱讀他人經驗細細體會當中某些可能的脈絡。這就是一個非常富有療癒性的追索過程,主要是因為我對一些深刻的經驗相當敏感,無論這些人是哲學家、藝術家、詩人、作家,甚至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他們在自己的生命脈絡或在特殊事件機緣之下所說出令人感到心動的經驗描述,常常讓我有一種通電的感覺。每當遇到這些經驗敘說,我就忍不住將之擷取下來,用我的感覺將某份深刻性重新說一遍。所以也許某一句話在某本書上只是淡淡的一句話,但到了我的心裡頭卻成為閃耀的寶石,跟我內心裡的某個部分互相照映。
我想,可能因為內心過於黑暗吧!在寫作過程透過與他人經驗交互串連,我總感覺到亮晶晶的什麼在我的意象裡繞來繞去,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裡頭我才發現自身已然脫離現實世界,進入令人迷醉的文學空間。當初的我並不曉得這個文學空間的存在,直到後來讀到布朗肖(註)的文學空間,他提到,寫作之人常不自覺地跌宕至此神祕氛圍,布朗肖提到卡夫卡與里爾克幾乎都是活在異於現實的世界裡。當我讀完布朗肖的書,我才想起那個空間也正是我進行心靈療癒的場所。心理學領域也有閱讀或寫作治療,而這樣的方式具有效果的前提是跌宕進文學空間裡。我當然無法教導讀者如何跌宕進去的方法,對我個人而言,我可能是躺在床上發呆一段時間、在街上遊蕩,或者在書局瀏覽書籍,我從不預設主題,也從不知道將寫出什麼,只有等待感覺到了,五、六千字的文章自然汩汩而動。
我還記得當年寫這些文章時,一定要用台大的實驗紙,大約是八十磅,上面畫滿了細格子,加上一定要用我的鋼筆來寫,如果不是鋼筆,也一定要用細字的墨水筆,如果是滾珠原子筆就無法下筆。鋼筆在紙面上的滑動是引領我進入文學空間的一個小小旋轉軌道,只要我手握著鋼筆開始在紙上沙沙的滑動,就可以感覺到文學空間的魔力召喚,開始發揮它的作用,也就是一般所謂的靈感泉湧。原來我也不敢使用「靈感」這個詞彙,但在布朗肖的文學空間特有一章在談靈感,我才知道靈感確有其真實的意義──凝視著看不見的空間,那裡居住著寫作者的靈魂,感覺到文學空間存在的同時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或許我就是在這樣的時光中暫時地脫離生活中的苦悶,讓自己沉浸在這靈感的狀態。那麼,靈感就不是一種形容詞,而是一份道地的感覺,帶有深刻的詩意乃至哲學的味道,去除了凡俗間的懊熱、煩憂、操勞,乃至於焦慮、不安。
這是一個很弔詭的現象。我的編輯經常抱怨,只要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就會覺得寫不出東西,好像每個月的寫稿只會把文思榨光,常常寫完一個月的稿子卻不知下個月的文思在哪裡,不知該如何是好。當初並沒有察覺到是怎麼一回事,就讓編輯們多參與一些工作坊或研討會,或者鼓勵他們多讀點書。這樣的建議顯然對編輯並不足夠,甚至常因交不出稿子常常半夜驚醒、哭泣,充滿了焦慮不安。這對我來說相當不解,對我來說,我的經驗剛好相反,每次寫文章好像從疲乏的現實裡頭拾回一些活潑的感覺,寫作對我來講完全沒有負擔,甚至常常自願承擔額外的寫作量。
所以,寫作不一定會造成療癒,如果我們心中的文學空間依舊是緊閉的狀態,任何寫作都可能是最艱難的負擔或引起大量的焦慮。一旦文學空間打開,將會發現極大的快樂、舒服、感動,使得心情像潺潺的流水一樣,不斷地流著、流著,就這樣不知不覺寫了幾十本書,自己也從來不覺得在做苦工,甚至會覺得這是當年張老師文化賜給我的恩情。所以當年離開張老師文化之際,我把大部分書籍的版權都捐給張老師文化,如今張老師文化重新整理我的作品加以出版,說來說去,就說是文學空間帶來的殊緣吧。
訂購/退換貨須知
購買須知:
使用金石堂電子書服務即為同意金石堂電子書服務條款。
電子書分為「金石堂(線上閱讀+APP)」及「Readmoo(兌換碼)」兩種:
- 請至會員中心→電子書服務「我的e書櫃」領取複製『兌換碼』至電子書服務商Readmoo進行兌換。
退換貨須知:
- 因版權保護,您在金石堂所購買的電子書僅能以金石堂專屬的閱讀軟體開啟閱讀,無法以其他閱讀器或直接下載檔案。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不受「網購服務需提供七日鑑賞期」的限制。為維護您的權益,建議您先使用「試閱」功能後再付款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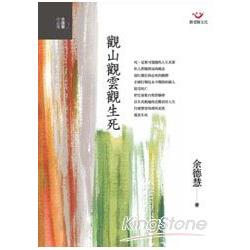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