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否定的日本: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
內容簡介
當我「說」日本,你「聽」到了什麼?
近代以來的中國與日本,同被西方之沙入侵,那一刻的痛楚,是否諭示著珍珠的生成?亦或整個東亞建立自我認同的神話,只是一道「心無外物,相由心生」的偈語?
本書意圖將理論思考滲入個人經驗中,從竹內好的「日本之否定」到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從止庵、陳子善等人對竹久夢二不假思索的推崇到浮世繪、歌舞伎、動漫亞文化的當代顯影,從大正畫家的夢幻耽美到昭和作家的海外情殤,從小林正樹的電影到三島由紀夫的小說,從台海兩岸幾代文化人的日本迷思到全球化時代東亞青年的「印象聯盟」,你和我眼中,究竟有幾多日本、幾重自我?將這些夢的因數掰開揉碎,來重建一個通往現代性,「戰後」、東亞、文化、政治的「日本」幻想式言詞之旅。
本書分上下篇,上篇為「否定的辯證法」,從「主體與行動」的辯證法討論竹內好的「日本否定性」,以及從「鬥爭」概念入手檢視柄谷行人的價值光譜,以此揭示近代日本是如何在戰後的東亞知識群體中被歷史/反覆地重構出來的;下篇為「想像的日本性」,通過梳理兩岸當代文學/文化與日本想像之間的互相觀看,反射出兩岸文化知識人對日本認知的「鏡中之旅」的光與影。
目錄
前言 作為「他者之謎」的日本
序論 進入歷史的方式
壹、題解
雙重失敗:進入歷史之前
「時代」的構型
一、失落的主語:以《平山冷燕》為鏡
二、謂項的造反:混亂‧自由
三、謂項的統理之一:國家與士
四、謂項的統理之二:旅行與家國
五、主語還是飾詞:浮世‧危機‧無常
結語 《高野聖僧》─時代,這隻苦惱的蝴蝶
上篇 否定的辯證法
貳、主體與行動:竹內好的辯證法
一、種與屬:「前進的歐洲─後退的東洋」
二、 主體的「不可能」性:竹內好、溝口雄三、柄谷行人的視點問題
三、情感與謬誤:(比想像)更抽象、更堅固的辯證法
四、竹內好與三島由紀夫:全面反撲與偏移 離題的結語
參、鬥爭的現場:沿著柄谷行人的價值光譜
一、題解「起源」
二、光譜正向的「戰鬥」
三、光譜負向的「顛倒夢想」
結語 批判的歸宿與相對層面的時態悖論:顛倒、涅磐與短路
下篇 想像的日本性
肆、「想像」三輯
一、作家之旅─追跡「魯迅」:雷驤/李銳
二、學者之旅─原鄉‧傳統:林文月/陳平原
三、羈留者言─人情日本:毛丹青/張燕淳
結語 家園與畫面
橋樑與印象聯盟:全球化與後現代
一、橋樑:大陸「知日派」的文化姿態
二、 日本人?臺灣人?茂呂美耶與新井一二三的全球化背景
三、文化主權政治:兩岸「80後」的日本文化印象聯盟
結語 夢魘與夢幻
參考文獻
序/導讀
前言
作為「他者之謎」的日本
本書是我這兩年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與師友之間學術交流以及個人理論閱讀的副產品。分為序論和上下兩輯,序論以近代中國和日本的幾個小說文本為媒介,討論一種進入歷史、反觀自我的方法,上輯主要是以竹內好和柄谷行人為中心,處理他們和中國學人之間思想資源及問題意識的重合與分歧。近年來,中國學界對「竹內魯迅」和日本著名後結構主義批評家柄谷行人的討論恰好達到了某種飽和度,似乎不再有新的話題,而我自己對「東亞」和「日本」問題多年來的關注和閱讀,卻並非源自學界的問題意識,倒是更多根源於少年時期大量閱讀日本文學和漫畫的經驗,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讓我很懷疑自己的文化身分。東亞視域似乎是學界討論中日問題的基本共識,但要等到孫歌提出了「為什麼談東亞」,才發現這一共識的基礎其實並不那麼牢靠,其間還存在不少的縫隙。這引起了我對「日本」更進一步的反思。如果說,那些被靜置許久的有關受害、沉默和重寫歷史的重大問題,可以通過「東亞」攪動起來,那麼東亞視域中的「日本」則更加能夠觸動整個亞洲漢文化圈的末梢神經。如果說「為何談東亞」問題的提出是因這一範疇對中國人文學界的有效性確實需要進一步論證,那麼「為何談論日本」,倒是一個十足的偽問題了。且不說我們不可能離開這個日本來談論19世紀以降中國革命與現代性的遺產與負債,細觀今日中國文化語境,從最「通俗」的網路文學、大眾傳媒,到高蹈的學術研究、大學院牆內的文化生活和日益窄化的「純文學」,乃至於「嚴肅」的政治思想、哲學議題,哪裏不是早已滲透了日本的「聲音碼」和「表情符」?
在這裏,我首先要談的是作為「他者之謎」的日本。
日本推理小說家京極夏彥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天,一隻鶴飛來,一個愛奴人(過去居住在日本北海道、樺太等地區的原住民族)一看到牠就落荒而逃,因為這個民族認為鶴是恐怖的禽鳥,而同樣看到牠的和人(大和民族)卻興高采烈,因為鶴在和人的傳統中是吉兆。
說開來是如此簡單,和人和愛奴人卻認為彼此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謎。儘管實際發生的,就只有「鶴飛來了」這一件事而已。
對東亞近現代史的起點來說,實際上發生的,也就只有「西洋入侵」這個事實而已,然而,圍繞著個事實,卻衍生了那麼多的夢魘與夢幻。中國、日本、朝鮮……無論哪一個民族國家主體,所繼承的都不僅僅是同一個事件的持續性後果,而是大相徑庭的現代視域。當聽說「東洋被入侵」時,不同的主體腦中可能會呈現出「黑船來襲」(日本)、「虎門硝煙」(中國)、「魯迅的幻燈片事件」等完全不同的視覺圖像和文字表述。─然而,這樣單一的歷史事件,只能以隱喻的形式象徵著「整體的」歷史進程。事實上,我們從來無法在同一平臺上、以同一種視鏡去觀察和講述「大東亞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和「支那事變」等等─它們早已被表徵為不同的能指。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和丸川哲史都曾指出,日本投入了如此驚人的資源陷入全面戰爭的深淵,最終也只能名之為「事變」,這一反差的重量是非日本人難於度量的。因此,身為中國人的我們,自然無法簡單地因竹內好曾賦予這一「事變」以革命的光澤而對「竹內魯迅」的價值提出質疑。然而,也許正是因為各自立場不同,對彼此的不斷闡釋才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當木山英雄研究在淪陷的北京陷入「附逆」悲劇的魯迅之弟、散文家周作人時,他正是以日本人和後來人身分的艱難立場來遙感周彼時彼地尷尬難解之心情的。
同樣,在20世紀30年代日軍佔領形勢日趨嚴峻的北京,對日本文化有著刻骨之愛和切膚之痛的「知日家」周作人艱難地寫出了一系列「日本管窺」散文,然而其在兩國交戰之際試圖雙方向地理解和溝通的文化努力卻遭受到了時代的沉重挫壓。在1937年的《管窺之四》中,他終於寫道,「日本人的宗教性格」可以用其常年舉行的神道儀式中抬神輿的青年壯丁「神人合一」的行進狀態為象徵。周的意思是,那終究是與中國人性格完全相異之物─理解「他者」的努力,最終不能不以「不可理解」為句點。與其說真的「不可理解」,不如說是「不允許進一步理解下去」。周從此關上了「日本研究小店」,走上了世人眼中可悲可鄙的「附逆」之路。
無獨有偶,戰後「極右主義」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也一直困擾於「抬神輿的壯丁」的神秘。儘管是日本人,三島卻一直為那個彷彿從遠古走來的、有著酩酊的眼神和腳步的強壯、赤裸的男子群體而著迷和困惑:他們在想什麼?映現在他們眼中的天空是怎樣的?三島一生都把這個意象留在視網膜中,他的小說作品,乃至他的政治立場和行動,都是為瞭解開自我與他者、與世界之謎而做的努力。誠如柄谷行人所說,不理解三島的文學作品和他在戰後6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行動(包括組織青年右翼團體「楯會」、與「全共鬥」的政治演說、在自衛隊「志願實習」、最後與楯會成員一起策謀挾持自衛隊官員、發表演說後切腹自殺),就不可能理解戰後日本的思想和文化形態。周作人一生文名陷於「附逆」,而三島以切腹為45歲生命的終局,在世人眼中,皆為「不合時宜之時所作的不合時宜之事」,中間橫亙的,不正是「他者之謎」麼?
他者是謎,是自我眼中的一道風景。令周作人和三島陷入某種「命運」中的「他者」的象徵,不論是作為交戰雙方的國家間彼此隔膜的證據,還是知識分子與沉默的大眾之間的鴻溝,真正發生的,也只是「鶴飛來了」(在這裏則是抬神輿的隊伍走來了)這一件事而已。
然而,離開了彼此,我們誰也無法僅在自身脈絡裏清點歷史的遺產和債務。在「東亞漢文化圈」中,日本和中國都是彼此最特別的鏡像,無論是竹內好、溝口雄三以中國、亞洲為方法反觀日本的「西洋之內在化」,還是身為後馬克思主義者的柄谷行人對「資本制市場經濟、民族、國家」這一「三位一體的圓環」之批判,都是圍繞著「他者之謎」展開的。
第二輯,這個「謎」的引線換成臺灣與大陸「兩岸」,其媒介則是日本。在「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歷史進程中,臺灣一直是「中國」內部的一個他者。它既是日本「亞洲主義」思想的外延地帶,又是中華文明「天下」情結的地理邊境和想像中心。本輯中,大陸、臺灣、日本,不同的文化主人公在尋找「東方文明」自我持存的價值時,各自不同的心理軌跡交織纏夾,投射出迷人而曖昧的映象,如溫庭筠的詞,「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這裏的難點是,鏡像不是一個完滿的、客觀的呈像,這其中既有時差(time-leg),也有視差(parallax view)。
本書上輯對溝口雄三批判竹內好的不滿之處,蓋在其沒有認識到視差的存在。而「視差」乃是柄谷行人的主要發現之一,這位後學思想家的創造力,很大部分體現在他的「時空辯證法」之中。在《歷史和反覆》中,柄谷強烈地關注「斷代」問題。他問道:為什麼在日本會有「昭和初年代」、「昭和十年代」這樣固定的說法,而沒有「昭和四十年」?在這些常識化的範疇背後,是什麼機制在運作?日本的「大正時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同一時代,然而,儘管日本人對每一段歷史都很熟悉,但有多少人曾把它們放在一起來同時思考呢?正是從這些「時差」與「視差」中,他看到了語言-歷史結構的可替換性,也看到了現代性的歷史中無止境的福禍交替。
從宏觀到微觀,視差隱藏在話語的各個層面。比如,時至今日,全球一體化中民族國家的區域效應仍然強烈地燃燒,東亞各國所感受到的「戰後」之不平等秩序,並不僅僅在國際政治的層面運作。在歐美獲得了「世界級藝術家」殊榮的畫家村上隆對此深有體會:日本的當代藝術在本國並不被視為藝術,除非它們獲得了美國和歐洲的承認─也就是世界的承認。他繼而發出驚人之語:日本並非處於「戰後」,而是「一直在戰敗」。這種失敗文化的精髓,就寄存在日本獨有的動漫御宅族(OTAKU)文化之中(從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到空知英秋風靡亞洲的動畫片《銀魂》,都滲透著這種「失敗」),然而,也正是在這種「自我否定」的文化中,日本才可能不是「美國的附屬物」,而成為「日本」之「日本」。
這個不懂「理論」的藝術家的概括,與半個多世紀前的竹內好對日本的「否定之否定」,不正可謂一脈相承麼?然而與村上的觀點產生共鳴的,想必並不是國內學界中進行竹內好研究的學者們,而恰恰是80後、90後的動漫御宅族。在某種意義上,戰後日本的歷史態度與文化精神的本質,比起專門的思想討論和「純文學」領域,就寄生在「動漫亞文化」裏,棲息在「御宅族」的文化產品和生活形態之中。這種精神通過網際和人際的交流而不斷地播散,形成一種「印象聯盟」,讓不同國家的同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共鳴。表面上只是流行的風,而其內在所網結的歷史、哲學和倫理的脈絡之深廣,恐怕早已超出了某些學者的「想像範圍」。正因此,學術研究不應被固定的題材所拴繫,而應隨思想所遷動,這也是本書下輯所要揭示的。
在狹義的政治層面,本輯也涉及到70年代以後日本的「文化輸出」戰略,即通過全球化市場分工給東亞各國帶去產業發展,以經濟之蜜療文化之痛。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而言,某種「文化滲透」在其初始階段(80年代)潛伏多年,一直處於實有但未命名的狀態,後來,隨著80、90後主體的生長,其影響就開始浮出水面,在他們書寫的文學作品中,呈露著鮮明的「日本表情」,而文學也早已與流行文化融為一體。日本動畫片《搞笑漫畫日和》、《銀魂》等在高中和大學青年群體中造
訂購/退換貨須知
購買須知:
使用金石堂電子書服務即為同意金石堂電子書服務條款。
電子書分為「金石堂(線上閱讀+APP)」及「Readmoo(兌換碼)」兩種:
- 請至會員中心→電子書服務「我的e書櫃」領取複製『兌換碼』至電子書服務商Readmoo進行兌換。
退換貨須知:
- 因版權保護,您在金石堂所購買的電子書僅能以金石堂專屬的閱讀軟體開啟閱讀,無法以其他閱讀器或直接下載檔案。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不受「網購服務需提供七日鑑賞期」的限制。為維護您的權益,建議您先使用「試閱」功能後再付款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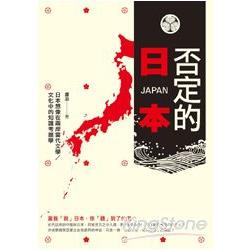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