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用閱讀開啟視野,讓書成為照亮你人生的光
【金石堂選書】本月推薦您這些好書👉 快來看看
內容簡介
當藝術家遇到哲學家,會擦出什麼火花?
書中兩位主角Simone及Andrea,遊走於法國、蘇格蘭、荷蘭、台灣及香港等地的博物館、美術館。她們所討論的九位藝術家,包括達利、羅丹、孟克、康丁斯基、梵谷、莫?、達文西、畢加索及安迪華荷,都是伴隨及促成著藝術歷史發展的不朽人物,他們高低起伏的人生經歷、輝煌成就,所留下的曠世作品與他們的獨特個性及睿智聯為一體,豐富了我們的生命。
每一個藝術家都有一個感悟題材
歷史上的藝術家都在其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肩負起各自的生存狀態,究竟他們在想甚麼?或許就是要尋找生命的依據。他們不停創作,利用他們不同風格的繪畫或其他藝術語言去表達心中情感、探索生命。每一次創作,都是一種選擇,但是否「非如此不可」,就確實難定答案,又或許一切都只是一個偶然。
其實藝術家、藝術作品與觀者的關係在詮釋的過程當中甚為微妙,這是一場心智遊戲。藝術家就有如魔術師,在其作品加添法力,為世界?添色彩;而我們也可以通過自我的創造力量,將自己的生活塑造成為一件藝術品,積極體驗生命的真正意義。
何為藝術?藝術的本質是甚麼?藝術有甚麼意義、功能?甚麼是真正的藝術作品?藝術的真理又是甚麼?藝術品的美與不美、價值高與低? 管它的,觀者要關注的是藝術家們在這些藝術品中留給我們甚麼,在我們生命起了甚麼功能、甚麼作用、甚麼意義。
法國哲學家沙特曾經節錄英國哲學家培根的話:「人就是人的未來」,人是以每個時代的生活狀況不斷重新創造自己的歷史;而 「未來就是在過去的時代中找到」,希望這本書為你帶來一個愉悅而具啟發性的精神之旅。
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亦肯定不是甚麼嚴肅正規的藝術哲學書。這是一本藝術欣賞、品味生活的入門通識書。
書中兩位主角Simone及Andrea,遊走於法國、蘇格蘭、荷蘭、台灣及香港等地的博物館、美術館。她們所討論的九位藝術家,包括達利、羅丹、孟克、康丁斯基、梵谷、莫?、達文西、畢加索及安迪華荷,都是伴隨及促成著藝術歷史發展的不朽人物,他們高低起伏的人生經歷、輝煌成就,所留下的曠世作品與他們的獨特個性及睿智聯為一體,豐富了我們的生命。
每一個藝術家都有一個感悟題材
歷史上的藝術家都在其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肩負起各自的生存狀態,究竟他們在想甚麼?或許就是要尋找生命的依據。他們不停創作,利用他們不同風格的繪畫或其他藝術語言去表達心中情感、探索生命。每一次創作,都是一種選擇,但是否「非如此不可」,就確實難定答案,又或許一切都只是一個偶然。
其實藝術家、藝術作品與觀者的關係在詮釋的過程當中甚為微妙,這是一場心智遊戲。藝術家就有如魔術師,在其作品加添法力,為世界?添色彩;而我們也可以通過自我的創造力量,將自己的生活塑造成為一件藝術品,積極體驗生命的真正意義。
何為藝術?藝術的本質是甚麼?藝術有甚麼意義、功能?甚麼是真正的藝術作品?藝術的真理又是甚麼?藝術品的美與不美、價值高與低? 管它的,觀者要關注的是藝術家們在這些藝術品中留給我們甚麼,在我們生命起了甚麼功能、甚麼作用、甚麼意義。
法國哲學家沙特曾經節錄英國哲學家培根的話:「人就是人的未來」,人是以每個時代的生活狀況不斷重新創造自己的歷史;而 「未來就是在過去的時代中找到」,希望這本書為你帶來一個愉悅而具啟發性的精神之旅。
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亦肯定不是甚麼嚴肅正規的藝術哲學書。這是一本藝術欣賞、品味生活的入門通識書。
試閱
5
表現主義先驅:梵谷
當Simone與Andrea完成圓滿的愛丁堡之旅後,腦中還纏繞著「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的「裊裊餘音」,她們的下一站行程,就決定計劃探訪影響孟克及康丁斯基至深的靈魂人物――表現主義先驅、荷蘭藝術家梵谷。
一提起荷蘭,腦海中就立即出現向日葵、梵谷、風車、木屐等景象。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處非常自由的城市,它既是荷蘭首都,亦是荷蘭的文化之都。荷蘭盛產世界級畫家,包括巴洛克時期的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1606-1669)、後印象派的梵谷,還有幾何抽象派畫家蒙德里安。到訪荷蘭的藝術愛好者亦可欣賞荷蘭的人文風景及藝術歷史足跡,感受到荷蘭當代藝術的自由及富生命力的一面。
Simone與Andrea此行的目的是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館(Van Gogh Museum)。博物館於1973年成立,是收藏及擁有梵谷畫作最豐富的美術館。館內收藏梵谷二百餘幅的油畫、五百多幅的素描和七百多封私人書信等,包括梵谷由最初的荷蘭時期、巴黎時期、亞耳時期直至聖雷米、奧維爾時期的大部份名作。每年專程到荷蘭朝聖的人數以千萬計。
梵谷是牧師之子,他的叔叔是畫廊合夥人,弟弟提奧(Theo Van Gogh,1857- 1891)既是他的知心密友、經理人,亦是他的精神及經濟支柱。在他短暫的人生中,梵谷學懂多國語言包括法語、德語及英語,也學習了基本的繪畫技巧;他曾當過藝術品交易公司的見習員、教師,後也當過傳教士,向貧困的採礦工人傳教,直到大約27歲時,即1880年,梵谷才開始他的畫家生涯。在他生前的最後十年間,卻創作了超過二千幅畫,包括約八百多幅油畫與一千多幅素描,當然還有許多水彩畫、版畫等。可惜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只賣出過一幅畫,反而在他死後,他的作品如《星夜》(The Starry Night)、《向日葵》(Sunflowers)等傳世經典,卻是天價難求。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就這樣說過:「他生前沒人看得起,死後無人買得起。」非常諷刺,但這是現實。在決定畫畫之後,梵谷在荷蘭閒待了5年(1880-1885),隨後赴法國(1886-1888),在巴黎那段時間,他致力學習、創新及嘗試。從1886 年春開始,與弟弟提奧一起住在蒙馬特(Montmartre)的藝術區。1888年2月,他厭倦了巴黎喧鬧的生活,搬往南部小鎮亞耳(Arles),追尋明亮的陽光,期間創作了不少名作,如《梵谷的房間》,在這時期,他特別喜愛黃色。1889年4月,梵谷主動到亞耳附近的聖雷米鎮(St-Remy-de-Provence)一所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1890年5月,梵谷定居於奧維爾(Auvers-sur-Oise)這座鄰近巴黎的藝術村,作品多表達不安的情緒,《麥田群鴉》(Wheat Field with Crows)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1890年7月27日,他朝自己胸部開槍,兩天後去世,而提奧亦於梵谷死後半年去世,兄弟倆同被葬在奧維爾墓地內。
Simone與Andrea在第二天清晨乘坐路面電車出發至梵谷博物館,路面電車是當地市民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非常方便。只消十多分鐘的車程,她們已經到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
梵谷博物館共有四個樓層,二樓主要展出梵谷油畫,畫作是依照他不同時期的居住地方來展示。若有意深入瞭解,可跟樓下服務台租用導覽設備Audio guide。跟著導覽的指示,可以對他的作品及創作時的心境有更透徹的瞭解。打算計劃參觀梵谷博物館的朋友,最好預先進行網上登記,以減省排隊購票的時間。期待已久的「朝聖」旅程即將開始。
梵谷與高更:友誼容不下,悲劇一觸即發
S:這幅畫你又有何看法?
A:這幅《高更的椅子》(Paul Gauguin’s Armchair),有著高雅絨布座墊,紅綠相配,椅子寬敞精細,而椅上更放著點燃的蠟燭和兩本書,還有一盞煤氣燈。
S:我記得我在英國倫敦看過另一張畫,《梵谷的椅子》(Vincent’s Chair with his Pipe),椅子木質簡陋,較為粗糙,椅子上放著煙斗和煙葉,顏色以黃藍為主,非常簡樸。這兩張畫的故事背景是這樣的:當梵谷在1888年2月赴亞耳旅居後,他邀請好友高更10月來訪,而這兩幅椅子畫作是梵谷在1888年11月作的,從他畫出的《梵谷的椅子》及《高更的椅子》,你已略知他們兩者性格的差異。
A:依我看,兩張椅子,見證了兩種不同的性格:梵谷是較著重精神層面,而高更則較世俗。一個浪漫認真,是防守內向型;而另一個則原始不羈,是進攻外向型,本來一正一負,應是最佳組合。奈何高更卻逼出一個潛藏毀滅爆炸力的梵谷。S:他倆相識,原本的美意是相互切磋交流,可惜最後卻釀成無以彌補的傷痛。割席收場或許是必然的結局。朋友相交,很在乎大家的腦電波是否相符,就如你我。
A:幸好我們也肯互相遷就。其實「找」朋友與「交」朋友是兩碼子的事,也許梵谷搞錯了。但朋友爭拗可以刺激大腦思維,未嘗不好,只是梵谷過分執著。
S:顯然他對高更期望過高,將自己的價值完全寄托在他身上,這就出事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越把高更放得無上至高,自然不知不覺間把自己擺得低下卑微,連自我認同的價值也失去了。 而情況一旦逆轉,他則無法承受那股巨大的張力,失控如同他所說的「通了高壓電」,就崩潰了。梵谷的心靈其實非常脆弱。
A:其實我們交朋友也許決定我們的一生……說實在的,圍繞我們身邊的朋友,他們是天使或是魔鬼,真的不走至最後,難言對錯。
S:又或者命該如是,逃不得。他與高更的相遇,已逐步將他迫上絕路。
A:悲劇的發展總是遵循一個軌跡,一個命數。
S:梵谷對高更的執著,或許近乎病態,這卻是事實。如果一方受另一方的影響太大,以對方為全部,以對方的觀念意向判準為自己的全部所有,一旦一方被「遺棄」或被「打下去」的時候,弱勢的一方自然會潰不成軍,無力前行。
A:認真就會輸,特別在感情方面,悲劇一觸即發。
自畫像的精神呈現:為自己賦予一種存在價值
S:你是否記得一幅梵谷《綁繃帶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and pipe)? 那是1888年12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梵谷與高更吵鬧激烈,他們爭吵的內容沒有人知道,之後高更走了,當天晚上梵谷就用刮鬍子的刀割傷了自己的耳朵,從此兩個人沒有再見過面,而梵谷就畫了那幅自畫像,受傷的耳朵上還包著紗布,叼著煙斗,完全反映了他的惘然。
A:相信他的失控,是他的自尊及自我形象受損。他要自我毀滅,要他的身軀與靈魂逐步在這世界引退,宣洩他在世的不受認同。聽說他割掉的是左耳,是嗎?為何在畫中是右耳?
S:因為他總是看著鏡中的自己作畫,所以畫中的是右耳。其實每個人都需要認同感。梵谷對高更的憤怒和失望等負面情緒,轉為向他自己的身體宣洩。A:可能最初梵谷對高更的依戀是源於自戀,他選擇了高更,完全是出於自戀心理。當高更無法符合他的許多期望時,他的怒向內轉,朝向自己。這種內轉,令他時常怨怪自己,終至自虐。高更是他的一面鏡子,他要放棄的其實可能就是他自己。
S:這個說法也有可能。其實朋友的一切交往,都有種神秘不可超越的藩籬,不同朋友有不同的界限,但這界限卻是模糊難辨的。
A:有時衝突就在某方想突破或超越這個界限,一觸及這脆弱的防守線距離,便引起相互排斥或反感,一旦理智維持秩序,其中一方必定開始引退,心靈也再沒有溝通的餘地。梵谷與高更的交往也如是。所以如果大家價值觀不一樣,最好就是盡快止蝕離場。
S:代價或許太大了。
A:但其實我們每天都會遇上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將我們帶到不同的境界,所以我們每分每秒都在變,變成不再是以往的「舊人」,而是另一個「新人」。所以我們每時每刻都是個棄「舊」立「新」的新人。
S:但從好的角度看。與高更的邂逅,確實給梵谷帶來了不少的啟迪及靈感,啟蒙了梵谷的藝術路,這是不能否定的。高更迫出梵谷自己潛藏的張力,影響他在畫的創作,在色彩、在結構等方面的運用,而梵谷亦確信高更給了他不少啟發。他倆的相遇,在藝術歷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A:梵谷身上燃燒著激情的細胞,你看這邊,他還有很多自畫像,似是需要一種另類的自我肯定。
S:他的自畫像系列大多在巴黎完成,數量有三十多幅。你知道嗎,自畫像是西方人文主義文明的一種產物,第一幅自畫像約在1485年出現,由意大利畫家所作。
A:依我看來,自畫像是展示個人的一個符號,一個表徵,宣示了主體自我個人的誕生,為自己賦予一種存在價值,就像我們現在的selfie自拍一樣。
S:在療養院期間,梵谷畫了多幅自畫像,你記得我們在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見過的一幅,全幅交織著綠色線條,面容緊繃,雙眉鎖緊,兩唇緊閉。從梵谷的自畫像,亦看出他精神層面及他自視的一點端倪。
A:還記得他那憂鬱的眼神斜視,帶點警覺,卻帶點呆滯,亦帶點不安,展現一種無人理解的孤獨。
S:像是幽靈般冷眼看世界。A:古典哲人當中,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傑出哲學家、政治家、詩人、劇作家、藝術家均受憂鬱所苦。其實你認為創意與精神疾病有沒有關聯?藝術家都有精神分裂與躁鬱症嗎?究竟精神疾病對這些天才來說是助力還是阻力?
S:你有興趣可以看看心理學家兼神經學家Nancy Andreasen的The Creating Brain:The Neuroscience of Genius,這本書可為你所有問題提供了事實的答案。Nancy認為創意與精神疾病是沒有太大的關聯性的。但他的《星夜》(The Starry Night)卻折射出梵谷的另一種精神狀態。畫中線條扭曲,立體生動。梵谷的畫作啟發了往後的以孟克及康丁斯基為其中骨幹人物的表現主義。
A:梵谷的畫作很前衛,他能在百多年前已經畫出那種3D的立體效果,非常佩服。看《星夜》時也感覺星月跳動,雲捲風起,生動得看得到、聽得見,有種超自然、超現實的感覺。但梵谷的另一作品,如《夜間咖啡館》(The Night Café)又表現了另一種空虛的可怕。依我說,他只是用了美麗的色彩蓋掩著他精神上的孤獨感。
S:他是在畫布上塗上明亮的油畫顏料,用油畫刀和手指在畫面上塑形,讓顏料成為主角。
A:我覺得梵谷的畫作,很有意識地強化色彩,但在取得絕美和諧的同時,你總覺得他在作品的色彩背後,展現出濃烈的孤獨寂寞感,如四旁無依,星宿之一栗。
S:他著實擁有很強的視覺語言。我們先前提過的愛爾蘭畫家培根,他也非常欣賞梵谷。他曾經形容梵谷為藝術界的甘地。他曾說:「繪畫是將個人神經系統投射於畫布上。」或許梵谷以畫布作他的出口,宣洩他心中的不自由。
A:他內心沉重的孤寂可想而知。
S:1886年左右當梵谷去巴黎與弟弟提奧會合,當時的巴黎鬧得熱烘烘,他認識了一批印象派畫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1830-1903)、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秀拉、高更等人,他曾說過,他好像靈光乍現,突然看見了色彩,興奮極了。他開始練習印象主義即興的筆觸及技巧,而他畫作的色彩亦開始擺脫了以往在荷蘭時代的沉鬱,變得明亮鮮艷;在色彩的運用上,更為隨心所欲。
A:當時的巴黎,是追求變革的巴黎:政治巨變、攝影技術的發明、科技演進,還有令人興奮的哲學思想。巴黎是當時走在時代尖端的先進城市。S:梵谷早期在荷蘭只以灰暗色系進行創作,直到他在巴黎遇見了印象派與新印象派,遂開始融入了他們的鮮艷色彩與獨特畫風,創造了他自己的個人畫風,尤其在法國亞耳的那段時間,他最著名的作品多半是他在生前最後兩年創作的,期間梵谷深陷於精神疾病中。
梵谷的「瘋癲」與「自由」
S:梵谷為了成為畫家,努力達成夢想,確實下了不少苦功,亦走了很多的艱苦路。他吃不飽、睡不好、穿不暖、身心俱疲。雖然他畫了很多的作品,但他在世的時候,真正賣出的只有一件。生前寂寂無名,死後畫作名揚後世,相信當時很多藝術家確實如此!
A:我有時想,如果命運逆轉,能活多幾十年的話,那他隨後的畫作不知會是怎樣?人的命運,實在有太多的偶然及無奈,可能只有死,才令他的作品耀眼於人前。
S:你似乎很相信命運?
A:沒有相信不相信。命運似是偶然引發,但卻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最積極的態度還是與之結伴同行,來得安然,處之亦泰然。
S:同意。這是看待命運最正確的方法。你知嗎?梵谷在他死前的一段時間依然不停地創作。在他的作品中,你會感覺到他那深厚的洞察力,而這種深厚的洞察力也可能更令他產生強烈的超脫感,最後決定以死亡作結。
A:在他了結生命前的一段日子,他仍努力繪畫,可能就是因為他已再找不到更好更舒服的退隱之地、容身之所,唯有繪畫才能成為他精神最後的支柱,最終的避難所,至少能讓他專注,暫時忘記生活中的苦。
S:他晚期的畫作,蘊藏著憂傷與不安,似是無力單打獨鬥,但特別的是,畫作的色彩卻與大自然的更加相和應,似是隱藏著很強烈的生命語言的密碼,有待觀者用心靈去發掘去解讀。他曾說過,從早到晚繪畫,是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他更認為繪畫是「對抗病魔最有效的避雷針」。
A:用繪畫放鬆心情,令他分散注意力,增強克服的意志,抵抗疾病帶來精神上及肉體上的痛苦。
S:在他死前的兩個多月內,他就畫了70幅油畫。
A:夠諷刺,矛盾就在這裡。他努力地作畫,但他知道他的畫一直得不到市場及社會的普遍認同,即使他如何投入心力,自己的作品依然是毫無價值。
S:不管賣不賣得出,他可能都想以畫作來記錄他的一生。
A:而高更這個過客,就益發變成他的催命使者。悲劇的計時秒表已經按下,正在一一倒數。S:《麥田群鴉》(Wheat Field with Crows)那幅畫是梵谷去世前幾周的作品,是他最著名的畫作之一,一般認為這是他的絕筆之作。畫中展現的風很大,烏雲密佈,漫天群鴉,沒有出路,似是絕境,彷彿埋下他向這個世界說「不」的伏線。他選擇的顏色亦暗示他已找不到光明的前路。而麥田是梵谷最愛的創作題材之一。
A:我覺得這幅畫是他自殺前的預演,他正想像那轟然一槍時的群鴉亂舞,可能自殺的念頭已醞釀多時―一下畫破長空的槍聲Bang!
S:虧你想得出來。
A:你認為他一生的努力是為了甚麼?
S:為實現一種價值,一種美的價值。
A:他的一槍,帶走了他一生的孤獨。原來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而是內生的。即使他的軀體被外在的力量囚禁在有限的空間之內,但這卻沒有窒礙他享受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在他的作品當中,你依然感應到他那純真的本性,一顆鮮活敏感的心靈。
S:我記得過去曾看過梵谷的一幅畫作,不知在這個展覽中我們會否看到。作品圖像是他被禁錮在一所酷似瘋人院或療養院的地方,當時的他神情呆滯,跟其他病者一起在院內的廣場運動,他的處境,有種很強烈被社會排斥、被監管,被剝奪權力的孤獨感,儼如被投放在另一世界中。他在信中也曾指出:「我感到自己很虛弱,又不安,又害怕……一種巨大的恐懼震懾我,阻止我思考。」他當時已經不太「自由」,不能盡情發揮他本身固有的能力,這令他沮喪。
A:他被關在精神病院期間,一定受盡精神及肉體上的折磨。你知道嗎,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對瘋狂、對實踐主體自由概念這方面有很精闢的詮釋。傅柯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討論了歷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及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界定為影響社會秩序的一部份到將他們定義為必須關閉起來的人,在某程度下是對瘋子進行懲罰,代表的意義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與絕對的過渡和淨化的一種行為,在這樣的過程中瘋人被賦予了邊緣的地位,不再自由。
S:人們說他瘋了,他亦只好瘋了,況且他也不再在乎。A:我記得法國神學家及哲學家帕斯卡(Pascal,1623-1662)說過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可圈可點。
S:如果說:藝術家以「自由」為他的本位,你就會明白為何梵谷身體精神上的痛苦沒有攔阻到他的意志,他要超越這些桎梏,不要成為它的奴隸,而個體的不自由正正是鼓動他創作的最大力量,直至最後一刻。
A:我們既有內在的精神自我,又有外在的肉身自我。相信繪畫是梵谷內在精神自我的活動,一種內在視覺,將正在受苦的外在肉身自我掙脫開來,建構一個新世界,一個新的自由空間,尋找屬於他的價值之所在。雖然梵谷生命短暫,大部份時間受病魔紛擾,但相信他很多時都是自得其樂,世界色彩依然是美妙的。
S:說得很美,很有意思。他就是盡最大努力,為的是實現一種價值理想,一種真善美,以實現更高的價值而抗衡病魔的糾纏。
A:梵谷一定是個天才,可惜才能卻成為他沉重的包袱。相信他努力作畫是希望將自己的所有才能釋放開來,這才是他感覺自由的唯一出路,或許旁人不易理解,更誤解他為瘋癲。
S:正正是他不歇息地努力作畫,使他留下了無數不朽名作。
A:可惜最後他還是訴諸命運對他的冷待,而他的絕望,亦唯有死可解決之。
S:他曾說過:「在世上有所作為,就必須自我死掉……人生在世,並不僅僅為了生活幸福,是要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超越幾乎所有人一生跋涉的平庸。」他在1890年7月某日傍晚散步時自殺。
A:他的死,至今仍是一個謎,可能是財困逼他上絕路;亦可能是他窮得只剩下這個了結自己的權利;又或梵谷感覺自己的創作靈感已耗盡,不能再以創作支持他活下去;更有可能是他想用這種毀滅性的暴力,證明自己依然擁有最後的權利,一種自我價值肯定的方式,即使超越理性。
S:梵谷這麼多年來,都是完完全全奉獻在沒有為他帶來經濟效果的事業。當他在某時某刻以為問題的解決有了轉機,生命似有曙光,總會有另外一些問題把他拖垮下來,令他感到懊惱沮喪,他或許已厭倦了這些起起伏伏的生活,亦已再沒有勁沒有力量支撐創作。
A:在藝術界生存,相信必須掌握業界的生態。藝術家是一種殘酷的職業,而梵谷不懂處世之道,這就令他的藝術之路更難行,畢竟藝術是一種People Business。S:其實與人溝通真的很費勁。
A:我全然明白。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認為:人所有的煩惱,都是人際關係的煩惱。
S:這個我也絕對同意。
A:你知道嗎?其實我們能夠被理解就是我們的語言,「語言是人的家園」,而語言亦是思維的工具,如果我們不能好好地透過言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時,就會如梵谷,變得寸步難行。
S:而沒有提奧的經濟支持,就成就不了梵谷偉大的藝術生命。兩隻鞋子,一隻已破損,另一隻也乏力前行。梵谷死後僅半年,提奧亦病逝了,死後葬於其兄墓旁,兄弟情深。
A:看著他的畫,想起他的生平,我感到有點不能自已的悲懷。
S:梵谷自己也當過牧師,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而基督教信仰並不主張教徒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生命是來自於神的創造,生命是神聖的,人是照著神的形象,按著神的樣式造的,應是高於一切的,自殺就是毀壞神的創造。而梵谷,一個虔誠的基督追隨者,上帝本是他所能抓住的一個最安穩的浮木,但他卻選擇了死亡,他作這個決定的時候,必然有一番左思右想的掙扎。
A: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死亡是終極、亦是最大的痛苦。我們暫不論自殺是否罪惡或對上帝的冒犯,但從他的畫作,他的生平,你可以看出梵谷對生命本是充滿熱情盼望,但最後卻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作結,是痛苦絕望的控訴,卻是何等的無奈。
S:可能他認為活著只是被囚之身,生活著的每一剎都不能再給予他任何意義,而他認為死後到了彼岸可能才會得到自由,當人已厭惡自己的肉身,存在對他來說已不是自由,再沒有生存的慾望,自然沒有死亡的恐懼。
A:「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古希臘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B.C. 460-B.C.395) 這樣說過。
表現主義先驅:梵谷
當Simone與Andrea完成圓滿的愛丁堡之旅後,腦中還纏繞著「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的「裊裊餘音」,她們的下一站行程,就決定計劃探訪影響孟克及康丁斯基至深的靈魂人物――表現主義先驅、荷蘭藝術家梵谷。
一提起荷蘭,腦海中就立即出現向日葵、梵谷、風車、木屐等景象。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處非常自由的城市,它既是荷蘭首都,亦是荷蘭的文化之都。荷蘭盛產世界級畫家,包括巴洛克時期的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1606-1669)、後印象派的梵谷,還有幾何抽象派畫家蒙德里安。到訪荷蘭的藝術愛好者亦可欣賞荷蘭的人文風景及藝術歷史足跡,感受到荷蘭當代藝術的自由及富生命力的一面。
Simone與Andrea此行的目的是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館(Van Gogh Museum)。博物館於1973年成立,是收藏及擁有梵谷畫作最豐富的美術館。館內收藏梵谷二百餘幅的油畫、五百多幅的素描和七百多封私人書信等,包括梵谷由最初的荷蘭時期、巴黎時期、亞耳時期直至聖雷米、奧維爾時期的大部份名作。每年專程到荷蘭朝聖的人數以千萬計。
梵谷是牧師之子,他的叔叔是畫廊合夥人,弟弟提奧(Theo Van Gogh,1857- 1891)既是他的知心密友、經理人,亦是他的精神及經濟支柱。在他短暫的人生中,梵谷學懂多國語言包括法語、德語及英語,也學習了基本的繪畫技巧;他曾當過藝術品交易公司的見習員、教師,後也當過傳教士,向貧困的採礦工人傳教,直到大約27歲時,即1880年,梵谷才開始他的畫家生涯。在他生前的最後十年間,卻創作了超過二千幅畫,包括約八百多幅油畫與一千多幅素描,當然還有許多水彩畫、版畫等。可惜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只賣出過一幅畫,反而在他死後,他的作品如《星夜》(The Starry Night)、《向日葵》(Sunflowers)等傳世經典,卻是天價難求。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就這樣說過:「他生前沒人看得起,死後無人買得起。」非常諷刺,但這是現實。在決定畫畫之後,梵谷在荷蘭閒待了5年(1880-1885),隨後赴法國(1886-1888),在巴黎那段時間,他致力學習、創新及嘗試。從1886 年春開始,與弟弟提奧一起住在蒙馬特(Montmartre)的藝術區。1888年2月,他厭倦了巴黎喧鬧的生活,搬往南部小鎮亞耳(Arles),追尋明亮的陽光,期間創作了不少名作,如《梵谷的房間》,在這時期,他特別喜愛黃色。1889年4月,梵谷主動到亞耳附近的聖雷米鎮(St-Remy-de-Provence)一所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1890年5月,梵谷定居於奧維爾(Auvers-sur-Oise)這座鄰近巴黎的藝術村,作品多表達不安的情緒,《麥田群鴉》(Wheat Field with Crows)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1890年7月27日,他朝自己胸部開槍,兩天後去世,而提奧亦於梵谷死後半年去世,兄弟倆同被葬在奧維爾墓地內。
Simone與Andrea在第二天清晨乘坐路面電車出發至梵谷博物館,路面電車是當地市民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非常方便。只消十多分鐘的車程,她們已經到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
梵谷博物館共有四個樓層,二樓主要展出梵谷油畫,畫作是依照他不同時期的居住地方來展示。若有意深入瞭解,可跟樓下服務台租用導覽設備Audio guide。跟著導覽的指示,可以對他的作品及創作時的心境有更透徹的瞭解。打算計劃參觀梵谷博物館的朋友,最好預先進行網上登記,以減省排隊購票的時間。期待已久的「朝聖」旅程即將開始。
梵谷與高更:友誼容不下,悲劇一觸即發
S:這幅畫你又有何看法?
A:這幅《高更的椅子》(Paul Gauguin’s Armchair),有著高雅絨布座墊,紅綠相配,椅子寬敞精細,而椅上更放著點燃的蠟燭和兩本書,還有一盞煤氣燈。
S:我記得我在英國倫敦看過另一張畫,《梵谷的椅子》(Vincent’s Chair with his Pipe),椅子木質簡陋,較為粗糙,椅子上放著煙斗和煙葉,顏色以黃藍為主,非常簡樸。這兩張畫的故事背景是這樣的:當梵谷在1888年2月赴亞耳旅居後,他邀請好友高更10月來訪,而這兩幅椅子畫作是梵谷在1888年11月作的,從他畫出的《梵谷的椅子》及《高更的椅子》,你已略知他們兩者性格的差異。
A:依我看,兩張椅子,見證了兩種不同的性格:梵谷是較著重精神層面,而高更則較世俗。一個浪漫認真,是防守內向型;而另一個則原始不羈,是進攻外向型,本來一正一負,應是最佳組合。奈何高更卻逼出一個潛藏毀滅爆炸力的梵谷。S:他倆相識,原本的美意是相互切磋交流,可惜最後卻釀成無以彌補的傷痛。割席收場或許是必然的結局。朋友相交,很在乎大家的腦電波是否相符,就如你我。
A:幸好我們也肯互相遷就。其實「找」朋友與「交」朋友是兩碼子的事,也許梵谷搞錯了。但朋友爭拗可以刺激大腦思維,未嘗不好,只是梵谷過分執著。
S:顯然他對高更期望過高,將自己的價值完全寄托在他身上,這就出事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越把高更放得無上至高,自然不知不覺間把自己擺得低下卑微,連自我認同的價值也失去了。 而情況一旦逆轉,他則無法承受那股巨大的張力,失控如同他所說的「通了高壓電」,就崩潰了。梵谷的心靈其實非常脆弱。
A:其實我們交朋友也許決定我們的一生……說實在的,圍繞我們身邊的朋友,他們是天使或是魔鬼,真的不走至最後,難言對錯。
S:又或者命該如是,逃不得。他與高更的相遇,已逐步將他迫上絕路。
A:悲劇的發展總是遵循一個軌跡,一個命數。
S:梵谷對高更的執著,或許近乎病態,這卻是事實。如果一方受另一方的影響太大,以對方為全部,以對方的觀念意向判準為自己的全部所有,一旦一方被「遺棄」或被「打下去」的時候,弱勢的一方自然會潰不成軍,無力前行。
A:認真就會輸,特別在感情方面,悲劇一觸即發。
自畫像的精神呈現:為自己賦予一種存在價值
S:你是否記得一幅梵谷《綁繃帶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and pipe)? 那是1888年12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梵谷與高更吵鬧激烈,他們爭吵的內容沒有人知道,之後高更走了,當天晚上梵谷就用刮鬍子的刀割傷了自己的耳朵,從此兩個人沒有再見過面,而梵谷就畫了那幅自畫像,受傷的耳朵上還包著紗布,叼著煙斗,完全反映了他的惘然。
A:相信他的失控,是他的自尊及自我形象受損。他要自我毀滅,要他的身軀與靈魂逐步在這世界引退,宣洩他在世的不受認同。聽說他割掉的是左耳,是嗎?為何在畫中是右耳?
S:因為他總是看著鏡中的自己作畫,所以畫中的是右耳。其實每個人都需要認同感。梵谷對高更的憤怒和失望等負面情緒,轉為向他自己的身體宣洩。A:可能最初梵谷對高更的依戀是源於自戀,他選擇了高更,完全是出於自戀心理。當高更無法符合他的許多期望時,他的怒向內轉,朝向自己。這種內轉,令他時常怨怪自己,終至自虐。高更是他的一面鏡子,他要放棄的其實可能就是他自己。
S:這個說法也有可能。其實朋友的一切交往,都有種神秘不可超越的藩籬,不同朋友有不同的界限,但這界限卻是模糊難辨的。
A:有時衝突就在某方想突破或超越這個界限,一觸及這脆弱的防守線距離,便引起相互排斥或反感,一旦理智維持秩序,其中一方必定開始引退,心靈也再沒有溝通的餘地。梵谷與高更的交往也如是。所以如果大家價值觀不一樣,最好就是盡快止蝕離場。
S:代價或許太大了。
A:但其實我們每天都會遇上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將我們帶到不同的境界,所以我們每分每秒都在變,變成不再是以往的「舊人」,而是另一個「新人」。所以我們每時每刻都是個棄「舊」立「新」的新人。
S:但從好的角度看。與高更的邂逅,確實給梵谷帶來了不少的啟迪及靈感,啟蒙了梵谷的藝術路,這是不能否定的。高更迫出梵谷自己潛藏的張力,影響他在畫的創作,在色彩、在結構等方面的運用,而梵谷亦確信高更給了他不少啟發。他倆的相遇,在藝術歷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A:梵谷身上燃燒著激情的細胞,你看這邊,他還有很多自畫像,似是需要一種另類的自我肯定。
S:他的自畫像系列大多在巴黎完成,數量有三十多幅。你知道嗎,自畫像是西方人文主義文明的一種產物,第一幅自畫像約在1485年出現,由意大利畫家所作。
A:依我看來,自畫像是展示個人的一個符號,一個表徵,宣示了主體自我個人的誕生,為自己賦予一種存在價值,就像我們現在的selfie自拍一樣。
S:在療養院期間,梵谷畫了多幅自畫像,你記得我們在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見過的一幅,全幅交織著綠色線條,面容緊繃,雙眉鎖緊,兩唇緊閉。從梵谷的自畫像,亦看出他精神層面及他自視的一點端倪。
A:還記得他那憂鬱的眼神斜視,帶點警覺,卻帶點呆滯,亦帶點不安,展現一種無人理解的孤獨。
S:像是幽靈般冷眼看世界。A:古典哲人當中,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傑出哲學家、政治家、詩人、劇作家、藝術家均受憂鬱所苦。其實你認為創意與精神疾病有沒有關聯?藝術家都有精神分裂與躁鬱症嗎?究竟精神疾病對這些天才來說是助力還是阻力?
S:你有興趣可以看看心理學家兼神經學家Nancy Andreasen的The Creating Brain:The Neuroscience of Genius,這本書可為你所有問題提供了事實的答案。Nancy認為創意與精神疾病是沒有太大的關聯性的。但他的《星夜》(The Starry Night)卻折射出梵谷的另一種精神狀態。畫中線條扭曲,立體生動。梵谷的畫作啟發了往後的以孟克及康丁斯基為其中骨幹人物的表現主義。
A:梵谷的畫作很前衛,他能在百多年前已經畫出那種3D的立體效果,非常佩服。看《星夜》時也感覺星月跳動,雲捲風起,生動得看得到、聽得見,有種超自然、超現實的感覺。但梵谷的另一作品,如《夜間咖啡館》(The Night Café)又表現了另一種空虛的可怕。依我說,他只是用了美麗的色彩蓋掩著他精神上的孤獨感。
S:他是在畫布上塗上明亮的油畫顏料,用油畫刀和手指在畫面上塑形,讓顏料成為主角。
A:我覺得梵谷的畫作,很有意識地強化色彩,但在取得絕美和諧的同時,你總覺得他在作品的色彩背後,展現出濃烈的孤獨寂寞感,如四旁無依,星宿之一栗。
S:他著實擁有很強的視覺語言。我們先前提過的愛爾蘭畫家培根,他也非常欣賞梵谷。他曾經形容梵谷為藝術界的甘地。他曾說:「繪畫是將個人神經系統投射於畫布上。」或許梵谷以畫布作他的出口,宣洩他心中的不自由。
A:他內心沉重的孤寂可想而知。
S:1886年左右當梵谷去巴黎與弟弟提奧會合,當時的巴黎鬧得熱烘烘,他認識了一批印象派畫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1830-1903)、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秀拉、高更等人,他曾說過,他好像靈光乍現,突然看見了色彩,興奮極了。他開始練習印象主義即興的筆觸及技巧,而他畫作的色彩亦開始擺脫了以往在荷蘭時代的沉鬱,變得明亮鮮艷;在色彩的運用上,更為隨心所欲。
A:當時的巴黎,是追求變革的巴黎:政治巨變、攝影技術的發明、科技演進,還有令人興奮的哲學思想。巴黎是當時走在時代尖端的先進城市。S:梵谷早期在荷蘭只以灰暗色系進行創作,直到他在巴黎遇見了印象派與新印象派,遂開始融入了他們的鮮艷色彩與獨特畫風,創造了他自己的個人畫風,尤其在法國亞耳的那段時間,他最著名的作品多半是他在生前最後兩年創作的,期間梵谷深陷於精神疾病中。
梵谷的「瘋癲」與「自由」
S:梵谷為了成為畫家,努力達成夢想,確實下了不少苦功,亦走了很多的艱苦路。他吃不飽、睡不好、穿不暖、身心俱疲。雖然他畫了很多的作品,但他在世的時候,真正賣出的只有一件。生前寂寂無名,死後畫作名揚後世,相信當時很多藝術家確實如此!
A:我有時想,如果命運逆轉,能活多幾十年的話,那他隨後的畫作不知會是怎樣?人的命運,實在有太多的偶然及無奈,可能只有死,才令他的作品耀眼於人前。
S:你似乎很相信命運?
A:沒有相信不相信。命運似是偶然引發,但卻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最積極的態度還是與之結伴同行,來得安然,處之亦泰然。
S:同意。這是看待命運最正確的方法。你知嗎?梵谷在他死前的一段時間依然不停地創作。在他的作品中,你會感覺到他那深厚的洞察力,而這種深厚的洞察力也可能更令他產生強烈的超脫感,最後決定以死亡作結。
A:在他了結生命前的一段日子,他仍努力繪畫,可能就是因為他已再找不到更好更舒服的退隱之地、容身之所,唯有繪畫才能成為他精神最後的支柱,最終的避難所,至少能讓他專注,暫時忘記生活中的苦。
S:他晚期的畫作,蘊藏著憂傷與不安,似是無力單打獨鬥,但特別的是,畫作的色彩卻與大自然的更加相和應,似是隱藏著很強烈的生命語言的密碼,有待觀者用心靈去發掘去解讀。他曾說過,從早到晚繪畫,是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他更認為繪畫是「對抗病魔最有效的避雷針」。
A:用繪畫放鬆心情,令他分散注意力,增強克服的意志,抵抗疾病帶來精神上及肉體上的痛苦。
S:在他死前的兩個多月內,他就畫了70幅油畫。
A:夠諷刺,矛盾就在這裡。他努力地作畫,但他知道他的畫一直得不到市場及社會的普遍認同,即使他如何投入心力,自己的作品依然是毫無價值。
S:不管賣不賣得出,他可能都想以畫作來記錄他的一生。
A:而高更這個過客,就益發變成他的催命使者。悲劇的計時秒表已經按下,正在一一倒數。S:《麥田群鴉》(Wheat Field with Crows)那幅畫是梵谷去世前幾周的作品,是他最著名的畫作之一,一般認為這是他的絕筆之作。畫中展現的風很大,烏雲密佈,漫天群鴉,沒有出路,似是絕境,彷彿埋下他向這個世界說「不」的伏線。他選擇的顏色亦暗示他已找不到光明的前路。而麥田是梵谷最愛的創作題材之一。
A:我覺得這幅畫是他自殺前的預演,他正想像那轟然一槍時的群鴉亂舞,可能自殺的念頭已醞釀多時―一下畫破長空的槍聲Bang!
S:虧你想得出來。
A:你認為他一生的努力是為了甚麼?
S:為實現一種價值,一種美的價值。
A:他的一槍,帶走了他一生的孤獨。原來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而是內生的。即使他的軀體被外在的力量囚禁在有限的空間之內,但這卻沒有窒礙他享受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在他的作品當中,你依然感應到他那純真的本性,一顆鮮活敏感的心靈。
S:我記得過去曾看過梵谷的一幅畫作,不知在這個展覽中我們會否看到。作品圖像是他被禁錮在一所酷似瘋人院或療養院的地方,當時的他神情呆滯,跟其他病者一起在院內的廣場運動,他的處境,有種很強烈被社會排斥、被監管,被剝奪權力的孤獨感,儼如被投放在另一世界中。他在信中也曾指出:「我感到自己很虛弱,又不安,又害怕……一種巨大的恐懼震懾我,阻止我思考。」他當時已經不太「自由」,不能盡情發揮他本身固有的能力,這令他沮喪。
A:他被關在精神病院期間,一定受盡精神及肉體上的折磨。你知道嗎,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對瘋狂、對實踐主體自由概念這方面有很精闢的詮釋。傅柯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討論了歷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及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界定為影響社會秩序的一部份到將他們定義為必須關閉起來的人,在某程度下是對瘋子進行懲罰,代表的意義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與絕對的過渡和淨化的一種行為,在這樣的過程中瘋人被賦予了邊緣的地位,不再自由。
S:人們說他瘋了,他亦只好瘋了,況且他也不再在乎。A:我記得法國神學家及哲學家帕斯卡(Pascal,1623-1662)說過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可圈可點。
S:如果說:藝術家以「自由」為他的本位,你就會明白為何梵谷身體精神上的痛苦沒有攔阻到他的意志,他要超越這些桎梏,不要成為它的奴隸,而個體的不自由正正是鼓動他創作的最大力量,直至最後一刻。
A:我們既有內在的精神自我,又有外在的肉身自我。相信繪畫是梵谷內在精神自我的活動,一種內在視覺,將正在受苦的外在肉身自我掙脫開來,建構一個新世界,一個新的自由空間,尋找屬於他的價值之所在。雖然梵谷生命短暫,大部份時間受病魔紛擾,但相信他很多時都是自得其樂,世界色彩依然是美妙的。
S:說得很美,很有意思。他就是盡最大努力,為的是實現一種價值理想,一種真善美,以實現更高的價值而抗衡病魔的糾纏。
A:梵谷一定是個天才,可惜才能卻成為他沉重的包袱。相信他努力作畫是希望將自己的所有才能釋放開來,這才是他感覺自由的唯一出路,或許旁人不易理解,更誤解他為瘋癲。
S:正正是他不歇息地努力作畫,使他留下了無數不朽名作。
A:可惜最後他還是訴諸命運對他的冷待,而他的絕望,亦唯有死可解決之。
S:他曾說過:「在世上有所作為,就必須自我死掉……人生在世,並不僅僅為了生活幸福,是要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超越幾乎所有人一生跋涉的平庸。」他在1890年7月某日傍晚散步時自殺。
A:他的死,至今仍是一個謎,可能是財困逼他上絕路;亦可能是他窮得只剩下這個了結自己的權利;又或梵谷感覺自己的創作靈感已耗盡,不能再以創作支持他活下去;更有可能是他想用這種毀滅性的暴力,證明自己依然擁有最後的權利,一種自我價值肯定的方式,即使超越理性。
S:梵谷這麼多年來,都是完完全全奉獻在沒有為他帶來經濟效果的事業。當他在某時某刻以為問題的解決有了轉機,生命似有曙光,總會有另外一些問題把他拖垮下來,令他感到懊惱沮喪,他或許已厭倦了這些起起伏伏的生活,亦已再沒有勁沒有力量支撐創作。
A:在藝術界生存,相信必須掌握業界的生態。藝術家是一種殘酷的職業,而梵谷不懂處世之道,這就令他的藝術之路更難行,畢竟藝術是一種People Business。S:其實與人溝通真的很費勁。
A:我全然明白。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認為:人所有的煩惱,都是人際關係的煩惱。
S:這個我也絕對同意。
A:你知道嗎?其實我們能夠被理解就是我們的語言,「語言是人的家園」,而語言亦是思維的工具,如果我們不能好好地透過言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時,就會如梵谷,變得寸步難行。
S:而沒有提奧的經濟支持,就成就不了梵谷偉大的藝術生命。兩隻鞋子,一隻已破損,另一隻也乏力前行。梵谷死後僅半年,提奧亦病逝了,死後葬於其兄墓旁,兄弟情深。
A:看著他的畫,想起他的生平,我感到有點不能自已的悲懷。
S:梵谷自己也當過牧師,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而基督教信仰並不主張教徒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生命是來自於神的創造,生命是神聖的,人是照著神的形象,按著神的樣式造的,應是高於一切的,自殺就是毀壞神的創造。而梵谷,一個虔誠的基督追隨者,上帝本是他所能抓住的一個最安穩的浮木,但他卻選擇了死亡,他作這個決定的時候,必然有一番左思右想的掙扎。
A: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死亡是終極、亦是最大的痛苦。我們暫不論自殺是否罪惡或對上帝的冒犯,但從他的畫作,他的生平,你可以看出梵谷對生命本是充滿熱情盼望,但最後卻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作結,是痛苦絕望的控訴,卻是何等的無奈。
S:可能他認為活著只是被囚之身,生活著的每一剎都不能再給予他任何意義,而他認為死後到了彼岸可能才會得到自由,當人已厭惡自己的肉身,存在對他來說已不是自由,再沒有生存的慾望,自然沒有死亡的恐懼。
A:「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古希臘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B.C. 460-B.C.395) 這樣說過。
訂購/退換貨須知
購買須知:
使用金石堂電子書服務即為同意金石堂電子書服務條款。
電子書分為「金石堂(線上閱讀+APP)」及「Readmoo(兌換碼)」兩種:
- 請至會員中心→電子書服務「我的e書櫃」領取複製『兌換碼』至電子書服務商Readmoo進行兌換。
退換貨須知:
- 因版權保護,您在金石堂所購買的電子書僅能以金石堂專屬的閱讀軟體開啟閱讀,無法以其他閱讀器或直接下載檔案。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不受「網購服務需提供七日鑑賞期」的限制。為維護您的權益,建議您先使用「試閱」功能後再付款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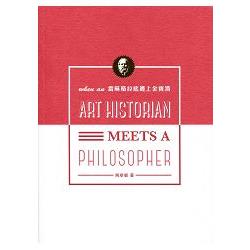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