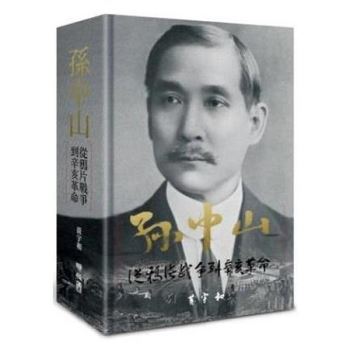第二章 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論
2004年2月,八十多歲的澳洲英裔資深學者哈利.蓋爾伯(Harry Gelber)講座教授,出版了他的名著《鴉片、士兵與傳教士:1840-1842英國與中國的戰爭及其後遺症》。茲歸納他的研究心得如下:「從英國的政治角度看,1840-1842那場與中國的戰爭,並非一場鴉片戰爭」。言下之意正是: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他繼續寫道:
它只是區區一些地方性的小摩擦。英國堅决反抗那腐朽透頂,卻高高在上而又狂妄無知的中國,堅决維護英王的尊嚴,堅决保護英國男女的性命安全,堅决追償被中國政府搶奪了的財物。沒有任何一個倫敦人,也沒有任何一個帶兵攻打中國的軍官,會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係。若中國人有本事控制鴉片走私,就讓他們大顯身手吧,英軍絕對不會代勞。那場戰爭,打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卻後患無窮,到了數十年後,傳教士目睹中國的苦難,悲天憫人,竟錯誤地怪罪英國把鴉片強加給中國,由此改變了英美輿論。
因此,蓋爾伯講座教授責無旁貸地以糾正此等所謂錯誤的輿論為己任。本偵探讀後極為詫異,因為它大別於鄙人所讀過的所有中外有關專著。大別的地方在於:過去哪怕有盎格魯.撒克遜的文明精英千方百計地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而辯護,但辯護的方式都是防守型的;蓋爾伯講座教授辯護的方式卻是攻擊型的。這種巨大變化,促使筆者立志查明蓋爾伯講座教授的立論方式,辦法是從逐句鑑定其微言大義做開始。
其劈頭第一句,手法就很高明。的確,當時大英帝國的領地遍布全球,在中國開闢的戰場,只能稱之為局部性戰爭,這是最為明顯不過的事實。當讀者接受了這個明顯的事實以後,蓋爾伯教授之把局部性戰爭等同於這場戰爭並非鴉片戰爭的說法,這也會先入為主地印在讀者的腦海裡。
他第二句話的前一段說「英國堅决反抗那腐朽透頂,卻高高在上而又狂妄無知的中國」。此言不但外國讀者熟悉,中國讀者也痛心疾首當時清朝的腐朽及天朝上國的狂妄。英國反對這些現象,是合理的。接下來第二句話的中間一段,謂英國「堅决維護英王的尊嚴,堅决保護英國男女的性命安全」,也合情合理,哪一個政府不堅決維護自己國家元首的尊嚴,不堅決保護本國公民的性命安全?如此,待蓋爾伯教授估計到已經取得讀者信任以後,就在第二句話的後一段畫龍點睛:「堅决追償被中國政府搶奪了的財物」。表面上這句話也合情合理,哪國政府不竭力保護本國公民的財物?讀者同樣會由衷地支持。但問題在於,蓋爾伯教授並沒有告訴他的讀者,這些財物具體是什麼?
容本偵探指出,這些財物非比尋常,正是違禁的毒品鴉片煙!中國政府並非搶奪了別國公民的一般財物,而是沒收了英國公民明知故犯所走私的鴉片。但是當今的普通外國讀者不一定知道當時中國政府所沒收的是違禁品,很容易誤會是中國貪污腐敗的官員橫蠻無理地搶奪了英國公民的一般財物。蓋爾伯教授用字遣詞的手法極其高明,他所用的英文字seize,既可理解為搶奪,也可理解為充公。一般不明歷史細節的外國讀者,會理解為搶奪,因為蓋爾伯整句話是以「英國堅决反抗那腐朽透頂,卻高高在上而又狂妄無知的中國」作為開端的。
他的第三句話的前半段說「沒有任何一個倫敦人〔會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係〕」。蓋爾伯講座教授有所不知:在鴉片戰爭時期當然有不少倫敦人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密切關係,但是現代人已經被諸如蓋爾伯教授的高論蒙蔽住了,極少人知道當時英國有著非常強烈的反對鴉片貿易及鴉片戰爭的群體。詳見下文。
蓋爾伯教授的第三句話的後半段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帶兵攻打中國的軍官,會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係」,則官兵的天職是奉命打仗,絕對不容花半秒鐘問「為什麼?」這一切都是那麼地合情合理,難怪深得讀者信任。
至於他第四句話:「若中國人有本事控制鴉片走私,就讓他們大顯身手吧,英軍則絕對不會代勞」。當然,英軍不是中國政府所僱傭的警察,自然不會為中國政府緝私。因此,這句話同樣言之成理。關鍵是:蓋爾伯既不是倫敦高層,也不是販夫走卒,他是地位崇高的歷史學與政治學講座教授,天職是明辨是非,主持公道!
他最後一句話的前半段說「那場戰爭,打起來不費吹灰之力」。他在故技重施,說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在讓讀者不斷微微頷首之際,就說出誤導性很強的最後一段話:「卻後患無窮,到了數十年後,傳教士目睹中國的苦難,悲天憫人,竟錯誤地怪罪英國把鴉片強加給中國,由此改變了英美輿論」。我的天!不待數十年後,也不光是傳教士,其實在鴉片戰爭期間甚至之前,已經有英國貴族、傳媒、大批正當商人、不少家庭主婦挺身而出,反對英國把鴉片強加給中國了。詳見下文。
蓋爾伯教授這種瞞天過海的寫法,對於一知半解的當今廣大西方知識分子,非常見效。君不見,他這本書,在英國售70英鎊,在美國賣107美金,仍然供不應求:初版連再版前後共5版(見下表倒數第二欗)。
書成之後,蓋爾伯教授又環遊世界到處演講來廣為散播他的高論。例如,2006年2月24日,他在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所做公開講座,題目竟然是:「那場並非『鴉片戰爭』的所謂鴉片戰爭」。容本偵探再次強調:英國出兵攻打中國的理由,正是要強迫中國政府賠償所繳去英商的鴉片,為此而打的戰爭,怎能說它與鴉片無關?為了鴉片而發動的戰爭,怎能不稱之為鴉片戰爭?聽眾當中的哈佛大學美國本土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若記得美國紐約州最高法院著名法官約翰.埃德蒙(John Worth Edmonds, 1799-1874)的話,肯定啼笑皆非。因為該法官曾說過:「現在英國政府竟然要求中國政府賠償被充公了的東西。容我進言:這將是文明史上第一個案例(若非第一個案例,就讓我們盼望它是最後一個案例),一個用大炮的炮口來提出賠償走私犯的案例」。
最後,為了擴大其影響力,蓋爾伯教授乾脆把其大著全文放在網路上,任由讀者免費下載。鴉片戰爭真的與鴉片無關?關係密切極了!如何密切?請看本書題為〈太平天國的命運懸於一線──茶葉〉的第二十二章。
其實蓋爾伯教授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這本大作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華夏冤枉了高尚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該打!這種歪論,雖然滿足了當今全球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當中不少人的好勝心理,但其實對於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清譽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它埋沒了哪怕是鴉片戰爭時代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當中真正高尚的品質。據本偵探考證,蓋爾伯教授的論調基本上是撿拾鴉片戰爭時期當事人──1830年代鼓吹鴉片戰爭不遺餘力的鴉片私梟渣顛(William Jardine, 1784-1843)與其合伙人孖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等鷹派在其《廣州紀事報》(Canton Register)中的叫囂,而完全忽視了當時在穗哪怕同樣是走私鴉片的英商坦誠的話,諸如下面刊登在《廣州報》(Canton Press)的一段讀者來函:「難道我們不是一個龐大的走私集團?無論我們如何自欺欺人,也無法否認我們是走私犯──一名世界公民〔謹啟〕」。
在英國本土的反戰聲音更為嘹亮。1839年12月2日,倫敦的《晨報》把英國準備發動的對華戰爭譴責為「玷污了英國的尊嚴」。1840年3月28日,《旁觀者報》(Spectator)更評論說:「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拼命地替對華戰爭塗脂抹粉,把一名黑得比黑炭還黑的非洲黑人塗成白人:加油吧!盡情地塗白吧!歷史將把此場戰爭命名為『鴉片戰爭』!」結果在1840年4月7日,「鴉片戰爭」此詞首次在英國國會的下議院辯論中出現了,那是英國戰爭大臣的發言,哪怕他的動機是要譴責某些「英國輿論竟然荒唐地認為英國政府之發動對華戰爭是為了擴大非法的鴉片貿易」。翌日,議員格拉德斯通反駁說:「擬發動之戰爭,比我曾經聽說過的、或曾經閱讀過的任何一場戰爭,都要使得本國蒙受更大的恥辱」。結果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泰晤士報》在1840年4月25日和5月1日也用上「鴉片戰爭」這個名詞。
哈哈!原來最早──比中國人更早──把該場戰爭命名為「鴉片戰爭」者,竟然是與鴉片煙販同樣是浸潤在基督宗教《聖經》之中、但是言行一致的英國人!還不止此,1840年4月24日,三百多名倫敦市民自發地擠進倫敦大皇后街(Great Queen Street)的共濟會堂(Freemasons’ Hall),參加一個公眾集會,當中不乏衣冠楚楚的女士。他們熱烈討論當時英國政府擬發動的對華戰爭。集會期間,他們排除了個別鷹派分子的各種干擾,終於以大多數通過決議:對於「本國為了支持英商把鴉片輸往中國而對華開戰」,由此而「玷污了本國道德和宗教的感情」,表示強烈不滿。翌日,包括《泰晤士報》的倫敦各大報章都報導了集會過程和決議案;而以《旁觀者報》的評論最為激烈:「這場戰爭本身已經是罪大惡極;而戰爭的目標竟然是為了把鴉片強行加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頭上,更是滔天的罪惡」。接下來的好幾天,超過二十份英國的地方報章紛紛轉載!
的確,當時確實有不少英國上下人士認為鴉片戰爭嚴重地玷污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尊嚴和基督宗教的崇高道德。老夫對他們三鞠躬!讓老夫更為感動的是,《南京條約》簽署後,在英國工商界憧憬著從中國取得龐大經濟收益而紛紛舉杯慶賀之際,英國的和平協會(Peace Party)哀鳴曰:「將來的世世代代都無法洗脫這場罪惡的戰爭替大不列顛所帶來的恥辱」。《利茲時報》更嚴辭譴責一致舉杯慶祝的人說:「不!一致舉杯慶祝成功地進行了大屠殺,成功地發動了一場罪惡的、百辭莫辯的戰爭;一致舉杯祝賀海陸兩軍,在鴉片戰爭中,犯下了愧對國家民族的滔天罪行,這一切、一切,都是為了追求一個見不得光的目標」。老夫讀來感動得簡直老淚縱橫!
2004年2月,八十多歲的澳洲英裔資深學者哈利.蓋爾伯(Harry Gelber)講座教授,出版了他的名著《鴉片、士兵與傳教士:1840-1842英國與中國的戰爭及其後遺症》。茲歸納他的研究心得如下:「從英國的政治角度看,1840-1842那場與中國的戰爭,並非一場鴉片戰爭」。言下之意正是: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他繼續寫道:
它只是區區一些地方性的小摩擦。英國堅决反抗那腐朽透頂,卻高高在上而又狂妄無知的中國,堅决維護英王的尊嚴,堅决保護英國男女的性命安全,堅决追償被中國政府搶奪了的財物。沒有任何一個倫敦人,也沒有任何一個帶兵攻打中國的軍官,會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係。若中國人有本事控制鴉片走私,就讓他們大顯身手吧,英軍絕對不會代勞。那場戰爭,打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卻後患無窮,到了數十年後,傳教士目睹中國的苦難,悲天憫人,竟錯誤地怪罪英國把鴉片強加給中國,由此改變了英美輿論。
因此,蓋爾伯講座教授責無旁貸地以糾正此等所謂錯誤的輿論為己任。本偵探讀後極為詫異,因為它大別於鄙人所讀過的所有中外有關專著。大別的地方在於:過去哪怕有盎格魯.撒克遜的文明精英千方百計地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而辯護,但辯護的方式都是防守型的;蓋爾伯講座教授辯護的方式卻是攻擊型的。這種巨大變化,促使筆者立志查明蓋爾伯講座教授的立論方式,辦法是從逐句鑑定其微言大義做開始。
其劈頭第一句,手法就很高明。的確,當時大英帝國的領地遍布全球,在中國開闢的戰場,只能稱之為局部性戰爭,這是最為明顯不過的事實。當讀者接受了這個明顯的事實以後,蓋爾伯教授之把局部性戰爭等同於這場戰爭並非鴉片戰爭的說法,這也會先入為主地印在讀者的腦海裡。
他第二句話的前一段說「英國堅决反抗那腐朽透頂,卻高高在上而又狂妄無知的中國」。此言不但外國讀者熟悉,中國讀者也痛心疾首當時清朝的腐朽及天朝上國的狂妄。英國反對這些現象,是合理的。接下來第二句話的中間一段,謂英國「堅决維護英王的尊嚴,堅决保護英國男女的性命安全」,也合情合理,哪一個政府不堅決維護自己國家元首的尊嚴,不堅決保護本國公民的性命安全?如此,待蓋爾伯教授估計到已經取得讀者信任以後,就在第二句話的後一段畫龍點睛:「堅决追償被中國政府搶奪了的財物」。表面上這句話也合情合理,哪國政府不竭力保護本國公民的財物?讀者同樣會由衷地支持。但問題在於,蓋爾伯教授並沒有告訴他的讀者,這些財物具體是什麼?
容本偵探指出,這些財物非比尋常,正是違禁的毒品鴉片煙!中國政府並非搶奪了別國公民的一般財物,而是沒收了英國公民明知故犯所走私的鴉片。但是當今的普通外國讀者不一定知道當時中國政府所沒收的是違禁品,很容易誤會是中國貪污腐敗的官員橫蠻無理地搶奪了英國公民的一般財物。蓋爾伯教授用字遣詞的手法極其高明,他所用的英文字seize,既可理解為搶奪,也可理解為充公。一般不明歷史細節的外國讀者,會理解為搶奪,因為蓋爾伯整句話是以「英國堅决反抗那腐朽透頂,卻高高在上而又狂妄無知的中國」作為開端的。
他的第三句話的前半段說「沒有任何一個倫敦人〔會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係〕」。蓋爾伯講座教授有所不知:在鴉片戰爭時期當然有不少倫敦人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密切關係,但是現代人已經被諸如蓋爾伯教授的高論蒙蔽住了,極少人知道當時英國有著非常強烈的反對鴉片貿易及鴉片戰爭的群體。詳見下文。
蓋爾伯教授的第三句話的後半段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帶兵攻打中國的軍官,會認為該場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係」,則官兵的天職是奉命打仗,絕對不容花半秒鐘問「為什麼?」這一切都是那麼地合情合理,難怪深得讀者信任。
至於他第四句話:「若中國人有本事控制鴉片走私,就讓他們大顯身手吧,英軍則絕對不會代勞」。當然,英軍不是中國政府所僱傭的警察,自然不會為中國政府緝私。因此,這句話同樣言之成理。關鍵是:蓋爾伯既不是倫敦高層,也不是販夫走卒,他是地位崇高的歷史學與政治學講座教授,天職是明辨是非,主持公道!
他最後一句話的前半段說「那場戰爭,打起來不費吹灰之力」。他在故技重施,說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在讓讀者不斷微微頷首之際,就說出誤導性很強的最後一段話:「卻後患無窮,到了數十年後,傳教士目睹中國的苦難,悲天憫人,竟錯誤地怪罪英國把鴉片強加給中國,由此改變了英美輿論」。我的天!不待數十年後,也不光是傳教士,其實在鴉片戰爭期間甚至之前,已經有英國貴族、傳媒、大批正當商人、不少家庭主婦挺身而出,反對英國把鴉片強加給中國了。詳見下文。
蓋爾伯教授這種瞞天過海的寫法,對於一知半解的當今廣大西方知識分子,非常見效。君不見,他這本書,在英國售70英鎊,在美國賣107美金,仍然供不應求:初版連再版前後共5版(見下表倒數第二欗)。
書成之後,蓋爾伯教授又環遊世界到處演講來廣為散播他的高論。例如,2006年2月24日,他在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所做公開講座,題目竟然是:「那場並非『鴉片戰爭』的所謂鴉片戰爭」。容本偵探再次強調:英國出兵攻打中國的理由,正是要強迫中國政府賠償所繳去英商的鴉片,為此而打的戰爭,怎能說它與鴉片無關?為了鴉片而發動的戰爭,怎能不稱之為鴉片戰爭?聽眾當中的哈佛大學美國本土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若記得美國紐約州最高法院著名法官約翰.埃德蒙(John Worth Edmonds, 1799-1874)的話,肯定啼笑皆非。因為該法官曾說過:「現在英國政府竟然要求中國政府賠償被充公了的東西。容我進言:這將是文明史上第一個案例(若非第一個案例,就讓我們盼望它是最後一個案例),一個用大炮的炮口來提出賠償走私犯的案例」。
最後,為了擴大其影響力,蓋爾伯教授乾脆把其大著全文放在網路上,任由讀者免費下載。鴉片戰爭真的與鴉片無關?關係密切極了!如何密切?請看本書題為〈太平天國的命運懸於一線──茶葉〉的第二十二章。
其實蓋爾伯教授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這本大作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華夏冤枉了高尚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該打!這種歪論,雖然滿足了當今全球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當中不少人的好勝心理,但其實對於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清譽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它埋沒了哪怕是鴉片戰爭時代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當中真正高尚的品質。據本偵探考證,蓋爾伯教授的論調基本上是撿拾鴉片戰爭時期當事人──1830年代鼓吹鴉片戰爭不遺餘力的鴉片私梟渣顛(William Jardine, 1784-1843)與其合伙人孖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等鷹派在其《廣州紀事報》(Canton Register)中的叫囂,而完全忽視了當時在穗哪怕同樣是走私鴉片的英商坦誠的話,諸如下面刊登在《廣州報》(Canton Press)的一段讀者來函:「難道我們不是一個龐大的走私集團?無論我們如何自欺欺人,也無法否認我們是走私犯──一名世界公民〔謹啟〕」。
在英國本土的反戰聲音更為嘹亮。1839年12月2日,倫敦的《晨報》把英國準備發動的對華戰爭譴責為「玷污了英國的尊嚴」。1840年3月28日,《旁觀者報》(Spectator)更評論說:「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拼命地替對華戰爭塗脂抹粉,把一名黑得比黑炭還黑的非洲黑人塗成白人:加油吧!盡情地塗白吧!歷史將把此場戰爭命名為『鴉片戰爭』!」結果在1840年4月7日,「鴉片戰爭」此詞首次在英國國會的下議院辯論中出現了,那是英國戰爭大臣的發言,哪怕他的動機是要譴責某些「英國輿論竟然荒唐地認為英國政府之發動對華戰爭是為了擴大非法的鴉片貿易」。翌日,議員格拉德斯通反駁說:「擬發動之戰爭,比我曾經聽說過的、或曾經閱讀過的任何一場戰爭,都要使得本國蒙受更大的恥辱」。結果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泰晤士報》在1840年4月25日和5月1日也用上「鴉片戰爭」這個名詞。
哈哈!原來最早──比中國人更早──把該場戰爭命名為「鴉片戰爭」者,竟然是與鴉片煙販同樣是浸潤在基督宗教《聖經》之中、但是言行一致的英國人!還不止此,1840年4月24日,三百多名倫敦市民自發地擠進倫敦大皇后街(Great Queen Street)的共濟會堂(Freemasons’ Hall),參加一個公眾集會,當中不乏衣冠楚楚的女士。他們熱烈討論當時英國政府擬發動的對華戰爭。集會期間,他們排除了個別鷹派分子的各種干擾,終於以大多數通過決議:對於「本國為了支持英商把鴉片輸往中國而對華開戰」,由此而「玷污了本國道德和宗教的感情」,表示強烈不滿。翌日,包括《泰晤士報》的倫敦各大報章都報導了集會過程和決議案;而以《旁觀者報》的評論最為激烈:「這場戰爭本身已經是罪大惡極;而戰爭的目標竟然是為了把鴉片強行加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頭上,更是滔天的罪惡」。接下來的好幾天,超過二十份英國的地方報章紛紛轉載!
的確,當時確實有不少英國上下人士認為鴉片戰爭嚴重地玷污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尊嚴和基督宗教的崇高道德。老夫對他們三鞠躬!讓老夫更為感動的是,《南京條約》簽署後,在英國工商界憧憬著從中國取得龐大經濟收益而紛紛舉杯慶賀之際,英國的和平協會(Peace Party)哀鳴曰:「將來的世世代代都無法洗脫這場罪惡的戰爭替大不列顛所帶來的恥辱」。《利茲時報》更嚴辭譴責一致舉杯慶祝的人說:「不!一致舉杯慶祝成功地進行了大屠殺,成功地發動了一場罪惡的、百辭莫辯的戰爭;一致舉杯祝賀海陸兩軍,在鴉片戰爭中,犯下了愧對國家民族的滔天罪行,這一切、一切,都是為了追求一個見不得光的目標」。老夫讀來感動得簡直老淚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