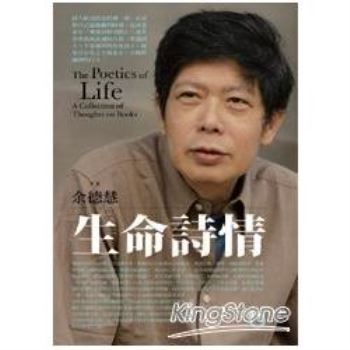〔摘文一〕
〔前言〕身心靈書籍的演變
大約在六十年代,美式的「心靈解放運動」透過反越戰的熱潮而崛起,提摩喜(Timothy Leary),一位因試驗品嚐LSD而遭哈佛大學解雇的心理學教授,帶領加州的越戰抗議者比出心靈解放的手勢,同樣被哈佛大學開除的伙伴雷達斯(Ram Dass)則以心靈導師的身分領導美國身心靈運動,在學界,存在主義的心理學家、哲學家以及現象學家參與了身心靈療癒的理論工作,而使得身心靈運動在學術界的一角獲得歇腳的機會,在七十年代慢慢醞釀出「新時代運動」,參與的學者融合物理學、數學、心靈學、中國的老莊、西藏的佛典、中東的蘇非、印度的瑜珈、北美印地安的薩滿,提出一連串的身心靈修練之道。
這身心靈療癒運動一波波往前推移,在八十年代末期,新時代運動遭身心靈界的批判而走下坡,繼之而起的是九十年代的實踐身心靈運動,這個運動以臨終照顧為核心,發展出許多生死有關的實踐議題,也帶動身體─心理─靈性為主軸的心理照護。這條身心靈運動的本質既非勵志,亦非宗教修行,而是繼六十年代的政治抗議所轉變成精神養生的綜合體。
首先,它不是勵志。身心靈運動從社會抗議轉入內心活化,因此有很強烈的反俗世性格,在理論上,俗世的心靈被稱為Ego(自我),在勵志的脈絡下,「自我」是被肯定的,無論己立或立人,都必須使自我精壯,而精壯的自我成為處事成功的要件。中國傳統的勵志書,如《了凡四訓》、《菜根譚》、《小窗幽記》都有明顯的處世技巧的探討。《了凡四訓》強調行善可以成功升官、延壽,《菜根譚》則以二元的對比與辯證指出各種應事理法、尺寸拿捏之道,而這些精壯自我卻是身心靈所批判的,認為「自我」所造就的現實其實是阻礙心靈開發的元兇,人無法獲得心靈本心的認識,正是因為受阻於「自我」的「妄識」。
身心靈運動的「反自我」是有原因的。許多實踐的身心靈運動是從人的苦難處出身的,尤其是末期癌症到死亡之間的時間,病人特別受難,一方面外在世界已經逐漸證明其無益於身心靈療癒,即使擁有最好的醫療、最成功的事業、最美好的人間關係,都與眼前的死亡疏離,繼續把心智投入這世界其實是徒勞的,另一方面,「內向轉向」(inward turning)成了一種死亡前的反歸家園,我們真實地感受的內心的害怕、愛、喜悅與痛苦,也希望有相關的論述來支持內在轉向之後的精神領域。
其次,它不是宗教修行。一般宗教修行以教門的教義為修行的框架,依教奉行。但是身心靈療癒並不遵行任何宗教的教義,雖然身心靈運動者可能會在泰國叢林修行,或者在西藏及其鄰近地區(緬甸、尼泊爾、北印度或不丹)追隨喇嘛古魯,但是他們的論述自由出入於老莊、佛、基督、蘇非之間,他們冥想的論述可以摻和禪的靜坐、道的丹功與天主的冥想,身心靈修練者從不忠於任何宗教的意識型態,也不舉旗迎這拒那,望似聯合國的雜牌軍,其實反而是朝向更自由寬廣的心靈世界。
再者,它不是哲學。身心靈運動的論述全非哲學論述那套語法。表面上身心靈書籍與存在哲學很親近,但是那只是觀念的親合,在根本的意涵是非常不相類的。身心靈書籍不太理會思辨,反而類似宗教文本,對某些觀念大力推展。身心靈書籍論述有非常清楚的選言綜合,他們雖然毫無顧忌地使用哲學家的話,但絕不是去質疑它,而是用來輔助自己的觀點。一般的身心靈哲學也不會參考這些身心靈書籍。
實踐性的身心靈書籍通常會在某些特殊領域發揮特定的效果。以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來說,這是一本綜合藏佛大圓滿教法的實踐版,人們可以從前半部獲得具有啟發性的「反俗世」念頭,但在後半部則以臨終照顧的具體施為為著眼點,索甲將藏佛臨終中陰的各種情況放入具體的病人處境。他的弟子龍緹可則是從生活經驗層面,將自己喪夫的過程以及她如何參與安寧照顧的方式,搭配索甲的論述而成為非常實用的準則書。最富有代表性的《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The Grace in Dying:how we are transformed spiritually as we die)這本書則以蘇非的心靈圖誌為引導,細數臨終的各種狀態,以超個體心理學的論述來疏導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許多讀者在他們的親人過世之前,發現這些書是他們在徬徨無依的時刻,所給予的最大的指引。
這世間的知識日益膨脹,但對身心靈的認識卻幾乎不存在。瞭解生理的醫師越不過心理那一圈,瞭解自我心理的心理學家越不過靈性那一圈,而似乎瞭解靈性的宗教師卻常常引經據典到與事實脫節,甚不知所云。許多初接觸身心靈書的讀者常常會覺得不得其門而入,一方面人們越來越不相信那看不見的「領域」,如靈魂、能量、本心等慣用名詞,不是覺得過度抽象就是覺得實證性不夠,另一方面,身心靈書的背後假設與一般知識書很不相同,如果讀者用他的習慣態度來閱讀,往往難以接受身心靈書的論點。
我個人因為長期在臨終病房擔任志工,也做了多年國科會的專案研究,包括對臨終神聖、臨終啟悟、臨終陪伴等議題,使得我不得不注意身心靈書對家屬的幫助。許多朋友在他們親人往生之前,徹夜哭著讀這類書籍,使我動容。我發現,對面臨深淵的人來說,身心靈書籍要有幾個特性才能發揮身心安頓的力量:(一)作者必須有經歷深刻體驗的受苦歷程,並能將受苦與離苦的中間步驟說清楚,而不是談玄說道,信口開河;(二)必須將實徵與理論扣緊,讓引導的圖像具體跟著實情走;(三)作者有深刻的啟悟經驗;(四)不傳任何特定宗教。
我曾經讀過最具震撼力的身心靈書是哥倫比亞大學神學教授盧雲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在他毅然放棄教職,到一家重殘病患之家擔任義工,在他過世的那一年,他寫就一本小書《亞當──神的愛子》(God's Beloved)。亞當是他照顧的一個重殘小孩,無法言語、生活無法自理。盧雲的經驗剛好顛覆一般宗教的觀點,別人憐憫亞當,說他可憐,盧雲卻發現亞當的沈默神性。這是很深刻的東西,盧雲鑽研神學四十年,不如他當義工一年的啟悟。
身心靈書寫的不是知識而是體驗。許多假身心靈書會偷渡超心理學、宗教意識型態。身心靈書籍的正典性來自於對身體的重視。但是對身體的重視不在於養生(如道家的成仙之道),而是某種現代意義的「道成肉身」:身體是修練場,我們在身體的作為裡創造精神(神性)的力量。
〔摘文二〕
輯一 瀕臨╱生死道場
面對生死的姿態(摘錄)
每每談及生死,長輩們總要怨我「哪壺不開提哪壺」,顯見大家都不太願意去談論生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死亡這件事落到言談上,總是怪異;誰也不願見到一天到晚把死亡掛在嘴邊的人,多不健康啊!但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問:為何禪師在修行時要參破生死?參破生死又是何意呢?
貪生──怕死
臨終者往生時,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憂懼,他們不是被死亡嚇死的;真正被嚇到的反而是周遭的活人
長年在安寧病房工作,只消一閉上雙眼,我腦中就會浮現許多陪伴多時的亡者身影。由於工作環境使然,我常覺得不舒服,若是病了,便有醫師和練氣功的朋友極力勸我不要再進出安寧病房,就怕我的氣被吸光。這當然是朋友關心我的好意,但我本身倒不太在意;反正去或不去,最終都是死路一條,有何差別?所以我還是繼續在安寧病房服務。
因生病而觸及生死大事,我意識到:該是面對問題的時候了。坊間有很多書籍告訴我們,要勇敢地面對生死;但是,「面對」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而「勇敢」又是什麼意思呢?
無庸置疑,絕大多數人一想到行將就死,都會害怕不已。美國生死學專家,同時也是知名的精神科醫師庫柏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年輕時就研究發現,每個人都會貪生怕死,但後來也都會接受死亡。接受本身並不困難,問題在於:接受是怎麼發生的?真有「接受」這件事嗎?
正因為死亡令人害怕,所以人們致力於尋求不害怕死亡的方法。然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說,我們若不害怕死亡,根本就過不了死亡這一關;換言之,要經過死亡這道關卡,就一定會害怕。海德格認為,死亡是一個巨大的空洞,所以一定會引起人們的憂懼害怕。其實,害怕是好現象;若是不害怕,就不會轉動;只有害怕才能促進轉動。
住進安寧病房的人,大致心裡已有數,餘生將在病房中度過;有些家屬會在一旁竊竊私語:「現在直直地進來,一定會滿面愁容地橫著出去。」但依我們在醫院長期陪伴所見,橫著出去的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憂懼,他們不是被死亡嚇死的;真正被嚇到的反而是周遭的活人。這之中的奧妙在於,臨終者走上臨終之路時,已經在轉了;還沒走上臨終之路的人,則還沒有轉。臨終的人轉了,就很自然地過去了,不會有擔憂;周遭的活人因為還沒有轉,所以擔憂不已。
活人和臨終者最大的不同是:活人還想繼續活下去,而臨終者已經走在臨終的路上,是親自以行動在轉。因此,若是活著的人對臨終者說,你的時候快到了,你就要走了,臨終者會憤怒;若是勸告臨終者「你要放下」,臨終者會感到被汙辱。因為,臨終者是以實際行動,用全副生命在轉動,而活著的人只是嘴巴上說說罷了,臨終者當然無法接受。
轉動──空無
臨終者的腦細胞已經少到無法理解「我」的過程,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害怕死亡。死亡的空無感是人類的想像,它從未真實存在過
那麼,什麼是「轉動」?臨終者為何會轉動?
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每位臨終者最後都有一個機會背對社會、不理會社會,彷彿轉著轉著,就背對了社會。這種現象,我們名之為「背立轉向」。每一個人病沉到某種程度,便會自然地放棄社會性勾連,也會開始不在乎世間的聲名、地位與角色。經常看到一些知交滿天下的病人,在進入病沉之後,就會在病房門口掛起「拒絕訪客」的牌子,一堆訪客的花籃與卡片凌亂地擺在門外;它們的主人早已進入內在轉動的境界,真正陪伴他的只有夢幻與破碎的回憶而已。
這種轉動,他人無從查覺,是疾病讓臨終者自然地去接受;也許臨終者只是昏睡或是虛弱地躺在床上呻吟,但是轉動的旅程已經開始。只要細心地陪伴,便能發覺臨終者的心思轉動得很快;今天才說:「我要堅持下去,奮鬥下去!」明天可能就說:「都到這個地步了,要放下走了。」他們的情緒轉變就在瞬間。
這主要是兩個機制使然。首先,是腦細胞的大量死亡,才講過的話可能沒多久就忘了;其次,在腦細胞死亡的過程中,患者已不太能理解社會意義,他自己也被掏空了。因此,其實不必太掛念臨終者生前念念不忘的心願,一切都是此一時、彼一時也,沒有一句話是長時間有效的。他們可能上一刻感到痛苦,下一刻又覺得舒服多了;這種轉動一直持續進行著,難以預料,也無法預料。
明白臨終者會有這種轉動,對周遭的活人而言,不啻是個福音;既然會忘,就會忘記生死,因為腦細胞已經少到不知生死為何物了。就像動物瀕臨死亡,也不太容易反省自身即將面臨死亡。人類在大腦最健全的時刻會考慮生死,但在進入死亡的過程時,就進入了無法理解「我」的過程;既不知我的存在,就意味著不害怕死亡。這也許是老天所設計的自動的熄燈號。有了這項安全機制,對死亡何懼之有?
然而,對活著的人而言這個熄燈號畢竟是可怕的。重點是,我們並不瞭解臨終者的意識狀態,沒有必要假裝自己很懂,而要去教導臨終者如何面對生死。相反地,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該如何面對生死?既然我們沒有這個轉動過程,並且要繼續活在「我」的世界中,就必須知道這個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生死的姿態是什麼?
海德格說,死亡是一種巨大的失去、巨大的空無,大到我們的心智無法面對;因此,想到死亡便會不由自主地害怕。我要反駁這項說法。事實上,只有少數的人是如此,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把死亡當成空無。因為,尚未經歷死亡,就無法體會何為空無;而當死神降臨,你已無法感覺,何知空無?
換言之,死亡的空無,根本是人類的想像;當你看到別人垂死,便設身處地想像自己也可能不再存在、不能再這樣和那樣。但是,畢竟一切都是想像;即使真的發生了,你也了無知覺,這種害怕的感覺自然無從發生,那個想像中的空無根本不會來到。更確切地說,那種空無根本不會被你感受到;你現在所感受到的,是想像中用來恐嚇自己的空無,它從未真實存在過,你根本從未有如此經驗。
只要確定面對死亡的憂懼是自己想像出來的;那麼,轉個身,聽首快樂的歌、讀點宗教的勵志文章,可能就快活起來了。想想天國之美、想想極樂世界,甚至是乘願再來,可能就不怕死了;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從憂懼中恢復過來。
既然這個空無不存在,海德格的理論自然要被推翻。他說,因為死亡的空無巨大得可怕,所以讓人願意轉變,變成為一個真摯、願意聽從良心召喚的人,不再過著欺騙的生活。根據這個論點,人們寫出了許多文章。《讀者文摘》就曾刊載一篇,內容描述:美國一名牙醫被醫生判定只剩十年可活;於是,牙醫立即把診所關了,去實現多年的願望──當一名木匠。這類文章透過網路傳播出去,啟發了很多人;於是,有老師辭掉工作去環島旅行,汲汲營生的人不再為生活打拚而去實現夢想等等。當然,這類文章勉勵人要自我實現、忠於自己,也彷彿像童話般有著美好的結局。
但是,海德格這個理論在近年來的各種研究討論上,都不斷被挑戰和懷疑。結果是,上述這些因為害怕死期將近而變得真摯過活的人,其實並沒有處理掉他們對死亡的問題,死亡不會因為真摯生活而改變或停止。也許有人會說,心願已成,死而無憾;但是,問題其實並非這麼簡單。
牙醫改行去當木匠,即使這是他最喜歡的工作和身分,過不了幾年,仍有厭倦的時候;接著,「我要做什麼?」的困惑便會襲捲而來。顯然地,這只是童話式的結局,不能再有續集;否則,王子和公主可能走上離婚一途。換言之,以這種「遮蔽法」要簡單地蓋過死亡這個複雜的問題,並不恰當。
錯認──失算
我們不斷地「錯認」而做了錯誤的行為,這些行為讓我們往相反的路上走,然後因失算而痛苦;卻也因此,讓我們從沉迷中醒悟,瞭解到真正的事實
那麼,有其他解決死亡疑慮的方法嗎?
我們都還活著,就表示我們還擁有自我意識。雖然許多宗教譴責「我」的意識阻擋人生的解脫之道;但不可否認地,這個「我」的確存在。
人有可能縮小自我、或者消解自我,然後瀟灑地走嗎?這個嘗試是失敗的;因為,絕大多數人只縮小了一段時間後,沒幾天自我又恢復了。就像每天揹著二十斤米到山上送給窮困的居民,每回都感動地落下淚來;但連續幾次過後,就不會再流淚了。
我們總是試圖尋找一個解決死亡疑慮的根本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始終不存在;當我們企圖處理它,就會造成荒謬的結果。換言之,解決疾病和死亡的這個「針對性」一旦發生,結果一定是荒謬的。這是很重大的轉折。
舉例而言,有人虔信某種解脫生死的宗教,每天虔誠地讀經、聽開示,反省教義並不斷修為,一心一意企圖解脫生死。這樣求道心切的努力是很了不起;只可惜,把努力正好放到錯誤的位置上了。這就好比一隻被放進透明乾淨玻璃瓶裡的蒼蠅,牠望見瓶外的極樂世界或天國近在眼前,便一心飛往目的地;卻不斷撞壁,怎麼也到不了。
在安寧病房,我們最害怕看到極聰明的人;聰明的人知道自己生命將盡,會不斷追問如何才能解脫生死,獲得身心大安樂。一般沒讀什麼書的阿公、阿嬤並不會問這個問題,他們糊里糊塗地就走了;但聰明的病人會保持著高度精明的意識,他們自我要求不昏不昧,希望能達到一念往生的境界。但是,這樣的信念在安寧病房就顯得難以理解和諷刺;原因在於,他們愈是集中心念想往生所欲之處,便會感到距離愈遠、愈無法到達,與經書所說的「含笑九泉」差別愈大。
這是因為,他們用全副意識僅僅抓取一種名為「修行」的東西,是「抓」來的;但是,真正的死亡過程是「放」。愈是集中強烈意識面對死亡,就愈是無法到達目標境界,完全適得其反;這種行為叫做「錯認」。
我們對我們的人生,不斷地進行「錯認」而做了錯誤的行為;這些行為造成了虛假的想像,讓我們誤以為得以解脫或朝解脫之路邁進;事實上,是剛好往相反的道路上走。
明白被錯認所誤之後,我們就真能及時踩煞車、懸崖勒馬嗎?還是做不到啊!如何能不錯認呢?當一塊石頭還未進行雕琢之前,誰都說它是一塊石頭;但當它被雕成藝術品或某人的石像後,你會說這是什麼作品或直接說出人像的名字,雖然本質上它還是塊石頭。
直接說出作品名稱或石像所代表的人名,這個行為就是錯認,我們要回頭認識它的本質。然而,這也只是理論上的說法,事實上本質是無法認識的。所謂本質,就是隱藏看不見的;從未有任何物質是以本質面貌為人所見。石頭不過是簡單的物質例子,尚有更為抽象的精神層次,如何捕捉本質呢?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要被我們的錯認所誤導。曾有一篇刊在《中國時報》的讀者投書,作者提到她公公生病了,緊急送醫後,公公就此病逝在醫院。作者不解地問:「現在的醫學不是很發達嗎?」她理所當然地認為生病要就醫,但壓根兒沒想到人會這麼死去。這就是被錯認所誤導的真實案例。作者失算了,但這個失算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失算讓我們痛苦,痛苦才讓我們從沉迷中醒悟,才可能了解真正的事實。
換言之,錯誤本身也是一個墊腳石,人就是靠錯誤這塊墊腳石轉身。失婚的女性一定很能理解:當初滿心歡喜地嫁給對方,全心全意甚至不顧一切地付出所有;等到婚姻失敗、結束一切後自己變得一無所有時,才醒悟到女人也應保有財產和獨立的能力,才能站穩雙腳。這個慘痛的經驗,未必讓女人害怕婚姻,但她不會再重蹈覆轍,會保有自己的獨立能力;若有第二次婚姻,通常會更健康而真實。
這就是真真實實的學習,不是口頭上的理論,也不是價值、主義這些高渺的目標,一切按部就班。面對死亡,我們可以按部就班、務實地一步一步來,不必再談超生了死的闊論。
〔前言〕身心靈書籍的演變
大約在六十年代,美式的「心靈解放運動」透過反越戰的熱潮而崛起,提摩喜(Timothy Leary),一位因試驗品嚐LSD而遭哈佛大學解雇的心理學教授,帶領加州的越戰抗議者比出心靈解放的手勢,同樣被哈佛大學開除的伙伴雷達斯(Ram Dass)則以心靈導師的身分領導美國身心靈運動,在學界,存在主義的心理學家、哲學家以及現象學家參與了身心靈療癒的理論工作,而使得身心靈運動在學術界的一角獲得歇腳的機會,在七十年代慢慢醞釀出「新時代運動」,參與的學者融合物理學、數學、心靈學、中國的老莊、西藏的佛典、中東的蘇非、印度的瑜珈、北美印地安的薩滿,提出一連串的身心靈修練之道。
這身心靈療癒運動一波波往前推移,在八十年代末期,新時代運動遭身心靈界的批判而走下坡,繼之而起的是九十年代的實踐身心靈運動,這個運動以臨終照顧為核心,發展出許多生死有關的實踐議題,也帶動身體─心理─靈性為主軸的心理照護。這條身心靈運動的本質既非勵志,亦非宗教修行,而是繼六十年代的政治抗議所轉變成精神養生的綜合體。
首先,它不是勵志。身心靈運動從社會抗議轉入內心活化,因此有很強烈的反俗世性格,在理論上,俗世的心靈被稱為Ego(自我),在勵志的脈絡下,「自我」是被肯定的,無論己立或立人,都必須使自我精壯,而精壯的自我成為處事成功的要件。中國傳統的勵志書,如《了凡四訓》、《菜根譚》、《小窗幽記》都有明顯的處世技巧的探討。《了凡四訓》強調行善可以成功升官、延壽,《菜根譚》則以二元的對比與辯證指出各種應事理法、尺寸拿捏之道,而這些精壯自我卻是身心靈所批判的,認為「自我」所造就的現實其實是阻礙心靈開發的元兇,人無法獲得心靈本心的認識,正是因為受阻於「自我」的「妄識」。
身心靈運動的「反自我」是有原因的。許多實踐的身心靈運動是從人的苦難處出身的,尤其是末期癌症到死亡之間的時間,病人特別受難,一方面外在世界已經逐漸證明其無益於身心靈療癒,即使擁有最好的醫療、最成功的事業、最美好的人間關係,都與眼前的死亡疏離,繼續把心智投入這世界其實是徒勞的,另一方面,「內向轉向」(inward turning)成了一種死亡前的反歸家園,我們真實地感受的內心的害怕、愛、喜悅與痛苦,也希望有相關的論述來支持內在轉向之後的精神領域。
其次,它不是宗教修行。一般宗教修行以教門的教義為修行的框架,依教奉行。但是身心靈療癒並不遵行任何宗教的教義,雖然身心靈運動者可能會在泰國叢林修行,或者在西藏及其鄰近地區(緬甸、尼泊爾、北印度或不丹)追隨喇嘛古魯,但是他們的論述自由出入於老莊、佛、基督、蘇非之間,他們冥想的論述可以摻和禪的靜坐、道的丹功與天主的冥想,身心靈修練者從不忠於任何宗教的意識型態,也不舉旗迎這拒那,望似聯合國的雜牌軍,其實反而是朝向更自由寬廣的心靈世界。
再者,它不是哲學。身心靈運動的論述全非哲學論述那套語法。表面上身心靈書籍與存在哲學很親近,但是那只是觀念的親合,在根本的意涵是非常不相類的。身心靈書籍不太理會思辨,反而類似宗教文本,對某些觀念大力推展。身心靈書籍論述有非常清楚的選言綜合,他們雖然毫無顧忌地使用哲學家的話,但絕不是去質疑它,而是用來輔助自己的觀點。一般的身心靈哲學也不會參考這些身心靈書籍。
實踐性的身心靈書籍通常會在某些特殊領域發揮特定的效果。以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來說,這是一本綜合藏佛大圓滿教法的實踐版,人們可以從前半部獲得具有啟發性的「反俗世」念頭,但在後半部則以臨終照顧的具體施為為著眼點,索甲將藏佛臨終中陰的各種情況放入具體的病人處境。他的弟子龍緹可則是從生活經驗層面,將自己喪夫的過程以及她如何參與安寧照顧的方式,搭配索甲的論述而成為非常實用的準則書。最富有代表性的《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The Grace in Dying:how we are transformed spiritually as we die)這本書則以蘇非的心靈圖誌為引導,細數臨終的各種狀態,以超個體心理學的論述來疏導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許多讀者在他們的親人過世之前,發現這些書是他們在徬徨無依的時刻,所給予的最大的指引。
這世間的知識日益膨脹,但對身心靈的認識卻幾乎不存在。瞭解生理的醫師越不過心理那一圈,瞭解自我心理的心理學家越不過靈性那一圈,而似乎瞭解靈性的宗教師卻常常引經據典到與事實脫節,甚不知所云。許多初接觸身心靈書的讀者常常會覺得不得其門而入,一方面人們越來越不相信那看不見的「領域」,如靈魂、能量、本心等慣用名詞,不是覺得過度抽象就是覺得實證性不夠,另一方面,身心靈書的背後假設與一般知識書很不相同,如果讀者用他的習慣態度來閱讀,往往難以接受身心靈書的論點。
我個人因為長期在臨終病房擔任志工,也做了多年國科會的專案研究,包括對臨終神聖、臨終啟悟、臨終陪伴等議題,使得我不得不注意身心靈書對家屬的幫助。許多朋友在他們親人往生之前,徹夜哭著讀這類書籍,使我動容。我發現,對面臨深淵的人來說,身心靈書籍要有幾個特性才能發揮身心安頓的力量:(一)作者必須有經歷深刻體驗的受苦歷程,並能將受苦與離苦的中間步驟說清楚,而不是談玄說道,信口開河;(二)必須將實徵與理論扣緊,讓引導的圖像具體跟著實情走;(三)作者有深刻的啟悟經驗;(四)不傳任何特定宗教。
我曾經讀過最具震撼力的身心靈書是哥倫比亞大學神學教授盧雲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在他毅然放棄教職,到一家重殘病患之家擔任義工,在他過世的那一年,他寫就一本小書《亞當──神的愛子》(God's Beloved)。亞當是他照顧的一個重殘小孩,無法言語、生活無法自理。盧雲的經驗剛好顛覆一般宗教的觀點,別人憐憫亞當,說他可憐,盧雲卻發現亞當的沈默神性。這是很深刻的東西,盧雲鑽研神學四十年,不如他當義工一年的啟悟。
身心靈書寫的不是知識而是體驗。許多假身心靈書會偷渡超心理學、宗教意識型態。身心靈書籍的正典性來自於對身體的重視。但是對身體的重視不在於養生(如道家的成仙之道),而是某種現代意義的「道成肉身」:身體是修練場,我們在身體的作為裡創造精神(神性)的力量。
〔摘文二〕
輯一 瀕臨╱生死道場
面對生死的姿態(摘錄)
每每談及生死,長輩們總要怨我「哪壺不開提哪壺」,顯見大家都不太願意去談論生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死亡這件事落到言談上,總是怪異;誰也不願見到一天到晚把死亡掛在嘴邊的人,多不健康啊!但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問:為何禪師在修行時要參破生死?參破生死又是何意呢?
貪生──怕死
臨終者往生時,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憂懼,他們不是被死亡嚇死的;真正被嚇到的反而是周遭的活人
長年在安寧病房工作,只消一閉上雙眼,我腦中就會浮現許多陪伴多時的亡者身影。由於工作環境使然,我常覺得不舒服,若是病了,便有醫師和練氣功的朋友極力勸我不要再進出安寧病房,就怕我的氣被吸光。這當然是朋友關心我的好意,但我本身倒不太在意;反正去或不去,最終都是死路一條,有何差別?所以我還是繼續在安寧病房服務。
因生病而觸及生死大事,我意識到:該是面對問題的時候了。坊間有很多書籍告訴我們,要勇敢地面對生死;但是,「面對」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而「勇敢」又是什麼意思呢?
無庸置疑,絕大多數人一想到行將就死,都會害怕不已。美國生死學專家,同時也是知名的精神科醫師庫柏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年輕時就研究發現,每個人都會貪生怕死,但後來也都會接受死亡。接受本身並不困難,問題在於:接受是怎麼發生的?真有「接受」這件事嗎?
正因為死亡令人害怕,所以人們致力於尋求不害怕死亡的方法。然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說,我們若不害怕死亡,根本就過不了死亡這一關;換言之,要經過死亡這道關卡,就一定會害怕。海德格認為,死亡是一個巨大的空洞,所以一定會引起人們的憂懼害怕。其實,害怕是好現象;若是不害怕,就不會轉動;只有害怕才能促進轉動。
住進安寧病房的人,大致心裡已有數,餘生將在病房中度過;有些家屬會在一旁竊竊私語:「現在直直地進來,一定會滿面愁容地橫著出去。」但依我們在醫院長期陪伴所見,橫著出去的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憂懼,他們不是被死亡嚇死的;真正被嚇到的反而是周遭的活人。這之中的奧妙在於,臨終者走上臨終之路時,已經在轉了;還沒走上臨終之路的人,則還沒有轉。臨終的人轉了,就很自然地過去了,不會有擔憂;周遭的活人因為還沒有轉,所以擔憂不已。
活人和臨終者最大的不同是:活人還想繼續活下去,而臨終者已經走在臨終的路上,是親自以行動在轉。因此,若是活著的人對臨終者說,你的時候快到了,你就要走了,臨終者會憤怒;若是勸告臨終者「你要放下」,臨終者會感到被汙辱。因為,臨終者是以實際行動,用全副生命在轉動,而活著的人只是嘴巴上說說罷了,臨終者當然無法接受。
轉動──空無
臨終者的腦細胞已經少到無法理解「我」的過程,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害怕死亡。死亡的空無感是人類的想像,它從未真實存在過
那麼,什麼是「轉動」?臨終者為何會轉動?
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每位臨終者最後都有一個機會背對社會、不理會社會,彷彿轉著轉著,就背對了社會。這種現象,我們名之為「背立轉向」。每一個人病沉到某種程度,便會自然地放棄社會性勾連,也會開始不在乎世間的聲名、地位與角色。經常看到一些知交滿天下的病人,在進入病沉之後,就會在病房門口掛起「拒絕訪客」的牌子,一堆訪客的花籃與卡片凌亂地擺在門外;它們的主人早已進入內在轉動的境界,真正陪伴他的只有夢幻與破碎的回憶而已。
這種轉動,他人無從查覺,是疾病讓臨終者自然地去接受;也許臨終者只是昏睡或是虛弱地躺在床上呻吟,但是轉動的旅程已經開始。只要細心地陪伴,便能發覺臨終者的心思轉動得很快;今天才說:「我要堅持下去,奮鬥下去!」明天可能就說:「都到這個地步了,要放下走了。」他們的情緒轉變就在瞬間。
這主要是兩個機制使然。首先,是腦細胞的大量死亡,才講過的話可能沒多久就忘了;其次,在腦細胞死亡的過程中,患者已不太能理解社會意義,他自己也被掏空了。因此,其實不必太掛念臨終者生前念念不忘的心願,一切都是此一時、彼一時也,沒有一句話是長時間有效的。他們可能上一刻感到痛苦,下一刻又覺得舒服多了;這種轉動一直持續進行著,難以預料,也無法預料。
明白臨終者會有這種轉動,對周遭的活人而言,不啻是個福音;既然會忘,就會忘記生死,因為腦細胞已經少到不知生死為何物了。就像動物瀕臨死亡,也不太容易反省自身即將面臨死亡。人類在大腦最健全的時刻會考慮生死,但在進入死亡的過程時,就進入了無法理解「我」的過程;既不知我的存在,就意味著不害怕死亡。這也許是老天所設計的自動的熄燈號。有了這項安全機制,對死亡何懼之有?
然而,對活著的人而言這個熄燈號畢竟是可怕的。重點是,我們並不瞭解臨終者的意識狀態,沒有必要假裝自己很懂,而要去教導臨終者如何面對生死。相反地,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該如何面對生死?既然我們沒有這個轉動過程,並且要繼續活在「我」的世界中,就必須知道這個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生死的姿態是什麼?
海德格說,死亡是一種巨大的失去、巨大的空無,大到我們的心智無法面對;因此,想到死亡便會不由自主地害怕。我要反駁這項說法。事實上,只有少數的人是如此,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把死亡當成空無。因為,尚未經歷死亡,就無法體會何為空無;而當死神降臨,你已無法感覺,何知空無?
換言之,死亡的空無,根本是人類的想像;當你看到別人垂死,便設身處地想像自己也可能不再存在、不能再這樣和那樣。但是,畢竟一切都是想像;即使真的發生了,你也了無知覺,這種害怕的感覺自然無從發生,那個想像中的空無根本不會來到。更確切地說,那種空無根本不會被你感受到;你現在所感受到的,是想像中用來恐嚇自己的空無,它從未真實存在過,你根本從未有如此經驗。
只要確定面對死亡的憂懼是自己想像出來的;那麼,轉個身,聽首快樂的歌、讀點宗教的勵志文章,可能就快活起來了。想想天國之美、想想極樂世界,甚至是乘願再來,可能就不怕死了;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從憂懼中恢復過來。
既然這個空無不存在,海德格的理論自然要被推翻。他說,因為死亡的空無巨大得可怕,所以讓人願意轉變,變成為一個真摯、願意聽從良心召喚的人,不再過著欺騙的生活。根據這個論點,人們寫出了許多文章。《讀者文摘》就曾刊載一篇,內容描述:美國一名牙醫被醫生判定只剩十年可活;於是,牙醫立即把診所關了,去實現多年的願望──當一名木匠。這類文章透過網路傳播出去,啟發了很多人;於是,有老師辭掉工作去環島旅行,汲汲營生的人不再為生活打拚而去實現夢想等等。當然,這類文章勉勵人要自我實現、忠於自己,也彷彿像童話般有著美好的結局。
但是,海德格這個理論在近年來的各種研究討論上,都不斷被挑戰和懷疑。結果是,上述這些因為害怕死期將近而變得真摯過活的人,其實並沒有處理掉他們對死亡的問題,死亡不會因為真摯生活而改變或停止。也許有人會說,心願已成,死而無憾;但是,問題其實並非這麼簡單。
牙醫改行去當木匠,即使這是他最喜歡的工作和身分,過不了幾年,仍有厭倦的時候;接著,「我要做什麼?」的困惑便會襲捲而來。顯然地,這只是童話式的結局,不能再有續集;否則,王子和公主可能走上離婚一途。換言之,以這種「遮蔽法」要簡單地蓋過死亡這個複雜的問題,並不恰當。
錯認──失算
我們不斷地「錯認」而做了錯誤的行為,這些行為讓我們往相反的路上走,然後因失算而痛苦;卻也因此,讓我們從沉迷中醒悟,瞭解到真正的事實
那麼,有其他解決死亡疑慮的方法嗎?
我們都還活著,就表示我們還擁有自我意識。雖然許多宗教譴責「我」的意識阻擋人生的解脫之道;但不可否認地,這個「我」的確存在。
人有可能縮小自我、或者消解自我,然後瀟灑地走嗎?這個嘗試是失敗的;因為,絕大多數人只縮小了一段時間後,沒幾天自我又恢復了。就像每天揹著二十斤米到山上送給窮困的居民,每回都感動地落下淚來;但連續幾次過後,就不會再流淚了。
我們總是試圖尋找一個解決死亡疑慮的根本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始終不存在;當我們企圖處理它,就會造成荒謬的結果。換言之,解決疾病和死亡的這個「針對性」一旦發生,結果一定是荒謬的。這是很重大的轉折。
舉例而言,有人虔信某種解脫生死的宗教,每天虔誠地讀經、聽開示,反省教義並不斷修為,一心一意企圖解脫生死。這樣求道心切的努力是很了不起;只可惜,把努力正好放到錯誤的位置上了。這就好比一隻被放進透明乾淨玻璃瓶裡的蒼蠅,牠望見瓶外的極樂世界或天國近在眼前,便一心飛往目的地;卻不斷撞壁,怎麼也到不了。
在安寧病房,我們最害怕看到極聰明的人;聰明的人知道自己生命將盡,會不斷追問如何才能解脫生死,獲得身心大安樂。一般沒讀什麼書的阿公、阿嬤並不會問這個問題,他們糊里糊塗地就走了;但聰明的病人會保持著高度精明的意識,他們自我要求不昏不昧,希望能達到一念往生的境界。但是,這樣的信念在安寧病房就顯得難以理解和諷刺;原因在於,他們愈是集中心念想往生所欲之處,便會感到距離愈遠、愈無法到達,與經書所說的「含笑九泉」差別愈大。
這是因為,他們用全副意識僅僅抓取一種名為「修行」的東西,是「抓」來的;但是,真正的死亡過程是「放」。愈是集中強烈意識面對死亡,就愈是無法到達目標境界,完全適得其反;這種行為叫做「錯認」。
我們對我們的人生,不斷地進行「錯認」而做了錯誤的行為;這些行為造成了虛假的想像,讓我們誤以為得以解脫或朝解脫之路邁進;事實上,是剛好往相反的道路上走。
明白被錯認所誤之後,我們就真能及時踩煞車、懸崖勒馬嗎?還是做不到啊!如何能不錯認呢?當一塊石頭還未進行雕琢之前,誰都說它是一塊石頭;但當它被雕成藝術品或某人的石像後,你會說這是什麼作品或直接說出人像的名字,雖然本質上它還是塊石頭。
直接說出作品名稱或石像所代表的人名,這個行為就是錯認,我們要回頭認識它的本質。然而,這也只是理論上的說法,事實上本質是無法認識的。所謂本質,就是隱藏看不見的;從未有任何物質是以本質面貌為人所見。石頭不過是簡單的物質例子,尚有更為抽象的精神層次,如何捕捉本質呢?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要被我們的錯認所誤導。曾有一篇刊在《中國時報》的讀者投書,作者提到她公公生病了,緊急送醫後,公公就此病逝在醫院。作者不解地問:「現在的醫學不是很發達嗎?」她理所當然地認為生病要就醫,但壓根兒沒想到人會這麼死去。這就是被錯認所誤導的真實案例。作者失算了,但這個失算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失算讓我們痛苦,痛苦才讓我們從沉迷中醒悟,才可能了解真正的事實。
換言之,錯誤本身也是一個墊腳石,人就是靠錯誤這塊墊腳石轉身。失婚的女性一定很能理解:當初滿心歡喜地嫁給對方,全心全意甚至不顧一切地付出所有;等到婚姻失敗、結束一切後自己變得一無所有時,才醒悟到女人也應保有財產和獨立的能力,才能站穩雙腳。這個慘痛的經驗,未必讓女人害怕婚姻,但她不會再重蹈覆轍,會保有自己的獨立能力;若有第二次婚姻,通常會更健康而真實。
這就是真真實實的學習,不是口頭上的理論,也不是價值、主義這些高渺的目標,一切按部就班。面對死亡,我們可以按部就班、務實地一步一步來,不必再談超生了死的闊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