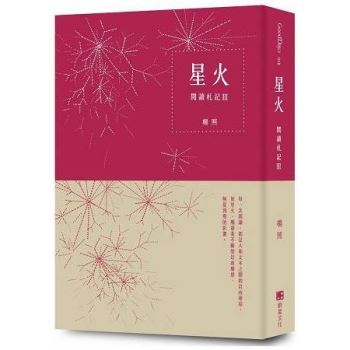1
電影出現在十九世紀末歐洲,那是個奇特的時代,那是書籍享有人類歷史上最高地位的時候,文字文學的影響力也升到最高點。年輕時我看到的電影,就是受到那樣的時代價值影響,一時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電影史前面七十年的主軸其實是認同錯亂,認賊作父。電影以為自己是文字文學,以為自己是書。
為什麼閱讀會和「自我」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因為面對文字,一套抽象的紀錄符號,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沒辦法,因為文字就不是那麼強勢地對你展示聲音、畫面、意義,要先將具體的現象轉譯成符號,然後再在讀者腦中將符號還原成現象。前面的轉譯是作者做的,後面的還原作者就幫不上忙了,只能由讀者自己來做。而且,轉譯不會是完全的轉譯,還原更不可能是完全的還原。
文字逼著我們每個人必須要動用自己的感官,去決定裡面究竟記錄了什麼,因而同樣的文字,不同的人讀來會讀到不一樣的東西,還原為不一樣的現象。這是文字最大的特色,也是文學的本質。
我常常覺得很慶幸自己經歷了、體驗了前面七十年走錯路的電影。那個時代的電影有一個今天已經無法想像的重要標準。什麼叫做好電影?──一部能夠讓不一樣的人看有不一樣感受的電影。好電影讓你得到「自己的」的感受,讓你察覺到你看到的和身旁女朋友看到的不一樣,所以你們能夠一起回味討論,所以你還有機會可以炫耀一下你多看出來的東西。(當然,也有可能是你沮喪地發現她看到的、體會到的,比你多、比你深刻。)認賊作父的電影,變得和文學一樣,逼著你去發現自己,自己的豐富或貧乏。
然而,之後電影醒過來了,它突然發現:「我根本不是文字,為什麼要模仿文字,拿文學當我的標準呢?我真正最大的本事不就在能夠強勢地控制全場,鋪天蓋地決定觀眾的感覺與想法嗎?我要讓你們在這裡覺得女主角多麼值得讓人同情,我要你們哭,你們就哭;我要你們在這裡緊張、害怕,你們就都嚇得縮在椅子裡;我在這裡表現這角色多可惡,就一定可以叫你們恨他。」
電影可以完全操縱!它是那麼強勢的複合感官刺激,它根本不需要觀眾的配合,可以從頭到尾決定觀眾的感受。換句話說,電影輕易就能做到文字絕對做不到的──取消接受上的個別差異,讓每個人看了都得到一樣的感受。電影醒來了,高傲地和文字文學分道揚鑣,從此之後,電影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是我年輕時看電影所不認識的東西──完全操控現場觀眾的情緒跟感受,不讓不一樣的人有不一樣看法的電影就出現了。抱歉,我主觀的偏見,電影從此之後就不好看了。
8
小說家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幼年時在外祖父家,每當外婆要他安安靜靜待著時,就會跟他說:「別亂動,要是亂動,佩特拉表姑就來啦,她正在她的房間裡;要不然拉薩羅表叔就來了,他正在他的房間裡。」佩特拉、拉薩羅,還有許許多多外婆口裡講的人,小賈西亞.馬奎斯都看不見,他們是死去了的人,然而,從外婆口中講來,這些幽靈,所有曾經在這座宅院裡住過生活過的的人,都取得了另一種生命,隨時可能被驚擾,嚇得小男孩一動都不敢動。
外婆還有一套非常複雜的信仰與禁忌,也時時影響小男孩的作息。例如說,陰魂走開前就應該讓小孩睡覺;孩子們躺著的時候,如果有出殯隊伍經過,要叫他們坐起來,以免跟著門口的死人一起走了;應該注意別讓黑蝴蝶飛入家中,因為黑蝴蝶代表死亡;若是金龜子飛進來,那表示有客人要來了;如果聽到怪聲響,那是巫婆進了家門;如果聞到硫磺味,那是因為附近有妖怪……
出了大宅院,外面世界裡,最大的大事,是狂歡節。吉普塞人帶來了各式各樣難得一見的商品。有可以迷惑不順從的女人的「馬古阿鳥粉」、止血用的 「野鹿眼」、避妖術的「四瓣切乾檸檬」、擲骰子時能帶來好運的「聖波洛尼亞大牙」、可保五穀豐登的「乾狐狸骸骨」,能幫助打架和角力中獲勝的「十字架上的嬰孩」、夜晚走路時可免受煉獄中贖罪的幽靈糾纏的「蝙蝠血」……
在如此環境中長大的賈西亞.馬奎斯,一直存留著對世界的特殊印象。活人與死人沒有明確分別的一個世界,每個死掉的人,不會因而消失了他的記憶,他化作幽靈繼續在自己的房間中停留。還有,各種東西間存在著複雜關係的一個世界,互為因果彼此影響,什麼都有可能,從來沒有「不可能」的界線。
賈西亞.馬奎斯從來沒有被現代社會的理性馴服過。理性,是現代人類生活中真正的霸主、真正的統治陰影、真正的必要之惡。理性,尤其是科學理性,協助我們理解世界,其主要方式就是消去法。科學建立起一套套的規則,告訴我們──規則以外的事,絕對不會發生。科學、理性提供現代人空前未有的安全感。我們因為明瞭並相信什麼是絕對不會發生,不須去考慮的,而感到安全。人死了就是死了,幽靈不存在,鬼魂不存在,於是我們就只需要對付活人的世界,不必再分神管那些看不到的死人們,當然就活得輕鬆多了。石頭一定不會變黃金,所以就不必費心去考慮萬物的轉相變形,周圍的東西就嚇不了我們。
科學、理性征服了全世界,因為大家都喜歡這份安全感。不過,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工具,也就被科學、理性收拾得愈來愈少;我們能想像的世界也就愈來愈小。在我們開始與世界接觸之前,科學、理性已經先把世界收拾得只剩下一點點了。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的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中,男主角溫斯頓任職於「大洋國」的「真理部」,負責編字典的部門。
他們編的字典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新版要比舊版薄,每一版都要比前一版薄。也就是利用字典來控制讓日常流通的語彙愈來愈少、愈來愈少,這樣許多「不方便」的語彙消失了,相應地,「不方便」的概念也就消失了,再來,自然就不會有任何批判性反抗性的「不方便」行為了。
人活在狹小的範圍內,不能去想像其他可能性,就會活得很安全、很安分,《一九八四》裡的獨裁者用這種方式統治。科學、理性也用這種方式統治。我們只能看到科學、理性願意讓我們看到的小小空間,以為這乏味、無變化的規律,就是一切。於是,除了臣服於這乏味、無變化的規律之外,別無選擇。
還好,科學、理性,以及所有用乏味無變化的規律來進行統治的技倆,至今無法完全排除藝術、消滅藝術。賈西亞.馬奎斯以他的童年記憶寫出了像《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那樣的小說。小說一開頭就說:「這個世界太新了,還來不及命名,許多事物需要用手指去指。」那是一個拒絕被固定命名的世界,一個所有因果都還有可能的世界,一個開放性的世界。
被稱之為「魔幻寫實」的寫作風格,內裡充滿強烈的政治性。不只是藉由穿梭於活人及死人的空間,馬奎斯及其拉美小說同行,得以鮮活保留獨裁統治下種種「不方便」的往事記憶;更重要的還有,擺明了不接受理性科學排除性規律來主宰「現實」。這批小說提供了現代人難得的喘息機會,重新去探索被 科學、理性剝除掉了的自由。賈西亞.馬奎斯及「魔幻寫實」小說,是現代藝術中的一支。的確,我們不可能去除科學、理性,去過「前理性」的生活,就像我們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各種形式的統治,回歸成真正的自由人。然而,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可以藉由 藝術來探索、來表現我們的想像,在這探索、表現的過程中,反抗統治的必然性。
藝術不是要反抗任何具體形式的統治,因為打倒了一種統治,只會換來另一個新的統治者與統治形式。藝術是要更勇敢地向科學、理性挑戰,向統治概念本身挑戰,不懈地發出訊號,反抗統治,質疑統治的必要性與必然性。藝術不能、也不需創造「非統治」的事實,因為「非統治」很快就會僵化成為另一種新名目的「統治」。藝術要做的、能做的,是提供不斷脫離的經驗,有統治,就有脫離統治的方法,統治與脫離統治的企圖,永遠在角力對抗。這是現代藝術的使命,也是現代藝術維持世界不至於塌縮的具體功能。
電影出現在十九世紀末歐洲,那是個奇特的時代,那是書籍享有人類歷史上最高地位的時候,文字文學的影響力也升到最高點。年輕時我看到的電影,就是受到那樣的時代價值影響,一時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電影史前面七十年的主軸其實是認同錯亂,認賊作父。電影以為自己是文字文學,以為自己是書。
為什麼閱讀會和「自我」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因為面對文字,一套抽象的紀錄符號,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沒辦法,因為文字就不是那麼強勢地對你展示聲音、畫面、意義,要先將具體的現象轉譯成符號,然後再在讀者腦中將符號還原成現象。前面的轉譯是作者做的,後面的還原作者就幫不上忙了,只能由讀者自己來做。而且,轉譯不會是完全的轉譯,還原更不可能是完全的還原。
文字逼著我們每個人必須要動用自己的感官,去決定裡面究竟記錄了什麼,因而同樣的文字,不同的人讀來會讀到不一樣的東西,還原為不一樣的現象。這是文字最大的特色,也是文學的本質。
我常常覺得很慶幸自己經歷了、體驗了前面七十年走錯路的電影。那個時代的電影有一個今天已經無法想像的重要標準。什麼叫做好電影?──一部能夠讓不一樣的人看有不一樣感受的電影。好電影讓你得到「自己的」的感受,讓你察覺到你看到的和身旁女朋友看到的不一樣,所以你們能夠一起回味討論,所以你還有機會可以炫耀一下你多看出來的東西。(當然,也有可能是你沮喪地發現她看到的、體會到的,比你多、比你深刻。)認賊作父的電影,變得和文學一樣,逼著你去發現自己,自己的豐富或貧乏。
然而,之後電影醒過來了,它突然發現:「我根本不是文字,為什麼要模仿文字,拿文學當我的標準呢?我真正最大的本事不就在能夠強勢地控制全場,鋪天蓋地決定觀眾的感覺與想法嗎?我要讓你們在這裡覺得女主角多麼值得讓人同情,我要你們哭,你們就哭;我要你們在這裡緊張、害怕,你們就都嚇得縮在椅子裡;我在這裡表現這角色多可惡,就一定可以叫你們恨他。」
電影可以完全操縱!它是那麼強勢的複合感官刺激,它根本不需要觀眾的配合,可以從頭到尾決定觀眾的感受。換句話說,電影輕易就能做到文字絕對做不到的──取消接受上的個別差異,讓每個人看了都得到一樣的感受。電影醒來了,高傲地和文字文學分道揚鑣,從此之後,電影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是我年輕時看電影所不認識的東西──完全操控現場觀眾的情緒跟感受,不讓不一樣的人有不一樣看法的電影就出現了。抱歉,我主觀的偏見,電影從此之後就不好看了。
8
小說家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幼年時在外祖父家,每當外婆要他安安靜靜待著時,就會跟他說:「別亂動,要是亂動,佩特拉表姑就來啦,她正在她的房間裡;要不然拉薩羅表叔就來了,他正在他的房間裡。」佩特拉、拉薩羅,還有許許多多外婆口裡講的人,小賈西亞.馬奎斯都看不見,他們是死去了的人,然而,從外婆口中講來,這些幽靈,所有曾經在這座宅院裡住過生活過的的人,都取得了另一種生命,隨時可能被驚擾,嚇得小男孩一動都不敢動。
外婆還有一套非常複雜的信仰與禁忌,也時時影響小男孩的作息。例如說,陰魂走開前就應該讓小孩睡覺;孩子們躺著的時候,如果有出殯隊伍經過,要叫他們坐起來,以免跟著門口的死人一起走了;應該注意別讓黑蝴蝶飛入家中,因為黑蝴蝶代表死亡;若是金龜子飛進來,那表示有客人要來了;如果聽到怪聲響,那是巫婆進了家門;如果聞到硫磺味,那是因為附近有妖怪……
出了大宅院,外面世界裡,最大的大事,是狂歡節。吉普塞人帶來了各式各樣難得一見的商品。有可以迷惑不順從的女人的「馬古阿鳥粉」、止血用的 「野鹿眼」、避妖術的「四瓣切乾檸檬」、擲骰子時能帶來好運的「聖波洛尼亞大牙」、可保五穀豐登的「乾狐狸骸骨」,能幫助打架和角力中獲勝的「十字架上的嬰孩」、夜晚走路時可免受煉獄中贖罪的幽靈糾纏的「蝙蝠血」……
在如此環境中長大的賈西亞.馬奎斯,一直存留著對世界的特殊印象。活人與死人沒有明確分別的一個世界,每個死掉的人,不會因而消失了他的記憶,他化作幽靈繼續在自己的房間中停留。還有,各種東西間存在著複雜關係的一個世界,互為因果彼此影響,什麼都有可能,從來沒有「不可能」的界線。
賈西亞.馬奎斯從來沒有被現代社會的理性馴服過。理性,是現代人類生活中真正的霸主、真正的統治陰影、真正的必要之惡。理性,尤其是科學理性,協助我們理解世界,其主要方式就是消去法。科學建立起一套套的規則,告訴我們──規則以外的事,絕對不會發生。科學、理性提供現代人空前未有的安全感。我們因為明瞭並相信什麼是絕對不會發生,不須去考慮的,而感到安全。人死了就是死了,幽靈不存在,鬼魂不存在,於是我們就只需要對付活人的世界,不必再分神管那些看不到的死人們,當然就活得輕鬆多了。石頭一定不會變黃金,所以就不必費心去考慮萬物的轉相變形,周圍的東西就嚇不了我們。
科學、理性征服了全世界,因為大家都喜歡這份安全感。不過,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工具,也就被科學、理性收拾得愈來愈少;我們能想像的世界也就愈來愈小。在我們開始與世界接觸之前,科學、理性已經先把世界收拾得只剩下一點點了。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的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中,男主角溫斯頓任職於「大洋國」的「真理部」,負責編字典的部門。
他們編的字典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新版要比舊版薄,每一版都要比前一版薄。也就是利用字典來控制讓日常流通的語彙愈來愈少、愈來愈少,這樣許多「不方便」的語彙消失了,相應地,「不方便」的概念也就消失了,再來,自然就不會有任何批判性反抗性的「不方便」行為了。
人活在狹小的範圍內,不能去想像其他可能性,就會活得很安全、很安分,《一九八四》裡的獨裁者用這種方式統治。科學、理性也用這種方式統治。我們只能看到科學、理性願意讓我們看到的小小空間,以為這乏味、無變化的規律,就是一切。於是,除了臣服於這乏味、無變化的規律之外,別無選擇。
還好,科學、理性,以及所有用乏味無變化的規律來進行統治的技倆,至今無法完全排除藝術、消滅藝術。賈西亞.馬奎斯以他的童年記憶寫出了像《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那樣的小說。小說一開頭就說:「這個世界太新了,還來不及命名,許多事物需要用手指去指。」那是一個拒絕被固定命名的世界,一個所有因果都還有可能的世界,一個開放性的世界。
被稱之為「魔幻寫實」的寫作風格,內裡充滿強烈的政治性。不只是藉由穿梭於活人及死人的空間,馬奎斯及其拉美小說同行,得以鮮活保留獨裁統治下種種「不方便」的往事記憶;更重要的還有,擺明了不接受理性科學排除性規律來主宰「現實」。這批小說提供了現代人難得的喘息機會,重新去探索被 科學、理性剝除掉了的自由。賈西亞.馬奎斯及「魔幻寫實」小說,是現代藝術中的一支。的確,我們不可能去除科學、理性,去過「前理性」的生活,就像我們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各種形式的統治,回歸成真正的自由人。然而,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可以藉由 藝術來探索、來表現我們的想像,在這探索、表現的過程中,反抗統治的必然性。
藝術不是要反抗任何具體形式的統治,因為打倒了一種統治,只會換來另一個新的統治者與統治形式。藝術是要更勇敢地向科學、理性挑戰,向統治概念本身挑戰,不懈地發出訊號,反抗統治,質疑統治的必要性與必然性。藝術不能、也不需創造「非統治」的事實,因為「非統治」很快就會僵化成為另一種新名目的「統治」。藝術要做的、能做的,是提供不斷脫離的經驗,有統治,就有脫離統治的方法,統治與脫離統治的企圖,永遠在角力對抗。這是現代藝術的使命,也是現代藝術維持世界不至於塌縮的具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