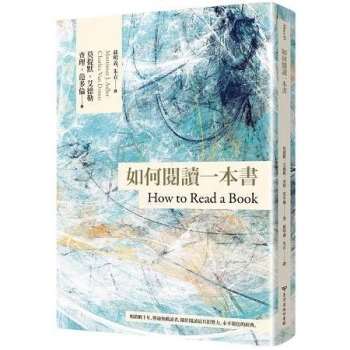第一章 閱讀的活力與藝術
這是一本為閱讀的人,或是想要成為閱讀的人而寫的書。尤其是想要閱讀書的人。說得更具體一點,這本書是為那些想把讀書的主要目的當作是增進理解能力的人而寫。
這裡所謂「閱讀的人」(readers),是指那些今天仍然習慣於從書寫文字中汲取大量資訊,以增進對世界了解的人,就和過去歷史上每一個深有教養、智慧的人別無二致。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即使在收音機、電視沒有出現以前,許多資訊與知識也是從口傳或觀察而得。但是對智能很高又充滿好奇心的人來說,這樣是不夠的。他們知道他們還得閱讀,而他們也真的身體力行。
現代的人有一種感覺,讀書這件事好像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必要了。收音機,特別是電視,取代了以往由書本所提供的部分功能,就像照片取代了圖畫或藝術設計的部分功能一樣。我們不得不承認,電視有部分的功能確實很驚人,譬如對新聞事件的影像處理,就有極大的影響力。收音機最大的特點在當我們手邊正在做某件事(譬如開車)的時候,仍然能提供我們資訊,為我們節省不少的時間。但在這中間還是有一個嚴肅的議題:到底這些新時代的傳播媒體是否真能增進我們對自己世界的了解?
或許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比以前的人多了,在某種範圍內,知識(knowledge)也成了理解(understanding)的先決條件。這些都是好事。但是,「知識」是否那麼必然是「理解」的先決條件,可能和一般人的以為有相當差距。我們為了「理解」(understand)一件事,並不需要「知道」(know)和這件事相關的所有事情。太多的資訊就如同太少的資訊一樣,都是一種對理解力的阻礙。換句話說,現代的媒體正以壓倒性的氾濫資訊阻礙了我們的理解力。
會發生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所提到的這些媒體,經過太精心的設計,使得思想形同沒有需要了(雖然只是表相如此)。如何將知識份子的態度與觀點包裝起來,是當今最有才智的人在做的最活躍的事業之一。電視觀眾、收音機聽眾、雜誌讀者所面對的是一種複雜的組成—從獨創的華麗辭藻到經 審慎挑選的資料與統計—目的都在讓人不需要面對困難或努力,很容易就整理出「自己」的思緒。但是這些精美包裝的資訊效率實在太高了,讓觀眾、聽眾或讀者根本用不著自己做結論。相反的,他們直接將包裝過後的觀點裝進自己的腦海中,就像錄影機願意接受錄影帶一樣自然。他只要按一個「倒帶」的鈕,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適當言論。他根本不用思考就能表現得宜。
主動的閱讀
我們在一開始就說過,我們是針對發展閱讀書的技巧而寫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跟隨並鍛練這些閱讀的技巧,你便可以將這些技巧應用在任何印刷品的閱讀上—報紙、雜誌、小冊子、文章、短訊,甚至廣告。
既然任何一種閱讀都是一種活動,那就必需要有一些主動的活力。完全被動,就閱讀不了—我們不可能在雙眼停滯、頭腦昏睡的狀況下閱讀。既然閱讀有主動、被動之對比,那麼我們的目標就是:第一提醒讀者,閱讀可以是一件多少主動的事。第二要指出的是,閱讀越主動,效果越好。這個讀者比另一個讀者更主動一些,他在閱讀世界裡面的探索能力就更強一些,收穫更多一些,因而也更高明一些。讀者對他自己,以及自己面前的書籍,要求得越多,獲得的就越多。
雖然嚴格說來,不可能有完全被動閱讀這回事,但還是有許多人認為,比起充滿主動的寫跟說,讀與聽完全是被動的事。寫作者及演說者起碼必需要花一點力氣,聽眾或讀者卻什麼也不必做。聽眾或讀者被當作是一種溝通接收器,「接受」對方很賣力地在「給予」、「發送」的訊息。這種假設的謬誤,在認為這種「接收」類同於被打了一拳,或得到一項遺產,或法院的判決。其實完全相反,聽眾或讀者的「接收」,應該像是棒球賽中的捕手才對。
捕手在接球時所發揮的主動是跟投手或打擊手一樣的。投手或打擊手是負責「發送」的工作,他的行動概念就是在讓球動起來的這件事上。捕手或外野手的責任是「接收」,他的行動就是要讓球停下來的這件事上。兩者都是一種活動,只是方式有點不同。如果說有什麼是被動的,就是那只球了。球是毫無感覺的,可以被投手投出去,也可以被捕手接住,完全看打球的人如何玩法。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也很類似。寫作與閱讀的東西就像那只球一樣,是被主動、有活力的雙方所共有的,是由一方開始,另一方終結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類比的概念往前推。捕手的藝術就在能接住任何球的技巧—快速球、曲線球、變化球、慢速球等等。同樣的,閱讀的藝術也在盡可能掌握住每一種訊息的技巧。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捕手與投手密切合作時,才會成功。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也是如此。作者不會故意投對方接不到的球,儘管有時候看來如此。在任何案例中,成功的溝通都發生於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剛好被讀者掌握住了。作者的技巧與讀者的技巧融合起來,便達到共同的終點。
事實上,作者就很像是一位投手。有些作者完全知道如何「控球」:他們完全知道自己要傳達的是什麼,也精準正確地傳達出去了。因此很公平地,比起一個毫無「控球」能力的「暴投」作家,他們是比較容易被讀者所「接住」的。
這個比喻有一點不恰當的是:球是一個單純的個體,不是被完全接住,就是沒接住。而一本作品,卻是一個複雜的物件,可能被接受得多一點,可能少一點;從只接受到作者一點點概念到接受了整體意念,都有可能。讀者想「接住」多少意念完全看他在閱讀時多麼主動,以及他投入不同心思來閱讀的技巧如何。
主動的閱讀包含哪些條件?在這本書中我們會反覆談到這個問題。此刻我們只能說:拿同樣的書給不同的人閱讀,一個人卻讀得比另一個人好這件事,首先在於這人的閱讀更主動,其次,在於他在閱讀中的每一種活動都參與了更多的技巧。這兩件事是息息相關的。閱讀是一個複雜的活動,就跟寫作一樣,包含了大量不同的活動。要達成良好的閱讀,這些活動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人越能運作這些活動,閱讀的效果就越好。
閱讀的目標:為獲得資訊而讀,以及為求得理解而讀
你有一個頭腦。現在讓我再假設你有一本想要讀的書。這本書是某個人用文字書寫的,想要與你溝通一些想法。你要能成功的閱讀這本書,完全看你能接獲多少作者想要傳達的訊息。
當然,這樣說太簡單了。因為在你的頭腦與書本之間可能會產生兩種關係,而不是一種。閱讀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經驗可以象徵這兩種不同的關係。
這是書,那是你的頭腦。你在閱讀一頁頁的時候,對作者想要說的話不是很了解,就是不了解。如果很了解,你就獲得了資訊(但你的理解不一定增強)。如果這本書從頭到尾都是你明白的,那麼這個作者跟你就是兩個頭腦卻在同一個模子裡鑄造出來的。這本書中的訊息只是將你還沒讀這本書之前,你們便共同了解的東西傳達出來而已。讓我們來談談第二種情況。你並不完全了解這本書。讓我們假設—不幸的是並非經常如此—你對這本書的了解程度,剛好讓你明白其實你並不了解這本書。你知道這本書要說的東西超 你所了解的,因此認為這本書包含了某些能增進你理解的東西。
那你該怎麼辦?你可以把書拿給某個人,你認為他讀得比你好的人,請他替你解釋看不懂的地方。(「他」可能代表一個人,或是另一本書—導讀的書或教科書。)或是你會決定,不值得為任何超越你頭腦理解範圍之外的書傷腦筋,你理解得已經夠多了。不管是上述哪一種狀況,你都不是本書所說的真正的在閱讀。
只有一種方式是真正的在閱讀。不要有任何外力的幫助,你就是要讀這本書。你什麼都沒有,只憑著內心的力量,玩味著眼前的字句,慢慢的提升自己,從只有模糊的概念到更清楚的理解為止。這樣的一種提升,是在閱讀時的一種腦力活動,也是更高的閱讀技巧。這種閱讀就是讓一本書向你既有的理解力做挑戰。
這樣我們就可以粗略地為所謂的閱讀藝術下個定義:這是一個憑藉著頭腦運作,除了玩味讀物中的一些字句之外,不假任何外助,以一己之力來提升自我的 程。1你的頭腦會從粗淺的了解推進到深入的理解。而會產生這種結果的運作技巧,就是由許多不同活動所組合成的閱讀的藝術。
憑著你自己的心智活動努力閱讀,從只有粗淺的了解推進到深入的體會,就像是自我的破繭而出。感覺上確實就是如此。這是最主要的作用。當然,這比你以前的閱讀方式要多了很多活動,而且不只是有更多的活動,還有要完成這些多元化活動所需要的技巧。除此之外,當然,通常需要比較高難度閱讀要求的讀物,都有其相對應的價值,以及相對應水平的讀者。
為獲得資訊而閱讀,與為增進理解而閱讀,其間的差異不能以道里計。我們再多談一些。我們必需要考慮到兩種閱讀的目的。因為一種是讀得懂的東西,另一種是必需要讀的東西,二者之間的界限通常是很模糊的。在我們可以讓這兩種閱讀目的區分開來的範圍內,我們可以將「閱讀」這個詞,區分成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種意義是我們自己在閱讀報紙、雜誌,或其他的東西時,憑我們的閱讀技巧與聰明才智,一下子便能融會貫通了。這樣的讀物能增加我們的資訊,卻不能增進我們的理解力,因為在開始閱讀之前,我們的理解力就已經與他們完全相當了。否則,我們一路讀下來早就應該被困住或嚇住了—這是說如果我們夠誠實、夠敏感的話。
第二種意義是一個人試著讀某樣他一開始並不怎麼了解的東西。這個東西的水平就是比閱讀的人高上一截。這個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能增進閱讀者的理解力。這種雙方水準不齊之下的溝通,肯定是會發生的,否則,無論是透 演講或書本,誰都永遠不可能從別人身上學習到東西了。這裡的「學習」指的是理解更多的事情,而不是記住更多的資訊—和你已經知道的資訊在同一水平的資訊。
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要從閱讀中獲得一些和他原先熟知的事物相類似的新資訊,並不是很困難的事。一個人對美國歷史已經知道一些資料,也有一些理解的角度時,他只要用第一種意義的閱讀,就可以獲得更多的類似資料,並且繼續用原來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假設他閱讀的歷史書不只是提供給他更多資訊,而且還在他已經知道的資訊當中,給他全新的或更高層次的啟發。也就是說,他從中獲得的理解超越了他原有的理解。如果他能試著掌握這種更深一層的理解,他就是在做第二種意義的閱讀了。他透 閱讀的活動間接地提升了自己,當然,不是作者有可以教他的東西也達不到這一點。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我們會為了增進理解而閱讀?有兩種狀況:第一是一開始時不相等的理解程度。在對一本書的理解力上,作者一定要比讀者來得「高桿」,寫書時一定要用可讀的形式來傳達他有而讀者所無的洞見。其次,閱讀的人一定要把不相等的理解力克服到一定程度之內,雖然不能說全盤了解,但總是要達到與作者相當的程度。一旦達到相同的理解程度,就完成了清楚的溝通。
簡單來說,我們只能從比我們「更高桿」的人身上學習。我們一定要知道他們是誰,如何跟他們學習。有這種想法的人,就是能認知閱讀藝術的人,就是我們這本書主要關心的對象。而任何一個可以閱讀的人,都有能力用這樣的方式來閱讀。只要我們努力運用這樣的技巧在有益的讀物上,每個人都能讀得更好,學得更多,毫無例外。我們並不想給予讀者這樣的印象:事實上,運用閱讀以增加資訊與洞察力,與運用閱讀增長理解力是很容易區分出來的。我們必須承認,有時候光是聽別人轉述一些訊息,也能增進很多的理解。在這裡我們想要強調的是:這本書是關於閱讀的藝術,是為了增強理解力而寫的。幸運的是,只要你學會了這一點,為獲取資訊而閱讀的另一點也就不是問題了。
當然,除了獲取資訊與理解外,閱讀還有一些其他的目標,就是娛樂。無論如何,本書不會談論太多有關娛樂消遣的閱讀部分。那是最沒有要求,也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做到的事。而且那樣的閱讀也沒有任何規則。任何人只要能閱讀,想閱讀,就能找一份讀物來消遣。
事實上,任何一本書能增進理解或增加資訊時,也就同時有了消遣的效果。就像一本能夠增進我們理解力的書,也可以純粹只讀其中所包含的資訊一樣。(這個情況並不是倒 來也成立:並不是每一種拿來消遣的書,都能當作增進我們的理解力來讀。)我們也絕不是在鼓勵你絕不要閱讀任何消遣的書。重點在,如果你想要讀一本有助於增進理解力的好書,那我們是可以幫得上忙的。因此,如果增進理解力是你的目標,我們的主題就是閱讀好書的藝術。
這是一本為閱讀的人,或是想要成為閱讀的人而寫的書。尤其是想要閱讀書的人。說得更具體一點,這本書是為那些想把讀書的主要目的當作是增進理解能力的人而寫。
這裡所謂「閱讀的人」(readers),是指那些今天仍然習慣於從書寫文字中汲取大量資訊,以增進對世界了解的人,就和過去歷史上每一個深有教養、智慧的人別無二致。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即使在收音機、電視沒有出現以前,許多資訊與知識也是從口傳或觀察而得。但是對智能很高又充滿好奇心的人來說,這樣是不夠的。他們知道他們還得閱讀,而他們也真的身體力行。
現代的人有一種感覺,讀書這件事好像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必要了。收音機,特別是電視,取代了以往由書本所提供的部分功能,就像照片取代了圖畫或藝術設計的部分功能一樣。我們不得不承認,電視有部分的功能確實很驚人,譬如對新聞事件的影像處理,就有極大的影響力。收音機最大的特點在當我們手邊正在做某件事(譬如開車)的時候,仍然能提供我們資訊,為我們節省不少的時間。但在這中間還是有一個嚴肅的議題:到底這些新時代的傳播媒體是否真能增進我們對自己世界的了解?
或許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比以前的人多了,在某種範圍內,知識(knowledge)也成了理解(understanding)的先決條件。這些都是好事。但是,「知識」是否那麼必然是「理解」的先決條件,可能和一般人的以為有相當差距。我們為了「理解」(understand)一件事,並不需要「知道」(know)和這件事相關的所有事情。太多的資訊就如同太少的資訊一樣,都是一種對理解力的阻礙。換句話說,現代的媒體正以壓倒性的氾濫資訊阻礙了我們的理解力。
會發生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所提到的這些媒體,經過太精心的設計,使得思想形同沒有需要了(雖然只是表相如此)。如何將知識份子的態度與觀點包裝起來,是當今最有才智的人在做的最活躍的事業之一。電視觀眾、收音機聽眾、雜誌讀者所面對的是一種複雜的組成—從獨創的華麗辭藻到經 審慎挑選的資料與統計—目的都在讓人不需要面對困難或努力,很容易就整理出「自己」的思緒。但是這些精美包裝的資訊效率實在太高了,讓觀眾、聽眾或讀者根本用不著自己做結論。相反的,他們直接將包裝過後的觀點裝進自己的腦海中,就像錄影機願意接受錄影帶一樣自然。他只要按一個「倒帶」的鈕,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適當言論。他根本不用思考就能表現得宜。
主動的閱讀
我們在一開始就說過,我們是針對發展閱讀書的技巧而寫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跟隨並鍛練這些閱讀的技巧,你便可以將這些技巧應用在任何印刷品的閱讀上—報紙、雜誌、小冊子、文章、短訊,甚至廣告。
既然任何一種閱讀都是一種活動,那就必需要有一些主動的活力。完全被動,就閱讀不了—我們不可能在雙眼停滯、頭腦昏睡的狀況下閱讀。既然閱讀有主動、被動之對比,那麼我們的目標就是:第一提醒讀者,閱讀可以是一件多少主動的事。第二要指出的是,閱讀越主動,效果越好。這個讀者比另一個讀者更主動一些,他在閱讀世界裡面的探索能力就更強一些,收穫更多一些,因而也更高明一些。讀者對他自己,以及自己面前的書籍,要求得越多,獲得的就越多。
雖然嚴格說來,不可能有完全被動閱讀這回事,但還是有許多人認為,比起充滿主動的寫跟說,讀與聽完全是被動的事。寫作者及演說者起碼必需要花一點力氣,聽眾或讀者卻什麼也不必做。聽眾或讀者被當作是一種溝通接收器,「接受」對方很賣力地在「給予」、「發送」的訊息。這種假設的謬誤,在認為這種「接收」類同於被打了一拳,或得到一項遺產,或法院的判決。其實完全相反,聽眾或讀者的「接收」,應該像是棒球賽中的捕手才對。
捕手在接球時所發揮的主動是跟投手或打擊手一樣的。投手或打擊手是負責「發送」的工作,他的行動概念就是在讓球動起來的這件事上。捕手或外野手的責任是「接收」,他的行動就是要讓球停下來的這件事上。兩者都是一種活動,只是方式有點不同。如果說有什麼是被動的,就是那只球了。球是毫無感覺的,可以被投手投出去,也可以被捕手接住,完全看打球的人如何玩法。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也很類似。寫作與閱讀的東西就像那只球一樣,是被主動、有活力的雙方所共有的,是由一方開始,另一方終結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類比的概念往前推。捕手的藝術就在能接住任何球的技巧—快速球、曲線球、變化球、慢速球等等。同樣的,閱讀的藝術也在盡可能掌握住每一種訊息的技巧。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捕手與投手密切合作時,才會成功。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也是如此。作者不會故意投對方接不到的球,儘管有時候看來如此。在任何案例中,成功的溝通都發生於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剛好被讀者掌握住了。作者的技巧與讀者的技巧融合起來,便達到共同的終點。
事實上,作者就很像是一位投手。有些作者完全知道如何「控球」:他們完全知道自己要傳達的是什麼,也精準正確地傳達出去了。因此很公平地,比起一個毫無「控球」能力的「暴投」作家,他們是比較容易被讀者所「接住」的。
這個比喻有一點不恰當的是:球是一個單純的個體,不是被完全接住,就是沒接住。而一本作品,卻是一個複雜的物件,可能被接受得多一點,可能少一點;從只接受到作者一點點概念到接受了整體意念,都有可能。讀者想「接住」多少意念完全看他在閱讀時多麼主動,以及他投入不同心思來閱讀的技巧如何。
主動的閱讀包含哪些條件?在這本書中我們會反覆談到這個問題。此刻我們只能說:拿同樣的書給不同的人閱讀,一個人卻讀得比另一個人好這件事,首先在於這人的閱讀更主動,其次,在於他在閱讀中的每一種活動都參與了更多的技巧。這兩件事是息息相關的。閱讀是一個複雜的活動,就跟寫作一樣,包含了大量不同的活動。要達成良好的閱讀,這些活動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人越能運作這些活動,閱讀的效果就越好。
閱讀的目標:為獲得資訊而讀,以及為求得理解而讀
你有一個頭腦。現在讓我再假設你有一本想要讀的書。這本書是某個人用文字書寫的,想要與你溝通一些想法。你要能成功的閱讀這本書,完全看你能接獲多少作者想要傳達的訊息。
當然,這樣說太簡單了。因為在你的頭腦與書本之間可能會產生兩種關係,而不是一種。閱讀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經驗可以象徵這兩種不同的關係。
這是書,那是你的頭腦。你在閱讀一頁頁的時候,對作者想要說的話不是很了解,就是不了解。如果很了解,你就獲得了資訊(但你的理解不一定增強)。如果這本書從頭到尾都是你明白的,那麼這個作者跟你就是兩個頭腦卻在同一個模子裡鑄造出來的。這本書中的訊息只是將你還沒讀這本書之前,你們便共同了解的東西傳達出來而已。讓我們來談談第二種情況。你並不完全了解這本書。讓我們假設—不幸的是並非經常如此—你對這本書的了解程度,剛好讓你明白其實你並不了解這本書。你知道這本書要說的東西超 你所了解的,因此認為這本書包含了某些能增進你理解的東西。
那你該怎麼辦?你可以把書拿給某個人,你認為他讀得比你好的人,請他替你解釋看不懂的地方。(「他」可能代表一個人,或是另一本書—導讀的書或教科書。)或是你會決定,不值得為任何超越你頭腦理解範圍之外的書傷腦筋,你理解得已經夠多了。不管是上述哪一種狀況,你都不是本書所說的真正的在閱讀。
只有一種方式是真正的在閱讀。不要有任何外力的幫助,你就是要讀這本書。你什麼都沒有,只憑著內心的力量,玩味著眼前的字句,慢慢的提升自己,從只有模糊的概念到更清楚的理解為止。這樣的一種提升,是在閱讀時的一種腦力活動,也是更高的閱讀技巧。這種閱讀就是讓一本書向你既有的理解力做挑戰。
這樣我們就可以粗略地為所謂的閱讀藝術下個定義:這是一個憑藉著頭腦運作,除了玩味讀物中的一些字句之外,不假任何外助,以一己之力來提升自我的 程。1你的頭腦會從粗淺的了解推進到深入的理解。而會產生這種結果的運作技巧,就是由許多不同活動所組合成的閱讀的藝術。
憑著你自己的心智活動努力閱讀,從只有粗淺的了解推進到深入的體會,就像是自我的破繭而出。感覺上確實就是如此。這是最主要的作用。當然,這比你以前的閱讀方式要多了很多活動,而且不只是有更多的活動,還有要完成這些多元化活動所需要的技巧。除此之外,當然,通常需要比較高難度閱讀要求的讀物,都有其相對應的價值,以及相對應水平的讀者。
為獲得資訊而閱讀,與為增進理解而閱讀,其間的差異不能以道里計。我們再多談一些。我們必需要考慮到兩種閱讀的目的。因為一種是讀得懂的東西,另一種是必需要讀的東西,二者之間的界限通常是很模糊的。在我們可以讓這兩種閱讀目的區分開來的範圍內,我們可以將「閱讀」這個詞,區分成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種意義是我們自己在閱讀報紙、雜誌,或其他的東西時,憑我們的閱讀技巧與聰明才智,一下子便能融會貫通了。這樣的讀物能增加我們的資訊,卻不能增進我們的理解力,因為在開始閱讀之前,我們的理解力就已經與他們完全相當了。否則,我們一路讀下來早就應該被困住或嚇住了—這是說如果我們夠誠實、夠敏感的話。
第二種意義是一個人試著讀某樣他一開始並不怎麼了解的東西。這個東西的水平就是比閱讀的人高上一截。這個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能增進閱讀者的理解力。這種雙方水準不齊之下的溝通,肯定是會發生的,否則,無論是透 演講或書本,誰都永遠不可能從別人身上學習到東西了。這裡的「學習」指的是理解更多的事情,而不是記住更多的資訊—和你已經知道的資訊在同一水平的資訊。
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要從閱讀中獲得一些和他原先熟知的事物相類似的新資訊,並不是很困難的事。一個人對美國歷史已經知道一些資料,也有一些理解的角度時,他只要用第一種意義的閱讀,就可以獲得更多的類似資料,並且繼續用原來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假設他閱讀的歷史書不只是提供給他更多資訊,而且還在他已經知道的資訊當中,給他全新的或更高層次的啟發。也就是說,他從中獲得的理解超越了他原有的理解。如果他能試著掌握這種更深一層的理解,他就是在做第二種意義的閱讀了。他透 閱讀的活動間接地提升了自己,當然,不是作者有可以教他的東西也達不到這一點。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我們會為了增進理解而閱讀?有兩種狀況:第一是一開始時不相等的理解程度。在對一本書的理解力上,作者一定要比讀者來得「高桿」,寫書時一定要用可讀的形式來傳達他有而讀者所無的洞見。其次,閱讀的人一定要把不相等的理解力克服到一定程度之內,雖然不能說全盤了解,但總是要達到與作者相當的程度。一旦達到相同的理解程度,就完成了清楚的溝通。
簡單來說,我們只能從比我們「更高桿」的人身上學習。我們一定要知道他們是誰,如何跟他們學習。有這種想法的人,就是能認知閱讀藝術的人,就是我們這本書主要關心的對象。而任何一個可以閱讀的人,都有能力用這樣的方式來閱讀。只要我們努力運用這樣的技巧在有益的讀物上,每個人都能讀得更好,學得更多,毫無例外。我們並不想給予讀者這樣的印象:事實上,運用閱讀以增加資訊與洞察力,與運用閱讀增長理解力是很容易區分出來的。我們必須承認,有時候光是聽別人轉述一些訊息,也能增進很多的理解。在這裡我們想要強調的是:這本書是關於閱讀的藝術,是為了增強理解力而寫的。幸運的是,只要你學會了這一點,為獲取資訊而閱讀的另一點也就不是問題了。
當然,除了獲取資訊與理解外,閱讀還有一些其他的目標,就是娛樂。無論如何,本書不會談論太多有關娛樂消遣的閱讀部分。那是最沒有要求,也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做到的事。而且那樣的閱讀也沒有任何規則。任何人只要能閱讀,想閱讀,就能找一份讀物來消遣。
事實上,任何一本書能增進理解或增加資訊時,也就同時有了消遣的效果。就像一本能夠增進我們理解力的書,也可以純粹只讀其中所包含的資訊一樣。(這個情況並不是倒 來也成立:並不是每一種拿來消遣的書,都能當作增進我們的理解力來讀。)我們也絕不是在鼓勵你絕不要閱讀任何消遣的書。重點在,如果你想要讀一本有助於增進理解力的好書,那我們是可以幫得上忙的。因此,如果增進理解力是你的目標,我們的主題就是閱讀好書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