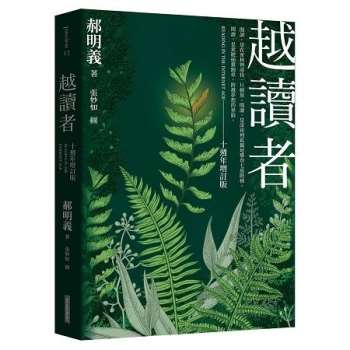〈無辜的網路〉
*人類一直有一種方便了,就不想閱讀的根性。
有一次演講結束後,聽眾交流的時間,有兩位女士先後發言。
先發言的顯然是一位母親,她為孩子日益偏向於使用網路而不接近書籍而煩惱;後發言的則似乎是一位當姊姊的人,她認為毋須為孩子操心那麼多,他們自有出路。就像我們自己,父母也曾為我們操心很多,但我們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兩位針鋒相對了一陣,令我印象深刻。
閱讀本來就是各說各話的事情。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談、談了這麼久的時間,結果還是得不斷地談。
網路風行之後,給我們新添的一個苦惱是,給「閱讀」這件事情增添了更多容易講不清、分辨不清的面貌。
所以,對於網路,最常聽到的一個說法,就是網路使得人遠離了書。甚至,遠離了閱讀。
但,真的是這樣嗎?
翻開人類的歷史,我們總是拚命想把閱讀這件事情變得比較容易,比較便利些。
文字和圖畫,從早期刻在石頭上、動物甲殼上、竹子上,到寫到皮革上、紙張上,到印刷、裝訂成冊,再到轉化為電子與數位型態,可以用電腦、手機與其他行動載具來顯示,我們一直希望把閱讀這件事情變得越方便越好。
從最早只有和神界可以溝通的祭司才有資格閱讀,到王公貴族壟斷閱讀的權利,再到民間富有之家也可以閱讀,再到推廣給更普及的人民,終於成為人人皆須接受國民教育,我們一直希望閱讀的能力與機會,能推廣到越多的人手上越好。
但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想把閱讀推廣與普及的力量越大,吸引我們不想閱讀的力量也就越來越大。
在中國,公元十一世紀的宋代,印刷術大盛,突破了過去書籍只能用手抄的,費時又少量的侷限,於是各種書籍的種類和數量都擴大,「莫之不有」。但也就在這時,蘇東坡寫了〈李氏山房藏書記〉,感嘆過去書籍取得不易的時代,大家願意千里迢迢追尋一本自己想讀的書,但到了什麼書都有了的時候,卻反而大都不愛讀書,只顧得「游談無根」(愛八卦)。到了清朝,書籍出版得更多了,袁枚寫〈黃生借書說〉,感嘆就比蘇東坡的時代又多了一層。
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情況。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帶動起「民主」與「國家」的觀念,在推動國民的教育與閱讀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與影響。同一時間,工業革命所帶動的印刷技術的改良,在書籍演進史上也有很關鍵的影響。然而也就在那之後不久,火車出現了,於是很多人感嘆過去大家願意守在家裡安安靜靜讀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現在都急於到處去旅行了。
大約一百年後,十九世紀末的時候,英國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把出版者與印刷者的角色做了劃時代的分工,出版產業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書籍的樣貌與形式也有了很大的革新。不過,這時電話出現了。於是,像梭羅這樣的很多人又開始感嘆,過去大家可以在火車上旅行,安安靜靜讀點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現在,大家只愛在電話上煲電話粥了。
進入了二十世紀的20年代,西方出現了平裝本革命,書籍再次以前所未有的便宜價格,與方便攜帶的形式出現。書籍與大眾之間,出現了零距離。但是也就在這之後不久,電視登場了。電視登堂入室的結果,使更多人感嘆我們離閱讀這件事又遠了。
二十世紀末,網際網路(internet)現身,人類自有書籍以來的最關鍵一次的革命,登場了。原先是美國學術機構裡,方便大家為了交流論文而發展出來的網際網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到90年代終於普及到每一個人手上。閱讀,突破了書籍時代所面臨的空間與時間障礙。但也就在這同時,網上各種遊戲與娛樂的風行,讓許多人又感嘆,我們從沒有如此背離閱讀的可能。
我們一直想把閱讀這件事情弄得更普及,更便利。
然而,閱讀越是方便的時候,我們越是不想閱讀。
人性如此。從來如此。和網路無關。
〈為什麼不必是文字與書〉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
那兩位女士的發言,表面看來像是兩個極端,但事實上是同一個出發點。
第一位母親的發言,太過重視書的作用了。
那位當姊姊的發言,表面看來雖然顯示了她對「網路」與「書」的平等對待,但是她引用今天之前的人曾經自己找到出路,而對下一代的人主張平常心看待,則又忽視了今天面對的變局,是人類過去所從未有過的。
一個閱讀的嶄新時代已經來臨,如果只是援用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經驗,遠遠不夠。只是主張以平常心來看待「網路」與「書」,同樣也只是延續書籍時代的思維而已。今天大家都在談網路帶來的閱讀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的真實面貌,很容易隱沒在烽火的煙霧之中。像那位母親,許多人擔心網路挾帶著大量影像、聲音,會不會徹底破壞(尤其是以書籍來呈現的)文字的閱讀。
要思考這個問題,不妨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字與書籍,對我們到底有什麼意義?」
人類發明文字,不論中西,大約都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事。
懂得利用文字,在人類幾百萬年的進化史上,當然是極為震撼的一件事。人類的思想,從此便於同輩人交流,前後代流傳。古人說倉頡發明文字後,「造化不能藏其祕,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可以說明這個事件的震撼性。近代科學研究指出,閱讀及使用文字對大腦及智力的重要性,則更有許多書籍與論述,這裡不再贅述。
至於書籍這件事情,就是更近的事情了。人類有紙張,是大約二千年的事;有印刷術,在中國大約是一千四百年,西方大約五百多年的事。而中文世界裡,習慣以目前我們常見的書籍形式來閱讀,則不過是一百多年的事情。
總之,在人類演化的四百萬年歷史中,從五千年前學會閱讀文字、一千年前懂得使用書籍之後,雖然給人類的文明與文化發展,都帶來遠非其前所擬的推展,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文字與書籍的重要性再大,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這頂多五、六千年的演變,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
文字與書的出現雖然晚,人類的閱讀可不是。早從非常遙遠的過去,我們的閱讀就開始了。只是那時候的方式不同而已。
那時的閱讀可能是白天看地上野獸的足跡,可能是夜裡仰望天上的星星;可能是看山洞裡的壁畫,更可能是聽別人的口述。
文字出現的好處是,多了一個可以極為抽象又方便地認知這個世界的方式;壞處是,我們原先綜合運用各種感官的全觀能力逐漸退化。書籍出現的好處是,把文字的傳播力量做到最大的擴散;壞處是,我們容易疏忽──甚至,貶低──書籍以外的知識來源。
柏拉圖講過一個文字剛發明時候的故事。埃及的一個古神⋯⋯名字是圖提。他首先發明了數目、算術、幾何和天文⋯⋯尤其重要的是他發明了文字。當時全埃及都受塔穆斯的統治⋯⋯圖提晉見了塔穆斯,把他的各種發明獻給他看,向他建議要把它們推廣到全埃及。那國王便問他每一種發明的用處⋯⋯輪到文字,圖提說:「大王,這件發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記憶力,它是醫治教育和記憶力的良藥!」
聽了圖提的說明,埃及國王回答了下面這麼一段話:
現在你是文字的父親,由於篤愛兒子的緣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說反了!你這個發明結果會使學會文字的人們善忘,因為他們就不再努力記憶了。他們就信任書文,只憑外在的符號再認,並非憑內在的腦力回憶。
對於圖提認為文字可以對教育產生的功能,塔穆斯也有不同的看法:
至於教育,你所拿給你的學生們的東西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界的本身。因為借文字的幫助,他們可無須教練就可以吞下許多知識,好像無所不知,而實際上卻一無所知。還不僅如此,他們會討人厭,因為自以為聰明而實在是不聰明。(柏拉圖〈斐德若篇〉.朱光潛譯)
站在文字發明到今天的五千年歷史的中間點上,柏拉圖二千五百年前的這段話,把文字閱讀可能發生的問題,做了歸納,也做了預言。
1920年代的時候,一位先生說:「書只是供給知識的一種工具,供給知識其實並不一定要靠書。」他又說:「太古時代沒有書,將來也可不必有書,書的需要可以說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現象。」
說話的人,是民國初年的教育家夏丏尊。他沒來得及看到網路時代的來臨,但是他所歸納的,也在預言今天網路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人類對世界認知的方式,先是有觀察,再用圖像、肢體表達、音樂、語言,之後再發展出文字來表達。
在文字的出現之前,人類的「閱讀」並不是不存在的──只是以聲音、圖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而存在的。
人類演化了幾百萬年終於在最後的五千年出現文字,以及其後更近的時間出現書籍來方便文字的傳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人類在使用了文字與書籍一段路程之後,又透過科技發明了一種新的形式,企圖擺脫文字與書籍閱讀的限制,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
從某個角度而言,我們的確是進入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全新時代。網路出現的本意,雖然是為了方便文字的交換與傳播,但卻註定要提供一個文字以外的閱讀與溝通的過程。網路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讓人類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種種全新的發展,難免令我們忐忑不安。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能不過是回到過去,恢復一些被壓抑了許久的需求。
所以我對伴隨網路時代而來的圖像閱讀、影音閱讀、多媒體閱讀等等,沒有那麼多擔心。
因為這不是人類沒有過的經驗,更不是人類不需要的經驗,只是過去幾千年被壓抑後的釋放而已。
我們需要擔心的,與其說是這些發展會不會破壞文字閱讀、書籍閱讀,不如說是如何讓文字閱讀與書籍閱讀,配合這些既古老又新興的多媒體閱讀形式,一起產生更新的作用。
〈當紙本書是一個黑夜〉
*黑夜不是和少數人相關的藝術品,而是每個健康、完整的人都不可缺的必需品。
有一天晚上,我決定拿出一張紙,把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的特質分列兩邊,做個比較。
我列出的圖是像這樣的。
我先列出了網路與數位閱讀的特質:多媒體、具象、活潑、外擴、社交、零碎、多工、動態、陽性。
再列出紙本書相對應的特質:文字、抽象、安靜、收斂、孤獨、整體、線性、靜態、陰性。
也就在整理、比較這兩排的特質和價值的時候,我突然在最底下發現,這兩列特質的總結,不就是白晝與夜晚的對比嗎?
所有網路閱讀的特質,可以比喻為白晝;所有紙本書閱讀的特質,可以比喻為黑夜。
而一旦把紙本書的獨特價值和黑夜相連接,所有問題的答案就都跳出來了。
人類從來都是需要代表夜晚和白晝的閱讀並存,也就是書和書以外的閱讀並存。
中文裡說的「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英文裡說的「Read the Word, Read the World」,講的都是閱讀這件事,需要倚靠書,也需要倚靠書以外對世界的理解。
但過去,就像電燈還沒進入人類生活之前,我們白晝與夜晚的時間大致相當,網路還沒出現之前,我們從書及書以外的生活裡吸取知識的時間也大致相當。
但是就像電燈發明之後,我們使用夜晚的習慣、方法、時間大受改變,網路出現之後,隨著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來閱讀世界的機會擴大,我們使用紙本書的習慣、方法與時間也產生劇變,隨之縮小。尤其,等到行動載具、智慧型手機流行之後,大家都在忙著當低頭族。我們隨時隨地在收發訊息、資料、知識,從某個方面來說,也形同隨時隨地在閱讀書本以外的世界。所以很多人都認為紙本書會走上沒落之路。
然而,把紙本書的閱讀價值和黑夜相連接之後,我覺得終於可以安心了。
就像人類有了電燈之後可以延長白晝的時間,可以連著熬好幾夜,但畢竟最後還是得需要黑夜,我們對紙本書的需求也是。
不論我們可以從網路、手機上得到多少訊息、知識、多媒體的閱讀樂趣、協力共享的學習,最後還是有一個打開紙本書的需求。
人,沒有夜晚,是會生病的。我們沒有紙本書的閱讀,也會如此。不論從心理或生理上來說,都如此。
黑夜不是和少數人相關的藝術品,而是每個人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一個會使用、享受夜晚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完整的人。
一個會使用、享受紙本書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完整的人。
我們要懂得善用影像、動畫、聲音的力量,也要懂得善用文字的力量。
今天我們要理解世界、理解任何知識,固然有太多文字以外其他便利的可能,但是任何影像、動畫、聲音又怎能替代下面這一首詩,短短的四十個字?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杜甫〈春夜喜雨〉
事實上,就在網路把過去長期受文字壓制的影像、動畫、聲音的力量解放的同時,網路也把我們對使用文字的需求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無時無刻,我們不是在使用文字來表達自己,與別人溝通。簡訊、臉書、電郵。每個人對使用文字的需求都在提高。
正因為大家都在如此頻繁地使用文字,每個人都應該注意文字的品味。使用文字的講究,不再只是一些特別的文字工作者才要關注的事。而是每個人。
而紙本書,正是讓我們最能學習、也體會文字力量的一種媒介。上面杜甫那一首詩,印在紙本書上,和呈現在電子書上,會有截然不同的氣場。我們閱讀的感受,也截然不同。
這就是紙本書對社會裡每一個人都具備的意義。不論那個社會多麼網路化、數位化。
前幾年我在紐約經常去參訪一些小學。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這些小學上網很不方便。不要說取得學校網路密碼總是困難重重,連自己的手機也常有被屏蔽之感。後來發現,他們就是怕小學生在學校隨意上網,覺得要先把他們離線的教育做好。
美國是網路和iPad等的發源地,但是他們卻如此重視讓小孩先把紙本書的閱讀打好基礎。用夜晚的比喻來說,就是他們知道:出了校門,外頭到處都是白晝,根本不必擔心孩子是否適應,所以在校園之內,反而重點是如何讓孩子從小先習慣、學會對夜晚的使用。
*人類一直有一種方便了,就不想閱讀的根性。
有一次演講結束後,聽眾交流的時間,有兩位女士先後發言。
先發言的顯然是一位母親,她為孩子日益偏向於使用網路而不接近書籍而煩惱;後發言的則似乎是一位當姊姊的人,她認為毋須為孩子操心那麼多,他們自有出路。就像我們自己,父母也曾為我們操心很多,但我們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兩位針鋒相對了一陣,令我印象深刻。
閱讀本來就是各說各話的事情。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談、談了這麼久的時間,結果還是得不斷地談。
網路風行之後,給我們新添的一個苦惱是,給「閱讀」這件事情增添了更多容易講不清、分辨不清的面貌。
所以,對於網路,最常聽到的一個說法,就是網路使得人遠離了書。甚至,遠離了閱讀。
但,真的是這樣嗎?
翻開人類的歷史,我們總是拚命想把閱讀這件事情變得比較容易,比較便利些。
文字和圖畫,從早期刻在石頭上、動物甲殼上、竹子上,到寫到皮革上、紙張上,到印刷、裝訂成冊,再到轉化為電子與數位型態,可以用電腦、手機與其他行動載具來顯示,我們一直希望把閱讀這件事情變得越方便越好。
從最早只有和神界可以溝通的祭司才有資格閱讀,到王公貴族壟斷閱讀的權利,再到民間富有之家也可以閱讀,再到推廣給更普及的人民,終於成為人人皆須接受國民教育,我們一直希望閱讀的能力與機會,能推廣到越多的人手上越好。
但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想把閱讀推廣與普及的力量越大,吸引我們不想閱讀的力量也就越來越大。
在中國,公元十一世紀的宋代,印刷術大盛,突破了過去書籍只能用手抄的,費時又少量的侷限,於是各種書籍的種類和數量都擴大,「莫之不有」。但也就在這時,蘇東坡寫了〈李氏山房藏書記〉,感嘆過去書籍取得不易的時代,大家願意千里迢迢追尋一本自己想讀的書,但到了什麼書都有了的時候,卻反而大都不愛讀書,只顧得「游談無根」(愛八卦)。到了清朝,書籍出版得更多了,袁枚寫〈黃生借書說〉,感嘆就比蘇東坡的時代又多了一層。
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情況。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帶動起「民主」與「國家」的觀念,在推動國民的教育與閱讀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與影響。同一時間,工業革命所帶動的印刷技術的改良,在書籍演進史上也有很關鍵的影響。然而也就在那之後不久,火車出現了,於是很多人感嘆過去大家願意守在家裡安安靜靜讀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現在都急於到處去旅行了。
大約一百年後,十九世紀末的時候,英國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把出版者與印刷者的角色做了劃時代的分工,出版產業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書籍的樣貌與形式也有了很大的革新。不過,這時電話出現了。於是,像梭羅這樣的很多人又開始感嘆,過去大家可以在火車上旅行,安安靜靜讀點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現在,大家只愛在電話上煲電話粥了。
進入了二十世紀的20年代,西方出現了平裝本革命,書籍再次以前所未有的便宜價格,與方便攜帶的形式出現。書籍與大眾之間,出現了零距離。但是也就在這之後不久,電視登場了。電視登堂入室的結果,使更多人感嘆我們離閱讀這件事又遠了。
二十世紀末,網際網路(internet)現身,人類自有書籍以來的最關鍵一次的革命,登場了。原先是美國學術機構裡,方便大家為了交流論文而發展出來的網際網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到90年代終於普及到每一個人手上。閱讀,突破了書籍時代所面臨的空間與時間障礙。但也就在這同時,網上各種遊戲與娛樂的風行,讓許多人又感嘆,我們從沒有如此背離閱讀的可能。
我們一直想把閱讀這件事情弄得更普及,更便利。
然而,閱讀越是方便的時候,我們越是不想閱讀。
人性如此。從來如此。和網路無關。
〈為什麼不必是文字與書〉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
那兩位女士的發言,表面看來像是兩個極端,但事實上是同一個出發點。
第一位母親的發言,太過重視書的作用了。
那位當姊姊的發言,表面看來雖然顯示了她對「網路」與「書」的平等對待,但是她引用今天之前的人曾經自己找到出路,而對下一代的人主張平常心看待,則又忽視了今天面對的變局,是人類過去所從未有過的。
一個閱讀的嶄新時代已經來臨,如果只是援用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經驗,遠遠不夠。只是主張以平常心來看待「網路」與「書」,同樣也只是延續書籍時代的思維而已。今天大家都在談網路帶來的閱讀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的真實面貌,很容易隱沒在烽火的煙霧之中。像那位母親,許多人擔心網路挾帶著大量影像、聲音,會不會徹底破壞(尤其是以書籍來呈現的)文字的閱讀。
要思考這個問題,不妨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字與書籍,對我們到底有什麼意義?」
人類發明文字,不論中西,大約都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事。
懂得利用文字,在人類幾百萬年的進化史上,當然是極為震撼的一件事。人類的思想,從此便於同輩人交流,前後代流傳。古人說倉頡發明文字後,「造化不能藏其祕,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可以說明這個事件的震撼性。近代科學研究指出,閱讀及使用文字對大腦及智力的重要性,則更有許多書籍與論述,這裡不再贅述。
至於書籍這件事情,就是更近的事情了。人類有紙張,是大約二千年的事;有印刷術,在中國大約是一千四百年,西方大約五百多年的事。而中文世界裡,習慣以目前我們常見的書籍形式來閱讀,則不過是一百多年的事情。
總之,在人類演化的四百萬年歷史中,從五千年前學會閱讀文字、一千年前懂得使用書籍之後,雖然給人類的文明與文化發展,都帶來遠非其前所擬的推展,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文字與書籍的重要性再大,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這頂多五、六千年的演變,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
文字與書的出現雖然晚,人類的閱讀可不是。早從非常遙遠的過去,我們的閱讀就開始了。只是那時候的方式不同而已。
那時的閱讀可能是白天看地上野獸的足跡,可能是夜裡仰望天上的星星;可能是看山洞裡的壁畫,更可能是聽別人的口述。
文字出現的好處是,多了一個可以極為抽象又方便地認知這個世界的方式;壞處是,我們原先綜合運用各種感官的全觀能力逐漸退化。書籍出現的好處是,把文字的傳播力量做到最大的擴散;壞處是,我們容易疏忽──甚至,貶低──書籍以外的知識來源。
柏拉圖講過一個文字剛發明時候的故事。埃及的一個古神⋯⋯名字是圖提。他首先發明了數目、算術、幾何和天文⋯⋯尤其重要的是他發明了文字。當時全埃及都受塔穆斯的統治⋯⋯圖提晉見了塔穆斯,把他的各種發明獻給他看,向他建議要把它們推廣到全埃及。那國王便問他每一種發明的用處⋯⋯輪到文字,圖提說:「大王,這件發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記憶力,它是醫治教育和記憶力的良藥!」
聽了圖提的說明,埃及國王回答了下面這麼一段話:
現在你是文字的父親,由於篤愛兒子的緣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說反了!你這個發明結果會使學會文字的人們善忘,因為他們就不再努力記憶了。他們就信任書文,只憑外在的符號再認,並非憑內在的腦力回憶。
對於圖提認為文字可以對教育產生的功能,塔穆斯也有不同的看法:
至於教育,你所拿給你的學生們的東西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界的本身。因為借文字的幫助,他們可無須教練就可以吞下許多知識,好像無所不知,而實際上卻一無所知。還不僅如此,他們會討人厭,因為自以為聰明而實在是不聰明。(柏拉圖〈斐德若篇〉.朱光潛譯)
站在文字發明到今天的五千年歷史的中間點上,柏拉圖二千五百年前的這段話,把文字閱讀可能發生的問題,做了歸納,也做了預言。
1920年代的時候,一位先生說:「書只是供給知識的一種工具,供給知識其實並不一定要靠書。」他又說:「太古時代沒有書,將來也可不必有書,書的需要可以說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現象。」
說話的人,是民國初年的教育家夏丏尊。他沒來得及看到網路時代的來臨,但是他所歸納的,也在預言今天網路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人類對世界認知的方式,先是有觀察,再用圖像、肢體表達、音樂、語言,之後再發展出文字來表達。
在文字的出現之前,人類的「閱讀」並不是不存在的──只是以聲音、圖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而存在的。
人類演化了幾百萬年終於在最後的五千年出現文字,以及其後更近的時間出現書籍來方便文字的傳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人類在使用了文字與書籍一段路程之後,又透過科技發明了一種新的形式,企圖擺脫文字與書籍閱讀的限制,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
從某個角度而言,我們的確是進入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全新時代。網路出現的本意,雖然是為了方便文字的交換與傳播,但卻註定要提供一個文字以外的閱讀與溝通的過程。網路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讓人類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種種全新的發展,難免令我們忐忑不安。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能不過是回到過去,恢復一些被壓抑了許久的需求。
所以我對伴隨網路時代而來的圖像閱讀、影音閱讀、多媒體閱讀等等,沒有那麼多擔心。
因為這不是人類沒有過的經驗,更不是人類不需要的經驗,只是過去幾千年被壓抑後的釋放而已。
我們需要擔心的,與其說是這些發展會不會破壞文字閱讀、書籍閱讀,不如說是如何讓文字閱讀與書籍閱讀,配合這些既古老又新興的多媒體閱讀形式,一起產生更新的作用。
〈當紙本書是一個黑夜〉
*黑夜不是和少數人相關的藝術品,而是每個健康、完整的人都不可缺的必需品。
有一天晚上,我決定拿出一張紙,把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的特質分列兩邊,做個比較。
我列出的圖是像這樣的。
我先列出了網路與數位閱讀的特質:多媒體、具象、活潑、外擴、社交、零碎、多工、動態、陽性。
再列出紙本書相對應的特質:文字、抽象、安靜、收斂、孤獨、整體、線性、靜態、陰性。
也就在整理、比較這兩排的特質和價值的時候,我突然在最底下發現,這兩列特質的總結,不就是白晝與夜晚的對比嗎?
所有網路閱讀的特質,可以比喻為白晝;所有紙本書閱讀的特質,可以比喻為黑夜。
而一旦把紙本書的獨特價值和黑夜相連接,所有問題的答案就都跳出來了。
人類從來都是需要代表夜晚和白晝的閱讀並存,也就是書和書以外的閱讀並存。
中文裡說的「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英文裡說的「Read the Word, Read the World」,講的都是閱讀這件事,需要倚靠書,也需要倚靠書以外對世界的理解。
但過去,就像電燈還沒進入人類生活之前,我們白晝與夜晚的時間大致相當,網路還沒出現之前,我們從書及書以外的生活裡吸取知識的時間也大致相當。
但是就像電燈發明之後,我們使用夜晚的習慣、方法、時間大受改變,網路出現之後,隨著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來閱讀世界的機會擴大,我們使用紙本書的習慣、方法與時間也產生劇變,隨之縮小。尤其,等到行動載具、智慧型手機流行之後,大家都在忙著當低頭族。我們隨時隨地在收發訊息、資料、知識,從某個方面來說,也形同隨時隨地在閱讀書本以外的世界。所以很多人都認為紙本書會走上沒落之路。
然而,把紙本書的閱讀價值和黑夜相連接之後,我覺得終於可以安心了。
就像人類有了電燈之後可以延長白晝的時間,可以連著熬好幾夜,但畢竟最後還是得需要黑夜,我們對紙本書的需求也是。
不論我們可以從網路、手機上得到多少訊息、知識、多媒體的閱讀樂趣、協力共享的學習,最後還是有一個打開紙本書的需求。
人,沒有夜晚,是會生病的。我們沒有紙本書的閱讀,也會如此。不論從心理或生理上來說,都如此。
黑夜不是和少數人相關的藝術品,而是每個人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一個會使用、享受夜晚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完整的人。
一個會使用、享受紙本書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完整的人。
我們要懂得善用影像、動畫、聲音的力量,也要懂得善用文字的力量。
今天我們要理解世界、理解任何知識,固然有太多文字以外其他便利的可能,但是任何影像、動畫、聲音又怎能替代下面這一首詩,短短的四十個字?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杜甫〈春夜喜雨〉
事實上,就在網路把過去長期受文字壓制的影像、動畫、聲音的力量解放的同時,網路也把我們對使用文字的需求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無時無刻,我們不是在使用文字來表達自己,與別人溝通。簡訊、臉書、電郵。每個人對使用文字的需求都在提高。
正因為大家都在如此頻繁地使用文字,每個人都應該注意文字的品味。使用文字的講究,不再只是一些特別的文字工作者才要關注的事。而是每個人。
而紙本書,正是讓我們最能學習、也體會文字力量的一種媒介。上面杜甫那一首詩,印在紙本書上,和呈現在電子書上,會有截然不同的氣場。我們閱讀的感受,也截然不同。
這就是紙本書對社會裡每一個人都具備的意義。不論那個社會多麼網路化、數位化。
前幾年我在紐約經常去參訪一些小學。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這些小學上網很不方便。不要說取得學校網路密碼總是困難重重,連自己的手機也常有被屏蔽之感。後來發現,他們就是怕小學生在學校隨意上網,覺得要先把他們離線的教育做好。
美國是網路和iPad等的發源地,但是他們卻如此重視讓小孩先把紙本書的閱讀打好基礎。用夜晚的比喻來說,就是他們知道:出了校門,外頭到處都是白晝,根本不必擔心孩子是否適應,所以在校園之內,反而重點是如何讓孩子從小先習慣、學會對夜晚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