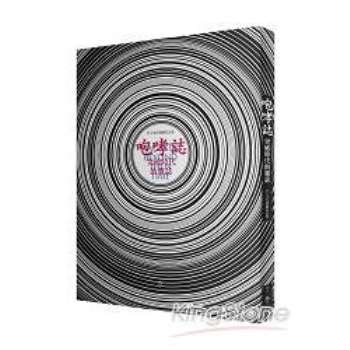好讀:一本專業閱讀生活雜誌
「當時誠品的氛圍自由,《好讀》無須畫地自限為一本僅止介紹閱讀的雜誌,我們可以作各種嘗試,挖掘主流媒體忽視或不願討論的議題。」
《好讀》從無到有、直至結束,蔣慧仙始終是這本雜誌的靈魂人物。曾在《破報》工作的她,彼時因緣際會與誠品合辦「夏日遊戲」系列活動(比如「街頭扮裝」),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觀點與充滿開創性的熱情,吸引了當時誠品企畫部主管曾乾瑜的注意。
《好讀》創刊
一九八九年開幕的誠品書店,誕生於解嚴第三年,當時無論是閱讀出版或社會風氣,都充滿了亟欲改變、突破的氣息,誠品也因此被形塑成「另一種書店」。
一九九二年誠品推出以雙月刊形式發行的《誠品閱讀》,四年出版二十五期,後因不堪虧損,一九九六年二月宣布停刊。曾乾瑜回憶:「一年虧三百多萬,訂戶也不多,怎麼算都很難繼續下去,只能選擇結束。」那一年,企畫部熱熱鬧鬧的舉辦了「當蝙蝠飛完時:誠品閱讀停刊」活動,為這本叫好不叫座的閱讀誌畫下了句點。
但誠品還是需要一個與會員溝通對話的管道。起初是一封簡單的信函,接著擴張成兩大張報紙,直到一九九九年誠品十週年,誠品敦南店開始二十四小時營業,曾乾瑜眼中生性浪漫的創辦人吳清友,決定「再試一次」,再度推出正式的紙本刊物。這項任務交到了曾乾瑜手中。雖說《好讀》是專為會員打造的雜誌,肩負展現書店經營風格與打造誠品文化品牌的任務,但雜誌性格由主編形塑,曾乾瑜先以熟悉的誠品人馬組成穩定的編輯團隊,再找來蔣慧仙擔任雜誌主編,「我喜歡《破報》的活力,也喜歡慧仙一些怪異的觀點能撞擊這個團隊。當慧仙答應來《好讀》時,我已經能想像《好讀》的風格了。」對他來說,蔣慧仙就像是大富翁遊戲中即將被掀開的「機會」牌,充滿了無限可能。
那是二○○○年,台灣像只壓力鍋爆發了蓄積十多年的能量,迎接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同時面對社會重組造成的混亂、變動與困惑。蔣慧仙知道自己被邀請加入《好讀》團隊的原因,是期望她能帶入《破報》特有的次文化活力與城市現場觀察;而當時已轉到報紙副刊工作的她,也渴望以主題性的策畫,即時記錄變動性高的社會文化現場。
曾乾瑜總愛說,挑人是他的長處,他對《好讀》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蔣慧仙。接下來,編輯團隊只需要更大空間,去嘗試各種可能性。大開本《好讀》試刊號推出,一連三期,以「新世紀預言書」、「少女革命」、「當詩歌蔓延時」吸引了社會目光。每本雜誌印製成本五十元,會員可以會員卡到店內免費索取,非會員則是以四十九元購買,雖然賣一本賠一本,但其實增加來店率與購書率,「作為一間書店,只能被動的等讀者上門,但《好讀》是書店與會員溝通的媒介,傳達書店關切的文化議題,呈現書店的社會關懷,而非賺錢的工具。」曾乾瑜說。
讀現象、趨勢、思想與時代
《好讀》被外界視為是誠品打造的發聲媒介,除了替自家文化事業品牌加分,也欲塑造一種新中產階級品味樣貌,那並非是誇耀式的品味消費風格,而是關懷社會、重視生活品質、崇尚自由和自然,同時緊抓流行趨勢的生活型態。
《好讀》經歷了多次的改版,從最早的騎馬釘裝訂,到二○○四年第四十一期改成膠裝的綜合閱讀生活類雜誌,隨著誠品在全台持續拓店,《好讀》也慢慢地變成代表足以代表台灣人文、出版業的雜誌。
讀《好讀》,讀的是現象、趨勢、思想,而《好讀》的確也為這個時代留下紀錄,例如九二一週年推出「記憶的斷層」(3),二○○一年「恐怖主義全檔案」(16)即時回應九一一事件,二○○三年SARS期間有「瘟疫,劫餘紀事」(32)。
《好讀》鮮少以書或作家當封面,封面故事都是各種文化現象與社會議題。例如「可愛力量大」(42)、「絕妙好歌詞」(45)、「我的玩具情人」(46)、「大話周星馳」(51)、「新台客,正騷熱?」(56)、「春耕,飲食的革命」(64),各形各色的題目再裹以閱讀,重新解讀。「除了企畫部主管,沒有其他部門會干涉《好讀》。我們的座位在採購同事旁邊,自成一區,亂七八糟疊滿書。吳清友先生有時會走過來,看一看,笑一笑,不管那些題目他看不看得懂,都不曾插手。」蔣慧仙說。
彷彿是為了回報上頭全心信任,編輯團隊每個月都在拚博一場血汗交織的極限運動。例如二○○七年六月,香港回歸十週年,編輯們主動向香港旅遊局提案申請贊助機票住宿,全員飛到香港,進行五天四夜密集採訪,探討日常生活、政治社會經濟、表演藝術、時尚潮流、教育環境等十個面向,同時在街頭即時抓拍一百名香港人,短時間內完成「香港心事10×10」(77)一題;下個月緊接而來的題目是「環島,上路吧!」(78)又讓編輯跳下海,親身挑戰二十四小時「搭火車」環島。
沒有幾本雜誌能像《好讀》,封面故事造就當代文化記憶。讀者不會忘記「新台客」讓曾被貶為底層文化的台客大翻身;也記得「絕妙好歌詞」裡李宗盛、方文山、阿信、林夕的詞如何被當作文學作品細細評析;還有「大話周星馳」讓星爺文化成為一門顯學。
這幾個題目都是二○○四年改版後的代表作,雜誌開始出現設計生活風格與商品介紹,「有些讀者覺得我們改變了,不再那麼純粹;誠品內部也有人質疑,難道不能仿效日本《達文西》,單純作一本專門的閱讀雜誌嗎?」蔣慧仙的回答很簡單:「不要,那樣好無聊,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她先是正色的說:「但不代表市面上不能有一本做得好的閱讀雜誌,我覺得一定可以,只是我們選擇僅僅如此!」話一說完,她就忍不住笑了。
「一個都不能少。」是蔣慧仙當時常掛在嘴邊的瘋話,鼓勵編輯全力發揮,策畫內容。她形容自己是貪心的人,總愛在一本雜誌裡塞太多東西,只要編輯能提出好構想,她就排上版面,爆頁數大多不是因為廣告多,而是想做的題目太多了。「就負責廣告業務的同事都問,可不可以做得鬆一點?留一點空間?也有讀者反應,看《好讀》必須拿著尺,一行一行對著字讀,因為字級小、密度高、評論性強,產生閱讀門檻,我們始終在企畫的完整度與內容的承載量之間拉鋸。」
以蔣慧仙為帶領者的編輯團隊,起初只有兩名文編、兩名美編,後期雖有擴編,但常面臨流動性高的問題,平均工作時間是兩年,「《好讀》大多是年輕編輯的第一份或第二份工作,這個世代的編輯比傳統編輯更有主見、會思考,但也比較任性,把這一點發揮出來,就是《好讀》的樣貌。」
《好讀》人生
如果不是誠品決定停刊,蔣慧仙大概不會有離開《好讀》的一天,「做這本雜誌一點也不無聊,永遠不怕沒題目,我們就是奮力將雜誌的『雜』發揮到極致。」
《好讀》八年,走過台灣關鍵時刻,「創刊的二○○○年,台灣社會充滿樂觀積極的氛圍,主流論述鼓吹著台灣在華文世界占有重要位置,而台灣也有文化自信成為華人世界的中心;一直到二○○四年,社會氣氛有了轉折,人民有了生活上的危機意識,出版景氣也一路向下,書店從月結改採寄售制、大型經銷商無預警倒閉,出版產業面臨重整,不能再以書養書,必須盡量出版暢銷或長銷書籍,那是個出版業憂心忡忡的年代。在那個時刻,《好讀》的任務是繼續維持著一種生活態度與閱讀方法,但那並非專為中產階級所打造。
「無論是免費或付費,我們都保有真正的編輯自由,沒有誰為了銷量干預我們,唯一幾次封面選擇的歧見,雖然與主管起了爭執,最後仍照美編設計,選了不那麼商業走向的封面。」蔣慧仙思索了一下,又說:「許多人認為誠品、《好讀》屬於中產階級,但《好讀》從來沒有要為中產階級的品味或任何消費文化背書,我們會去分析定義社會架構的權力與界線在哪裡,去測繪社會上不被主流認可、無法發聲,或是被刻板印象箝制的族群,嘗試打開對話空間。許多時候我們都站在另翼或少數者的那一端,例如東南亞新移民、新台客;或是當我們以旅館為封面故事,我們探討日本的愛情賓館,而非五星級精品旅館。」蔣慧仙不否認自己就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屬於有利的角色,但在每一場編輯會議上,她的任務就是和團隊一起釐清社會定義跟界線,不斷質疑現有價值觀,開啟新對話空間。或許《好讀》讀者真的以中產階級為多,那她也希望藉由《好讀》,讓中產階級脫離舒適圈、接觸自己必須理解的社會現象,讓不同的社會位置、不同的身分認同互相碰撞,並為台灣文化留下現場紀錄,那就是《好讀》的當代功能。
「當時誠品的氛圍自由,《好讀》無須畫地自限為一本僅止介紹閱讀的雜誌,我們可以作各種嘗試,挖掘主流媒體忽視或不願討論的議題。」
《好讀》從無到有、直至結束,蔣慧仙始終是這本雜誌的靈魂人物。曾在《破報》工作的她,彼時因緣際會與誠品合辦「夏日遊戲」系列活動(比如「街頭扮裝」),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觀點與充滿開創性的熱情,吸引了當時誠品企畫部主管曾乾瑜的注意。
《好讀》創刊
一九八九年開幕的誠品書店,誕生於解嚴第三年,當時無論是閱讀出版或社會風氣,都充滿了亟欲改變、突破的氣息,誠品也因此被形塑成「另一種書店」。
一九九二年誠品推出以雙月刊形式發行的《誠品閱讀》,四年出版二十五期,後因不堪虧損,一九九六年二月宣布停刊。曾乾瑜回憶:「一年虧三百多萬,訂戶也不多,怎麼算都很難繼續下去,只能選擇結束。」那一年,企畫部熱熱鬧鬧的舉辦了「當蝙蝠飛完時:誠品閱讀停刊」活動,為這本叫好不叫座的閱讀誌畫下了句點。
但誠品還是需要一個與會員溝通對話的管道。起初是一封簡單的信函,接著擴張成兩大張報紙,直到一九九九年誠品十週年,誠品敦南店開始二十四小時營業,曾乾瑜眼中生性浪漫的創辦人吳清友,決定「再試一次」,再度推出正式的紙本刊物。這項任務交到了曾乾瑜手中。雖說《好讀》是專為會員打造的雜誌,肩負展現書店經營風格與打造誠品文化品牌的任務,但雜誌性格由主編形塑,曾乾瑜先以熟悉的誠品人馬組成穩定的編輯團隊,再找來蔣慧仙擔任雜誌主編,「我喜歡《破報》的活力,也喜歡慧仙一些怪異的觀點能撞擊這個團隊。當慧仙答應來《好讀》時,我已經能想像《好讀》的風格了。」對他來說,蔣慧仙就像是大富翁遊戲中即將被掀開的「機會」牌,充滿了無限可能。
那是二○○○年,台灣像只壓力鍋爆發了蓄積十多年的能量,迎接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同時面對社會重組造成的混亂、變動與困惑。蔣慧仙知道自己被邀請加入《好讀》團隊的原因,是期望她能帶入《破報》特有的次文化活力與城市現場觀察;而當時已轉到報紙副刊工作的她,也渴望以主題性的策畫,即時記錄變動性高的社會文化現場。
曾乾瑜總愛說,挑人是他的長處,他對《好讀》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蔣慧仙。接下來,編輯團隊只需要更大空間,去嘗試各種可能性。大開本《好讀》試刊號推出,一連三期,以「新世紀預言書」、「少女革命」、「當詩歌蔓延時」吸引了社會目光。每本雜誌印製成本五十元,會員可以會員卡到店內免費索取,非會員則是以四十九元購買,雖然賣一本賠一本,但其實增加來店率與購書率,「作為一間書店,只能被動的等讀者上門,但《好讀》是書店與會員溝通的媒介,傳達書店關切的文化議題,呈現書店的社會關懷,而非賺錢的工具。」曾乾瑜說。
讀現象、趨勢、思想與時代
《好讀》被外界視為是誠品打造的發聲媒介,除了替自家文化事業品牌加分,也欲塑造一種新中產階級品味樣貌,那並非是誇耀式的品味消費風格,而是關懷社會、重視生活品質、崇尚自由和自然,同時緊抓流行趨勢的生活型態。
《好讀》經歷了多次的改版,從最早的騎馬釘裝訂,到二○○四年第四十一期改成膠裝的綜合閱讀生活類雜誌,隨著誠品在全台持續拓店,《好讀》也慢慢地變成代表足以代表台灣人文、出版業的雜誌。
讀《好讀》,讀的是現象、趨勢、思想,而《好讀》的確也為這個時代留下紀錄,例如九二一週年推出「記憶的斷層」(3),二○○一年「恐怖主義全檔案」(16)即時回應九一一事件,二○○三年SARS期間有「瘟疫,劫餘紀事」(32)。
《好讀》鮮少以書或作家當封面,封面故事都是各種文化現象與社會議題。例如「可愛力量大」(42)、「絕妙好歌詞」(45)、「我的玩具情人」(46)、「大話周星馳」(51)、「新台客,正騷熱?」(56)、「春耕,飲食的革命」(64),各形各色的題目再裹以閱讀,重新解讀。「除了企畫部主管,沒有其他部門會干涉《好讀》。我們的座位在採購同事旁邊,自成一區,亂七八糟疊滿書。吳清友先生有時會走過來,看一看,笑一笑,不管那些題目他看不看得懂,都不曾插手。」蔣慧仙說。
彷彿是為了回報上頭全心信任,編輯團隊每個月都在拚博一場血汗交織的極限運動。例如二○○七年六月,香港回歸十週年,編輯們主動向香港旅遊局提案申請贊助機票住宿,全員飛到香港,進行五天四夜密集採訪,探討日常生活、政治社會經濟、表演藝術、時尚潮流、教育環境等十個面向,同時在街頭即時抓拍一百名香港人,短時間內完成「香港心事10×10」(77)一題;下個月緊接而來的題目是「環島,上路吧!」(78)又讓編輯跳下海,親身挑戰二十四小時「搭火車」環島。
沒有幾本雜誌能像《好讀》,封面故事造就當代文化記憶。讀者不會忘記「新台客」讓曾被貶為底層文化的台客大翻身;也記得「絕妙好歌詞」裡李宗盛、方文山、阿信、林夕的詞如何被當作文學作品細細評析;還有「大話周星馳」讓星爺文化成為一門顯學。
這幾個題目都是二○○四年改版後的代表作,雜誌開始出現設計生活風格與商品介紹,「有些讀者覺得我們改變了,不再那麼純粹;誠品內部也有人質疑,難道不能仿效日本《達文西》,單純作一本專門的閱讀雜誌嗎?」蔣慧仙的回答很簡單:「不要,那樣好無聊,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她先是正色的說:「但不代表市面上不能有一本做得好的閱讀雜誌,我覺得一定可以,只是我們選擇僅僅如此!」話一說完,她就忍不住笑了。
「一個都不能少。」是蔣慧仙當時常掛在嘴邊的瘋話,鼓勵編輯全力發揮,策畫內容。她形容自己是貪心的人,總愛在一本雜誌裡塞太多東西,只要編輯能提出好構想,她就排上版面,爆頁數大多不是因為廣告多,而是想做的題目太多了。「就負責廣告業務的同事都問,可不可以做得鬆一點?留一點空間?也有讀者反應,看《好讀》必須拿著尺,一行一行對著字讀,因為字級小、密度高、評論性強,產生閱讀門檻,我們始終在企畫的完整度與內容的承載量之間拉鋸。」
以蔣慧仙為帶領者的編輯團隊,起初只有兩名文編、兩名美編,後期雖有擴編,但常面臨流動性高的問題,平均工作時間是兩年,「《好讀》大多是年輕編輯的第一份或第二份工作,這個世代的編輯比傳統編輯更有主見、會思考,但也比較任性,把這一點發揮出來,就是《好讀》的樣貌。」
《好讀》人生
如果不是誠品決定停刊,蔣慧仙大概不會有離開《好讀》的一天,「做這本雜誌一點也不無聊,永遠不怕沒題目,我們就是奮力將雜誌的『雜』發揮到極致。」
《好讀》八年,走過台灣關鍵時刻,「創刊的二○○○年,台灣社會充滿樂觀積極的氛圍,主流論述鼓吹著台灣在華文世界占有重要位置,而台灣也有文化自信成為華人世界的中心;一直到二○○四年,社會氣氛有了轉折,人民有了生活上的危機意識,出版景氣也一路向下,書店從月結改採寄售制、大型經銷商無預警倒閉,出版產業面臨重整,不能再以書養書,必須盡量出版暢銷或長銷書籍,那是個出版業憂心忡忡的年代。在那個時刻,《好讀》的任務是繼續維持著一種生活態度與閱讀方法,但那並非專為中產階級所打造。
「無論是免費或付費,我們都保有真正的編輯自由,沒有誰為了銷量干預我們,唯一幾次封面選擇的歧見,雖然與主管起了爭執,最後仍照美編設計,選了不那麼商業走向的封面。」蔣慧仙思索了一下,又說:「許多人認為誠品、《好讀》屬於中產階級,但《好讀》從來沒有要為中產階級的品味或任何消費文化背書,我們會去分析定義社會架構的權力與界線在哪裡,去測繪社會上不被主流認可、無法發聲,或是被刻板印象箝制的族群,嘗試打開對話空間。許多時候我們都站在另翼或少數者的那一端,例如東南亞新移民、新台客;或是當我們以旅館為封面故事,我們探討日本的愛情賓館,而非五星級精品旅館。」蔣慧仙不否認自己就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屬於有利的角色,但在每一場編輯會議上,她的任務就是和團隊一起釐清社會定義跟界線,不斷質疑現有價值觀,開啟新對話空間。或許《好讀》讀者真的以中產階級為多,那她也希望藉由《好讀》,讓中產階級脫離舒適圈、接觸自己必須理解的社會現象,讓不同的社會位置、不同的身分認同互相碰撞,並為台灣文化留下現場紀錄,那就是《好讀》的當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