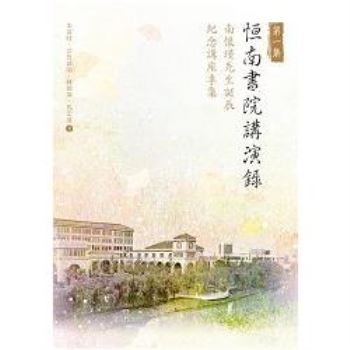愛因斯坦:「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宗教不但不與科學相違,而且每一次的科學新發現都能夠驗證它的觀點,這就是佛教。」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一九七九年,商務印書館)。
序言
今天我很榮幸能夠應邀在南老師九十六歲誕辰日來作這一次報告。南老師一生用了七十年來教化眾生,被他教化的人無以計數,我就是其中一個。我在二○○四年,有一天很有幸去拜訪南老師,當時在上海康平路的一座別墅裡,我們從中午一直談到晚上吃飯,談了整整一下午,談的主要內容就是佛學、現代科學、生命科學。談完之後,在吃飯前,南老師就給我手書了一首詩,唐朝杜荀鶴寫的:「利門名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圖1)這首詩充滿了南老師對我的關懷和開導,我知道南老師希望我能把精力投入到科普上。從那以後,我每年一有機會就到南老師那裡去,接受南老師的教導,聽南老師講課講經。
我覺得,南老師對自然科學非常尊重和渴望。在近十年我參加他的講經活動中,他多次提到了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我記得有一次講《楞嚴經》的時候,他跟我們說,釋迦牟尼講經用了當時自然科學的最高成就。比如「佛觀一杯水,十萬八千蟲」,那個時候就能夠看到一杯水裡有十萬八千個微生物,這是相當相當了不起的。他講《楞嚴經》、講了光學,講了很多東西,也講了生命科學,那是當時自然科學的最高成就。他有一次又講過: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佛在傳授法門的時候是因時、因地、因人而設教,用不同的方法對不同的人。那麼對現代的人,你要引導他瞭解佛法,最好的法門是自然科學法門,就是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把佛法講清楚。南老師自己在著述和講經中,也處處引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和概念來說明深奧的佛學原理。
南師在《楞伽大義今譯》的「自敘」中說:「而一般佛學,除了注重在根身,和去後來先做主公的尋討以外,絕少向器世界(物理世界)的關係上,肯做有系統而追根究柢的研究,所以佛法在現代哲學和科學上,不能發揮更大的光芒。也可以說是拋棄自家寶藏不顧,缺乏科學和哲學的素養,沒有把大小乘所有經論中的真義貫串起來,非常可惜。如果稍能擺脫一些濃厚而無謂的宗教習氣,多向這一面著眼,那對於現實的人間世,和將來的世界,可能貢獻更大;我想,這應該是合於佛心,當會得到吾佛世尊的會心微笑吧!」
南老師對我的教化,就是希望我能夠把精力投入到科普工作中去。科普不是個簡單的東西,南老師一生把古代聖人的名著包括佛經,用普通大眾能夠接受的語言講出來了,使大家能夠看懂古代這些經典名著和佛經。他的功力非常深、他的功德很大,現在我們自然科學界還沒有人有他這個功力,能夠把現代自然科學的知識用普通大眾能夠瞭解的語言來講清楚。所以我發願,在南老師的開導之下,努力從事科普,把自然科學的語言,忠實地、原汁原味地編成老百姓能夠理解的語言,把它講清楚,供大家研究自然科學和佛學之間的關聯。今天我給大家彙報的就是,我在南老師指導之下,在近十年的時間裡,把自然科學和佛學作比較,得出的兩個心得。之一是:我在最初的五六年中間跟南老師學習「空觀」,這是佛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思想,就是萬法皆空,一切有形態的東西實際上都是空的,有色相的東西都是空的,這個觀點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已經比較好理解了。我之前在南老師那裡寫過好些讀書心得,其中一篇就叫做《物理學步入禪境──緣起性空》,就是寫了這方面的心得。但是在進一步的學習中發現,光理解佛學的「空觀」是不夠的,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一切皆空」,那豈不是你做好事壞事最後都「空」了,好事壞事沒有分別了嗎?一定有個東西,能把好事壞事區別得很清楚,才能夠抑惡揚善,才能使大家一心從善。佛學進一步的道理是什麼呢?就是南老師後來用數年時間給我們講的唯識法相宗的學說,其中說,人的每個念頭、每做一件事,都被記錄在阿賴耶識的種子裡頭了,這些種子一旦有緣就會發芽開花。這種唯識法相宗的學說,我覺得是我們最應該下工夫理解的。我今天要報告的讀書心得就是圍繞著唯識法相宗來看現代自然科學有些什麼樣的進展和發現。
今天講的題目是〈量子意識──現代科學與佛學的匯合處?〉,大家一聽到這個題目可能覺得很玄。意識怎麼會是量子?量子這個東西大家可能都覺得很神祕,實際上一點兒也不神祕。二十世紀被最精密地證實的自然科學理論就是量子理論。二十世紀有大量的科技成就和社會的技術發展,都是跟量子理論有關的,像核能、半導體,我們現在用的手機、電腦,這些都和量子理論有關。下面我再簡要介紹量子理論。
那麼意識是什麼呢?學自然科學的人都知道,意識是被科學拒之門外、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東西。我們這代人都知道一句老話,叫做:「科學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句話大家是不是很清楚?這是以前的老生常談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意志」就是意識,就是說自然科學把自己擺脫得乾乾淨淨的,把所有意識的東西都排除在外,它不承認自己的東西跟意識有關,所以自然科學和意識是撇得很清楚的。但是人類發展到今天,發現意識是規避不了的。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自然科學發展到後來,發現意識是怎樣都規避不了的,而且意識在自然科學理論中,反而可能是最基礎的。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如果大家聽懂了,為什麼意識是規避不了的,而且意識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是最基礎的,大家就可能知道自然科學最終應該會和佛學殊途同歸。
佛學研究的正是「意識」(當然不能完全用意識來概括佛學),而自然科學要研究的,就是剛才說的,要和意識撇得很清楚的客觀世界。它把所有意識都排除在外,它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客觀世界、物質世界。那麼人類另一部分的知識、宇宙中間另一部分的東西,就是意識,實際上是從釋迦牟尼之前就開始研究,釋迦牟尼之後就更發達,佛學研究人的意識。如果佛學跟科學研究的東西是分不開的,那麼佛學和科學一定就會走在一起。果然現在自然科學就發現,意識和客觀物質世界是不能截然分開的,隨著研究的深入,相信佛學最終會和自然科學殊途同歸。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也是我現在對佛學和科學的認識。
有很多人習慣說佛學是迷信,我說不,佛學不是迷信,佛學研究的東西和自然科學不同,是宇宙的另一方面,就是意識。佛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就像爬喜馬拉雅山一樣,一個從北坡往上爬,一個從南坡往上爬,總有一天兩者要會合的。
大家對這個說法先有了思想準備,對我後面講的東西可能就容易接受了。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一九七九年,商務印書館)。
序言
今天我很榮幸能夠應邀在南老師九十六歲誕辰日來作這一次報告。南老師一生用了七十年來教化眾生,被他教化的人無以計數,我就是其中一個。我在二○○四年,有一天很有幸去拜訪南老師,當時在上海康平路的一座別墅裡,我們從中午一直談到晚上吃飯,談了整整一下午,談的主要內容就是佛學、現代科學、生命科學。談完之後,在吃飯前,南老師就給我手書了一首詩,唐朝杜荀鶴寫的:「利門名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圖1)這首詩充滿了南老師對我的關懷和開導,我知道南老師希望我能把精力投入到科普上。從那以後,我每年一有機會就到南老師那裡去,接受南老師的教導,聽南老師講課講經。
我覺得,南老師對自然科學非常尊重和渴望。在近十年我參加他的講經活動中,他多次提到了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我記得有一次講《楞嚴經》的時候,他跟我們說,釋迦牟尼講經用了當時自然科學的最高成就。比如「佛觀一杯水,十萬八千蟲」,那個時候就能夠看到一杯水裡有十萬八千個微生物,這是相當相當了不起的。他講《楞嚴經》、講了光學,講了很多東西,也講了生命科學,那是當時自然科學的最高成就。他有一次又講過: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佛在傳授法門的時候是因時、因地、因人而設教,用不同的方法對不同的人。那麼對現代的人,你要引導他瞭解佛法,最好的法門是自然科學法門,就是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把佛法講清楚。南老師自己在著述和講經中,也處處引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和概念來說明深奧的佛學原理。
南師在《楞伽大義今譯》的「自敘」中說:「而一般佛學,除了注重在根身,和去後來先做主公的尋討以外,絕少向器世界(物理世界)的關係上,肯做有系統而追根究柢的研究,所以佛法在現代哲學和科學上,不能發揮更大的光芒。也可以說是拋棄自家寶藏不顧,缺乏科學和哲學的素養,沒有把大小乘所有經論中的真義貫串起來,非常可惜。如果稍能擺脫一些濃厚而無謂的宗教習氣,多向這一面著眼,那對於現實的人間世,和將來的世界,可能貢獻更大;我想,這應該是合於佛心,當會得到吾佛世尊的會心微笑吧!」
南老師對我的教化,就是希望我能夠把精力投入到科普工作中去。科普不是個簡單的東西,南老師一生把古代聖人的名著包括佛經,用普通大眾能夠接受的語言講出來了,使大家能夠看懂古代這些經典名著和佛經。他的功力非常深、他的功德很大,現在我們自然科學界還沒有人有他這個功力,能夠把現代自然科學的知識用普通大眾能夠瞭解的語言來講清楚。所以我發願,在南老師的開導之下,努力從事科普,把自然科學的語言,忠實地、原汁原味地編成老百姓能夠理解的語言,把它講清楚,供大家研究自然科學和佛學之間的關聯。今天我給大家彙報的就是,我在南老師指導之下,在近十年的時間裡,把自然科學和佛學作比較,得出的兩個心得。之一是:我在最初的五六年中間跟南老師學習「空觀」,這是佛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思想,就是萬法皆空,一切有形態的東西實際上都是空的,有色相的東西都是空的,這個觀點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已經比較好理解了。我之前在南老師那裡寫過好些讀書心得,其中一篇就叫做《物理學步入禪境──緣起性空》,就是寫了這方面的心得。但是在進一步的學習中發現,光理解佛學的「空觀」是不夠的,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一切皆空」,那豈不是你做好事壞事最後都「空」了,好事壞事沒有分別了嗎?一定有個東西,能把好事壞事區別得很清楚,才能夠抑惡揚善,才能使大家一心從善。佛學進一步的道理是什麼呢?就是南老師後來用數年時間給我們講的唯識法相宗的學說,其中說,人的每個念頭、每做一件事,都被記錄在阿賴耶識的種子裡頭了,這些種子一旦有緣就會發芽開花。這種唯識法相宗的學說,我覺得是我們最應該下工夫理解的。我今天要報告的讀書心得就是圍繞著唯識法相宗來看現代自然科學有些什麼樣的進展和發現。
今天講的題目是〈量子意識──現代科學與佛學的匯合處?〉,大家一聽到這個題目可能覺得很玄。意識怎麼會是量子?量子這個東西大家可能都覺得很神祕,實際上一點兒也不神祕。二十世紀被最精密地證實的自然科學理論就是量子理論。二十世紀有大量的科技成就和社會的技術發展,都是跟量子理論有關的,像核能、半導體,我們現在用的手機、電腦,這些都和量子理論有關。下面我再簡要介紹量子理論。
那麼意識是什麼呢?學自然科學的人都知道,意識是被科學拒之門外、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東西。我們這代人都知道一句老話,叫做:「科學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句話大家是不是很清楚?這是以前的老生常談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意志」就是意識,就是說自然科學把自己擺脫得乾乾淨淨的,把所有意識的東西都排除在外,它不承認自己的東西跟意識有關,所以自然科學和意識是撇得很清楚的。但是人類發展到今天,發現意識是規避不了的。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自然科學發展到後來,發現意識是怎樣都規避不了的,而且意識在自然科學理論中,反而可能是最基礎的。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如果大家聽懂了,為什麼意識是規避不了的,而且意識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是最基礎的,大家就可能知道自然科學最終應該會和佛學殊途同歸。
佛學研究的正是「意識」(當然不能完全用意識來概括佛學),而自然科學要研究的,就是剛才說的,要和意識撇得很清楚的客觀世界。它把所有意識都排除在外,它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客觀世界、物質世界。那麼人類另一部分的知識、宇宙中間另一部分的東西,就是意識,實際上是從釋迦牟尼之前就開始研究,釋迦牟尼之後就更發達,佛學研究人的意識。如果佛學跟科學研究的東西是分不開的,那麼佛學和科學一定就會走在一起。果然現在自然科學就發現,意識和客觀物質世界是不能截然分開的,隨著研究的深入,相信佛學最終會和自然科學殊途同歸。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也是我現在對佛學和科學的認識。
有很多人習慣說佛學是迷信,我說不,佛學不是迷信,佛學研究的東西和自然科學不同,是宇宙的另一方面,就是意識。佛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就像爬喜馬拉雅山一樣,一個從北坡往上爬,一個從南坡往上爬,總有一天兩者要會合的。
大家對這個說法先有了思想準備,對我後面講的東西可能就容易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