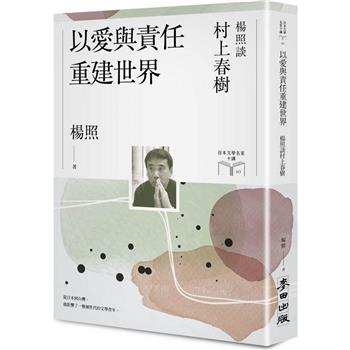【前言】
沒有終點的歷程──破解村上春樹的小說世界
談村上春樹的這本書,是「日本文學名家十講」系列中的最後一本,不過書中有一小部分內容,卻是我最早就動筆的。
三十多年前,從一九九○年開始,我在當時的《中國時報.開卷版》寫一個專欄,討論一些值得注意的暢銷書與出版現象。我記得在那個專欄裡寫過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荳荳》,寫過黃仁宇和「戰爭機器」(還有人記得這是什麼?),也寫了正在台灣開始流行的村上春樹。為了寫那篇文章,我將中山北路的「永漢書店」裡能找到的村上春樹原文書,再加上一部份中文譯本都讀了,形成了我最早對這位從日本紅到台灣的作家的作品意見。
之後村上春樹持續書寫,我也持續閱讀他的新作,愈來愈驚服於他旺盛的創作力量,以及堅忍琢磨鋪陳小說深厚底蘊的強大意志。十多年後,當我在「誠品講堂」開設「現代經典細讀」長期課程時,我已經明確認定,村上春樹的書,他那獨具風格的寫作手法,必然形成現代經典,於是也就將出版沒有多久的《海邊的卡夫卡》選入了「現代經典」分析講授的書單中。
再到二○一○年,我將誠品講堂課程內容整理擴充,以《永遠的少年:村上春樹與《海邊的卡夫卡》》的書名出版。書還沒正式出版,我已經知道那會是一本未完之書,因為就在書稿最後整理階段,村上春樹的《1Q84》第三冊問世了,我當然來不及將這部篇幅龐大的小說新作相關解讀放入《永遠的少年》書中,但我又很明白,在《1Q84》中,村上春樹不只是再度突破了自己,而且他又寫了一本高度考驗讀者耐心與專注力的作品。這種作品的特性就在於讀者愈是有耐心與文本周旋,愈是專注看待各種細節,會在閱讀過程中得到愈高又愈深的滿足。這種作品豈不也正是解讀者最該面對最值得面對的挑戰嗎?
出版前夕,我只能勉強以附錄的形式多塞進一篇文章,概要地討論《1Q84》。然而如此一來卻又打破了我原本自己對《永遠的少年》這本書的設定──聚焦細讀《海邊的卡夫卡》,盡量將《海邊的卡夫卡》裡所藏的諸多典故、互文有憑有據、條理清晰地鋪陳出來。如果不以《海邊的卡夫卡》為限,那麼不只是《1Q84》,村上春樹之前的幾部長篇小說,也有很多值得討論值得破解的地方啊!
那幾年我總想著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補足對村上春樹的認識與解說,然而也在那幾年間,村上春樹繼續猛進,以不同形式又交出了更多精采的成績。更進一步,那幾年間,村上春樹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水漲船高,真正的重點不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居高不下,而是走到世界各大城市的主要書店裡,幾乎都找得到以那個地方的語言翻譯的村上春樹作品,而且到處吸引了數量眾多的讀者。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德文版上市時,我剛好在德國,見證了德國廣播電台第一時間將書稿製播成節目,每天早晨按時連載播放,書店裡一位年紀較大的顧客在收銀檯前和年輕的店員熱情地交換他們天天聽書的心得。
一直到二○一八年,我才終於有機會在「藝集講堂」對感覺上闕漏愈來愈多的村上春樹理解做一些補償。我先用了五堂課解讀當時新出版的《刺殺騎士團長》,因為講課中不斷提到這本新作與《1Q84》之間的關係,經學員反覆要求,於是再用六堂課回頭完整解讀了《1Q84》。
擺在大家眼前的這本《以愛與責任重建世界:楊照談村上春樹》收錄了之前講《海邊的卡夫卡》的內容,再加上二○一八年對於《1Q84》的解讀。因為這兩部分加在一起,就已經有十五萬字左右的篇幅,為了顧及讀者閱讀所需的心力投入,本來已經整理為文字的《刺殺騎士團長》課程內容就沒有再放進來了。
事實上我私心以為可以放進來、該放進來的內容還有更多更多。去年(二○二二年)連續看了濱口龍介的兩部電影,先是對《偶然與想像》視為天人,讓我重拾了年少時看完電影可以將每個鏡頭詳記重述的樂趣;接著則是對《在車上Drive My Car》產生了複雜衝突的觀影感覺。《在車上Drive My Car》仍然是一部好電影,可以卻明顯比不上村上春樹的小說原著。不是說電影非得依照小說複製村上春樹所寫的意念、情感,然而要改編,應該要改得比小說更有電影性、電影感,不然就改得更深刻、更廣袤,但濱口龍介的改法卻顯然是沒有能充分掌握、展現村上春樹更深刻、更廣袤意念、情感的結果。
不見得是對濱口龍介的失望,毋寧是更增加了對村上春樹的佩服,也增加了對於讀者經常不能讀到他作品最深刻、最廣袤處的遺憾。我不知道今年七十三歲的村上春樹是不是還會再交出令人眼界大開的作品,但我確知我自己對於村上春樹作品的解讀還離終點很遠。不只是他有一些精采的短篇小說(例如〈Drive My Car〉)也值得被用最認真的態度仔細領略,他早期的長篇小說都留藏了許多很少被好好挖掘的曖曖內含光。
例如將最早的三部作品──《聽風的歌》、《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和《尋羊冒險記》放在一起當作三部曲來讀,和單獨看其中任何一本,境界與意趣完全不同。要是再將隔了許多年才寫的《舞.舞.舞》放進來成為第四部,突然之間,原本三部曲中極其濃厚的悲哀之感獲得了紓解,反而化為某種抗拒無奈的力量。別忘了,還有收錄在《麵包店再襲擊》短篇集子中的〈雙胞胎與沉沒的大陸〉也是從《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裡延續出來的啊!
類似卻性質不同的相關性還發生在:短篇〈螢火蟲〉是長篇《挪威的森林》的前身;短篇〈發條鳥與星期二的女人們〉是長篇《發條鳥年代記》的前身;而《麵包店再襲擊》和《電視人》兩部小說集裡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短篇小說,卻幾乎每篇都有一個叫「渡邊昇」的角色,不只是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關係嗎?而且他們跟《挪威的森林》裡的那位「渡邊君」也有什麼關係嗎?
太多太有趣的線索與謎,還在等著我們接受村上春樹的召喚勇敢地前往探尋。
第一章|村上春樹的創作背景
◎複製村上春樹
三十多年來,我持續閱讀村上春樹,大概他在台灣出版的中譯本都看了,還有一些原本以為台灣不太可能會有譯本,也就多花一點時間直接讀了日文版。例如他寫音樂的文章,關於爵士樂和古典音樂。
讀村上春樹最大的樂趣,在於書中藏著的各種「下一步做什麼」的暗示、甚至指令。這裡出現一段音樂、那裡出現一本書,於是一邊讀著一邊就想:「嗯,那就去把舒伯特找出來聽聽吧!」或「等我讀完這段就來讀讀《魔山》吧!」
那是一種奇特的閱讀經驗,和平常讀書,專心從第一行讀到最後一行的經驗不太一樣,毋寧比較像是在書中遊逛,逛到這裡會分心想去做點別的事,一面一面的大櫥窗展示著不同的物件,讓你猶豫思考,是要繼續走下去,還是停下來走進這個店家?
而且我清楚知道這種分心,是村上春樹書中本來就內建的邏輯,不是因為我這個讀者特別不認真,也不是因為他這位作者缺乏能力寫出讓人認真讀下去的文字。他的小說,站在這樣的遊逛式基礎上,因而很不一樣。
不過讀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會有特別的困擾。
其中一項困擾,是他的小說在台灣曾經有過眾多模仿者。尤其是一九九○年代初期,突然冒出來一大堆當時被稱為「新人類小說」的作品,裡面充斥了「贗品村上」。很明顯地,這些作者都讀村上春樹,被他小說中的氣氛、腔調吸引了,所以下筆一寫就寫出這樣的東西。
可是他們的「贗品村上」,很容易讓人看破手腳,馬上明白了他們是怎麼讀村上春樹小說的。他們似乎都可以不去注意到村上小說裡藏著的各種暗號、暗示,從來不走進村上小說大街上開設的種種商店,去看看裡面究竟真的擺放了些什麼;他們輕易就被大街上一種燈光氣氛眩惑了,將櫥窗裡展示的,不管是舒伯特、戴維斯、錢德勒或湯瑪斯.曼,都當作只是這氣氛的道具,就這樣走過大街,然後回家在自己的書桌上幻想複製一條那樣的大街。
他們是村上春樹太認真又太草率的讀者。太認真,因為他們很用力地閱讀村上寫出來的文字;太草率,因為他們沒有興趣追究村上鋪陳的各種符號的確切內容。因而他們自己搭蓋出來的大街,如此扁平,像是電視劇裡的拙劣道具布景,街道兩邊的櫥窗都是假的,隨便貼幾張照片,連櫥窗中的物品都不堪細看,當然就更沒有可以供人進入遊逛的店家了。
我極度厭惡這樣沒有景深的小說作品,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寫了文章批判這種現象,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很多人的印象裡,總以為我是討厭村上春樹的。
不,我沒有討厭村上春樹。比較接近事實的是,村上春樹對我,一直是困惑的謎題,吸引著我不斷思考、不斷試圖解題。
◎最暢銷的小說──《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會是村上春樹最暢銷的小說,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挪威的森林》在日本一上市大賣幾百萬冊,累積至今超過了一千萬冊,卻無可避免在我心中引發了問題:「為什麼一本如此哀傷的小說,可以在一個逃避哀傷的時代裡,變得如此熱門?」
《挪威的森林》小說一開頭,鋪陳完了飛機上的回憶情景後,立即出現的,是一口井。「井在草原盡頭開始要進入雜木林的分界線上。大地忽然打開直徑十公尺左右的黑暗洞穴,被草巧妙地覆蓋隱藏著。周圍既沒有木柵,也沒有稍微高起的井邊砌石。只有那張開的洞口而已。」
這是真正的開端,也是整部小說的核心隱喻。我們的人生,至少是小說主角們的人生,就是一段走在有著一口隱藏的井的草原上的旅程。他們之所以成為小說的主角,之所以一起發展他們的愛情故事,因為他們都在無從防備的情況下,掉入了那可怕的井中。
直子形容了掉入井中的可怕:「如果脖子就那樣骨折,很乾脆地死掉倒還好,萬一只是扭傷腳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儘管大聲叫喊,也沒有人聽見,不可能有誰會發現,周圍只有蜈蚣或蜘蛛在爬動著,周圍散落著一大堆死在那裡的人的白骨,陰暗而潮溼。而上方光線形成的圓圈簡直像冬天的月亮一樣小小地浮在上面。在那樣的地方孤伶伶地逐漸慢慢地死去。」
這其實也就是直子自己生命的描述。在她無從防備的情況下,青梅竹馬的情人キズキ突然自殺了。沒有遺書、沒有解釋,就這樣死了。直子被拋入那大聲喊叫也不會有人聽見的井裡。她僅有能夠得到的一點安慰,是同樣因為キズキ之死大受打擊的渡邊君。他們兩個人的愛情,是困守在井底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絕望的哀傷。
玲子姊是另一個掉入井裡的人。她比直子幸運又比直子不幸。幸運的是她曾經從井裡被救上去過。她遇到一個單純的人,單純到想和她「共同擁有心中一切」的男人,她能夠重新過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一次被救上來,無法保證不會第二次再掉下去,又是在無從防備的情況下,玲子栽在一個邪惡的小女孩手中,又掉入那可怕的井裡。
在這樣的核心角色之外,村上春樹又加上了一個冷酷、現實、算計,根本無法或不願體會人間愛情的永澤,和永澤身邊偏偏沒有辦法算計、沒有辦法背叛自己愛情感受的初美姊,兩個人之間無望的糾結。
◎小林綠的勇氣
這些人物構成的關係,為什麼能吸引那麼多人來讀,為什麼他們不會在閱讀過程中,被那深深的哀傷凍傷,至少沒有被逼退繼續閱讀下去的欲望?顯然很多人讀下去,而且還願意口耳相傳鼓吹別人也來讀,這本書才成為一個社會現象,乃至於社會事件。
難道是因為小說中另外一個角色,那個常常瘋瘋癲癲做著大膽行為,講著別人不一定能理解的話的小林綠?只有她,身上沒有沾染那份莫名其妙掉入井中的慌亂、失序與哀涼。
然則,在這樣一群陷入井中掙扎著的人之間,小林綠是什麼?或說,她有什麼力量,不只介入他們的世界,進而改變了這個世界原本的架構呢?
沒有終點的歷程──破解村上春樹的小說世界
談村上春樹的這本書,是「日本文學名家十講」系列中的最後一本,不過書中有一小部分內容,卻是我最早就動筆的。
三十多年前,從一九九○年開始,我在當時的《中國時報.開卷版》寫一個專欄,討論一些值得注意的暢銷書與出版現象。我記得在那個專欄裡寫過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荳荳》,寫過黃仁宇和「戰爭機器」(還有人記得這是什麼?),也寫了正在台灣開始流行的村上春樹。為了寫那篇文章,我將中山北路的「永漢書店」裡能找到的村上春樹原文書,再加上一部份中文譯本都讀了,形成了我最早對這位從日本紅到台灣的作家的作品意見。
之後村上春樹持續書寫,我也持續閱讀他的新作,愈來愈驚服於他旺盛的創作力量,以及堅忍琢磨鋪陳小說深厚底蘊的強大意志。十多年後,當我在「誠品講堂」開設「現代經典細讀」長期課程時,我已經明確認定,村上春樹的書,他那獨具風格的寫作手法,必然形成現代經典,於是也就將出版沒有多久的《海邊的卡夫卡》選入了「現代經典」分析講授的書單中。
再到二○一○年,我將誠品講堂課程內容整理擴充,以《永遠的少年:村上春樹與《海邊的卡夫卡》》的書名出版。書還沒正式出版,我已經知道那會是一本未完之書,因為就在書稿最後整理階段,村上春樹的《1Q84》第三冊問世了,我當然來不及將這部篇幅龐大的小說新作相關解讀放入《永遠的少年》書中,但我又很明白,在《1Q84》中,村上春樹不只是再度突破了自己,而且他又寫了一本高度考驗讀者耐心與專注力的作品。這種作品的特性就在於讀者愈是有耐心與文本周旋,愈是專注看待各種細節,會在閱讀過程中得到愈高又愈深的滿足。這種作品豈不也正是解讀者最該面對最值得面對的挑戰嗎?
出版前夕,我只能勉強以附錄的形式多塞進一篇文章,概要地討論《1Q84》。然而如此一來卻又打破了我原本自己對《永遠的少年》這本書的設定──聚焦細讀《海邊的卡夫卡》,盡量將《海邊的卡夫卡》裡所藏的諸多典故、互文有憑有據、條理清晰地鋪陳出來。如果不以《海邊的卡夫卡》為限,那麼不只是《1Q84》,村上春樹之前的幾部長篇小說,也有很多值得討論值得破解的地方啊!
那幾年我總想著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補足對村上春樹的認識與解說,然而也在那幾年間,村上春樹繼續猛進,以不同形式又交出了更多精采的成績。更進一步,那幾年間,村上春樹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水漲船高,真正的重點不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居高不下,而是走到世界各大城市的主要書店裡,幾乎都找得到以那個地方的語言翻譯的村上春樹作品,而且到處吸引了數量眾多的讀者。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德文版上市時,我剛好在德國,見證了德國廣播電台第一時間將書稿製播成節目,每天早晨按時連載播放,書店裡一位年紀較大的顧客在收銀檯前和年輕的店員熱情地交換他們天天聽書的心得。
一直到二○一八年,我才終於有機會在「藝集講堂」對感覺上闕漏愈來愈多的村上春樹理解做一些補償。我先用了五堂課解讀當時新出版的《刺殺騎士團長》,因為講課中不斷提到這本新作與《1Q84》之間的關係,經學員反覆要求,於是再用六堂課回頭完整解讀了《1Q84》。
擺在大家眼前的這本《以愛與責任重建世界:楊照談村上春樹》收錄了之前講《海邊的卡夫卡》的內容,再加上二○一八年對於《1Q84》的解讀。因為這兩部分加在一起,就已經有十五萬字左右的篇幅,為了顧及讀者閱讀所需的心力投入,本來已經整理為文字的《刺殺騎士團長》課程內容就沒有再放進來了。
事實上我私心以為可以放進來、該放進來的內容還有更多更多。去年(二○二二年)連續看了濱口龍介的兩部電影,先是對《偶然與想像》視為天人,讓我重拾了年少時看完電影可以將每個鏡頭詳記重述的樂趣;接著則是對《在車上Drive My Car》產生了複雜衝突的觀影感覺。《在車上Drive My Car》仍然是一部好電影,可以卻明顯比不上村上春樹的小說原著。不是說電影非得依照小說複製村上春樹所寫的意念、情感,然而要改編,應該要改得比小說更有電影性、電影感,不然就改得更深刻、更廣袤,但濱口龍介的改法卻顯然是沒有能充分掌握、展現村上春樹更深刻、更廣袤意念、情感的結果。
不見得是對濱口龍介的失望,毋寧是更增加了對村上春樹的佩服,也增加了對於讀者經常不能讀到他作品最深刻、最廣袤處的遺憾。我不知道今年七十三歲的村上春樹是不是還會再交出令人眼界大開的作品,但我確知我自己對於村上春樹作品的解讀還離終點很遠。不只是他有一些精采的短篇小說(例如〈Drive My Car〉)也值得被用最認真的態度仔細領略,他早期的長篇小說都留藏了許多很少被好好挖掘的曖曖內含光。
例如將最早的三部作品──《聽風的歌》、《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和《尋羊冒險記》放在一起當作三部曲來讀,和單獨看其中任何一本,境界與意趣完全不同。要是再將隔了許多年才寫的《舞.舞.舞》放進來成為第四部,突然之間,原本三部曲中極其濃厚的悲哀之感獲得了紓解,反而化為某種抗拒無奈的力量。別忘了,還有收錄在《麵包店再襲擊》短篇集子中的〈雙胞胎與沉沒的大陸〉也是從《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裡延續出來的啊!
類似卻性質不同的相關性還發生在:短篇〈螢火蟲〉是長篇《挪威的森林》的前身;短篇〈發條鳥與星期二的女人們〉是長篇《發條鳥年代記》的前身;而《麵包店再襲擊》和《電視人》兩部小說集裡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短篇小說,卻幾乎每篇都有一個叫「渡邊昇」的角色,不只是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關係嗎?而且他們跟《挪威的森林》裡的那位「渡邊君」也有什麼關係嗎?
太多太有趣的線索與謎,還在等著我們接受村上春樹的召喚勇敢地前往探尋。
第一章|村上春樹的創作背景
◎複製村上春樹
三十多年來,我持續閱讀村上春樹,大概他在台灣出版的中譯本都看了,還有一些原本以為台灣不太可能會有譯本,也就多花一點時間直接讀了日文版。例如他寫音樂的文章,關於爵士樂和古典音樂。
讀村上春樹最大的樂趣,在於書中藏著的各種「下一步做什麼」的暗示、甚至指令。這裡出現一段音樂、那裡出現一本書,於是一邊讀著一邊就想:「嗯,那就去把舒伯特找出來聽聽吧!」或「等我讀完這段就來讀讀《魔山》吧!」
那是一種奇特的閱讀經驗,和平常讀書,專心從第一行讀到最後一行的經驗不太一樣,毋寧比較像是在書中遊逛,逛到這裡會分心想去做點別的事,一面一面的大櫥窗展示著不同的物件,讓你猶豫思考,是要繼續走下去,還是停下來走進這個店家?
而且我清楚知道這種分心,是村上春樹書中本來就內建的邏輯,不是因為我這個讀者特別不認真,也不是因為他這位作者缺乏能力寫出讓人認真讀下去的文字。他的小說,站在這樣的遊逛式基礎上,因而很不一樣。
不過讀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會有特別的困擾。
其中一項困擾,是他的小說在台灣曾經有過眾多模仿者。尤其是一九九○年代初期,突然冒出來一大堆當時被稱為「新人類小說」的作品,裡面充斥了「贗品村上」。很明顯地,這些作者都讀村上春樹,被他小說中的氣氛、腔調吸引了,所以下筆一寫就寫出這樣的東西。
可是他們的「贗品村上」,很容易讓人看破手腳,馬上明白了他們是怎麼讀村上春樹小說的。他們似乎都可以不去注意到村上小說裡藏著的各種暗號、暗示,從來不走進村上小說大街上開設的種種商店,去看看裡面究竟真的擺放了些什麼;他們輕易就被大街上一種燈光氣氛眩惑了,將櫥窗裡展示的,不管是舒伯特、戴維斯、錢德勒或湯瑪斯.曼,都當作只是這氣氛的道具,就這樣走過大街,然後回家在自己的書桌上幻想複製一條那樣的大街。
他們是村上春樹太認真又太草率的讀者。太認真,因為他們很用力地閱讀村上寫出來的文字;太草率,因為他們沒有興趣追究村上鋪陳的各種符號的確切內容。因而他們自己搭蓋出來的大街,如此扁平,像是電視劇裡的拙劣道具布景,街道兩邊的櫥窗都是假的,隨便貼幾張照片,連櫥窗中的物品都不堪細看,當然就更沒有可以供人進入遊逛的店家了。
我極度厭惡這樣沒有景深的小說作品,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寫了文章批判這種現象,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很多人的印象裡,總以為我是討厭村上春樹的。
不,我沒有討厭村上春樹。比較接近事實的是,村上春樹對我,一直是困惑的謎題,吸引著我不斷思考、不斷試圖解題。
◎最暢銷的小說──《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會是村上春樹最暢銷的小說,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挪威的森林》在日本一上市大賣幾百萬冊,累積至今超過了一千萬冊,卻無可避免在我心中引發了問題:「為什麼一本如此哀傷的小說,可以在一個逃避哀傷的時代裡,變得如此熱門?」
《挪威的森林》小說一開頭,鋪陳完了飛機上的回憶情景後,立即出現的,是一口井。「井在草原盡頭開始要進入雜木林的分界線上。大地忽然打開直徑十公尺左右的黑暗洞穴,被草巧妙地覆蓋隱藏著。周圍既沒有木柵,也沒有稍微高起的井邊砌石。只有那張開的洞口而已。」
這是真正的開端,也是整部小說的核心隱喻。我們的人生,至少是小說主角們的人生,就是一段走在有著一口隱藏的井的草原上的旅程。他們之所以成為小說的主角,之所以一起發展他們的愛情故事,因為他們都在無從防備的情況下,掉入了那可怕的井中。
直子形容了掉入井中的可怕:「如果脖子就那樣骨折,很乾脆地死掉倒還好,萬一只是扭傷腳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儘管大聲叫喊,也沒有人聽見,不可能有誰會發現,周圍只有蜈蚣或蜘蛛在爬動著,周圍散落著一大堆死在那裡的人的白骨,陰暗而潮溼。而上方光線形成的圓圈簡直像冬天的月亮一樣小小地浮在上面。在那樣的地方孤伶伶地逐漸慢慢地死去。」
這其實也就是直子自己生命的描述。在她無從防備的情況下,青梅竹馬的情人キズキ突然自殺了。沒有遺書、沒有解釋,就這樣死了。直子被拋入那大聲喊叫也不會有人聽見的井裡。她僅有能夠得到的一點安慰,是同樣因為キズキ之死大受打擊的渡邊君。他們兩個人的愛情,是困守在井底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絕望的哀傷。
玲子姊是另一個掉入井裡的人。她比直子幸運又比直子不幸。幸運的是她曾經從井裡被救上去過。她遇到一個單純的人,單純到想和她「共同擁有心中一切」的男人,她能夠重新過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一次被救上來,無法保證不會第二次再掉下去,又是在無從防備的情況下,玲子栽在一個邪惡的小女孩手中,又掉入那可怕的井裡。
在這樣的核心角色之外,村上春樹又加上了一個冷酷、現實、算計,根本無法或不願體會人間愛情的永澤,和永澤身邊偏偏沒有辦法算計、沒有辦法背叛自己愛情感受的初美姊,兩個人之間無望的糾結。
◎小林綠的勇氣
這些人物構成的關係,為什麼能吸引那麼多人來讀,為什麼他們不會在閱讀過程中,被那深深的哀傷凍傷,至少沒有被逼退繼續閱讀下去的欲望?顯然很多人讀下去,而且還願意口耳相傳鼓吹別人也來讀,這本書才成為一個社會現象,乃至於社會事件。
難道是因為小說中另外一個角色,那個常常瘋瘋癲癲做著大膽行為,講著別人不一定能理解的話的小林綠?只有她,身上沒有沾染那份莫名其妙掉入井中的慌亂、失序與哀涼。
然則,在這樣一群陷入井中掙扎著的人之間,小林綠是什麼?或說,她有什麼力量,不只介入他們的世界,進而改變了這個世界原本的架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