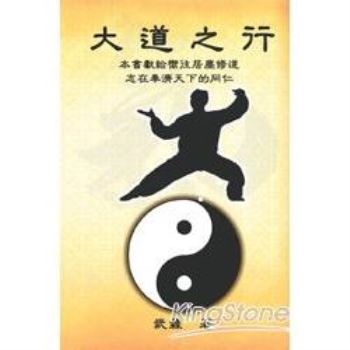第一章 古典氣功的啟示
1975年在青海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個雙耳陶罐。罐體上,有一彩繪的浮雕人像,雙目微睜,口張大,近圓形,如呵氣狀;腹部微隆,雙腳平放而寬於肩;下肢微曲,呈蹲襠式;雙手張開,置於腹部兩側;不僅很像後世所傳的站樁練功的樣子,而且和某些吐納功法的練功外表很相似。據考證,這是屬於公元前3000-2000年的馬廠文化(約略與黃帝同時)的文物。可見當時氣功之流行。? 在公元前1100-前770年的周代金文中,也有關於氣功的記載。
春秋戰國時編纂的《呂氏春秋》中說,某地 “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根據文中所言,此“舞”可治筋骨之患,可推斷為一種宣導氣脈、通利關節、去陳苛、防疾患,類似於氣功中的“動功”的導引術。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和在某些原始部落發現的原始民的“舞”的風格、體姿分析,這裡的“舞”更似乎是指帶有一定的節奏、類似於氣功的“自發動功”的人體運動形式。
出土文物《行氣玉佩銘》,被考古學者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作品,其十二面體上銘有:“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幾舂在上,地幾舂在下,順則生,逆則死”。四十五個字,不僅闡明了氣功於養生的作用,也將真氣在體內的運行路徑描述得一清二楚。? 1970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初期(約公元前200年)的44幅彩帛導引圖和《卻穀服氣篇》中,有各種練功姿態。從中能夠看到當時流行的氣功行氣方法。
據史載最早的氣功修煉時期,是諸子蜂起、百家爭豔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既是中華古文化的黃金時代,也是樸素氣功的隆盛時期。春秋時期的氣功,尚屬士大夫們的專門之學;至戰國後期,修煉人群下移至“仕”,開始了有普及的趨勢。?作為在“天人合一”宇宙觀指導下的一門“術”,氣功散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學派著作中。氣功術是當時學術家共研之學。儒家的六藝 (禮、樂、射、禦、書、數),道家的老、莊學說,醫家的卓越成就,兵家的傑世之作,墨家的物質理論等,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再結合氣功學理論來推斷,這些成就都是在氣功實踐中建立的。這一時期的氣功,風格樸實無華,內容簡易明瞭,功法直指本源。?氣功修煉在此時期,以提高人的身心素質為首務,將練功開發的功能(人體潛能)用於探索自然和人體生命,以及人和自然、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等。所以,這一時期的氣功已有了學問的性質。囿於時代文化的局限,氣功在那時沒有上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條件。我們從“學富五車”這個出自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典故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文化普及狀況。
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制皇朝——秦皇朝,誕生於公元前221年。中國從此開始走進她漫長的君主集權統治之路。春秋戰國時期自由爭鳴的學術風範,在專制制度的威棒之下漸而褪色。西漢武帝(前156—前87年)是一個崇尚神仙之術的皇帝,當時的儒士墨客亦以修仙為時髦,為此趨之若鶩。因神仙方術的主要內容是氣功修煉。以治學、理政見長的儒學士們的氣功實踐,無意間深化了氣功在社會領域中的運用。漢武帝繼而又採納儒學大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主張,也突顯儒家理念有助於統治者的攝政的優勢。中國社會歷來以“人治”為主要政管手段,統治者因此極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的說教,來規範和約束民眾的思想、行為,以此行安定社會秩序之實。例如,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在世時就很崇敬“周禮”。周禮內容之全面、周到、細致、深入的程度讓人矚目,夫妻圓房都要由天氣或月亮的狀況決取。這一方面有最大限度地維護人的生命活動正常化的作用,因那個時代的醫療狀況不能和現在同日而語;另一方面,那時的民風淳僕,人的思想簡單,有了現成的倫理說教,民眾會按其中的規範說教處世、行事,社會秩序能由此得到穩定。這是一個讓民眾自行維護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的有效途徑。
儒家不像道家,把興趣多放在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上。種種原因,讓中國早期的統治者,最後選擇了儒家而非道家,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老大。儒家由此得天勢地利,孔子思想在公元以後的中國,逐步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隨著儒家思想的發揚光大,以探索自然和人體奧秘見長的道家,漸而退出社會領域,完全讓位於儒家。道學士們或隱跡於山野宮觀,享紅顏駐世之趣;或逍遙於世外之域,行長生久視之遁。戰國、先秦時代造就的氣功生命之光還沒來得及普照人間,就退出了“學”之殿堂。
道家雖然選擇了循世修煉之路,但在氣功學說方面是主要貢獻者。道家內氣修煉派在公元初成形,其經驗之說充實了春秋戰國以來的氣功學說。約於公元280—316年的西晉時代,道家氣功學說已初具規模。?經過歷代道家修煉者不斷總結和擴充積累起來的氣功典藉中的學說,是中國古典氣功理論的重要一部分。她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步入公元世紀,印度人攜佛經傳中原大地。公元2世紀中葉,中國首個道教團體現世。從此的中國,儒、道、釋(佛)三家鼎立,氣功依附於“三教”的歷史從此開始。
唐朝(公元618—907年)以前的道家,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輸於、也不服於佛家。畢竟道家是在中原大地土生土長的“大老”之學。然越山涉水的“移民”宗教——印度原始佛教,初來乍到之時,曾歷盡道、儒二家,特別是道教的欺淩、數落。進入大唐以後,歷盡苦心經營的佛家,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從勢單力薄到根基漸實,繼而羽翼豐滿,甚可獨當一方。而儒學在進入宋朝以後,脫變成為訓詁研典的經院之學,失去了以往欣欣向上的學術風範,由此漸失與佛家在哲學上的抗衡之勢。
漢地佛家不注重肉身修煉,但在意識實踐上,是道家望塵莫及的。道家人士當然明白,意識實踐乃是“得道登仙”、“白日飛昇”之圭旨秘臬,是修煉之根本。但是,在佛家精神修煉文化這個背景中的道家,顯然苦於自身對意識的研究既貧乏又無績,而不得不甘認服輸、聽命仰望於佛家。另外,在傳功理念上,道家的是主張“道不傳匪人”,“法不傳六耳”等;這些理念,使道家失去了群眾基礎。而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卻以“三根普被”、“眾生得救”為已任。佛教從此贏得民眾的青睞,在勢力範圍上反客為主,坐大中原。
唐朝是中國繼春秋戰國以後,政治、經濟、文化最鼎盛的時期,也是漢地佛教最興旺的時期。例如,初唐貞觀年間,曾出現長安十萬人念佛的壯舉。經濟的興旺,帶來了文化的發達,使人們的思維變得躍活,也越來越複雜和精細。這反映在氣功修煉上,就是修煉人在與修煉相關的領域,如自然、社會、人體和意識方面的探索不斷深化。人體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機能體。提昇人體生命質度的氣功功法,隨著一代又一代修煉人不同的個人體會,從最初的“一氣混元”到“陰陽二分”,從“二儀”到 “四像”、繼而建立“五運”,“六氣”,又將“八卦”、“六十四卦”理論都融入了氣功的功法理論中。氣功功法由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解釋功法的理論也越來越冗繁。這是造成氣功修煉門派越來越多的主因。
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各家修煉門派,為了自身的發展,相繼興起過神化氣功起源的風潮。這在以文盲農民為主體人群的古代中國社會,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宣傳自身理念的辦法。標榜己之一派為某仙、某神所傳,貶他派為“傍門”、“外道”、“佐道”,不但在古中國司空見慣(當代中國氣功界內此現象就原於此)。戰國、先秦時期用於探索自然和生命奧秘的內向性運用意識這一部分修身之學,在宗教內部演變成教徒們追求宗教體驗的手段和完成宗教信仰的工具。練氣功開發的人體潛能,在那個時代被稱作“神通”。宗教借由“神通”得顯其非同凡響和神秘外表,“神通”的光暈賦於宗教超自然的威儀和引人膜拜的神聖之態。然而,氣功與宗教的關係愈演愈密切的後果卻是:很大一部分氣功修煉方法,隱入了道觀、佛殿的幽門高牆內,以特權專利和絕世秘技之形式,在封閉式的教學方式中單線續傳。
站在氣功學的立場看,氣功的宗教化確實異化了氣功的本質,但在古中國的人文環境裡,氣功的宗教化勢在必行。因為在文化並不普及,又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的社會里,宗教化的氣功修煉形式就是既能兼顧精神信仰,又有修身養命之效的實?方式。然而,大中華民族的意識深處,歷來不缺探索生命奧秘的強烈願望。氣功的宗教化無法影響這一文化因素的繼定發揮。中華道統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唯物主義精神。這個精神,又無時不刻地反映在中國的宗教思想中,影響著中國宗教氣功的發展方向。這一原因,使得中國的宗教與世界其它的宗教有一個根本差別,那就是,中國的宗教徒從來不缺人體修煉活動。皆由此因,中國的宗教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氣功生命科學的內容。特別從道教徒的修煉活動中,我們得到了這種保留的大量證據。雖然說這種保留還是感性的、不自覺的。
越過唐朝之輝煌,中國社會歷經了“五代十國”的紛亂,自宋朝(公元960—1279年)以後,中國的政、經、文、科再也沒有出現大唐之盛景。佛教從唐早期在中國盛行,到唐朝的中後期,佛教無論在勢力範圍還是文化影響力,都列百家之首。儒家由此首起“外服儒風,內宗梵行”的主張;道家接著開宗明義地喊出“三教混一”,“三教圓融”的口號。當宋朝的君皇為祈求大宋江山能萬代延續而再次祭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幡,在程朱理學把儒家說教再次簇擁到無上高峰之時,經歷了盛世洗練的儒、道、釋、醫各家,此刻都不約而同地開始學借他派的長處充實自身。例如,佛、道二家吸收儒家的養性培德心法和處世倫理精神;儒家攝取佛學之禪理,又納道家一部分養生術於其中;道家又取佛家的心性和禪修的理論,充實了道家養生學的內容;佛家亦取了道家的養生學說和醫家之理。歷經了從漢到唐的分化,儒、道、釋、醫各家的學說和功法經彼此間的滲透和融合,出現了“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犬牙交錯、大同小異之像,給人一種“萬法歸宗”的勢頭。氣功功法有了走向合流之勢。這是人體修煉的本質所決定的。這個本質就是——用意識整合人的整體生命活動。所謂的“萬法歸宗”,就是要歸到人的意識修煉上。這顯然是氣功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國氣功發展史上的一個大的進步。從這一歷史現象可以理悟到:氣功功法的統一化,是有其歷史淵由的。而過於複雜的功法,不但有悖於人體修煉原則,也讓人難以掌握,就會有失傳之嫌。
氣功功法統一化,源於一個因素:中華民族的意識中根植的“身心和諧”、“人天相應”的生命觀,使得中華民族在探索人體奧秘上,比其它民族有更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更執切的渴求。在這一民族精神背景中爭相豔異的氣功功法,在探索人體生命奧秘、強化人體生命運動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中國氣功文化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五花八門的氣功功法隱含著歸合一統的“先天基因”。氣功的發展由此合乎從單元到多元,再從多元綜合歸一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學規律。? 遺憾的是,在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制中生存與發展的氣功,雖然自古即具統一而樸素的整體方法論思想,但由於整個社會還欠缺“為公”的思想,氣功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沒有能?完成功法、功理上的統一大業。
宋代的中國頻遭異族侵犯,以致疆土分裂,後亡國,處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元朝(公元1217—1368年)是漢民族第一次蒙恥成為中國史上的亡國奴的朝代。在漢人反抗外來民族思緒的推波助瀾下,產生了一種將氣功融於武技的新型氣功——武術氣功。自元朝起,武術氣功有了長足的發展。明、清二代(公元1368—1616—1911年)是武術氣功的鼎盛時期。鴉片戰爭以後,武術氣功在西方列強的洋槍大炮面前,失去了其“刀槍不入”的肉博防身自衛的優勢。至20世紀初,高層次的武術氣功功法漸之?傳。
歷朝歷代的氣功修煉者們從其自身實踐中深悟到一個真理:功夫是艱辛鍛煉的結果。而最講究實際功夫效應的是武林中人。武術人士因此是第一批不動搖地認同這個理念的修煉者。武術氣功理念由此衝擊了氣功中的宗教思想。顯然,宗教思想在人體生命修煉中並不是積極的。在此舉二個例子:一個是唐玄奘(公元602-664),是公認的佛學大家,按理說也是人體修煉大家。但從其62歲的壽辰的事實,不得不對他所傳的大乘佛教中的人體修煉學說,和他個人的修行方法作氣功學術上的重新評估。另一個是從《辭海 ‧ 宗教分冊》?中統計而來的數據:自東漢末年到唐朝後的五代十國後期的近800年中,漢地佛教高僧有67位(國外來漢學佛者不計其內);而從宋朝初年到1950年代的1000年裡,只有高僧17位。這個數據間接證明,以瑜伽修煉為根基的佛教漢傳分支,至唐朝達盛極,此後走向了衰落的主因就是,近千年來的漢佛,淡化與忽略了氣功修煉這個最具實質效應的人體實踐活動。
我們所言的“古氣功”的截止年代,是1911年。19世紀中葉以後,歐美文化大進中國。國人自20世紀初起,全面向西方學習。氣功中的宗教思想在這一時期又受到了實證科學的衝擊,西方文化中的唯物、無神哲學觀,從這個時期始,給氣功造就了一個新的文化比較和參照環境。
中國氣功門派眾多,源流到底從何而來,又在哪些領域存在和保留?作者曾於1981年10月在浙江紹興舉辦的浙江省首屆太極拳比賽期間的一個氣功講座上,首次聆聽到杭州氣功家胡美成先生做的關於這個論題的演講。他認為,中國氣功源流於、保留於“儒、釋、道、醫、武、民間”這六大領域。這一觀點後被中國氣功界普遍認同。由於釋(佛)家,在中國的出現,遲於道、儒二家。中國文化的統領者,又是道家文化。為此,在次序的排列上,道家應為首。又因儒家在漢朝以後成了中國文化界的主流,無論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還是於世界的知名度,都遠在道、佛家之上。若按此六大淵源流派對氣功的依賴程度和對氣功的認識水平排列,又以“道、佛、儒、醫、武、民間”為適。本書的排列順序對此的排列順序,選定為“儒、道、佛、醫、武、民間”。
各大家對氣功這個實踐方法,一直以來都有各自的稱謂:道家自言煉丹、服氣、吐納、坐忘等,認為這是得道成仙之必須方法;佛家認為這是觀想、禪定、見性,是成佛的唯一通途;儒家喜稱守中、誠意、正心、養性等,將其視為修身、治學的基本功夫;醫家謂之導引、內視,譽其為直達上乘醫道的捷徑;武術家視“站樁煉氣”為“武練”之道、“靜坐養心”為“文修”之境,認為練氣養心,既是入門基本功課,也是提高武技的精要秘術。
古典氣功的方方面面,將在我們今天認識氣功這個文化形式時,有不可多得的啟示。
1975年在青海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個雙耳陶罐。罐體上,有一彩繪的浮雕人像,雙目微睜,口張大,近圓形,如呵氣狀;腹部微隆,雙腳平放而寬於肩;下肢微曲,呈蹲襠式;雙手張開,置於腹部兩側;不僅很像後世所傳的站樁練功的樣子,而且和某些吐納功法的練功外表很相似。據考證,這是屬於公元前3000-2000年的馬廠文化(約略與黃帝同時)的文物。可見當時氣功之流行。? 在公元前1100-前770年的周代金文中,也有關於氣功的記載。
春秋戰國時編纂的《呂氏春秋》中說,某地 “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根據文中所言,此“舞”可治筋骨之患,可推斷為一種宣導氣脈、通利關節、去陳苛、防疾患,類似於氣功中的“動功”的導引術。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和在某些原始部落發現的原始民的“舞”的風格、體姿分析,這裡的“舞”更似乎是指帶有一定的節奏、類似於氣功的“自發動功”的人體運動形式。
出土文物《行氣玉佩銘》,被考古學者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作品,其十二面體上銘有:“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幾舂在上,地幾舂在下,順則生,逆則死”。四十五個字,不僅闡明了氣功於養生的作用,也將真氣在體內的運行路徑描述得一清二楚。? 1970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初期(約公元前200年)的44幅彩帛導引圖和《卻穀服氣篇》中,有各種練功姿態。從中能夠看到當時流行的氣功行氣方法。
據史載最早的氣功修煉時期,是諸子蜂起、百家爭豔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既是中華古文化的黃金時代,也是樸素氣功的隆盛時期。春秋時期的氣功,尚屬士大夫們的專門之學;至戰國後期,修煉人群下移至“仕”,開始了有普及的趨勢。?作為在“天人合一”宇宙觀指導下的一門“術”,氣功散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學派著作中。氣功術是當時學術家共研之學。儒家的六藝 (禮、樂、射、禦、書、數),道家的老、莊學說,醫家的卓越成就,兵家的傑世之作,墨家的物質理論等,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再結合氣功學理論來推斷,這些成就都是在氣功實踐中建立的。這一時期的氣功,風格樸實無華,內容簡易明瞭,功法直指本源。?氣功修煉在此時期,以提高人的身心素質為首務,將練功開發的功能(人體潛能)用於探索自然和人體生命,以及人和自然、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等。所以,這一時期的氣功已有了學問的性質。囿於時代文化的局限,氣功在那時沒有上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條件。我們從“學富五車”這個出自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典故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文化普及狀況。
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制皇朝——秦皇朝,誕生於公元前221年。中國從此開始走進她漫長的君主集權統治之路。春秋戰國時期自由爭鳴的學術風範,在專制制度的威棒之下漸而褪色。西漢武帝(前156—前87年)是一個崇尚神仙之術的皇帝,當時的儒士墨客亦以修仙為時髦,為此趨之若鶩。因神仙方術的主要內容是氣功修煉。以治學、理政見長的儒學士們的氣功實踐,無意間深化了氣功在社會領域中的運用。漢武帝繼而又採納儒學大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主張,也突顯儒家理念有助於統治者的攝政的優勢。中國社會歷來以“人治”為主要政管手段,統治者因此極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的說教,來規範和約束民眾的思想、行為,以此行安定社會秩序之實。例如,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在世時就很崇敬“周禮”。周禮內容之全面、周到、細致、深入的程度讓人矚目,夫妻圓房都要由天氣或月亮的狀況決取。這一方面有最大限度地維護人的生命活動正常化的作用,因那個時代的醫療狀況不能和現在同日而語;另一方面,那時的民風淳僕,人的思想簡單,有了現成的倫理說教,民眾會按其中的規範說教處世、行事,社會秩序能由此得到穩定。這是一個讓民眾自行維護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的有效途徑。
儒家不像道家,把興趣多放在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上。種種原因,讓中國早期的統治者,最後選擇了儒家而非道家,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老大。儒家由此得天勢地利,孔子思想在公元以後的中國,逐步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隨著儒家思想的發揚光大,以探索自然和人體奧秘見長的道家,漸而退出社會領域,完全讓位於儒家。道學士們或隱跡於山野宮觀,享紅顏駐世之趣;或逍遙於世外之域,行長生久視之遁。戰國、先秦時代造就的氣功生命之光還沒來得及普照人間,就退出了“學”之殿堂。
道家雖然選擇了循世修煉之路,但在氣功學說方面是主要貢獻者。道家內氣修煉派在公元初成形,其經驗之說充實了春秋戰國以來的氣功學說。約於公元280—316年的西晉時代,道家氣功學說已初具規模。?經過歷代道家修煉者不斷總結和擴充積累起來的氣功典藉中的學說,是中國古典氣功理論的重要一部分。她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步入公元世紀,印度人攜佛經傳中原大地。公元2世紀中葉,中國首個道教團體現世。從此的中國,儒、道、釋(佛)三家鼎立,氣功依附於“三教”的歷史從此開始。
唐朝(公元618—907年)以前的道家,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輸於、也不服於佛家。畢竟道家是在中原大地土生土長的“大老”之學。然越山涉水的“移民”宗教——印度原始佛教,初來乍到之時,曾歷盡道、儒二家,特別是道教的欺淩、數落。進入大唐以後,歷盡苦心經營的佛家,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從勢單力薄到根基漸實,繼而羽翼豐滿,甚可獨當一方。而儒學在進入宋朝以後,脫變成為訓詁研典的經院之學,失去了以往欣欣向上的學術風範,由此漸失與佛家在哲學上的抗衡之勢。
漢地佛家不注重肉身修煉,但在意識實踐上,是道家望塵莫及的。道家人士當然明白,意識實踐乃是“得道登仙”、“白日飛昇”之圭旨秘臬,是修煉之根本。但是,在佛家精神修煉文化這個背景中的道家,顯然苦於自身對意識的研究既貧乏又無績,而不得不甘認服輸、聽命仰望於佛家。另外,在傳功理念上,道家的是主張“道不傳匪人”,“法不傳六耳”等;這些理念,使道家失去了群眾基礎。而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卻以“三根普被”、“眾生得救”為已任。佛教從此贏得民眾的青睞,在勢力範圍上反客為主,坐大中原。
唐朝是中國繼春秋戰國以後,政治、經濟、文化最鼎盛的時期,也是漢地佛教最興旺的時期。例如,初唐貞觀年間,曾出現長安十萬人念佛的壯舉。經濟的興旺,帶來了文化的發達,使人們的思維變得躍活,也越來越複雜和精細。這反映在氣功修煉上,就是修煉人在與修煉相關的領域,如自然、社會、人體和意識方面的探索不斷深化。人體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機能體。提昇人體生命質度的氣功功法,隨著一代又一代修煉人不同的個人體會,從最初的“一氣混元”到“陰陽二分”,從“二儀”到 “四像”、繼而建立“五運”,“六氣”,又將“八卦”、“六十四卦”理論都融入了氣功的功法理論中。氣功功法由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解釋功法的理論也越來越冗繁。這是造成氣功修煉門派越來越多的主因。
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各家修煉門派,為了自身的發展,相繼興起過神化氣功起源的風潮。這在以文盲農民為主體人群的古代中國社會,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宣傳自身理念的辦法。標榜己之一派為某仙、某神所傳,貶他派為“傍門”、“外道”、“佐道”,不但在古中國司空見慣(當代中國氣功界內此現象就原於此)。戰國、先秦時期用於探索自然和生命奧秘的內向性運用意識這一部分修身之學,在宗教內部演變成教徒們追求宗教體驗的手段和完成宗教信仰的工具。練氣功開發的人體潛能,在那個時代被稱作“神通”。宗教借由“神通”得顯其非同凡響和神秘外表,“神通”的光暈賦於宗教超自然的威儀和引人膜拜的神聖之態。然而,氣功與宗教的關係愈演愈密切的後果卻是:很大一部分氣功修煉方法,隱入了道觀、佛殿的幽門高牆內,以特權專利和絕世秘技之形式,在封閉式的教學方式中單線續傳。
站在氣功學的立場看,氣功的宗教化確實異化了氣功的本質,但在古中國的人文環境裡,氣功的宗教化勢在必行。因為在文化並不普及,又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的社會里,宗教化的氣功修煉形式就是既能兼顧精神信仰,又有修身養命之效的實?方式。然而,大中華民族的意識深處,歷來不缺探索生命奧秘的強烈願望。氣功的宗教化無法影響這一文化因素的繼定發揮。中華道統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唯物主義精神。這個精神,又無時不刻地反映在中國的宗教思想中,影響著中國宗教氣功的發展方向。這一原因,使得中國的宗教與世界其它的宗教有一個根本差別,那就是,中國的宗教徒從來不缺人體修煉活動。皆由此因,中國的宗教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氣功生命科學的內容。特別從道教徒的修煉活動中,我們得到了這種保留的大量證據。雖然說這種保留還是感性的、不自覺的。
越過唐朝之輝煌,中國社會歷經了“五代十國”的紛亂,自宋朝(公元960—1279年)以後,中國的政、經、文、科再也沒有出現大唐之盛景。佛教從唐早期在中國盛行,到唐朝的中後期,佛教無論在勢力範圍還是文化影響力,都列百家之首。儒家由此首起“外服儒風,內宗梵行”的主張;道家接著開宗明義地喊出“三教混一”,“三教圓融”的口號。當宋朝的君皇為祈求大宋江山能萬代延續而再次祭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幡,在程朱理學把儒家說教再次簇擁到無上高峰之時,經歷了盛世洗練的儒、道、釋、醫各家,此刻都不約而同地開始學借他派的長處充實自身。例如,佛、道二家吸收儒家的養性培德心法和處世倫理精神;儒家攝取佛學之禪理,又納道家一部分養生術於其中;道家又取佛家的心性和禪修的理論,充實了道家養生學的內容;佛家亦取了道家的養生學說和醫家之理。歷經了從漢到唐的分化,儒、道、釋、醫各家的學說和功法經彼此間的滲透和融合,出現了“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犬牙交錯、大同小異之像,給人一種“萬法歸宗”的勢頭。氣功功法有了走向合流之勢。這是人體修煉的本質所決定的。這個本質就是——用意識整合人的整體生命活動。所謂的“萬法歸宗”,就是要歸到人的意識修煉上。這顯然是氣功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國氣功發展史上的一個大的進步。從這一歷史現象可以理悟到:氣功功法的統一化,是有其歷史淵由的。而過於複雜的功法,不但有悖於人體修煉原則,也讓人難以掌握,就會有失傳之嫌。
氣功功法統一化,源於一個因素:中華民族的意識中根植的“身心和諧”、“人天相應”的生命觀,使得中華民族在探索人體奧秘上,比其它民族有更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更執切的渴求。在這一民族精神背景中爭相豔異的氣功功法,在探索人體生命奧秘、強化人體生命運動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中國氣功文化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五花八門的氣功功法隱含著歸合一統的“先天基因”。氣功的發展由此合乎從單元到多元,再從多元綜合歸一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學規律。? 遺憾的是,在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制中生存與發展的氣功,雖然自古即具統一而樸素的整體方法論思想,但由於整個社會還欠缺“為公”的思想,氣功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沒有能?完成功法、功理上的統一大業。
宋代的中國頻遭異族侵犯,以致疆土分裂,後亡國,處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元朝(公元1217—1368年)是漢民族第一次蒙恥成為中國史上的亡國奴的朝代。在漢人反抗外來民族思緒的推波助瀾下,產生了一種將氣功融於武技的新型氣功——武術氣功。自元朝起,武術氣功有了長足的發展。明、清二代(公元1368—1616—1911年)是武術氣功的鼎盛時期。鴉片戰爭以後,武術氣功在西方列強的洋槍大炮面前,失去了其“刀槍不入”的肉博防身自衛的優勢。至20世紀初,高層次的武術氣功功法漸之?傳。
歷朝歷代的氣功修煉者們從其自身實踐中深悟到一個真理:功夫是艱辛鍛煉的結果。而最講究實際功夫效應的是武林中人。武術人士因此是第一批不動搖地認同這個理念的修煉者。武術氣功理念由此衝擊了氣功中的宗教思想。顯然,宗教思想在人體生命修煉中並不是積極的。在此舉二個例子:一個是唐玄奘(公元602-664),是公認的佛學大家,按理說也是人體修煉大家。但從其62歲的壽辰的事實,不得不對他所傳的大乘佛教中的人體修煉學說,和他個人的修行方法作氣功學術上的重新評估。另一個是從《辭海 ‧ 宗教分冊》?中統計而來的數據:自東漢末年到唐朝後的五代十國後期的近800年中,漢地佛教高僧有67位(國外來漢學佛者不計其內);而從宋朝初年到1950年代的1000年裡,只有高僧17位。這個數據間接證明,以瑜伽修煉為根基的佛教漢傳分支,至唐朝達盛極,此後走向了衰落的主因就是,近千年來的漢佛,淡化與忽略了氣功修煉這個最具實質效應的人體實踐活動。
我們所言的“古氣功”的截止年代,是1911年。19世紀中葉以後,歐美文化大進中國。國人自20世紀初起,全面向西方學習。氣功中的宗教思想在這一時期又受到了實證科學的衝擊,西方文化中的唯物、無神哲學觀,從這個時期始,給氣功造就了一個新的文化比較和參照環境。
中國氣功門派眾多,源流到底從何而來,又在哪些領域存在和保留?作者曾於1981年10月在浙江紹興舉辦的浙江省首屆太極拳比賽期間的一個氣功講座上,首次聆聽到杭州氣功家胡美成先生做的關於這個論題的演講。他認為,中國氣功源流於、保留於“儒、釋、道、醫、武、民間”這六大領域。這一觀點後被中國氣功界普遍認同。由於釋(佛)家,在中國的出現,遲於道、儒二家。中國文化的統領者,又是道家文化。為此,在次序的排列上,道家應為首。又因儒家在漢朝以後成了中國文化界的主流,無論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還是於世界的知名度,都遠在道、佛家之上。若按此六大淵源流派對氣功的依賴程度和對氣功的認識水平排列,又以“道、佛、儒、醫、武、民間”為適。本書的排列順序對此的排列順序,選定為“儒、道、佛、醫、武、民間”。
各大家對氣功這個實踐方法,一直以來都有各自的稱謂:道家自言煉丹、服氣、吐納、坐忘等,認為這是得道成仙之必須方法;佛家認為這是觀想、禪定、見性,是成佛的唯一通途;儒家喜稱守中、誠意、正心、養性等,將其視為修身、治學的基本功夫;醫家謂之導引、內視,譽其為直達上乘醫道的捷徑;武術家視“站樁煉氣”為“武練”之道、“靜坐養心”為“文修”之境,認為練氣養心,既是入門基本功課,也是提高武技的精要秘術。
古典氣功的方方面面,將在我們今天認識氣功這個文化形式時,有不可多得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