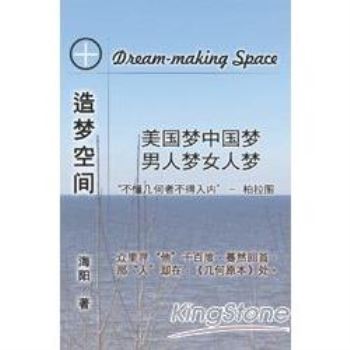世界上有數不勝數的路,有無窮無盡的路,但它們全部加起來,都沒有一條路長。這條路就是“Sea to Sky”:一條從大海通到天空的路。這也是一條人類從初始到未來的路,一條文化路,一條從“模擬”到“虛擬”的思想路。
大海與天空,只一線之隔,這麼近,又那麼遠。它們朝夕相處,卻無法跨越。大海還是大海,天空就是天空。海裡的魚兒,空中的鳥兒,它們時時相望,也常常相親,但魚兒始終在海裡,鳥兒永遠在天空:總是有一條無可超越的界線。
只有人,能夠超越這大海與天空的界限,從大海走向天空。
在這條路上,人類的文化以水的三種不同形式進行著,或液體,或固體,或氣體。
世界本是無色,象水一樣,
世界本是透明的,象冰一樣,
世界本是看不見的,象氣一樣。
不管是無色的水,還是透明的冰,或是看不見的氣,都是由H2O組成的。H2O的三種狀態(液態,固體,氣態),在大海與天空之間循環往復,周而復始。不管是哪種形態,怎樣不同的形象或外觀,各種的特性,特徵和特色,它們的基本元素都是H2O。
生命源于水,歸於天。人,陸地上的生命,行走在大海與天空之間,形形色色,千姿百態,就變成了人類的文化路。
這本書的第0卷就是關於這樣一條路。在這路上,一個“石頭人”,看著“一幅畫”,哼著“一首詩”,唱著 “一支歌”,頭仰望著一個“天符”,心裡裝著一個“心符”,腳上踩著一個“地符”,找著 “一條路”,從大海走向天空。
這一個“石頭人”是溫哥華英格列海灣的“Inukshuk”—“想像中的人”,“引路人”。
這“一幅畫”是“海天一色”,溫哥華英格列海灣的一景。
這“一首詩”是美國詩人艾蜜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1830年12月10日-1886年5月15日)的一首詩其中的三句:
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 (智慧比天空還廣寬)
The Brian is deeper than the sea (智慧比大海還深浩)
The Brain is just the weight of God (智慧的分量正好與上帝一樣)
這“一支歌”是美國歌星Richard Mars(理查.馬思)八十年代末自創自唱的一首經典歌曲“Right here Waiting”(此情可待):
Ocean apart day after day (天海相隔,日復一日)…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waiting for you(我始終在此等候著你,等候著你 …)。
這“一條路”是從溫哥華到滑雪勝地威士拿的高速公路“Sea to Sky Hwy”( 海至天大道)。
這“一個符”是 “太陽十字元”。
讓我帶著你一起來走一走這一條神奇的“海至天大道”。
===
第0章 海市蜃樓(序幕)
萬里尋“夢”千百度,驀然回首,那“夢”卻在,“大海天空”處。
2010年4月22日,是世界的地球日,也是我登陸加拿大溫哥華這片土地的20周年。這是一個風和日麗,春光明媚的傍晚。我騎著自行車,獨自來到溫哥華英格列海灣。
在這海灣,有的人在散步有的人在跑步,有的人在騎自行車有的人在滑旱冰,有的人在滑風帆有的人在開遊艇,有的人在看日落有的人在吹海風。在這無數的人群中,有一位高大偉岸的人屹立在這海灣旁,一動不動地望著大海的遠方,幾十年如一日,無論風和日麗還是強風暴雪,無論黑夜還是白天。他就是“Inukshuk”,一個“石頭人”。當你走進荒無人煙的深山野林裡,當你來到一望無際的雪原上,看到這樣的“石頭人”,你一定明白曾經有人“到此一站”或“到此一遊”。他就是“想像中的人”,因約特語“Inukshuk”的意思。這“想像中的人”正是加拿大北部地域最原始的人文之一。他告訴經過的路人,已經有人來過這裡了,放心走吧
站在海灣的陸地上,我看到了這樣一幅風景畫:一輪紅日徐徐越過那水平線,沉向海裡。當半個紅日消失後,我無意識地看了一下時間:下午六點正(夏令時間)。在太平洋另一邊的中國,此時應是早上的九點正,太陽升起的時候。確實,東方太陽升起的時候,正是西方太陽落下的時候。
天空中的太陽終於鑽進了海裡,留下一片霞光。陸地上的“石頭人”一如既往地站立在那裡,頭頂藍天,遠望碧海,在霞光裡閃閃發亮。
(生態環境)從宏觀來看,陸地,天空,和大海正是世界的三大背景,人類生存的三大世界。從微觀來看,土地、空氣、和清水是世界的三大基本元素,人類生存的三大前提,也是人類的“近身物”,屬於每一個人,養育每一個人。然而還有一樣離我們遠遠的,我們卻又離不開的東西,那就是剛剛落下的太陽。它除了給我們光和熱,還時刻關照著我們,溫暖著我們。人類得以生存,完全依靠水,土,氣和陽光,這是一個3+1的世界真正主宰這個世界的,並非我們的“近身物”,而是遠離我們的太陽。這個巨大的火球,離我們不能遠一厘,也不可近一分。這樣的力度與溫度才恰恰好。它是地球公轉的中心,它是我們“近身物”的支配者和調度者。
古代的哲人與智者,把它們概括為世界的“四大基本元素”,古希臘哲人認為天下萬物皆由“土、水、氣、火”四大基本元素構成。古印度智者則認為構成物質的基礎是 “地、水、火、風”。在中國的智者也認為世界都是由“天、地、水、火”組成,雖然在用字上略有出入,它們其實說著相同的東西。古希臘的“氣”,古印度的“風”和古中國的“天”,都是相對應的。而且,古印度與古中國的“地”與古希臘的“土”,指的都是同一樣東西。生存在不同地域的人們對世界有共同的認知。
“石頭人”站立在陸地上,一個“想像中的人”,是我們的“指路的人”。沿著他的視線,遠處,天海一線;在這之間,隱隱約約朦朦朧朧中,從左至右,連綿起伏的山影裡是一條從大海到天空的路,它就是 “海天公路(Sea to Sky Hwy)”。20年前,我遇上了這條路。
走進楓國
一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我經過中國對外開放的“視窗”-- 深圳羅湖口岸到達中國的進出“港口”香港。重重的大霧下終於漸漸地散去了一點,停飛了一天的飛機終於在有限度的條件下起飛了。我帶著既激動、興奮,又迷茫、焦急的心情登上了去加拿大的飛機,開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路程。
這還是我第一次乘飛機,也是第一次在高空俯瞰地球,這個海洋與陸地的世界。飛機從東方之珠香港起飛,穿雲拔霧,跨越太平洋,進入加國的領空。從飛機上眺望這片北美的土地,我第一眼看到飛機窗框視野內的加拿大,下半邊是一片蔚藍色的汪洋大海,上半邊是一片綠油油的陸地。在大海與陸地交迭處,海浪輕輕地拍打著海岸,一進一退,一退一進,不停地重複著,交替著。這麼說,我正在跨越的是大海與陸地的交織區。如果藍色大海的一邊表示浩大深澳而神秘的東方世界,綠色陸地的一邊表示一望無遺而透明的西方世界,那麼這一刻,我正在從東方世界跨越到西方世界。
(路在何方)飛機開始慢慢降落,離地面越來越近,我的目的地溫哥華的景象已漸漸顯現在眼簾; 一條條的馬路和一點點的建築物開始從綠樹叢中走了出來。飛機輕輕接觸到地面的那一瞬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已登陸在這北美大陸。四百多年前哥倫比歷史性地發現的新大陸,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與中國幾千年悠久歷史相比,四百多年的時間已令這塊原始的土地變成現代文明社會。是什麼“靈丹妙藥”有這麼大的效力?
飛機跑道兩旁是綠油油、整齊齊的草地。那個年代,中國正奔向工業化,城市化,到處都在大動土木,大建工廠,大建高樓大廈。所以,我真還沒有看到過這麼大一片整齊的草地,也沒有想像過一大片的草地給人的感覺會是那樣的寧靜與平和(綠色的波長是可見光的中間)。這種感覺頓時令我喜歡上了這片平坦的草地,也喜歡上了這片廣闊的土地。原來喜歡一樣東西就這樣的簡單。
(國家概念)飛機在跑道上減速跑,我的心卻在加速跳,我的心情也因而加速地興奮著。雖然我已登陸了並且喜歡上了這片土地,然而我還沒有真正進入這個西方的國家:經過了加拿大海關,我才算進入這個國家。四百多年前哥倫比亞與他的探索者就無需經過這一“關”:那時這裡還沒有國家的概念,只有新大陸之說。
(心態與心境)飛機停定了,我的心也停定了下來。我既沒有抱著太多的眷戀離開故鄉,也沒有抱著太大的抱負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我有的只是一顆平常的心、平靜的心、平凡的心:中國雖大,但人生有限。我要在有生之年,到這個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年輕西方國家走一走,看一看,游一遊。
(大背景)入關很順利。我輕鬆地走出機場,一下子似乎走進了大自然的懷抱:頭頂著是蔚藍色的天空,呼吸著的是還帶著綠草味的清新空氣,遙望著的是遠處一排雪峰連綿的群山,周圍更是綠油油的草地和鬱鬱蔥蔥的樹木。這是一個以藍色和綠色為基調的自然世界,其他的顏色只是點綴而以。我感覺這個世界突然變得簡單了,變得寬廣了:只有綠地和藍天,任你跑,任你飛。
(視覺的路:顏色與視野)我的親戚來機場接我,然後驅車直奔我在溫哥華臨時的家。第一眼所看到那灰黑黑的“瀝青(混凝土)路”讓我想起了中國70年代的“柏油路”和當時正在大興土木修建中灰白白的“水泥路”。在我的概念裡,當然是灰白白的“水泥路”比灰黑黑的“瀝青路”好看又好用。一條又寬又直又平的馬路隨著我眼光漸漸地變窄,到盡頭處聚成一點。這是路的盡頭嗎?在這新的國度,我頓覺前路茫茫。然而,當車一直往前開,路也以車的速度往後移,路的盡頭也一樣地往後移,似乎根本沒有路的盡頭;路總是往前方推進,消失在遠方。
過了橋就是溫哥華市。一路上,所見到的樹木都不認識。南方的風情是榕樹,是梆樹。這裡是北國的風光。在南方長大的我,覺得這北國風光格外清新。我不僅從東方世界來到西方世界,也是從南方的土域來到北方的疆土。
真正令我驚喜和意外的,是一路上很多街道兩旁的樹都開著粉紅色的花。我從來沒見過這種會開花的樹,經親戚的介紹,才知道這是櫻花樹。接著,他向我介紹了溫哥華櫻花樹的由來和櫻花樹春夏交替時花開花落的過程和情景。
(生命的兩個階段)原來櫻花樹在春天到來的時候,首先是小小的花蕾冒出樹枝,然後花蕾開花,花瓣飄謝。花謝之時,也是綠茵冒出來之時。這才是春天的過去,夏天的開始。花開與花謝,此乃為綠葉誕生的前奏曲,花謝是迎接綠葉的來臨。這花落與綠葉交替之瞬間,不正是懷胎十月之後誕生那一刻?生命誕生之時,確是如此:花謝之時,也是生命誕生之時。這是生命兩個階段的交替期,是從“胎兒”到“嬰兒”的交替期。
春天是孕育生命的季節,就象母親肚裡的十月懷胎,花謝時才迎來了人生的開始。夏天是生命的另一季節,是從母親的胎盤裡水的環境來到大自然裡太陽照耀下有自由空氣的陸地環境。這是生命的兩個階段,前期的陰性生態環境與後期的陽性生態環境。
在這春天裡,我完全陶醉在櫻花的路上。
大海與天空,只一線之隔,這麼近,又那麼遠。它們朝夕相處,卻無法跨越。大海還是大海,天空就是天空。海裡的魚兒,空中的鳥兒,它們時時相望,也常常相親,但魚兒始終在海裡,鳥兒永遠在天空:總是有一條無可超越的界線。
只有人,能夠超越這大海與天空的界限,從大海走向天空。
在這條路上,人類的文化以水的三種不同形式進行著,或液體,或固體,或氣體。
世界本是無色,象水一樣,
世界本是透明的,象冰一樣,
世界本是看不見的,象氣一樣。
不管是無色的水,還是透明的冰,或是看不見的氣,都是由H2O組成的。H2O的三種狀態(液態,固體,氣態),在大海與天空之間循環往復,周而復始。不管是哪種形態,怎樣不同的形象或外觀,各種的特性,特徵和特色,它們的基本元素都是H2O。
生命源于水,歸於天。人,陸地上的生命,行走在大海與天空之間,形形色色,千姿百態,就變成了人類的文化路。
這本書的第0卷就是關於這樣一條路。在這路上,一個“石頭人”,看著“一幅畫”,哼著“一首詩”,唱著 “一支歌”,頭仰望著一個“天符”,心裡裝著一個“心符”,腳上踩著一個“地符”,找著 “一條路”,從大海走向天空。
這一個“石頭人”是溫哥華英格列海灣的“Inukshuk”—“想像中的人”,“引路人”。
這“一幅畫”是“海天一色”,溫哥華英格列海灣的一景。
這“一首詩”是美國詩人艾蜜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1830年12月10日-1886年5月15日)的一首詩其中的三句:
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 (智慧比天空還廣寬)
The Brian is deeper than the sea (智慧比大海還深浩)
The Brain is just the weight of God (智慧的分量正好與上帝一樣)
這“一支歌”是美國歌星Richard Mars(理查.馬思)八十年代末自創自唱的一首經典歌曲“Right here Waiting”(此情可待):
Ocean apart day after day (天海相隔,日復一日)…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waiting for you(我始終在此等候著你,等候著你 …)。
這“一條路”是從溫哥華到滑雪勝地威士拿的高速公路“Sea to Sky Hwy”( 海至天大道)。
這“一個符”是 “太陽十字元”。
讓我帶著你一起來走一走這一條神奇的“海至天大道”。
===
第0章 海市蜃樓(序幕)
萬里尋“夢”千百度,驀然回首,那“夢”卻在,“大海天空”處。
2010年4月22日,是世界的地球日,也是我登陸加拿大溫哥華這片土地的20周年。這是一個風和日麗,春光明媚的傍晚。我騎著自行車,獨自來到溫哥華英格列海灣。
在這海灣,有的人在散步有的人在跑步,有的人在騎自行車有的人在滑旱冰,有的人在滑風帆有的人在開遊艇,有的人在看日落有的人在吹海風。在這無數的人群中,有一位高大偉岸的人屹立在這海灣旁,一動不動地望著大海的遠方,幾十年如一日,無論風和日麗還是強風暴雪,無論黑夜還是白天。他就是“Inukshuk”,一個“石頭人”。當你走進荒無人煙的深山野林裡,當你來到一望無際的雪原上,看到這樣的“石頭人”,你一定明白曾經有人“到此一站”或“到此一遊”。他就是“想像中的人”,因約特語“Inukshuk”的意思。這“想像中的人”正是加拿大北部地域最原始的人文之一。他告訴經過的路人,已經有人來過這裡了,放心走吧
站在海灣的陸地上,我看到了這樣一幅風景畫:一輪紅日徐徐越過那水平線,沉向海裡。當半個紅日消失後,我無意識地看了一下時間:下午六點正(夏令時間)。在太平洋另一邊的中國,此時應是早上的九點正,太陽升起的時候。確實,東方太陽升起的時候,正是西方太陽落下的時候。
天空中的太陽終於鑽進了海裡,留下一片霞光。陸地上的“石頭人”一如既往地站立在那裡,頭頂藍天,遠望碧海,在霞光裡閃閃發亮。
(生態環境)從宏觀來看,陸地,天空,和大海正是世界的三大背景,人類生存的三大世界。從微觀來看,土地、空氣、和清水是世界的三大基本元素,人類生存的三大前提,也是人類的“近身物”,屬於每一個人,養育每一個人。然而還有一樣離我們遠遠的,我們卻又離不開的東西,那就是剛剛落下的太陽。它除了給我們光和熱,還時刻關照著我們,溫暖著我們。人類得以生存,完全依靠水,土,氣和陽光,這是一個3+1的世界真正主宰這個世界的,並非我們的“近身物”,而是遠離我們的太陽。這個巨大的火球,離我們不能遠一厘,也不可近一分。這樣的力度與溫度才恰恰好。它是地球公轉的中心,它是我們“近身物”的支配者和調度者。
古代的哲人與智者,把它們概括為世界的“四大基本元素”,古希臘哲人認為天下萬物皆由“土、水、氣、火”四大基本元素構成。古印度智者則認為構成物質的基礎是 “地、水、火、風”。在中國的智者也認為世界都是由“天、地、水、火”組成,雖然在用字上略有出入,它們其實說著相同的東西。古希臘的“氣”,古印度的“風”和古中國的“天”,都是相對應的。而且,古印度與古中國的“地”與古希臘的“土”,指的都是同一樣東西。生存在不同地域的人們對世界有共同的認知。
“石頭人”站立在陸地上,一個“想像中的人”,是我們的“指路的人”。沿著他的視線,遠處,天海一線;在這之間,隱隱約約朦朦朧朧中,從左至右,連綿起伏的山影裡是一條從大海到天空的路,它就是 “海天公路(Sea to Sky Hwy)”。20年前,我遇上了這條路。
走進楓國
一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我經過中國對外開放的“視窗”-- 深圳羅湖口岸到達中國的進出“港口”香港。重重的大霧下終於漸漸地散去了一點,停飛了一天的飛機終於在有限度的條件下起飛了。我帶著既激動、興奮,又迷茫、焦急的心情登上了去加拿大的飛機,開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路程。
這還是我第一次乘飛機,也是第一次在高空俯瞰地球,這個海洋與陸地的世界。飛機從東方之珠香港起飛,穿雲拔霧,跨越太平洋,進入加國的領空。從飛機上眺望這片北美的土地,我第一眼看到飛機窗框視野內的加拿大,下半邊是一片蔚藍色的汪洋大海,上半邊是一片綠油油的陸地。在大海與陸地交迭處,海浪輕輕地拍打著海岸,一進一退,一退一進,不停地重複著,交替著。這麼說,我正在跨越的是大海與陸地的交織區。如果藍色大海的一邊表示浩大深澳而神秘的東方世界,綠色陸地的一邊表示一望無遺而透明的西方世界,那麼這一刻,我正在從東方世界跨越到西方世界。
(路在何方)飛機開始慢慢降落,離地面越來越近,我的目的地溫哥華的景象已漸漸顯現在眼簾; 一條條的馬路和一點點的建築物開始從綠樹叢中走了出來。飛機輕輕接觸到地面的那一瞬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已登陸在這北美大陸。四百多年前哥倫比歷史性地發現的新大陸,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與中國幾千年悠久歷史相比,四百多年的時間已令這塊原始的土地變成現代文明社會。是什麼“靈丹妙藥”有這麼大的效力?
飛機跑道兩旁是綠油油、整齊齊的草地。那個年代,中國正奔向工業化,城市化,到處都在大動土木,大建工廠,大建高樓大廈。所以,我真還沒有看到過這麼大一片整齊的草地,也沒有想像過一大片的草地給人的感覺會是那樣的寧靜與平和(綠色的波長是可見光的中間)。這種感覺頓時令我喜歡上了這片平坦的草地,也喜歡上了這片廣闊的土地。原來喜歡一樣東西就這樣的簡單。
(國家概念)飛機在跑道上減速跑,我的心卻在加速跳,我的心情也因而加速地興奮著。雖然我已登陸了並且喜歡上了這片土地,然而我還沒有真正進入這個西方的國家:經過了加拿大海關,我才算進入這個國家。四百多年前哥倫比亞與他的探索者就無需經過這一“關”:那時這裡還沒有國家的概念,只有新大陸之說。
(心態與心境)飛機停定了,我的心也停定了下來。我既沒有抱著太多的眷戀離開故鄉,也沒有抱著太大的抱負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我有的只是一顆平常的心、平靜的心、平凡的心:中國雖大,但人生有限。我要在有生之年,到這個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年輕西方國家走一走,看一看,游一遊。
(大背景)入關很順利。我輕鬆地走出機場,一下子似乎走進了大自然的懷抱:頭頂著是蔚藍色的天空,呼吸著的是還帶著綠草味的清新空氣,遙望著的是遠處一排雪峰連綿的群山,周圍更是綠油油的草地和鬱鬱蔥蔥的樹木。這是一個以藍色和綠色為基調的自然世界,其他的顏色只是點綴而以。我感覺這個世界突然變得簡單了,變得寬廣了:只有綠地和藍天,任你跑,任你飛。
(視覺的路:顏色與視野)我的親戚來機場接我,然後驅車直奔我在溫哥華臨時的家。第一眼所看到那灰黑黑的“瀝青(混凝土)路”讓我想起了中國70年代的“柏油路”和當時正在大興土木修建中灰白白的“水泥路”。在我的概念裡,當然是灰白白的“水泥路”比灰黑黑的“瀝青路”好看又好用。一條又寬又直又平的馬路隨著我眼光漸漸地變窄,到盡頭處聚成一點。這是路的盡頭嗎?在這新的國度,我頓覺前路茫茫。然而,當車一直往前開,路也以車的速度往後移,路的盡頭也一樣地往後移,似乎根本沒有路的盡頭;路總是往前方推進,消失在遠方。
過了橋就是溫哥華市。一路上,所見到的樹木都不認識。南方的風情是榕樹,是梆樹。這裡是北國的風光。在南方長大的我,覺得這北國風光格外清新。我不僅從東方世界來到西方世界,也是從南方的土域來到北方的疆土。
真正令我驚喜和意外的,是一路上很多街道兩旁的樹都開著粉紅色的花。我從來沒見過這種會開花的樹,經親戚的介紹,才知道這是櫻花樹。接著,他向我介紹了溫哥華櫻花樹的由來和櫻花樹春夏交替時花開花落的過程和情景。
(生命的兩個階段)原來櫻花樹在春天到來的時候,首先是小小的花蕾冒出樹枝,然後花蕾開花,花瓣飄謝。花謝之時,也是綠茵冒出來之時。這才是春天的過去,夏天的開始。花開與花謝,此乃為綠葉誕生的前奏曲,花謝是迎接綠葉的來臨。這花落與綠葉交替之瞬間,不正是懷胎十月之後誕生那一刻?生命誕生之時,確是如此:花謝之時,也是生命誕生之時。這是生命兩個階段的交替期,是從“胎兒”到“嬰兒”的交替期。
春天是孕育生命的季節,就象母親肚裡的十月懷胎,花謝時才迎來了人生的開始。夏天是生命的另一季節,是從母親的胎盤裡水的環境來到大自然裡太陽照耀下有自由空氣的陸地環境。這是生命的兩個階段,前期的陰性生態環境與後期的陽性生態環境。
在這春天裡,我完全陶醉在櫻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