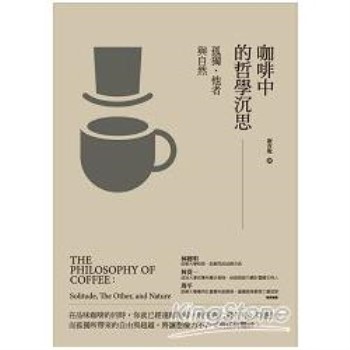●〈孤獨的各種面貌〉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品味孤獨吧!
首先就先來談談什麼是孤獨?根據科克的定義,孤獨是一種持續若干時間、沒有別人涉入的意識狀態。有了這個核心的特徵,孤獨的其他特徵也就跟著源源而出了:單獨一個人、具有反省心態、擁有自由、擁有寧靜、擁有特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等等。看來,孤獨不僅惠贈了人們休息與恢復的好處,它也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時間感與空間感,讓人在這裡得以癒合那些在社會與人群中所扯裂的傷口。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經驗,恐怕非得親身經歷孤獨經驗的人,不能深刻地描繪出在孤獨情境下的身心狀態。說到孤獨的體驗,還有比梭羅(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在《湖濱散記》(Walden)裡描寫的來得更為傳神的嗎?該書〈孤獨〉一章中,他開頭就如此寫道:
這是一個恬靜的黃昏,我全身的感官渾然為一,難以名狀的歡欣浸潤了每一個毛孔。我以一種奇怪的自由在自然中來去自如,彷彿成了她的一部分。
我穿著襯衫,沿多石子的湖岸信步而行,儘管天有點涼,雲多,風也多,而且也沒有甚麼特別吸引我的事物,但我卻感到大自然的種種,跟我異乎尋常的投契。牛蛙呱呱鳴唱,邀人前來欣賞夜色,夜鷹的梟叫聲也被風從水面上吹送了過來。我神移於赤楊和白楊的款款擺動中,幾乎喘不過氣來;然而,我的心情卻像湖面一樣,波而不亂。被晚風吹起的陣陣小水波,雖然使湖面不能保持平靜如鏡,卻還算不上是波濤洶湧。
梭羅在華爾騰湖(WaldenPond)的獨居生活中,並沒有用華麗的詞藻來誇大他的生活哲學或體驗,相反地,他用一種奇特的平凡觀點,忠實記載了他在華爾騰湖的一點一滴,娓娓道來在一片寧靜平凡的大自然裡,他內心如何湧起一陣波而不亂的心境。這樣的體會,我也曾經有過。記得有一次,我從電梯走出來,依往常的習慣,快步走向教室大樓準備上課。望著熙來攘往的學生,我也早已習慣了,只是當天的人潮似乎比平常為多。於是我避開了穿堂,轉向教室大樓的中庭走去。這是一處四面環繞建築物的方形中庭,其中綴以幾許熱鬧的綠色植物,小小的綠地偶而也會間歇灑水,為這中庭帶來不少生氣。平時裡,我很少走過這裡,倒是常在下課休息時間,從教室或研究室的大落地窗,遠眺這個靜中帶鬧卻又鬧中有靜的中庭。今日不經意走過,只覺豔陽高照,炙膚生疼。無怪乎平日裡很少有人駐足在這中庭,往來的學生雖多,但總是匆匆走過。不過,就在我行經這一小片綠地時,我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奇妙的感應,似乎有什麼力量,讓我停下腳步。站在一叢茂盛的低矮灌木旁,一陣微風拂來,輕輕地流轉在我四周的空氣裡,似乎使陽光也不再那麼刺眼了。我抬頭望向天際,只見湛藍的一片天空,被這四面環繞的教室大樓,構築在一個四方形的輪廓裡,其中沒有一絲白雲,也沒有一隻飛鳥,就只是純靜的四方形藍色天空,就像一張淡藍色的正方形色紙一般,端端正正地平放在我的頭上。這景象讓我進入了渾然忘我的時空裡,眼前的一切顯得緩慢而平靜,所有的感覺與動作似乎都在時間的流動中停格。我不知道我究竟這樣在中庭裡站了多久,等到在意識裡隱約聽到鐘聲響起,這才喚回我悠遊的思緒與心靈,於是我收回遠眺的目光,重新跨步向教室走去,結束這段秋日午后的奇妙境遇。
這是一次有趣的經驗。從此以後,每當閒暇下來,我都會從研究室的落地窗凝望這片曾經令我目眩神迷的藍天與綠地,而且更有幾次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我竟又重現了那樣的心境與感受。這時的我不再像那次一樣陷入混沌的迷離狀態,而是更能深入自我的內心裡,觀察自己在心境上的各種微小變化──似乎有另外一個「我」正在觀察這個進入迷離狀態的我,於是「我」看到了我站在落地窗前,視線越過窗戶玻璃,望向園中那些隨風搖曳的灌木和枝木上尚未掉落的泛紅秋葉,雖然中庭裡仍有學生走動著,但四周一片安靜,聽不到任何的聲響,「我」任由這片靜謐包圍和穿透我,那些繁忙的日常生活、那些人們對我的目光(不論是出自關懷或是怨懟)、那些縈繞在心裡的未來計畫、……所有一切的細節,都逐漸在隱退,隱退至我意識範圍的底層,就像相機的焦距逐漸模糊一般,此時的「我」清楚感覺得到自己正在沉靜下來。
這樣的經驗,算得上是一種奇怪的時間體驗,大概就是哲學家口中常說的「主觀時間」吧!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就認為,主觀的時間──由主體所感知的時間──與客觀時間的根本分野之一是:它會緜延(endure)。因此他說道:
毫無疑問,我們的時間感最初來自內在經驗的連續性。那是怎樣的一種連續性?這種連續性類似一道流,但卻是一道自足的流,不牽涉任何的流動體。出現在這道流之中的任何物,都是對流的一種人為性的打擾;這道流,恰如其分地去體驗它的話,無非就是純粹的緜延。……當我們閉起眼睛,全神貫注地傾聽一段旋律的時候,那種體驗極端接近我們對內在時間之流的經驗。
這種內在的主觀時間,像極了孤獨時的深刻感受,無怪乎當我們翻閱所有歌頌孤獨的文章典籍時,就會發現它們何其喜歡強調孤獨有它自成一格的時間模式。很明顯地,孤獨與主觀時間幾乎完全被連結在一起。這是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他所身處的社會中,而這個社會常常要求我們去配合別人的時間,當一個場合裡涉及的人數愈多,個體所被要求的配合度就愈大,以至於不得不以一個客觀的外在時間作為共同的基準。但是,只有在孤獨中,在人與人不發生任何交涉的情況下,個人的主觀時間才有可能完全的自由揮灑。就像梭羅在華爾騰湖畔所描述的時間觀:
有時,夏天的清晨,經過我習以為常的沐浴後,我會坐到陽光明暢的門口,從日出到中午,忘我地在遐想中、在松樹與山胡桃與漆樹之中、在未經騷擾的孤獨和寂靜之中,鳥在周圍鳴唱,或無聲的穿屋飛過。一直到太陽從西邊的窗子落進來,或遠處公路上傳來篷車的轆轆聲,我才會覺察到時間的過去。
這樣的主觀時間與一般人所理解的客觀時間有很大的不同。但問題是:真存在有客觀時間嗎?當人們不再透過孤獨來彰顯個別獨特的內在時間之後,真的有一個完全客觀的外在時間是可以作為所有人的共同時間基準嗎?於是,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何謂時間?
●〈雨中的咖啡館〉
那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夏日午后,陽光從落地窗灑進我的研究室內,從樹梢之間的閃動,投映入我的眼簾,使我原本注視書本的雙眼為之一亮,望向窗外的陽光與婆娑的樹影,從林間跳躍的小鳥與隨風而起舞的樹葉中,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並深深地為這分美感所震懾。閉上雙眼,靜靜地聆聽風與樹之間的對話,一時間,從心靈深處突然泛起陣陣的悸動與波瀾,久久不能自已。就在我想著「索性放下手邊的書本,盡情地享受這夏日午后的陽光」的時候,窗外卻傳來「滴答!滴答!」的聲響,讓我再度張開雙眼,原來是一陣突如其來的雨勢滴落陣陣的雨水在窗臺上。
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午后啊!適才還陽光遍灑滿地,搖曳的樹影風姿還讓我驚嘆不已,可是就這麼一轉眼間,怎麼就下起雨來了?抬頭望著遠處飄來的一片烏雲,使陽光羞怯地隱蔽在雲後,恰巧這時收音機傳來蕭邦的〈雨滴〉,更增此情此景的淒美之感。昏暗的天空映著墨綠的樹影,隨著雨聲、鋼琴聲的唱和,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那股想飛的衝動,輕輕帶上研究室的門,驅車悠遊在這大片田園的雨中。在大雨滂沱中,駕車行經一家位於田園中的咖啡館,在一大片田園中,沒有其他住家與店面,就只有她佇立在這雨中的田園裡。雖然車外大雨不斷,但是這樣的一家店與那一片碧綠的背景,仍深深地吸引著我。
終於,我還是停下車子,在傾盆如瀉的大雨中,匆匆地衝進了這家咖啡館。「歡迎光臨」的語聲幾被門外滂沱的雨聲所掩蓋,而我就像是一隻落水狗般,站在門邊抖落一身的雨水。選了靠窗的座位,靜靜地觀賞著店主用熟練的手法,從秤豆、研磨、到煮水,一切都顯得是那麼從容不迫。看著沸騰的水從Siphon的下壺逐漸上升,慢慢地浸滿濾器中的咖啡粉,攪拌幾下,等待計時鈴響,快速地移走酒精燈,用毛巾擦拭下壺,使那完全萃取出咖啡原味的汁液,從上壺中回流至下壺。觀賞整個煮咖啡的過程,真是品嚐咖啡之前的另一種享受。只見店主端起這剛煮好的咖啡走來,我用一種近乎虔敬的心接過這杯咖啡。現在,這杯咖啡就在我眼前,但我並不急著喝它,因為我知道此刻它的溫度還不適合飲用。過高的溫度只會使我的味覺遲鈍,我必須等待,等待那絕佳的飲用時機。但是,這並不代表我也必須枯坐無聊,在這等待的時光中,那陣陣若有似無的香氣,其實已然足夠彌補這短暫的等待過程。因為這濃厚無比的香氣正深入我的肺葉中,與我整個身心融於一體。說真的,喝咖啡的過程中,此刻才是最幸福的時刻,那沉鬱飽滿的咖啡香氣進入五臟六腑的心靈充實感,莫可言喻。終於,我端起了杯子,輕輕地啜著一口苦苦甘甘的咖啡汁液,只覺滿嘴的厚實感,再啜一口,汁液流經喉嚨、穿過食道、直達胃壁,這分滿足感一直是我那些不喝咖啡的朋友們所無法領略的。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間,我才意識到我身處何地,於是抬頭望向窗外的大雨,這才醒悟過來,適才那幾分鐘的時光裡,我竟完全忘了那一度讓我倉皇逃難的大雨。再喝一口咖啡,我不禁笑了起來,在這雨中的咖啡館。顯然,在喝咖啡的過程中,我可以感覺到一種「雙重性」。如同梭羅所說的:
我可以感覺到一種雙重性,由於這種雙重性,我可以站得離自己遠遠的,像跟別人的關係一樣。我的經驗不論何等強烈,我都可以感到有另一部分的我在場,並感到它的評論;這一部分的我,可以說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一個旁觀者,只是觀察記錄我的經驗,卻不分享我的經驗;說它是我也可以,說它是你也可以。
在咖啡的品嚐中開放所有感官知覺,得以開放自我的心靈,如此才能品味咖啡真正的味道:亦即主體性的消解,解放禁錮的心靈,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才能聽到平時聽不到的聲音。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常常有一種特殊的境遇:有時當全班正在熱烈地討論某一個議題時,雖然我仍身處講臺上,並且用心地聆聽每一位同學的意見,甚至還能加以講評,但是我卻常會有一種奇特的心理變化,就好像我的心靈跳脫出身體,懸浮在教室上空一般,俯視著全班同學及那個正在講臺上努力教學的我,構成一幅頗令我玩味的畫面。
就是這種「雙重性」,讓我體悟到在孤獨與非孤獨之間,其實是存在著一些中間的灰色地帶,我們至少可以將這個中間灰色地帶區分為兩種不同的狀態,即「涉入的不涉入」(engageddisengagement)與「不涉入的涉入」(disengagedengagement)。假設以全然的非孤獨(即「完全的涉入」,pureengagement)與全然的孤獨(即「完全的不涉入」,puredisengagement)作為光譜軸的兩端,那麼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著「涉入的不涉入」與「不涉入的涉入」這兩種中間地帶。
後者係緊臨「完全的不涉入」一端的「不涉入的涉入」,即在完全的孤獨中又保有部份的他者存在的可能性,這是因為雖然孤獨是一種知覺、思想、感情和行動上的不涉入狀態,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樣的不涉入狀態,仍會有一些間接或替代性的他者涉入,常見的「睹物思人」或「擬人化」就是從物而指涉至人的情形。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就經常把自然事物擬人化:
我從未有過像孤獨這樣好的良伴……
……在自然界的事中你可以找到最甜美、最溫柔、最純潔,也最令人鼓舞的社會關係……
我突然明悟到在自然界中含有甜潤的、有益身心的社會關係,就在雨聲的滴答中,就在那環繞我房子的每個聲音、每個景象中,一種無限的、無量的友善遽時像一種空氣一樣支持住我……
它是那樣清楚地讓我察覺到,即使在我們通常稱之為荒野的陰沉的地方,也有一種與我那麼親近的東西在場;讓我察覺到,跟我血緣最近、最有著人性氣息的,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村民……
我並不比湖中笑得那麼響的潛鳥寂寞,不比湖本身寂寞。請問,這寂寞的湖又有什麼同伴呢?……我並不比草地上的單莖毛蕊花或蒲公英寂寞,不比一片葉子、一棵酢漿草或一隻馬蠅或蜜蜂寂寞。
顯然,孤獨者的意識在許多時候仍然會處於一種不自覺的涉入狀態。
不管是「涉入的不涉入」還是「不涉入的涉入」,其實都是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人類的意識狀態,極少是能夠完全的非孤獨或是完全的孤獨,每一個事件的凝視與關注總是免不了會被一層「底景」(containment)所圍繞,有時候是以其他的人、事、或物所構成的「底景」以突顯自我存在的樣貌,另一些時候則可能是以自身作為「底景」以彰顯某些人、事、物的特殊意涵。因此,「底景」就像電影的背景音樂一樣,是一種我們雖然隱約意識到,卻不會去加以特別注意的事物。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對「底景」都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但是我們沒有把意識的鏡頭對焦在某些人、事、或物身上,並不代表它們就不在鏡頭之內,他們其實一直都在,只是在背景的位置上而已。這樣的「底景」是可以忽略、可有可無的背景而已嗎?不,根據完形心理學(GestaltPsychology)的看法,「底景」非但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相反地,它更是影響著我們對事物的認知的關鍵所在。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很喜歡使用音樂的例子來說明時間的連續性,我倒是覺得胡塞爾的音樂例子也頗能解釋「底景」的概念:旋律當然是由一個一個的音符組合而成的,但在聽音樂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剎那聽到所有的音符,而只能在每一剎那聽到一個音符;但如果我們一次只能聽到一個音符的話,我們又怎麼可能聽到需要由一個以上的音符所組成的旋律呢?答案就在於,音符雖然一個一個響起以後又一個一個消失,但它們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消失,而只是成為了意識的「底景」而已。沒有這個「底景」,我們所聽到的,只可能是一個一個的音符,而不可能是一段一段的旋律。
「底景」對人的影響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來舉一個我們生活中常見的例子說明。常常在許多重要的場合裡,我們總是能看到某些人在講述著他的一些事跡,彷彿他的生命中充滿了不平凡的經歷,連帶使得這個人也似乎跟著不平凡起來。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覺?雖然有時可能是這些人的自信,使他相信自己是不平凡的,因而他就真的不平凡起來了,不過,更多的時候,是當我們在相形見絀之下,相信這些人是不平凡的,因而突顯了他們的不平凡。此時的我們在無意中扮演了他人的「底景」,他們的不平凡是藉由我們的平凡而彰顯出來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品味孤獨吧!
首先就先來談談什麼是孤獨?根據科克的定義,孤獨是一種持續若干時間、沒有別人涉入的意識狀態。有了這個核心的特徵,孤獨的其他特徵也就跟著源源而出了:單獨一個人、具有反省心態、擁有自由、擁有寧靜、擁有特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等等。看來,孤獨不僅惠贈了人們休息與恢復的好處,它也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時間感與空間感,讓人在這裡得以癒合那些在社會與人群中所扯裂的傷口。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經驗,恐怕非得親身經歷孤獨經驗的人,不能深刻地描繪出在孤獨情境下的身心狀態。說到孤獨的體驗,還有比梭羅(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在《湖濱散記》(Walden)裡描寫的來得更為傳神的嗎?該書〈孤獨〉一章中,他開頭就如此寫道:
這是一個恬靜的黃昏,我全身的感官渾然為一,難以名狀的歡欣浸潤了每一個毛孔。我以一種奇怪的自由在自然中來去自如,彷彿成了她的一部分。
我穿著襯衫,沿多石子的湖岸信步而行,儘管天有點涼,雲多,風也多,而且也沒有甚麼特別吸引我的事物,但我卻感到大自然的種種,跟我異乎尋常的投契。牛蛙呱呱鳴唱,邀人前來欣賞夜色,夜鷹的梟叫聲也被風從水面上吹送了過來。我神移於赤楊和白楊的款款擺動中,幾乎喘不過氣來;然而,我的心情卻像湖面一樣,波而不亂。被晚風吹起的陣陣小水波,雖然使湖面不能保持平靜如鏡,卻還算不上是波濤洶湧。
梭羅在華爾騰湖(WaldenPond)的獨居生活中,並沒有用華麗的詞藻來誇大他的生活哲學或體驗,相反地,他用一種奇特的平凡觀點,忠實記載了他在華爾騰湖的一點一滴,娓娓道來在一片寧靜平凡的大自然裡,他內心如何湧起一陣波而不亂的心境。這樣的體會,我也曾經有過。記得有一次,我從電梯走出來,依往常的習慣,快步走向教室大樓準備上課。望著熙來攘往的學生,我也早已習慣了,只是當天的人潮似乎比平常為多。於是我避開了穿堂,轉向教室大樓的中庭走去。這是一處四面環繞建築物的方形中庭,其中綴以幾許熱鬧的綠色植物,小小的綠地偶而也會間歇灑水,為這中庭帶來不少生氣。平時裡,我很少走過這裡,倒是常在下課休息時間,從教室或研究室的大落地窗,遠眺這個靜中帶鬧卻又鬧中有靜的中庭。今日不經意走過,只覺豔陽高照,炙膚生疼。無怪乎平日裡很少有人駐足在這中庭,往來的學生雖多,但總是匆匆走過。不過,就在我行經這一小片綠地時,我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奇妙的感應,似乎有什麼力量,讓我停下腳步。站在一叢茂盛的低矮灌木旁,一陣微風拂來,輕輕地流轉在我四周的空氣裡,似乎使陽光也不再那麼刺眼了。我抬頭望向天際,只見湛藍的一片天空,被這四面環繞的教室大樓,構築在一個四方形的輪廓裡,其中沒有一絲白雲,也沒有一隻飛鳥,就只是純靜的四方形藍色天空,就像一張淡藍色的正方形色紙一般,端端正正地平放在我的頭上。這景象讓我進入了渾然忘我的時空裡,眼前的一切顯得緩慢而平靜,所有的感覺與動作似乎都在時間的流動中停格。我不知道我究竟這樣在中庭裡站了多久,等到在意識裡隱約聽到鐘聲響起,這才喚回我悠遊的思緒與心靈,於是我收回遠眺的目光,重新跨步向教室走去,結束這段秋日午后的奇妙境遇。
這是一次有趣的經驗。從此以後,每當閒暇下來,我都會從研究室的落地窗凝望這片曾經令我目眩神迷的藍天與綠地,而且更有幾次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我竟又重現了那樣的心境與感受。這時的我不再像那次一樣陷入混沌的迷離狀態,而是更能深入自我的內心裡,觀察自己在心境上的各種微小變化──似乎有另外一個「我」正在觀察這個進入迷離狀態的我,於是「我」看到了我站在落地窗前,視線越過窗戶玻璃,望向園中那些隨風搖曳的灌木和枝木上尚未掉落的泛紅秋葉,雖然中庭裡仍有學生走動著,但四周一片安靜,聽不到任何的聲響,「我」任由這片靜謐包圍和穿透我,那些繁忙的日常生活、那些人們對我的目光(不論是出自關懷或是怨懟)、那些縈繞在心裡的未來計畫、……所有一切的細節,都逐漸在隱退,隱退至我意識範圍的底層,就像相機的焦距逐漸模糊一般,此時的「我」清楚感覺得到自己正在沉靜下來。
這樣的經驗,算得上是一種奇怪的時間體驗,大概就是哲學家口中常說的「主觀時間」吧!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就認為,主觀的時間──由主體所感知的時間──與客觀時間的根本分野之一是:它會緜延(endure)。因此他說道:
毫無疑問,我們的時間感最初來自內在經驗的連續性。那是怎樣的一種連續性?這種連續性類似一道流,但卻是一道自足的流,不牽涉任何的流動體。出現在這道流之中的任何物,都是對流的一種人為性的打擾;這道流,恰如其分地去體驗它的話,無非就是純粹的緜延。……當我們閉起眼睛,全神貫注地傾聽一段旋律的時候,那種體驗極端接近我們對內在時間之流的經驗。
這種內在的主觀時間,像極了孤獨時的深刻感受,無怪乎當我們翻閱所有歌頌孤獨的文章典籍時,就會發現它們何其喜歡強調孤獨有它自成一格的時間模式。很明顯地,孤獨與主觀時間幾乎完全被連結在一起。這是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他所身處的社會中,而這個社會常常要求我們去配合別人的時間,當一個場合裡涉及的人數愈多,個體所被要求的配合度就愈大,以至於不得不以一個客觀的外在時間作為共同的基準。但是,只有在孤獨中,在人與人不發生任何交涉的情況下,個人的主觀時間才有可能完全的自由揮灑。就像梭羅在華爾騰湖畔所描述的時間觀:
有時,夏天的清晨,經過我習以為常的沐浴後,我會坐到陽光明暢的門口,從日出到中午,忘我地在遐想中、在松樹與山胡桃與漆樹之中、在未經騷擾的孤獨和寂靜之中,鳥在周圍鳴唱,或無聲的穿屋飛過。一直到太陽從西邊的窗子落進來,或遠處公路上傳來篷車的轆轆聲,我才會覺察到時間的過去。
這樣的主觀時間與一般人所理解的客觀時間有很大的不同。但問題是:真存在有客觀時間嗎?當人們不再透過孤獨來彰顯個別獨特的內在時間之後,真的有一個完全客觀的外在時間是可以作為所有人的共同時間基準嗎?於是,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何謂時間?
●〈雨中的咖啡館〉
那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夏日午后,陽光從落地窗灑進我的研究室內,從樹梢之間的閃動,投映入我的眼簾,使我原本注視書本的雙眼為之一亮,望向窗外的陽光與婆娑的樹影,從林間跳躍的小鳥與隨風而起舞的樹葉中,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並深深地為這分美感所震懾。閉上雙眼,靜靜地聆聽風與樹之間的對話,一時間,從心靈深處突然泛起陣陣的悸動與波瀾,久久不能自已。就在我想著「索性放下手邊的書本,盡情地享受這夏日午后的陽光」的時候,窗外卻傳來「滴答!滴答!」的聲響,讓我再度張開雙眼,原來是一陣突如其來的雨勢滴落陣陣的雨水在窗臺上。
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午后啊!適才還陽光遍灑滿地,搖曳的樹影風姿還讓我驚嘆不已,可是就這麼一轉眼間,怎麼就下起雨來了?抬頭望著遠處飄來的一片烏雲,使陽光羞怯地隱蔽在雲後,恰巧這時收音機傳來蕭邦的〈雨滴〉,更增此情此景的淒美之感。昏暗的天空映著墨綠的樹影,隨著雨聲、鋼琴聲的唱和,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那股想飛的衝動,輕輕帶上研究室的門,驅車悠遊在這大片田園的雨中。在大雨滂沱中,駕車行經一家位於田園中的咖啡館,在一大片田園中,沒有其他住家與店面,就只有她佇立在這雨中的田園裡。雖然車外大雨不斷,但是這樣的一家店與那一片碧綠的背景,仍深深地吸引著我。
終於,我還是停下車子,在傾盆如瀉的大雨中,匆匆地衝進了這家咖啡館。「歡迎光臨」的語聲幾被門外滂沱的雨聲所掩蓋,而我就像是一隻落水狗般,站在門邊抖落一身的雨水。選了靠窗的座位,靜靜地觀賞著店主用熟練的手法,從秤豆、研磨、到煮水,一切都顯得是那麼從容不迫。看著沸騰的水從Siphon的下壺逐漸上升,慢慢地浸滿濾器中的咖啡粉,攪拌幾下,等待計時鈴響,快速地移走酒精燈,用毛巾擦拭下壺,使那完全萃取出咖啡原味的汁液,從上壺中回流至下壺。觀賞整個煮咖啡的過程,真是品嚐咖啡之前的另一種享受。只見店主端起這剛煮好的咖啡走來,我用一種近乎虔敬的心接過這杯咖啡。現在,這杯咖啡就在我眼前,但我並不急著喝它,因為我知道此刻它的溫度還不適合飲用。過高的溫度只會使我的味覺遲鈍,我必須等待,等待那絕佳的飲用時機。但是,這並不代表我也必須枯坐無聊,在這等待的時光中,那陣陣若有似無的香氣,其實已然足夠彌補這短暫的等待過程。因為這濃厚無比的香氣正深入我的肺葉中,與我整個身心融於一體。說真的,喝咖啡的過程中,此刻才是最幸福的時刻,那沉鬱飽滿的咖啡香氣進入五臟六腑的心靈充實感,莫可言喻。終於,我端起了杯子,輕輕地啜著一口苦苦甘甘的咖啡汁液,只覺滿嘴的厚實感,再啜一口,汁液流經喉嚨、穿過食道、直達胃壁,這分滿足感一直是我那些不喝咖啡的朋友們所無法領略的。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間,我才意識到我身處何地,於是抬頭望向窗外的大雨,這才醒悟過來,適才那幾分鐘的時光裡,我竟完全忘了那一度讓我倉皇逃難的大雨。再喝一口咖啡,我不禁笑了起來,在這雨中的咖啡館。顯然,在喝咖啡的過程中,我可以感覺到一種「雙重性」。如同梭羅所說的:
我可以感覺到一種雙重性,由於這種雙重性,我可以站得離自己遠遠的,像跟別人的關係一樣。我的經驗不論何等強烈,我都可以感到有另一部分的我在場,並感到它的評論;這一部分的我,可以說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一個旁觀者,只是觀察記錄我的經驗,卻不分享我的經驗;說它是我也可以,說它是你也可以。
在咖啡的品嚐中開放所有感官知覺,得以開放自我的心靈,如此才能品味咖啡真正的味道:亦即主體性的消解,解放禁錮的心靈,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才能聽到平時聽不到的聲音。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常常有一種特殊的境遇:有時當全班正在熱烈地討論某一個議題時,雖然我仍身處講臺上,並且用心地聆聽每一位同學的意見,甚至還能加以講評,但是我卻常會有一種奇特的心理變化,就好像我的心靈跳脫出身體,懸浮在教室上空一般,俯視著全班同學及那個正在講臺上努力教學的我,構成一幅頗令我玩味的畫面。
就是這種「雙重性」,讓我體悟到在孤獨與非孤獨之間,其實是存在著一些中間的灰色地帶,我們至少可以將這個中間灰色地帶區分為兩種不同的狀態,即「涉入的不涉入」(engageddisengagement)與「不涉入的涉入」(disengagedengagement)。假設以全然的非孤獨(即「完全的涉入」,pureengagement)與全然的孤獨(即「完全的不涉入」,puredisengagement)作為光譜軸的兩端,那麼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著「涉入的不涉入」與「不涉入的涉入」這兩種中間地帶。
後者係緊臨「完全的不涉入」一端的「不涉入的涉入」,即在完全的孤獨中又保有部份的他者存在的可能性,這是因為雖然孤獨是一種知覺、思想、感情和行動上的不涉入狀態,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樣的不涉入狀態,仍會有一些間接或替代性的他者涉入,常見的「睹物思人」或「擬人化」就是從物而指涉至人的情形。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就經常把自然事物擬人化:
我從未有過像孤獨這樣好的良伴……
……在自然界的事中你可以找到最甜美、最溫柔、最純潔,也最令人鼓舞的社會關係……
我突然明悟到在自然界中含有甜潤的、有益身心的社會關係,就在雨聲的滴答中,就在那環繞我房子的每個聲音、每個景象中,一種無限的、無量的友善遽時像一種空氣一樣支持住我……
它是那樣清楚地讓我察覺到,即使在我們通常稱之為荒野的陰沉的地方,也有一種與我那麼親近的東西在場;讓我察覺到,跟我血緣最近、最有著人性氣息的,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村民……
我並不比湖中笑得那麼響的潛鳥寂寞,不比湖本身寂寞。請問,這寂寞的湖又有什麼同伴呢?……我並不比草地上的單莖毛蕊花或蒲公英寂寞,不比一片葉子、一棵酢漿草或一隻馬蠅或蜜蜂寂寞。
顯然,孤獨者的意識在許多時候仍然會處於一種不自覺的涉入狀態。
不管是「涉入的不涉入」還是「不涉入的涉入」,其實都是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人類的意識狀態,極少是能夠完全的非孤獨或是完全的孤獨,每一個事件的凝視與關注總是免不了會被一層「底景」(containment)所圍繞,有時候是以其他的人、事、或物所構成的「底景」以突顯自我存在的樣貌,另一些時候則可能是以自身作為「底景」以彰顯某些人、事、物的特殊意涵。因此,「底景」就像電影的背景音樂一樣,是一種我們雖然隱約意識到,卻不會去加以特別注意的事物。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對「底景」都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但是我們沒有把意識的鏡頭對焦在某些人、事、或物身上,並不代表它們就不在鏡頭之內,他們其實一直都在,只是在背景的位置上而已。這樣的「底景」是可以忽略、可有可無的背景而已嗎?不,根據完形心理學(GestaltPsychology)的看法,「底景」非但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相反地,它更是影響著我們對事物的認知的關鍵所在。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很喜歡使用音樂的例子來說明時間的連續性,我倒是覺得胡塞爾的音樂例子也頗能解釋「底景」的概念:旋律當然是由一個一個的音符組合而成的,但在聽音樂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剎那聽到所有的音符,而只能在每一剎那聽到一個音符;但如果我們一次只能聽到一個音符的話,我們又怎麼可能聽到需要由一個以上的音符所組成的旋律呢?答案就在於,音符雖然一個一個響起以後又一個一個消失,但它們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消失,而只是成為了意識的「底景」而已。沒有這個「底景」,我們所聽到的,只可能是一個一個的音符,而不可能是一段一段的旋律。
「底景」對人的影響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來舉一個我們生活中常見的例子說明。常常在許多重要的場合裡,我們總是能看到某些人在講述著他的一些事跡,彷彿他的生命中充滿了不平凡的經歷,連帶使得這個人也似乎跟著不平凡起來。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覺?雖然有時可能是這些人的自信,使他相信自己是不平凡的,因而他就真的不平凡起來了,不過,更多的時候,是當我們在相形見絀之下,相信這些人是不平凡的,因而突顯了他們的不平凡。此時的我們在無意中扮演了他人的「底景」,他們的不平凡是藉由我們的平凡而彰顯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