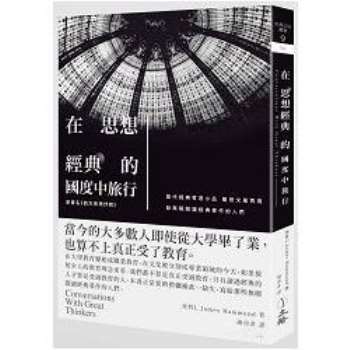倫理
正在消失的四種情愫
抱負、驕傲、欽佩和鄙夷往往混然而為一體,這種情愫往往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存在。然而,在當代西方人身上,抱負、驕傲、欽佩和鄙夷卻一概不件。西方人只有廉價的抱負與驕傲。他只想勝過自己的鄰人。只要他勝過自己的鄰人,他就引以為自豪了。他從不把自己與歷史人物相比較,他從無名垂青史的大志向。
欽佩與鄙夷不可分割。一個崇敬某些人的人自然就鄙視另一些人。尼采就注意到欽佩與鄙夷之間的聯繫,他說:「我熱愛偉大的藐視者,因為他們同時又是偉大的崇敬者。」現在,人們既不崇敬任何人,也不藐視任何人。人門再也不仰視或崇敬任何人,人們認為自己和其他人是平等的。我曾聽到有人說:「如今,我們只藐視那些藐視別人的人。」
現代西方人不僅失去了對他人的鄙夷,也失去了對自己的鄙夷。對他人的欽敬往往伴之以對自己的鄙夷。由於現代人不再仰視別人,他也不再俯視自己。尼采指出:「最可鄙視的時代正在到來,因為人類再也不鄙視自己。」最可鄙視的時代已經到來,因為現代人再也不鄙視自己。
這些情愫——抱負、驕傲、欽佩和鄙夷——一直是西方世界生命力的來源,它們使西方世界以雄厚而豐富的實力,生氣勃勃、鬥志昂揚地向無盡的未來進取。這些情愫在近代西方的消失使西方世界日益窮困、淺薄並衰落。
威脅西方的並不是外族侵略、經濟衰退或環境污染。威脅西方的是精神的匱乏、思想與目標的匱乏、志向與抱負的匱乏,以及對物質的過份追求和對營利與消費的過份追求。
經典著作
學習經典不僅在於擴充知識,也在於改善品行、提高生活水平、使個性得到發展。學習經典使人超越物質世界和日常瑣事。學習經典使人有所尊崇、鼓舞人為崇高的目標奮鬥。學習經典無論從倫理或智力發展的角度來看,都是重要的;它能改善人的精神境界,也能改善人的性格。
然而,學習經典也有不利的一面。它要求精力高度集中和艱苦努力,它有時導致對無意識的抑制,進而引起心理的不平衡。許多學者,包括韋伯(Max Weber)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由於過度的智力消耗而受到精神崩潰的折磨。如果說智慧既包括廣博的知識,也包括平和的內心的話,那麼,對經典就應只作適度的研究。任何人在試圖給經典下定義時,都不應忽視這一點:經典應該是少而經,應該儘可能地簡約可讀。藝術與道德
藝術應不應該具有道德意義?柏拉圖和孔夫子認為應該。他們認為,音樂應該具有增強道德和培育性格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應該禁止那些道德不純的音樂;他們認為,放蕩的音樂會慫恿放蕩的行為,並最終導致無政府狀態和政治動亂。柏拉圖和孔夫子認為,音樂和文學都應具有鼓舞人心和催人向上的作用。
悲劇和史詩的語言及內容通常鼓舞人心,催人向上。悲劇和史詩刻畫英雄人物,也鼓勵英雄行為。有些視覺藝術,如古希臘的雕塑和米開朗基羅的雕塑,就與悲劇相似。它們表現英雄人物,提高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音樂一般也具有鼓舞人心和催人向上的作用。貝多芬的音樂就是如此。很明顯,偉大的藝術具有道德意義,但不說教。偉大的藝術提高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但不宣揚道德善行。
道德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對道德的宣揚到了虛偽的程度,就會引起反動。十九世紀末的寫實主義藝術就是對過份的道德感和感傷主義的反動。不久,邪惡便成了藝術的一個主題,正如過去善良曾是藝術的主題一樣。二十世紀的藝術,包括電影,被令人毛骨悚然和非道德的內容所困擾。似乎有許多現代藝術家認為,深刻見之於對人的邪惡、非理性和病態的表現。現代藝術對病態的表現和十九世紀初的感傷主義一樣,是片面的、誇大的和做作的。現代藝術在道德上的無政府狀態,尤其是流行音樂和電影在這方面的表現,毫無疑問地對現代社會的道德無政府主義狀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正在消失的四種情愫
抱負、驕傲、欽佩和鄙夷往往混然而為一體,這種情愫往往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存在。然而,在當代西方人身上,抱負、驕傲、欽佩和鄙夷卻一概不件。西方人只有廉價的抱負與驕傲。他只想勝過自己的鄰人。只要他勝過自己的鄰人,他就引以為自豪了。他從不把自己與歷史人物相比較,他從無名垂青史的大志向。
欽佩與鄙夷不可分割。一個崇敬某些人的人自然就鄙視另一些人。尼采就注意到欽佩與鄙夷之間的聯繫,他說:「我熱愛偉大的藐視者,因為他們同時又是偉大的崇敬者。」現在,人們既不崇敬任何人,也不藐視任何人。人門再也不仰視或崇敬任何人,人們認為自己和其他人是平等的。我曾聽到有人說:「如今,我們只藐視那些藐視別人的人。」
現代西方人不僅失去了對他人的鄙夷,也失去了對自己的鄙夷。對他人的欽敬往往伴之以對自己的鄙夷。由於現代人不再仰視別人,他也不再俯視自己。尼采指出:「最可鄙視的時代正在到來,因為人類再也不鄙視自己。」最可鄙視的時代已經到來,因為現代人再也不鄙視自己。
這些情愫——抱負、驕傲、欽佩和鄙夷——一直是西方世界生命力的來源,它們使西方世界以雄厚而豐富的實力,生氣勃勃、鬥志昂揚地向無盡的未來進取。這些情愫在近代西方的消失使西方世界日益窮困、淺薄並衰落。
威脅西方的並不是外族侵略、經濟衰退或環境污染。威脅西方的是精神的匱乏、思想與目標的匱乏、志向與抱負的匱乏,以及對物質的過份追求和對營利與消費的過份追求。
經典著作
學習經典不僅在於擴充知識,也在於改善品行、提高生活水平、使個性得到發展。學習經典使人超越物質世界和日常瑣事。學習經典使人有所尊崇、鼓舞人為崇高的目標奮鬥。學習經典無論從倫理或智力發展的角度來看,都是重要的;它能改善人的精神境界,也能改善人的性格。
然而,學習經典也有不利的一面。它要求精力高度集中和艱苦努力,它有時導致對無意識的抑制,進而引起心理的不平衡。許多學者,包括韋伯(Max Weber)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由於過度的智力消耗而受到精神崩潰的折磨。如果說智慧既包括廣博的知識,也包括平和的內心的話,那麼,對經典就應只作適度的研究。任何人在試圖給經典下定義時,都不應忽視這一點:經典應該是少而經,應該儘可能地簡約可讀。藝術與道德
藝術應不應該具有道德意義?柏拉圖和孔夫子認為應該。他們認為,音樂應該具有增強道德和培育性格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應該禁止那些道德不純的音樂;他們認為,放蕩的音樂會慫恿放蕩的行為,並最終導致無政府狀態和政治動亂。柏拉圖和孔夫子認為,音樂和文學都應具有鼓舞人心和催人向上的作用。
悲劇和史詩的語言及內容通常鼓舞人心,催人向上。悲劇和史詩刻畫英雄人物,也鼓勵英雄行為。有些視覺藝術,如古希臘的雕塑和米開朗基羅的雕塑,就與悲劇相似。它們表現英雄人物,提高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音樂一般也具有鼓舞人心和催人向上的作用。貝多芬的音樂就是如此。很明顯,偉大的藝術具有道德意義,但不說教。偉大的藝術提高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但不宣揚道德善行。
道德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對道德的宣揚到了虛偽的程度,就會引起反動。十九世紀末的寫實主義藝術就是對過份的道德感和感傷主義的反動。不久,邪惡便成了藝術的一個主題,正如過去善良曾是藝術的主題一樣。二十世紀的藝術,包括電影,被令人毛骨悚然和非道德的內容所困擾。似乎有許多現代藝術家認為,深刻見之於對人的邪惡、非理性和病態的表現。現代藝術對病態的表現和十九世紀初的感傷主義一樣,是片面的、誇大的和做作的。現代藝術在道德上的無政府狀態,尤其是流行音樂和電影在這方面的表現,毫無疑問地對現代社會的道德無政府主義狀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