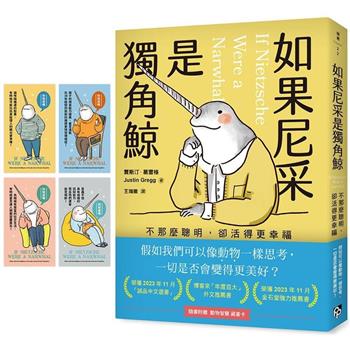橋詰愛平是日本皇軍第六師團的一名士兵,一八六八年三月八日,橋詰的兵團駐紮在海邊的堺市(大阪附近),適逢一艘停泊在港口的法國軍艦杜普雷斯號的士兵上岸。這時明治維新 開始僅一年,日本正從幕府將軍(軍事獨裁者)統治的封建制度過渡到中央帝國政府,數世紀來首次允許西方人進入日本領土。這是堺市民眾第一次見到外國人,眼看法國士兵開始隨意地穿過他們神聖的廟宇,和當地人調情,他們驚慌起來。法國水兵的行為完全符合十九世紀上岸休假的西方船員的作風,日本人卻認為這是一種可憎的失禮行為。橋詰和他的同袍奉命去勸說法國士兵回到他們的船上,由於語言隔閡,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沮喪之餘,日本兵採取行動,抓住其中一人,綁住他的雙手加以羈押。法國人認為這是衝突的開始,紛紛逃回船上,但其中一人順手摸走一面日本軍旗;日本旗手是一個名叫梅吉的消防員,他立刻追上這名法國偷旗賊,並用斧頭劈開他的頭作為報復,法國人也開始用手槍射擊梅吉,橋詰和戰友們則扛起步槍來還擊,法方無論人數或槍枝數都遠遜於對手,他們只不過想探索一下這座小鎮(並和當地婦女搭訕),完全沒有準備要戰鬥。而在短暫的交火之後,日本人殺死了十六名法國士兵。
由於彼此關係還很生疏且不穩定,雙方外交官急著平息怒火,防止流血事件擴大。法國人堅持日本軍方必須為傷亡負責,要求正式道歉,賠償十五萬美元,並處決二十名應對大屠殺負責的日本士兵。
涉及該事件的七十三名士兵全都接受了審訊,其中二十九人承認開了槍,為了向他們的天皇致敬,二十九人全都願意接受處決。由於法國外交官只要求二十人,士兵們去了一趟寺廟,在那裡抽籤決定誰要受死。結果橋詰勝出,沒抽中的九名士兵大失所望,他們抗議命運不公,要求和橋詰及其戰友一起被處決,但他們的請求被否決了。
故事到了這裡,我們發現,所謂正確的道德途徑,可說完全取決於你的文化背景。
橋詰和其他被判死的士兵接受(甚至欣然接納了)自己的命運,但他們不同意自己違反了任何軍事法規,畢竟,是法國人先開的槍。他們要的是修改判決:透過儀式性自殺(切腹)而死,而不是被處決。這麼做會將他們提升到武士的地位,這是所有步兵的終極目標。他們的請求被獲准了,在日本當局看來,這是一個暗中羞辱法國人,並將榮耀(而非懲罰)賦予那些被判死士兵的機會。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橋詰和十九名同袍身穿白袴 和黑色羽織 ,在數百名士兵的陪同下乘著肩輿(華麗的有蓋轎子)來到一座佛寺。他們被招待魚和清酒的最後一餐,兩國權貴分坐在切腹場地的兩側,其中包括到場查核日方是否會遵守協議的法國高官:杜普雷斯號指揮官,名字取得頂好的杜佩蒂-圖阿爾 。
士兵們一個接一個走向前,他們平靜地跪在榻榻米上,將劍刺入肚子,切斷腹部的腸繫膜上動脈。在極度痛苦中,他們低下頭,由他們的助手實施斬首。切腹是一種在七百年武士歷史中形成的古老習俗,但這是第一次被非日本人目睹,杜佩蒂-圖阿爾含蓄地說:他相當震驚。根據某些說法,杜佩蒂-圖阿爾在儀式當中不斷起身,被那些人在給自己開膛破肚時表現的難以置信的冷靜嚇住了。橋詰排在第十二位,就在他要開始切腹時,杜佩蒂-圖阿爾要求儀式停止,譴責這種血債血還的方式,接著他召集其餘法國要員,匆匆撤回到了船上。
對橋詰來說,這是奇恥大辱,他的正義死亡(為他自己和他的天皇帶來榮耀的機會)被否決了。儘管杜佩蒂-圖阿爾認為中止儀式是一種慈悲之舉,對橋詰來說卻恰恰相反。幾天後,剩下的九名武士被告知,杜佩蒂-圖阿爾已申請撤銷對他們的死刑判決,這對橋詰打擊太大了,他在聽到這消息的當下咬破自己的舌頭,希望能流血而死。對於橋詰等人來說,杜佩蒂-圖阿爾所展現的仁慈是比死更糟的劫難。
試想一下這個故事所引發的道德困境:一開始,法國人要求執行死刑作為殺害他們士兵的補償,這點是否合理?以牙還牙的方式是否合乎道德?還是國家批准的死刑原本就是野蠻而不道德的?杜蒂-圖阿爾中止儀式時是仁慈的嗎?如果是,那是誰覺得仁慈?那些被赦免的日本兵肯定不以為然。自殺是不是一種不合時宜的道德準則?如同本故事所示,這些道德問題的答案隨著你問的人、他們來自哪裡,以及身處的時代而異,儘管道德不見得是全然隨意的,但大致取決於文化。
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對於我們視為對或錯的行為的影響如此之大,此一事實顯示,我們的道德感並不是由外在、超自然力量所賦予的單一準則,它看來更像是一套被文化微調過的遺傳規定。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的道德能力和其他認知特徵一樣,是演化而來的,至少,對那些研究動物行為的科學家來說似乎是如此。靈長類動物學者德瓦爾 出版了許多關於動物社會複雜性主題的精采書籍,宣揚了人類道德演化「由下而上路徑」的觀點,這顯示人類道德(包括宗教信仰)並不是(眾)神傳給我們的,也並非完全來自對於非本質的高層次思考。相反地,它是所有群居動物共有行為和認知的自然顯露(由演化形成)。「道德法則不是從上面強加的,也不是從論證周密的原則衍生而來,」德瓦爾在《倭黑猩猩與無神論者》(The Bonobo and the Atheist)一書中寫道,「而是源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存在的、根深柢固的價值觀。」
例如,想想其他一些受到古老、固有價值觀滋養的靈長類動物,是如何處理類似堺事件的社交衝突的。例如短尾猴,一種生活在隔海與日本相望的東南亞舊大陸獼猴,如同大多數靈長類動物,衝突是牠們社交生活的常態,戰鬥決定了誰是主子,以及彼此在社會階梯上的位置。短尾猴群體可以多達六十隻,其中以雄性猴王為群體的主要保護者,並且擁有和雌性交配和生育後代的專有權。雄性猴王偶爾會受到年輕雄猴的挑戰,所以必須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想像一下一個場景,一隻年輕雄猴閒晃到了猴王正忙著給雌猴梳理毛髮的地方,此時年輕雄猴坐下,開始用手指摩挲雌猴的皮毛,尋找蟲子。以地位來說,有權優先替這隻雌猴梳理毛髮的是猴王,這種干擾完全站不住腳。猴王啪的摑了下年輕雄猴的腦袋,來訓斥這個早熟的小子。為了賠罪,年輕雄猴轉過身來,將自己的後背展示給猴王,在他面前擺動屁股。猴王意識到這是一種懺悔行為,抓住年輕雄猴的臀部,緊摟著好一陣子,這是一個信號,顯示牠們的關係已恢復,沒事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兩隻動物都知道某種規則被打破了,必須做些什麼來釐清誰是主子。
群居動物(如獼猴)生活在各種準則中,這些準則支配著牠們在社交世界中該有和不該有的行為,科學家稱這些規則為動物界規範。如同接下來將談到的,人類也有用來引導行為的規範,但人類還有用來引導行為的、以道德為形式的額外規範。不同於行為規範,道德不僅要我們以某種方式行事,而且還告訴我們為什麼。橋詰認為他應該切腹,因為這可以榮耀天皇,讓他像武士那樣死去;杜佩蒂-圖阿爾認為他應該中止執行死刑,因為那造成了無謂的痛苦。不同於在幕後運作的潛規則的行為規範,道德立場是經過個人、社會/文化,甚至神祇們明確考量、評估和認定的。
本章旨在說明,我們截至目前提到的這些人類認知技能(例如發問專長、死亡智慧、心智理論),已經從動物「規範性」 的泥土中形塑出人類的道德感。此外我也要闡明,儘管缺乏成熟的人類道德思維能力,實際上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往往是動物。要知道,人類的道德推理經常帶來比起動物界規範性行為所展現更多的死亡、暴力和破壞。所以說人類的道德,就如同我要主張的:實在有點糟。
想想看,堺事件在獼猴作風的修復式正義 中會如何得到解決?想像一下,法國人了解到日本人有權保護他們的村莊,因為他們具有猴王的地位,而需要為自己部隊在上岸休假期間的不良行為贖罪的是杜佩蒂-圖阿爾。當武士們圍坐在戶外涼亭四周觀望著,身著軍服的杜佩蒂-圖阿爾會走到跪著的橋詰身邊,蹲在他面前,將屁股高高抬起。而橋詰會抓住杜佩蒂-圖阿爾的臀部,將它緊摟在懷裡好一陣子,在這當中圍觀人群將紛紛點頭讚許。沒人會死,也不會有榮譽或者出於政治動機的懲罰概念。此時只有和解,以及武士抱住法國人臀部的暖心畫面。
屁股抬高
所有動物(包括人類)從生到死似乎都遵從著許多隱密、未經檢驗的潛規則,科學家和學者使用規範這字眼來指稱動物社交界的一些隱含規則――這決定哪些行為是被允許或預期的。約克大學學者安德魯斯(Kristin Andrews)和韋斯特拉(Evan Westra)使用「規範性規律」一詞來描述管理動物社會的、以規範為基礎的系統,並把它定義為「群體內的一種由社群維繫的行為從眾模式」。
對於花時間觀察動物的人來說,安德魯斯和韋斯特拉強調的這些從眾模式可說是再明顯不過,例如,我養的雞群有明確的行為模式,可以決定哪隻雞最先吃到我扔進牠們柵欄中的義大利麵。其中一隻雞「影子」在「啄食順序」 中占有優勢,總是第一個搶走我扔過去的食物。另一方面,「貝琪博士」接近社會等級的最底層,總是在群體的外圍附近徘徊。要是貝琪博士試圖在輪到牠之前硬闖進去咬義大利麵,就會被影子啄一下,因為貝琪博士這麼做將違反一條關於「誰先進食」的規範。我的雞群有一套決定彼此在進食時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制度(以及違反這些規範的後果),來維持群體的從眾模式(即「啄食順序」)。
韋斯特拉透過Email向我解釋,規範並不等同於規則,因為「在實務上,你很難判斷動物的某種行為實際上遵循的是什麼規則——如果有規則的話」,而且「其實許多學者和認知科學家認為,比起實際制定一套規則,『感覺』才是社會規範的核心部分」。當規範被打破,通常會造成以負面情緒(侵犯者和被侵犯者雙方皆然)形式呈現的後果,有時還會有積極的懲罰。如果某種規範遭到侵犯,動物會感受到必須以焦慮、不安甚至憤怒的形式去遵守規範的壓力。違反規範通常會導致一些有助於重建現狀的行為,因而消除這那些負面情緒,例如影子啄咬貝琪博士,或者獼猴喜歡的抱臀部和解技巧。動物感受到的遵守規範的壓力,以及牠們所經歷的以負面情緒形式呈現的,違反規範的後果,是所有動物群體賴以維持社會架構的要素。
雞之類的動物不需要太多複雜的認知方式,就能讓這些社會規範冒出來,同時透過負面情緒引導牠們的行為,雞不需要用心智理論來猜測其他雞對啄食順序有多少了解。我的雞群也不必透過因果推理,思索貝琪博士為何應該等到最後吃,以及這是否公平合理。對動物而言,多數規範都是這樣運作的,而這樣的行為模式,其實由一些很欠考慮的情緒所引導的。事實上,對人類而言,大多數規範也是如此。
人類行為受制於一些已經內化但未經明確教導的規範,因為它們未經檢驗和教導,因此不受好/壞或對/錯觀念的限制,沒有被提升到道德層次。想想「替別人擦臉」是不是可被接受的規範,你所生活的社會十之八九不會接受當街拿著餐巾走向陌生人,替他們擦去嘴角食物殘渣的做法。這是一種我們特別保留給孩子、親人或密友的親密舉動,完全不是我們會對陌生人做的事。沒人教過你,但你依然遵守這規則,而且很可能你在此之前從沒想過或看過這種擦臉規則,這也證明了,你早在我提到這規則之前就把它內化了。嘗試用餐巾擦拭陌生人的臉確實會讓你渾身不自在,這正是規範的典型本質:一種透過「操控情緒」來引導你的行為的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