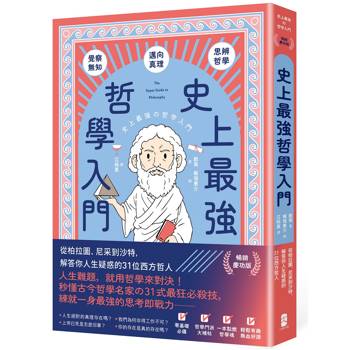第一輪 真理的「真理」──真的有絕對的真理存在嗎?
沙特 用我們的雙手來把人類導向真理吧!
法國哲學家沙特(一九○五年~一九八○年)是個特殊的哲學家,他不喜歡住在固定地點。他每天都會前往巴黎一個叫聖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的地方(以日本來說大概相當於澀谷、原宿),在咖啡廳裡與「奇裝異服、髮型新奇的當代年輕人」一面辯論,一面寫哲學書渡過時光。年輕人都很敬仰這樣的他,而稱他為「聖日耳曼大道的教皇」。
如此集年輕人的尊敬於一身的沙特,對於黑格爾與齊克果的對立問題,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既然這樣,那就用我們自己的雙手,推動追求終極真理的歷史往前進吧!為此,應該賭上自己的人生看看!」
也就是說,沙特建議,不要把黑格爾的哲學當成事不關己,而是自己積極參與,找出「身為一個人活在當下的意義」。當時的年輕人固然覺得資本主義的成功帶來的豐足生活很不錯,卻也煩惱著人生到底該如何渡過才好。沙特這番熱切的話語,大大撼動了這些年輕人。
自由之刑
順便一提,一談到沙特,他也是以「人類遭處以自由之刑」的論點,而知名的哲學家。但為什麼會有「自由之刑」這種東西呢?一般而言,自由應該是一種任何人都追求的美好狀態才是呀?沙特卻主張並非如此。他對於自由給了以下的解釋:
「所謂的自由,是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你明明不知道什麼才是對的,人家卻把你丟出去,對你說『隨你高興怎麼做』。」
打個比方,假設在某個地方有個神,他清清楚楚把一切都告訴人類,說:「這就是真理唷!這就是你生存的目的唷!」那人類就完全沒必要煩惱了。就像父親的手牽著小朋友往前走一樣,我們也一樣,只要安心地跟隨著真理,照著祂講的生活下去就行了。
然而,事實上,既沒有人告訴我們這樣的真理以及生存的目的,也沒有人為我們說清楚講明白。因此,對於「該怎麼做才好?」人類非得要自己「決定」不可。
可是……我們到底該「決定」些什麼才好?要做「決定」,就必須要有某種「做決定的標準」存在才行。假設我們稱之為「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好了。可是,世界上卻有多種「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存在。它可能是宗教A,可能是宗教B,或者是哲學A、哲學B。這樣的東西,要多少有多少吧。那麼,在為數不少的「價值觀」當中,到底該選哪個好呢?假如、萬一,誤選了一個「糟糕的價值觀」的話……人生搞不好就白走一遭了!因此,我們必須要慎重地選擇正確的價值觀才行。
也就是說,在許多「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中」,我們必須要決定採用其中一個,也因此我們會需要能夠做出這個決定的正確標準。咦?這樣的話,會變成「需要一個價值觀,來做決定選擇一個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而要選擇這樣的價值觀,也一樣需要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結果,會變成「需要價值觀」的無窮迴圈。從理論上來說,我們會變成無從找到「用於做決定的正確價值觀」。
這樣的話,就無計可施了!我們也只能咬著牙,隨便從中決定一個了!
不過,沒有人能夠保證我們所選的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可能因而碰到可怕的遭遇。只有一次的人生,我們可能會白白浪費。當然,還有一種選擇是「什麼也不選」吧。但也沒人能保證,「什麼也不選」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那麼,該怎麼做才好呢?……束手無策。對於「人生之中,該做些什麼?」這樣的重大問題,無論是神、國家、學校,都不會把「你應該這樣這樣去做」的正確價值觀告訴我們。因此,我們非得要自己做決定。就算害怕失敗或害怕選擇錯誤,還是必須要在不安當中勉力做出「不知道到底正確與否的某種決定」,生存下去。
而這樣的決定,是絕對「自由」的。選什麼都行。你可以為了上好大學拼命用功;你也可以不讀書、一直把時間都花費在幫電玩遊戲的角色練功。你可以去當木匠,也可以去當上班族。你可以被甩好幾次也不氣餒,不斷參加聯誼後找到結婚對象;你也可以因為覺得麻煩而把圖片上的二次元女孩當成代用品、一輩子不結婚。一切都是自由的。
不過,由於不管你選什麼,都無法得知正確的選擇是什麼,因此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你搞不好會心驚於自己先前的選擇。
「為什麼我會從事這樣子的工作呢?為什麼我沒結婚、變成一個大叔呢?我的人生,就只有這種程度,再來就只剩下老和死了嗎?……那個時候,我明明可以做出不同選擇的……」
然而,對於這樣的狀況,任誰都無法抱怨。因為,那是自己選擇來的。因此,就算因為這樣的選擇而失敗了,而感到後悔,所有的責任都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說,我們明明沒有要求這樣,卻突然被丟到一個不知該如何選擇才好的世界裡,被迫接受「這是你的人生,所以依你自己的喜好去選擇吧」的自由。不但什麼事都得選擇,到頭來如果因為那樣的選擇而失敗了,還被迫得要負起責任,因為「這是你自己選擇的!」──人就是帶著這樣的宿命而誕生的。沙特指出了人類的這種狀況,並以「人類遭處以自由之刑」或是「人類受到自由的詛咒」來形容。
參與歷史
不過,對於人生,他並非只從悲觀的角度來描述而已。他也主張,「就是因為這樣,人類更應該參與歷史」。因為,與其不知道哪個價值標準才正確,就什麼也不選、無所事事地消費人生下去,還不如背負著可能會錯的風險,選擇某種方式去過活,會好得多。
因此,沙特主張,人類固然背負著「自由之刑」的詛咒,仍然應該自行做出決定,堅強地生活下去,不要因而轉移目光。也就是說,既然都一樣要接受「自由之刑」,不如反過來承擔起失敗的責任,斷然而積極地做出決定。而且,難得要動手,乾脆盡可能找個大舞台……於是沙特提議,不如找個「能夠讓人類朝理想的社會與真理前進的歷史大舞台」,站上去看看。
沙特所生長的那個時代,恰好是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成為世界主流的時代。不過,如果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歷史一定會在辯證法下漸漸成長下去,因此就算是大家容易誤以為會永遠持續下去的資本主義社會,遲早也會遭到否定,而有更為出色的社會體系取而代之才是。那麼,這個更為出色的社會體系,究竟是什麼呢?當時,大家認為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很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體系。
因此,在沙特的呼籲下受到感召的那些年輕人,開始接二連三投入了共產主義革命以及學生運動當中。於是,所謂「反社會活動」,也就是戴著頭盔丟擲汽油彈,或是與機動警察隊起衝突的那些行動,成了席捲全球的一大風潮。
沙特 用我們的雙手來把人類導向真理吧!
法國哲學家沙特(一九○五年~一九八○年)是個特殊的哲學家,他不喜歡住在固定地點。他每天都會前往巴黎一個叫聖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的地方(以日本來說大概相當於澀谷、原宿),在咖啡廳裡與「奇裝異服、髮型新奇的當代年輕人」一面辯論,一面寫哲學書渡過時光。年輕人都很敬仰這樣的他,而稱他為「聖日耳曼大道的教皇」。
如此集年輕人的尊敬於一身的沙特,對於黑格爾與齊克果的對立問題,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既然這樣,那就用我們自己的雙手,推動追求終極真理的歷史往前進吧!為此,應該賭上自己的人生看看!」
也就是說,沙特建議,不要把黑格爾的哲學當成事不關己,而是自己積極參與,找出「身為一個人活在當下的意義」。當時的年輕人固然覺得資本主義的成功帶來的豐足生活很不錯,卻也煩惱著人生到底該如何渡過才好。沙特這番熱切的話語,大大撼動了這些年輕人。
自由之刑
順便一提,一談到沙特,他也是以「人類遭處以自由之刑」的論點,而知名的哲學家。但為什麼會有「自由之刑」這種東西呢?一般而言,自由應該是一種任何人都追求的美好狀態才是呀?沙特卻主張並非如此。他對於自由給了以下的解釋:
「所謂的自由,是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你明明不知道什麼才是對的,人家卻把你丟出去,對你說『隨你高興怎麼做』。」
打個比方,假設在某個地方有個神,他清清楚楚把一切都告訴人類,說:「這就是真理唷!這就是你生存的目的唷!」那人類就完全沒必要煩惱了。就像父親的手牽著小朋友往前走一樣,我們也一樣,只要安心地跟隨著真理,照著祂講的生活下去就行了。
然而,事實上,既沒有人告訴我們這樣的真理以及生存的目的,也沒有人為我們說清楚講明白。因此,對於「該怎麼做才好?」人類非得要自己「決定」不可。
可是……我們到底該「決定」些什麼才好?要做「決定」,就必須要有某種「做決定的標準」存在才行。假設我們稱之為「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好了。可是,世界上卻有多種「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存在。它可能是宗教A,可能是宗教B,或者是哲學A、哲學B。這樣的東西,要多少有多少吧。那麼,在為數不少的「價值觀」當中,到底該選哪個好呢?假如、萬一,誤選了一個「糟糕的價值觀」的話……人生搞不好就白走一遭了!因此,我們必須要慎重地選擇正確的價值觀才行。
也就是說,在許多「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中」,我們必須要決定採用其中一個,也因此我們會需要能夠做出這個決定的正確標準。咦?這樣的話,會變成「需要一個價值觀,來做決定選擇一個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而要選擇這樣的價值觀,也一樣需要用於做決定的價值觀……結果,會變成「需要價值觀」的無窮迴圈。從理論上來說,我們會變成無從找到「用於做決定的正確價值觀」。
這樣的話,就無計可施了!我們也只能咬著牙,隨便從中決定一個了!
不過,沒有人能夠保證我們所選的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可能因而碰到可怕的遭遇。只有一次的人生,我們可能會白白浪費。當然,還有一種選擇是「什麼也不選」吧。但也沒人能保證,「什麼也不選」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那麼,該怎麼做才好呢?……束手無策。對於「人生之中,該做些什麼?」這樣的重大問題,無論是神、國家、學校,都不會把「你應該這樣這樣去做」的正確價值觀告訴我們。因此,我們非得要自己做決定。就算害怕失敗或害怕選擇錯誤,還是必須要在不安當中勉力做出「不知道到底正確與否的某種決定」,生存下去。
而這樣的決定,是絕對「自由」的。選什麼都行。你可以為了上好大學拼命用功;你也可以不讀書、一直把時間都花費在幫電玩遊戲的角色練功。你可以去當木匠,也可以去當上班族。你可以被甩好幾次也不氣餒,不斷參加聯誼後找到結婚對象;你也可以因為覺得麻煩而把圖片上的二次元女孩當成代用品、一輩子不結婚。一切都是自由的。
不過,由於不管你選什麼,都無法得知正確的選擇是什麼,因此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你搞不好會心驚於自己先前的選擇。
「為什麼我會從事這樣子的工作呢?為什麼我沒結婚、變成一個大叔呢?我的人生,就只有這種程度,再來就只剩下老和死了嗎?……那個時候,我明明可以做出不同選擇的……」
然而,對於這樣的狀況,任誰都無法抱怨。因為,那是自己選擇來的。因此,就算因為這樣的選擇而失敗了,而感到後悔,所有的責任都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說,我們明明沒有要求這樣,卻突然被丟到一個不知該如何選擇才好的世界裡,被迫接受「這是你的人生,所以依你自己的喜好去選擇吧」的自由。不但什麼事都得選擇,到頭來如果因為那樣的選擇而失敗了,還被迫得要負起責任,因為「這是你自己選擇的!」──人就是帶著這樣的宿命而誕生的。沙特指出了人類的這種狀況,並以「人類遭處以自由之刑」或是「人類受到自由的詛咒」來形容。
參與歷史
不過,對於人生,他並非只從悲觀的角度來描述而已。他也主張,「就是因為這樣,人類更應該參與歷史」。因為,與其不知道哪個價值標準才正確,就什麼也不選、無所事事地消費人生下去,還不如背負著可能會錯的風險,選擇某種方式去過活,會好得多。
因此,沙特主張,人類固然背負著「自由之刑」的詛咒,仍然應該自行做出決定,堅強地生活下去,不要因而轉移目光。也就是說,既然都一樣要接受「自由之刑」,不如反過來承擔起失敗的責任,斷然而積極地做出決定。而且,難得要動手,乾脆盡可能找個大舞台……於是沙特提議,不如找個「能夠讓人類朝理想的社會與真理前進的歷史大舞台」,站上去看看。
沙特所生長的那個時代,恰好是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成為世界主流的時代。不過,如果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歷史一定會在辯證法下漸漸成長下去,因此就算是大家容易誤以為會永遠持續下去的資本主義社會,遲早也會遭到否定,而有更為出色的社會體系取而代之才是。那麼,這個更為出色的社會體系,究竟是什麼呢?當時,大家認為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很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體系。
因此,在沙特的呼籲下受到感召的那些年輕人,開始接二連三投入了共產主義革命以及學生運動當中。於是,所謂「反社會活動」,也就是戴著頭盔丟擲汽油彈,或是與機動警察隊起衝突的那些行動,成了席捲全球的一大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