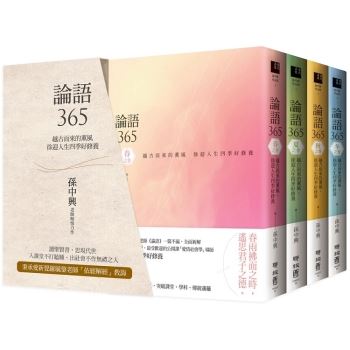[學而‧第一]
5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孔子這麼說過:「要治理一個有一千輛四匹馬拉馬車的大國〔,要注意下面三件事情〕:要做每件大小事情之前要用敬慎之心來謀劃並且還能夠信守對人民的承諾;人民繳納的血汗錢要節儉使用並且還能夠讓人民安居樂業〔,不可讓人們陷入戰爭之苦〕;有築城或修路等等公共建設需要徵用人民時,也要配合人民農作閒暇之時〔,不可妨礙到農事〕。」
這章從管理者的角度談論治國最重要的三件事,如果細分解,其實是五件事(敬事、信、節用、愛人,使民),環環相扣。朱子就認為「五者亦務本之義」,顯然是繼〈學而2〉有子說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而說的,朱子還強調「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許仁圖學長說這是孔子的「導國三經」,其實也可以說是「導國五經」。
這裡的「道」—音島,當動詞,有的版本就用「導」這個字。和〈為政3〉的「道之以政」的「道」是一樣的。「道」,馬融說是「政教」,包咸說是「治」,皇侃綜合兩位前輩的說法:「道,猶治也,亦謂為之政教也。」朱子也說是「治」。許仁圖學長說是有「因勢利導、善用人性」的意思。
「一乘」—是四匹馬拉的馬車,「千乘」是有一千輛四匹馬拉的馬車。包咸說「千乘之國」是「百里之國」。皇侃說是「大國」,並說明「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他還詳細比照古籍考證了「千乘之國」到底有多大的分歧說法,最後也沒敢有定論。邢昺後來就乾脆快刀斬亂麻地說:「千乘之國謂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從「百里」到「四、五百里」,古人的注釋相去太大,實在叫人看了眼花撩亂。
「敬」—朱子說「主一無適之謂」,王夫之說是「慎重以治其事」,戴望說是「行事肅警」。「事」,王夫之說是「祭祀、兵戎、邦交之類,理財、用人、養民、使民不在內」。「敬事而信」,包咸說是「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朱子簡單說是「敬其事而信於民」,許仁圖學長強調是「敬始成終」。「而」,王夫之認為「〔此〕字不要緊,乃湊成句法耳」,我覺得還是毓老師說的當「能」解比較好。「信」—王夫之說是「始終不渝」,戴望說是「信於令」。
「節用」—是指對政府財政而言,主要是指「用物」而言,這就是其他地方強調的「儉」。「愛人」不是講「兒女私情」,而是像現在說的「大愛」。這兩樣後來「墨家」都拿去當招牌而不是儒家的專利。
「使」—有「派令」的意思。「使民」,戴望說是「起徒役也」,也就是要人民服築城或修路等等公共服務。「使民以時」就是派令人民從事公共勞動時要配合農時。「使民」和「民可使」是一樣的意思。〈泰伯9〉中孔子說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許就該和此章的解釋配合看,是要徵召人民服公共服務,而不是通常認為儒家強調專制陰謀的鐵證。
「時」—朱子說是「農隙之時」。《禮記‧王制》〈33〉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但是從《詩經》中這麼多人民抱怨政府「使民不時」的記載看來,「歲不過三日」只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
孔子強調「敬事」的段落不少:〈子路19〉「執事敬」就是到了夷狄都不能放棄的道德;〈衛靈公38〉他強調「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季氏10〉中「事思敬」就是「九思」的條目之一。此外,他還強調要以敬行禮(〈八佾26〉),內在誠心要和外在的儀式配合;他也跟子路強調君子的重點在於「修己以敬」(〈憲問42〉),先從修身能敬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人對事,都是要這樣「一以敬之」。這裡既然是講「道千乘之國」,所以「敬事而信」的「信」應該是指「治理者」對「被治理者」的「信」,而不是朋友間的「信」。這種上對下的「信」,孔子非常重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22〉)、「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7〉)、「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4〉)、「信以成之」(〈衛靈公18〉),以及「信則人任焉」(〈陽貨6〉)或「信則民任焉」(〈堯曰1〉)。這種政府取信於民,人民相信政府,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礎。如果人民和政府之間沒有相互的信任,最壞的情況就是:今日世界某些地區的戰火頻仍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甚至逃亡難民潮,這不是更顯得是普世的渴望和真理嗎?
「節用」的反面就是「奢侈」,主要講的是國家的財政用途。孔子一貫強調一般性的「寧儉勿奢」(〈述而36〉),在政府需要大量花費的禮制上他更是這麼主張的(〈八佾4〉)。所以後來弟子「厚葬」孔子,應該不是孔子所願。孔門後學的荀子也強調「節用裕民」,特別是「節用以禮,裕民以政」,才是「足國之道」(《荀子‧富國》〈2〉)。這才是承傳孔子之道的孔門好弟子。
「愛人」不是今天字面上的意思,還是要放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關係來看。簡言之,就是為政者要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能夠獲得政府的保障。孔子弟子樊遲三次問過「仁」,孔子有一次給出最簡潔有力的回答就是「愛人」(〈顏淵22〉)。子游也在孔子跟他開玩笑說「割雞焉用牛刀」的時候提醒孔子自己說過「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4〉)。《禮記‧哀公問》〈6〉、〈10〉中都記載孔子說過:「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在其中一段,孔子提到從「愛人」可以延伸到其他領域:「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哀公問6〉)在另一段,他則說「愛人」和「有身」、「成身」有關聯:「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哀公問10〉)
私淑孔子的孟子也說過「仁者愛人」,他還說「愛人者人恆愛之」(《孟子‧離婁下》〈56〉),強調這種君民互愛關係的互惠性質。
到了董仲舒,「愛人」就有了更明確的說法:一是承傳孔子「仁者愛人」的主張,強調「愛人」而不是「愛我」(《春秋繁露‧仁義法》〈1〉);一是「愛人」既不應該「善殺」:「《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春秋繁露‧竹林》〈1〉)他還強調「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春秋繁露‧俞序》〈1〉),毓老師上課也強調過為政應該「神武不殺」(《易經‧繫辭上》〈11〉)。
這種「仁者愛人」的想法,也在先秦兩漢古籍中,幾乎不分門派,隨處可見:《大戴禮記‧主言》〈9〉說:「仁者莫大於愛人。」
墨子也在多處說過類似的話。《墨子‧法儀》:〈4〉「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5〉:「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墨子‧兼愛上》〈4〉:「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墨子的「兼愛」學說也就是這種體現。
常被歸為道家的莊子引用過:「愛人利物之謂仁」的說法(《莊子‧外篇》〈天地2〉);《文子‧微明》〈8〉也說老子說過「仁莫大於愛人」,還進一步延伸說「愛人即無怨刑」。
法家的韓非子也深知:「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韓非子‧解老》〈3〉)。
同被歸為法家的管子也說:「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管子‧任法》〈5〉)這裡強調的是因為「愛人」而獨厚(或「私賞」)於人,是會危害統治者的地位。這當然和前面幾種流派的想法是相反的。法家重法不重情,於此可見一斑。
「使民」的問題,季康子就請教過孔子:「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回答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20〉)這章認為「使民」以「莊」,就會得到人民的「敬」。孔子弟子子夏也強調過「勞其民」(也就是「使民」)的重點在於要人民對君上有信任,否則同樣的勞民行為就會被認為是在虐待人民(〈子張10〉)。這裡將「使民」和「信」的關聯說得如此清楚,也算是得到孔子真傳。
班固的《漢書‧食貨志上》〈7〉提到本章,認為這是「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孔子這裡說是「道千乘之國」要注意這三大綱領,難道治理小國還有別的方法?還是說,這種方法也可以適用到小國寡民呢?我覺得應該是普世的價值吧!看看現在戰火頻仍的國家,人民流離失所,更讓人深刻體會此章在現代世界的合宜性!
5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孔子這麼說過:「要治理一個有一千輛四匹馬拉馬車的大國〔,要注意下面三件事情〕:要做每件大小事情之前要用敬慎之心來謀劃並且還能夠信守對人民的承諾;人民繳納的血汗錢要節儉使用並且還能夠讓人民安居樂業〔,不可讓人們陷入戰爭之苦〕;有築城或修路等等公共建設需要徵用人民時,也要配合人民農作閒暇之時〔,不可妨礙到農事〕。」
這章從管理者的角度談論治國最重要的三件事,如果細分解,其實是五件事(敬事、信、節用、愛人,使民),環環相扣。朱子就認為「五者亦務本之義」,顯然是繼〈學而2〉有子說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而說的,朱子還強調「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許仁圖學長說這是孔子的「導國三經」,其實也可以說是「導國五經」。
這裡的「道」—音島,當動詞,有的版本就用「導」這個字。和〈為政3〉的「道之以政」的「道」是一樣的。「道」,馬融說是「政教」,包咸說是「治」,皇侃綜合兩位前輩的說法:「道,猶治也,亦謂為之政教也。」朱子也說是「治」。許仁圖學長說是有「因勢利導、善用人性」的意思。
「一乘」—是四匹馬拉的馬車,「千乘」是有一千輛四匹馬拉的馬車。包咸說「千乘之國」是「百里之國」。皇侃說是「大國」,並說明「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他還詳細比照古籍考證了「千乘之國」到底有多大的分歧說法,最後也沒敢有定論。邢昺後來就乾脆快刀斬亂麻地說:「千乘之國謂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從「百里」到「四、五百里」,古人的注釋相去太大,實在叫人看了眼花撩亂。
「敬」—朱子說「主一無適之謂」,王夫之說是「慎重以治其事」,戴望說是「行事肅警」。「事」,王夫之說是「祭祀、兵戎、邦交之類,理財、用人、養民、使民不在內」。「敬事而信」,包咸說是「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朱子簡單說是「敬其事而信於民」,許仁圖學長強調是「敬始成終」。「而」,王夫之認為「〔此〕字不要緊,乃湊成句法耳」,我覺得還是毓老師說的當「能」解比較好。「信」—王夫之說是「始終不渝」,戴望說是「信於令」。
「節用」—是指對政府財政而言,主要是指「用物」而言,這就是其他地方強調的「儉」。「愛人」不是講「兒女私情」,而是像現在說的「大愛」。這兩樣後來「墨家」都拿去當招牌而不是儒家的專利。
「使」—有「派令」的意思。「使民」,戴望說是「起徒役也」,也就是要人民服築城或修路等等公共服務。「使民以時」就是派令人民從事公共勞動時要配合農時。「使民」和「民可使」是一樣的意思。〈泰伯9〉中孔子說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許就該和此章的解釋配合看,是要徵召人民服公共服務,而不是通常認為儒家強調專制陰謀的鐵證。
「時」—朱子說是「農隙之時」。《禮記‧王制》〈33〉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但是從《詩經》中這麼多人民抱怨政府「使民不時」的記載看來,「歲不過三日」只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
孔子強調「敬事」的段落不少:〈子路19〉「執事敬」就是到了夷狄都不能放棄的道德;〈衛靈公38〉他強調「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季氏10〉中「事思敬」就是「九思」的條目之一。此外,他還強調要以敬行禮(〈八佾26〉),內在誠心要和外在的儀式配合;他也跟子路強調君子的重點在於「修己以敬」(〈憲問42〉),先從修身能敬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人對事,都是要這樣「一以敬之」。這裡既然是講「道千乘之國」,所以「敬事而信」的「信」應該是指「治理者」對「被治理者」的「信」,而不是朋友間的「信」。這種上對下的「信」,孔子非常重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22〉)、「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7〉)、「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4〉)、「信以成之」(〈衛靈公18〉),以及「信則人任焉」(〈陽貨6〉)或「信則民任焉」(〈堯曰1〉)。這種政府取信於民,人民相信政府,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礎。如果人民和政府之間沒有相互的信任,最壞的情況就是:今日世界某些地區的戰火頻仍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甚至逃亡難民潮,這不是更顯得是普世的渴望和真理嗎?
「節用」的反面就是「奢侈」,主要講的是國家的財政用途。孔子一貫強調一般性的「寧儉勿奢」(〈述而36〉),在政府需要大量花費的禮制上他更是這麼主張的(〈八佾4〉)。所以後來弟子「厚葬」孔子,應該不是孔子所願。孔門後學的荀子也強調「節用裕民」,特別是「節用以禮,裕民以政」,才是「足國之道」(《荀子‧富國》〈2〉)。這才是承傳孔子之道的孔門好弟子。
「愛人」不是今天字面上的意思,還是要放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關係來看。簡言之,就是為政者要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能夠獲得政府的保障。孔子弟子樊遲三次問過「仁」,孔子有一次給出最簡潔有力的回答就是「愛人」(〈顏淵22〉)。子游也在孔子跟他開玩笑說「割雞焉用牛刀」的時候提醒孔子自己說過「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4〉)。《禮記‧哀公問》〈6〉、〈10〉中都記載孔子說過:「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在其中一段,孔子提到從「愛人」可以延伸到其他領域:「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哀公問6〉)在另一段,他則說「愛人」和「有身」、「成身」有關聯:「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哀公問10〉)
私淑孔子的孟子也說過「仁者愛人」,他還說「愛人者人恆愛之」(《孟子‧離婁下》〈56〉),強調這種君民互愛關係的互惠性質。
到了董仲舒,「愛人」就有了更明確的說法:一是承傳孔子「仁者愛人」的主張,強調「愛人」而不是「愛我」(《春秋繁露‧仁義法》〈1〉);一是「愛人」既不應該「善殺」:「《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春秋繁露‧竹林》〈1〉)他還強調「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春秋繁露‧俞序》〈1〉),毓老師上課也強調過為政應該「神武不殺」(《易經‧繫辭上》〈11〉)。
這種「仁者愛人」的想法,也在先秦兩漢古籍中,幾乎不分門派,隨處可見:《大戴禮記‧主言》〈9〉說:「仁者莫大於愛人。」
墨子也在多處說過類似的話。《墨子‧法儀》:〈4〉「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5〉:「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墨子‧兼愛上》〈4〉:「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墨子的「兼愛」學說也就是這種體現。
常被歸為道家的莊子引用過:「愛人利物之謂仁」的說法(《莊子‧外篇》〈天地2〉);《文子‧微明》〈8〉也說老子說過「仁莫大於愛人」,還進一步延伸說「愛人即無怨刑」。
法家的韓非子也深知:「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韓非子‧解老》〈3〉)。
同被歸為法家的管子也說:「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管子‧任法》〈5〉)這裡強調的是因為「愛人」而獨厚(或「私賞」)於人,是會危害統治者的地位。這當然和前面幾種流派的想法是相反的。法家重法不重情,於此可見一斑。
「使民」的問題,季康子就請教過孔子:「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回答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20〉)這章認為「使民」以「莊」,就會得到人民的「敬」。孔子弟子子夏也強調過「勞其民」(也就是「使民」)的重點在於要人民對君上有信任,否則同樣的勞民行為就會被認為是在虐待人民(〈子張10〉)。這裡將「使民」和「信」的關聯說得如此清楚,也算是得到孔子真傳。
班固的《漢書‧食貨志上》〈7〉提到本章,認為這是「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孔子這裡說是「道千乘之國」要注意這三大綱領,難道治理小國還有別的方法?還是說,這種方法也可以適用到小國寡民呢?我覺得應該是普世的價值吧!看看現在戰火頻仍的國家,人民流離失所,更讓人深刻體會此章在現代世界的合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