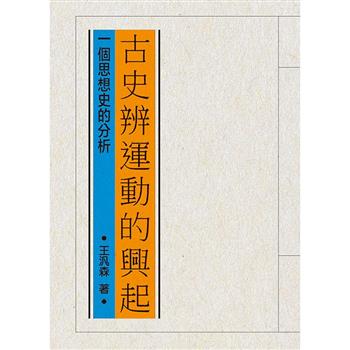引論 激烈反傳統與黃金古代觀念的破滅
一、愛國主義與反傳統思想的內在關聯
魯迅二十三歲時(一九○三年)寫的〈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張照片是送給許壽裳),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之下的困境與悲願。在那樣無奈的困境之下,如何愛國強國,成為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目標。
許多學者都強調,目標的選擇是沒有任何邏輯規律可循的,其實手段的選擇也可能是非邏輯的,在意圖與手段之間,可以有無限種方式的扣接,只要行動者主觀地認為二者之間合乎邏輯,即可成立。我們可以從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情形清楚地看出這一個現象。
在西方勢力猛力叩關,中國知識分子為傳統辯護與抵抗的過程中,有些保守主義者是把西學吸收到傳統的「軀殼」中以達成他們保守的目的,有些則是回歸到比目前所認知的傳統更為傳統的狀態中,這兩種辦法的目標都是為了使傳統更有效地回應當前的變局,可是,他們用以達成目標的手段是何等不同!由於意圖與手段組合方式的變化,中國近代思想人物的風貌亦繁複萬端,他們有的是意態極為保守而手段極為西化;有的是意態極為前進,而手段卻極傳統;有的是意態保守,手段傳統;有的是意態激進,手段西化。同樣的意圖可能藉著全然不同的手段去達成,而同樣的手段也可能為完全不同的意圖服務。所以單是用「傳統」或「前進」,「新」或「舊」來描述他們,常常是不夠充分的。
在愛國救國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所出現的無數手段中,有兩種最值得注意。第一便是以激烈破壞、激烈個人主義來達成愛國救國的目標,以致把大規模的毀棄傳統作為正面價值來信奉。這樣的行動對有些人的情感來說可能是痛苦的,可是為了國家民族更高的利益,許多知識分子卻願意犧牲在情感上相當依賴的某些傳統的質素,同時也要求別人作同樣悲壯的犧牲。所以我們經常可以在這一個時期的知識分子身上同時看到全盤反傳統與在某些層面上戀執傳統的情形,從表面看來這是一種矛盾,其實是在「救國」這一個最終極的目標下目的與手段間的緊張和兩難。
第二種態度是認為愛國就必須保持傳統。即使這些人中間已警覺到傳統的許多成分不周於世用了,但是他們仍願以李文遜(Joseph R. Levenson)所謂的對木乃伊審美式的懷念心情來對待傳統。
在這裡想著重討論的是以大破壞為愛國的手段,以打破傳統的倫理結構,把全中國澈底重新組合為救國手段的現象。對他們來說,愛國保種之熱情愈為深切,則打破傳統的決心亦更為熾烈,二者如影隨形,成為近代中國最奇特的一種力量。而許多傳統型知識分子之所以決然轉向西化,也必須在這一個脈絡下來理解。清季掀天揭地而來的變局對那一代傳統知識分子的刺激是很深刻的,而且國家每經一次挫敗,其痛苦就愈深,有良心的讀書人雖然希望對國族有所濟救,可是正如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所說的:「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他們腦中那一套傳統知識顯然不足以應付這個變局,那麼該當如何呢?—許多讀書人開始移步轉身向壓迫他們的西方帝國主義身上尋找醫己的良方。他們之所以轉向西方,並不是厭棄祖國,相反地,正是為了要增強自己護衛祖國的能力,才決然賤棄舊學,向敵人學習。以清末大詩人范當世(一八五四—一九○四)為例。陳三立(一八五三—一九三七)在為他的《范伯子文集》所寫的〈跋〉中,便很精確地道出范氏向西轉的心路歷程。他說范氏:「好言經世……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范氏原是個不折不扣的傳統型知識分子,他之所以昌言賤棄生平所習,並不是不要中國,而是因為他太愛中國了,因為太愛中國,所以他猜想把中國打得七零八落的泰西諸國,應該有足以拯救中國的學說。當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大量引進西方思想時,他的真正用心也是要對抗帝國主義。而不是如攻擊他的人所說的:康有為是要把中國出賣給西方帝國主義。那一代知識分子這種藉著吸收帝國主義的長處,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曲折心態,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西化論之所以風起雲湧、沛然莫之能禦,至少在意圖的層面上,與強烈的民族情操正是密相結合的,而不一定是崇洋媚外的買辦心理之產物。
一、愛國主義與反傳統思想的內在關聯
魯迅二十三歲時(一九○三年)寫的〈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張照片是送給許壽裳),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之下的困境與悲願。在那樣無奈的困境之下,如何愛國強國,成為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目標。
許多學者都強調,目標的選擇是沒有任何邏輯規律可循的,其實手段的選擇也可能是非邏輯的,在意圖與手段之間,可以有無限種方式的扣接,只要行動者主觀地認為二者之間合乎邏輯,即可成立。我們可以從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情形清楚地看出這一個現象。
在西方勢力猛力叩關,中國知識分子為傳統辯護與抵抗的過程中,有些保守主義者是把西學吸收到傳統的「軀殼」中以達成他們保守的目的,有些則是回歸到比目前所認知的傳統更為傳統的狀態中,這兩種辦法的目標都是為了使傳統更有效地回應當前的變局,可是,他們用以達成目標的手段是何等不同!由於意圖與手段組合方式的變化,中國近代思想人物的風貌亦繁複萬端,他們有的是意態極為保守而手段極為西化;有的是意態極為前進,而手段卻極傳統;有的是意態保守,手段傳統;有的是意態激進,手段西化。同樣的意圖可能藉著全然不同的手段去達成,而同樣的手段也可能為完全不同的意圖服務。所以單是用「傳統」或「前進」,「新」或「舊」來描述他們,常常是不夠充分的。
在愛國救國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所出現的無數手段中,有兩種最值得注意。第一便是以激烈破壞、激烈個人主義來達成愛國救國的目標,以致把大規模的毀棄傳統作為正面價值來信奉。這樣的行動對有些人的情感來說可能是痛苦的,可是為了國家民族更高的利益,許多知識分子卻願意犧牲在情感上相當依賴的某些傳統的質素,同時也要求別人作同樣悲壯的犧牲。所以我們經常可以在這一個時期的知識分子身上同時看到全盤反傳統與在某些層面上戀執傳統的情形,從表面看來這是一種矛盾,其實是在「救國」這一個最終極的目標下目的與手段間的緊張和兩難。
第二種態度是認為愛國就必須保持傳統。即使這些人中間已警覺到傳統的許多成分不周於世用了,但是他們仍願以李文遜(Joseph R. Levenson)所謂的對木乃伊審美式的懷念心情來對待傳統。
在這裡想著重討論的是以大破壞為愛國的手段,以打破傳統的倫理結構,把全中國澈底重新組合為救國手段的現象。對他們來說,愛國保種之熱情愈為深切,則打破傳統的決心亦更為熾烈,二者如影隨形,成為近代中國最奇特的一種力量。而許多傳統型知識分子之所以決然轉向西化,也必須在這一個脈絡下來理解。清季掀天揭地而來的變局對那一代傳統知識分子的刺激是很深刻的,而且國家每經一次挫敗,其痛苦就愈深,有良心的讀書人雖然希望對國族有所濟救,可是正如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所說的:「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他們腦中那一套傳統知識顯然不足以應付這個變局,那麼該當如何呢?—許多讀書人開始移步轉身向壓迫他們的西方帝國主義身上尋找醫己的良方。他們之所以轉向西方,並不是厭棄祖國,相反地,正是為了要增強自己護衛祖國的能力,才決然賤棄舊學,向敵人學習。以清末大詩人范當世(一八五四—一九○四)為例。陳三立(一八五三—一九三七)在為他的《范伯子文集》所寫的〈跋〉中,便很精確地道出范氏向西轉的心路歷程。他說范氏:「好言經世……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范氏原是個不折不扣的傳統型知識分子,他之所以昌言賤棄生平所習,並不是不要中國,而是因為他太愛中國了,因為太愛中國,所以他猜想把中國打得七零八落的泰西諸國,應該有足以拯救中國的學說。當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大量引進西方思想時,他的真正用心也是要對抗帝國主義。而不是如攻擊他的人所說的:康有為是要把中國出賣給西方帝國主義。那一代知識分子這種藉著吸收帝國主義的長處,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曲折心態,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西化論之所以風起雲湧、沛然莫之能禦,至少在意圖的層面上,與強烈的民族情操正是密相結合的,而不一定是崇洋媚外的買辦心理之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