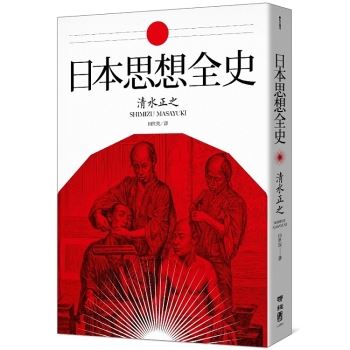第一章古代
1「日本」這個境域
自然史及思想史
思想史是由文字化的文本及其讀解而形成的。而日本的思想,指的是以這個列島上固有的語言所生成及展開的思想。不論是個人的意識或集團的意識,如果將包含初發性的意識階段都稱為思想的話,要去追問那樣的意識的起源或始源是怎樣的面貌並不容易。有關自我意識或集團意識被記錄以前是何種樣態,以及對其給予規定的東西,可以舉出以下三項:列島的成立及自然史,考古學的見解,中國史書所描繪的日本。
由於這個列島的人類長久以來不具備文字,因此具有自我意識之人類的形態首先是在與他者—亦即中國大陸—的關係當中,藉由大陸對列島的關注並留下文字(漢字)記載而初發形成的。但是,那種他者的視線本身所成立的根據,是在於自然史之中。在日本至今所建立的文化裡面,與大陸及朝鮮半島之間的地理關係扮演著很大的角色。
列島的形成
從地球誕生至數十億年之間,日後的日本列島尚未形成而仍舊是大陸的一部分。新生代的新第三紀,也就是二千五、六百萬年前,大陸的東邊出現一個裂縫並形成了原日本海。接著,雖然仍舊與大陸是相連的,日本列島的原型開始出現是距今一千萬年前。之後,進入人類誕生的洪積世,造山、火山活動開始活絡起來。冰河時代的中期,琉球群島首先與大陸分離,接著列島從大陸分離開來。接著不斷重複冰期和間冰期,到了二萬年前之最後的沃姆(Wurm)冰期,海平面下降後出現連結大陸與列島間最後的陸橋,並且有人類及動物的移居。之後,在一萬八千年前形成朝鮮海峽,一萬二千年前形成宗古海峽,今天日本列島的雛形大致確定了下來(平朝彥,《日本列島的誕生》)。琉球群島較本州及其他的島嶼更早從大陸分離開來。這一點與琉球群島在現在被稱為日本的境域裡,在自然、語言、文化方面保有文化的獨特性一事息息相關。
這個列島根據板塊構造學說(plate tectonics)是由四個板塊在近海相銜接的地方形成,並且頻繁地遭遇巨大的地震和海嘯。之前的東日本大震災即具有重新回顧這樣的自然史的意義。在列島上孕育成長的思想對自然及人類所關懷的是與如此的自然史具有深遠關聯性的種種,同時對思想史來說亦具有根源性的意義。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自然」一詞的意義,與近代以前的「自然」相異。最早出現在《萬葉集》之源自漢語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中世、特別是親鸞的「自然法爾」,也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那樣的歷史可以說是指,潛藏在今天我們稱為「自然」的對象背後的原理或根據。這一點或許正是近代意外容易地將nature譯成「自然」而接受的理由。自然的概念形塑著日本思想史重要的課題。
另一方面,在列島上展開了舊石器文化以及新石器文化。在新石器文化裡,從考古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獲知繩文文化、彌生文化這些生活的形態。前此有關舊石器時代的認知,以及有關繩文時代的時代開展和社會形態的認知逐漸產生變化。對稻作的開始等問題也提出了新的見解。長久以來,彌生文化被視為稻作的文化,並且是與今天日本的文化直接連繫的同質文化,但現在稻作已被證實可較以前更往上追溯而始於繩文時代。
以「太陽之塔」而聞名的獨特藝術家岡本太郎(一九一一一九九六)曾提倡復興繩文文化的美意識。包括他的南島琉球文化論等,這樣的主張透視了日本的文化起源本身的多樣性,並且打破輕易被視為日本的同質性之類的東西,具有給予均質的日本這類固定的文化觀一定的隔閡及刺激的意義。他者眼中的日本――中國史書及地緣政治學上的地位
在沒有文字紀錄的時期,列島上有什麼樣的意識呢?這方面是與思想及文學的方法位於較遠的位置上。沒有探究無文字文化之完美的方法。從而,除了考古學告訴我們的知識以外,直到五世紀為止不存在文字的這個列島的種種(漢字的使用本身,有稻荷山古墳及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劍、鐵刀銘文等例子),首先是以記載於他者—亦即中國—典籍裡的形式,最早出現在文字化的歷史上。一直到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為止,唯有通過他者的眼光始能窺探自身的起源,這件事是關係至今為止日本的思想文化深層的一大問題。
那麼,出現在中國史書裡的日本是什麼樣子的呢?最早是以「倭」、「倭人」的姿態登場。雖然無法全部概括,但「倭」的稱呼指的是列島及其住民,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才對。就正史來看的話,後漢班固所撰的《漢書.地理志》(七六八六年完成)有「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的敘述,並描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此外,有西元五七年光武帝下賜給倭「印綬」(金印)的記載(《後漢書.東夷傳》)。
在《魏志.倭人傳》(三世紀後半成立)裡,更詳細地對倭的諸國,以及其中的「女王國」(邪馬台國)和女王卑彌呼有長達二千字左右的記載。內容描述三十國「共立」的卑彌呼「事鬼道」,以及倭人的政治、官制、風俗、產物、自然、地理、死後的禮儀,還有生活習慣、社會體制等。如此這般,日本的模樣以及在列島上所展開的文化,一開始是透過他者的眼光來描述的。如同以下將隨時提及的,日本一直以來即自覺地關注擁有先進文明的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或是佛教傳來以後的天竺(印度)。一海相隔的大陸與日本,古代的一段時期或是元寇等除外,鮮少直接對峙。大陸這方在地緣政治學上與其說視列島為支配的對象而抱持著強烈的關注,毋寧說是秉持著對其投以恰如其分的關心這樣的態度。這也可視為將周邊民族置於下位之「華夷思想」的表現,而日本亦屢次派遣使節建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然而,如果將中國史書所描述的日本照單全收的話也有問題。第一,史書的成立年代本身即有先後落差。例如:記載西元五七年光武帝下賜倭國金印一事的《後漢書.東夷傳》成書於五世紀,比起描述三世紀邪馬台國的《魏志》是較晚的作品,記載倭國的史書成立的年代有先後的差距。但是,這些中國史書的紀載不僅關係著邪馬台國所在何處這個問題,還的確隱藏著「何謂倭人?」這個關係著現代我們的自我認識及思想的問題。
再者,在二六六年繼承卑彌呼的壹與(台與)向西晉朝貢這個記載之後(《晉書》),到四一三年倭國與高句麗聯袂向東晉朝貢的記載為止,約一百五十年之間,中國這方沒有關於倭的描述(成謎的四世紀)。相對於此,至今仍存在朝鮮半島的記載(高句麗的「廣開土王碑文」傳達了四世紀倭國的動靜)。在這約一百五十年之間,列島上出現大規模的前方後圓墳,四二一年以降(《宋書》)有所謂倭國五王(讚、珍、濟、興、武。有說法認為「武」是雄略天皇,但這五王的人物推定尚未有定論。)活躍的描述。在某個時期自外部視線大幅脫落,這對日本的自我意像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之後在《舊唐書》裡(十世紀)雖然使用「日本國」這個稱呼,但也舉出使者有倭國之別種而自改稱號的說法、以及日本併吞倭國的說法,而懷疑其說法的真實性(藤堂明保等,《倭國傳》)。
這種他者—亦即古代的大陸—對日本所投以的視線,在江戶時代再次浮上檯面成為思想的問題。儒者松下見林(一六三七一七○三)蒐集並考察了日本在中國史書裡的記載(《異稱日本傳》)。新井白石也因關注古代史而提到史書的記載,其說法並影響了本居宣長等國學的思想。
1「日本」這個境域
自然史及思想史
思想史是由文字化的文本及其讀解而形成的。而日本的思想,指的是以這個列島上固有的語言所生成及展開的思想。不論是個人的意識或集團的意識,如果將包含初發性的意識階段都稱為思想的話,要去追問那樣的意識的起源或始源是怎樣的面貌並不容易。有關自我意識或集團意識被記錄以前是何種樣態,以及對其給予規定的東西,可以舉出以下三項:列島的成立及自然史,考古學的見解,中國史書所描繪的日本。
由於這個列島的人類長久以來不具備文字,因此具有自我意識之人類的形態首先是在與他者—亦即中國大陸—的關係當中,藉由大陸對列島的關注並留下文字(漢字)記載而初發形成的。但是,那種他者的視線本身所成立的根據,是在於自然史之中。在日本至今所建立的文化裡面,與大陸及朝鮮半島之間的地理關係扮演著很大的角色。
列島的形成
從地球誕生至數十億年之間,日後的日本列島尚未形成而仍舊是大陸的一部分。新生代的新第三紀,也就是二千五、六百萬年前,大陸的東邊出現一個裂縫並形成了原日本海。接著,雖然仍舊與大陸是相連的,日本列島的原型開始出現是距今一千萬年前。之後,進入人類誕生的洪積世,造山、火山活動開始活絡起來。冰河時代的中期,琉球群島首先與大陸分離,接著列島從大陸分離開來。接著不斷重複冰期和間冰期,到了二萬年前之最後的沃姆(Wurm)冰期,海平面下降後出現連結大陸與列島間最後的陸橋,並且有人類及動物的移居。之後,在一萬八千年前形成朝鮮海峽,一萬二千年前形成宗古海峽,今天日本列島的雛形大致確定了下來(平朝彥,《日本列島的誕生》)。琉球群島較本州及其他的島嶼更早從大陸分離開來。這一點與琉球群島在現在被稱為日本的境域裡,在自然、語言、文化方面保有文化的獨特性一事息息相關。
這個列島根據板塊構造學說(plate tectonics)是由四個板塊在近海相銜接的地方形成,並且頻繁地遭遇巨大的地震和海嘯。之前的東日本大震災即具有重新回顧這樣的自然史的意義。在列島上孕育成長的思想對自然及人類所關懷的是與如此的自然史具有深遠關聯性的種種,同時對思想史來說亦具有根源性的意義。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自然」一詞的意義,與近代以前的「自然」相異。最早出現在《萬葉集》之源自漢語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中世、特別是親鸞的「自然法爾」,也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那樣的歷史可以說是指,潛藏在今天我們稱為「自然」的對象背後的原理或根據。這一點或許正是近代意外容易地將nature譯成「自然」而接受的理由。自然的概念形塑著日本思想史重要的課題。
另一方面,在列島上展開了舊石器文化以及新石器文化。在新石器文化裡,從考古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獲知繩文文化、彌生文化這些生活的形態。前此有關舊石器時代的認知,以及有關繩文時代的時代開展和社會形態的認知逐漸產生變化。對稻作的開始等問題也提出了新的見解。長久以來,彌生文化被視為稻作的文化,並且是與今天日本的文化直接連繫的同質文化,但現在稻作已被證實可較以前更往上追溯而始於繩文時代。
以「太陽之塔」而聞名的獨特藝術家岡本太郎(一九一一一九九六)曾提倡復興繩文文化的美意識。包括他的南島琉球文化論等,這樣的主張透視了日本的文化起源本身的多樣性,並且打破輕易被視為日本的同質性之類的東西,具有給予均質的日本這類固定的文化觀一定的隔閡及刺激的意義。他者眼中的日本――中國史書及地緣政治學上的地位
在沒有文字紀錄的時期,列島上有什麼樣的意識呢?這方面是與思想及文學的方法位於較遠的位置上。沒有探究無文字文化之完美的方法。從而,除了考古學告訴我們的知識以外,直到五世紀為止不存在文字的這個列島的種種(漢字的使用本身,有稻荷山古墳及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劍、鐵刀銘文等例子),首先是以記載於他者—亦即中國—典籍裡的形式,最早出現在文字化的歷史上。一直到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為止,唯有通過他者的眼光始能窺探自身的起源,這件事是關係至今為止日本的思想文化深層的一大問題。
那麼,出現在中國史書裡的日本是什麼樣子的呢?最早是以「倭」、「倭人」的姿態登場。雖然無法全部概括,但「倭」的稱呼指的是列島及其住民,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才對。就正史來看的話,後漢班固所撰的《漢書.地理志》(七六八六年完成)有「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的敘述,並描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此外,有西元五七年光武帝下賜給倭「印綬」(金印)的記載(《後漢書.東夷傳》)。
在《魏志.倭人傳》(三世紀後半成立)裡,更詳細地對倭的諸國,以及其中的「女王國」(邪馬台國)和女王卑彌呼有長達二千字左右的記載。內容描述三十國「共立」的卑彌呼「事鬼道」,以及倭人的政治、官制、風俗、產物、自然、地理、死後的禮儀,還有生活習慣、社會體制等。如此這般,日本的模樣以及在列島上所展開的文化,一開始是透過他者的眼光來描述的。如同以下將隨時提及的,日本一直以來即自覺地關注擁有先進文明的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或是佛教傳來以後的天竺(印度)。一海相隔的大陸與日本,古代的一段時期或是元寇等除外,鮮少直接對峙。大陸這方在地緣政治學上與其說視列島為支配的對象而抱持著強烈的關注,毋寧說是秉持著對其投以恰如其分的關心這樣的態度。這也可視為將周邊民族置於下位之「華夷思想」的表現,而日本亦屢次派遣使節建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然而,如果將中國史書所描述的日本照單全收的話也有問題。第一,史書的成立年代本身即有先後落差。例如:記載西元五七年光武帝下賜倭國金印一事的《後漢書.東夷傳》成書於五世紀,比起描述三世紀邪馬台國的《魏志》是較晚的作品,記載倭國的史書成立的年代有先後的差距。但是,這些中國史書的紀載不僅關係著邪馬台國所在何處這個問題,還的確隱藏著「何謂倭人?」這個關係著現代我們的自我認識及思想的問題。
再者,在二六六年繼承卑彌呼的壹與(台與)向西晉朝貢這個記載之後(《晉書》),到四一三年倭國與高句麗聯袂向東晉朝貢的記載為止,約一百五十年之間,中國這方沒有關於倭的描述(成謎的四世紀)。相對於此,至今仍存在朝鮮半島的記載(高句麗的「廣開土王碑文」傳達了四世紀倭國的動靜)。在這約一百五十年之間,列島上出現大規模的前方後圓墳,四二一年以降(《宋書》)有所謂倭國五王(讚、珍、濟、興、武。有說法認為「武」是雄略天皇,但這五王的人物推定尚未有定論。)活躍的描述。在某個時期自外部視線大幅脫落,這對日本的自我意像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之後在《舊唐書》裡(十世紀)雖然使用「日本國」這個稱呼,但也舉出使者有倭國之別種而自改稱號的說法、以及日本併吞倭國的說法,而懷疑其說法的真實性(藤堂明保等,《倭國傳》)。
這種他者—亦即古代的大陸—對日本所投以的視線,在江戶時代再次浮上檯面成為思想的問題。儒者松下見林(一六三七一七○三)蒐集並考察了日本在中國史書裡的記載(《異稱日本傳》)。新井白石也因關注古代史而提到史書的記載,其說法並影響了本居宣長等國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