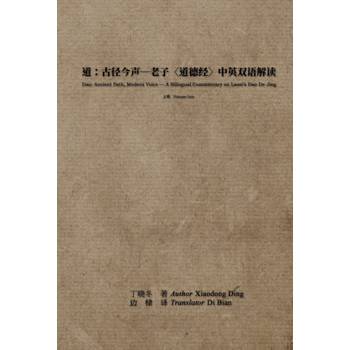第1章 觀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解字說文】
“道可道,非常道。”一句,歷來解讀紛呈,我提出區別於傳統的詮釋為:第一個“道”為名詞,指宇宙之本原、萬有之根理,即所謂“真理”;第二個“道”為動詞,意為踐行、言說、表達之意。此句旨在揭示:凡可行之道,皆為“非常之道”,即特別的,唯一的道。同理,“名可名,非常名”一句中,首“名”為名詞,指“道”的稱謂或名狀;次“名”為動詞,意為命名、界定、言說。此言指出:可被命名的,與道論相同,皆是”非常之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兩句的解釋:常無,欲以觀其妙:看見它的奇妙,常因為未能體悟其“道”奧妙本源之故。徼:音jiào,門徑,通往內理、萬象之始。引申為通向萬象之始的界域。常有,欲以觀其徼:如果要想找到奇妙與變化之“道”的來源,就是“常有”, 即瞭解和通達了其妙處生成與變化的門徑。此等義理,非王弼與蘇轍獨論。戰國末期的《韓非子•解老》《喻老》諸篇,亦嘗作詮釋。韓非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又曰:“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其明確區分“道”與“物”,以“所然”之自然為旨歸,揭示“道”既超形而上,又內涵於事物之中,兼具形上與形下、超越與內在的二重屬性。
北宋蘇轍亦曾注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後世則對此論述一脈相承,皆強調“道”之不可名、不可言、不可常的玄妙本質。然而,對“非常恒之道”與“非常恒之名”的傳統理解,實有值得反思之處。若謂“可道者非恒道” ,則所有言說之道皆不足道,此命題本身即陷入悖論:若 “此言” 為真,則 “此言” 本身亦不可道,邏輯自陷其身。此為語言自指悖論之一例,亦使 “不可說之道” 的命題難以自洽。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兩句,古今學者對此章斷句亦有異見。除主流解釋外,尚有嘗試將句式斷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雖此類讀法非經傳正宗,然其邏輯嘗試與哲思結構,亦別具探討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經》版本眾多,傳抄遞嬗、方言演變、書手誤增漏簡,皆使其文本源流複雜。然即便在不同的古本中, “道可道,非常道。” 的句式仍屬通行,雖有字序微異,卻不離其大義。此廣泛共識,正反映出傳統對 “道” 的不可言、不可執、不可名哲學謬誤的體認與尊崇。
【白話釋義】
第1章 觀妙
道可道,道在踐行中形成,道之所以稱為“道”,正在於其可開發性與可實踐性。它在踐行中顯現、流轉不居,故稱“非常之道”。 名,是人為所賦,定於一物,止於一形,故謂之“非常之名”。“無” ,為孕育萬象之始,天地由 “無” 而生;“有” ,在道踐行之後而顯現,萬物以 “有” 為母。道未明時,萬象茫然,所見之象,稱為“妙觀”;道既通達,心眼雙明,所觀之相,謂之“徼觀”。“有” 與 “無” ,乃道之通途,可視為道存在之前與得道之後的兩種觀象。所觀雖同,道之始末不同,故觀象亦異。“有” 與 “無” ,皆深且玄;其深奧之處,亦可交融會通。其奧無窮,探索不盡,是通達萬物之妙的門戶,亦為通向真理的無盡之路。
【哲學闡釋】
“道” 必須在實踐中才能顯現;它的本質可以被發掘、被感知、被描述。但正因為它不斷變化,因時因人而異,所以稱之為 “非常之道” 。同樣, “名” 是人為賦予的符號,用來標識事物,它也隨著認知與語境的變化而改變,因此被稱為 “非常之名” 。
“無” 代表世界尚未顯現之前的狀態,是宇宙的起點; “有” 則是從 “無” 中顯現出的種種存在。我們通過實踐 “道” ,從 “無” 走向 “有” ,也在這個過程中體會 “道” 的真意。未得其道時,人們面對世界感到神秘莫測,只能用直覺去 “妙觀” ; 得道之後,便可順理而行,從顯象中觀察其所指,即 “徼觀” 。所謂 “妙” ,是自然本有的奧妙; “徼” ,則是理解之後的主動追尋。得與不得之間,是一個從感性到理性、從現象通達本質的過程。正是在 “有” 與 “無” 的流轉交替之間,我們逐步走近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
“有”與“無”並非彼此對立,而是“道”在不同層面的呈現。“無”是未成,是潛能;“有”是已顯,是實現。兩者相輔相成,互為鏡像。老子在這一章中,通過“道”與“名”這兩個核心概念,為其宇宙論奠定了基礎。他告訴我們:“道”不是一條固定的軌跡,而是在行走中被開闢出來的;“名”也並非某物的絕對定義,而是對事物的階段性指稱。人人心中有“道”,萬象之中有“名”,因此道為非常之道,名亦非常之名。如果沒有實踐,“道”便無法成立;如果沒有表達,“名”也無所附著。實踐與表達,是人通達“道”的兩種方式。“無”與“有”這兩個概念,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的兩個端點:“無”是源頭,是隱性的原初;“有”是顯現,是事物成形之後的狀態。兩者交替作用,共同構成宇宙萬象的生成機制。正如俗話所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熱鬧是表像,是“妙”;門道是規律,是“徼”。真正的智慧,在於能在熱鬧中看出門道,並在門道中重新理解熱鬧。
那麼,有了“道可道,非常道”,是否意味著還有一個“常道”的存在?這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所謂“常道” ,或許並不是真實存在的某種實體,而是人類對真理與秩序的一種理性投射,是設定的抽象標準。它類似于柏拉圖的 “理念” ,或海德格爾所說的 “存在的意義” ,但不是一個可以直接抵達的目標。尼采之所以批判 “永恆真理” 的觀念,正是試圖拆解這座人類自造的精神神壇。
我們從自然的一些現象中,也可以得到啟發:比如皮亞諾曲線在一維中填滿二維空間,希爾伯特曲線通過無限折返逼近整體,科赫雪花曲線則構造出一個1.26維的奇異圖形。這些看似違反直覺的“維度跳躍” ,其實突破了我們固有認知中的 “有” 與 “無” 的界限。道,也正是通過這種生成與突破的過程而被顯現出來。
尼采說:“你有你的道路,我有我的道路。至於唯一的和正確的道路,是不存在的。”這句話就像是在和“常道”道別。而紀伯倫也寫道:“你是弓,孩子是你射出的箭;弓箭手知道,箭從不沿相同的軌跡射向靶心。”每個人的生命之路,都是獨一無二的“非常之道”。
“常道” 更多是一種文化和宗教中建構出來的理想形式,而 “非常道” 才是個體真實的經歷、不斷選擇並親自走出的路徑。我們或許都曾被 “常道” 的幻象吸引,以為某種永恆不變的真理確實存在。但老子提醒我們,一切 “道” 都是相對的、流動的,是在實踐中逐步顯現出來的結果。
這一章的深刻之處在於,它不僅觸及本體論(道是萬物之源),也涉及實踐論(道如何在行為中體現),並進一步引導我們進入認識論(我們如何理解道)。因此,這不僅是對宇宙之道的描述,更是對人生之路的啟蒙。在現實層面看,“道”可以被理解為自然規律,也可以理解為個體生命的方向選擇。它不是上天預設的劇本,而是我們每一個人親自走出來的路。李白有:“道由白雲外,人從青嶂中。”泰戈爾也有:“霧像愛情,雲雨山中,孕育美麗無限。” 都說的是這個意思。
比如學騎自行車,一開始戰戰兢兢,後來慢慢熟練,最終不用思考,身體便能自然完成動作。這正是“技近乎道” 的體現。藝術、科學、修行皆如此。 當行為背後的規律逐漸內化成一種無意識的流動時,我們便進入 “無為而無不為” 的境界。順其自然,卻又無所不能。老子說 “道可道” ,這個 “道” 不僅是指可言說的語言之道,更應理解為開闢道路。一切真正的 “道” ,都不是預設的,而是在行走中不斷生成的。人類的歷史如此,個體的人生亦然。 我曾在YouTube上看過一位美籍道士的訪談,在武當山修行多年,道號“三豐派第十六代傳人”。他談到了“道” 的非常性。那一刻讓我意識到:無論文化背景如何,每一個內心尋道的人,終將在某處相遇。這是一種穿越語言與歷史的共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這不只是一句哲學命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表達思想,如何選擇人生的路徑。
“道” 並不是空洞的形而上之談,而是腳下真實可行的道路。如果我們以此來理解 “道可道” ,它的意義就不再遙遠。道之所以為 “道” ,正在於它可以被開闢出來、被實踐、被領悟、被昇華。它不是封閉的、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一條在行走的實踐中不斷生成、不斷展開的路。
紀伯倫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詩:“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穌就會與基督的耶穌在黎巴嫩山中的花園裡見面。長談之後,每次拿撒勒的耶穌向基督的耶穌道別時都說:‘我的朋友,我擔心我們永遠,永遠無法達成共識。’” 拿撒勒的耶穌,是那個行走在世間的真實之人;而基督的耶穌,則是後人賦予其上的符號與教義。這,正是“非常道”與“常道”之間的張力:活著的“道”,常常被凝固為教條;個體的經驗,被歸入集體的定義。而哲人的任務,正是重新點燃“非常道”的火焰,讓它再次照亮我們腳下的道路。
泰戈爾寫道:“上天啊,敞開的,是你獨有的王國,獨有的,是我心靈的小窗,我的心只在小窗與你相會。”如果這扇“心靈之窗”關閉了,即使真理近在眼前,也無從看見。
蘇格拉底以否定性的發問接近真知,尼採用火焰焚毀絕對真理的幻影。真理,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被安放在某處的“實體”,而是我們在理解、追問與前行中不斷生成的過程。所謂 “玄之又玄” ,不是玄虛空洞,而是不斷深入、持續展開的可能性。 “非常道” 不是偶發的例外,而正是生命與世界的常態。兩千多年前,老子寫下 “道可道,非常道” ,表面看似含糊其辭,實則一語破萬法。他所說的,不僅是哲學的根本,更是人生的本真。
正是:
有無相生本非二,虛實交融乃為道。名非常名遮真象,常非常道悟玄奧。
道無定式步無聲,踐履方知理自成。有無交映觀玄妙,非常之處見真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解字說文】
“道可道,非常道。”一句,歷來解讀紛呈,我提出區別於傳統的詮釋為:第一個“道”為名詞,指宇宙之本原、萬有之根理,即所謂“真理”;第二個“道”為動詞,意為踐行、言說、表達之意。此句旨在揭示:凡可行之道,皆為“非常之道”,即特別的,唯一的道。同理,“名可名,非常名”一句中,首“名”為名詞,指“道”的稱謂或名狀;次“名”為動詞,意為命名、界定、言說。此言指出:可被命名的,與道論相同,皆是”非常之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兩句的解釋:常無,欲以觀其妙:看見它的奇妙,常因為未能體悟其“道”奧妙本源之故。徼:音jiào,門徑,通往內理、萬象之始。引申為通向萬象之始的界域。常有,欲以觀其徼:如果要想找到奇妙與變化之“道”的來源,就是“常有”, 即瞭解和通達了其妙處生成與變化的門徑。此等義理,非王弼與蘇轍獨論。戰國末期的《韓非子•解老》《喻老》諸篇,亦嘗作詮釋。韓非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又曰:“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其明確區分“道”與“物”,以“所然”之自然為旨歸,揭示“道”既超形而上,又內涵於事物之中,兼具形上與形下、超越與內在的二重屬性。
北宋蘇轍亦曾注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後世則對此論述一脈相承,皆強調“道”之不可名、不可言、不可常的玄妙本質。然而,對“非常恒之道”與“非常恒之名”的傳統理解,實有值得反思之處。若謂“可道者非恒道” ,則所有言說之道皆不足道,此命題本身即陷入悖論:若 “此言” 為真,則 “此言” 本身亦不可道,邏輯自陷其身。此為語言自指悖論之一例,亦使 “不可說之道” 的命題難以自洽。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兩句,古今學者對此章斷句亦有異見。除主流解釋外,尚有嘗試將句式斷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雖此類讀法非經傳正宗,然其邏輯嘗試與哲思結構,亦別具探討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經》版本眾多,傳抄遞嬗、方言演變、書手誤增漏簡,皆使其文本源流複雜。然即便在不同的古本中, “道可道,非常道。” 的句式仍屬通行,雖有字序微異,卻不離其大義。此廣泛共識,正反映出傳統對 “道” 的不可言、不可執、不可名哲學謬誤的體認與尊崇。
【白話釋義】
第1章 觀妙
道可道,道在踐行中形成,道之所以稱為“道”,正在於其可開發性與可實踐性。它在踐行中顯現、流轉不居,故稱“非常之道”。 名,是人為所賦,定於一物,止於一形,故謂之“非常之名”。“無” ,為孕育萬象之始,天地由 “無” 而生;“有” ,在道踐行之後而顯現,萬物以 “有” 為母。道未明時,萬象茫然,所見之象,稱為“妙觀”;道既通達,心眼雙明,所觀之相,謂之“徼觀”。“有” 與 “無” ,乃道之通途,可視為道存在之前與得道之後的兩種觀象。所觀雖同,道之始末不同,故觀象亦異。“有” 與 “無” ,皆深且玄;其深奧之處,亦可交融會通。其奧無窮,探索不盡,是通達萬物之妙的門戶,亦為通向真理的無盡之路。
【哲學闡釋】
“道” 必須在實踐中才能顯現;它的本質可以被發掘、被感知、被描述。但正因為它不斷變化,因時因人而異,所以稱之為 “非常之道” 。同樣, “名” 是人為賦予的符號,用來標識事物,它也隨著認知與語境的變化而改變,因此被稱為 “非常之名” 。
“無” 代表世界尚未顯現之前的狀態,是宇宙的起點; “有” 則是從 “無” 中顯現出的種種存在。我們通過實踐 “道” ,從 “無” 走向 “有” ,也在這個過程中體會 “道” 的真意。未得其道時,人們面對世界感到神秘莫測,只能用直覺去 “妙觀” ; 得道之後,便可順理而行,從顯象中觀察其所指,即 “徼觀” 。所謂 “妙” ,是自然本有的奧妙; “徼” ,則是理解之後的主動追尋。得與不得之間,是一個從感性到理性、從現象通達本質的過程。正是在 “有” 與 “無” 的流轉交替之間,我們逐步走近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
“有”與“無”並非彼此對立,而是“道”在不同層面的呈現。“無”是未成,是潛能;“有”是已顯,是實現。兩者相輔相成,互為鏡像。老子在這一章中,通過“道”與“名”這兩個核心概念,為其宇宙論奠定了基礎。他告訴我們:“道”不是一條固定的軌跡,而是在行走中被開闢出來的;“名”也並非某物的絕對定義,而是對事物的階段性指稱。人人心中有“道”,萬象之中有“名”,因此道為非常之道,名亦非常之名。如果沒有實踐,“道”便無法成立;如果沒有表達,“名”也無所附著。實踐與表達,是人通達“道”的兩種方式。“無”與“有”這兩個概念,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的兩個端點:“無”是源頭,是隱性的原初;“有”是顯現,是事物成形之後的狀態。兩者交替作用,共同構成宇宙萬象的生成機制。正如俗話所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熱鬧是表像,是“妙”;門道是規律,是“徼”。真正的智慧,在於能在熱鬧中看出門道,並在門道中重新理解熱鬧。
那麼,有了“道可道,非常道”,是否意味著還有一個“常道”的存在?這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所謂“常道” ,或許並不是真實存在的某種實體,而是人類對真理與秩序的一種理性投射,是設定的抽象標準。它類似于柏拉圖的 “理念” ,或海德格爾所說的 “存在的意義” ,但不是一個可以直接抵達的目標。尼采之所以批判 “永恆真理” 的觀念,正是試圖拆解這座人類自造的精神神壇。
我們從自然的一些現象中,也可以得到啟發:比如皮亞諾曲線在一維中填滿二維空間,希爾伯特曲線通過無限折返逼近整體,科赫雪花曲線則構造出一個1.26維的奇異圖形。這些看似違反直覺的“維度跳躍” ,其實突破了我們固有認知中的 “有” 與 “無” 的界限。道,也正是通過這種生成與突破的過程而被顯現出來。
尼采說:“你有你的道路,我有我的道路。至於唯一的和正確的道路,是不存在的。”這句話就像是在和“常道”道別。而紀伯倫也寫道:“你是弓,孩子是你射出的箭;弓箭手知道,箭從不沿相同的軌跡射向靶心。”每個人的生命之路,都是獨一無二的“非常之道”。
“常道” 更多是一種文化和宗教中建構出來的理想形式,而 “非常道” 才是個體真實的經歷、不斷選擇並親自走出的路徑。我們或許都曾被 “常道” 的幻象吸引,以為某種永恆不變的真理確實存在。但老子提醒我們,一切 “道” 都是相對的、流動的,是在實踐中逐步顯現出來的結果。
這一章的深刻之處在於,它不僅觸及本體論(道是萬物之源),也涉及實踐論(道如何在行為中體現),並進一步引導我們進入認識論(我們如何理解道)。因此,這不僅是對宇宙之道的描述,更是對人生之路的啟蒙。在現實層面看,“道”可以被理解為自然規律,也可以理解為個體生命的方向選擇。它不是上天預設的劇本,而是我們每一個人親自走出來的路。李白有:“道由白雲外,人從青嶂中。”泰戈爾也有:“霧像愛情,雲雨山中,孕育美麗無限。” 都說的是這個意思。
比如學騎自行車,一開始戰戰兢兢,後來慢慢熟練,最終不用思考,身體便能自然完成動作。這正是“技近乎道” 的體現。藝術、科學、修行皆如此。 當行為背後的規律逐漸內化成一種無意識的流動時,我們便進入 “無為而無不為” 的境界。順其自然,卻又無所不能。老子說 “道可道” ,這個 “道” 不僅是指可言說的語言之道,更應理解為開闢道路。一切真正的 “道” ,都不是預設的,而是在行走中不斷生成的。人類的歷史如此,個體的人生亦然。 我曾在YouTube上看過一位美籍道士的訪談,在武當山修行多年,道號“三豐派第十六代傳人”。他談到了“道” 的非常性。那一刻讓我意識到:無論文化背景如何,每一個內心尋道的人,終將在某處相遇。這是一種穿越語言與歷史的共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這不只是一句哲學命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表達思想,如何選擇人生的路徑。
“道” 並不是空洞的形而上之談,而是腳下真實可行的道路。如果我們以此來理解 “道可道” ,它的意義就不再遙遠。道之所以為 “道” ,正在於它可以被開闢出來、被實踐、被領悟、被昇華。它不是封閉的、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一條在行走的實踐中不斷生成、不斷展開的路。
紀伯倫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詩:“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穌就會與基督的耶穌在黎巴嫩山中的花園裡見面。長談之後,每次拿撒勒的耶穌向基督的耶穌道別時都說:‘我的朋友,我擔心我們永遠,永遠無法達成共識。’” 拿撒勒的耶穌,是那個行走在世間的真實之人;而基督的耶穌,則是後人賦予其上的符號與教義。這,正是“非常道”與“常道”之間的張力:活著的“道”,常常被凝固為教條;個體的經驗,被歸入集體的定義。而哲人的任務,正是重新點燃“非常道”的火焰,讓它再次照亮我們腳下的道路。
泰戈爾寫道:“上天啊,敞開的,是你獨有的王國,獨有的,是我心靈的小窗,我的心只在小窗與你相會。”如果這扇“心靈之窗”關閉了,即使真理近在眼前,也無從看見。
蘇格拉底以否定性的發問接近真知,尼採用火焰焚毀絕對真理的幻影。真理,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被安放在某處的“實體”,而是我們在理解、追問與前行中不斷生成的過程。所謂 “玄之又玄” ,不是玄虛空洞,而是不斷深入、持續展開的可能性。 “非常道” 不是偶發的例外,而正是生命與世界的常態。兩千多年前,老子寫下 “道可道,非常道” ,表面看似含糊其辭,實則一語破萬法。他所說的,不僅是哲學的根本,更是人生的本真。
正是:
有無相生本非二,虛實交融乃為道。名非常名遮真象,常非常道悟玄奧。
道無定式步無聲,踐履方知理自成。有無交映觀玄妙,非常之處見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