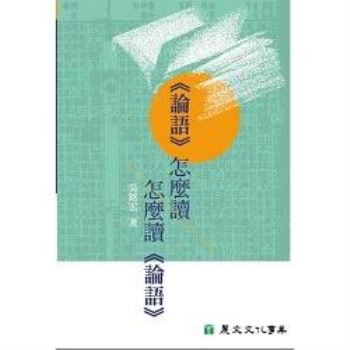啟蒙篇(儒家思想精義的引導啟發)
一、《論語》很難懂嗎?
年輕人普遍不愛讀《論語》,因為《論語》這本書,從大處看,沒系統;從小處看,沒精神。全書只是一段一段的話頭,話與話之間,好像也沒個關聯性,再加上又沒有故事性,難怪大家興趣缺缺。
其實,《論語》這本書比一般的書好讀,因為一般的書,必須各章節的內容你都了解之後,才算讀懂一本書,也纔能起作用。《論語》卻不必如此,了解一則,懂得其中的道理,在生活上照著去做,就能起作用。譬如《論語》首篇首章記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一則,分開來看,好像在講三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它主要在講「終身學習」的樂趣。而當一個人能完全掌握這種「自得」之樂,別人是否懂得他的才華,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
其次,在生活上,如果你不但能「學」,還能時「習」之,最終,那種所謂的「樂趣」,自然就會產生。在「樂趣」未產生之前,學習上的辛苦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一旦工夫做得徹底,辛苦慢慢就會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喜悅。換言之,工夫成熟也就「苦盡甘來」,讀書到此,可算是「入門」了。
入門之後,若有同好同道,前來一起論學,那麼學習上所產生的樂趣,鐵定會有相乘的效果,因為它會產生共鳴。生命裡,學習的樂趣時時湧現;生活當中,又充滿自得之樂。試問:別人能不能欣賞你?能不能重用你?你還會太在意嗎?
二、點亮生命中的光彩!
孔子一生的學問,重點就在一個「仁」字。《中庸》第20 章: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要依據,亦即身而為人,所言所行能符合「仁」這個標準,才算「成其為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仁」代表的就是「人性」。發揚仁道,就是發揚人性的光輝。《禮記‧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就是點亮我們生命中本然就具有的光采,而什麼是人類生命的光采?就是「互助」呀!你幫助我,我幫助你;你成就我,我成就你。你看不清前路,我為你指點,為你照亮;你挨餓受凍,我提供衣物熱食,給你溫暖――這就是人性的光和熱。有了人性的光和熱,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才有意義,才有價值。否則在「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之下,人類即便擁有極高度的物質文明,這個物種在宇宙中又有什麼特殊的存在價值呢?
孔子在《論語‧八佾篇》中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在〈陽貨篇〉中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在在都說明了,禮樂的真實意義,從來就不在代表著物質的禮器與樂器上。人類能確實發揚人性的光輝,禮樂也纔能跟著有意義、有價值。「禮樂」都已然如此,人類創造的「文明」,又何嘗不然?
三、禮怎麼來的?
《論語》末篇末章記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泰伯篇》第2章記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根據上述這兩則,「禮」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然則,「禮」何所從來?周公制禮作樂,又是何所本?
《中庸》第20 章: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禮」是本於人性、人情創造發展出來的,仁就是「人性」,義就是「人情」,「仁、義」指的就是人情事理之必然與得當者。「義者,宜也。」「宜」就是恰到好處,既沒有「太過」,也沒有「不及」,也就是「中庸之道」。
足見周公制禮作樂,絕對不是憑空創造發明的,也絕不是想些點子來整大家。禮樂的存在,一定是因應人性、人情的實際需要所產生的。而時代的需求有所改變之時,禮的規範也就跟著有所斟酌損益。
以葬禮的沿革為例――上古之人,穴居野處,人死之後,屍腐難聞,往往將屍體拖到野外。某天某人從野外打獵歸來,見到親人的遺體,遭受野獸蚊蠅的滋擾,心中不忍,遂用枝葉與石塊將之掩埋,這便是葬禮的起源。其後,有人發現枝葉、石塊,仍不足以阻擋巨獸之侵擾,遂又演變成挖土埋葬,這是土葬的起源。日後,又有人常思念亡故的親人,欲往憑弔,於是高土為墳、植樹為記、墓碑為誌等等沿革,遂因應實際的需要,一一產生。
後世之人,不了解禮的作用與沿革,乃視禮的儀節繁瑣累人,簡直是厚誣了古人!四、讓善良的本心重起作用!
孔子的學問,只用一個字來說明,就是「仁」字;若是分開來講,也可以是「忠」和「恕」兩個字。
《論語‧里仁篇》記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熹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無論「忠」或「恕」,有關道德的事,都是自己的事,也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謂的「操之在己,盡其在我」。
道德的特性,就是內在於你生命中本然就具有的,它是「與生俱來」的,只要生而為人,就一定擁有這樣的特性,也就是孟子所謂的「善性」。試問:「仁、義、禮、智」四個善端,誰不具備?
從現實觀點看,有些惡人,惡行惡狀,似乎不具絲毫善性。其實,他不是不具備,也不是沒有,只是暫時失去了作用而已。他的善性之所以會暫時失去作用,主要是因為他受到太多物慾的蒙蔽。如果能夠把蒙蔽善良本心的物慾給排除掉,善性自然就能明朗呈現,就能重新再起作用。換言之,他的人性也就恢復了。
在物慾橫流、科技掛帥的今日,我們要如何來充實人類文明的內涵呢?重點已然不再是持續向外探索,追求太空科技的發展,而是到了該重視內省的時候了。如何把我們善良的本心找回來,使它再起作用,並喚起人類普遍道德意識的覺醒,纔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要的課題。
一、《論語》很難懂嗎?
年輕人普遍不愛讀《論語》,因為《論語》這本書,從大處看,沒系統;從小處看,沒精神。全書只是一段一段的話頭,話與話之間,好像也沒個關聯性,再加上又沒有故事性,難怪大家興趣缺缺。
其實,《論語》這本書比一般的書好讀,因為一般的書,必須各章節的內容你都了解之後,才算讀懂一本書,也纔能起作用。《論語》卻不必如此,了解一則,懂得其中的道理,在生活上照著去做,就能起作用。譬如《論語》首篇首章記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一則,分開來看,好像在講三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它主要在講「終身學習」的樂趣。而當一個人能完全掌握這種「自得」之樂,別人是否懂得他的才華,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
其次,在生活上,如果你不但能「學」,還能時「習」之,最終,那種所謂的「樂趣」,自然就會產生。在「樂趣」未產生之前,學習上的辛苦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一旦工夫做得徹底,辛苦慢慢就會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喜悅。換言之,工夫成熟也就「苦盡甘來」,讀書到此,可算是「入門」了。
入門之後,若有同好同道,前來一起論學,那麼學習上所產生的樂趣,鐵定會有相乘的效果,因為它會產生共鳴。生命裡,學習的樂趣時時湧現;生活當中,又充滿自得之樂。試問:別人能不能欣賞你?能不能重用你?你還會太在意嗎?
二、點亮生命中的光彩!
孔子一生的學問,重點就在一個「仁」字。《中庸》第20 章: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要依據,亦即身而為人,所言所行能符合「仁」這個標準,才算「成其為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仁」代表的就是「人性」。發揚仁道,就是發揚人性的光輝。《禮記‧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就是點亮我們生命中本然就具有的光采,而什麼是人類生命的光采?就是「互助」呀!你幫助我,我幫助你;你成就我,我成就你。你看不清前路,我為你指點,為你照亮;你挨餓受凍,我提供衣物熱食,給你溫暖――這就是人性的光和熱。有了人性的光和熱,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才有意義,才有價值。否則在「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之下,人類即便擁有極高度的物質文明,這個物種在宇宙中又有什麼特殊的存在價值呢?
孔子在《論語‧八佾篇》中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在〈陽貨篇〉中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在在都說明了,禮樂的真實意義,從來就不在代表著物質的禮器與樂器上。人類能確實發揚人性的光輝,禮樂也纔能跟著有意義、有價值。「禮樂」都已然如此,人類創造的「文明」,又何嘗不然?
三、禮怎麼來的?
《論語》末篇末章記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泰伯篇》第2章記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根據上述這兩則,「禮」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然則,「禮」何所從來?周公制禮作樂,又是何所本?
《中庸》第20 章: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禮」是本於人性、人情創造發展出來的,仁就是「人性」,義就是「人情」,「仁、義」指的就是人情事理之必然與得當者。「義者,宜也。」「宜」就是恰到好處,既沒有「太過」,也沒有「不及」,也就是「中庸之道」。
足見周公制禮作樂,絕對不是憑空創造發明的,也絕不是想些點子來整大家。禮樂的存在,一定是因應人性、人情的實際需要所產生的。而時代的需求有所改變之時,禮的規範也就跟著有所斟酌損益。
以葬禮的沿革為例――上古之人,穴居野處,人死之後,屍腐難聞,往往將屍體拖到野外。某天某人從野外打獵歸來,見到親人的遺體,遭受野獸蚊蠅的滋擾,心中不忍,遂用枝葉與石塊將之掩埋,這便是葬禮的起源。其後,有人發現枝葉、石塊,仍不足以阻擋巨獸之侵擾,遂又演變成挖土埋葬,這是土葬的起源。日後,又有人常思念亡故的親人,欲往憑弔,於是高土為墳、植樹為記、墓碑為誌等等沿革,遂因應實際的需要,一一產生。
後世之人,不了解禮的作用與沿革,乃視禮的儀節繁瑣累人,簡直是厚誣了古人!四、讓善良的本心重起作用!
孔子的學問,只用一個字來說明,就是「仁」字;若是分開來講,也可以是「忠」和「恕」兩個字。
《論語‧里仁篇》記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熹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無論「忠」或「恕」,有關道德的事,都是自己的事,也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謂的「操之在己,盡其在我」。
道德的特性,就是內在於你生命中本然就具有的,它是「與生俱來」的,只要生而為人,就一定擁有這樣的特性,也就是孟子所謂的「善性」。試問:「仁、義、禮、智」四個善端,誰不具備?
從現實觀點看,有些惡人,惡行惡狀,似乎不具絲毫善性。其實,他不是不具備,也不是沒有,只是暫時失去了作用而已。他的善性之所以會暫時失去作用,主要是因為他受到太多物慾的蒙蔽。如果能夠把蒙蔽善良本心的物慾給排除掉,善性自然就能明朗呈現,就能重新再起作用。換言之,他的人性也就恢復了。
在物慾橫流、科技掛帥的今日,我們要如何來充實人類文明的內涵呢?重點已然不再是持續向外探索,追求太空科技的發展,而是到了該重視內省的時候了。如何把我們善良的本心找回來,使它再起作用,並喚起人類普遍道德意識的覺醒,纔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要的課題。